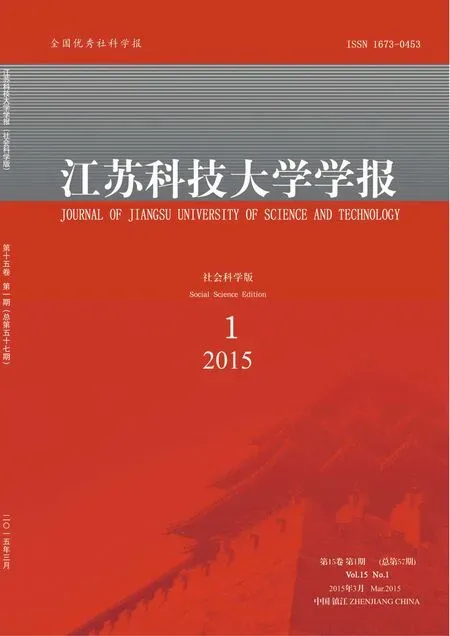“大美配天而华不作”
——王弼的自然观与魏晋美学
2015-04-14李红丽
李红丽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大美配天而华不作”
——王弼的自然观与魏晋美学
李红丽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王弼的“大美配天而华不作”是对老庄“美在自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种自然观建立在“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基础之上,并从总体上表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重视自然、崇尚朴拙的审美风尚。这种审美风尚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自然天放的人格美、怡情畅神的自然美和自然天成的艺术美。
魏晋;自然观;王弼;玄学;美学
一、 “大美配天而华不作”的自然观
(一) 老子哲学的自然观
中国人认为美的本源在自然,这很大程度上是从先秦道家的理论中总结出来的。“自然”一词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最早见于《老子》。《老子》中的“自然”,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总体上,它代表哲学的最高原则,此“自然”相当于本体论意义上的“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163这里的“道”是世界的最后根据或源头,代表着规律和原则,其本身虽然贯通着天、地、人三者,但它遵循着“自然”。“自然”最基本的意义是“自然而然”,即本然、天然。老子说:“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1]261这里的“自然”就是自然而然的意思,指的是事物的本性。他认为事物按其“所以然”而存在就是美,美在自然、本真。“自然”是“道”的规定者,“道”的本质特征是“自然而然”,道与自然合二为一,“道”即“自然”,以“道”为本体也即以“自然”为本体。
第二,从方法论意义上讲,“自然”是指天地依照“道”的自然无为去存在,以及人遵循“道”的自然无为去办事。老子讲“无为”,“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1]261。“道”在生成、养育万物的过程中遵循着“自然”的规律,“道”使自然顺其本性去存在、去发展,这就是“道”的“无为”,即任物的自然之性,不妄为。这种“为”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即“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1]130,无为而功成。这个意义上的“自然”,也可表达为“自化”,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1]284
总之,《老子》中的“自然”,从本体论角度上讲相当于“道”,是宇宙创化之总规律、总原则,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任事物之本性自然而然去发展。同时,“道”依据“自然”而创化万物,人也应当效法“道”之自然无为去行事,天道无为,人道亦无为。
(二) 庄子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哲学中的“自然”思想,提出“大美”这一美学范畴,认为美在于“无为”。《庄子》一书中多处谈及这种思想,尤其在《知北游》中作了充分的表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2]735庄子首先明确肯定了美存在于“天地”之中。这里说的“天地”首先指自然界,说明庄子肯定了自然界的美。但若要更进一步追问,“天地”即自然界何以有美?在庄子看来,“天地”之所以有“大美”在于它体现了“道”的自然无为的根本特征。其所指的“大美”大在“道”的存在方式,或者说是“道”的形象。“原天地之美”即是追溯、效法“道”之美。而这种追溯、效法的关键在“无为”,也就是尊重事物的本性,让事物处于自然而然的状态。因此,自然无为才是“天地有大美”的根本原因。
在《天道》中,庄子说:“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2]457-458“虚静恬淡,寂寞无为”是万物之本体,同时也是美之本体。所谓“素朴”,就是一切纯任自然的意思,也就是“虚静恬淡,寂寞无为”的表现。因此,若达到了“素朴”,就是达到了美之极致。
老子的自然思想更侧重于“以人合天”,主张人应顺应天道之自然无为,依照客观自然规律办事。而庄子虽然也要求人应效法天道之自然无为,但其终极目的是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在庄子那里,人如果效法天道的“自然无为”,就可以保持住人的自然本性,无拘无束,逍遥自在,达到最大的精神自由,也就达到了“大美”。《庄子》中多次描写到了“真人”“圣人”“神人”的形象,“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镇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2]96。正是因为他们懂得和效法“自然无为”的天道,才获得了至高至美的人生境界。所以说“庄子以自然无为为美,也就是以个体人格的自由的实现为美。这是庄子美学的实质和核心[3]。
(三) 王弼“大美配天而华不作”的自然观
王弼在继承了老子、庄子关于“美在自然”的思想基础之上,提出了“大美配天而华不作”的自然观。
王弼“大美配天而华不作”的思想是建立在他“以无为本”的哲学基础之上的。王弼在注释《老子》的过程中,运用“得意忘象”的玄学方法,建立了一套“以无为本”的玄学体系。在他的哲学中,“无”即是“道”,“道”是宇宙本体,它无形、无声、无味,无法用名言概念来把握。但“道”又不等于空无,不是什么也不存在,而是万物之本。“道”与“物”分别属于“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层面。那么,“道”与“万物”之间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也即“道”如何成为“万物之所由”的?“万物”又是如何获得其统一性的?这是摆在王弼面前的难题。
王弼借助了“自然”这一概念来贯通“道”与“物”。在他看来,“道”即是“自然”,他在注释“道常无为”时说“顺自然也”[4]91。所谓“顺自然”就是自然而然、任事物本性发展,与人为相对。王弼注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时说:“法,谓法则也。人不违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违天,乃得全载,法天也。天不违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为也。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4]65。在这个注释中,“自然”有两个含义:“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这“性”,就是指自然本性,各物皆有其本性,并且皆能顺其本性而生存,即为“法自然”。这一层“自然”的含义是功能性的。王弼再解释“法自然者”,说“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为也”。这“自然”就是自然界了,这一层“自然”的含义是物质性的。
至此,可以得到如下结论:所谓“以无为本”,首先是指以自然为本。虽然“道”与“物”分属“形而上”与“形而下”两个领域,但二者皆以自然为性,并且通过自然, 二者得以联结。虽然道之自然与物之自然有同有异, 但皆须遵循自然, 皆以自然为准则。王弼对“自然”的推崇,不管是重在自然的功能义,还是重在物质义,抑或是兼顾二义,都对魏晋时期的美学思潮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 “大美配天而华不作”的自然观与魏晋美学
从美学观点看,审美主体只有不断地超越有限去追求无限的整体,才能获得最大的审美享受。王弼指出:“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4]95在王弼看来,一方面,“大美”就是“圣人”能守母存子,崇本举末,不为有限所局限而能达于无限的表现。由于达到了无限,所以不为个别、有限的形名所引诱而走向邪道(“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另一方面,所达到的美又并非那种外在的华饰、雕琢的美,而是真实自然的朴拙之美(“大美配天而华不作”)。
王弼用“无”来谈“道”,又用“朴”来谈“无”。他说:“朴之为物,以无为心,以无为心也,亦无名,故将得道,莫若守朴。”[4]81“朴”即为自然本色,也称为“素”,与“华”相对。王弼以“无”作为宇宙之本体,在人生观上也主张“反本”。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言,王弼“其形而上学在以无为本,其人生之学以反本为鹄”[5]。而“道”即是“自然”,是“朴”,所以说王弼的人生观是“守朴”。既然他在人生观上“守朴”,那么在美学上也必然会倡导一种朴拙之美。王弼认为上天最具有这种品格,所以说“大美配天而华不作”。王弼玄学以美为无限的表现,而无限之为无限在于它包含了一切具有潜在可能性的“无形”“无名”,就像水可以和以众味,但其本身却是淡而无味的。“道之出言,淡兮其无味也,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然则无味不足听之言,乃自然之至言也。”[4]57可见,王弼崇尚自然、朴拙、平淡无味之美,并且认为这是一种最高的美。
(一) 自然天放的人格美
魏晋时代,知识分子在着力构建理想的人格本体,即超越有限而达到无限的精神自由状态。其在美学上首先表现为倡导一种自然天放的率真美、一种不拘礼法的旷达美。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推崇的“法天贵真,不拘于俗”的君子人格美,虽肇始于先秦的老子、庄子,但真正形成风气并为众多人认可的却是在魏晋。这集中体现在《世说新语》的人物品藻当中。
首先,重视人物容貌。魏晋对人物容貌美给予空前的重视。这种对容貌的重视首先表现在离开德行、才能等内在品质专门品评容貌的美丑,且明显地表现出对容貌美的赞赏。比如,“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6]341,“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6]342,“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素素,爽朗清举’”[6]335。
其次,重视人物风度。风度不仅包括容貌,还包括从人的外在容貌、言谈举止所透出的精神气概。风度是人的内在素质与外在表现的统一,理性内容与感性形式的统一。风度在人物品藻中最富有美学意义。比如:“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锋太俊。’太尉答曰:‘诚不如卿落落穆穆。’”[6]239“顾悦与简文帝同年,而发蚤白。简文曰:‘卿何以先白?’对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6]65
再次,倡导自然率真的君子人格。《世说新语》中记载了很多有趣的事情:“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6]393阮籍醉酒躺在邻家妇身边,这在中国其他封建时代是非常忌讳的,但是在魏晋时代并没有被认为是很可耻的事情,反倒得到了理解。又如:“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6]397这种无视礼法、放达通脱的生活作风一时成为风气,不仅在野隐士以之标榜,而且不少达官贵人也风流自赏。曹丕好诗文,其与朋友交往也极通脱:“王仲宣好驴鸣,既丧,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6]347
(二) 怡情畅神的自然美
王弼“大美配天而华不作”的自然观,也影响到魏晋南北朝人自然美的观念。它促使人们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欣赏山水之美,将自然山水之美看作是“自然之道”的显现,从中获得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志悦神的审美愉悦感。
中国人对自然美的欣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远古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还处于蒙昧状态,山崩地裂、雷动风行等自然现象往往被赋予一种恐怖惊惧的宗教色彩。如《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中说“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证也”。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哲学思想的发展,人们对山水自然的认识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山水自然不再是可怖可惧的,而成为被人们广泛认识、欣赏的对象。其中最基本的特征是山水被赋予道德精神的属性。最具代表性的是孔子提出的“智者乐山,仁者乐水。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7]。到西汉,由于宗教神学的猖獗,皇帝封禅祭山不绝,导致自然带有很浓重的迷信色彩。到东汉末年,士人有感于时局的动荡,转向从山水中寻求精神寄托。如荀爽在《贻李膺书》中自述:“知以直道不容于时,悦山乐水,家于阳城。”由此可见,山水自然之美在魏晋以前是没有独立的审美价值的。
进入魏晋时代,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和对山水之美的欣赏发生了巨大变化。自然界不再被看作压迫人的宗教神灵,或仅仅是作为道德的比附,而是与人能够相亲相近的客观事物了。在魏晋时期,“晋人以其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乃能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8]。可以说,直到魏晋,自然山水独立的美学价值才得到了人们的充分认识。
正因为自然美是自然之道的显现,所以山水自然才与人相亲相近,人们在欣赏、感受自然美时才可以领略到与天地同体的无穷乐趣。魏晋时期,游山玩水已经成为人们的一桩赏心乐事。《世说新语》记载:“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忘怀。’”[6]8“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6]81
晋人喜欢自然山水,还因为山水审美能够寄情畅神。《世说新语》中记载:“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6]67简文帝“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这句话,不仅表现出人在自然山水欣赏中的移情态度,而且强调在欣赏中人与自然山水的亲和感。“王司州至吴兴印诸中看,叹曰:‘非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6]77这突出了自然山水欣赏中的愉悦性。这种愉悦性是由自然山水的美所激发的,但它反过来又让人在想象中增添了自然山水的美。宗炳在《画山水序》中将人对自然山水的审美态度作了新的理论概括:“圣人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神”能“畅”,这说明这种欣赏是人与自然山水的一种愉快的情感邂逅。这一命题将审美通常所具有的移情现象、愉悦效应都概括在内了。
(三) 自然天成的艺术美
推崇自然天成的创作方法,溯其源,是先秦道家贵在天工的哲学观念的体现。老子哲学中的“自然”,最基本的意义是“自然而然”,即本然、天然。他对美学的表达就是“朴”。“朴”不是一味的排斥华丽,它排斥的只是那种不合乎事物本性的虚假的华丽,而合乎事物本性的华丽其实也是朴。老子视朴为美,庄子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认为“天地有大美”,美就存在于天地自然之中,美在自然无为。
王弼将其发挥之,说“大美配天而华不作”。真正的“大美”,必是一种洗尽尘滓、独存孤迥的最真实、最纯净的美。王弼认为,“顺自然而行,不造不施”,“顺物之性,不别不析”,“因物之数,不假形也”[4]71。天地万物任其自然产生,自然消灭,顺应自然,则会邂逅最高的美,即自然之大美。
刘勰认为文学艺术之美是自然之道的表现。他在《原道》篇中赞美天地万物都有“文”,焕然绮丽,人在天地两仪之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在此篇中,他反复强调美和艺术的本质是自然之道的体现,“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同时,他认为,文学艺术创作的动机来自文学家对外物的情感触发,这种情感是自然而然的。《明诗》篇中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可见,刘勰在文学创作中十分推崇文学家的自然生情、真诚无伪。
对自然的推崇不仅是玄学诸子的共同特点,也是魏晋思想的一个突出特征, 在嵇康、阮籍、郭象的思想中, 在记载魏晋人的生活方式的《世说新语》中, 在魏晋六朝的文学艺术中, 我们处处可以看到自然主义的影子。虽然这种自然主义的形成与先秦老庄“道法自然”的思想有内在联系, 但就魏晋时代而言, 王弼“大美配天而华不作”的“自然”观念无疑对此具有更直接、更深刻的影响,它是魏晋玄学通向美学的一个重要命题。
[1] 陈鼓应.老子著译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 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编)[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325.
[4] 楼宇烈.王弼集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40.
[6]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4.
[7] 李学勤.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79-80.
[8]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11.
(责任编辑: 郭红明)
“The Great Beauty of Whole Cosmos Consists in Simplicity”——Wang Bi′s Naturalism and Wei-Jin Aesthetics
关于摘要的写作
摘要既反映论文的主要内容,也反映作者的写作水平和能力。摘要应是论文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应具有自明性和独立性,可以看成是论文的缩写,即不阅读全文就能获得必要的信息。不少论文采用中学生总结中心思想句式表述摘要,如“通过……采用……分析……研究……得出……”之类公式化的方式写摘要。这种摘要一般以经济管理和教育类论文为多,往往与下面四种情况有关:一是这篇论文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二是要表述的内容作者自己本身没有形成明晰的看法,三是作者缺乏概括自己论文的能力,四是受自然科学论文写法的影响。摘要不能反映论文主要内容和结论的文章编辑是可以由此对论文及作者水平作出初步判断。
LI Hongli
(School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The Great Beauty of the whole cosmos consists in simplicity”, which is regarded as the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Wang Bi's naturalism inclination. The naturalism of Wang Bi's metaphysics inherits and develops the thought of “beauty exists in nature”, which is put forward by Lao Zi and Zhuang zi. This new naturalism is based on the proposition of “noumenon based on nothingness”, and it affects Wei -Jin aesthetics widely from three aspects:the beauty of personality, the beauty of nature, the beauty of arts.
Wei-Jin; naturalism; Wang Bi; metaphysics; aesthetics
2014-12-26
李红丽(1984—),女,陕西宝鸡人,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哲学和美学研究。
1673-0453(2015)01-0015-05
B21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