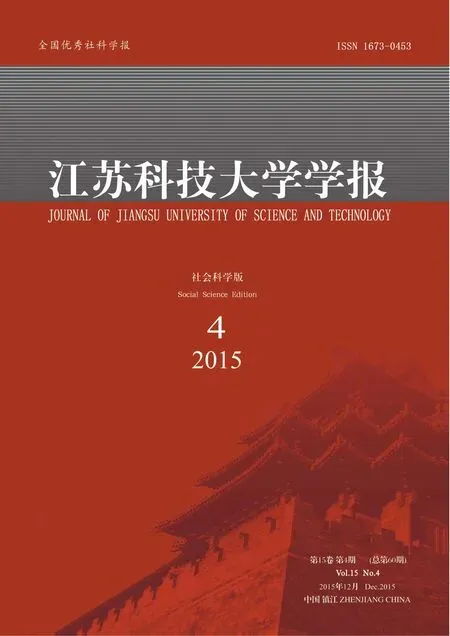论庄子生死观道德形态的三重逻辑
2015-04-14孙全胜
孙全胜
(山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论庄子生死观道德形态的三重逻辑
孙全胜
(山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庄子一方面通过揭示“生”所展示的双重逻辑——感性之身的本然逻辑及其中蕴涵的应然价值,另一方面通过揭示“死”体现的超然意义,力图超越“命”的本然逻辑及其中呈现的实然轨迹。在此基础上,庄子生死观道德形态的出场以“道”为一体,以“追求”和“超越”为两翼,一体带两翼,两翼促主体,多元化展开。其出场逻辑从追求“心不死”的精神境界到超越物理过程的生死,达到等生死、齐荣辱,进而于生无所恋、于死有所怀,并从气化、物化的角度达到物我同一的终极境界。他以得道的超越替代了生之追求,其对人类生存境遇的展望必然是悲观和绝望的。
庄子;生死观;道德形态;三重逻辑
庄子生死观道德形态的出场经历了追求和超越的“否定之否定”的三重追问。在这种“否定之否定”的三重追问中,庄子生死观的道德形态以“道”为核心,从追求“心不死”的精神境界到超越生死,再达到“齐荣辱”的圣人境界,进而实现与天地同在的神人境界。“追求”和“超越”的本然追问就是为了达到安天乐命、逍遥自由的应然境界。
一、庄子生死观道德形态的逻辑起点:感性之身的经验意义何以错误?
首先,庄子生死观道德形态出场的逻辑起点是从追问人的感性存在的价值开始的。
庄子揭示了“生”蕴涵的双重逻辑——感性之身的本然逻辑及其中隐含的应然价值。在他看来,认识的最高境界就是穷尽一生懂得自然的作为、了解人的作为,并维护本性、本心,“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1]88。也就是说,人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就可以用所了解的知识去保护自己无知的天性,让自己不会中途死亡。这是知识能够达到的顶峰。这实际上是试图通过增长见识来达到“养生”之目的。
在如何保养性命的问题上,庄子有特别的养生理论。他要求“少私、寡欲、静心和超然”。其一,私是万恶的根源。人如果私欲缠身,必定会瞻前顾后,忧郁寡欢,思虑重重,不得安宁。这样下去必定导致精亏血虚、体弱无力。只有胸无挂碍、坦坦荡荡、知道保守本心的人,才能知足常乐,延年益寿。其二,纵欲会迷失本心。不能放纵欲望,纵欲必然会侵染本心、本性。性欲毕竟只是人的一种动物本能,放纵本能会压抑人的自由意志。人若少情欲,则会情意诚平;少物欲,则不会贪图别人的财物;少权欲,则不会迷失良知。只有守正道、言行谨慎的人,才会顺服安顺、泰然处世。这样就会减少灾祸、平安一生。其三,不守本心是得病之源。人若终日浮躁,不能谨守内心,定会百病侵身。只有心平气和、温柔平静的人才能在遇到事情时做到波澜不惊,才能少受浮世影响,保守健康的体魄和赤子之心。其四,世间浮华会冲淡本心。人如果沉迷在物质世界中,就会灵魂朽灭。世上一切皆是虚幻,惟有天道才是永恒。天道就是真理、生命、方向。天道会作用于人的心灵,使人获得真理和意义,而真理和意义必须借助语言才能呈现。由于口语能由人随意说出,因而它更靠近心灵。惟有以超然的立场对待生活,一切顺应天道,才能保全自己、成就生命、奉养亲人、不负华年。庄子生死观的伦理起点就是保养人的感性身体。他指出,“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身,又况他物乎”[2]。而实际上,人的生命最主要的就是感性之身,肯定生命就需要关注感性之身。这是用总体性的眼光去看待生活。“总体性就是用全面的眼光看待社会生活,拒斥碎片和分裂。”[3]因此,庄子一开始就很关注人的感性之身的存在及其保养,追求生命的不朽不灭。庄子以其特有的伦理批判视角,通过重视人的感性存在揭示了其中蕴涵的“养生”的应然逻辑。
其次,庄子还深刻揭示了“死”蕴涵的双重逻辑——感性生命之死的本然逻辑及其中隐含的“无我”的应然逻辑。
庄子在倾心于人的感性生命存在的本然逻辑时,又对生命存在的实然逻辑予以超越。此一阶段的超越是从追问生命的原因开始的。他认为,人应该回归生命的本然状态,打破道德伦理规范对人本性的束缚,达到无拘无束的生活状态。有追求的人生才不寂寞,超越俗世的人生才更潇洒。在生之艰难中坚持信念,在真理指引中喜乐忍耐。庄子不高歌健康,而赞美身有残疾。因为身有残疾可以不用担负国家沉重的徭役,可以在战乱中保全自己。庄子总能从不好的事物中看到喜乐之处。这虽然是自我精神胜利法,但在面对艰难时势时,人有时需要麻痹自己才能生存下去。庄子认为“支离”可以保命,而“支离其德”可以心安。这是比养生更高的境界。“支离其德者”表面意思是指道德支离破碎、思想“有残疾”的人,实质上是指摆脱道德枷锁、具有独立思想的人。庄子号召“吾丧我”,就是要把自造壁垒、陷于与他人对立境地中的“我”抛弃掉。人只有解除道德枷锁,复归自然的本然逻辑,才能不受社会定见的束缚。无形的“道”孕育了世间万物,世界是从无到有的过程。借助这种逻辑,庄子还悟出了性命存亡的真谛,那就是生死存亡不过是一个命定的过程。他在解除人的道德枷锁之后,又借孔子之口对人生死背后的推动力量作了猜想:“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1]81这其实是想说明人的生死是“命”在掌控着,“命”作为超能的力量规定万物的存在。这是上天的旨意,“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1]92。庄子认为,“命”作为一种不可违背的规律,是道法出自自然的表现,其来去都无影无踪,“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1]272。原初的世界本是无,从无中产生了“道”,“道”经过发展产生了很多“道”,“道”作用于人的身上就是命。面对这种出于自然而又不可违背的法则,庄子认为,有自知之明的人就要“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1]79。因为面对不可抗拒的规律,任何挣扎都是徒劳的,任何犹豫与拷问都是无意义的。既然一切早已决定,那还需要什么努力呢?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会更快乐。
庄子在对世俗的“喜生恶死”观念作了初步消解后,阐述了他自己明快而新奇的生死观。庄子用时间的浩瀚消解了生命存在的意义:“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1]6相对于川流不息的时间长河,人生的确短暂。生命相对于死亡,只是短暂一瞬。人生只是过客,过客的意义何在?世人一般都喜欢生命长久,贪图现世的幸福,庄子却指出生死存亡只是大自然精妙的安排,“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吾所以善吾死也”[1]97。庄子用“丽姬出嫁”的例子证明死亡的快乐:“丽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晋国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与王同筐床,驰豢,而后悔其泣也。”[1]39也就是说,死亡就像结婚,非常愉悦,代表着平庸生活的结束;就像“回家”,非常喜悦,显示着旅途的劳累得到缓解。既然死亡如同结婚,是一件喜事,那么就无须哭哭啼啼、悲伤不已;既然死亡如同回家,是一件好事,那么就完全没必要恐惧死亡。这显然是想破解世人“喜生恶死”的魔咒,力劝人们认清自己的位置,在恪守本分中超越俗世的苦难。
最后,庄子还深刻揭示了“生死”蕴涵的双重逻辑——生死相连的本然逻辑及其中隐含的“本体论”的应然逻辑。
庄子对生死背后的推动力量作了探寻。在他看来,“道”产生了气,万事万物都是由气组成的。生死只是气化的本然过程。生死相连,生死只不过是气一聚一散的产物,气聚则为生,气散则为死,“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1]332。庄子把气的聚散称为“机”,“机”可产生万事万物。既然人死之后回归自然,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那么就没有必要为死亡哭泣和悲伤。生死只是形态的变化。所谓生死存亡,无非如昼夜的更替,我们无需好昼而恶夜,也没必要乐生而悲死。在消解生死界限之后,庄子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人生观:人生是痛苦的过程,死亡未尝不是一种解脱、一种安眠。死亡不是归于虚无,而是转化为一种更为恬静的存在。“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1]97庄子在《至乐》篇中借骷髅之口说出了死亡的无比快乐:死亡后没有拘束,有无上的自由,与天地同寿。“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1]265因此,在庄子看来,死后要进入的是极乐世界,不但没有痛苦,反而非常快乐,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解脱。就这样,庄子像一个看破红尘的智者,得道、明了、顿悟到了人世实相。世间万物终究都是虚无,终究摆脱不了生老病死、成住坏空的宿命。孟子主张舍生取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4]。庄子则认为,世间的荣辱繁华只是浮云。
庄子提倡“坐忘”,忘掉尘世的一切。当我们深切体会无常表象,就可以坦然体悟到“虚无”乃是世间万物的本相。实际上,人的一切痛苦都来自欲望,欲望给人生存的动力,欲望越大痛苦越大。这是生存不得不承受的代价。如果消除欲望,人倒是没了痛苦,可也没了快乐。人总不能要求太多,企望事事做到尽善尽美。“庄子的‘堕肢体’、‘离形’,实指的是摆脱由生理而来的欲望。‘默聪明’、‘去知’,实指的是摆脱普通所谓的知识活动。”[5]或许,这不是寡情无义、看破红尘,而是在知性上体悟到了万物实相,在本能欲望上不因执著而磨灭自由意志。庄子对于死的看法极其达观,当造物主召唤他离开时,他就静静地起身而去。就这样,庄子消解了人们对死亡的厌恶和恐惧,使人们不贪恋于生,也不畏惧于死。庄子认为,生死只不过是物质不断变化的结果,死亡不过是生的另一种状态。因此,庄子是不承认人彻底死亡的。“故知天乐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责。故曰:‘其动也天,其静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万物服。’言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天乐者,圣人之心,以畜天下也。”[1]194接下来,庄子又用梦蝶的故事论证生死相随。梦与现实究竟哪个更真实?庄子的回答更倾向梦。“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避避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1]43庄子既疑惑又超然:生和死哪个更可贵?“气化”和“物化”是从本体论视角论证生死的辩证关系,号召生死达观,以解除死之恐惧。保持自己意志的独立,即“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才能实现“物化”,否则便是随波逐流。快乐就是身体的轻便和灵魂的无纷扰。善就是顺应自然,与自然达成和谐。但这只是庄子生死观伦理形态出场的逻辑起点,庄子接下来又对死后的精神世界作了进一步思考。
二、庄子生死观道德形态的逻辑演进:何以执著追求“逍遥游”的境界?
应该说,庄子是在揭示世俗的“喜生恶死”观念的错误时揭示了“生死”呈现的双重逻辑——生死相连的实然逻辑及其中体现的“本体论”的应然逻辑。人的本能是喜生恶死的,可庄子扬弃了生命感性存在的实然逻辑,进而盼望达到“心不死”的应然逻辑。在他看来,“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1]315。也就是说,最大的悲痛莫过于人的心境黯然、意志沮丧到无法自拔。即使人死了也不比这种情况更糟糕。在这一层次上,庄子把人的感性之身的死排在“心死”的从属地位,告诉我们精神生命的重要价值。
首先,庄子把“心不死”看成是一种更高的应然存在,试图彻底消除世人对死亡的恐惧。在他看来,人的肉体死亡并不代表人生命的终结,人死亡之后只是进入了另一种存在。
庄子把“心不死”看成是人的另一种存在,这表明了庄子试图超越人的感性之身。人的感性之身的存在是虚无缥缈的,人生在世和世界万物相比不过是短短一瞬,在还没有好好体味之时,它就会终结或者戛然而止,“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1]340。死亡是人的必然结局,死后必然是一片虚无。不仅自然界害怕真空,人也害怕虚无。千百年来,无数人都试图消除这种虚无。各种宗教用“来世”来消除人对死亡的恐惧,连马克思主义也坚持物质不灭、物质可以转化。而庄子认为,人的形体朽灭后,心还会继续存在,“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1]50。庄子把“心不死”看作高于“感性之身”的存在,表明了他对人如何在死后还能继续活着的思索。因此,庄子对“身死”之后的“心不死”特别推崇。在肉体和灵魂之间,庄子认为灵魂更高贵。由此可见,庄子特别渴求获得一种无纷扰的精神生命。实际上,人的高贵之处就在于人有自由意志,有自由自觉的意识。从这一点看,庄子强调“心”的重要是有积极意义的。合乎“大道”的精神生命究竟是怎样的?在他看来,合理的精神存在是顺应自然,而不是逆天而行。“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积财而不得尽用,其为形也亦外矣!夫贵者,夜以继日,思虑善否,其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寿者惛惛,久忧不死,何之苦也!”[1]259也就是说,一些有钱人身患重病,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更影响了他的心情。即便积攒了很多财富却不能换回健康的身体。那些地位高的人,很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没日没夜地操心。这种人的感性存在痛苦而无意义,活得没有价值,只是一具不断满足动物本能的行尸走肉。庄子对这种感性存在很反感,主张放平心态,知足常乐。
庄子超越了感性存在的实然逻辑,进而追求实现精神永恒存在的应然逻辑,这也表明了庄子超然于物外的淡泊心态。但是,庄子并不仅仅追求“心不死”的精神存在,还对世俗生死观念作了更深层的解构。“特犯人之形而犹喜之,若人之形者,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其为乐可胜计邪?故圣人将游于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1]92庄子在肯定精神存在的价值后,还站在宇宙本体论高度解读了生死关系。
其次,庄子从宇宙生成论角度论证了生死的本然关系。在他看来,宇宙始于“无”,一切事物都源于“无”,人的生死也来源于“无”。“无”是一种天道,人必须遵循。
庄子站在宇宙演化高度看待生死的由来。他竭力填平生死之间的本然鸿沟,全力缩短生死的实然距离,以实现生死混同的应然境界。在一般人看来,生死天差地别,生指代的是积极、价值、存在,而死显示的是消极、失落、虚无。而庄子认为,生和死有共同的根源,而且无尽循环,最终都要归于无。第一,生死有着共同的本原——无。庄子指出:“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体。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犹其有物也。”[1]351生死的根源来自哪里?庄子认为,生死都源于无,“其次曰始无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无有为首,以生为体,以死为尻[1]372。人应当把生死看作自然运动的本然逻辑,而不是截然不同的实然“断裂”。和其他思想家一样,庄子的“无”并不是一种绝对的虚无,而是一种与生存相反的存在。第二,生死是一个循环往复的本然逻辑过程。天地万物不但实现着由生到死的实然逻辑,也可以实现从死中复活的应然逻辑。庄子指出:“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1]332“生死周而复始,永无止境,如同昼夜的往返更替,“死生为昼夜。”[1]263死生的更替是没有止息的,婴儿的出生恰是死亡的开始。自出生之时就开始走向死亡之路。“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1]26在这里,庄子肯定了世界存在的永恒,死亡仍是一种存在,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存在方式。第三,死亡比生存更应得到推崇。在庄子看来,不承认人生命存在的渺小是很可悲的。人的肉体存在只是短短一瞬,宇宙恒常的存在方式是无欲无求。“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未生之时。”[1]240死无需恐怖,生不必感恩。因为死亡不是彻底归于寂寥,而是一种更好的存在方式。
庄子追求“心不死”的精神生命。这里的“追求”和“超越”还是简单的论断,其主要征兆为:“追求”和“超越”的界限分明,人虽然超越了世俗生死观念的实然逻辑,但仍追求“心不死”的应然存在。但换一个角度来看,生与死还是在执著追求人的精神生命方面实现了一定意义上的交融:追求“心不死”的精神存在,是从肯定的角度论证死亡之后的精神生命的永恒、自由和超然,从而让人获得心灵的平静;超越世俗的“喜生恶死”观念则是从否定的角度论证生的恐怖、死的喜悦,从而给人的精神生命以抚慰。因此,在这一发展层次上,“追求”和“超越”泾渭分明,但还没有完全融合。在庄子看来,生死是物化和气化的本然逻辑过程,这就实现了“齐生死”的目的。在下一个发展层次上,“追求”和“超越”在“道”的方面终于实现了水乳交融。
最后,庄子生死观“伦理-道德”形态的逻辑演进是和“道”联系在一起的。他追求“道”的本然状态,而超越“依道”的实然逻辑,最终实现“达道”的应然逻辑。
庄子对“道”有很多阐释。在他那里,“道”是一种至高存在。何谓“道”?第一,“道”是一种飘渺的东西。“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不为深。”[1]93“道”以自己为本,以自己为根,在天地没有存在之前就存在了。“道”产生了天地万物。“道”支配着宇宙从无到有的过程。第二,“道”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庄子指出:“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1]338因此,“道”统摄着宇宙万物,人的生死当然也由“道”统摄。既然“道”是宇宙的本然状态,统摄万物,那么人的行为就要合乎“道”。庄子指出,“解其天袠,堕其天弢。纷乎宛乎,魂魄将往,乃身从之,乃大归乎”[1]340。第三,“道”是世界的本原,得道者才能成事。“道”无所不在,但“道”不会自动生成于人的头脑,需要人去感悟才能得道。而得道之人,就会在人间无所不能。庄子指出,“以道观言,而天下之名正;以道观分,而君臣之义明;以道观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泛观,而万物之应备。故通于天者,道也;顺于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义也;上治人都,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6]141。在他看来,人可以从“道”中体悟出生活的真谛,“追求”和“超越”通过“道”可以实现交融,“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6]29。在“悟道”过程中,庄子通过等生死、齐荣辱,进而于生无所恋、于死有所怀,并从气化、物化角度实现物我同一的达观,达到乐天安命的应然境界。当然,这还不是庄子生死观伦理形态演化的逻辑至高点。只有在神人境界里,生和死本身也被消解了,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实现了与天地同在,一切行为都合乎“天道”时,才算实现了“逍遥游”的境界,“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6]10。
总之,本然的“道”是庄子生死观伦理理论形态出场并不断演进的起点和终点。庄子生死观伦理理论形态出场的逻辑演进是这样一个过程:追求于“心不死”的本然生命,依“命”而超越生死的实然分离,在“悟道”中实现逍遥游的应然境界。因此,庄子生死观伦理形态的出场是一个在“悟道”过程中不断演进的逻辑过程。
三、庄子生死观道德形态的逻辑终点:何以解决人的生存危机?
庄子生死观“一体两翼”的道德形态,不仅显示了庄子生死观的内在思路,也昭示了庄子生死观的外在成因。庄子生死观道德形态的本然逻辑体现的是他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反思和超越,其深刻性与局限性是并存的。他以逍遥游的应然追求消解了生命的本然存在,其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展望必然是悲观和绝望的。
(一)庄子生死观道德形态的本然逻辑立足于人的生存困境
庄子对于人的生存方式的病症开出的药方是以自我修养为基础的。这是由其生存的时代境遇决定的。因为任何人都无法脱离自己生活的时代境遇。“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7]庄子生死观道德形态的出场体现了他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反思,表现了思想积极入世的一方面。“任何哲学思想,都是产生在一定的文化环境和时代条件下,要了解一种哲学思想,首先就要‘知人论世’,将它放在产生它的文化环境和时代背景中,了解它所面临的问题和它自己的传统。否则根本就不可能了解这种哲学。”[8]庄子生活在一个动荡不断的时代,“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1]151。生活在战争年代,生命如同断根的草芥,脆弱、细微得不堪一击,惟有死亡还算公道。死亡来临之际,任何人都没有不死的特权。改变不了残酷的社会,就只能改变自己。改变自己就要克服自己的欲望,不断修养自己的身心,尽量服从统治阶级的意志。庄子一开始也希望生命能够长久。但在处处充满杀戮的社会里,养生根本不可能,所以庄子幻想死后精神能够永恒存在,以消除内心的死亡恐惧。有的人即使侥幸生存下来,可“小恐惴惴,大恐缦缦”[1]20。这种生活只是动物的生活,所以庄子又强调精神生活的价值。最后,庄子又指出“依道”的重要性,其目的是使人超脱死之恐惧和生之苦恼。“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9]人类作为有限的存在,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始终无法挣脱不自由的窘境。
庄子生死观道德形态的不断演进是对生之困境的追问与摆脱。顺应自然的人应当摒除极度、奢靡、过分的行为和做法。“只有人自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10]当时,统治者推崇的伦理道德成为无数“正人君子”窃取私利的工具。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迁剧烈,时局动荡不安,百家之说峰起,论辩之风活跃。庄子对当时由诡辩引起的奇说异辞泛滥的情况十分不满,对制造奇辞之人深感愤怒。在他看来,“圣人”是比“大盗”还可恶的人,他们比盗窃财物的人更该杀,他们制定的伦理道德是社会败坏的根源,所以庄子非常反感“仁义道德”,主张破除一切束缚,成为自由的人。“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1]125庄子认为,所谓的自由境界就是万物遵循其自然形态而互不干扰。从一定意义上说,庄子要求废除“圣人”制定的道德的主张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因为“圣人”制定的道德只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权力秩序,而不是为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因此,庄子生死观道德形态出场的本然逻辑的不断演进也是从正反两方面对人的生存困境思考的结果。“真正重要的事情不是活着,而是活得好。”[11]当时,人生存于“水深火热”之中,这种生存困境促使庄子试图建构出人的美丽精神家园。庄子的“追求”是从人的精神生命方面论证人的感性存在,“超越”是从解构世俗的生存观念视角反观人的病态生存。“追求”和"超越"的契合点就是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拷问和反思。庄子指出,人类要实现美好生活,就必须皈依“道”。因此,生死要实现融合的唯一路径也是“道”。他要求的不是一时的放下,而是一生的放下。所以,庄子对人的生存困境有了最终的解决路径——“道”。他的生死观伦理理论形态也不断地走向融合,并最终皈依“道”。从有所追求的相对自由到一无所求的绝对逍遥自在,庄子体察了自由的真谛。马克思认为,“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12]。庄子的理论建构也是当时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因此,庄子生死观道德形态的出场及演进都是立足于人类的生存困境而生发的反思和追问。
(二)庄子生死观道德形态的应然逻辑的深刻性与局限性并存
庄子生死观道德形态出场的应然逻辑的深刻性表现在其对人生境遇的积极关注。死是一种必然规律,任何人都无法逃脱。“任何人都要死,自然的死亡是一种绝对的法律。”[13]对生死的忧虑与恐惧是智慧生物所特有的一种情结。这种恐惧情结让人制造了很多理论以回避那可怕的虚无。意志选择自由、灵魂永恒不死、上帝必定存在是康德定的三项理性公设。除了人类,地球上的其他生物都不会关注生死的意义。就是人类自己,也可以凭借看待生死的态度是否达观区分出智慧的有无与人生层次的高低。人类一直在寻求实现对生死问题的达观,而“休闲,从根本上说,是对生命之意义和快乐的探索”[14]。人的存在应该是一种“场”的休闲存在。海德格尔也指出:“此在作为存在者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本体论地存在。”[15]生死问题与每个人最重要、最基本的需求相联。对生死问题的解答,是形成正确人生态度的基础,是建立健康合理人格的基石。一个真正弄懂生死意义的人,必定是一个豁达和宽容的人。生死观道德就是教会人如何成为自己。伦理则是让人思考如何更好地生活在一起。人活世上不能只消极避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虽然能达成基本的文明底线,但我们也要奉行“已所欲,施于人”,积极去爱人、帮助人、拯救世人。人不仅要克制自己,不要伤害他人,惩恶扬善,也要主动去爱人,以善扬善。
庄子生死观道德形态的应然追求很具智慧,包涵了他对人生境遇的积极关注。第一,表明了人与自然的契合。人与自然是否能够交融、感应?人与自然是否有必然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深刻的人生命题。唯心主义哲学家们认为这一问题是无法回答的,而庄子却用“蝴蝶梦”的形象比喻填平了物我分离的鸿沟,让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达到物我不分的境界。第二,表达了对天真烂漫、无拘无束的人生境界的追求。庄子通过“化蝶”的形象比喻表达他对自由意志的追求。这表明他试图摆脱肉体的奴役。王弼也从易学周而复始之道的角度来论说:“虽死而以为生之道不亡,乃得全其寿,身殁而道犹存,况身存而道不卒乎?”[16]因此,庄子的思想比唯心思想家更为积极、更为深刻。第三,揭示了“人生如梦”的生存真相。不过,庄子“人生如梦”的涵义,除了后人理解的“人生的短暂、虚幻与飘忽”的意思,还有人生如梦般美丽的暗示。庄子用“蝴蝶梦”的比喻,既把人的生存境遇予以超现实的美化,又把人的生存境界加以理想的升华。庄子在这里表明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而不是后人强加给他的消极避世的人生虚无主义。第四,用“气化”和“物化”清除了生与死之间的界限。这与后来马克思主义物质相互转化的观点有契合之处。面对死,世人感到的是颤栗与恐惧、排斥和反感,而庄子认为,生与死体现的只是物质形态的变化,而物质形态都是气生成的。
庄子生死观道德形态出场的应然逻辑的局限性体现在他对人类生存展望的悲观和绝望。关于死,庄子的观点集中在《庄子至乐》一章记载的“鼓盆而歌”一节中。庄子的妻子死后,其友惠子去礼节性吊丧,却发觉庄子正敲打着乐器唱歌,非常高兴的样子。惠子看了很不舒服,便责备他:“你与她生活了这么多年,她还为你养育儿女,现在死了,你不伤心也就算了,竟然要敲着乐器唱歌,这样做岂不是太过分了吗?”庄子却回答:“其实,当她死时,我怎么不感慨?只是仔细想想,便明白她原本就是没有生命的;不仅没有生命,而且没有形体;不仅没有形体,而且也没有气息。在若有若无恍恍忽忽之间,那原初的东西变成气息,又变成形体,又变成生命,现在又变化为死。这样的变化,就像春夏秋冬四季那样运行不止,是自然之理。现在她终于安稳地存在于天地之间,而我们还要哭哭啼啼,我认为这样对于生命的道理是太不通达了,所以不哭她,而唱歌赞美自然的大能。”[1]262庄子批评死后厚葬的风俗,也从另一方面表明了他对生存的悲观。送葬队伍中传来的哭声,在他耳中是美妙动听的音乐。他笑着看人们出殡,简直要摆酒庆祝了。庄子弥留之际,其学生商量想厚葬他,在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却说:“我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以星辰为珠玑,以万物为赍送。我的葬礼还不够吗?何必要那些无用的俗物!”[1]530老子认为,人的生死如同草木的枯槁一样自然,“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17]。庄子也认为,生死是十分自然的事,对生不必喜,也不必厌;对死不必惧,也不必乐;人生于天地间,福祸死生都应坦然处之。这与儒家“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18]形成了鲜明对比。梁启超也指出,“人的肉体寿命不过区区数十载,不可能长生不老,但人的精神可以永垂不朽。因为他的肉体虽消失了,而他的学说,他的思想,他的精神,都会长期影响当代及后代的人们。从这个意义讲,人完全可以做到‘死而不亡’”[19]。庄子很难被大众理解和接受的主要原因就是他的智慧总是超出时间的限制,他的思想总是跨越空间的阻隔。对于俗世的人来说,他就是怪人与疯子,所以他被妖魔化。“真理使精神自由,自由使精神真实。”[20]哲人的痛苦是不小于精神病人的,因为他们是清醒而又绝望的。的确,凡人很难超越平凡的生活,而当哲学家试图超越时,人们却百般阻扰。在庄子看来,与其在是非对错中挣扎,不如跳出是非之后再观照是非之真,“美者还其为美,恶者还其为恶;不以恶而掩美,亦不以美而讳恶,则美恶齐矣。是者还其为是,非者还其为非;不以非而绌是,亦不以是而没非,则是非齐矣”[21]。圣人以此态度才是真正地因循“是”。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庄子生死观伦理思想的局限性是时代的必然。这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超出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能够超出他的皮肤。”[22]。
庄子在表述自己的生死观“伦理-道德”时是怀着一种期待天下安宁的政治理想的,让人体会到宽广的胸怀、宏大的气魄和较强的逻辑性。庄子的生死观伦理属于“黎明之光”,用的是“黑色的眼”,看起来冷峻,实际上充满对人生的关爱。庄子的生死观对后世思想影响甚深,其后儒、释、道三家都从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其实,中国的文明从未离开过精神世界,这种自古传承的豁达的出世精神对我们仍有积极意义。
[1] 孟庆祥.庄子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2]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966.
[3] 孙全胜.列斐伏尔空间生产批判理论的思想谱系及逻辑形态[J].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12-23.
[4] 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783.
[5]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3.
[6] 张小木.庄子解说[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2.
[8] 张汝伦.中西哲学十五章[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32.
[9] 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4.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76.
[11] 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1.
[1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4.
[13]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44.
[14] 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96.
[15]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6.
[16] 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8:84.
[17] 朱谦之.老子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4:294.
[18] 孔子.论语[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125.
[19] 陈国庆,张爱东.道德经[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33.
[20] 黑格尔.精神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20.
[21] 钟泰.庄子发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6.
[22]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57.
(责任编辑:郭红明)
Research on Triple Logic of Moral Form of Zhuangzi's Life and Death
SUN Quansheng
(Marxism College,Shandong Normal U niversity,Jinan Shandong 250014,China)
O n the one hand,by revealing the dual logic of“life”——inherent logic of sensual body with im plied deserved value and on the other hand,by revealing the transcendent meaning of“death”,Zhuangzi tries to go beyond the inherent logic of“fate”and its factual track.On this basis,the m oral form of Zhuangzi′s life and death takes“Tao”as the body with pursuit and transcension as tw o wings to pro m ote diversification.The logic gets fro m the pursuit of the spirit of“not dead heart to transcension of the physical process of life and death and it will achieve the ultimate goal of”I of the same.“T herefore his enlighten ment replaces the pursuit of life and his outlook on hu man living circu mstances m ust be gloo m y and hopeless.”
Zhuangzi;life and death;m oral form;triple logic
B223.5
A
1673-0453(2015)04-0007-08
2015-09-3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科技伦理的应然逻辑研究”(12BZ X07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科技伦理思想及其当代发展研究”(08JA720004)、江苏省道德哲学与中国道德发展研究基地项目“高技术道德哲学研究”(2009-03-01)、“科技、伦理与艺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研究项目“科学伦理研究”(2010-03-03)
孙全胜(1985—),男,山东临沂人,山东师范大学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