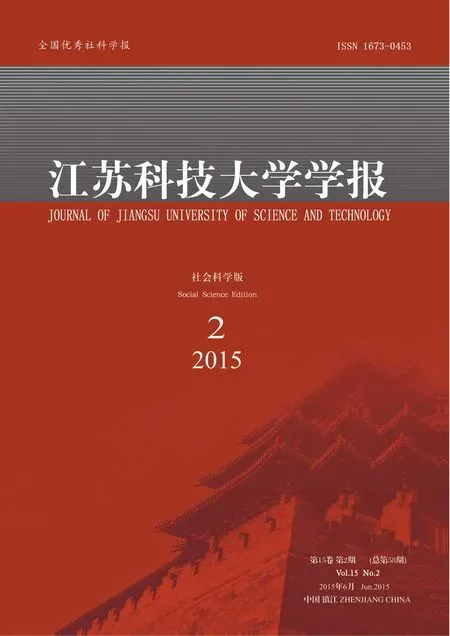论荀子的人-心秩序观
2015-04-14王军
王 军
(江苏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镇江212003)
人-心秩序观的核心即如何处理人与内心关系问题。因此,人-心秩序又可称之为内心秩序。在荀子看来,人-心(内心)秩序乃外在秩序在内心的反映。整顿人-心秩序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重整现实社会秩序。由于儒家以修身为本,而修身又以修心为起点,这决定了荀子的人-心(内心)秩序观在其整个秩序学说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荀子的人-心(内心)秩序思想并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相关研究成果甚少。这显然与其在荀子整个思想中的地位不相称。故笔者不揣简陋,在阅读《荀子》及相关文本基础上,对荀子的人-心(内心)秩序观进行专门梳理与解读,并发掘其在当代社会的积极意义,以请教于大方之家。
一、礼与义:理想人-心(内心)秩序的准则
荀子所说的人-心(内心)秩序更多地可以理解为外在秩序在人内心的反映,其标准也来自外界。在荀子看来,这个标准就是外在秩序的准则——“礼”与“义”。
人-心(内心)秩序的第一个准则是“礼”。“礼”在荀子学说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人间秩序的法则。一方面,礼是为政的纲领:“礼者,政之挽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1]589又云:“礼者,人主之所以为群臣寸、尺、寻、丈检式也。”[1]139另一方面,“礼”还贯穿于日用伦常之中,乃“分辨是非的标准”[2]。易言之,无论是政治生活还是人们的日常生活,都要以“礼”为准则,不能违背“礼”的规定。非但如此,荀子所说的“礼”还是“自然秩序的体现”[3]。荀子云:“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物变而不乱,贰之则丧也。礼岂不至矣哉!”[1]402也就是说,自然界也要遵循“礼”。既然“礼”乃自然秩序和人间秩序共同的法则,而人-心(内心)秩序又是外在秩序的反映,那么,人-心(内心)秩序也必须遵循“礼”。如此,“礼”就成了自然、人间和人-心(内心)秩序共同的准则。
人-心(内心)秩序的第二个准则是“义”。荀子所说的“义”与“礼”的地位并非等同,而是从属于“礼”的。因此,“义”往往与“礼”连用:“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1]61依荀子所说,“义”要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这与《中庸》“义者,宜也”[4]是一致的,因而可解释为恰当、合适的行为,其言说的对象主要是如何守“礼”。荀子云:
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故怀负石而赴河,是行之难为者也……山渊平,天地比,齐、秦袭,入乎耳、出乎口,钩有须,卵有毛,是说之难持者也……盗跖吟口,名声若日月……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1]31
在荀子看来,守“礼”并不是世人所说的像申徒狄那样特立独行,或如惠施、邓析之流故作高论,更不是追求盗跖那样名扬于世,而是要做到“礼义之中”,即“以义(宜)守礼”。具体地说,就是要做到:“宽而不僈,廉而不刿,辩而不争,察而不激,寡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1]34也只有这样才可以称之为君子:
君子贫穷而志广,隆仁也;富贵而体恭,杀势也;安燕而血气不惰,柬理也;劳倦而容貌不枯,好交也。怒不过夺,喜不过予,是法胜私也。《书》曰:“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也。[1]28
在荀子看来,无论是贫穷、安燕、劳倦还是发怒,君子都能保持良性的人-心(内心)秩序。这就是因为君子能够做到以公义胜私欲,因为欲乃破坏人-心秩序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欲”与“蔽”:人-心(内心)秩序混乱的根源
虽然人-心(内心)秩序是外在秩序在内心的反映,它却可以对外在秩序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因为一旦人们内心深处对秩序失去希望或干脆漠视秩序,就算保留了一些维持秩序的仪式,也只能是僵死的躯壳,所以孔子才会感叹“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5]易言之,良性的人-心(内心)秩序对于良性秩序的建构与维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实的人-心(内心)秩序并不理想,所以荀子才会有“人之性恶”的论断。为什么会这样?荀子认为这源于“欲”和“蔽”。
首先是“欲”。何谓“欲”?荀子云:“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1]490杨倞注:“性者,成于天之自然。情者,性之质体。欲又情之所应。所以人必不免于有欲。”[6]易言之,“欲”源于“性”,是人人都有的。非但如此,在很多时候,荀子又直接将“欲”等同于“性”:“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1]55“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1]503所以陈大齐[7]、徐复观[8]等学者认为,荀子乃“以欲为性”。人性中固有的“好利”“疾害”“耳目之欲”之类本能,一方面构成了人类社会前进最原初的动力;另一方面,如果顺其发展、任其泛滥,“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1]498,就会造成对秩序的破坏。秩序的破坏不仅包括以社会政治秩序为核心的人-人秩序,也包括人与自然、人与内心的秩序,而对秩序的破坏正是从人-心(内心)的崩溃开始的。欲望的泛滥不仅使人内心无法平静,而且有可能使人产生邪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荀子才有“性恶”之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荀子的“性恶”其实是“人欲倾恶”,而非通常理解的“性恶”。
其次是“蔽”。所谓“蔽”即蒙蔽、遮蔽、遮挡。荀子认为,“蔽”有很多种:“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1]497-498显然,在“好与恶”“始与终”“远与近”“博与浅”“古与今”五对对立关系中,无论执着于哪种情形都会蒙蔽人的眼睛(智慧)而造成错误判断;并且由于万事万物无不存在对立面,所以“蔽”是很难避免的。非但如此,常人所说的“见”有时也是“蔽”:“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愚者为一物一偏,而自以为知道,无知也。”[1]360这种“蔽”的危害更为严重:“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有后而无先,则群众无门;有诎而无信,则贵贱不分;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有少而无多,则群众不化。”[1]360这种因“见”而造成的“蔽”其实质是偏见或成见,因而更难克服:
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谓之道,尽利矣;由俗(欲)谓之道,尽嗛矣;由法谓之道,尽数矣;由势谓之道,尽便矣;由辞谓之道,尽论矣;由天谓之道,尽因矣。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1]360
墨子、宋子、慎子、申子和惠子都是世人公认的智者,但他们都因为自己的“见”而“蔽”,因而他们的“见”其实都是偏见。而偏见并非反映了“道”的本质:
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曲知之人,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故以为足而饰之,内以自乱,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祸也。[1]360)
既然“蔽”如此之多,因而在认识过程中一旦“有所蔽”就很难有正确认识:“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1]453对秩序的认识亦如此,由于有所蔽,所以很难认识到秩序的重要性,进而造成对秩序的忘却或漠视。
三、合性伪:理想人-心(内心)秩序的实现途径
既然人-心(内心)秩序很容易陷入混乱,那么良性的人-心(内心)秩序是否可能?荀子的回答是肯定的,所谓“涂之人可以为禹”[1]510。“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1]510-511人性中不仅有欲望,而且还有知善、知恶的能力与材质。这是人性向善的保障,也是构建与维系良性人-心秩序的前提。非但如此,人性中容易倾恶的欲望,只要控制得好,也可以变为善的因素。在人性中权衡利害的知性充分发展之后,必然会将人的欲望规导到符合其长远利益的礼义——良性秩序上。那么,怎样实现良性的人-心秩序?荀子给出的方案是“化性起伪”,最终做到“性伪合”:“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1]415性伪合的结果就是人-心秩序合乎“礼”与“义”的准则。
为了实现“性伪合”,荀子给出了一些具体措施。
首先是节欲:“虽为天子,欲不可尽。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所欲虽不可尽,求者犹近尽;欲虽不可去,所求不得,虑者欲节求也。道者,进则近尽,退则节求,天下莫之若也。”[1]490如何“节欲”?这就离不开“礼”。荀子云:“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1]393这从物、欲对立与平衡的角度说明了“礼”对调节人的欲求、维持秩序的作用。但节欲并不同于禁欲:“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以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故虽为守门,欲不可去,性之具也。”[1]490荀子反对的是人的欲望无限度地扩张,其目的是促进良性人-心(内心)秩序的实现。
其次是解蔽。解蔽是为了实现对事物的正确认识,避免蔽塞所造成的不利后果。荀子云:“圣人知心术之患,见蔽塞之祸,故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县衡焉。是故众异不得相蔽以乱其伦也。”[1]455此处所谓的“衡”就是尺度、标准,也就是“道”。因此,“解蔽”的关键在“知道”:“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则不可道,而可非道……故治之要在于知道。”[1]456要“知道”则离不开“心”,而“心”认识“道”的途径就是“虚壹而静”:“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谓之虚……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壹……不以梦剧乱知谓之静。未得道而求道者,谓之虚壹而静。”[1]457为了更好地“知道”,荀子提出了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胆猛戾,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庸众驽散,则劫之以师友;怠慢僄弃,则炤之以祸灾;愚款端悫,则合之以礼乐,通之以思索。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1]19-20荀子尤为重视的则是“诚”,所谓“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1]38。
最后是为学。与孔子一样,荀子也十分重视“学”的作用,所谓“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1]3。当然,荀子所说的“学”,绝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知识学习,而是更注重在道德修养和人格塑造方面的意义:“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1]39-10“学”的目标是“全”与“粹”:“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1]14在“学”的过程中要不断地反躬自省:“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恶也。故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1]16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成就大人君子的人格,最终形成良性的人-心秩序。
四、荀子人-心(内心)秩序观的现代启示
荀子的人-心(内心)秩观对当今社会具有重要启示,略述如下:
第一,荀子的节欲主张启示我们:良性的人-心(内心)秩序的培育需要合理控制人的欲望。在荀子看来,欲望是人-心(内心)秩序混乱的根源之一,因此需要节欲。节欲不同于禁欲,其目的是控制人的过分的欲望。对于人的正常欲望,荀子主张“养”:“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以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故虽为守门,欲不可去。”[1]490在当时社会生产力并不十分发达的情况下,荀子的主张是有其合理性的,此其一;其二,即便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物质资料对于人的欲望来说总是相对稀缺的,从这个意义上看,约束人的过分的欲望也是维系社会良性运转的必要举措;其三,从当时社会背景来看,荀子反对的是为政者过分的私欲,而不是庶民百姓基本生活需求。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的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这不仅带来了物质资料的空前丰富,而且助长了人类欲望的急剧膨胀。人类欲望过分膨胀不仅造成人与自然、与社会之间诸多无谓冲突,而且带来很多心理疾病:被无尽欲望搅动的人心躁动不安、不知餍足,最终在欲望之海中迷失自己。因此,为了实现良性秩序,必须妥善控制人的欲望,对合理的欲望要满足,对过分的欲望要节制。
第二,荀子的解蔽学说告诉我们:良性的人-心(内心)秩序的培育需要凸显理性(智)的地位。“蔽”是造成人-心(内心)秩序混乱的另一个根源,因而荀子提倡“解蔽”,而“解蔽”的实质即用理性(智)破除错误认识。显然,人-心(内心)秩序绝非简单的道德(德)或理性(智)问题,但德与智确实是两个最重要的可控因素。我们知道,儒家重道德(德)而轻理性(智),而荀子则是一个相对重视理性(智)的“另类”。其实,智与德两种因素都会影响人-心(内心)秩序。其中,“德”离不开“智”,只有“智”得到充分发展,“德”的根基才会牢固,而离开了“智”的“德”很可能是偏执的迷信;而“智”的发展,也必须自觉地接受“德”的约束。整顿人-心(内心)秩序亦如此。从短期看,把主要精力放在道德灌输上确实有利于良性人-心(内心)秩序的建立,但这个秩序由于缺少“智”的砥砺,其基础往往是不坚实的,在西方文化冲击下,这种不足就更明显了。因此,良性人-心(内心)秩序的培育不仅要重视德的作用,更要将智提到应有地位,做到德、智双修。
第三,荀子关于“身心之学”与“口耳之学”的区分提醒我们:只有真正的“为己之学”才能实现良性的人-心(内心)秩序。“学”的本义即“觉悟”[9],依此,真正的“学”只能是荀子提倡的“身心之学”而非其批评的“口耳之学”。“身心之学”以“美其身”为目标,“美其身”即提升自己、完善自己,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为己之学”。与“身心之学”的“为己”不同,“口耳之学”则“为人”。如此衡量“为人之学”的标准就在“人”而不在“己”。标准在“己”,则宠辱不惊;标准在“人”,则患得患失。宠辱不惊,故能保持良性的人-心(内心)秩序;患得患失,则焦虑不安、心神不宁。所以,为了实现良性的人-心(内心)秩序,必须提倡真正的“为己之学”,反对沽名钓誉甚至以博取眼球为目的的“为人之学”。
最后,荀子因对秩序的过分追求而表现出的专制主义倾向,则是需要特别警醒之处。为了实现良性的人-心(内心)秩序,荀子反对不合“礼”“义”的想法,而且在讲述孔子诛少正卯事件[1]642-643时,甚至冒出了“诛心”的苗头。为了维护秩序,“诛心”成了后世儒者惯用的手段。儒家“诛心”原本是为了追求良性秩序,但讽刺的是,这一手段不仅没能实现既定目标,而且被统治者利用,成为儒生们无法摆脱的精神枷锁,这可真是作茧自缚、自取其辱。更为严重的是,“诛心”之论还使中国政治笼罩一层阴影: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文字狱”愈演愈烈,思想者逐渐丧失自我,所谓的秩序只不过是毫无生机的死寂罢了。事实上,良性秩序的实现必须建立在主体审慎思考与选择基础之上,人-心(内心)秩序尤其如此。而“诛心”所带来的所谓秩序,则是以断灭人的理性思考为基础的。这显然不符合现代精神,也是需要特别警惕的。
[1]张觉.荀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240-241.
[3]惠吉星.荀子与中国文化[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46.
[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28.
[5]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185.
[6]王天海.荀子校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923.
[7]陈大齐.荀子学说[M].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47.
[8]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205.
[9]许慎.说文解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