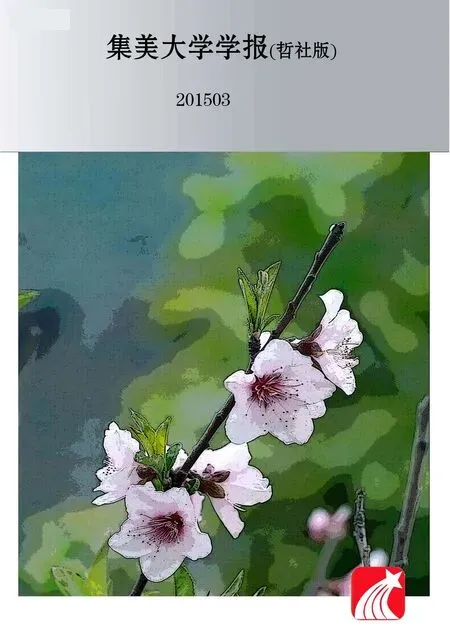《闽都别记》中的海洋叙事及文化价值
2015-04-14邹剑萍
[摘要]《闽都别记》是清代福建地区的一部长篇白话小说。对这部小说中的海洋叙事加以梳理,从海洋观念的发展、海商形象自由精神的大量描绘、海洋文化下特殊风俗的体现、海洋叙事中猎奇性和纪实性并重的时代特色等四个方面,探讨《闽都别记》中所展现的多元化的海洋文化价值。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89X ( 2015) 03-06-06
[收稿日期]2015-03-27
[修回日期]2015-04-23
[作者简介]邹剑萍( 1983—),女,福建莆田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清代福建地区的长篇白话小说《闽都别记》为“里人何求”所撰写, ①小说有400回,大约120万字,以闽都福州及附近区域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将这一地区从唐末五代至清初的历史为线索,讲述闽人闽事以及各种传说轶闻。藕根居士《跋》曰:“其书合于正史及别史载记者各十之三,野说居其四焉。以福州方言叙闽中佚事,且多引俚谚俗腔,复详于名胜古迹,文词典故,多沿袭小说家言。” [1]因此,此书一直被视为研究福建地区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福建地区有着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古时就有“闽在海中”的传说,作为东南沿海地区的闽地,生长于其上的文化是吹着海洋气息而逐渐发展的。“人类往往于不同的自然环境产生不同的文化,又于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产生不同的习惯行为和生活方式”。 [2]因此,描述闽地闽人闽事的小说《闽都别记》所展现的人物故事文化现象,都与海洋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笔者试图从海洋观念的发展、海商形象的描绘、海洋风俗体现、海洋叙事的猎奇性和纪实性等四大方面对《闽都别记》中的海洋叙事加以梳理,以期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小说的文化价值。
一、《闽都别记》中海洋观念的时代发展
何为海洋叙事?即“记叙有关海洋风光、物产及以海洋为背景发生的故事”。 [3]中国古典文学中海洋叙事的历史悠久,从《诗经·大雅·江汉》开始就有了关于海洋的描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4]《列子·汤问》一文:“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八纮九野之水,天汉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无减焉。”《庄子·秋水篇》则描述了河伯“望洋向若而叹曰:今我睹子之难穷也”。由于认识的历史性和阶级局限性,人们对海洋的观念主要停留在无法想象的广袤之上。也因此,从先秦时期开始,“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帝王们就不能满足于内陆,非常热衷于派遣使臣去往遥远辽阔难以穷尽的大海之上去求仙得道。《史记》里就记录了齐国的齐宣王、齐威王、燕昭王等人的派遣故事。从此以后,后代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普通文人为求仙得道而出海的记载在史书和文学里就不绝于缕。“至此,仙山林立的大海早已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大海,而是可以超越尘俗界限、通往仙境的必由之路”。 [5]唐宋以降,随着对海洋了解的加深,在先秦作品中云遮雾涌的海上仙山逐渐撕下它神秘的面纱,以一种更为朴素的面孔出现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涉海描写当中,比如晚明时期的《二拍》中多次提到“爪哇国”一词,如“丢在爪哇国里去了”“竟不知撩在爪哇国那里去了”等,都作为“很遥远的地方”来解释,“显而易见,这一用法在当时已相当普遍,甚至具有某种约定俗成的意味”。 [5]以海上仙山形式出现的海岛形象逐渐还原为遥远的一块土地形象,也说明在漫长的文学史中,渗透在文学作品中的海洋观念正在一步步深入和逐渐明晰当中。
《闽都别记》中的海洋叙事就有着明显的时代和地域印记。福建文学的海洋性不同于内陆地区,它最早的源头应该是来自于闽地土著们位于海边险恶环境中不得不“习于水斗,便于用舟”的生活习性,之后,伴随着唐宋以降海外贸易浪潮的兴起,加上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对于海洋的了解也逐渐加深,过去人们在对海洋了解缺失的情况下,就加以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联想,而现在,逐渐就被现实层面的理性认知所代替。《闽都别记》中“涉及到闽人海外交往内容的章回就有四十多回处,约占全书篇幅的十分之一”。 [6]小说中的海洋叙事不再像过去描述的那样是一种遥远的想象,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土地。明代徐孚远“东南边海之地,以贩海为生,其来已久,而闽为甚。闽之福兴漳泉襟山带海,田不足耕,非市舶无以助衣食;其民恬波涛而轻生死,亦其习使然”。 [7]《闽都别记》第167回中就记载福州临近的福清地区“该处无人读书,都是讨海种田”。闽人以海为田,使得《闽都别记》中的海洋叙事不仅仅是将海洋作为一种想象性符号来表现和描述,使得这本小说中的海洋观念具有了现实主义层面的含义。
实际上,虽然闽人很早就开始了与海打交道,但人们对海洋的能力尚处于近海航运、近海捕捞的状态,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福建地区的海上活动逐渐转换为海洋商贸型,与周边开展海上贸易活动。明清以来,福建地区与海外诸国的交流对闽人的观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人们对海外诸国的认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闽都别记》中,海岛更呈现出一种真实的姿态,对当地的生活习俗、风土人情进行了细致真实的描写。第180回描写南洋一岛“有讨鱼者泛竹排,排边有四五人蹲在,以两手入海里捕鱼,其人身不满五尺,手长丈余,捕有鱼或捉入篓,或入口即食,手长似虾摄物入嘴一样”。第144回、145回、146回描写胆大的商人们漂泊大海之上,一一经过大人国、小人国、一目国、黑齿国、蓬莱国、穿身国、烛阴国、轩辕国、交胫国等具有不同地域风情的海岛国家。这里面所描写的烛阴国常年黑夜,只有烛龙常出现在天空,极似出现北极光的北极气象,可能是北极小岛。第147回记载扶余国“该国离中华甚远,闻木船至便喜”。古代朝鲜半岛上的一个国家,因五代时北方辽国的阻断而通过海路和南中国进行贸易,《闽都别记》中第147回、148回、177回及178回等处多次谈到扶余国的情况,描述闽人在该国活动的情况。第261回记载有六人漂至麻喇国,该国国王“凸嘴仰鼻”,国人皮肤漆黑,从人种特征看,多半为非洲国家。第177回描写渤泥国“此处风俗婚娶,不知什么拜堂合卺,惟双牵手,对抱腰,便成夫妻”。
《闽都别记》中的故事虽发生在不同历史阶段,但就成书时间而言,它所体现的海洋观念却是在清代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闽都别记》继承了春秋以来的海洋叙事,并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加以自觉的追求,将它与时人的生活紧密联系起来,散发出越来越浓郁的现实主义气息。当小说家将海洋以一种现实主义的姿态纳入审美视野之后,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海洋文学从虚幻到写实的走向。从此前海洋文学作品与《闽都别记》的对比中,可以明显看到从虚构性走向写实性的变化,这体现了清代海洋观念的深入与发展。
二、《闽都别记》中的海商形象
除以海为田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外,促使闽人扬帆入海的,更是伴随着海贸的繁盛而带来的巨大的经济利益。从小说中记载来看,东汉时期,福州就与东南亚地区有贸易往来。而古代的海外贸易利润极高,“其去也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其来也,又以一倍而博首倍之息”。 [8]因此到了唐宋时期诗人笔下就出现“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 [9]的福州港口繁华景象。《闽都别记》中第60回就描述了五代时期福州台江商贾海船贸易的盛况,说“台江上下数千号商船”。元时马可波罗描写闽江码头:“停泊着大批船只,满载着商品……许多商船从印度驶达这个港口。”明代中期在福州设立市泊司,清代又开禁设关,福州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使西南洋诸口咸来互市”,大量对外贸易通过闽江口,成为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重要口岸。
《闽都别记》中记载了大量福建商人依海而富的奋斗史,尤其是远洋航行的发家史。第19回中记载福州南台大洋客吴光“有百万家财”。第29回描写连江商人刘海福年轻时在外国商船上做水手,顺带帮本地人带些货物,后来就自己运货到外国贸易,不到几年就赚了几十万家产,晚年“不复飘洋,将银尽置田产皆本乡地场,周围一眼望之不尽,都是刘家田园”。第167回中描写主人公“他是王姓,有百万家财,父兄皆在海中行钓船”。《闽都别记》中那些漂洋过海的商人们基本上都能发财,虽然旅途艰险,但所到之处都收获颇丰。第144回描写商人林仁翰离开倭国时盘点倭国国王所送的礼物“多是奇珍异宝,及笙管诸乐,悉金玉所造”。第145回在离开烛阴国的时候“国王早遣送奇珍异宝、粮食各物在船”。第179回中商人离开扶余国时,也是“财宝粮食,装原船满载而至”。《闽都别记》中大量的海商故事都描述着大海带来的巨大财富,在这些描述中我们都能看到人们对资本的向往。
内陆文化以海岸为终点,而海洋文化则以此为起点。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土地才是唯一可以依赖的根本,海洋是陆地的结束,只要有一线生机就要在陆地上讨生活,这造就了内陆人民温和保守的性格。而对福建沿海居民而言,海洋却意味着新生,是除了陆地之外更为广阔的选择。相对于民风较为保守的北方和内地,面海而生的福建人更具有开放和开拓意识。
以海洋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赋予了闽人对未知疆域无所畏惧的精神。第183回描写福州长乐商人祝长安“有船行洋贸易”,到渤泥国经商,到港后却触礁破船,只得向当地国王借钱置买,赚了些钱,结果第二次又触礁破船,国王不肯借,只好把亲生儿子作为人质,借钱采买,最后终于“置货往返数回,得息数倍”,才赎回儿子。第261回描述了福建一艘海船失事的故事,“忽遇暴风突起,船被击碎,通船数十人皆溺于水,死活不知”,就剩五个人抱着木头漂流到海岸才侥幸得救。第180回则描写海船险遭鲸鱼吞噬,“海水奔流入洞急如百箭,船舵下转,将流入”的惊险经历。这些描写,虽有作者为求奇而对危险做出的夸饰之笔,但更多的是对探海之人勇敢行为的浓墨重彩的渲染。第238回中贯穿《闽都别记》的灵魂人物铁麻姑曾表示:“万里不为远,三年不算迟,总在乾坤内,何须谈别离。”借她之口,作者对福建当地人民勇于探海的冒险精神、开阔的视野、豪迈的胸襟表达了由衷的赞叹之情。
在对未知疆域无所畏惧的精神引领下,闽商在茫茫大海的波涛之上远航,游离于政治和权威边缘之外。海岸线以外的庞大区域,传统的中央集权很难完全覆盖,只有在船只进港的时候才与政府发生较为密切的关系,因此,相对内陆文化而言,海洋文化有着逃避暴政的传统。“闽越族人的好斗精神,加之海洋文化所激发的进取精神,以及宋元时期惯于海上交通的阿拉伯穆斯林等文化因子的渗入”, [10]闽商养成了敢于离经叛道、勇于铤而走险的独立自主精神。《闽都别记》中对海商逃避暴政的描写在第60回和第125回中。第60回记载五代时闽地国计使薛文杰找了个私通外国的借口将商人吴光的十条商船尽数抄封以后,当地商民早就对薛文杰的横征暴敛感到极度怨恨,听到这消息以后,人人都愤而不平,因此,“台江上下数千号商船来会齐,助吴光反出”。等到官兵奉诏来斩吴光之时,“而吴光之船已出扬子江大洋去矣”。第125回描写吴光在打死地霸李龙以后,就跟他的孩子们将十条大船都装满货物,然后“一同驶至日本倭国”,安排他的五个儿子们“共掌十只洋船在苏州,素往来倭国贸易”,并安排伙计林秀与小儿子在日本“坐庄接货”。海岸文化给闽商带来的拼搏探险精神,贯穿了整个贸易时代。“不仅仅在海洋,作为内陆与海洋的联结点,整个贸易网络遍布山区与江南”。 [11]作为一个重要的贸易中介点,闽地海商不仅掌握了海外贸易的交易权,同时也掌握了大量内地和山区贸易的资源。《闽都别记》中大量描写的商人与山区贸易往来的故事也极大佐证了这一点。
《闽都别记》所体现的开放意识和勇于探索的冒险精神,这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分不开。商人走海贩货的盛行在《闽都别记》中有着充分的描述,文人也豪不掩饰对财富的兴趣,这与当时整个社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历史走向是相印证的。人们对金钱强烈的欲望有了更直接更赤裸的表达。从《闽都别记》中对这些海商形象的塑造上来看,作者对此较多正面积极的肯定。“重商与务实逐利精神是海洋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10]在这样的海洋文化影响下,闽商身上那种逃避暴政、无所畏惧的自由精神和冒险气质得到了更突出的体现。商人形象的大量出现,对冒险逐利观念与行动的推崇,也正是清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时代气息在作品中的表现。因此,《闽都别记》的海洋叙事中,对这些海商形象反抗暴政、无所畏惧的自由独立精神的大量描绘,不仅是现实层面的描述,也是随时代发展而来的超迈开放的海洋文化意识的展现。海洋叙事的这一新形象新发展,也正是海洋文化内涵深化的体现。
三、《闽都别记》中的海洋民俗
《闽都别记》有不少有趣的民间传说和神话传说,这些传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闽地作为沿海地区所具有的独特习俗。“一切文化现象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决定于各民族的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 [12]地理环境往往决定一个地区生活的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从地形地貌来看,福建地区有三个主要特征:“一、山地丘陵广布,二、海岸曲折、港湾优良、岛屿散布,三、江河众多、下游多有冲积平原。” [13]在适应这种海岸线地带独特生态环境的过程中,闽地人民随之衍生出一套相应的认知体系。“在东南漫长的海岸线地带,由于这样的地形地貌,人们以水生动物为象征的水神崇拜文化中,蛇占据主要地位。” [13]可以佐证的是,《说文解字》解释“闽”字云:“闽,东南越,蛇种也。” [14]而《闽都别记》在第353回中就讲述雌蛇化女择婿,并生下一男婴的故事。故事中雌蛇修炼多年能幻化成人,知书达礼劫富济贫,婚后虽现出原形试探丈夫心意,但丈夫并不嫌弃,从此夫妻和谐生活。第82回则描写临水夫人陈靖姑所怀的三月孕胎被蛇首盗食并在斗法中被蛇首在水底拖坠暗害而死。这些故事实际上从正反两面都反映了闽人蛇崇拜的心理。这种崇蛇风俗实际上带有海洋文化的气息。
此外,沿海一带男风之俗在《闽都别记》中也有展现。由于海上贸易频繁,古代福建的海商、水手、渔夫的数量庞大,加上闽地流行女性船忌,即禁止女性上船,因此,海船之上成为清一色的男性世界。第173回描述了一道船上禁忌:“不许携带家小,亦严禁劫掠妇女,如违令,即斩之。”有海盗抢了个妇女偷偷藏在船舱里面,过了没多久被发现,这名海盗就要因为违背禁令而被斩首。清一色的男性生活,加上航海生活的漫长与枯燥,极容易发生同性恋现象。明代沈德符认为同性恋起源于海盗之中,“闻其事肇于海寇,云大海中禁妇人在师中,有之辄遭覆溺,故以男宠代之”。 [15]《闽都别记》中有相应的佐证,其中就写了三个海盗同性恋的故事。第167回中海盗铁英横行海内,却钟情台江都指挥使之子攀桂,后为救攀桂杀入敌群,两人战死一处,死时紧紧拥抱,四五人掰不能开。第175回中海盗林来财为报复江涛“海兔之嘲”,将江涛劫至海船带入舱内奸淫。第229回一群临时起意的海盗将船客都郎“剥得赤条条,欲与轮头轮奸之”,幸亏都郎忽得神助才免遭难。
因为远洋贸易的危险性,富裕人家多收养契儿这一习俗也是福建同性恋盛行的原因之一。“闽人酷重男色,无论贵贱妍媸,各以其类相结。长者为契兄,少者为契弟”。福建的史籍则记载“殷富之家,大都以贩洋为业,而又不肯以亲生之子令彼涉险。因择契弟之才能者螟蛉为子,给以厚资,令其贩洋贸易,获有厚利,则与己子均分”。 [16]《闽都别记》对此也有记载,第37回中黄甫行船时从水中搭救一个18岁的少男,收纳在船,“寝食不离,宛如夫妇”。第52回田杲和归玉两人年过而立尚寝处如伉俪。第56回,艾生引诱冷光要结成断袖之好,“生生世世为弟兄”。第164回、165回写新月与申樾结交为契兄弟,两人动情交往,后来发现申樾是女扮男装最后意外之喜。183回中,祝长安以儿子晓烟为人质向渤泥国借本,“谁知晓烟甚美,番王恋之不舍,以为买断无赎”。除此之外,“曲蹄”这一特殊的靠海靠江而停的船舱中男妓角色,在《闽都别记》中也有记载。比如第109到第111回中林庆云的故事。
古代福建同性恋仅《闽都别记》中就记载了十几对同性恋,涉及同性恋的章回多达70多回。当然同性恋现象并非只因远洋航行而产生与存在,几乎每个阶层和身份都有。从《闽都别记》的主调上来看,忠贞不渝的同性恋感情,是被当做典范来歌颂的,比如铁连环和攀桂为国家战死沙场死后受到祭拜等。古代福建同性恋者生活在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之中,这与东南沿海依托海洋文化而产生的生活氛围不无关系。首先,海洋经济带来的资本发展,使得传统礼教对人的束缚在松脱,民间的氛围相对自由开放。其次,海洋文化用于开拓创新的人文性格也反映在对封建主流文化的叛逆之上。最后,远洋航行所到之处颇广,海船能将人带到各个地方,所以海洋也教人学会了多元化的视角,文化沙文心态没有内陆严重,使得闽人能够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看待一些不寻常事。清代以来,在经济和思想的双重影响下,东南沿海人民对欲望的追求以及对自由的表达相较内陆人士而言更为直接。从这几点上来说,男风之俗与海洋文化也不无关系,因为生活于此处的人们的情感结构、感受生活和观照世界的方式,与海洋生活是分不开的。
四、海洋叙事的猎奇性与写实性
一方面,《闽都别记》中的海洋叙事呈现了一种内在的写实性倾向。小说在反映当时市民生活,再现人们生活场景方面,与整个闽地的历史背景是息息相关的。小说描述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包括黄巢入闽、五代兴亡、宋开泉州城降元、宋元对台湾的开发、明永乐间郑和下西洋驻扎长乐、唐王在闽称帝、郑成功抗荷及降清等,具有讲史性质。第316回、343回叙述郑成功下海发家及受招为官以及抗击荷兰侵略者控制制海权的经历,虽有想象元素,但基本与历史文献记载相吻合。郑和下西洋的出发地为福建的长乐,同时涉及福州、泉州等地,《闽都别记》中涉及郑和下西洋的章节有219、272至275回等处。小说中的写实因素是大量存在的,印证了中国海洋文学从虚幻到写实的发展趋势。
另一方面,《闽都别记》中的海洋叙事呈现了一种鲜明的平民化姿态,这与当时的社会审美是比较一致的。福建沿海地区经济和海外贸易的发展,市民阶层蓬勃发展,展现商业城市里普通人生活境遇的作品就随之大量产生,适应市民阶层审美情趣的拟话本小说的盛行也决定了《闽都别记》的娱乐性。《闽都别记》中有很多关于出海探险的神秘离奇的故事,比如第141到146回描写海船历经大人国、小人国等近10个奇异风情的岛国历险故事;第180回描写海船差点被鲸鱼吞没的故事;第241回描述将日渐消瘦的人肚子中的消麦虫引出,带到海边用油锅煮,就会有海中夜叉来献珠宝。小说中描写闽商海外经商和冒险的故事,还有大量关于遥远的海岛世界奇异的风土人情的描绘,这无疑就是吻合了当时不断兴起的市民阶层的娱乐需求而创作出来的故事。福建沿海地区自古存在的海洋文化自然而然将人们的文学描写对象放在了海洋之上,而与海外不断的扩大交流加深了人们对海洋世界的了解,对海洋文化的这种自信心表现在文学当中,人们大胆书写海洋,想象海洋,在了解认识的基础上再进行大胆的描绘和想象,这些都符合沿海地区已经发展起来的市民的趣味,受到广泛喜爱。《闽都别记》中海洋叙事展现出的猎奇性是与清代福建沿海经济发展密不可分的,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色。
《闽都别记》中多元化的海洋叙事和以各种形式呈现出来的海洋文化价值,无不展示了丰富的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在福建人民与海的漫长关系史中,《闽都别记》中所表现出来的海洋价值取向,表现了清朝时期海洋文学独特的文化特点,意蕴深刻丰富。小说中的海洋叙事,在反映文学审美取向的同时,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清代经济的发展以及随之改变的社会文化的变迁。无论是对海洋观念从想象性元素到写实性元素的深化,还是对海商形象反抗暴政、无所畏惧的自由独立精神的大量描绘,无论是开放超迈的海洋文化所影响的特殊风俗体现,还是海洋叙事猎奇性和纪实性并重的时代特色,《闽都别记》都体现了闽人在经历了海洋交流后实现的多元化的海洋文化价值。这些梳理不仅对探讨福建海洋文学的发展脉络和特征有所裨益,也对研究福建海洋社会意识形态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