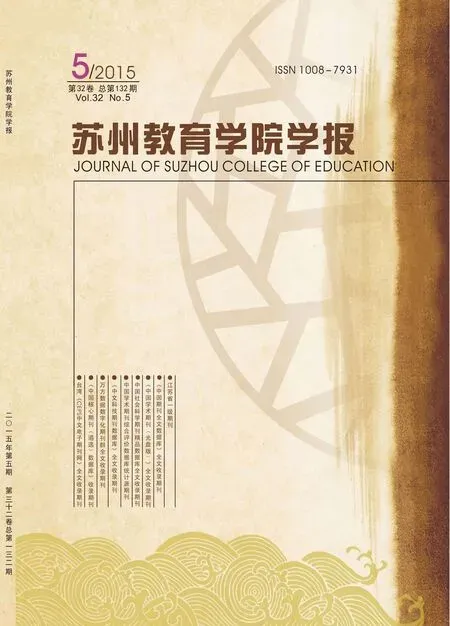加拿大华人文化涵化的历史轨迹
—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金山》
2015-04-10池雷鸣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510632
池雷鸣(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加拿大华人文化涵化的历史轨迹
—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金山》
池雷鸣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在文化人类学视野下对张翎的《金山》进行解读,引入文化“涵化”概念,以聚焦方得法家族的代际差异,并窥探加拿大华人文化涵化的历史轨迹大致呈现出“接触—排斥—回归”的历史线条。华人文化涵化的差异,不仅体现在代际之间,而且还存在于同代之间;在地方性和历史性之中,展现出多样和丰富的华人形态。加拿大华人只要仍将自己归属于华人族群,同样是中华文化的载体,而他们差异性的文化表现,也即意味着中华文化多样的延续。
关键词:《金山》;加拿大华人;文化涵化
一、文化涵化与代际差异
1936年,美国人类学家M.赫斯柯维茨等人曾指出:“当拥有不同文化的个人的群体间进行直接的接触,继而引起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叫做涵化。这个概念说明涵化与文化变迁和同化具有不同含义,前者是涵化的一个方面,后者是涵化的一个阶段。”①转引自马季芳:《文化人类学与涵化研究(上)》,见《国外社会科学》1994年第12期,第11—17页。根据这一在人类学界堪称经典的定义,我们至少可以厘清“涵化”的三个特征:1.文化涵化是一种自然的客观现象,也就是说,只要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文化发生“直接的接触”,那么,自然就会出现文化涵化现象;2.文化涵化因其自然性而必然是一种双向性的互动现象,即你涵化了我,我也涵化了你,但涵化的双向性并非意味着双方的同等关系,其中双方文化的强弱将影响彼此的涵化程度;3.涵化、文化变迁和同化是三个既有关联又有区分的概念,文化的涵化能够引起文化变迁或文化的同化。[1]需要指出的是,文化变迁并非是涵化的一个方面,相反,涵化仅是文化变迁的一个方面,因为文化变迁还包含文化共同体因自身的发明和发现而导致的发展变化。另外,同化指的是族群归属的转变。列宁曾在《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中指出,“同化”即是关于丧失民族特性,过渡到另一民族的问题。换句话说,同化意味着族群甲已经在族群意识上融入了族群乙,并且失去了他们原来的族群认同。而涵化虽可以引起同化,但本身并不能够使发生涵化的双方或多方失去各自的族群认同。总之,涵化强调的是一种向对方的文化特征逐渐靠拢却不会失去族群认同的文化变迁。
在“文化涵化”这一研究视点的观照下,《金山》[2]中的代际差异,不能仅以血缘为基准进行区分,还需要倚重代际之间的文化、社会属性差异,制定综合的代际区分标准。在下面的研究中,我们将以人物的“出生地”和华人文化涵化程度的强弱作为两个基本要素进行代际分界。
是否在中国出生、成长或者是否在加拿大出生、成长,不仅意味着地理空间的更迭,而且蕴含着文化空间的转换,正如Edward W.Soja所言:“我们日益意识到社会、历史和空间的共时性和它们盘根错节的复杂性,它们难分难解的相互依赖性。空间性—历史性—社会性的这一三面的情愫,正在带来的不仅是我们对空间思考方式的深刻变化,同样也是开始导向我们历史和社会研究方式的巨大修改。”[3]所以,在中国出生、成长的方得法、方锦山、方锦河与土生土长的方延龄、艾米之间有关“中国记忆”的方式、清晰度必然存有差异,而“中国记忆”往往又内嵌于个体的成长记忆之中。关于成长记忆对一个人心理发展的重要意义,弗洛伊德在研究达•芬奇的绘画时就曾清晰地表述过:“一个人对他童年时代的记忆的思索不是一件不值得注意的事情,通常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的残存的记忆,恰恰掩盖着他的心理发展中最重要特征的难以估计的证据。”[4]可见,海外华人“中国记忆”的差异将影响他们自我认同的形成以及文化涵化的程度。这样,《金山》中的代际差异即可表现为三代人的差异,即出生在中国,之后来到加拿大的以方得法、方锦山、方锦河为代表的“第一代华人”;在加拿大土生土长的以方延龄为代表的“第二代华人”;第二代华人的后代、以艾米为代表的“第三代华人”。
1928年,普罗普在《民间故事形态学》中提出“叙事功能”的概念并认为,“与大量的人物相比,功能的数量少得惊人”[5]。在我们看来,文化涵化在某种意义上对加华史书写而言也是一种叙事功能,但与普罗普不同的是,与其说我们关注功能,不如说更在乎功能的负载者—人物—如何完成其使命。事实上,正如我们下面即将阐述的那样,每一个人物的文化涵化过程都是不同的,这种差异不仅呈现在代际之间,还体现在同代之间。
在“中国记忆”和“加拿大经验”之间,或者说两种文化模式或多种文化模式之间(比如中华文化、白人文化、原住民文化等),每一代际在文化涵化的程度上都有一定的类似,比如第一代华人大多有牢固的中华文化根基,涵化程度相对较弱,可称为“接触的一代”;第二代华人,一方面面对着富有浓郁中国色彩的家庭文化,一方面又面临着日益增加的加拿大经验的种种考验,致使他们处于两种甚至多种文化的夹缝处,涵化的程度相对较高,但涵化的过程充满挣扎与迷惘,可称为“迷惘的一代”;第三代华人有着牢靠的加拿大经验,与第一代华人的文化涵化方向相反,他们的涵化是面向中华文化的,所以可称为“寻根的一代”。而在涵化程度相似的前提下,同代之间在涵化的方式、领域、态度或情感上又呈现出诸多差异,比如第一代华人中,方得法是经济方面的涵化,方锦山是伦理方面的涵化,方锦河是政治方面的涵化。
张翎的长篇小说《金山》是一部涵盖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加拿大华人历史的力作。自面世以来,学界对此研究与解读已颇多。本文试图引入文化人类学中的“涵化”概念,以聚焦方得法家族的代际差异,并窥探加拿大华人文化涵化的历史轨迹。
二、《金山》中三代人的文化涵化
(一)方得法、方锦山、方锦河:接触的一代
在加拿大华文文学史书写中,作为大洋彼岸的开拓者,由于“中国记忆”的亲历性,第一代华人都一致地倾向于坚守自己的中国认同:方得法、方锦山等仍然怀有叶落归根的传统思想,即便方锦河已有了落地生根的想法,但也并没有打算放弃自身的中国认同。尽管如此,第一代华人并没有固守已有的文化价值观念,而是不同程度地实现了与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自然接触。纵观《金山》的文本语境,文化涵化在华人社会文化生活各个领域中的不同表现,才是第一代华人文化涵化的中心。
1.方得法:经济交往与文化涵化
《金山》卷首那首广东童谣:“喜鹊喜,贺新年,阿爸金山去赚钱;赚得金银千万两,返来买房又买田。”[2]1从某种程度上讲,可看作小说的缩影。从叙事功能上讲,一位家庭成员去金山赚钱,“返来买房又买田”,不正是小说里一个主要的功能项吗?但在小说众多人物形象中,只有方得法才是这一功能的真正负载者。
方得法在加拿大的人生历程,除去他和金山云的暧昧故事外,即可简化为卖炭、修铁路、第一次开洗衣馆、卖洗衣馆回家、第二次开洗衣馆、卖洗衣馆资助保皇党、第三次开洗衣馆、暴乱后申请赔偿、开办农场、破产申请、开烧腊店等一系列经济行为和事件。其间唯一算得上异族交往的事件,即他与亨德森的友情。从修铁路劳资纠纷中的相识到洗衣店里的相遇,再到太平洋车马店的承包,法庭作证,聘请律师获取洗衣馆的赔偿,农场破产保护申请,甚至锦河到亨德森家做佣人等一系列两人之间的交往行为来看,几乎全部(不包含唐人街白人暴乱出手相助)是在经济交往中完成的。然而,方得法不仅是“赚钱”的负载者,还是文化涵化的承载者,可是在他加拿大的故事中,似乎并没有承载这一功能。这实际上是小说虚实相映的叙事策略,它有意将其掩藏在大洋彼岸的“碉楼”意象之中,却又在洗衣馆(方得法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场所)的位置变迁上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
方得法的第一家洗衣馆“开在唐人街的紧边缘上,一只脚踩在唐人的地盘里,一只脚踩在洋番的地盘里”[2]66,而第二家“却开在了洋番的地界”[2]109,虽然紧接着叙述者就交代出“阿发的店铺在唐人街之外,吃住却依旧在唐人街”[2]122,但还是从侧面呈现出方得法对白人文化的自愿、开放心态,尽管裹扎在经济交往的限度之内。如果说这是方得法文化涵化一个小小的提示,那么在“碉楼”意象所蕴含的文化意味中,则可以窥探出他的文化涵化的风貌。
方家的碉楼是广东开平一带修建得最早的碉楼之一,虽说“建这样的楼,第一是为了防贼防匪,第二是为了防水”[2]67,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但从还未落成的那一刻起,就因其与中国建筑的差异(五层楼的高度、建筑材料、“巴洛克式门框”、“罗马式窗楣”等西式建筑风格)而成为了一道靓丽的地理景观。在文化地理学家迈克•布朗看来,地理景观是一个价值观念的象征系统[6],而西式外观、中式布局的碉楼就是一个中西文化杂糅的象征系统,从建筑图纸到水泥、云石、玻璃、厨厕用具,甚至连窗边门檐上的雕刻花纹设计,都是由方得法亲自选定,所以可以肯定地说,碉楼象征着方得法在经济交往中出现的文化涵化。在文化人类学看来,一般文化涵化出现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自然发生的,一种是强制实行的。而作者采用经济交往为实、文化涵化为虚的叙事策略,正是为了突出文化涵化的自发性。
2.方锦山:伦理碰撞与文化涵化
……如阿母执意不肯放妻来金山,可否让锦山儿先过埠?农庄新开张,万事艰难。阿林已是五旬之人,吾亦四旬有加,急需后生帮衬……[2]148
从方得法的这份家书中可知,帮父亲挣钱是方锦山来到加拿大的主要目的,但事与愿违,方锦山到后不久就因断辫风波而离家出走,后又因私留猫眼再次离家出走,最后因腿上有疾而无力赚钱。可见,“赚钱”或者“帮父亲挣钱”不再是方锦山所承担的,也就意味着,他文化涵化的轨迹将不会重走父亲的旧路,而是即将开辟出一条“伦理”之途。
从方锦山到达加拿大的那一刻起,叙述者就在精心营造一种陌生、紧张的父子关系。方锦山眼里的阿爸,并不是回乡时的阿爸,甚至真假难辨,“不知这个阿爸是真的阿爸,还是回乡时的那个阿爸是真的阿爸?”[2]176而在方得法眼里,自己的儿子也是一样的陌生:方锦山不像别的金山客的孩子,也不同于年轻时的自己—“这个家太小太暗太安静了,怕是拴不住这个儿子的”[2]183。这种父子之间双向的陌生感,致使他们“干涩对峙”,终于爆发了那场互不相让的“鞭打”风波。似乎整个叙事正朝着“弑父”的方向发展,然而方锦山所承载的叙事功能,再次超出了我们的阅读期待,并非是“弑父”,而是相反的“敬父”。从后面的“断辫” “逃婚” “相遇”等事件来看,方锦山的“敬父”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畏惧,二是捍卫,三是延续。
“平生头一回,他懂得了什么叫惧怕。”[5]196而这“惧怕”的源头,就是“断辫”。由于方锦山的革命意识,辫子对他并没有多大的意义,然而“这根辫子是阿爸的心,阿爸的脸面,少了这两样东西阿爸就活不下去”[2]196。也就是说,在方锦山的心中,辫子是阿爸的象征,也是家庭伦理的象征。可见,方锦山因“断辫”引起的“惧怕”实际上是一种伦理意义上的敬畏。他可以对亲情隔膜沉默不语,也可以偷偷践行革命理念,但是不敢也不愿明目张胆地有悖家庭伦理。当违背行为发生的时候,“他若丢了一只手,一只脚,哪怕一只眼睛,他都可以回去跟阿爸交差。可是他偏偏丢的是一根辫子”[2]196。他只能选择出走,并期待着一条新的发辫来填平罪感的深渊,以便与父亲团聚。
怀揣着对家庭伦理的畏惧之心,因偶然的机缘(被保皇党扔入莎菲河之后,为桑丹丝的阿爸所救),方锦山来到了印第安部落,随即开启又关闭了一条文化涵化的新径,即中华文化与印第安文化的接触。
所谓“开启”,是指方锦山在与印第安人紧密交往之后,不仅改变了原初对印第安人“割头皮,挖心,用人牙齿做项圈”[2]203等野蛮的刻板印象,而且在听了桑丹丝所讲的中国外公离开外婆坐船回中国的故事之后,对“红番”产生了同情之心—“只觉得那红番并不真的野蛮,倒是那个淘金的,反而有些薄情寡义”[2]212,甚至在最后即将离开印第安部落时对桑丹丝产生了一丝爱恋之情—“他跨进独木舟,伸出手来拉她,她上来了,他却依旧没有松手。她没有挣扎,只是任她的手在他的手里捏出了温热湿黏的汗水。”[2]222但当方锦山得知自己要和桑丹丝成婚的时候,一句“祖宗,不认你的……”[2]222的逃婚理由又关闭了刚刚开启的文化涵化之门。同时,“祖宗,不认你的”也暗示出方锦山对家族纯正血统的考量,也就意味着,他的逃婚源于对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捍卫。
从晚年方锦山对桑丹丝的思念行为(在报上刊发寻人启事、梦境、梦呓等)来看,他对桑丹丝的感情是真实的。但等桑丹丝真的出现在他面前,并期待重续前缘的时候,他再一次选择了“逃离”,小说这样描写二人相遇后分别的场景:
锦山送桑丹丝走到门口,桑丹丝说了一声再见,眼里分明有着期盼。他知道她期盼的是什么,可是他却偏偏不能给她期盼的理由。他想她想了十几年,而在终于见到她的时候,他情愿他们一生没有再见过。[2]405
“偏偏不能”道出了方锦山对桑丹丝感情的无奈和决绝,却单单未给出那个“理由”。这实际上又是小说的故伎重演,它在桑丹丝故意留下的照片背面的一行字—“保罗五十七岁生日与伊恩合影,1970年3月22日”[2]405—中印下了能够寻找到理由的蛛丝马迹。当方锦山意识到保罗很可能是自己的儿子时,“他追出门去,大喊了一声:‘桑丹丝!’”,不顾(很可能根本就没有听见)桑丹丝的约会期待(“你最终,还是决定约会我了,是吗?”),将照片举到桑丹丝眼前,一字一句地问“保罗,是谁的孩子”之后,“桑丹丝怔了一怔,笑容渐渐凝固成蒺藜一样的皱纹”。[2]405在我们看来,方锦山再次“逃离”的理由就在桑丹丝的“蒺藜一样的皱纹”里。“皱纹”是一生的见证,桑丹丝一生都期待、渴望得到方锦山的感情,却一生都被阻隔在方锦山的“祖宗”和“儿子”之外。“儿子”对于方家的重要性,在小说中被反复强调,但又一个一个地相继死去(方耀楷溺水而亡,谢怀国被日军炸死,方锦河战死欧洲战场,方得法去世),后来方锦山也毫无征兆地去世了,却是在得知有了骨血(保罗)留世之后。方锦山的遗言只有两个字—“木棉”,在此处应作为“根”的象征理解。
不得不说的是,尽管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成功地阻隔了方锦山和桑丹丝之间的感情进展,但却无力阻碍中华文化的涵化进程。保罗作为方家骨血的存在,实现了方家几代人梦寐以求的血脉延续,然而吊诡的是,保罗的混血儿身份,实际上也在瓦解血统纯正的家庭伦理理想。在血脉延续和血统纯正之间,对一生都在敬畏和捍卫家庭伦理的方锦山而言,他应作何处置?方锦山在得知保罗—方家唯一的儿子—存在的当天夜里,就毫无征兆地死去,仅以“木棉”两字作为在世的最后留存。显然,在“木棉”这一意象中存有方锦山的应答。作为文学意象的“木棉”,我们并不陌生,在舒婷的《致橡树》中,木棉作为独立女性的象征,广为人知。而在此处的文本语境中,木棉因其是岭南一带的代表性植物(广州市花)而具有“故乡” “思乡” “家”的文化意蕴,同时又有指代“保罗”之意,将二者相关联,就可衍生出“家族之根”的伦理意蕴。
可见,在方锦山最后时刻对保罗作为家族血脉延续的承认中,因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阻挠而被迫关闭的文化涵化之门又再次打开。然而,方锦山的文化涵化之门从开启到关闭再到打开,却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意味着一种新的中国家庭伦理文化的诞生。
3.方锦河:国家意识与文化涵化
在文化涵化的领域中,正如方得法与经济、方锦山与伦理之间的关联那样,如果将国家认同归属于政治范畴的话,方锦河与政治之间的关联更引人关注。
政治视域下的国家认同,核心内容是指海外华人获取所在国的公民权,享受公民权利,并承担公民义务,在心理上、感情上主观地意识到自我是国家的一份子,意识到个人与该国家息息相关。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认为,方锦河与其他人物相比,其独特之处在于,在文化涵化的过程中,他萌发了对加拿大的国家认同意识,并以实际行动(参军)履行了作为加拿大公民应尽的义务。
当阿爸提到有钱回开平老家的时候,“锦河觉得阿爸的话有些道理,又不全有道理。其实在金山呆的久了,就知道金山也有金山的好呢—只是他不能把这个话告诉阿爸”[2]261。金山的“好”,如同一颗种子,经过和亨德森一家朝夕相处的25年的成长,终于使金山具有另一处家园的意义。在方锦河对四千加元的遗产规划里,如果说,既给阿妈在开平买田,又给阿哥在金山买房,意味着他拥有“开平是家,金山也是家”的双重家园意识,那么,最后他把四千加元捐给中国买飞机,而自己以加拿大的公民身份参军,就意味着他实现了由“家”到“国”的转换,即他拥有双重的国家意识。
虽说方锦河有“跟阿爸回去” “还是留在阿哥身边”的困惑,但并不意味着他陷入了身份认同的困境,因为从文本语境来看,中西文化冲突显然不是他与亨德森一家25年来一起朝夕相处生活中的障碍。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相处还是一种相互交往中的促进。在方锦河与亨德森一家的交往中,有两处涉及种族歧视(或者说中西文化冲突)的情境:一处是实写,讲方锦河被白人孩子的石头所伤;另一处是虚写,讲家里的中国佣人给珍妮带来的成长的烦恼。而这些种族歧视的情境是方锦河逐渐融入亨德森一家的背景,小说曾通过珍妮的心理活动形象地将他对亨德森一家的影响比作一棵树的成长:
珍妮知道这个叫吉米的中国人,刚来她家的时候,不过是一株小苗。没有人想到这些年后,这株小苗已经长成了一棵枝桠繁茂的大树。这些枝桠深入到家里的每一个角落,若砍了这棵树,她的家到处都是树根留下来的瘢痕,填不满,也抹不平。[2]292
可见,在方锦河的文化涵化过程中,并没有涉及“我是谁”的问题,也就无从谈起身份认同困境了,但从他的家园意识和国家意识的双重性来看,他具备了新的国家认同,然而“无奈卑诗省政府不予华裔以选举资格,华裔不得参军报效国家”[2]303,也就意味着,方锦河留下还是回去的困惑是因新的国家认同和与现有法律政策相冲突而引起的,换句话说,方锦河的文化涵化产生了新的国家认同,但还没有达到引起认同危机的强度。“真”的身份认同困境以及文化认同危机要到第二代华人的文化涵化过程中才会出现。
(二)方延龄:迷惘的一代
《金山》中的方延龄,作为第二代华人的代表,在其文本语境中凸显了她的“土生土长”性(下文的阐述中将称之为“加拿大性”),或者说是对原乡的疏离。方延龄的原乡疏离裹挟在方锦河的家园意识中:
当然,给阿哥买房的最重要原因是延龄。延龄是在金山的泥土里栽下的种子,就着金山的日头和风水长大,若把延龄拔起来种到开平乡下,怕是死也不肯的。[2]300
可见,“加拿大性”已经成为方延龄毋庸置疑的特质,是其区别于第一代华人的显著社会特征。这一代际差异的存在预示着她的文化涵化过程将是一番别样的旅程。虽说第一代华人的文化涵化在经济、伦理、政治等领域有着各自的表现,甚至出现了“叶落归根”到“落地生根”家园意识的转换,但因其牢靠的中国记忆,文化涵化并没有影响他们的自我认同,在涵化态度①“涵化态度”是美国人类学家J.W.贝里的观点,他将其分为同化、分化、整合和边缘化四种涵化态度。他认为,在持何种态度上取决于两种不同方面的相互作用:1.愿意保持并反对放弃原有文化(如认同、语言、生活方式等)的程度;2.愿意与异文化进行日常接触,反对只在本文化圈内活动的程度。根据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贝里将涵化态度分为四类,即同化现象、分化现象、整合现象和边缘化现象:1.当一文化模式中的个人不愿保持原有的认同而愿意与另一文化模式进行密切交往时,则会出现同化现象;2.与上述现象相反,若执意坚持其固有的文化价值观,同时有意回避与其他文化发生联系,则出现分化现象;3.若既保持了原有的文化特征,又不可避免地同异文化相接触,就会出现整合现象;4.若既无意保持原有文化,又不愿与异文化相联系,会出现边缘化现象。参见马季芳:《文化人类学与涵化研究(上)》,见《国外社会科学》1994年第12期,第11—17页。上也多表现为整合现象;然而,在方延龄的涵化过程中出现了涵化的消极影响:个人在“加拿大性”和“中国性”的强烈冲突中逐渐丧失自我,为自己的身份混乱而感到迷惘。
对于海外的中国人而言,万水千山也阻断不了他们对故乡的无限眷恋,反而会积蓄他们内心深处落叶归根的情结。方得法、方锦山甚至方锦河都莫不如此,当这种眷恋和思绪由于战争、移民政策、种族歧视、荣归故里的心理因素等种种原因而无处依附时,钱就成了唯一的寄托。即便自己在“金山”的世界里生存窘迫,也要让故乡的家人们风光生活。正是这种心理,甚至可以说这样的信念,使他们把钱雷打不动地寄往故乡。
但对于土生土长的方延龄而言,上一代对故乡的眷恋之情已经被“hate”所替代,延龄要写的不仅是一句话,延龄还有很多很多句话排在这句话后边,急急地等待着出场。延龄想说:“奶奶和锦绣姑姑你们自己不会挣钱吗?你们每张照片上都穿得很美丽,可是我在这里却连一件新大衣也没有,因为我阿妈每个月都要把钱省下来寄给你们。”延龄还想说:“我同学都笑话中国佬一个毫子掰成两个花,可是我们家却把一个毫子掰成四个花,都是因为你们。”[2]322那块魂牵梦绕的乡土已不再具备“养育之根”的寓意了,反而成了亟待斩断的附庸。如果说,故乡对于海外华人而言是维持自身中国性的源泉,思念故乡,就是保留自身的中国性,那么对于方延龄而言,故乡是令其陷入自身困境的深渊;排斥故乡,就是排除自身的中国性。对她而言,故乡已经演变为一种符号、一种文化场:阴暗的小屋、昏黄的灯光、争吵、麻将、焦黄的牙齿、烂英文、餐馆油烟气味、破旧大衣等等。这些不仅意味着物质上的窘迫,还预示着精神上的压抑,令其对自身的中国性产生了焦虑。但正如马克•柯里所说:“身份是关系,即身份不在个人之内,而在个人与他者的关系之中。”[7]也就是说,因原乡的疏离而产生的对中国性的焦虑,还不足以改变方延龄的身份认同,还需要从“与他者的关系”中寻找她的身份意识转变的原因。在方延龄的世界里,庄尼和教导主任沙列文太太可以说是“他者”的代言人:
“我们必须约定一个时间,和你的父母开一次会,谈谈你的补考和学习计划。”沙列文太太说。沙列文太太肤色很白,白得脖子上额上都是隐隐的青筋,沙列文太太说话的时候,那些青筋蚯蚓似的爬动起来,“假如希望今年毕业的话。”[2]339
沙列文太太的语言中,渗透着一种话语权力:她决定着方延龄能否毕业,而这一权力与她的肤色息息相关,这一切给方延龄带来了恐惧感:“父母?她那个瘸了一条腿,牙齿被烟熏得焦黄,英文烂得跟淘米的箩筐似的父亲?她那个衣裳头发上沾满了餐馆油烟气味的母亲?让这两个人在众目睽睽之下走进沙列文太太的办公室?”[2]339对父母的厌恶和贬低,是方延龄恐惧感下的一种自我投射,隐喻着她在“白色权力”下严重的自卑意识。这样就表现出了方延龄在以父母为代表的中国性和以沙列文太太为代表的白人性之间的双向焦虑和疏离,也隐喻着第二代华人在成长过程在自我身份寻找与定位中的迷惘。此刻,庄尼的出现,预示着一个新的世界的发现。如果说沙列文太太是一个令人恐惧的不敢靠近的“他者”,对于方延龄而言,庄尼就是一个富有吸引力、令人憧憬的“他者”:
庄尼是班级里个头最高最壮硕的一个男生。庄尼的头发是亚麻色的,带了些乱乱的卷子,尤其在下雨落雾的天气里,庄尼的额头上就会出现一串小圆圈。庄尼的校服,很少规规矩矩地穿,或是露出一截袖子,或是领口随意地开散着。庄尼还敢在华生小姐去盥洗室照镜子梳头的空当里抽烟。庄尼抽烟的时候眯着眼睛,头仰得高高的,仿佛嘴里含着的是一个世界。[2]317
一句一个“庄尼”的修辞方式表达出庄尼在方延龄眼中新世界的意义。在这个世界里,有着与熟悉的中国气息迥异的新奇情调,并且充斥着反叛的青春气息。新奇,是那个像装朱古力的铁罐一样压抑的、陈旧的家所匮乏的;而反叛,是那个充满“白色权力”威吓的学校所忌讳的。正是庄尼的召唤,最终使方延龄打碎了铁罐,逃离了学校,开始了“穿着溜冰鞋”的生活:
从一个小镇流浪到另一个小镇,用不着知道街道的名字,用不着认识邻居,还没有把地皮踩热的时候,已经在另一个省的地界了。每天都是在不同的屋檐下入睡,醒来时看见的是另一片天。[2]340
这是对中国性和白人性双重疏离类似于青春宣言式的理想。然而,事实上,从方延龄一生囿于“他要的是白妞”的肤色焦虑进而导致无婚姻的生活状态来看,她的生存理想仅仅实现了一半,即对中国性的疏离。无论是从自身法国式的形象自塑,还是“后来跟的男人都是白人,在家里,在工作场所,说的都是滴溜溜的英文”[2]3以及对女儿艾米“高鼻梁,深眼窝,栗色头发,棕色眼睛,皮肤白得几乎接近贫血儿童。假如不仔细看,很难在那张脸上看出任何黄种人的特征”[2]395的外貌的欣喜以及西式培育和要求上来看,方延龄对中国性的极度排斥实际上体现出其自我西方化的人生策略。然而,方延龄的自我西方化依然无法实现“穿着溜冰鞋”的理想,正如庄尼所言,“走到哪里,也走不出别人的眼睛”[2]348,在他者之眼中,方延龄永远都是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等她在外流浪十几年再度回来之后,青春的梦想已经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支离破碎,她只能将白化的梦想寄托在自己的女儿身上:“我做中国人,吃了一辈子亏,总不能让艾米,还接着吃亏。”[2]402
可见,方延龄不幸的一生呈现出对白人性的最初疏离,到渴求同化,再到最终不可求的人生轨迹,而这与白人文化的涵化过程是在对中国性的排斥中完成的;也就意味着,在白人性和中国性的二元对立中,方延龄彻底否定了中国性,最终臣服于白人性;但正如她的婚姻缺失所寓意的那样,这种单一性的执迷追寻,注定是一个自我认同的残缺之旅,或许生命最后时刻语言的神秘复苏,是她迷惘航程中最后的灯塔。
(三)艾米:寻根的一代
在加拿大华文文学史书写中,《金山》中的艾米是目前为数不多的第三代加拿大华人形象。她的文化涵化过程与前两代华人相比,颇有些独特。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尝试着阐述每一代华人文化涵化中的“共性里的差异”:第一代华人各自的涵化领域和第二代华人不同的消极涵化结果,然而两代人之间却有一个不可辩驳的共性,即他们显著的中国性特征,尽管第一代人是中国性的守护者,而第二代人却是中国性的遗弃者。正是这一共性的存在,映照出第三代华人艾米的独特,即中国性的缺失。艾米的这一独特性,在小说的开头就得到很好的展现:
当栗色头发棕色眼睛的艾米拨开喧嚷的人流,在那块写着“方延龄女士”的牌子跟前站定时,接机的人吃了一惊,对看了一下,满眼都是问号:“怎么来了个洋人?”[2]1
艾米的独特性在他者的吃惊和质疑中凸显而出,即已有的生理属性(外貌特征)与应有的文化属性(姓名“方延龄”所包含的文化意蕴)的冲突;换句话说,在他者眼中,艾米的外貌特征已不具备中国性,这正如她的母亲方延龄所愿。而艾米的中国行,与其说是受母亲方延龄的委托,不如说是被她胁迫后的不情愿之旅。当男友马克送机的时候对她说这将成为她的寻根之旅时,艾米冷冷一笑,说:“像我这样拥有零位父亲,零点五位母亲的人,根是生在岩石之上的半寸薄土里的,一眼就看清,还需要寻吗?”[2]326可见,自我意识中的艾米,也没有将中国性与自己关联在一起。于是,艾米中国性的缺失将意味着她的文化涵化之旅将出现由西向东的转换,即是说,与其他华人不同的是,中国文化将成为她的接触文化。
实际上,艾米与中国文化的接触从小就已经开始,毕竟她的母亲和外公是中国人,甚至在艾米五岁的时候,外公还和她一起画过家族树。但记忆中一切中国文化的痕迹都被母亲方延龄的自我西方化给洗涤掉了,最好的例证就是语言。艾米从小并不会中文,后来学习中文,“既非出于兴趣,也非出于感情”,而是为了“较为轻松地拿到学分”,因为她多少有一点汉语基础。而这有限的汉语基础,也并非来自她的母亲—“母亲在她年轻的时候从来对她只说英文”,而是“有好几个假期都在一家中餐馆端盘子,就是在那里,她捡拾了一些零星的汉语知识”[2]327。可见,尽管很多人认为语言与文化是血与肉的关系,比如Kramsch就认为:“一个社会群体成员所使用的语言与该群体的文化身份有一种天然的联系。”[8]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认同和族群大部分是经由语言建立起来并加以维持的。”[9]但对来中国之前的艾米而言,会讲地道的汉语并未对她的社会认同和文化身份造成多大的影响,中国并不是她的根,华人也不是她的族群和文化身份。她之所以声称自己有“零点五位母亲”,或许与方延龄只赋予了她血肉,却没有给予她身份认同有关。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再来回顾她和欧阳的对话:
欧阳对艾米眨了眨眼,说:“看来你已经开始对这里的事情产生兴趣了。”艾米说:“我对世界上所有的社会现象感兴趣,这里和那里并没有区分。”[2]5
从中可以体悟到,原本那种世界公民的洒脱感逐渐地被无根的漂泊感所替代。以故事时间为基准,从艾米1961年第一次出现(5岁)到2004年再次出现,中间缺席了40余年,正如小说人物欧阳所言:“方家的历史,我还有一个大洞需要填补。作为方得法第四代唯一的后裔,我对你成人以后的故事所知甚少。”[2]408尽管在现实叙述中,艾米的三言两语就令欧阳产生了满足感,“谢谢你,方家的故事,终于,完整了”[2]409。但在我们看来,艾米所留下的叙事空白,还远远没有填补。正像我们前面就已经表明的那样,张翎在“留白”的同时,总是有意或无意地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在此处,艾米的婚恋就是很好的痕迹。
艾米在遇见马克之前是从未结过婚的,“一辈子都在和一个又一个无赖鬼混”[2]409,甚至对婚姻表现出一种恐惧感,“艾米之所以同意马克搬进来,是因为经过一年多考察,艾米看出马克并无求婚的意思—这叫艾米放了心”[2]325,但在解释艾米为什么不结婚时,无论是艾米对马克的解释—“基因,可能是我们家的基因”,还是叙述者“善意的提醒”—“艾米家族的女性,似乎都与婚姻无缘”[2]325(指猫眼、方延龄和艾米),实际上都呈现出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从整个文本语境来看,《金山》中几乎所有的婚恋(方得法和六指,方锦山和桑丹丝、猫眼,方锦河和买菜的小姑娘、区氏、亨德森太太,亨德森夫妇,方延龄和庄尼等一个又一个白人,艾米和一个又一个无赖等)无一例外都是残缺的,但如此众多的“残缺的悲情”却未必都要以爱情的圆缺为叙事的中心;换句话说,尽管瓦西列夫曾指出:“如果男女双方的亲昵结合不是以爱情为基础,他们繁衍后代却并不彼此相爱,有意地把个人利害或者崇尚虚荣的偏见置于自然规律之上,那他们就是对人类、对未来的人们犯下了过错。”[10]但在婚姻的殿堂中陈列的未必都是两性的爱情,某些时候还可以是族群的文化,至少有关方延龄、艾米的婚恋书写是这样。
我们认为,艾米的婚恋圆缺与其中国性的得失之间存有隐性却明显的映照关系。在小说即将结束的时候,在得知艾米和马克要在碉楼举行婚礼时,我们所获得的阅读意外,一点儿都不比欧阳少。两个独身主义者,尽管独身原因各有不同,但突如其来的结婚,着实让人多少有点儿理不清头绪。然而,只有将婚姻与中国性联系在一起时,我们才能领悟这突如其来却又“蓄谋已久”的妙处。
从《金山》的目录中,我们即可窥见小说对对称结构审美效果的精心营造,这实际上也是张翎小说一贯的叙事风格,而在此引起我们兴趣的是“引子”和“尾声”中有关“吃惊”的首尾相照。“引子”中,“吃惊”与艾米中国性缺失的关联,前文已经有所表述,而“尾声”中,欧阳在得知艾米马上要在碉楼里举行婚礼的时候,“又吃了一惊”,这一次是否又与艾米的中国性有关联呢?答案蕴藏在碉楼意象之中。在前文有关“碉楼”意象的解读中,我们已经从碉楼的西式装饰中得出了方得法在经济领域中文化涵化的观点,而在此刻的语境中,它将象征着艾米文化涵化中中国性的回归。
正如她亲手砸开被岁月侵蚀掉的碉楼大门一样,艾米在碉楼里的清点过程,也渐渐打开了在母亲方延龄那里关闭的中国性的大门。当艾米“意外地发现了那几十封书信,看见了她的外祖母抱着她的母亲站在无名河边微笑的照片时,根的感觉猝不及防地击中了她”[2]326。自此,她再也不是一个无根的漂泊者了,甚至“几乎要对全世界承认,她身上具有一半的中国血统”[2]409。此刻,碉楼已经成为一个中国文化的象征物、一个文化意义的载体,成为艾米自我认同的场所。
可见,无论是“吃惊”的首尾相照,还是碉楼意象在历史与现实中无言的穿梭,都是作家有意识的审美建构,而婚恋与中国性缺失之间的映照也绝非无稽之谈。总之,艾米的中国行,确如其男友马克所言,是一次意义非凡的寻根之旅,但它的意义,不仅仅是个人的,更是族群的。
三、多样性文化的延续
在分析艾米中国性的缺失时,我们已经指出了母亲方延龄的中国性排斥对艾米产生的影响,而实际上,艾米中国性的回归也与方延龄相关。
自从79岁生日那天中风以后,方延龄“竟将她的英文一把抹没了”,说起了“荒腔走板的广东话”,而且性情大变,无论在康复医院,还是养老院,“每到一处,无不大吵大闹”,直到“转进了一家华人开的养老院,话语通了,情景似乎得了些缓解”[2]3-4。这一语言的突然回归现象与她以往对中国性的排斥姿态形成了鲜明而又强烈的对比,正如艾米令人吃惊的婚礼一样,它也意味着方延龄中国性的突然复苏。而正是由于这中国性复苏后的胁迫①对中国性复苏后的“胁迫”应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对方延龄的内在胁迫,从她不停地嚷嚷说“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即可看出死亡威胁对文化根意识的深层召唤;二是对艾米的外在胁迫,方家唯一可寻的传人应尽的责任与义务(之所以说艾米是“可寻的”方家传人,是因为方家的传人里还应有桑丹丝的儿子一脉,只不过这一真相为历史所掩藏)。,艾米才开启了中国的寻根之旅。
至此,我们已经描绘出了加拿大华文文学史书写中华人文化涵化史的历史轨迹。它大致呈现出“接触—排斥—回归”的历史线条,正如我们早已提醒的那样,华人文化涵化的差异,不仅体现在代际之间,而且还存在于同代之间,在地方性和历史性之中,展现出多样和丰富的华人形态。而在众多的华人差异之中,仍然保留着一个恒量,即不同时空下的华人在族群认同上的同一,陈志明认为:“一个人可以是华人,但可以通过不同的文化方式来表达该认同,取决于这个人的社会化和本土化经验。人们可以自认为华人,但在文化方面华人存在不同的类型。在这个意义上,所有识别为‘华人’的人都是华人。理解不同的成为华人的途径(这常是不同的本地化所产生的结果),可以有助于理解自己的‘混合’身份,并且不必接受任何关于华人的固定的定义。”[11]也就是说,华人,这一建立在族群认同上的文化身份,是流动性、丰富性、复杂性、单一性和稳固性的混合体。
事实上,不管因地方性和历史性的经验造成了多大的华人文化认同上的差异,只要他们仍将自己归属于华人族群,那么他们同样是中华文化的载体,而他们差异性的文化表现,也即意味着中华文化多样的延续。
参考文献:
[1]胡夏,胡炳章.文化涵化与民族关系[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3(5):119-123.
[2]张翎.金山[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SOJA E W.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M].陆扬,刘佳林,朱志荣,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3.
[4]车文博.弗洛伊德文集:第7卷[M].刘平,译.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86-87.
[5]普罗普.民间故事形态学[M]//叶舒宪.结构主义神话学.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7.
[6]布朗 迈克.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宋慧英,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25.
[7]柯里 马克.后现代叙事理论[M].宁一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1.
[8]KRAMSCH C. Language and cultur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65-126.
[9]GUMPERZ J J, COOK-GUMPERZ J. Introduction:language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social identity/language and social identity[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7.
[10]瓦西列夫.情爱论[M].赵永穆,范国恩,陈行慧,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362.
[11]陈志明.迁徙、家乡与认同:比较文化视野下的海外华人研究[M].段颖,巫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66.
(责任编辑:石 娟)
The Historic Track of Canadian Chinese Acculturation: On Gold Mountain Under the Horizon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CHI Lei-m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The paper interprets Gold Mountain by Zhang Ling under the horizon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acculturation”. The paper focuses on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Fang Defa family, and detects the historical track of Canadian Chinese acculturation, which shows the pattern of “contactrepulsion-regression”. The acculturation differences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are embodied between different generations, and exist among the same generation as well, which reflects diversity and rich situations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terms of the local and historic elements. As long as continuing to belong to Chinese ethnic group, Canadian Chinese are also carriers of the Chinese culture,while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their performance means the continu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diversity.
Key words:Gold Mountain;Canadian Chinese;acculturation
作者简介:池雷鸣(1984—),男,河南虞城人,博士,博士后,研究方向:海外华人诗学、华人华侨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1&ZD111);2014年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二五”规划课题(14G38);第56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4M562250)
收稿日期:2015-05-25
文章编号:1008-7931(2015)05-0052-09
文献标志码:A
中图分类号:I2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