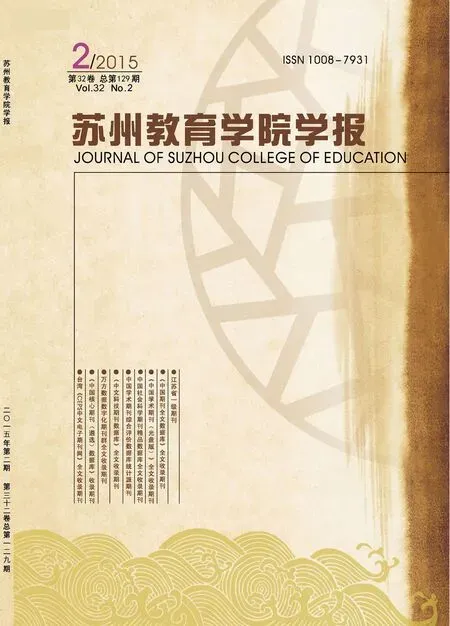泰州儒家学者学习思想管见
2015-04-10张树俊
摘 要: 泰州历史上的儒家学者思想非常活跃,在宋、明、清三朝以胡瑗、王艮、黄葆年为代表的思想家们大胆进行理论创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泰州儒家学者的创新根植于他们博学、兼收、师友等学习思想,即主张扩大视野、三教合一,强调学术融合、亲师取友,以获得全面的知识、增长学习者的实际才干。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931(2015)02-0071-03
收稿日期: 2014-11-17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科联研究课题(13SXH-085)
作者简介: 张树俊(1957—),男,江苏姜堰人,教授,研究方向:历史文化。
Insights into the Scholastic Concepts of the Confucian Scholars in Taizhou
ZHANG Shu-jun
(CPC Party School of Taizhou, Taizhou 225300, China)
Abstract:Active thoughts occurred among the Confucian scholars in the history of Taizhou, where thinkers represented by Hu Yuan, Wang Gen and Huang Bao in the respective dynasties of Song, Ming and Qing made bold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and exerted great infl uences. The innovation by the Confucian scholars in Taizhou derived from such scholastic concepts as erudition, integration and mentorship, i.e. they advocated broad scholastic horizon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and they emphasized the mingling of academic thoughts and the fraternity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so as to achieve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and to increase th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ies.
Key words:Taizhou;Confucian scholars;scholastic concepts;brief analysis
历史上,泰州是一个学术思想尤其是儒学思想极为活跃的地区。自古以来,泰州儒家学者名家辈出,并在宋、明、清三个时期形成了以胡瑗为代表的理学思想、以王艮为代表的平民儒学思想,以及以黄葆年为代表的圣功儒学思想三次理论创新高峰。泰州儒家学者的创新精神,主要来自于他们勇于学习和他们博学百家、兼收并蓄的精神和注重亲师取友的思想。
一、泰州儒家学者强调博学
强调博学是泰州儒家学者的一个重要特点。胡瑗是宋代理学的先驱,也是宋代著名的教育家,他讲求“明体达用”,强调知行合一,并首开“分斋教学”之先河。他的理学与教育思想推动了儒学革命,推进了教学改革,促进了宋及其以后的学校发展。王艮的社会贡献在于对王阳明的“心学”进行了改造,将“心本之学”变为“身本之学”,并传布于“愚夫愚妇”,创立泰州学派,是“觉民行道”的身体力行者。他的再传弟子李贽直接提出“童心说”,主张个性解放,具有鲜明的启蒙特质。黄葆年对社会的突出贡献是将佛道融入儒学,并且将儒学与练功结合起来,主张“心息相依”(心,意识;息,呼吸。强调内心与行为的调节),同样具有“知行合一”的成分。胡瑗、王艮、黄葆年自身也都是博学家。如胡瑗讲义理易学,同时他也精通象数之学,除精通儒家经学外,胡瑗对于礼仪也很精熟。此外,胡瑗还通晓音律,会制造乐器,对于军事理论也有研究。王艮是个儒者,但他既会制盐、会经商,还能给人看病。黄葆年的思想涉及哲学、政治、经学、教育、伦理诸多方面,所以他也是个博学家。他们之所以强调博学,是因为他们充分认识到了博学在人的知识的获得、人性的修养、处事的能力等方面的功能。
首先,博学是提高人的修养的重要途径。胡瑗认为,人的修养不能离开广博的学习,他认为即使是圣人已经具备了天生的完美的善性,也要广博其学,唯其如此,才能提高自己的思想品德。如果认为自己修养很好就停止学习,那么“终为浅大夫矣” [1]226。所以,君子之人要进一步全其天性,必须博学审问。王艮认为,博学可以避免自己认识上的偏差。他说:“论道理若只见得一边,虽不可不谓之道。” [2]6他还比喻说,学习就如观树一样,不能全面观察,就不能对树有一个全面认识。学习也是这样,不全面学习,就难以掌握真正的道理。太谷学派的思想集大成者黄葆年总结说:“古之人所以大有成者,无他焉,学而已矣。” [3]127可见,黄葆年把学习看成人成长的根本。
其次,博学有利于提高自己的处事能力。如胡瑗认为,要成为圣人,首先就要成为无所不通的人,只有成为无所不通的人,才能为国家所用,成为治理天下有用的人。他还从教师的角度阐述了博学的必要性。他说教师要能够掌教化之职,就要精通儒家治国之道,并具有治理国家的知识与能力。就学而后能为师问题,黄葆年阐述得最多。黄葆年认为,君子要想化民成俗,就一定要先学习。只有先学习,有了一身的知识才能“化民成俗于天下” [4]681。同时,他认为,学习是每个人都要做的事情,每个人都不能放弃学习,做教师的要担当移风易俗的责任,更离不开学习。他说,“知教之所由兴”,学然后能教;能教,“然后可以为人师也” [4]731。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博学”呢?首先,学习渠道要宽。如胡瑗的基本思想是,博学者既要学好孔孟之道,也要学好善言善事。王艮除了主张读经书以外,特别强调向普通老百姓学习。他说:“途之人皆明师也。” [2]19当然,要做到博学也不容易。一是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如胡瑗认为,做任何事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学习也在于日积月累。只要有坚定的意志,长期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成为博学之人。二是要不受束缚,如王艮强调率性,率性就是不受任何束缚而自由自在地学习。黄葆年也主张学习不应当受任何限制,不应有门户之见。三是要处理好博与约的关系。黄葆年认为,学习要实现接受知识与消化知识的统一。他说:“古人之修业也,求其多识多知而已矣。” [3]260事实上,一味地追求多识多知,最后反而是不识不知。为什么呢?人的知识的获得,不只在于获得知识的数量,更在于获得知识的质量,这种质量就是一种内化,是能力的提高。黄葆年这一思想,实际上阐述了博学的规律,他要求人们按照知识的接受规律去学习,而不是囫囵吞枣。
二、泰州儒家学者倡导兼收并蓄
泰州儒家学者几乎都主张“三教合一”。实践中,他们治学也不执一家,注重取长补短。其一,泰州儒家学者的思想之根在《易经》。儒家学说只是《易经》的支流,或者说《易经》也是儒家学说的源头。孔子也曾重新注释了《易》,并将其儒家思想渗入他的《易传》之中。从源头上说,孔子已经有了义理解《易》的思想,而道家也是直接从《易经》发展起来的,所以《易经》是道儒两家的经典。实际上,泰州的儒家学者们都对《易经》有所涉猎。如胡瑗开宋代义理易学之先河,他的“三教合一”思想与其解读《易经》就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易经》也是泰州儒家学者的根。
其二,泰州儒家学者的思想与儒学自身发展的需要有关。先秦儒学自春秋末年孔子创立以后发展迅速,并产生了许多流派。当儒学发展到魏晋玄学时开始异化,到了两汉时期,这种异化现象更加明显。儒学的这种异化使儒学面临着极大的危机。所以要挽救儒学,就要进行儒学的革命。到了宋初,以胡瑗等人为首创立的义理易学实际上就是一种改造儒学的具体实践。
其三,泰州儒家学者的思想受佛教影响。佛教的传入使儒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泰州的儒家学者都受到过佛教的影响,所以在他们的儒学理论创新过程中也都吸收了不少佛教思想。如在胡瑗语录中就有不少涉及佛道的话语,比如他常说卜筮之事。当然,胡瑗也认为,占卜之类只能用于小事,大的决策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客观地说,胡瑗是个无神论者,他认为不是人听从鬼神,而是鬼神听从于人,听从于国家治理的需要。显然,胡瑗的思想还是以儒家为主的。王艮同样认为:“体用一原,有吾儒之体,便有吾儒之用。佛老之用,则自是佛老之体也。” [2]5
其四,泰州儒家学者宣传儒学思想的需要。比如黄葆年在《祭帝君文》中说,“儒道合而道明” [4]188。他认为,汉晋唐宋诸儒所以出现辞不达意的毛病,主要是因为没有做到儒道合一。他认为,佛教重“致知”,是教人修性入门。人若要成佛而长生不老,就必须修身养性。道教重“格致”,是教人既重视修性,又重视修性成佛而长命。所以学习,既要修性,又要修命。黄葆年坚持“以儒为宗、旁通佛老”的风格。他说,道教是讲天道的,佛教是讲地道的,儒教是讲人道的。儒教与佛道相合是合天地之道的,如果排斥佛道,那么儒学发展就遇到困难了。黄葆年这一思想,实际上强调“三教合一”的作用。当然,在“三教”之中,他还是主张以儒教为主的。
三、泰州儒家学者主张师友
泰州的儒家学者主张亲师取友,原因有三:
第一,泰州儒家学者认为,亲师取友首先有利于学习水平的提高。如胡瑗认为,中国的儒学博大精深,仅靠一个人自己去学习研究,要取得成功不容易,必须有良师益友的辅助。因为通过良师益友共同切磋,可以相互促进,得到快速提高。王艮强调内悟,反对外铄,但他也不忽视亲师取友的作用,他曾比喻说:“阳者阴之主也,阴者阳之用也,一阴一阳之谓道。” [2]53他把自学与师友比喻为阴阳互补,这是有独特见解的。他还在《天理良知说》中说,学习者之间本来没有什么差别,对于学习的结果却有所不同。这就如同一个人,有名,有字,但有人看到的只是名,有的人看到的只是字,因而产生意见分歧。这时如果都听听对方的意见,就有利于弄清真相。他在谈到自己的学习经历时说,他能取得思想上的成就,主要是得益于“明师良友鼓舞于前” [2]28。黄葆年也重视师友的作用,他说:“天下古今不能独学而成一人”,所以“友之并重于师也”。 [5]728黄葆年还说:“大学始教,师友之功有居其大半者也。” [5]710他认为,讲学论道,必自亲师取友开始。
第二,泰州儒家学者认为,亲师取友对人的道德修养很有帮助。如胡瑗认为,朋友有着“辅仁之任”的作用。他说善与人相处,可闻“人之善言善行” [1]105。黄葆年重视“自觉”的作用。他认为,人之道德境界的提高,必从自觉开始,但他又说:“从古为学之士未有不出乡里而可以有成,亦未有不求师友而可以免于乡愿者也。” [4]112黄葆年解释“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时这样说:“寡闻者,寡闻善也,寡闻过也。不闻过则舍己无由,不闻善则从人亦无由。不能舍己从人,则长为乡人以没世,其孤陋其待言哉!” [5]728
第三,泰州儒家学者认为,亲师取友有利于成就自己的事业。亲师取友是我国儒家的传统思想。《论语》中,关于“友”的论述达十多次。如:“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6]148“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6]197-198泰州学者们继承了传统儒家的这一思想。如胡瑗认为,学者依靠良师益友的帮助,不仅可以成为圣贤之才,而且可以完成圣贤事业。如果势孤援寡,没有师友帮助,很难完成自己的事业。比如个人升进也必须有师友帮助。他认为,一个人的升进可以通过交往而求得朋友的帮忙。他说:“君子求进其身,欲行其道,而或势孤援寡,必不能独成其事。是必得其气类才德相合者推引而进。” [1]250太谷学派的黄葆年回忆自己的经历时曾说:“得友者昌,失友者亡。” [3]209他认为朋友必须“同德同心”。在黄葆年看来,在天下之达道中,“同德同心”的朋友至为重要。应该说,从人的知识的获得以及提高修养水平方面,亲师取友是一个重要渠道。泰州儒家学者们对亲师取友还作了不少具体的要求。比如胡瑗认为,交朋友不是乱交,交友要选友,要选择好交往的时期,要以正确的方式与人相交等等。再如王艮主张交友的目的主要是能得到明师良友指点,同时让明师良友能及时指出自己的缺点。当然,由于泰州儒家学者们总体上强调实学实用,所以他们的交友观也带有明显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尤其是胡瑗关于“升进”需要朋友帮助的思想比较低俗。所以对于泰州儒家学者关于亲师取友的思想我们一方面要辩证地理解,一方面要批判地吸收。
总之,泰州儒家学者的学习思想具有开放性,无论是胡瑗理学、泰州学派的平民哲学,还是太谷学派的圣功儒学,都主张博学兼收。同时他们在主张内悟与自得的同时,重视师友的作用,主张亲师取友,相互学习,相互帮助,这些思想至今仍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