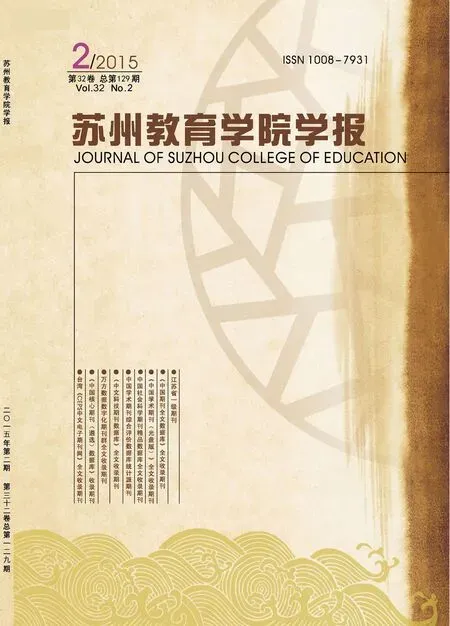从人性反思角度比较《认罪书》和《朗读者》
2015-04-10王美平
摘 要: 《认罪书》和《朗读者》均由对残酷历史的追问实现人性的反思,揭示历史背后潜藏的复杂人性。同样是审视人性,两部作品无论是在反思方式、反思力度上,还是在对人性的揭示和忏悔救赎之路上都呈现出一定差别,这源于不同文化视域下对待历史态度的差异及其所包含的自省意识、人文关怀的不同。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931(2015)02-0042-04
收稿日期: 2015-01-24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1&ZD110)
作者简介: 王美平(1989—),女,河南舞钢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A Comparison of The Confession and The Reader Based on the Refl ection of Human Nature
WANG Mei-pi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Abstract:By questioning the cruel history, both The Confession and The Reader have achieved the introspection of humanity, and revealed the complex human nature behind the history.The same point of both works is to review human nature, while the two works show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introspection manners, reflection intensity, the revelation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approaches to repentance and redemption. All these are because of different historical attitudes and different introspective consciousness and humanistic care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perspectives.
Key words:reflection of human nature;confession;The Confession;The Reader
人性反思历来是文学作品讨论的热点之一。一般情况下,历史风云往往对个人命运产生重大影响,对历史的重读也就往往涉及对人性的反思。乔叶的《认罪书》和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通过回溯历史,关注被掩藏的人性之恶,由于不同的历史意识、反思文化的差异等,使二者在反思忏悔的具体途径、力度,对人性的揭示和人文精神的彰显上有所不同。
一
“战争是人类的战争,对战争的反思最终要落到对人类自身的反思。人类发动战争有种种理由,但总是把真实的意图深深地埋藏起来。” [1]《认罪书》和《朗读者》分别以“文革”和“二战”的历史为故事背景,通过重读历史,深度开掘与复杂历史紧密纠缠的人性,打破了长久以来难以言说的伤痛,从谴责战争、揭露暴行转向对人性、对自我的反思。在道德灾难面前,法律往往会束手无策,两部作品中对于“罪”的界定,都不是以法律为标准,而是从道德和人性的角度甄别的,以期寻求对人性思考的理性超越。《认罪书》中,金金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探究历史幽微,借助众多历史参与者的回忆还原历史真相,在审视施害者罪行的同时,揭开了受害者也曾作为施害者对他人实施残害的秘密。曾经是历史灾难下受害者的梁文道、张小英、梁知等人,由于人性的冷漠、自私,造成了梅好和梅梅相继死亡,由此引发对普通人“平庸的恶”的思考,不仅施害者是有罪的,众多的旁观者、受害者是有罪的,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最后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自己,金金—揭开这一切真相的审判者,用嫁给梁知来报复梁新对自己的抛弃,同样也是有罪的。《认罪书》“撕开历史和现实的残酷和荒谬,在人性和伦理的幽暗和虚弱处觉醒并反思,对那些不能遗忘的恶进行‘认知、认证、认定’,对那些不可原谅的罪进行‘认领、认罚’” [2]。
《朗读者》讲述女主人公汉娜与少年时期的米夏产生了一段恋情,后因她曾在纳粹时期做过集中营的女看守受审判而入狱,失去了自由和爱情,她在狱中通过朗读来反思、忏悔、救赎自己,由此引发对二战历史的开掘,对平庸的恶进行反思,从而拷问人性的弱点。作者对汉娜并没有过多的谴责,而是层层铺开历史,将她的盲目与罪责并置,任所有人去评判、去思考,旨在使年青一代去理解和反思:个人的愚昧、盲从如何在历史的裹挟下充当了战争的帮凶。除汉娜之外,米夏、法官等作为审判者和法律权威的代表也是有罪的,米夏耻于面对曾经的恋情,选择尊重汉娜的秘密也是对自我责任的一种逃避,是汉娜被判终身监禁的一个推动因素。通过对二战历史的审视,抵达人性深处的弱点,反思个人的盲目、愚昧、麻木不仁如何在历史的裹挟中引发道德悲剧,进而寻求人类的普遍反思和自我忏悔。
回溯历史为反思人性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角度,面对战争、动乱,谴责并不是唯一目的,战争同样可以作为一面镜子,投射出人性的复杂面来,作为后来者,不仅要重新认识时代,更重要的是透过时代的幽微透视自己,审视当下。从关注历史的罪恶、施害者的残酷到聚焦受害者和旁观者背后的人性之恶,透视了复杂历史背后的人性弱点;从要求别人忏悔、逼迫别人忏悔到自我忏悔,批判的矛头由他人指向自己。两部作品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反思的具体方式、力度以及忏悔道路等都有所差别,但是殊途同归的是人性反思的最终目的。
二
《认罪书》和《朗读者》在如何实现人性反思的具体方式上有所不同。《认罪书》是以逼罪方式令当事人和后来者认罪并忏悔的。梁文道、张小英在“文革”中亲眼看着梅好走进群英河而不施救,置亲情和友情于不顾,梁知、梁新为了自己的前途宁愿把梅梅逼向死路等,这些事实都被当事人掩盖,直到金金刨根问底,将这些罪行昭之于众,迫使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罪责并忏悔。因此,他们不是自己反思罪行,而是被金金逼迫着忏悔,甚至可以说,若不是金金揭开了这一切,恐怕他们永远不会忏悔,还会继续依照预计的轨迹走下去。《朗读者》以主动认罪展开叙述,无论是汉娜还是米夏都自觉地进行反省,发现并忏悔自己的罪责,对历史和自身有一种清醒且全面的认识,显示了一种敢于承担责任的勇气和爱的能力。汉娜在法庭上接受审判时并不认为自己有罪,她坚信自己只是忠于作为看守的职责,后来她在狱中学习识字,阅读了大量关于纳粹罪行的书籍,认识到自己盲目无意识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在死后让米夏帮她看望曾经受到伤害的女儿并赠送自己全部的积蓄作为弥补,这些都是自觉地反思和忏悔。米夏为汉娜朗读是在反思自己在法庭上所做的选择,反思和汉娜的关系,最后终于可以坦然面对两人的爱情,主动向律师和女儿诉说内心的隐痛。
从反思方式上看,两部作品有逼罪和认罪之别。《认罪书》中的认罪以逼罪方式展开,逼迫当事人和曾经的受害者认领自己的罪责,是被迫地认罪,其中缺乏理性精神和自省意识。《朗读者》则是自觉地反思和认罪,反思被历史掩盖的个人罪责,反思人性中潜藏的平庸之恶,审视人性自身。“哲学理性所应当倾听的,倒正是对于恶的忏悔的最漫不经心的、最不能言喻的表达方式。所以,我们应当从‘思辨的’表达方式退回到‘自发的’表达方式。” [3]7-8真正的认罪,应该是自发的认罪、饱含着情愿的认罪,对人性的反思只有从被迫走向主动,反思才具有哲学价值。反思方式的不同也使得两部作品具有不同的反思力度,自发的普遍性反思无疑是更加彻底的,更具哲学意味的。时间虽在流逝,在不同的时空中,人性却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只有认清历史和自己,主动反思人性的弱点,才能照亮人类的精神世界。
反思方式和反思力度的差异使作品对人性复杂面的揭示有所不同。《朗读者》更多呈现的是人性之弱,而《认罪书》主要揭露人性之恶。在《朗读者》中,不管是汉娜还是米夏身上都不仅仅是单纯的人性之恶,更多的是复杂历史条件下的善恶交织,是人性无可奈何的弱点。米夏在汉娜接受审判时表现出的沉默是在爱情、道德和法律之间的艰难抉择,难以用对错区分。出于维护汉娜尊严的目的,米夏选择保守汉娜的秘密,但间接造成了汉娜被终身监禁,这样的结果使他内心经历了道德和良心的谴责;倘若忠于法律和事实,说出汉娜的秘密,虽可使汉娜免于监禁,但是却暴露了一直以来汉娜要保守的秘密,而米夏却没有勇气面对这段曾经的感情,所以他在隐藏和坦露自己的隐私之间艰难徘徊,艰难抉择。战后一代谴责父辈在纳粹时期的冷漠和无动于衷,责备父辈没有对纳粹暴行进行反抗,其与父辈之间尴尬的代际关系是亲情和理智之间矛盾的结果。
《认罪书》一改往常对受害者的同情立场,揭露旁观者和受害者身上潜藏的人性之恶。梁文道在“文革”中曾遭迫害,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妻子梅好被王爱国等人侮辱、伤害后投河自尽。他为了减轻自己当时所承受的政治迫害和舆论压力,目睹妻子寻死却不去施救,推卸丈夫对妻子所应承担的责任,充分暴露了人性之恶。梁知自认为是深爱梅梅的,却为了自己的仕途默许母亲把梅梅送到钟潮身边,后又和弟弟将前来闹事的梅梅送回南方,又狠狠责备梅梅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了麻烦,最后造成了梅梅的死亡。为了自己的前程,为了追求更大的权力和利益,梁知葬送了自己的爱情,把梅梅推上死亡之路,他的一生都在追悔中度过,忏悔曾经对梅梅所做的一切。由此看来,《朗读者》比《认罪书》在发掘人性时更多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之处,不单单是人性之恶,还有人性在不同历史条件、情感际遇下所暴露出的弱点。在《朗读者》中,这些均被作者视为面对矛盾处境时做出的无奈选择,给予了充分的人文关怀。
反思人性是为了知罪认罪,从而寻求自我的救赎之路,这是反思的最终目的以及价值所在。而两部作品的忏悔救赎之路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呈现了对人性反思的不同结果。在《认罪书》中,“忏悔者做忏悔的那种体验仍是深陷于情感、恐惧、苦恼原状之中的无识别力的体验” [3]4。无识别力的体验,即是由情感上的伤痛记忆而引发的被动的忏悔,其目的是为了摆脱痛苦、愧疚、自责的心理状态。作为曾经的受害者,当他们身上不为人知的罪行被昭示于众后,耻于面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选择了逃避作为救赎之路。以死亡来逃避救赎,是自我反思不彻底的结果,作品中一系列人物的最终命运也恰巧说明了这一点。梁知自杀、梁新出车祸、金金患肺癌,这一系列非正常死亡的结局不是简单的因果报应。当他们的罪行被揭发,人性之恶坦露在众人面前时,他们是缺乏勇气去面对的,所以死亡对他们来讲是一种逃避的方式,也是他们最简单直接的救赎方式。而最具哲学意味的救赎是继续活下去,用余生反思和忏悔自己,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赎罪。
与《认罪书》中以死亡寻求忏悔救赎不同,《朗读者》对人性的反思更加彻底,因此在救赎方式上也更彻底。作品中的忏悔和救赎之路并未通向死亡,而是以生存和一生的忏悔来寻求救赎。汉娜被法庭判处终身监禁之后并未放弃生命,她在牢狱中的生活一直井井有条:保持良好的阅读和生活习惯,通过阅读大量有关纳粹罪行的书籍,以期认清自己、认清历史、正视这一切,后来将自己所有的积蓄赠予纳粹时期曾受过伤害的那个女儿。汉娜并没有把这一切错误都归因于历史,而是认真反思自己在历史中应当承担的责任,她没有逃避忏悔、拒绝救赎,而是用其一生认真思考和反思,自己如何在无意识中、在历史的裹挟下成为罪恶链条上的一环,并在一定意义上寻求给自己赎罪的机会,汉娜所做的这一切都显示了她忏悔和救赎的勇气。除汉娜外,米夏也倾其一生忏悔,对汉娜忏悔,他反思自己当时面对汉娜所做出的选择,执着为汉娜朗读,直到最终可以坦然面对和汉娜之间的往事,所以米夏也是主动寻求救赎的。两部作品中人物的不同结局显示了不同的忏悔救赎之路,这一差异反映了对人性反思结果和程度的不同。
《朗读者》和《认罪书》虽然都涉及人性反思这一主题,反思普通人身上潜藏的恶,但是无论是在具体的反思方式、作品呈现出的反思力度、对人性复杂面的揭示以及忏悔救赎之路上,二者都表现出一定的差异,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三
《朗读者》和《认罪书》分别是反思“二战”和“文革”的作品,具有不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因此,构成人性反思差异的重要原因在于这两种不同文化视域下对待历史的不同态度、不同的自省意识和人文关怀。
许子东认为:“有关‘文革’的集体记忆,与其说记录了历史中的变革,不如说更能体现记忆者群体在‘文革’后想以‘忘却’来‘治疗’‘文革’心创,想以‘叙述’来‘逃避’‘文革’影响的特殊文化心理状态。” [4]3“文革”作为20世纪的重大事件,对其认识反映了国人认识历史、认识自身的能力。中国人在整理“文革”记忆时,缺乏足够的勇气清算历史和自身的错误,而只是建造一种“为了忘却的记忆” [4]213。重新回忆“文革”,讲述历史是为了忘却“文革”带来的心灵伤痛,而缺乏深刻的自省意识。而这样的理念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就是对“文革”以及自身的认识和反思不够彻底、深刻。
除此之外,《认罪书》中涉及的人性反思缺乏足够的自省意识和人文关怀,表现出一种道德上的洁癖,即以严格、完美的道德标准要求每个个体,而一旦触犯道德底线,立刻将其排除在道德行列之外。这种道德洁癖对道德、人性上有瑕疵的个体缺乏包容、同情和理解,缺少人文关怀精神,更多的是谴责。作者为书中的罪人关闭了通向未来的门,留给他们的是疾病和死亡的结局,作品中的人物逃避救赎的同时也是因为救赎无门。情感道德上的洁癖使得在对人性反思时缺乏人文关怀,缺乏承担的力量和爱的勇气,单纯呈现了人性之恶,忽略了多种复杂条件交织下的人性之弱。
二战以后,德国人对法西斯恶行的谴责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作家们反思二战,呼吁世界和平与安定。从揭露战争的残酷、法西斯的罪行给人民带来的苦难,逐渐转向“通过追溯和回忆,反思纳粹德国的历史以及德国人应当承担的责任” [5],实现了清算历史的残酷,反思了个人在历史中应当承担的责任。基于德国民族的反思文化,本哈德•施林克摆脱了尖锐的社会批判,对历史、社会、情感和道德等复杂条件纠缠下的人性进行了剖析,探讨了复杂的人性,诉说了以往反思文学无法言说的伤痛,同时更加关注人性和命运,饱含了强烈的人文关怀,使人们对二战时期的普通人既谴责又同情。
《朗读者》探讨了复杂的人性,指出了在历史进程中不能推脱的个人罪责,同时也不乏承担的力量和爱的勇气。“除了正义,还有人性与人道,直接与人类的心房对话,体现了他在思辨明晰的同时,对于人性与存在的深度把握,独立思考的态度和勇气。” [6]作者以独特的反思视角,充分的人文关怀看待如汉娜一样的普通民众,既谴责他们在集体无意识中,由于盲目、无知而充当了历史罪恶的帮凶,又同情他们在多种矛盾条件下的无奈抉择,给予对生命本身的关怀,使得反思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朗读者》和《认罪书》的主题都是复杂历史条件下的人性反思。但是,两部作品在反思的具体方式、力度、对人性复杂面的揭示以及忏悔救赎之途径上都存在不同,反映了人性反思的不同高度,而这一差异主要是因为不同文化视域下对待历史的不同态度,以及作品中不同的自省意识以及不同的人文关怀。对于人性的反思不仅仅是谴责,更要有勇于承担责任的勇气和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