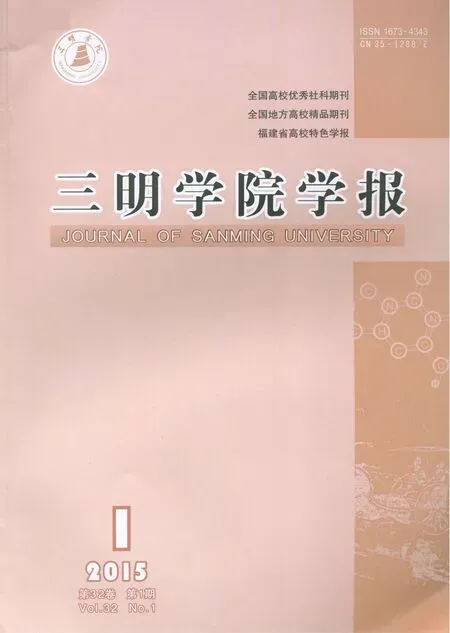董应举与陈第交游考略
2015-04-10王倩陈庆元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王倩,陈庆元(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董应举与陈第交游考略
王倩,陈庆元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摘要:董应举和陈第同为明代具有影响力的闽籍文人。在董应举的朋辈中,陈第是与其关系最为密切,也是最为特殊的一位。他们常因议论不相下,而把陈第称为“骂友”,并且成就了一段忘年之交。两人性情相近、志趣相投,都胸怀大志,有匡世济民之志,也都喜乐山水,探奇揽胜。在闽地,他们一起赋诗论文、赏游名胜,留下许多书信,从中可以明晰董应举的生平和思想,更好地认识其在闽中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关键词:董应举;陈第;交游考略
董应举(1557—1639年),字崇相,号见龙,闽县龙塘乡(今属福建连江县)人,经历了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六个皇帝年号。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中进士,授广州府教授,后升南京国子监博士,擢吏部文选郎中,升南京大理寺丞,太常少卿,太仆卿,工部右侍郎。董应举好学善文,在官慷慨敢任事,居家建筑附海城堡,又疏水利、修学校、置社仓义田、议官籴、严禁认澳课,皆有德于乡。有《崇相集》十九卷。
钟惺云:“闽有董崇相先生者,其人朴心而慧识,古貌而深情。”[1](P331)叶向高云:“公生平操修建树,一出于真诚。”[1](P4-5)这都言其为人真诚、朴实。董应举一生涉官较多,转战南北,所以游历广阔,交游甚多。《崇相集》十九卷,文据多,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云“崇相诗不多作”[2](P557),所以董应举和其他文人的交游主要集中在书信交往上。从其《崇相集》书四卷和诗一卷中可以确定的就有百余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公卿名流。基于地缘关系,董应举交往最密切、情谊最深厚的多为闽人,如陈第、叶向高、陈元凯、苏云浦、曹学佺等人。本文就与其关系最为密切,被号称为“骂友”之交的陈第之交游进行考述。
一、交游背景
在董应举的朋辈中,陈第是与其关系最为密切也是最为特殊的一位。据《连江县志》记载:“龙塘董公,常与陈一斋季立友善,而议论不相下,号为‘骂友’。”[3](P434)
陈第(1541—1617),字季立,号一斋,晚号温麻山农,福建连江人。为明代名将、旅行家、古音韵学家和藏书家。万历初诸生,聪颖博学,性喜谈兵。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戚继光追剿倭寇至连江,陈第上《平倭策》。万历后历任京城兵车营教官、潮河川提调、游击将军,坐镇蓟门十年。万历十一年(1583年)辞归南还。万历三十年(1602年),随沈有容渡海东蕃(今台湾)剿倭,返回后遍游名山大川。著有《蓟门塞曲》《五岳游草》《寄心集》等诗文集,其《毛诗古音考》《读诗拙言》《屈宋古音义》等对古音韵的研究颇有影响。生平储书最富,其后人作有《世善堂书目》。董应举云:“二戴粹纂虽有成书,惜与《海防事宜》、《东蕃记》俱逸而不传。”[4](P614)由此可知陈第所撰述中,还有许多大有价值的书。
两人之交情是在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夏,陈第解佩南归后才开始的。陈第卷甲归乡后,筑倦游庐于连江西郊,杜门读书,以吟咏自乐。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春初,董应举过访陈第于连江,而此时陈第56岁,董应举40岁,两人相见大悦。陈第在《与林日正书》有云:“近有闽县春元董见龙者,博学能文,深于理道,大非尘埃中人,春初枉顾,遂为知己,数数相遇,皆朝谈至夕,夜谈彻晓,殊慰孤寂,如兰精舍,后未有也。”[5](P301)二人社会地位、年龄相异,但结成了忘年之交。
一是性情相近,心有灵犀。董可威《崇相集序》言董应举有浩然正气,为人“廉直、劲挺、倜傥、磊落”[1](P6)。《明史》载,董应举“万历戊戌进士,除广州府教授。税珰李凤欲得学宫闲地,应举斥之。凤舍人驰过文庙前不下,遣人絷其马,用是有名”[6](P6289)。又《竹窗笔记》载:“为诸生时,有书田,与两广总督陈瑞子长祚毗连。长祚以厚值延至家,强券焉。先生袖归,至万寿桥,悉投江中。”[7](P89)由此可见,董应举为人廉直、倜傥、刚正豪迈,不畏权贵。陈第在戚继光追倭至连江受挫,献《平倭十策》,十分慷慨。据《连江县志》载:“一斋,少豪宕,自喜生平无忧色。尝与沈参戎有容浮黑水击倭。”[8](P285)陈第少年倜傥,被时人目为“狂生”。后因其为人耿直无私,得罪上司,弃职归辞。读两人之著作,可知“重实际,恶空谈”是其共同之特性。两人之文章多言国家时政,批判虚伪之儒者。综上可见,两人都豪气方刚,没有奴颜媚骨。
二是匡世济民,胸怀大志。陈第投笔从戎,戍边十载,手握重兵,大司马谭纶赞其“俞、戚之流亚也”[2](P542)。誓死抗倭,保国安民,为抗倭献《平倭十策》,后又有《定边靖乱策》扬名塞外。而董应举在其书信中也曾多次提到自己虽文弱,却喜武节。其一生忧国忧民,心系国家、桑梓之安危,多次上疏富国强兵、剿除奸臣恶贼之策。其《崇相集》中颇有关于当年闽海史事之记述。
三是喜乐山水,寄情山水。陈第一生足迹遍及全国大川名胜,即便是古稀之年,依然壮游五岳,乐在其中,并著《五岳游草》,人们将其与徐霞客并提。董应举也爱慕山水,曾一度旅居武夷八曲涵翠洞,《福建通志》载其“落职闲住,既归居武夷八曲之涵翠洞,与生徒讲学,老而不倦”[9](P6)。直至晚年不辞劳苦,倾家荡产开辟百洞山,使之成为一方之名胜。董应举诗文集中甚多描写闽地奇山异景之作。
在闽中诗派盛行的福州地区,董应举不甚遵从闽中诗派,而诗友陈第,也是不宗尚唐音,甚至有意与闽派分庭抗礼。可见,无论是从性情还是文学之好尚,两人都有太多的相通之处,虽然相差整整十六岁,却成了莫逆之交。
二、交游历程
自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春两人初见后,陈第邀董应举出游,董应举作《答陈季立招游》云:“绿满楼前雨复晴,间关欹枕听莺鸣。不知我友缘何意,却唤持柑别处行。”[1](P348)诗中表达了对身边美景之喜爱,有劝陈第无需消耗精力远涉寻景之意。秋十月,董应举奉母柩葬于连江,陈第为其襄理一切。董应举在《祭陈一斋文》中也曾说:“忆昔丙申之岁,葬我先慈,非兄将不能襄事。”[1](P131)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时董应举为内铨曹,陈第助其北山。董应举《祭陈一斋文》云:“丁酉之役,抱病自废,非兄将不能北首,其后鼓壮吾气,勤攻吾病,玉我非一,载之肺肠。”[1](P131)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陈第受林培之游罗浮之邀。秋,在罗浮怀崇相,寄诗三首。其一,“江头别去两经秋,献赋明光赐锦裘。遥约幔亭并太姥,此时踪迹在罗浮。”其二,“寒林枫叶两萧萧,一夜相思万里遥。人世飘蓬元不定,白云丛桂可相招。”其三,“蓟北春来两寄书,南归消息近何如。青云莫负杨雄草,太姥山中小结庐。”[5](P451)用悲凉意象渲染两地隔离之凄凉,悲慨人生之漂泊无定,表达对友人离别后的相思、相期。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冬,董应举时任广州府教授,陈第寄董应举书,并翻刻《谬言》,作《寄董崇相》云:“《谬言》为所者多,近又翻刻于粤,能使此书信今传后,实在老丈。不识有意否也?”[5](P1599)言因多人想得《谬言》一书,于粤再次翻刻,并望董应举为其保管,能使其传承于后。由此可见陈第对董应举的信任。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董应举官南京国子监博士,陈第作《怀董崇相博士》云:“别离已三载,秋风叶又稀。中夜起相忆,白露生庭帏。瑶音无一字,空有鸿雁飞。眷言禺山下,促膝情依依。闻向金陵去,官闲愿不违。六代繁华地,无能缁素衣。”[5](P367)三年前的一朝别离,从此天隔一方,杳无音信。诗中回忆了与董应举之往昔生活,无不透露对“骂友”深切之怀念。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夏末,董应举北上考核政绩,陈第以诗送之。作《时崇相北上课绩》云:“去岁闽来,就君白下;我诲我仪,奕奕大雅。青阳载转,朱明兆夏;非忍索离,敢云絷马!兹当奏绩,言别江浔;驱车既北,泛舟亦南。世途阻险,至人陆沉;相去日远,跂怀德音。蓟门鱼雁,慰我遐心。”[4](P367)后又有《再送崇相户部课绩》相赠:“岁昔在乙巳,送君入上京。乱流济扁棹,两岸多莺声。一别讵能几,今又送君行。浓谈殊未尽,里曲还愤盈。燕蓟正雨雪,胡为独北征。旅居半亩斋,愁想万里程。纡途登泰岱,吴门望正晴。上有无字碑,秦汉铭已倾。秣陵旧都地,守重隔江城。国初宿屯戍,五卫列藩营。自从崩圮后,洲渚坦以平。何当存犄角,识者为心惊。袖中有短疏,意在扣宸明。远臣既建白,公辅会相成。愿君且静默,造物忌取名。”[5](P369)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董应举乞归田里,陈第从永嘉归连江再出行永嘉。时董应举家居,与陈第常有书信来往。在这些书信中,真正体现了“平生有骂友,四海却无多,持论互非是,中心实匪他”。在文学探讨过程中,各陈己见,共同商榷。万历四十年(1612年),董应举在《答陈季立书》中,讨论有关读书和学习的态度、方法问题。就陈第建议其熟读五经,提出异议。他认为读书者在得其意,不在字字精熟,云:“夫读书者在得其意,不在字字精熟,字字精熟即好秀才耳。”[1](P454)在文学创作上反对模拟古人,追求本真自我,并给予陈第文学创作很高的评价。董应举归家期间,志在收拾先人余业,在经营闽安镇城工之事,资金紧缺,陈第赠金五两助其成,董应举《答陈季立》云:“兄乃为我过计,赠金五两。”[1](P456)在书信中还就陈第五岳之游的相关问题作以解答,并对其盲从经典提出建议。此后董应举又写给陈第第三封书信,《答陈季立》言:“丈诸书中,《图赞》为最。”[1](P458)肯定陈第的《伏羲图赞》,并认为陈第的《毛诗古音考》尚有可议之处,建议其著书不如修书,达到守一而致美。
董应举在其友苏云浦的书信中谈论陈第云:“季立七十有五,去死不远,游遍四岳矣,且欲游南岳,每言游一岳须白反黑,足疮尽愈,以山水为医王,其劈出伏羲图,直捷圆妙,伏羲犹应点头。”[1](P501)再一次肯定陈第的《伏羲图赞》,认为其直捷圆妙,就算伏羲在世亲眼看到也会对其作品得以认可。
陈第好游名山大川,董应举也喜爱探奇揽胜。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董应举辞官回乡。陈第刚好游罢南岳衡山归来,邀董应举共游城西草堂,而那时董应举由砍柴樵子带路发现并初次开拓了百洞山。立即写了《陈季立招我城西草堂》一诗作答:“城西草堂背江开,江樊林竹巧相回。一溪风雨时进艇,半榻图书独把杯。泄柳闭门非已甚,潜夫着论若为哉。我亦有山沧海外,苍茫秋色待君来。”[1](P339-340)诗中描绘了百洞山之秋色苍茫,胜旷之景,并邀请陈第来观赏他初辟的百洞山。陈第来住了十天。
第二年春,董应举又邀陈第来游。但76岁高龄的陈第因病不能应命,只寄《病中题虎馆三首》作答,其中第二首诗曰:“去年十日宿青芝,山色江风饱包知。闻说诸奇尽吐露,主人春酒为谁携。”[10](P120)病中念友,鸿雁传书,一唱一和,情谊深厚。但陈第病愈后,又治装出行,行至南平,病复发,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正月底折返连江,病情恶化。时董应举闻陈第病,乃作《陈季立病念之有赋》慰赠:
平生好争论,好友辄相骂。及其疾病时,皇皇忧日夜。如割一半身,如屋崩其瓦。百物皆可求,好友难再假。久交如熏兰,乍交如佩麝。麝性岂不烈,终不如兰化。吁嗟陈一斋,使我食不暇。君作五岳游,我为一官住。我凿百洞山,君病不能步。清福岂长存,良游安可暮。奇胜善骄人,山灵择人付。吾儿知我心,破家不复顾。君病若稍痊,为我移仗履。[1](P370)
全诗以悲沉的笔调,曲折往复。开篇先交代两人是“骂友”之交。后写因陈第患病,作为其好友的自己,因担心而夜不能寐,并感慨人生当中好友难求。运用打比方的手法,形象的说明了两人情谊如香气芬芳之“熏兰”,进而强调友谊之深与可贵。然后转向眼前,好友病卧在床,感慨往昔,因某些客观原因,两人总是交错而过,如今自己开辟百洞山,而好友却因病不能前来观赏,继而写到希望好友早日康复并邀来赏百洞。陈第作《病答董崇相骂友诗》云:“平生有骂友,四海却无多,持论互非是,中心实匪他。登山同啸傲,对酒发悲歌,处官自职事,钓月着渔蓑,纵迹若秦越,诗书共切磋,高山思仰止,矫首在峨峨,天生有五味,剂调乃为和,岂忍效流俗,委摩随江河,忠言本逆耳,不骂欲如何。”[10](P123)同样是回忆往昔之美好岁月,强调两人友谊之可贵。
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三月二十一日陈第殁,董应举闻此噩耗时,捶胸涕泪,悲不自胜,作《祭陈一斋文》曰:“遍交宇宙,无两一斋,自信平生无两骂友。今骂不可得闻矣!人之云忘,如割我体。”[1](P131)由此可见,董应举视陈第为唯一的知己,且二人之交,以骂为快,在争辩中提升和加强了两人的感情和友谊。文中还回顾了自己与陈第一生的交往的经历,极为哀戚。生前死后,两人之情义可见一斑。又董应举《答苏云浦书》亦云:“弟平生有两骂友,一是陈季立,一是潜父。”[1](501)由此可见,两人之情义,世所罕见。
总之,明代自中叶以后,国势衰颓,董应举和陈第作为有明一代有识之士本救世之心,研有用之学。在两人的书信交往中,董应举多以“兄”来称呼陈第。陈第不仅是董应举的诗友,更扮演着其长辈的角色,董应举在自己的文中也多次提到陈第对自己的关怀与帮助之大。二人彼此赞赏、彼此肯定,从他们的交游历程可知,这对董应举的思想、性格和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明]董应举.崇相集十九卷[M].明崇祯刻本,《四库禁毁书丛刊》本(集部第102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2][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邱景雍.连江县志[M].点校整理民国版.连江:连江县志编撰委员会整理,1989.
[4]陈遵统.福建编年史[M].福建省文史研究馆整理.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5][明]陈第.一斋集[M].据明万历会山楼刻本影印,《四库禁毁书丛刊》本(集部第57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6][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清]郭柏苍.竹间十日话[M].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福建:海风出版社出版,2001.
[8]邱景雍.民国连江县志[M].曹刚,修.1933年铅印本影印.
[9][清]魏敬中.重纂福建通志[M].程祖洛、吴孝铭,续修.同治七年(1868)刊本.
[10]金云铭.陈第(一斋)年谱[G]//沈云龙:明清史料汇编:第1册.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973.
(责任编辑:刘建朝)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Friendship between Dong Yingju and Chen Di
WANG Qian, CHEN Qing-yuan
(College of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Dong Yingju and Chen Di are both celebrated literary intellectuals of Ming dynasty in Fujian province. In the peers of Dong Yingju, Chen Di is the most intimate friend and the most special one. They are often in hot debates and never take a step back to each other, thus Chen Di is called "Scolding Friends" and they achieve friendship between old and young people. Not only are they similar in temperament, like-minded and ambitious, but also they uphold the right track and enjoy mountains and rivers. In Fujian province, they often make poems, discuss essays and look around attractions together, leaving many letters. Those letters give a clear view of Dong Yingju's life and thoughts as well as provide a better recognition of his special status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Fujian province.
Key words:Dong Yingju; Chen Di; textual research of friendship
作者简介:王倩,女,甘肃文县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明清文学、福建地方文学。陈庆元,男,福建金门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福建地方文学。
收稿日期:2014-12-22
doi:10.14098/j.cn35-1288/z.2015.01.014
文章编号:1673-4343(2015)01-0073-04
文献标志码:A
中图分类号:I2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