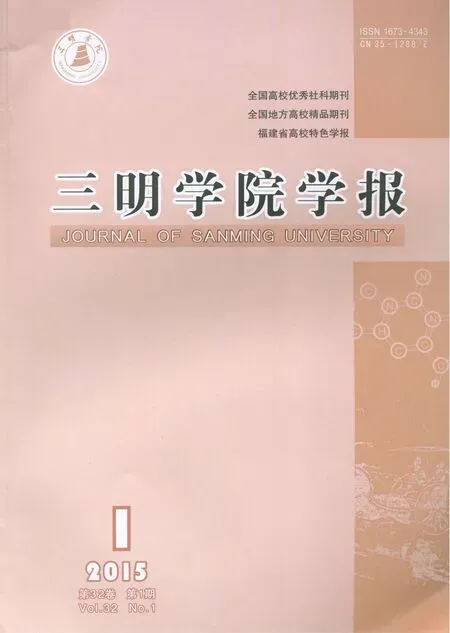探析政府承担农民工法律援助责任的依据
2015-04-10刘春明三明学院旅游学院福建三明365004
刘春明(三明学院旅游学院,福建三明365004)
探析政府承担农民工法律援助责任的依据
刘春明
(三明学院旅游学院,福建三明365004)
摘要:法律援助是为贫弱者提供的一种无偿法律服务制度。农民工由于经济、政治等地位的劣势,已被普遍认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获得法律援助是其应当具备的一种应有权利,而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则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责任。社会契约理论、人权保障原则、实质平等理论、程序正义理论、效率价值理论是政府承担农民工法律援助责任的法理基础,宪法、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和农民工自身的特性又为政府承担责任提供了法律和现实依据。
关键词:农民工;法律援助;政府责任
法律援助以保护社会弱势群体为主要价值目标,而农民工作为现代城市化进程中一支不可忽略的弱势群体,对他们实施法律援助是政府进行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的重要职责之一。因此,农民工获得法律援助是其应当具备的一种应有权利,而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则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责任。然而,纵观近几年来对农民工法律援助的研究,多停留在实践操作层面,基础理论研究显得不足。因此,梳理政府承担农民工法律援助责任的法理基础与法律现实依据,对提升农民工法律援助的理论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民工法律援助政府责任的内涵
(一)农民工的基本认知
农民工是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指那些进城打工,却仍保留农业户口、农民身份的人员。他们受自身科技文化水平和户籍制度的限制,在城市从事的基本是一些最苦最累而低薪的工作,造成其经济上的弱势。在政治上,农民工尴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中绝大部分人无法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无法享有政治上的发言权与参与权,形成了政治地位的弱势。而政治地位的弱势,极大地妨碍了他们经济地位的改善。同时,经济、政治地位的弱势又带来了文化、心理等的弱势。因此,农民工已被普遍认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
(二)农民工法律援助政府责任的内涵
法律援助,简而言之,就是为贫弱者提供的一种无偿法律服务制度。农民工因其经济困难、社会政治地位低下、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自身文化程度不高等因素已成为社会结构中的弱势群体。弱势群体需要社会的全方位帮助和支持,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当农民工因为经济上的弱势没钱请律师打官司,又因为自身法律知识缺乏无法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时,农民工理所当然地成为法律援助的受援对象。对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也是法律援助的应有之义。
政府责任即政府的责任。对责任的理解通常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分内应做的事或应尽的义务,如职责;二是指做不好分内应做的事或不尽应尽的义务而承担的不利后果。因此,政府责任就是指政府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对公民或社会应尽的职责以及因不能自觉依法合理履行相应职责而应当承担的不利后果。前者属于履行职责方面,是积极责任;后者属于承担责任方面,是消极责任。[1](P41)而政府责任不仅仅指法律责任,还包括道德责任、政治责任和行政责任。[2](P16)
农民工法律援助政府责任,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概念,更多的是一种治国理念,指的是政府应该为农民工这种新兴的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即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非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的责任,而农民工既是受援主体,又是政府承担法律援助责任相对应的权利主体。我国学者张成福教授将责任政府理念与制度安排进行统一,他认为:“责任政府既是现代民主政治一种基本理念,又是一种对政府公共行政进行民主性控制的制度安排。”[3](P77)
作为一种治国理念,农民工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应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来实施。从静态上来讲,对农民工法律援助进行立法,设置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职责及责任内容和形式,让农民工法律援助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设置法律援助机构与配备法律援助专业人员,具体实施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保证法律援助的经费,使具体承办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的社会律师或公职律师得到适当的补贴。从动态上来讲,通过外部和内部问责机制来追究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要将责任明确到具体的政府,属于哪一级政府,同时,通过责任内化制度,追究具体工作人员的责任。[4](P128)只有这样的政府才是回应民意的政府,才称得上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二、政府承担农民工法律援助责任的法理基础
(一)社会契约理论
社会契约理论是在反对君权神授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用以解释个人和政府之间适当关系的政治理念。它认为:国家之前是人类的无政府的自然状态,所有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人,都占有因自然法而产生的自然权利。但因人们滥用自然权利,而使人们的生命、自由及财产权利受到威胁。为了保障自然权利,人们通过订立契约来建立国家,并将天赋的自然权利部分让渡出来给政府形成公共权力。通过契约建立的政府,职责是遵守自然法,维护和实现公民的生命、自由、平等及财产等权利;如果政府违背契约,人民就有权推翻政府。根据社会契约理论,公民权利是政府公共权力的来源,政府是人民的公仆,政府权力受托于人民,政府权力应为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服务。因此,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执行机关,在社会公共管理活动中应承担起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的责任。
农民工具有公民身份,当他们的权益遭受侵害时,政府有责任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保障农民工实现自身权益。同时,农民工也是一个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地位上处于劣势的群体,即使法定的救济途径和方式很多,可农民工不仅法律专业知识匮乏,而且经济能力十分有限,无法聘请律师为其代理,作为有责任的政府就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保障他们能及时得到法律帮助,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人权保障原则
人权简言之就是作为一个人所应该具有的权利。“从一般意义上说,人权是人的价值的社会承认,是人区别于动物的观念上的、道德上的、政治上的、法律上的标准。”[5](P380)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权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人权不再是倡导性的宣言,许多国家不仅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人权的内容,还在一般法律中将人权的内容具体化,赋予其实质性的内容以及可操作的规程,使人们实现和享受人权的内容成为可能。人权的内容非常广泛,包含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权利和自由,而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没有生存权、发展权,其他一切人权均无从谈起。
农民工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劳动收入是他们唯一的经济来源,工资、工伤赔偿等物质权益成为了他们最为关注的问题。当农民工遭受工资、工伤赔偿等物质权益纠纷时,他们的物质生活就受严重威胁,如果这时还要求农民工自己去维权,只会让他们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劣,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都无法保障,这就与政府所倡导和宪法规定的人权原则相违背。因此,政府应以法律援助这种司法救济方式保障农民工最基本的人权,通过司法人权的实现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三)实质平等理论
平等是人类一直追求的核心理念之一,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原则。从内涵上看,平等分形式意义的平等和实质意义的平等。形式上的平等指人人生而平等,它完全不顾人由于先天或后天的各种因素导致的强弱之分,为的是保证在起跑线上的个人机会平等,即机会平等。但是,形式上平等在自由竞争环境下,由于各人起点、资质不同,必然导致结果上的不平等,从而产生新的不平等。因此,公民还应享有实质上的平等权。实质上的平等承认人生而不同,认为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而要使人们在事实上达到平等,国家有责任通过合理的差别对待,通过对特定主体的发展条件的补足,使得原本由于生理、历史、传统、地域等因素造成的在发展条件上先天不足的个体能够获得与其他公民同等的发展机会与条件,其目的是为保护社会上的弱势群体。
农民工由于先天的条件和后天发展的不足,在经济、文化上处于劣势。就司法救济而言,专业性非常强,普通公民根本无法应对,更何况是农民工。可普通公民可以聘请专业律师购买专业的法律服务为自己维权,而对农民工一点也不现实,实质平等就成了一句空话。实质平等要求政府设置合理的差别待遇,使农民工在法律服务面前能够获得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机会与条件。这就需要政府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承担法律援助的责任,为农民工法律援助买单,使农民工不因经济状况所限无法获得司法救济。
(四)程序正义理论
正义是人类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之一,是法律援助的理论基础。正义是指人们普遍认可的符合事实、规律、道理的具有公正性、合理性的观点、行为、活动、思想和制度等。正义有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实体正义指分配实体权利与义务的正义,程序正义指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程序上的正义。英国有一句古老的格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这里“看得见的正义”就是程序正义,就是指法律程序的正义。法律程序的正义要求所有的公民都平等地进入法律程序,平等地接受法律的裁量。另外,“看得见的正义”也是“一种高成本的正义”[6](P332),它以经济实力为基础,如启动司法救济程序的一方需预缴一定的诉讼费、委托律师提供专业法律服务需要支付律师费等。
农民工由于自身的生活状况都不是太理想,当遭遇纠纷时,根本没有多余的经济能力花费高昂的律师费聘请律师为自己提供法律服务,结果农民工要么选择放弃维权,要么舍弃自己应得的法律权益而与争议的另一方进行协商解决。这种情况之下,不仅实体正义未能实现,程序正义也未能伸张,而原因却只是农民工没有经济能力去承担法律服务的费用。如果因为经济状况而无法享受这种“看得见的正义”,正义就无法以看得见的形式实现,它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正义。财富的拥有可以有先后之分,可司法公正的获得却不能有先后之别。不能因为目前农民工经济条件弱而抹杀了他们享受程序正义的权利,政府应该保障农民工与其他主体一样平等地进入司法救济程序,平等地接受法律的裁量,享受程序的正义。
(五)效率价值理论
效率是经济学的一个概念,指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由于社会资源的稀缺性,人类不断努力追求资源配置的效率,希望以最少的资源消耗获得同样多的效果,或者以同样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效果,以求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价值极大化。因此,效率是一个基本的价值范畴。[7](P137)没有效率的社会算不上是一个理想的社会。效率价值又分为经济效率价值和社会效率价值,经济效率指的是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效率指的是社会良性的发展和运作,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都要考虑成本与收益的问题。在两者不矛盾的时候,任何一方面的增加都是效率价值的成果。但在两者发生矛盾的时候,却不能牺牲其中一方面来追求另一面,如果忽略经济效率一味追逐社会效率,即使社会效率获得成就,这种效率价值不得不让人怀疑;相反,如果无视社会效率一味追求经济效率,即使取得经济上的巨大成功,却是以牺牲社会效率为代价的,从整体上而言,效率价值也会被大打折扣。所以,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各自的成本与收益关系中找到一个均衡点,实现价值的极大化。
当农民工发生纠纷后,由于农民工群体及其劳动争议的特殊性,解决争议的过程就是付出相关成本的过程,这当中既有经济成本,也有社会成本。如果农民工遭遇纠纷后政府不为农民工购买法律服务提供法律援助,对政府而言,它没有消耗任何经济成本,但它却失去了农民工以及周围群体对政府的信任,如果这个范围再扩大,会导致整个社会对政府失去信任。而政府如果要挽回每个社会成员对政府的信任,则需要更多更长的时间,社会成本增大了,同时需要花费更多的金钱,经济成本显然也增多了,远比当初的购买法律服务的费用要高得多。因此,由政府承担农民工的法律援助责任,为农民工的法律服务提供经费支持,不仅能获得农民工乃至全社会成员对国家和政府的信任,还能为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降低成本,实现社会资源的效率极大化。
三、政府承担农民工法律援助责任的法律依据
(一)宪法依据
在我国,宪法是母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我国《宪法》在序言中明确规定,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同时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第5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可见,宪法不仅是政府权力来源的合法依据,也是其行为的最高准则。
我国《宪法》第33条对公民平等权和人权做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而该条文是放在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下的,因此,平等不仅是一项原则,也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作为一项基本的权利,公民是平等权的权利主体,政府则是保障公民平等权实现的义务主体。同时,只要属于人权的范畴,国家和政府不仅要给予充分的尊重,还要设置相关的具体制度和运行机制来保障公民实现人权。另外,《宪法》第125条赋予被告人辩护权。可见,辩护权也是公民的一项权利。农民工因为法律知识匮乏,又因经济能力有限得不到法律专业人士的帮助而导致自身的权益无法得到维护时,农民工的平等权、人权、辩护权就无法实现,政府的行为就与宪法相抵触,存在违宪的嫌疑。因此,这些宪法规定实际上成为了政府对农民工承担法律援助责任的依据,而且是最高的法律依据。
(二)法律、法规依据
这里的法律仅作狭义理解,专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而法规包括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
《刑事诉讼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属于法律的性质。其第34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是政府承担刑事辩护法律援助责任的法律依据,包括申请辩护和指定辩护两种。该条虽未明确规定农民工可享有刑事辩护法律援助的权利,但将经济困难作为申请刑事辩护法律援助的一个基本条件,农民工正是经济上的弱者,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应为其提供辩护。而对于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农民工,属于指定辩护的范围,政府应该承担这方面的责任。
《法律援助条例》由国务院于2003年7月制定,是我国第一部有关法律援助的行政法规。其第3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明确规定法律援助为政府责任,责任主体是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不包括乡镇政府,而责任形式主要是提供财政支持。另外,其第10条对因经济困难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采用列举的方式进行规定,“(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将劳动报酬纠纷与社会保险待遇纠纷纳入法律援助范围,而这两大类纠纷实际上是以农民工为主要援助对象的。再结合第3条的规定,很显然,政府负有为农民工承担法律援助的责任。
各省市的《法律援助条例》是政府承担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地方性法规依据。全国很多地方的省级人民代表大会或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市级人民代表大会或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制定了各自的《法律援助条例》,用于指导本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活动。目前,所有省级单位都有自己的《法律援助条例》。许多市级单位也有自己的《法律援助条例》,如广州、深圳、杭州、成都、福州、大连、太原等。这些地方性的《法律援助条例》都不同程度地为农民工法律援助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法规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依据
许多地方的省市人民政府在自己的《法律援助条例》基础上以地方性规章的形式制定相关《实施细则》《实施办法》,对各级政府具体实施法律援助给予了更为细致而明确的规定。
1996年6月司法部下发《关于迅速成立法律援助机构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成立法律援助机构,但未对法律援助做更深层次的说明。199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共同下发的《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对法律援助的刑事方面规定较为详细。而关于法律援助最为明确和全面的全国规范性文件,应属1997年5月《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该通知对法律援助的意义、定义、对象、范围和形式等做出了全面的规定。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发布《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首次对与农民工权益密切相关的劳动报酬、工伤等事项做出“可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的规定。
2009年12月财政部和司法部下发《关于印发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实施与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该通知明确规定农民工、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和未成年人是实施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的对象。第10条规定,地(市)和县(市、区)法律援助机构是主要项目实施单位。这些规定也是政府承担农民工法律援助责任的依据。
四、政府承担农民工法律援助责任的现实依据
(一)农民工人数众多,易生群体性事件,威胁社会和谐稳定
一方面,农民工数量十分庞大且每年都在继续增加。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3年农民工总量继续增加,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689 4亿人。[8]加上与他们息息相关的家人,保守估计,这部分弱势群体可能涉及六亿多人,接近我国一半人口的利益。如此庞大的一个群体,如果其受侵害的权益因得不到法律专业人士的帮助而无法实现,那么我们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的和谐社会又如何实现呢?另一方面,近年来农民工权益无法实现导致极端、过激行为甚至群体性事件不断,如果他们能及时得到法律专业人士的帮助,合法权益及时得以维护,事情也就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许多悲剧也就不会发生。
(二)农民工流动性大,单靠自己维权成本太高
由于农民工无法长期在某一个城市或单位工作,流动性非常大,一旦发生争议必然要重新找工作,甚至换城市找工作,这就会与劳动争议的管辖规则、解决时限发生冲突。一方面,劳动争议一般由用人单位所在地的仲裁委或法院管辖,而对于已经更换城市的农民工来说,回去仲裁或起诉、应诉的成本都显得太高。另一方面,从劳动争议的解决时限来看,劳动仲裁裁决的最长期限虽只有60天,但对于经济上处于弱势的农民工而言无法承受这个期间的各种风险,如果算上仲裁时效中断的期间,远比这60天多得多,这就更进一步加重了农民工的负担。而司法诉讼的解决时限就更长,一审审限最长6个月,二审审限最长3个月,加上再审和执行的时间,一个争议可能需要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如果政府为农民工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农民工签署授权委托书后,就可以安心的将争议事项交由法律专业人士来完成,而不必担心因仲裁或诉讼而承担的各种风险。
(三)农民工各方面素质偏低与法律的理性之间存在冲突
由于劳动争议处理程序复杂、期限较长,且农民工有些方面素质不足,特别是法律知识贫乏,一旦遭遇劳动纠纷,他们往往不能理性地面对仲裁和诉讼,极易激起这些弱势群体的心理认同,从而引发群体性事件。另外,法律在追求实体公正的同时,也追求程序公正,当农民工提出的诉求不能得到满足或提出的诉求不合理甚至不合法时,就需要有人对他们进行耐心地劝说,引导他们对法律问题形成正确的认识,否则极有可能激发他们与国家政府之间的矛盾。不管是前一种情况还是后一种情况,都需要法律专业人士对农民工进行引导和劝说。
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为弱势群体提供的旨在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一项重要制度。农民工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地位上处于劣势,且数量众多,政府承担农民工法律援助责任,不仅是道义和现实的需要,也是政府依法行政,构建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的要求。
参考文献:
[1]朱茜.责任政府的概念、特征与实现方式[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4(8).
[2]裴旭东.我国政策责任评价体系与责任政府对接机制探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
[3]张成福.责任政府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2).
[4]刘海,张雅丽,王彦娜.论公共行政精神与责任政府[J].管理现代化,2014(5).
[5]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6]卓泽渊:法的价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7]谢鹏程.基本法律价值[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
[8]国家统计局.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2014-05-12)[2014-10-20].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5/t20140512_551585.html.
(责任编辑:林泓)
The Basis of the Government's Responsibility for Offering Legal Aid to Migrant Workers
LIU Chun-ming
(College of Tourism, Sanming University, Sanming 365004, China)
Abstract:Legal aid is a free legal service system to the poor. Because of the disadvantages a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atus, migrant workers have been generally considered vulnerable groups in our society. To obtain the legal aid is a kind of due right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o provide legal aid for migrant worker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Social contract theory, the principle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substantive equality theory, procedural justice theory and efficiency value theory are the legislative principle of the government's responsibility for offering legal aid to migrant workers. Meantime, the constitution, laws, regulations and other regulatory documents and migrant workers' characteristics provide legislative authority and reality basis for the government to bear responsibility.
Key words:migrant workers; legal aid;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作者简介:刘春明,女,湖北黄石人,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行政法。
收稿日期:2015-01-05
doi:10.14098/j.cn35-1288/z.2015.01.008
文章编号:1673-4343(2015)01-0040-06
文献标志码:A
中图分类号:D9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