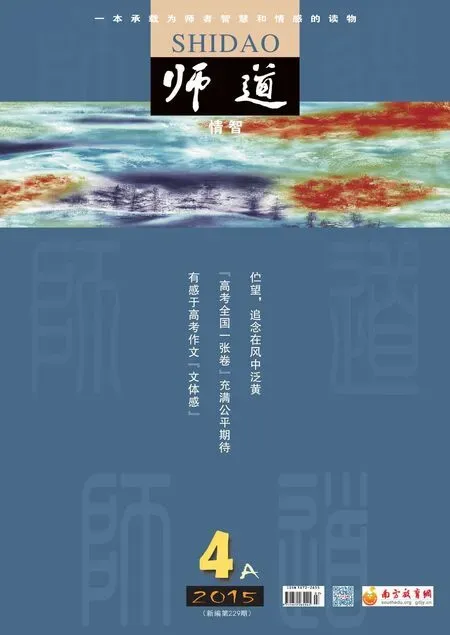伫望,追念在风中泛黄
——读叶圣陶感言
2015-04-09佘蜀强
佘蜀强
伫望,追念在风中泛黄
——读叶圣陶感言
佘蜀强
近几天,空中多了风的影子。在起风的日子里,我总喜欢合上窗帘,在书屋的角落里翻阅一些泛黄的书卷,追念那些远逝却滚热的智慧韶光。叶圣陶先生,便是那厚重书卷中的一抹熟悉的炙热。
一
叶圣陶,1894年10月28日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他是我国现当代著名的小说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在颇多熠熠生辉的名号中, “教育家”是一个既让人熟稔,又令人生涩的名词。但凡略懂语文教育史的人都会明晓,叶圣陶是 “语文三公” (语文教育界的三位老前辈,其他两位是 “吕叔湘”先生与 “张志公”先生)之一,为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奠定了平民化发展的路基。然而,叶圣陶先生早年的那段从教历程却鲜为人知。
叶永和 (叶圣陶之孙)在 《一百年前从事小学教育的叶圣陶》一文中这样说道:
“1912年3月6日,是叶圣陶从教的第一天。学生们看到新来的老师都窃窃私语,说他个子 ‘短小’,不像教员。叶圣陶报之一笑,‘人之以貌取人也’。他看到聚在一起的学生们 ‘儿童之态各殊,而各自多趣’,也不免喜欢……1912年,叶圣陶作了九个月的小学老师之后,在最后一天的日记中对自己作了一个非常悲观的总结: ‘回溯此一年中我圣陶之命运,进步乎?退步乎?乐乎?忧乎?圣陶不配做小学教师,自知之人知之。而竟低头下气,强颜以做之,不乐也。可知圣陶无止境者也。而竟自封于此,日事教授闲荡之外他无所事,其无进步又可知也。呜呼,度此一年,我甚不乐之,我欲追而使之还,已是不及,奈何奈何!酒醒灯昏,我欲一哭。’”
可以猜想,多数人读毕上述文字后,内心的情感是异样复杂的。我们很难相信这位后来的 “语文教育学界巨擘”曾拥有如此揪心的亲历。然而,静心思量,我们却会愈发感受到那段 “坎坷”中闪烁着非凡的价值辉芒。在教育的历程里,成功固然诱人夺目,然而,值得我们沉思的,是那些功成名就背后的挫折与失落。或许,缺失了那段难忘的 “小学从教经历”,叶圣陶可能仍会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但却可能与 “语文教育家”失之交臂。
近来,我批阅了一些学生习作。其间不乏文质兼美的文章。然而,现在的我却萌生了一个念想:是否可以暂将那些美文放置一边,而将更多的揣摩与思索放在那些有待提升的习作上呢?或许,叶老曾经的那段耐人寻味的经历给予了我一个明晰的回答。
二
“他19岁开始写文言小说,24岁用白话写小说、新诗。1921年,他27岁,成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支持沈雁冰革新 《小说月报》,与沈雁冰、郑振铎等共同筹办文学研究会之 《文学旬刊》,在《晨报副刊》发表40则 《文艺谈》,在 《儿童世界》发表童话。28岁那年,他和同人一起创办了 《诗》月刊,出版短篇集 《隔膜》,与周作人、朱自清等合著出版诗集 《雪朝》。29岁,出版童话集 《稻草人》,短篇集 《火灾》……33岁,出版为商务印书馆选注的 《传习录》、 《苏辛集》。34岁,长篇小说 《倪焕之》连载于 《教育杂志》,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上面是叶老一生成就的简略琐片。实际上,我们大可不必一味地赞赏,因为那个时代不乏大师精彩的履历,如:
“黎锦熙 (1890—1978),语言文字学家、词典编纂家、文字改革家、教育家。17岁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史地部;22岁开始编辑小学教科书;26岁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28岁促成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及常用字的标准读音;30岁促成教育部改定小学、初中 ‘国文科’为‘国语科’,取消小学读经,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
“夏丏尊 (1886—1946),文学家,语文学家。19岁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弘文学院;27岁发表 《学斋随想录》;36岁与李维桢合译《社会主义与进化论》;37岁将日译本 《爱的教育》译为中文……”
每每读到这样的叙录,我总喜欢 “不知天高地厚”地尝试着拿自己去比对:我在正规的文学杂志上发表过文学作品吗?我在语文专业领域发表过专业论文吗?我在文学、语言、文艺理论等方面有独特的爱好吗?显然,脑际中虽有近200篇大小杂乱文章,却始终不敢轻易翻出一篇。
综观大量语文教学与教育名家的成长历程,均离不开 “阅读”与“写作”两方面的修为。谁能在这两方面有所突破,便比别人多了一份先机。大量的阅读,固然不能少,阅读些什么,更值得关注,“文学作品” “理论文献” “考试测评”均需要分类研读,融会贯通;大量的写作,固然不能少,写作什么,更值得思考, “文学作品创作”会让我们持有一份文学语言的敏感, “学术论文写作”会让我们拥有一份缜密深邃的思维深度……然而,可惜的是,现在很少语文老师提笔写作了,更甭提 “举一反三”!
或许,大师的履历,不仅仅是生命的印痕与见证,更是一种对生命的不断敦促与鞭策。
三
“一个教员拿了几张油印的讲义 (或现成的国文课本)在课堂上逐字逐句的讲解。下面听讲的学生真是七零八落。那种精神涣散的样子,实在让人看了气短。坐在前面的几个学生,虽然 ‘一心以为鸿鹄将至’,表面上总算还在那里看讲义,至于坐在后排的学生,有的在讲义旁边放着英文教科书,自己在那里阅读;有的低头做他的算学题目;有的女生还在桌子下面打手工;有的偷看小说,有的简直睡着了。教员勉勉强强敷衍完了一点钟,夹着讲义去了;学生也就一哄而散。”
上面这段文字,出自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朱经农的真切描述。细细体味,虽暌隔近百年,语文课堂的这种困窘之况,依然未变,甚而有愈演愈烈之势。笔者亲历过的语文课 (当然包括自己的语文课),多多少少都有上面所描之景的印证之态或者照应之嫌。
叶老也曾说:
“他科教学的成绩虽然不见得优良,总还有些平常的成绩;国文教学却不在成绩优良还是平常,而在成绩到底有没有。……这并不是说现在学生的国文程度低落到不成样子的地步了,像一些感叹家所想的那样;而是说现在学生能够看书,能够作文,都是他们自己在暗中摸索,渐渐达到的;他们没有从国文课程得到多少帮助,他们能看能作,当然不能算是国文教学的成绩。另有一部分学生虽然在学校里修习了国文课程,可是看书不能了了,作文不能通顺,国文教学的目标原在看书能够了了,作文能够通顺,现在实效和目标不符,当然是国文教学没有成绩。”
叶老上番言说,固然有悲情决绝之意,但处于人生晚年,历经沧桑的叶老,在悲绝的言意之下,也有着 “事实固然如此”的本源根因,绝非骇人听闻。综观当下语文教育教学界,热词、新词丛生迭出,然而,语文教学与教育却始终低迷徘徊,并未从根本上超越百年以前的困局。我想,这样的结论并非为过,也不是我个人的标新立异之言。当下不少悲悯而敏锐的语文教育教学专家,也发出过不少类似的声音。百年以来,教学内容、方式方法等诸多语文教育教学的微观研究领域,都在不断的 “反复”乃至 “重复”中止步不前,甚而,“语文学科”究竟姓 “什”名 “谁”的问题都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语文’大概是当代中国最为诡谲的一个词,关于 ‘语文是什么’的问题虽然研讨很多,但多为自说自话,难以达成共识。梳理百年 ‘语文’用项,还原母语课程名称本义,是语文学科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客观地讲,只有正本清源,才能让 ‘语文’回归本义,即将 ‘语文’解释为’语言 (口语)文字 (书面语)’,而且也只有回归本义才能让 《语文课程标准》中 ‘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表述合乎逻辑。值得强调的是,回归本义并不意味着我们是以工具性来反对人文性,因为无论是海德格尔 ‘语言是存在的住所’还是伽达默尔 ‘语言是人类拥有世界的唯一方式’等理论都可帮助我们认识‘语文’的丰富内涵。”
这是山西大同大学张毅教授发表在 《语文学习》2013年01期的一篇题为 《呼唤母语课程的重新命名——关于我国母语课程命名的考证与思考》的文章节选。虽属断章撷意,但透过潜隐在字里行间的缕缕文气,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难以拂去的困惑与执着。这份精神早已远远超出了语文教育教学的本身,因为,在这篇长文的标题中,我们会汲获几枚宝贵的词汇 “呼唤”“命名” “考证”与 “思考”。综观当下教育教学,很多言说都是围绕这几枚核心词汇展开的。而这些言说往往是从 “叶圣陶”这样的大师起步的。
我始终感到,当面对争鸣丛生的教育教学时,我们需要一个时代的积淀与指引。民国是一个属于大师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回望的时代。
阅读叶老,不仅仅会读出感佩,或许我们更应该读出一份沉静。
在大师面前,我们能够做的可能只有——伫望。风乍起,将一抹思念,泛成一缕微黄,飘向那个“大师远去”的地方,将一种敬畏与孤寂留在了 “再无大师”的当下。
(作者单位:四川资阳市乐至县乐至中学)
责任编辑 李 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