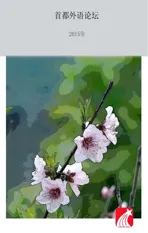二十世纪初的北京: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
2015-04-08首师大外院英文系北京语言大学在读博士秦晓星
首师大外院英文系 北京语言大学在读博士 秦晓星
二十世纪初的北京: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
首师大外院英文系北京语言大学在读博士秦晓星
本文探讨20世纪初欧美作家文学作品中的北京形象,以点带面地探讨20世纪初北京形象在西方文学中的变迁轨迹与丰富形态,揭示出北京作为异国形象的成因与文化意义。从而进一步探索北京作为异国异族形象被创造的过程,关注欧美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如何理解、描述和阐释作为“他者”的20世纪初的北京。
北京异国形象文学形象文化想象跨文化理解
绪 论
当今世界,全球化全面推进。面对着文化冲突的不断发生,加强研究异质文化间的相互交流与理解是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研究的重要任务。从更大的视角来观察,全球化进程中东西方的文化关系紧密复杂,而且二者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东西方文化在碰撞、冲突中寻求着对话、融合,在引进、借鉴中进行着排斥和批判,在共同性中寻找着差异性,在差异性中寻找着共同性”①刘登阁等:《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
北京,作为有着古老文明的中国的首都,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北京在20世纪经历了大起伏,大蜕变,尤其是“北京到了民初,历经前所仅见的时代裂变,才真正体现了时间流转、传统纷呈的可能”②陈平原、王德威:《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序二”,第2页。。北京城蕴积丰厚,“不论作为文化场域或是政治舞台”,“在过去与未来、传统与摩登间的曲折发展”③陈平原、王德威:《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序二”,第2页。,都为域外的中国文化研究者提供了不同的文化、历史、文学角度,勾勒了20世纪上半叶北京的多重视景。
一 “北京”之异国形象的阐释
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形象”主要指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它一方面研究的是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或描述,另一方面体现了一种跨种族、跨文化的性质。异国形象的创造是某种文化特征,也就是说,“它表达了存在于两种不同的文化现实间能够说明符指关系的差距”④[法]达尼尔-亨利·巴柔:《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孟华译,见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1页。⑤姚颖娟:《〈在北京最后的日子〉中的北京形象》,山西:中北大学学报2011年第27卷第1期,第104页。。
不言而喻,形象学既可以考察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又可以考察中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是西方作家笔下出现频率最高的中国城市之一,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西方人眼中的异域中国的形象⑤。关于西方作家对于北京的文学想象,因阶级不同,种族不同,身份不同,年龄及文化水准不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北京形象。美国作家赛珍珠 (Pearl.S. Buck)笔下的北京,传统,宽容,大气,随和,北京是她魂牵梦绕的情感归宿;对于瑞典汉学家喜仁龙 (Osvald Siren),北京的城墙和城门让他迷恋,而北京拥有仙境般的环境;而英国作家哈罗德·阿克顿 (Harold Acton)的北京,则是让人眷恋不已的心灵的归宿,是能够拯救西方顽疾的精神体现:“他发现自己竟那样强烈地想念着北京,就像宠物依恋着它的主人……他在古都北京呼吸到一种宁静的气息,任何事物都让他沉浸在超自然的、泛神论的幻想与惊喜之中”①Harold Acton,Peonies and Poni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1,p.1-2.转自姚颖娟:《〈在北京最后的日子〉中的北京形象》,山西:中北大学学报2011年第27卷第1期,第104页。。
二 “北京”之异国形象的流变
异国形象的流变是形象学的又一个研究重点,分析异国形象的流变需要立足于特定的文化语境。考察西方文学和文化中的北京形象的变迁,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内容。作为异邦的千年古都,古老北京的独具特色的建筑文化、历史地位、风俗民情,以及北京人的情感生活,都是西方作家借以产生幻想和表达欲望的载体。几个世纪以来,北京和北京文化在西方不同时代呈现出不同形象。17世纪以前的欧洲对东方及中国大都采取褒东贬西的态度和写法。写于14世纪的《曼德维尔游记》把关于东方的诱人景象吹嘘得眼花缭乱,把东方描述成了神话般的乌托邦世界;《马可·波罗游记》把北京描写得就像天堂一样。而写于14世纪的《曼德维尔游记》把关于东方的诱人景象吹嘘得眼花缭乱,把东方描述成了神话般的乌托邦世界。曼德维尔其实是“英国散文之父”须约翰 (John the Beard)的托名,人称“座椅上的旅行家”。他的游记在英国游记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它“首次或几乎是首次尝试把世俗主题引入英语散文领域。”作者其实没有到过中国,因此《曼德维尔游记》书中关于帝都的描写,多从中世纪四大探险家之一鄂多立克的游记脱胎出来,只是更加离奇,赞叹之情也更为强烈。当时的欧洲人很少有人怀疑曼德维尔虚构游记的真实性和天花乱坠的帝都镜像。在这神奇斑斓的幻境里,真实与传奇难以分辨,想象与欲望紧密交织,共同构造出人们心目中的乌托邦。因其虚构,这部浸润基督教教义和骑士精神的散文小说,才能更真切地反映出西方人集体无意识中的帝都想象。在充满奇迹的故事中,东方帝都的真实形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如何演变为神话与传说,如何作为“他者”体现着欧洲中世纪晚期文化中的世俗欲望。
对17世纪的英国人而言,富裕强盛的中国是他们向往的理想国,中国渐渐成为一个富有智慧与道德的邦城,整个欧洲都可以听到赞美中国的声音。而这种对中国的乌托邦式的幻景一直延续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欧洲的中国文化热关注的是中国的异国情调,特别是对中国园林艺术的追求。19世纪后,随着资本主义的新一轮扩张,中国形象开始变得黯淡了,中国文化热在西方出于退潮期,在启蒙运动中出现的中国巨大身影就这样慢慢远离,失去了它往日的光辉。1792年,英国外交官马嘎尔尼携带英王信件出使中国,把一个行将灭亡的中国形象带回了西方。40多年后,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形象更是一落千丈。《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一书作者英国女作家立德夫人在她的另一部著作《我的北京花园》中,描述了1900年至1902年间,在北京短暂居住并在周边旅行时的见闻与感想。其时八国联军大举侵华,立德夫人字里行间时时流露出对中国古老文化遭到战乱洗劫的痛惜。
在“英国文学里的中国题材:1793—1945”阶段性研究中,葛桂录①葛桂录:《“中国不是中国”: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形象》,福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第64页。指出:英国文学里设计中国题材的作品,所展现的其实是英国作家对中国的想象、认知,以及对自身欲望的体认、维护。中国对于一个英国作家,是作为一个“他者”。英国作家正是在这种对他者的想象与异域形象的描绘中,不断体悟和更新着自我的欲望。就像英国当代著名汉学家雷蒙·道森②雷蒙·道森:《中国变色龙》,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转引于葛桂录:《“中国不是中国”: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形象》,福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第64页。所说,“欧洲人对中国的观念在某些时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趣的是,这些变化与其说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不如说更多地反映了欧洲知识史的进展。”
此外,西方不仅把“他者”作为参照,而且还要从非西方文化中吸收新的内容。周宁①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9页。在《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一书中说:“中国作为西方的他者,是西方观照自身的一面镜子,西方从中看到自身倒置的现实。”东方救赎作为西方文明危机下的一种精神诉求,表明了西方人对自身文化的批判与反思。借助中国这面异域文化之镜,西方得以理解自身,反观自身,超越自身文化的困境。
三 北京: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
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对话的过程中,相互影响是历史的必然。赵毅衡在《对岸的诱惑》中写到了西方人来到中国,看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
事实上,早在第一次世纪大战爆发前后,西方许多知识分子就感到西方文明面临着历史性危机。面对战后西欧出现的文化危机,一些西方有识之士开始了自己的思考,他们不是求助于西方文明的两大源头——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和希伯来文化,而是向东方文化寻求救世救国之道。他们希望从中国文化中发现与科学精神相融洽的秩序信念,以保证自己在不断创新的同时有一个稳定、和平的世界秩序,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西方的一些著名学者曾在中国,尤其在北京居住、任教,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些人中就有赵毅衡先生在其书中提到的,比如英国知识界教育界的领袖人物狄金森,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源头的新批评奠基人I.A.瑞恰慈,英国新批评文学理论的先驱W.燕卜荪等。
(一)狄金森的中国偏爱
在20世纪前30年,狄金森是英国知识界教育界的领袖人物,在促进中西理解交流上,起了关键性作用。1912年,他在中国漫游了大半年,从香港到上海,从北京南下齐鲁。1914年他出版了考察报告《论印度,中国,日本文明》。在比较三个民族文化时,并不隐瞒各种文化的弱点,并且也公开他对中国文化的偏爱,认为中国文化更高一筹。他在报告中明确宣称,“现代化对中国只是个适应或采用问题”,原因是“中国固有的生活态度,与西方现代非常接近,比中世纪欧洲与现代的距离近得多”,“儒家思想很容易翻译成西方的实证主义”。以上观察,可能是新儒家思想的最早阐述。狄金森的结论几乎让人瞠目结舌:“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就是民主的,中国是西方民主主义的理想境界”①赵毅衡:《对岸的诱惑》,四川: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57页。。我们应该看到,狄金森是在1914年写下这些话的。此时整个欧洲被抛入空前惨烈的大战,西方民主本身看来正走向盲目的自杀。血腥的战争对狄金森的人本主义乐观精神是个重大的打击,“使得以获取一种稳定、和平与持久的宁静为归旨的生存期盼成为”他和这一时期其他“一些西方人的心理指向”②容新芳:《I.A.瑞恰慈与中国文化:中西方文化的对话及其影响》,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1页。。
在狄金森的影响下,以希腊与中国双模式来建立现代价值,成为一批英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在狄金森的学生中,就有理论家I.A.瑞恰慈,以及更年轻的文学家W.燕卜荪等人,都对中国抱有热情。
(二)瑞恰慈的中国情结
中国和英国天各一方,由于巨大的文化差异,双方要想了解各自真实的状况,仅从外部考察异国文化或者仅从内部阐释自身文化都是不够的,所以交流和对话成为历史的必然。具体讲,20世纪初随着中英间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增多,更多英国人来到中国。瑞恰慈是中英文化交流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从他身上体现的中西方文化的对话与影响,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
深受中国文化巨大影响的瑞恰慈,最早是于1927年到达北京的。中国给他留下美好的感觉,以至于他一生到中国六次,数度准备长居中国。瑞恰慈在华度过了近五年的时光,并在北京翻译了《孟子》并著有《孟子论心》。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代发生巨变的世界环境中,尤其是为了弥合一战给精神造成的创伤,瑞恰慈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东方和中国,希望从中国文化里寻求拯救西方文明危机的出路。他深刻意识到东西方文化交流对话的急迫性,认为复兴古老的中国思想传统将会使人类重新获得一种和平相处的和谐思想。他从中国文化中汲取了大量的文化营养,同时也对中国的文艺批评理论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可以说,除西方文化以外,中国文化是他思想的最大源头。
1927年来华后通过与中国直接接触,瑞恰慈了解了中国文化的不同层面。1930年瑞恰慈在《专题论丛》杂志上发表《信仰》一文,他在文章的前言中介绍了中国文化在思想上对自己的巨大影响:“北平的生活对作者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呀!①容新芳:《I.A.瑞恰慈与中国文化:中西方文化的对话及其影响》,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6页。”。在中国期间,瑞恰慈更多的是以一种学习而非批判的姿态,以旁观者的身份耳闻目睹,设身处地地审视着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能深得中国文化精髓还得益于他在清华和燕京大学任教时与两所大学中学者的频繁交流,如与吴宓就儒家思想的深入研讨②吴宓:《吴宓日记》第4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292页。。
在瑞恰慈的六次来华中,他第二次来华的时间最长,对中国学界的影响也最大。当时他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授课。在中国第二次旅行结束时,对即将离开北平,瑞恰慈不舍之情溢于言表:“在这待得越久,就越喜欢这个地方”。他与夫人“在墙上写着:离开北平令人悲伤”。“在这里我们正在或者已经把北平的生活装进了心田。我们正在打点行装,当准备对这个城市说再见的时候,这里的一切都变得更具吸引力——不仅是人,还有景色和感觉”③容新芳:《I.A.瑞恰慈与中国文化:中西方文化的对话及其影响》,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60页。。瑞恰慈以其对中国文化的执著与热情在中西方之间架起了一座致力于真诚理解和学术交流的文化桥梁;他更像一盏灯,照亮了中英文化交流与发展的漫漫前程。
(三)燕卜荪的中国元素
威廉·燕卜荪长期远离英国或欧美热闹的“文化中心”。1937年燕卜荪到北京大学任教。1948年后,燕卜荪留下与北大师生一起“迎接解放”。燕卜荪在英国被公认是左派,近年来由于布鲁姆等英美批评界领袖的倾心推崇,燕卜荪历史地位更高。
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时代背景下,燕卜荪在诗学方面吸收了中国古典诗学中的朦胧理念,并在其诗歌创作中注入了中国元素。燕卜荪因其导师瑞恰慈与中国的关系,接触到中国传统文化,发现“朦胧”为中西诗学的交点,成功地吸收了中国古典诗学中的朦胧概念,并细化朦胧的类型,超越了其笼统性。燕卜荪两度来华任教,对东方佛教文化的仰慕和难忘的中国经历也使燕卜荪的诗歌题材有了新的转向,体现了中国文化。
(四)阿克顿的中国梦
哈罗德·阿克顿是20世纪初活跃在中英文化交流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在中国生活了八年,此间结交了大量中国文化人士,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与深刻的造诣。
阿克顿刚进入北京时曾一度陷入极度的狂热,这儿的一切都让他振奋,他立刻奔向系念已久的紫禁城,天天步行于一座座宫殿间,力图走遍这个伟大帝国皇城的每个角落。紫禁城的建筑艺术虽然随着时间褪色,但其与自然融合得天衣无缝,庄严肃穆依如往昔。在皇城之外,阿克顿时常在街上散步,这成了他观赏中国人的一个极佳视角,而他自己也成了北京无数人力车夫争抢与热议的目标,在阿克顿眼中,虽然这些人都过着贫苦劳碌的生活,而且并未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他们在精神上却非常快乐满足,这与西方人享受着物质充裕但精神上却忧郁空虚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牡丹与马驹》是阿克顿写的一本关于20世纪初在中国北京生活的外国人圈子的故事,其中极尽展示了阿克顿对于中国美的理想,通过一个叫菲利浦·弗劳尔 (Philip Flower)的忧郁的英国爱美家在中国寻找心灵归宿并最终通过佛教来达到精神涅槃的故事来陈述阿克顿心目中爱美者的标准及其东方救赎观。现实中的阿克顿看似保全了理想中的中国,甚至经历了中国的战乱被迫离开之后还是希望有朝一日能重返中国,但是他已经以个人标准对中国生活进行了选择,他选择的是四合院、文人雅士、鼓乐笙歌、琴棋书画的古典中国趣味,在一个陶醉于中国的西方人立场上享受一个西方人的中国梦境;而小说中的菲利浦在看破现实纷扰后选择了佛教来“四大皆空”,这与现实中的阿克顿向往佛教与基督教完美融合的主旨是契合的,即以虚幻来终止虚幻,而达到最终的心灵自由与宁静,此后便可永久不受干扰地沉浸在中国梦中,这也是阿克顿在20世纪初的持有中国理想的一个典型思路,这使他的中国梦在20世纪初的文化背景下显得特立独行。
五 结 论
本文考察20世纪初他国文学中的北京形象,以点带面地探讨20世纪初北京形象在西方文学中的变迁轨迹与丰富形态,揭示出北京形象作为异国形象的成因与文化意义。从而进一步探索北京作为异国异族形象被创造的过程,关注欧美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如何理解、描述和阐释20世纪初的北京作为“他者”的异国异族。
对于当今处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人来说,要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就要把以往割裂开来的“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作为一个整体过程来看。要从文化平等的理念,而非文化中心的理念看问题,以此达到全球语境下的多极均衡、多元文化共存的新文明。由此产生的跨文化理解要避免中西文化被看作相互隔离的两个异质实体的现象,使人们能够尊重他文化,同时也得到他民族的尊重。在跨文化理解过程中,要通过不同角度的分析做出多角度的价值判断,从而使我们了解文化中的普适价值,了解文化中的民族属性,在这个基础上,使各民族、各文化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