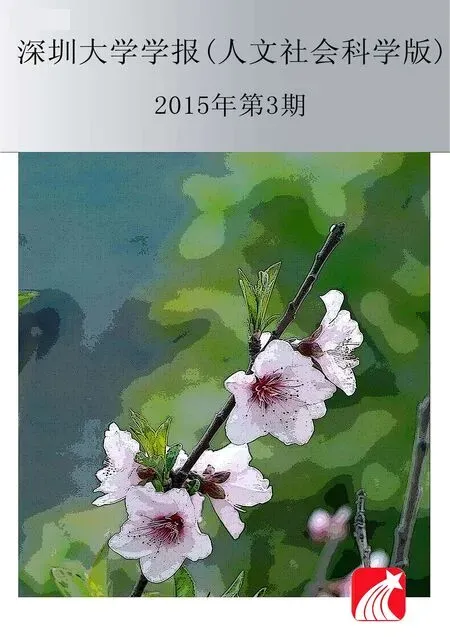安东金氏家族的女性教育与女性创作
2015-04-02左江
左江
(深圳大学文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安东金氏家族的女性教育与女性创作
左江
(深圳大学文学院,广东深圳518060)
虽然朝鲜社会的主流思想认为女性的职责是“中馈织纴”,“文墨之才非其所宜”,但士大夫阶层从家族传承与子女教育的角度出发,认为女性也应该学习《小学》、《内训》、《女诫》等等,这就为女性读书识字开启了门径。而安东金氏家族的男性对女性亲近书册尤为包容,在他们的鼓励与帮助之下,家族中出现了不少有“女中君子”、“女中大儒”之称的女性。再加上金盛达的倡导,更使家族女性文学达到繁盛,金浩然斋就是其中最出色的女性文人。由一斑窥全豹,从安东金氏家族女性文学的兴盛可以看出16世纪后期至18世纪中期朝鲜女性教育与女性创作的关系。
安东金氏;女性教育;女性创作;金盛达;金浩然斋
《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1]共收录了39种女性著作,其中《历代东洋女史诗选》、《洌上闺藻》、《李朝香奁诗》三种为总集,另有别集34种,专书2种。后36种著述共涉及39位女性作者,其中妾室或妓女11位,其他都为士族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士族女性求学之路更为艰难,但毕竟是“名父之女”、“才士之妻”或“令子之母”,家庭还是为她们营造了亲近知识施展自身文学才能的环境①。
在上述文集中,最能体现家庭创作氛围的是金盛达(1642~1696)一家。有《安东世稿》一种,为金盛达与其妻延安李氏(1643~1690)的唱和之作。又有《宇珍》一种,收录了金盛达和侧室蔚山李氏及二人之女的诗作。另有《联珠录》一种,也是家中成员的诗歌唱和集,金盛达与延安李氏生育子女8人,其中次女因嫁与王族密城君李栻,未能参与家人的诗歌唱和,其他人:金时泽(1660~1713)、李命世室(?~1702)、金时润(1666~1720)、李恒寿室(1674~1742)、金时济(1677~1742)、金时洽(1679~1699)、金浩然斋(1681~1722)、金时净(1685~1723)以及侧室蔚山李氏的唱和之作都收录其中。其中金浩然斋又是金氏家族女性中作品流传至今最多者,有《鳌头追到》、《自警篇》、《浩然斋遗稿》三种,仅诗作就达200余篇。
一
朝鲜女性创作并不很兴盛,这有其历史原因。徐居正(1420~1488)在《东人诗话》中称:“吾东方绝无女子学问之事,虽有英资,止治纺绩而已,是以妇人之诗罕传。”[2]女性以家事、女红为主,吟诗作赋非其本份,这是一种普遍的认识。鱼叔权《稗官杂记》卷四云:“妇人之职,中馈织纴而已。文墨之才,非其所宜。吾东之论,从古如此。虽有才禀之出人者,亦忌讳而不勉,可叹也。”②女性囿于舆论,不能在文学上施展才能,对此,鱼叔权只能一声长叹。
但另一方面,朝鲜社会的士大夫阶层从闺范的角度出发也很注重家中女性的教育。李瀷(1681~1763)云:“读书讲义是丈夫事,妇人有朝夕寒暑之供,鬼神宾客之奉,奚暇对卷讽诵哉?……其《小学》、《内则》之属,都是丈夫之任,宜默究而知其说,随事儆诲而已。若令闺壸缓于蚕织而先务执卷,则奚可哉?”[3]李瀷反对女性读书识字,但又强调女性要熟悉《小学》、《内则》等的规范。到李德懋(1741~1793)时,观念要圆融很多,他认为:“妇人当略读书史,《论语》、《毛诗》、《小学》书、《女四书》,通其义。识百家姓、先世谱系、历代国号、圣贤名字而已,不可浪作诗词,传播外间。”[4]虽然李德懋仍然认为女性不可以写作诗词流传世间,但从女性不可读书识字,到女性要“略读书史”“通其义”已是很大的跨越。这也就为女性亲近书册、接触文学作品保留了一点空间,所以从16世纪后期开始,读书识字、略通书史的女性越来越多,甚至不少人被赋予“女中君子”的称号。兹略举数例,看看士大夫阶层女性受教育的状况。
郑孝俊(1577~1665)之妻全义李氏(1597~1644),“性且夙慧,女红之暇,闻仲氏读书,辄能记诵,解其旨。”17岁嫁给郑氏,“诸子初学时,不就外傅,皆受夫人亲授。”李氏能亲自教育子弟,可见读书之多,识见之广,因此宗人皆称她为“妇女中君子”[5]。
李喜馨(1653~1704),字蕙英,她是密庵李栽(1657~1730)之姊,南阳洪亿之妻,“少聪明强记,尝在先公侧,闻所读书,辄能闇记,或尽一篇不错一字。先公异之,始授《小学》、《十九史》,皆不劳而通其义。如《二南》、《小雅》、《女教》等篇,皆其居恒所讽诵。……先公每称之曰‘女中君子’也。”[6]李喜馨所读典籍已不仅仅局限于《小学》、《女诫》之类,还包括《诗经》、《十九史略》等。
朴氏(1663~1702)为朴世采(1631~1695)之女、申圣夏(1665~1736)之妻。幼时父亲课子,她在旁窃听,往往成诵,朴世采于是教授她《内训》、《女诫》等书。此后,“女红之暇,惟终日闭门治训诫语。……又略通经史……间有评说,多有暗合于先儒所论者。且解缀文之法。”[7]朴氏的学习过程是女子接受教育的典型模式,从旁听兄弟们学习,到研读女性闺范,一直到了解经史,但她更具钻研精神,对可学可法之人之事要“精考博搜”,以至其书札、字画都成为闺阁学习的范本。
丰山洪氏(1677~1753),嫁安东金氏,“间从夫子受《毛诗》、《语》、《孟》、《小学》等书,旁及子史诸作者,每从容论古今事得失文章盛衰。或哦诗相答,翛然无怨尤色。”洪氏跟着丈夫不但学习了《小学》,还学习了《毛诗》、《论语》、《孟子》,又旁及子部、史部典籍。她知识面广,有见识,能吟诗,丈夫称她“有师友相长之益”[8]。
以上我们例举了数位生活在16世纪中后期至18世纪中期朝鲜士族女性的教育情况,她们都由《小学》、闺训入门,但个人的才识让她们不愿局限于此,由此开始诵读经史,旁及诗文写作。女性的学识一来可以帮她们成为更加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女性,二来也可以帮助她们课儿教女,让整个家族的学养传统、优良门风得以沿承。后人在提及她们“略通书史”时,也多从闺范的角度出发,所以这些女子虽然聪颖慧秀,知书识礼,但都不愿让外人知晓。
如上文论及的李喜馨虽通经史,但不以才学自炫,“终隐而不出。”[6]朴氏为文“并内而不出,虽兄弟鲜得以闻之也”[7]。又如金世濂(1593~1646)妻为文化柳氏(1602~1681),“通文词,亦不以文字示人”[9]。李维妻安东金氏(1705~1729):“观书过目成诵,尤喜读《小学·立敎篇》、《三纲行实录》、杜甫诗若而首,人鲜能知者,其识妇道甚。”[10]
士族女性虽有良好的知识素养,但由于闺范的约束,她们不愿意向世人展示自己的才能,甚至以此为耻。如何才能让女性走出这样的制约,让她们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价值,追求自我的实现呢?这就需要更多因素的刺激与鼓励。
二
朝鲜社会又称“两班社会”③,士大夫是社会中的特权阶层,他们又通过彼此联姻加强联系,巩固自己的权力。
金盛达出身于安东金氏,为仙源金尚容(1561~1637)曾孙,祖父金光炫(1584~1647),父亲金寿民。安东金氏是朝鲜历史上的名门望族,始于高丽太师讳宣平者,至仙源金尚容、清阴金尚宪(1570~1652)大盛,二人皆以名节著称。金盛达妻为延安李氏,号玉斋,为月沙廷龟(1564~1636)曾孙,祖父玄洲昭汉(1598~1645),父亲李弘相。安东金氏与延安李氏都是名门,两家世代联姻,关系紧密。
前已言及,16世纪中后期以后,朝鲜士族女性一般都有较高的知识素养,名门望族更是如此。李廷龟妻权氏(1569~1637),“组纴之暇,兼通《女训》、《内则》等书,即终身服膺。”因此被誉为“夫人之德,宜配君子”[11]。李廷龟与权氏有二子,即李明汉(1595~1645)、李昭汉。明汉妻朴氏“有高识至性,旁通经史”[12]。昭汉妻为李尚毅(1560~1624)女,也是名门之后,她:“女红之暇,能通书史大义。古今理乱得失,事是非,人邪正,无不了然分析,而亦未尝以文字自多于诸兄弟。”[13]丁丑之乱时,她为保名节自杀而亡,年仅39岁。
如此诗书礼仪之家培养出来的子女都很优秀,李明汉有四子,分别是一相、嘉相、万相、端相;李昭汉亦有四子,分别是殷相、弘相、有相、翊相,有“八荀”之称④。李氏一族人才济济,人才兴盛的背后,多少有着女性的功绩。
这是延安李氏的情况,可见女性读书识字在士大夫家庭中并不罕见,这对于女性整体素质的提高以及家中子女教育都有着重要的作用。随着识字女性增多、士族间的联姻,女性读书识字通达情理越来越普遍,这也就为女性进一步从事诗文写作提供了越来越宽松的环境。
我们将视线重新转回到安东金氏。金尚容有三子:光炯、光焕、光炫,光炫又有三子寿仁(1608~1660)、寿民、寿宾。金尚宪无子,过继尚宽之子光灿,光灿有三子寿增(1624~1701)、寿兴(1626~1690)、寿恒(1629~1689)。在金氏家族中,第一位引人注目的女性就是金寿兴的夫人尹氏(1626~1706),她为尹衡觉(1601~1664)之女。
前面我们说到金、李两大家族的联姻,实际上,其间还有一人非常重要,那就是尹衡觉。尹衡觉出自南原尹氏,同样身世显赫⑤。尹衡觉妻为坡平尹熻(1580~1633)之女(1602~1659),二人生三子三女,三女分别嫁给金寿民、李有相、金寿兴为妻,三婿又分别是金尚容、李廷龟、金尚宪之孙,而金尚容、李廷龟、金尚宪都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相臣⑥。
坡平尹氏虽也是名门,但跟金、李二族相比要逊色很多。那三大相之家为什么会跟尹氏联姻呢?名门望族为自己的子孙迎娶妻子,除了门当户对外,也很注重家庭教育及女子的品行。尹熻妻:“生长法家,擩染有素。及归公,得妇道甚,端庄和顺,夙夜无违。事兄嫂如舅姑,处妯娌间人无间言。教子女爱而严,御家众一以慈惠。平生制行有女士风,公常敬服曰:‘夫人真女中君子也。’”[14]由尹衡觉对自己妻子的“敬服”,我们可以看出那个时代对女性的理想设定,那就是:遵从丈夫、侍奉公婆(兄嫂)、友睦妯娌、教育子女、宽待下人。对这些要求,尹氏的表现可谓完美,所以她被称为“女中君子”,有“女士风”。这样的母亲养育的三个女儿,想来也是闺范甚严,能够担负起进入名门以后要背负的责任吧。
尹衡觉的三个女儿的确很出色,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寿兴妻,她“于女工之余,日随诸从兄弟后,听其讲论。经史子集靡不涉猎通晓,人以‘女中大儒’称之”。这是在历史上罕见的被称为“女中大儒”的女性,可见其学识之渊博。她:“记性绝人,凡史牒所载历代古今之变,贤人君子出处之迹,皆一经耳目终身不忘。于人家世系族派子孙远近,尤了然如指诸掌。虽好看书,而亦不肯作一句诗半行文,盖其心有所不屑也。……敦睦内外族党,待诸侄男女各有恩意。其男也,必与之讨论文字义理。女又爱护覆焘之故,皆乐于依归,归之如家。”[15]尹氏明达事理,记忆惊人。虽然不屑于诗文写作,但喜欢读书,并且与其他士族女性不一样,她从不掩盖对文字义理的喜好追求,常与家中子弟讨论。
尹氏之姊为金寿民妻,二人是姐妹也是妯娌,关系更加亲密,她们对文字的喜爱对义理的热衷必然会影响两家的子弟甚至影响到整个金氏家族。金寿兴与尹氏有二男五女,一女嫁与李晚成,“妣尹夫人女中士,夫人幼而擩染,略通书史。叔从兄农岩公昌协、百渊子昌翕常称赏之,故其见识若此。”[16]金昌协(1651~1708)与金昌翕(1653~1722)为金寿恒子,都是朝鲜时期著名文人。李晚成妻室少女时期因母亲的熏陶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略通书史”这一点在金氏家族中是被推崇欣赏的,她的堂兄弟们对此“称赏”有加。
三
安东金氏家族很注重女性教育,支持鼓励女子向学,家中男性也能欣赏女子的德与才,希望用文字为她们留下人生的印迹,让她们获得生命的永恒。
金寿恒娶罗星斗之女,二人生六子一女。唯一的女儿金氏(1665~1680)14岁时嫁与李涉,两年后因生产去世。金氏“聪明绝人,耳目所涉,虽细事亦不忘”。她虽未系统学习诗书,但在金氏家族中耳濡目染,也是“诗书洋洋”[17]。这是一位近乎完美的女性,金寿恒希望“其性行之懿……必须托之文字以永其传”,所以郑重其事地拜托“执事”其人:“以一言之重而不朽吾亡女者,非执事谁请哉?”[18]金寿恒想让自己的女儿通过文字得以不朽,其中寄托的不仅是一位父亲的哀思,传递的也是对女子生命的尊重。
金昌缉(1662~1713)为金寿恒之子,其一女金氏(1680~1700),6岁通谚文,8岁能为祖母罗氏“视出内代笔札”。出嫁后,仍亲近书册,“虽以勤执女红不得专于学书,而略通其义。稍得暇,又辄潜心焉。”[19]可惜的是,这样一位聪慧的女子21岁就夭折了。为了不让女儿的人生就此泯灭无闻,金昌缉为她书写行状,又请兄长金昌协为她写墓文,“若得我叔氏笔之以示后,则庶几死而不朽。”[19]此后,因昌协早逝,为金氏写作墓文的重任就落到了昌翕身上,昌翕感慨云:“呜呼,家有刘向而未蒙壸彝之收,是亦亡者之穷也。”[20]为女子立传扬名已是这个家族的男子义不容辞的职责,昌翕甚至认为如果不写作这篇墓文就好像家有刘向却不写作《列女传》,是死者的遗憾,也是家庭的损失。同样,在墓文中,金昌翕除了颂扬金氏的品行,也不会忘了对她读书识文通达事理的夸奖。
金寿恒、金昌缉两代人都表达了要通过文字让女儿“死而不朽”的心愿,这其间是父女深情,也是对女性德与才的认同。男性的支持,男性的尊重,是对女性的极大鼓励,这在安东金氏家族形成了良性循环,家族中读书识字的女性越来越多,在此过程中,女性也更多地提高了自我认识以及对自身价值的追求。
金寿增妻曹氏(1627~1687)为朝鲜名臣曹汉英(1608~1670)之女,自幼聪明颖悟,“夏兴公(指曹汉英)钟爱而教迪,手书班氏女训而授之。”她16岁嫁与寿增,因知书识理,深为金氏一族器重。仁宣王后(1618~1674)令金尚宪谚解《列女传》进献,金尚宪竟将如此重要的工作交给了孙媳妇曹氏,“仁宣王后在嫔宫,命文正公谚释《列女传》以进。文正公使淑人书其草本,仍以与之。淑人潜心循览,有所兴慕。”[21]足见曹氏的汉文素养深得金尚宪的信任,而她在义理上亦当有出色的见解。
曹氏汉文素养的提升,也离不开丈夫金寿增的支持,当寿增看书时,曹氏“从旁领会其一二。至格言善行,有所感动;其于古今治乱、事非、人邪正,能有所分别。论事设譬,亦无不中。”对于曹氏跟自己谈论古今之事,寿增并不认为越礼,而是赞誉有加。金氏家族对女性求知采取的宽容鼓励的态度,必然令女性对自我价值有更高的期许。曹氏“雅有鉴识,略通《小学》、《内训》等书”,对此她已很不满足,“常谓不幸为妇人,不可舍己所事,学习文史,此为可恨”[21]。身为妇人,为家事、女红束缚,不能全身心投入文史的学习,这让她深感遗憾。曹氏看起来非常不本分的想法背后,是对自己聪明才识的自信,是对实现人生更大价值的渴望。而对于如此“不安分”的想法,做丈夫的金寿增并不以为忤,反将它写了出来大为张扬。安东金氏的家庭环境为女性才学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条件,这样的家庭中出现众多有“女中君子”、“女中大儒”之称的女子,甚至出现优秀的女性文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认为女子有出众的才学,也可以流芳百世,这是安东金氏家族中被普通接受的观念。金昌协之妻为李端相女,也就是月沙李廷龟之孙,二人有一男五女,其中一女成年后嫁与吴晋周。1689年,因“己巳之祸”⑦,金氏一门遭受重创,金昌协隐居乡里。这时,吴晋周室金氏(1679~1700)年方11岁,“始同弟崇谦受书十数板,文理辄通,能自读朱子《纲目》无所碍。日闭户手卷,兀然潜玩,几不省寝饭。居士(金昌协自称)怜而奇之,故不禁,曰:‘是女性静而拙,虽识书无害也。’因略授《论语》、《尙书》,亦不竟。然其识解明彻,虽遍读六艺经传者不能绝也。”金氏聪明灵秀,酷爱读书,以至废寝忘食,她所受的教育已不仅仅是《女诫》、《小学》,还包括《通鉴纲目》、《论语》、《尚书》等。尽管未毕读《论语》、《尚书》,但其见解高明已超越了遍读六艺经传的人。金氏的向学之心,不但父亲昌协赞赏有加,族中其他男性也对她进行鼓励,“伯祖谷云先生(指金寿增)、叔父三渊子(指金昌翕),每爱呼与语,待以女士。”[22]他们都很赏识其才学、见识,并不以一般女子视之。金氏17岁嫁与吴晋周,晋周是吴斗寅(1624~1689)子,也是名门之后,其母为闵圣徽(1582~1647)女,闵氏(1625~1646)也曾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少受《小学》、《家礼》,略通大义”[23]。这两代女子都有知识有学养,但都禀守女子职守,闵氏“绝不自炫”[23],金氏嫁入后也“唯斤斤服女事,归吴氏七年,吴氏之人未尝见其一视书,虽明仲亦然”[22]。
因为女性的身份,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才华,但身为金氏族中女子,并不甘心于此,她与曹氏一样,也有身为女子不得全心亲近书册施展才能的遗憾:“顾尝私谓兄弟:使吾得为男子,无他愿,但愿结屋深山,庋书百千卷,萧然老其中足矣。”对丈夫她也不以世俗的功名利禄要求他,而是希望他能以学术文章立世,云:“没世而名不称,君子所疾也。”这虽是对丈夫的劝诫,话语中流露出的则是对不朽的渴望。她在见到金昌协为一女子所写墓文后,竟然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尙得翁文为不朽其死,非不幸也。”能得昌协文字传世,死亦不朽。又对丈夫说:“吾女子也,恨无功德见于世,无宁蚤死得吾父数行文,以镌墓石。”自己不是男儿身,不能以功德立世,如果能让父亲为自己写墓文,宁愿早死。其对不朽的追求可谓强烈,所以金昌协称她为“女子身,儒士识”[22],评价很高,而这六个字也的确可以让金氏为后人铭记了。
四
我们再来看看金尚容一支,尚容子金光炫,生三子寿仁、寿民、寿宾。金寿仁(1608~1660)娶成弘宪之女(1607~1655),生二子盛遇与盛运;金寿民娶尹衡觉女,生三子盛达、盛迪、盛道。金盛遇(1630~1657)娶尹衡圣女,尹氏“仁孝淑哲,博通书史,凛然有士君子识度。”盛遇去世时,长子时杰5岁,次子时保还在腹中。尹氏也就担负起了教育二子的任务,“训厉诱掖,无异父师。”[24]尹氏的才学能够教育子女,胜任父师之职,可见其书史造诣之精深、见解之高明。
金盛运(1633~1691)娶柳庆昌女,柳氏(1635~1692)无子,视盛遇子时保如己出,“教时保必以正。幼时作诗,就先进取高等,孺人为之喜,既而告以伯氏润色,则愀然曰:‘无实取名,欺人也,何足贵乎?’”柳氏对沽名钓誉、弄虚作假等行为的厌恶,对于子弟品行的培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她“喜看《内训》、《女诫》等书”,还常让时保诵读历史给她听,这令她“特重名义”[25]。
尹氏与柳氏都诵读书史,有见识通达事理,妯娌相处如姐妹,“同巷居三十年,无纤芥瑕尤,宗党叹服”[24]。金氏家族非常注重女性教育,知书识理不但是对自己家中女孩子的要求,也是为子弟选择配偶的重要条件,这样,嫁出去的女儿不会做出有辱门楣的事,娶进来的女子也才能敦睦族人、教育子女,对整个家族的延续、素养的提升都会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盛遇有二子,一时杰,一时保。时杰妻为沈瑞肩女,时保妻为尹抗女。沈氏(1653~1711)深明事理,随任时,有罪犯想通过她来行贿免罪,她立刻“变色还却”,并写信告知时杰,“自是以后,衙门益肃然”。在家中,身处娣姒之间,更是一团和气,时保妻尹氏病重时,“尽卖女婚之需而继蔘茶。既丧哀恸,与哭姊妹无间。”[26]
沈氏与尹氏(1656~1702)感情深厚,相处30年无芥蒂,这既有沈氏的努力,也有尹氏的付出。尹氏亦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其父为坡平尹抗,其母为延安李氏,即李廷龟孙、李昭汉女,父母两系都出身名门。“自幼爱看《小学》、《列女传》、《女戒》等书”[27],在家时就“负女士誉”[28]。嫁入金家,她不但孝敬姑翁,还常劝勉丈夫:“所勖临民之道,则以当事忘怒为要。又谓居官不如守墓,辄以早赋归来为士敬诵之。”一子虽体弱多病,“不以忧爱弛训,尝授‘直方’二字。”对家中妇女,自己“爱看《小学》、《女戒》,以是斅妇女,申申讲绎,使知无古今之异,而乐循仪法”[28]。尹氏同样亦是士族女性的典范。
金寿民所娶亦是尹衡觉女,二人生三子三女,三子为盛达、盛道、盛迪。盛达一门都是文学之士,长子金时泽妻为罗星纬之女。罗氏从小亦学习《内训》、《列女传》、《女诫》等书,“德性夙就,终日执女工,间讽书,淸越可听。”嫁入金家以后,“时与子侄讲讨经史,至岳飞、文天祥等事,辄慨惋。笑谓明行曰:‘此等人汝能及乎?汝母虽驽,不让为王陵、徐庶母也。’”[29]罗氏将历史上杰出的母亲作为自己效仿的对象,以此鼓励儿子金明行努力成为气节之士。
家中女性有学养、明事理,对于家庭的和睦、子女的教育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在家族运转的过程中,男性也越来越意识到女性的重要性,对她们有着更多的尊重,这也就使金氏家族越发注重女性教育,鼓励她们展示才华,承认她们的生命价值,希望她们亦能不朽。
五
安东金氏家族相对开明,鼓励女子接触儒家经典,于是家族中出现了较多在经史方面颇有见识的“女中君子”。加上男性对女性生命与价值的尊重,令家族中的女性也有立德立言以求不朽的思想,这一切都为女性创作奠定了基础。但很明显,这还不足以成为家族女性文学兴盛的条件,所以我们还得看看金盛达的倡导之功。
金盛达“酷好吟诗,殆于成癖,一时词伯诸人皆叹服,往往阁笔而让一头”[30],其爱诗成癖成为他留给族中兄弟及友人们的最深印象,金昌翕云:“畴昔联枕我兄在,烂熳觞咏总于此。我兄风流故澹荡,我兄诗调即正始。芙蓉淸水以自赏,镂锦错绣非其喜。雅致清缘与周旋,傲兀诗情到处是。”[31]金昌协云:“清诗逼唐,耻言黄陈。不事琢刻,语或惊人。吟哦自喜,惟是为癖。身虽未达,意有余适。念昔北里,比屋以居。提挈追逐,朝暮相于。二三兄弟,如篪如埙。草生之池,花开之园。持觞赋诗,兄必为政。手劈华笺,以次相命。酒酣笔落,有烂篇什。喜色敷腴,在兄眉睫。一句之佳,赏逾和璧。引喉清咏,声出金石。豪情逸兴,泛澜尊俎。”[32]金盛达诗学盛唐,诗作以清新自然为主,不喜雕饰,不喜用典。金昌协在祭文中生动地描绘了金氏一族兄弟们诗酒唱和的盛况,金盛达年龄稍长,在聚会中亦是意气风发,颇有领袖风采。
族中兄弟奔走于仕途,终究聚少离多,金盛达就将他的诗情转移到了家庭中,鼓励妻子李氏与自己诗歌唱和。李氏为名门之后,读书识字略通经史自不待言,有了夫婿的支持,其才华也被激发了出来。《安东世稿》共收诗249首(包括李弘相诗一首),其中金盛达诗177首,李氏诗71首。
金盛达采取了多种方式鼓励妻子写作,一是对其诗作进行指点,如《安东世稿》第三首《次内诗》小序云:“十年前,客游长安,君在鳌山本家,以诗寄之,律法误处,略加点改。”[1](P328)第一百首《寄女儿》题下云:“语势不成处,以其本意点改云。”[1](P347)这样的指导对李氏诗作水准的提高大有裨益。二是唱和李氏诗作。李氏共71首诗,每首金盛达都有次韵之作。李氏的每一首作品都能引起夫婿的共鸣、回应,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自然也会激发李氏更加用心,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三是金盛达对李氏之作有很多评点,毫不吝惜夸赞之辞,“佳”、“甚佳”、“绝佳”等评语随处可见。如李氏次韵诗一首云:“海阔孤帆迷远天,白鸥渔子共闲眠。夜来水落无寻处,惟见云间明月悬。”金盛达评曰:“声韵自高。”他情难自已,云“室人诗清新高超,以其意效嚬赋之”,又唱和一首[1](P331)。李氏此诗清新有气象,与金盛达的诗学追求、审美趣味正相契合,所以他非常欣赏。李氏得到如此夸赞,也会增强写作的信心与兴趣吧。四是金盛达与李氏琴瑟和谐,闺房乐趣并不限于写诗,还有下棋等等,他们输赢的赌注非常雅致,那就是写诗。如《次韵江村二首》题下注云:“玉斋时围棋见负我,乃依约赌诗。卷中所不次三十五绝,随元作次第信吟追次。别立其各题次韵之意,则都付此耳。”[1](P346)这也成为金盛达鼓励妻子从事诗歌创作的一种方法。
一家之长的态度决定了家庭文学创作的氛围,金盛达对妻子诗歌创作的鼓励欣赏也会影响到自己的子女,李氏有一诗序云:“时与子女步出竹间扉,杂花生草,香气可爱云。”诗云:“西去平湖细路开,步穿修竹踏青苔。林花发尽清香散,处处留连坐石台。”[1](P335)李氏与子女同游,赏花闲谈,写诗纪事,金盛达又唱和诗作。如此温馨和睦的家庭氛围让子女们感觉轻松自在,父母写作诗歌的热情也会点燃孩子们创作的兴趣,帮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天性,展示自己的才华。
金氏家族相对宽松的环境成就了家中的女性,金浩然斋“受学于母夫人”[1](P515),跟兄弟姊妹一起成长的经历更成为她难忘的记忆,其《鳌头追到》中的作品多是与兄弟们的唱和之作,以及对鳌头故居的思念追忆,如《赠士鹰》一首云:“昔在竹西室,四弟与三姊。四弟皆稚昧,三妹粗解事。我在雁行间,相随不相贰。朝则共床食,暮则同枕睡。入则必分劳,行则必联袖。看花后园林,弄月前溪水。湛乐自怡怡,情爱若同气。”兄弟姊妹之间出入同行,一起看花赏月,如此惬意美好的时光却因为自己嫁作人妇戛然而止了,“女子有三从,聚散各千里。莫言死别永,生离亦无异。”[1](P467)如能在异地他乡与兄弟们相逢,喜悦之情可想而知,其《相逢行》记载云:“朝来乌鹊报喜信,忽闻门外马嘶声。借问山村有谁至,知是吾家三弟兄。相见还疑梦寐中,乐乐怡怡不自形。杯酒相酬又联句,一席笑谈千金轻。”[1](P465)与族中弟兄重逢,如在梦中一样,数人杯酒相酬作诗联句,谈笑风生。可见,金浩然斋在金氏家族中度过了快乐轻松的童年与少女时期,与兄弟们相处融洽,可以一起作诗论文,可以一起杯酒唱和,全无男女之隔阂。
宽松的家庭环境造就了浩然斋相对豁达的个性,她的性格与她的字号一样,颇有些男儿气概,如《乞米三山守》云:“浩然堂上浩然气,云水柴门乐浩然。浩然虽好行于谷,乞米三山亦浩然。”[1](P498)生活拮据向人乞米求助,这本是尴尬之事,她在诗中却表现得坦坦荡荡。这样的浩然之气还表现在她对国事的关心中,诗集中《国哀》、《闻嗣主即位》、《青龙刀》、《武侯》数首,有着强烈的政治意识。这是一位有男儿气概关心国事的女子,自然不甘于生命的湮没无闻,《自伤》云:“可惜此吾心,荡荡君子心。表里无一隐,明月照胸襟。清清若流水,洁洁似白云。不乐华丽物,志在云水痕。弗与俗徒合,还为世人非。自伤闺女身,苍天不可知。奈何无所为,但能各守志。”[1](P491)自己虽然有男儿之志,也读了万卷书,“万卷诗书空老床,今来方觉度寻常”[1](P505)、“静对明窗万卷书,圣贤心迹坐森如”[1](P501),但受女儿身的制约,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有怀仲氏四郡之游》云“平生有志行无地,摆脱梳妆壁镜羞”[1](P505),希望有所作为的想法同样是追求生命不朽的体现。
六
一般认为女性是儒家伦理的受害者,的确,文中提到的大多数女性都没有名字,我们只能通过她们的父系一族或夫系一族来确定她们在历史上的模糊坐标,但她们的聪明才智还是透过历史的层层迷雾散发出微弱的光芒,吸引着我们后人去发现她们、了解她们、感受她们。
这些士族精英家庭的女性都严格按照儒家伦理的要求与规范来塑造自己,我们看到她们一个个因不孕而忧郁,因难产而死亡,因多产而疾病缠身,但是她们以她们的坚忍与善良支撑着大家庭的正常运转,陪着父兄、夫婿一起经历战乱、经历政治斗争、经历家庭沉浮,她们是每一个家庭存在的基石,她们也以自己的言行引导着儿女的成长,这大概也是一种生命的圆融吧。
安东金氏家族的男性看到了这些女性的伟大,认识到她们生命的价值,为这些女性写下了一篇又一篇的文字,表达他们的赞美,传达他们的哀思,希望这些女子通过文字得以不朽的心声也一遍又一遍地在文字中传扬。这必然也刺激着女性自我反省,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才能与价值,由“女中君子”这样的道德楷模进一步发展为文学上的自觉,更充分地展示自己的才华。
当时间推移到金盛达这里时,家族传统、几代人的努力已经为他排除了障碍,所以他能相对轻松地鼓励自己的妻妾女儿从事诗文写作,而金氏家族中传承的女性自我意识以及追求不朽的观念也让家中女性比较容易接受这件事情,写诗作文似乎已是顺理成章,所以金盛达与妻延安李氏、侧室蔚安李氏及子女十有三人俱能诗,并都达到较高的水准。
在金氏家族中,女性释放自己的个性、施展自己的才华、追求生命的不朽是被认同被鼓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家庭对女性都会如此宽容,嫁作人妇的女子背负着家庭的各种重任,也就很难随情适意地生活了。金浩然斋在女性文人中留下了较多的作品,成就也较高,其诗作中有很多与金氏族中兄弟的唱和之作,也有对夫家宋氏一门子侄的赠勉之作。但有趣的是,在她的众多作品中竟然没有一首与自己的丈夫宋尧和(1682~1764)相关。宋尧和为同春先生宋浚吉(0606~1672)之后,也是文学之士,为什么金浩然斋的创作与他毫不相干呢?
朝鲜时代对女性创作有太多的偏见与制约,“我邦闺范不尚文辞,而或有知者不欲传于闺外,故世所难知”[1](P477),金浩然斋有着出众的文学才华,后人提及她时虽也会说她“通经史能诗文”,但更强调的还是她“治妇道愈谨”[1](P512)。
宋明钦(1705~1768)在祭文中描写了金浩然斋与子弟谈诗论史的风采:“退从诸兄,昵侍左右。探讨经史,点评诗句。开怀烂漫,间以讽谕。每去复来,所闻益新。”但这些都比不上她的德行:“呜呼叔母,允矣女士。有编警身,有书戒子。不泥陈言,自合理致。人或有文,孰如德美。推诚任眞,娣姒妯娌。下及卑贱,亦寘腹内。迨其哭丧,如恸己私。夫孰使然,无为而为。”[33]金浩然斋留下了200多篇诗作,但这似乎都不及她的《自警篇》以及诫子诗《付家儿》更有价值,正如宋明钦诗中所言“人或有文,孰如德美”。宋尧和在论及浩然斋时也说道:“夫人柔嘉慧悟,事姑以诚,事夫以顺。通书史,能诗文。诗调清楚,警句逼唐,然不以自衒,惟服女事,虽其夫未尽知也。”[1](P476)浩然斋的文学成就在她德行的映衬之下似乎已经微不足道,她跟大多数通经史的的士族女性一样“不以文字示人”“人鲜知之”,甚至连她的丈夫都不清楚她的成就。
我们以安东金氏家族为中心讨论了16世纪后期至18世纪中期朝鲜的女性教育与女性创作的关系。我们看到,虽然朝鲜社会的主流思想认为女性的职责是“中馈织纴”,“文墨之才非其所宜”,但士大夫阶层从家族传承与子女教育的角度出发比较注重女性的闺范,认为女性也应该学习《小学》、《内训》、《女诫》等等,这就为女性读书识字开启了门径。女性由学习闺范到略通经史,随着士大夫阶层之间的联姻,读书识字通达事理的女性越来越多。
安东金氏家族的男性对女性读书识字采取了包容鼓励的态度,他们认识到女性的价值,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字让家中的女性不朽,这也刺激了家中女性对自我价值的追寻,所以这一家族中出现了不少有“女中君子”、“女中大儒”之称的女子。
到金盛达时,他由自己酷爱写诗,进而鼓励家中妻妾子女一起投入到诗文创作中来,这就使金氏家族成为朝鲜历史上罕见的文学家庭。但并不是每一个家庭都会鼓励女性从事创作,所以围绕着金浩然斋我们看到一些特别的现象,一是她的作品与自己的丈夫全无关系,二是她作为出色的文学女性,后人对她德行的评价却超过了她的诗作。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朝鲜时代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女性教育与女性创作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女性要真正自由地抒写还有漫长曲折的道路要走。
注:
①参见左江《朝鲜时代的知识女性与杜诗》,载《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8辑,中华书局,2012年出版。
②见《大东野乘本》,第587页。
③“士大夫是指导李朝政治生活的社会统治阶级。‘两班’作为在官僚机构中供职的文武臣僚归根到底是由士大夫组成的。这就是后来‘两班’一词被广泛用来专指李朝社会有权担任文武官职的那部分人的原因。”“两班按实际惯例已被免除劳役和军役这些通常对国家应尽的服役义务。”“两班只在他们中间通婚,两班的地位当然也就成了世袭的。两班与那些不是两班的人甚至不住在一起。”“两班对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也不感兴趣,因为这些不过是农夫、手工业者和商人的职业。两班学者企望通过对朝鲜民众进行道德教化来实现一种理想的政治,但这实际上并不意味着他们准备消除社会身份的差别。”参见李基白著,厉帆译《韩国史新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第183-185页。
④李端相《静斋观集》卷一四《祭正字堂兄文》云:“逮至吾昆季八人,两家伯仲先后通籍,而诸兄亦多以艺鸣于场屋者。虽以弟之不肖,亦随伯仲之后忝列朝行,人或以此妄拟于‘八荀’。”(《韩国文集丛刊》第130册,第242页。)八荀:东汉荀淑才德兼备,人称“神君”,他有八子,并有才名,时号“八龙”。见《世说新语·德行篇》。
⑤金寿兴《退忧堂集》卷一○《星州牧使尹公墓表》云:“南原之尹,始自高丽按廉使威,世为簪缨右族,入我朝有观察使世临,实公七代祖也。自观察传世至司谏院司谏时英、内资寺判官清、司饔院参奉赠吏曹参判民新。参判公有五丈夫子,并擢文科,掌故以为记。公之考曰(日吉),庭试壮元,历台省,官止承旨,用公原从功,再赠吏曹判书。聘完山李氏,系出璇源让宁大君之后赠参判世良之女。”《韩国文集丛刊》第127册,第193页。
⑥宋时烈《宋子大全》卷一九五《汉城庶尹尹公墓表》云:“尹牧使(指尹衡觉)甥馆都事金寿民、修撰李有相、判书金寿兴,仙源、月沙、清阴三大相孙也。”《韩国文集丛刊》第114册,第381页。
⑦朝鲜肃宗朝(1675~1720)是朝鲜历史上党争惨烈的时期。肃宗十五年己巳(康熙二十八年,1689)是著名的“己巳换局”,西人失败,南人掌权。金寿恒为西人领袖,先被流配珍岛,后又被赐死。金氏一族都受牵连,遭受重创。
[1]张伯伟,俞士玲,左江.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2]徐居正.东人诗话(卷下)[M].赵锺业.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1)[Z].首尔:太学社,1996.510-512.
[3]安鼎福编.妇女之教[A].星湖僿说类选(卷三上)[M].首尔:景文社,1981.207.
[4]李德懋.士小节·妇仪[A].青庄馆全书(卷三○)[M].韩国文集丛刊(257)[Z].首尔:景仁文化社,2000.516.
[5]姜柏年.资宪大夫知敦宁府事海丰君郑公墓志铭[A].雪峰遗稿(卷二八)[M].首尔:景仁文化社,1993.318.
[6]李栽.洪氏姊墓志[A].密庵集(文集卷一八)[M].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380.
[7]申暻.先妣遗事[A].直庵集(卷一九)[M].首尔:景仁文化社,1998.489.
[8]李喆辅.洪恭人墓志[A].止庵遗稿(册六)[M].首尔:景仁文化社,2009.161.
[9]许穆.户曹判书金公神道碑铭[A].记言(别集卷一六)[M].首尔:景仁文化社,1992.352.
[10]李縡.从弟妇孺人安东金氏墓志[A].陶庵集(卷四六)[M].首尔:景仁文化社,1997.466.
[11]李植.月沙李相国墓志铭并序[A]泽堂集(别集卷六)[M].首尔:景仁文化社,1992.364.
[12]朴世采.弘文馆副提学静斋李公行状[A].南溪集(卷八)[M].首尔:景仁文化社,1995.99.
[13]李殷相.先府君行状[A].东里集(卷一四)[M].首尔:景仁文化社,1994.554.
[14]金寿兴.星州牧使尹公墓表[A].退忧堂集(卷十)[M].首尔:景仁文化社,1994.193.
[15]李喜朝.贞敬夫人尹氏行状[A]芝村集(卷二七)[M].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557.
[16]李縡.仲母赠贞敬夫人安东金氏墓志[A].陶庵集(卷四六)[M].首尔:景仁文化社,1997.462.
[17]金昌协.亡妹哀辞并序[A].农岩集(卷三○)[M].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312.
[18]金寿恒.亡女行迹[A].文谷集(卷二二)[M].首尔:景仁文化社,1994.437.
[19]金昌缉.亡女行状[A].圃阴集(卷六)[M].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464.
[20]金昌翕.侄女李氏妇墓志铭并序[A].三渊集(卷二八)[M].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41.
[21]金寿增.亡室淑人曹氏行状[A].谷云集(卷六)[M].首尔:景仁文化社,1994.245.
[22]金昌协.亡女吴氏妇墓志铭并序[A].农岩集(卷二七)[M].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255.
[23]金昌协.吴忠贞公元配闵夫人墓碣铭并序[A].农岩集(卷二八)[M].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262.
[24]金时保.先府君墓志[A].茅洲集(卷一○)[M].首尔:景仁文化社,2008.428.
[25]金时保.季母柳孺人行状[A].茅洲集(卷一○)[M].首尔:景仁文化社,2008.437.
[26]金令行.先妣家状[A].弼云稿(册八)[M].首尔:景仁文化社,2008.274.
[27]金时保.亡室淑人尹氏行状[A].茅洲集(卷一○)[M].首尔:景仁文化社,2008.438.
[28]金昌翕.淑人坡平尹氏墓志铭并序[A].三渊集(卷二八)[M].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7.
[29]金时保.罗淑人墓志铭[A].茅洲集(卷一○)[M].首尔:景仁文化社,2008.430.
[30]尹拯.高城郡守金公墓碣铭[A].明斋遗稿(四○)[M].首尔:景仁文化社,1994.46.
[31]金昌翕.族兄盛达挽[A].三渊集(拾遗卷五)[M].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295.
[32]金昌协.祭族兄伯兼盛达文[A].农岩集(卷二九)[M].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292.
[33]宋明钦.祭从叔母淑人金氏迁葬文[A].栎泉集(卷一五)[M].首尔:景仁文化社,1999.304.
【责任编辑:来小乔】
A Study on Female Education and Literature of Anhdong Kim Family
ZUO Jiang
(College of Arts,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Guangdong,518060)
It was a main mainstream idea in the period of the Joseon Dynasty that a woman’s place was in the house doing household chores like cooking and needlework while reading and literary creation was inappropriate for them.However,in consideration of family tradition and children’s education,the scholar officials class thought women also needed to study Xiaoxue,Neixun,Nüjie and so forth,which opened up a gateway for women to read and write.In Anh-dong Kim family,men not only showed great tolerance toward women’s interest in reading and writing,but also encouraged them to do so,hence there appeared quite a few brilliant women in the family known as“women of noble characters”or“great female scholars”.Besides,with Kim Seongdal’s support,female literature thrived in the family,from which Kim Hoyeonjae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female literators.As the old saying goes,“from the claw we may infer the lion”.The prosperity of female literature in Anh-dong Kim Family offers us a glimps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male education and female literature in the period of the Joseon Dynasty from the late 16th century to the middle of 18th century.
Anh-dong Kim;female education;female literature;Kim Seohgdal;Kim Hoyeonjae
I 106.2
A
1000-260X(2015)03-0024-09
2015-04-12
左江,文学博士,深圳大学教授,从事域外汉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