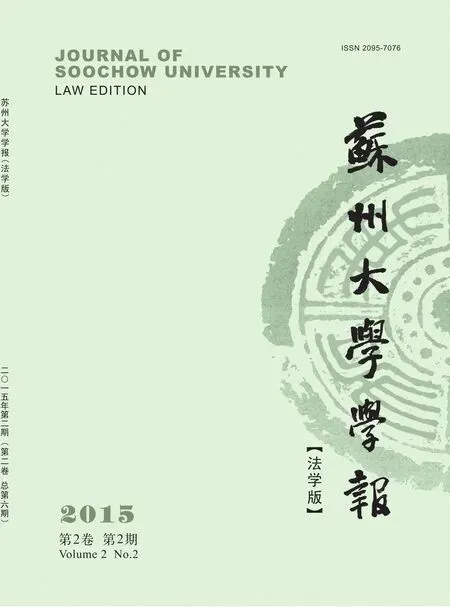刑法总论之困惑(二)
2015-04-02桥爪隆,王昭武
*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教授。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副教授。
***本文原载于日本《法学教室》2014年第6号(总第405号)。
正当防卫状况的判断 ***
一、引言
根据刑法第36条第1款的规定, ①针对“紧迫的非法侵害”而“不得已实施”的防卫行为,可以被正当化。但一般认为,即便是针对时间上非常紧迫的侵害而实施的对抗行为,考虑到那些使得侵害得以成为现实的先行情况,有时候也不能认定成立正当防卫。所谓“斗殴与正当防卫”的问题,还有“自招侵害”的问题,就是其适例。
围绕这一问题,一直以来,学界存在激烈论争,就问题的解决,也提出了各种观点。不过,对刑法的研修而言,重要的是,首先要正确理解判例的立场。实际上,判例已在这一领域提出了独特的问题解决路径,可以说,业已形成了极为缜密的判例理论。 ②而且,司法实务部门对正当防卫问题也抱有浓厚兴趣,已发表了很多颇有见地的观点。 ③对于理解判例理论,了解实务部门的实际认定方式,这些论文可谓重要的参考资料。当然,(包括笔者本人在内)学界也并非完全赞同判例理论,但要了解学说争议的背景,正确理解判例理论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有鉴于此,本文的做法是,在对有关“斗殴与正当防卫”、“自招侵害”问题的相关判例理论进行分析解读的基础之上,阐述笔者的若干研究心得。
另外,谈到我自己,难免总会有些“气短”。作为刑法学者,我最初研究的课题正是正当防卫论,历经各种困惑与苦恼,终于提出了笔者个人的问题解决路径(被学界称之为“侵害避免义务论”)。 ①我当时的研究原点,就正是基于对判例理论的分析。本文无意过多阐述笔者的个人观点,不过,倘若读者诸贤能从中看到笔者的研究心路——如何评价判例理论、对判例理论应如何修正、最终得出了现在的结论——并由此思考本文结论之当否,于笔者实乃意外之喜。
二、有关“斗殴与正当防卫”的判例理论
(一)对侵害的先行事实进行评价的必要性
对有关“斗殴与正当防卫”的最高裁判所判例而言,昭和23年(1948年)的最高裁判所大法庭判决(最大判昭和23年〔1948年〕7月7日刑集2卷8号793页)可谓重要起点。大致案情为:被告人在与被害人斗殴的过程中,因受到被害人的暴力打击,被告人过于激愤,用刀捅死了被害人。对于该案,最高裁判所大法庭认为,“相互施以暴力的所谓斗殴,属于争斗双方不断反复攻击与防御的一系列的连续争斗行为,即便在争斗过程中的某个瞬间,争斗的一方完全处于防御状态,因而呈现出正当防卫之表象,但从整个争斗过程来看,也存在没有考虑刑法第36条之正当防卫观念的余地的情形”,最终判定不成立正当防卫。对于是否成立正当防卫,该判决明确表示,不能仅看防卫行为这一瞬间,有必要将“整个争斗过程”作为评价对象,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即便是所谓“整个争斗过程”,显然不是指实施防卫行为之后的状况,因而可以理解为,该判决最终表明的态度是,不法侵害的先行情况可能限制正当防卫的成立。也就是,该判决设定了应考虑先行情况这一“平台”,此后的判例追求的是如何将此判断标准予以具体化。
该判决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它表明了最高裁判所对于斗殴行为的态度:即便是相互斗殴的情形,也并非当然不成立正当防卫。对于相互斗殴的情形,大审院曾援引“一个巴掌拍不响”这一谚语,做出了似乎只要是相互斗殴就不可能成立正当防卫的判断, ②而本判决的态度则是“也存在没有考虑刑法第36条之正当防卫观念的余地的情形”,这种表述似乎是说,不成立正当防卫的情形毋宁说是一种例外。为此,该判决的态度可以理解为,即便是相互斗殴的情形,也有成立正当防卫的余地。 ③
(二)昭和52年判例的“积极的加害意思论”
那么,通过考虑整个斗殴过程,而得出“也存在没有考虑刑法第36条之正当防卫观念的余地的情形”这一结论的,具体是指哪些情形呢?明确指出这些情形的,是最高裁判所昭和52年决定提出的“积极的加害意思论”。该案大致案情是:在为了召开政治集会而布置会场的过程中,击退了反对派学生的攻击之后,预想到对方还会来攻击,在为此而设置路障之时,反对派学生如期又来攻击,于是一起对这些学生实施了暴力(共同暴力)。对此,最决昭和52年〔1977年〕7月21日刑集31卷4号747页认为,“刑法第36条规定,正当防卫以侵害的紧迫性为要件,其旨趣并不在于,对预想到的侵害,科以避免义务,因此,即便是当然或者几乎确切地预想到了侵害,也并非是由此便直接丧失侵害的紧迫性,这样理解是妥当的”;“从该条以侵害的紧迫性作为要件的旨趣来看,在不只是为了避免预期的侵害,而是出于利用此机会积极地对对方实施加害行为的意思而面对侵害的场合,就(应该说)已经没有满足侵害的紧迫性要件”,最终判定不成立正当防卫。
该决定一边认为,即便预想到了侵害,也并非“由此便直接”否定紧迫性之存在,但同时表明了这样的态度:出于积极的加害意思而面对“预期的侵害”的场合,就应否定存在侵害的紧迫性。对于侵害的紧迫性,判例一直以来的定义是,“法益侵害已经迫在眉睫,即法益侵害的危险已经非常紧迫”(最判昭和24年〔1949年〕8月18日刑集3卷9号1465页)。这种作为时间性概念的定义,并未因最高裁判所昭和52年的决定而改变。 ①毋宁说,该决定是以侵害的紧迫性是具有规范性质的概念为前提,显示了两个视角:积极为紧迫性奠定根据的视角和例外阻却紧迫性的视角。
是否存在对侵害的预期,这对于紧迫性的判断发挥了很大作用,在理解最高裁判所昭和52年决定时,这一点很重要。从“在不仅仅是没有避免预期的侵害,而是出于利用此机会积极地对对方实施加害行为的意思而面对侵害的场合”这一表述可见,本决定是以存在所预期的侵害为前提,而研究是否存在积极的加害意思的问题。为此,凡不能认定对侵害存在预期的,原本就不会探讨是否存在积极的加害意思,只要能认定存在时间上的紧迫性就能肯定存在侵害的紧迫性。 ②
(三)积极的加害意思的内容
下面的问题是,所谓积极的加害意思,具体是指什么内容呢?判例未必对此予以了明确。由于最高裁判所昭和52年的决定是从“虽当然预想到对方的攻击,不是出于单纯防卫的意图,而是出于积极的攻击、争斗、加害的意图而面对”这一事实中,肯定存在积极的加害意思。为此,就被理解为,凡出于防卫目的、护身目的的,即否定存在积极的加害意思。 ③然而,(除了完全止于防御性防卫的情形之外)既然防卫行为也属于针对对方的加害行为,防卫目的与加害目的之间的区别,就是非常微妙的。也许会有人主张,应将重点置于积极的加害意思中的“积极的”这一表述,但依据对方的具体攻击内容的不同,防卫行为既有可能是积极的也有可能是消极的,因而所谓积极的加害意思,就不过是具有将防卫目的、护身目的排除在外这种程度的意义。 ④
前面已经谈到,积极的加害意思,是以对侵害的预期为契机才会产生的意思,是一种事前的意思内容,存在于对侵害存在预期之后直至侵害被现实化这一阶段, ⑤明确区别于防卫意思,后者是根据实际的对抗行为阶段的具体意思内容来判断。由此可见,即便同样属于主观要素,彼此的判断时点完全不同。为此,需要讨论是否存在防卫意思的案件,事实上就限于那些在侵害迫近之前,不能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存在侵害预期与积极的加害意思的案件。 ⑥
那么,在能认定存在侵害预期以及积极的加害意思的场合,为什么能否定侵害的紧迫性呢?负责最高裁判所昭和52年决定的最高裁判所调查官香城敏麿教授的解释是,该侵害“是行为人宁愿接受的结果,因而应该让行为人接受这种结果” ①,“在与对方的关系上,并非处于应受到法律特别保护的位置” ②。对于这种理解,可以做下述阐释:在正当防卫中,防卫行为人原则上不负有避免义务,也无需在防卫利益与侵害利益之间进行比较衡量。之所以能将正当防卫这种使用强力手段的情形予以正当化,就正是因为能评价为,必须通过正当防卫来保护被侵害者之利益,因而才以状况紧迫性为必要。只要非法侵害存在时间上的紧迫性,原则上就可认定这种状况紧迫性,不过,通过考虑侵害的先行情况,得出并无保护防卫行为人(被侵害人) ③之必要这一结论之时,就应当例外地否定这种状况紧迫性。虽对侵害有预期,也预想到会演变为相互斗殴,仍然宁愿接受这些,并选择正面对抗侵害的,就可以说,非法侵害正是防卫行为人自己接受的结果,既然如此,就鲜有必须动用正当防卫来予以保护的必要,因而能否定存在状况紧迫性。这种观点可以定位于为正当防卫状况奠定基础的紧迫性要件之下。对于判例背后的实质性考虑,也许可以以这种形式来理解。安广文夫教授所谓在能认定存在积极的加害意思的场合就可以认定“缺少属于正当防卫之本质属性的紧急行为性” ④,想必正是此意。 ⑤
(四)司法实务对紧迫性的判断
在司法实务中,是如何适用这种判例理论的呢?通过考察最高裁判所昭和52年决定之后的判例对紧迫性的判断, ⑥有一点引起了笔者的浓厚兴趣:是否实际存在对侵害的预期,对于侵害的紧迫性的有无判断具有决定性意义。亦即,在就是否存在紧迫性存在争议的案件中,那些肯定存在紧迫性的判例,绝大多数都是以不能认定对侵害存在充分的预期, ⑦或者实际的侵害远远超出了所预期的范围 ⑧为根据。反过来说,那些认定存在对侵害的预期的案件,也基本上都认定存在积极的加害意思,否定存在侵害的紧迫性。至于那些虽认定存在侵害的预期,但不能认定存在积极的加害意思,进而肯定存在侵害的紧迫性的案件,就限于那些极其例外的案件:在自己家里或者自己房间面对突然的侵害的、 ⑨虽曾试图避免所预期的侵害但最终仍不得不面对侵害的、 ⑩虽对上司的侵害存在预期但由于是在工作时间而难以避免的,等等。
判例的这种倾向,是完全能够理解的。例如,斗殴的对方让自己前往某处,自己若去现场很有可能面临非法侵害,在此情形下,只要没有仍不得不勉强去现场的合理理由,通常的判断想必是不去现场。尽管不是非去现场不可,但虽然预期到侵害,却仍不管不顾地前往现场的,几乎都是行为人宁愿接受侵害,并出于对抗侵害的意思而面对侵害的情形。也就是说,很多情况下,从虽然对侵害存在预期仍(没有正当理由地)赶赴现场这一行为本身,就能认定存在积极的加害意思。反之,对于在自己家等类似地方等待所预期的侵害到来的情形,就难以仅从在现场伺机而动这一点认定存在积极的加害意思,为此,还需要存在其他特别情况。 ①
如果判例的这种倾向被一般化,对于那些能认定存在对侵害的预期的情形,只要对正面面对侵害没有正当的理由,换言之,除了那些不能期待其避免侵害的情形之外,原则上都可以认定存在积极的加害意思。 ②这样的话,要认定存在积极的加害意思,作为证明这种意思的间接事实,是否存在可谓之为应该避免侵害的客观情况,就具有决定性意义。为此,着眼于这种客观事实本身的判例的出现,也就可以说是判例理论发展的一种自然进程。 ③例如,被告人受到挑战,被要求用刀决斗,对于对方执拗的挑衅,被告人一直保持克制,耐心劝说对方放弃斗殴,但最终因无法克制而应允,结果将被害人刺死。对于此案,大阪高判昭和62年(1987年)4月15日判时1254号140页判定,“对被告人来说,应该采取的手段是,甘愿忍受一时的屈辱而暂时逃离现场……尽管如此,被告人却以该屈辱为耻,不管不顾地接受并面对斗殴,既然如此……上述攻击就不能谓之为刑法第36条所谓‘紧迫的非法侵害’”。另外,对于事关暴力集团之间的争斗的案件,还有判例认为,从出于对抗所预期的侵害的意图而非法准备手枪这一事实本身,就可以否定存在侵害的紧迫性。 ④就这些判例而言,即便没有勉强地认定被告人存在积极的加害意思,但仍存在这样理解的余地:对于被告人准备手枪意图对抗所预期的侵害这一行为本身,就可以评价为违法行为,进而否定存在侵害的紧迫性。当然,对于这些判例,也有这样理解的可能:归根结底,积极的加害意思才是最重要的,那些客观事实不过是为了证明这一点的间接事实而已。然而,难以否定的是,虽然不过是间接事实,但实际存在的客观的先行事实——尽管处于应避免侵害的状况之下,却仍然准备凶器对抗所预期的侵害——对于否定侵害的紧迫性仍具有决定性意义。
三、学界态度
(一)对“积极的加害意思论”的批判
判例提出的这种“积极的加害意思论”,是从状况紧迫性这一角度来规范性地限定侵害的紧迫性,作为斗殴案件的解决路径,(除了后述本文的几点疑问之外)基本上应予支持。不过,学界多数观点对于“积极的加害意思论”却持批判态度。具体有哪些批判意见呢?这些批判又是否有充分的理由呢?下面想就此做些探讨。学界的批判形形色色,其要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点是针对通过考虑侵害的先行事实而限制正当防卫成立的做法本身的质疑。亦即,这种批判的意思是,是否成立正当防卫,应以非法侵害实际已经迫近的阶段为判断标准,(除了像自招侵害那样由自己引起侵害的这种例外情形之外)原则上不应考虑此前的状况。 ⑤这种主张应予以限定的批判观点本身,在理论上是完全能成立的,但也不能因为这一点就认为,像判例那样,将侵害的先行事实纳入到对被侵害者的要保护性判断之中这种做法,作为对第36条第1款的文理解释,应将其排除在外。尽管最终仍然会回到在什么范围之内肯定正当防卫是合适的这种价值判断,但本文以为,判例的问题解决方式也完全有其合理性。亦即,通过挑衅行为而招致对方的侵害的情形自不用说,即便不能认定存在这种事实,但如果存在出于斗殴的意思,不管不顾地赶赴现场,自己将自己的人身安全置于遭受侵害的危险之下这种事实,原则上就鲜有通过正当防卫来保护防卫行为人之必要。换言之,对于针对侵害者的生命、身体等的严重法益侵害行为,原则上就鲜有作为正当防卫予以正当化之必要。如果将这种观点引入正当防卫的解释论,就仍然不得不考虑先行于侵害的主观事实、客观事实。
对于本文的这种观点,也有论者提出了批驳:如果对侵害存在预期,防卫行为人就有时间进行充分的准备,事实上,可供选择的防卫手段也有很多,因此,即便不否定正当防卫的成立,防卫行为的相当性(最小必要限度)事实上也会受到限制,这样就足够了。 ①的确,与没有机会准备的情形相比,如果事前有机会进行准备,就能以相对更轻的手段达到防卫的目的,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却仍然采取了危险性很大的手段的,就会否定防卫行为的相当性(成立防卫过当)。但是,例如,在以刀具、枪械等进行攻击的危险迫近之时,即便事前进行了充分准备,可以用于防卫的手段自然也是有限的。即便防卫行为人预期到侵害,准备了枪械赶赴现场,在受到对方的严重侵害,若不开枪就无法充分防卫的状况之下,开枪行为就仍然属于最小必要限度的防卫行为,仍能成立正当防卫;反之,如果认为这种结论不妥,那么就应该承认,存在通过考虑侵害的先行事实而否定成立正当防卫的余地。 ②
第二点是针对否定正当防卫状况这种问题解决方式的批判。也就是,如果因存在积极的加害意思,就否定侵害的紧迫性,那么,对于对抗行为,也就排除了成立防卫过当的余地。但是,这种批判的旨趣在于,虽说是事关斗殴的案件,对于防卫行为人的保护必要性也是各式各样。因此,毋宁说,应该作为防卫行为性的问题,就具体案件分别探讨。 ③按照这种观点,即便是需要考虑先行事实,也只要在对防卫行为的相当性的判断中予以考虑即可。然而,这种批判未能做到有的放矢。首先是与司法实务所实际关心的问题之间存在罅隙。司法实务关心的问题似乎是,像出于斗殴目的准备凶器赶赴现场的案件那样,如何处理那些不应被评价为防卫行为的案件。为此,认为应将事关斗殴的案件广泛作为防卫过当的问题来处理,就有未能正面回应司法实务所关心的问题之嫌。 ④而且,本文以为,一边考虑先行事实,同时就各个具体案件分别判断防卫行为的相当性,这种提议也不具有可行性。这是因为,是否具有防卫行为的相当性,这种判断本身原本就是一种相当微妙的认定,另外,通过综合考虑先行于侵害行为的各种情况来判断有无相当性,就无法确保判断的明确性。就此问题这里无法详述,但本文坚持认为,防卫行为的相当性要件,应根据是否为防卫行为人在现场所能选择的最小必要限度的防卫行为来判断, ①此外再考虑其他判断要素,不仅是有关斗殴的案件,就是对通常的防卫行为的判断,也会造成混乱。进一步而言,虽说是认定成立防卫过当,但对于防卫过当,第36条第2款仅规定了刑罚的任意性减免,勉强将先行于侵害的事实关系纳入到防卫行为性的判断之中,也鲜有相应意义。 ②
第三点批判意见是,紧迫性属于客观范畴,不应考虑行为人主观方面的情况。学说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这一点, ③但作为时间性概念,未必需要纯客观地判断紧迫性。比如,在违法阻却事由的解释论中,也当然允许目的论解释,将能否谓之为允许通过正当防卫来实施对抗的状况,纳入到对紧迫性的解释中,根本不能说这超出了日语的“紧迫”的文意的射程。此前的学说多是在将侵害的紧迫性理解为客观性要件的基础之上,在防卫意思的要件中,判断积极的加害意思这种主观方面的问题, ④但在本文看来,这种解释方法并不比判例理论高明多少。如前所述,判例的做法是,将侵害迫近之前的意思内容与对抗行为阶段的意思内容分别定位于紧迫性要件、防卫意思要件,从而明确地区分二者。因为是主观方面的问题,所以要放在防卫意思的问题中集中考虑,这种研究方式就未免显得过于简单粗糙。
(二)侵害避免义务论
这样看来,通过考虑侵害的先行事实而判断状况紧迫性,在实质上不能认定存在状况紧迫性之时,就否定侵害的紧迫性,本文以为,这种判例理论有其充分的理由,其基本方向也是值得坚持的。尽管如此,本文仍存在下述几点疑问。
判例理论的出发点在于,仅仅是预期到侵害,并不能由此丧失状况紧迫性。这种理解是极为正确的。如果只要预期到侵害就要否定成立正当防卫,那么,只要存在侵害的危险,就连自己想去的地方也不能去,甚至于还需要从自己家中撤离。毫无疑问,这种结论是错误的。但是,在那些对抗所预期的侵害的案件中,也确实存在无法评价为紧迫状况的情形,这也是事实。为此,判例通过在侵害的预期之外另外加上某种“附加要素”,以此来否定状况紧迫性,进而否定成立正当防卫,这种“附加要素”就是所谓“积极的加害意思”。
然而,通过“积极的加害意思”来划定“附加要素”的限定范围,这是否真的合适呢?本文认为,如果是根据以正当防卫保护被侵害者的必要性来判断状况紧迫性,就应该是从被侵害者所处利益状况来判断,而像判例那样,仅对斗殴意思这种主观意图予以过度的重视,就并不妥当。 ⑤例如,接到已到自家门前的斗殴对方的电话:“现在去你那,你等着!”此时,即便能预期到此后的袭击,对防卫行为人而言,除了留在家中迎击侵害之外,想必已别无选择。因为,即便马上拨打110也已经来不及,也不应要求防卫行为人马上从家中逃离。在此情形下,如果防卫行为人冷静下来,出于保护自身的目的而伺机行事,就属于正当防卫。但如果防卫行为人过度兴奋而抱有加害意思,就不属于正当防卫,这种区别无疑是过度重视防卫行为人的心情,并不妥当。对此,有论者指出,在诸如难以避免侵害,或者向警方求助也未必来得及的场合,也照样适用积极的加害意思论,就并不合适。 ①这种观点的意思应该是,在紧迫性的判断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是积极的加害意思本身,而是处于其背后的客观利益状况。行为人留在自己家中,并且,处于无法期待事先避免侵害的状况之下,这些就能为侵害的紧迫性奠定基础,至于在自己家中伺机而动之时的主观方面的情况,并不会影响到对状况紧迫性的判断。
正是出于这种问题意识,本文的观点是:在被侵害者无需牺牲正当利益,就能相对容易地避免所预期的侵害(却面对侵害而实施了对抗行为)的场合,就属于本应予以避免的危险的现实化,应否定侵害的紧迫性(侵害避免义务论)。 ②具体而言,虽预期到侵害,仍前往现场的,只要不能认定前往现场有相当的正当理由,就否定存在紧迫性。另一方面,对于等候所预期的侵害(伏击)的情形,只要存在滞留现场的正当理由,就不能否定侵害的紧迫性,但如果是通过向警察求助等能切实避免侵害,却故意不采取这种措施而选择实施对抗行为的,就否定存在紧迫性。 ③
对于本文所主张的“侵害避免义务论”,虽有观点基本表示支持, ④但毋宁说批判意见居多。有力的批判意见是,“侵害避免义务论”不是以作为实行行为的防卫行为,而是以先行于防卫行为的、事前的义务违反作为处罚对象。 ⑤不可否认,“侵害避免义务论”这一命题的确会给人以处罚的是事前的义务违反之印象,但这种观点终究不过是通过考虑侵害的先行事实而否定实际存在正当防卫的状况,而并非是以没有避免侵害本身作为处罚对象。 ⑥另有批判意见指出,作为判断是否存在侵害避免义务的标准,是否存在“正当的利益”这一点并不明确。 ⑦不得不承认,对于是否存在正当利益的判断,确实未必明确,不过,笔者考虑的是,与直观地判断“对于所预期的侵害,在何种范围之内允许实施对抗行为”相比,基于被侵害者的事前的利益状况进行类型化分析,至少有可能进行可视化的研究。包括其他批判意见在内,笔者此后还会做进一步思考。
四、自招侵害
(一)问题之所在
所谓自招侵害,是指由防卫行为人本人先前的暴力行为等而自己招致了非法侵害的情形。自招侵害虽与“斗殴与正当防卫”的问题密切相关,但在理论上却属于另一层面的问题。亦即,“斗殴与正当防卫”考虑的是事前的积极的加害意思这一主观方面的问题,而自招侵害重视的是,防卫行为人本人创造出了非法的侵害这种客观关联性的问题。 ①
对自招侵害而言,如果对方的反击行为能被评价为,是针对(由自招侵害人实施的)起初的非法的暴力行为的正当防卫,由于不具有侵害的非法性,针对该反击行为的对抗行为,当然不能成立正当防卫。 ②这里要研究的问题是,在难以否定对方的反击行为属于非法侵害的情形下如何处理。例如,对方的反击行为被评价为防卫过当,或者对方的反击行为属于先前的非法暴力已经结束之后的反击,等等。 ③该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学界也提出了各种解决路径。但总体来说,多数说的观点是,意图招致对方的不法侵害而实施挑衅行为的(有意挑衅),应否定成立正当防卫,至于其他有责招致的情形,则应限制防卫行为的范围。 ④
对于有关自招侵害的案件,按照判例观点,针对那些有意挑衅的案件,也是通过“积极的加害意思论”来否定正当防卫。也就是,事先想到(预期)对方会反击,仍出于积极的加害意思实施了挑衅性的言行,在此情形下,就应否定存在侵害的紧迫性,否定成立正当防卫。 ⑤不过,也有下级裁判所的判例采取了着眼于自己招致了侵害这一事实本身的理论。例如,在上下班高峰时段,在火车站的台阶处,S与被告人发生口角,被告人用力抓住S的手腕,于是S殴打了被告人的面部。对于此情形,东京高判平成8年(1996年)2月7日判时1568号145页认为,“S的反击是由被告人自己违法招致,且该反击止于通常所能预想的范围之内,因此,认为不具有紧迫性是妥当的。”这种自己招致的侵害止于“通常所能预想的范围之内”这一判断标准,在其他有关自招侵害的判例中也多得到运用。 ⑥
(二)对最高裁判所平成20年决定的理解
最高裁判所第一次对自招侵害案件做出具体判断的是最决平成20年(2008年)5月20日刑集62卷6号1786页。 ⑦该案大致案情如下:本案被告人与甲发生口角,突然殴打甲的面部(第一暴力),然后逃离现场。甲骑自行车追赶被告人,从被告人的背后施加了职业摔跤的双勾拳(Lariat)那样的暴力(第二暴力),被告人予以还击,用随身携带的特殊警棍击打甲的面部与左手,致甲受伤(第三暴力)。这里的问题在于,第三暴力是否成立正当防卫。 ①对于该案,最高裁判所基于下述理由判定不成立正当防卫:“按照前述案情事实……甲的攻击可谓是由被告人的暴力所触发的、紧接着被告人的暴力且在相近地点实施的一系列、整体性的事态,因此,在甲的攻击并没有大幅超出被告人的前述暴力程度等本案事实之下,就应该说,本案中被告人的伤害行为不能谓之为,是在被告人实施某种反击行为能被正当化这一状况之下的行为。”
本决定的形式虽然是“事例判例”, ②但仍显示了判例的一定态度,即有时候可以根据自己招致了侵害这一事实而排除正当防卫的成立。在这一点上,该判例对于此后的司法实务具有重要意义。 ③本决定与前述最高裁判所昭和52年决定在两点上存在很大不同: ④(1)本决定完全没有言及侵害的预期、积极的加害意思等被告人的主观方面,而是从自己招致了非法侵害这一客观事实本身否定成立正当防卫;(2)在有关正当防卫的要件论方面,尽管二审判决显示了否定侵害的紧迫性这种解决方式,但本判决只是提到,“不能谓之为,是在被告人实施某种反击行为能被正当化这一状况之下的行为”,也完全没有言及紧迫性要件。由此可见,最高裁判所显然是试图通过本决定而明确显示,运用不同于最高裁判所昭和52年决定的其他理论来否定正当防卫的情形。也就是,最高裁判所昭和52年决定的“积极的加害意思论”是通过考虑行为人事前的主观方面的情况而否定正当防卫,与此相反,最高裁判所平成20年决定则是从自己招致了侵害这一客观事实中推导出对正当防卫的否定。两者都是通过考虑侵害的先行事实而否定成立正当防卫,因而都是前述最高裁判所大法庭昭和23年判决的判断标准的具体化。尽管对这两个判例都有进行这种评价的余地,但具体化的要点则各不相同。 ⑤本决定没有考虑侵害是否具有紧迫性的问题,而是否定被告人的行为“是在被告人实施某种反击行为能被正当化这一状况之下的行为”,其意图也显然在于,突出本判例采取的是不同于最高裁判所昭和52年决定的其他理论。不过,由于实质上也是否定了紧迫状况性,因而可以将其定位于,是与最高裁判所昭和52年决定相并列的判例。
也就是,本决定的前提终究在于,因自己的“非法行为”而自己招致了侵害。因此,即便是由未必能谓之为违法的行为(失礼的言行、压迫性态度等)而招致了对方的非法侵害,那也是最高裁判所平成20年决定的射程之外的问题;限于在先行行为阶段能认定存在侵害的预期以及积极的加害意思的情形,可按照最高裁判所昭和52年决定而否定紧迫性。并且,要评价为自招侵害,就要求对方的非法侵害“可谓是由被告人的暴力所触发的、紧接着被告人的暴力且在相近地点实施的一系列、整体性的事态”。为此,就可以理解为,其旨趣在于,要评价为是由行为人自己引起了非法侵害,必须存在足以评价为“一系列、整体性的事态”的密切关系。
不过,本决定也不是通过这些事实而直接一般性地否定正当防卫的成立,终究不过是做出了适于“本案事实关系”的判断。并且,在“本案事实关系”中,特意明确抽出了“甲的攻击并没有大幅超出被告人的前述暴力程度”这一事实。对于第一暴力与第二暴力之间的这种均衡性,也有学者指出,不过是指出了在本案中能认定存在这种事实,作为自招侵害的要件,并不具有规范性意义。 ①但从最高裁判所在本案事实中特意仅就该事实做出了判断来看,就应理解为,该事实对于排除正当防卫的成立,属于重要的考虑因素。为此,就可以说,如果甲的第二暴力的严重程度远远超出被告人的第一暴力的程度,此类案件就处于本决定的射程之外。 ②
那么,为什么需要这种标准呢?坦白地说,笔者也不清楚。 ③如果笔者是裁判官,提出的就不是该事实,而是“甲的第二暴力没有超出通常的预见程度”这一事实。因为,这种认定与前述下级裁判所的既往判例的判断之间也具有亲和性(容易保持一致)。从最高裁判所特意没有采用这种表述,就可以看出最高裁判所的强硬态度:不采用所谓“预见可能”这种可能与行为人的主观心态相关的表述,而试图完全从客观事实关系中提出明确的判断标准。 ④仅就“本案事实关系”而言,从与被告人的第一暴力的关系上看,甲的第二暴力属于通常所能预见的程度的暴力,而且,就两者的程度而言,也存在均衡性,因此,无论是考虑均衡性的问题,还是考虑预测可能性的问题,最终结论都不会有什么变化。但是,也有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第二暴力(与第一暴力相比)明显属于更为严重的侵害行为,但从第一暴力中很容易预测到会招致第二暴力那样严重的侵害,对于这类案件, ⑤两者的判断标准之间就会出现偏差。显然,这种案件已经超出了本决定的射程范围,但也并非因为这就不能直接得出肯定正当防卫之成立的结论。对于这类案件,也期待判例今后能做出明确的判断。
(三)若干探讨
笔者曾一度认为,对于自招侵害的问题,即便不设定特别的判断标准,只要一般适用“侵害避免义务论”即可。 ⑥当时之所以如此考虑,是因为考虑到正当防卫的解释论原本就已经十分复杂,如果再同时适用几个标准,势必会让研究陷入不必要的混乱。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对于自招侵害的案件,笔者也主张,仅限于那些能认定存在对侵害的预期的情形,才否定正当防卫的成立。 ⑦然而,最高裁判所平成20年决定之后,笔者又重新思考了此问题,比较没有避免应该避免的侵害因而侵害被现实化的情形、可以评价为是因自己的非法行为而引起了侵害的情形,就无法否认,与前者相比,对于后者更有必要否定正当防卫。为此,才想到区别这两种类型,并设定不同的判断标准,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尽管应事前避免非法侵害却仍让非法侵害被现实化,这属于否定正当防卫的根据,基于此一逻辑,即便对对方的反击不存在预期,但至少需要对该反击有预见的可能。 ⑧也就是,正因为对侵害(反击)具有预见的可能,才能让行为人承担采取相应措施以避免侵害被现实化的责任。对于这种理解,有学者提出,并非是处罚先行行为,因而在先行行为阶段,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会招致侵害存在预见或者预见可能性。 ⑨该观点可能是出于这样的理解:既然是由自己的非法行为招致了侵害,当然应接受不利益,因而也就不是必然要求对自己的行为会招致侵害存在预见或者预见可能性。但按照该观点,理应只要存在非法招致了侵害这一事实即可,那么,就无法推导出(属于本决定之问题的)第一暴力与第二暴力之间的均衡性要件。不过,像本决定那样,如果整体行为处于能被评价为“一系列、整体性的事态”的关系之下,且要求第一暴力与第二暴力之间存在均衡性,那么,几乎对于所有情形都能认定存在侵害的预见可能性,因此,这也许不过是说明方式上的不同。
总之,今后的裁判实务会从“积极的加害意思论”与“自招侵害论”这两个角度,来判断是否成立正当防卫。如果能认定自己招致了侵害这一客观事实,就按照最高裁判所平成20年决定,有可能属于能否定“是在被告人实施某种反击行为能被正当化这一状况之下的行为”的情形;而且,即便不能认定自己招致了侵害这一客观事实,也可以按照最高裁判所昭和52年决定的标准,而可能属于通过侵害的预期与积极的加害意思而否定侵害的紧迫性的情形。这样,作为将最高裁判所大法庭昭和23年判决提出的“整体考察方法”予以具体化的两个标准,会平行适用二者。 ①
接下来的问题是,作为对斗殴案件的整体考察方法的具体化,是止于这两个标准,还是另有其他类型呢?远藤邦彦裁判官提出了一个饶有兴致的问题:能否叠加适用最高裁判所昭和52年决定与最高裁判所平成20年决定的标准呢? ②亦即,对于那些无论适用哪一标准都尚不充分的案件,能否通过合并适用二者的实质性考虑,而排除正当防卫的成立呢?例如,下述案件就值得考虑:甲意欲杀害素来与自己不和的乙,于是在乙就寝之时进到乙的房间。甲想的是趁乙熟睡之际将其杀害,完全没有想到会招致乙的反击。然而,乙感到有人进入房间而惊醒过来,察觉到甲的意图,非常气愤,遂开始对甲实施暴力。在该案中,由于不处于甲因非法暴力等自己招致了侵害这种“一系列、整体性的事态”关系之下,因而最高裁判所平成20年决定的射程不直接及于该案;而且,甲对于乙的侵害也不存在预期,因而不能根据最高裁判所昭和52年决定而直接否定紧迫性。对于该案,能否通过叠加适用这两个决定的构想而否定成立正当防卫呢?这在理论上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如果广泛承认这种“合并之技”,就会使得正当防卫的判断越发不稳定,也有违谋求判断标准明确化的最高裁判所平成20年决定的意图。毋宁说,对于这种中间类型,还是寄望于通过具体探讨而提出更为明确的判断标准为宜。
防卫过当 *
一、引言
一般认为,防卫过当(第36条第2款)有质的过当与量的过当这两种类型。其中,质的过当,是指针对紧迫的非法侵害的防卫行为超出相当性限度的情形,这种情形完全符合第36条第2款的文意,当然适用该款。反之,量的过当,是指侵害结束之后继续实施追击行为的情形。 ③对于后一情形,究竟有
* 本文原载于日本《法学教室》2014年第7号(总第406号)。无适用该款之余地,尚存争议。通说通过对侵害持续过程中的对抗行为、侵害结束之后的追击行为进行整体性评价,认为从时间上看作为整体的防卫行为达到了过当程度,从而肯定适用第36条第2款。判例也是以此理解为前提。本文的目的在于,探讨对防卫行为进行整体性评价的根据,以及具体的判断标准。
进一步而言,这种对防卫行为进行整体性评价的问题,不限于量的过当类型。非法侵害持续过程中,实施数个防卫行为的场合,也会出现对于这些防卫行为究竟是应个别评价还是应作为整体防卫行为予以评价的问题。当然,如果各个具体的防卫行为均分别满足正当防卫的要件,则无论采取何种理论结构,也会成立正当防卫,因而不存在问题;但如果数个防卫行为中的部分行为未满足相当性要件,包括能够评价为正当防卫的部分行为在内,是否应该将整体防卫行为评价为防卫过当,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对于这种防卫行为的整体性的界限问题,最高裁判所的重要判例相继出现,最近更引起了极其广泛的关注。 ①尽管不无相关研究已经揭示了全部论点之感,但笔者还是想借此机会重新对该问题做些探讨。
二、判例及其理解
(一)判例动向
在最高裁判所判例中,早在1959年就已有关于防卫过当的判例。被告人实施防卫行为之后,对于已经失去侵害态势的被害人实施进一步的追击行为,结果造成被害人死亡,对此,最判昭和34年(1959年)2月5日刑集13卷1号1页判定,“本案被告人的一系列行为”整体上该当于防卫过当。该判决属于对于量的过当承认适用第36条第2款的判决。 ②而且,对于整体把握质的过当中的防卫行为的问题,最判平成9年(1997年)6月16日刑集51卷5号435页判定,包括用铁锹殴打被害人头部的暴力、使被害人从二楼摔下的行为这两个行为在内,“不得不说,被告人的一系列暴力作为整体,已经超出了为了防卫而不得已实施的程度”,通过整体性地把握一系列的防卫行为,最终判定成立防卫过当。由此可见,对防卫行为进行整体把握,这已经成为实务部门的一般倾向。 ③最决平成20年(2008年)6月25日刑集62卷6号1859页以及最决平成21年(2009年)2月24日刑集63卷2号1页均对此做出了具体判断。
作为最终结论,最高裁判所平成20年判例否定成立防卫过当,但作为一般论来说,重要的是,该判决以认定量的过当为前提,提出了整体性评价的标准。该案大致案情如下:针对被害人乙实施的殴打、用烟灰缸砸人等侵害行为,被告人甲在击打乙的面部并致乙摔倒之后(第一暴力),虽充分认识到乙已处于丧失意识不能动弹的状况,仍边骂边踢乙的腹部(第二暴力),结果致被害人乙死亡,但作为死因的伤害完全是由第一暴力所造成。对此,判例认为,“乙已经因第一暴力摔倒,已没有对被告人实施进一步侵害行为的可能,被告人在对此存在认识的基础上,完全出于攻击的意思而实施了第二暴力,因此,第二暴力显然没有满足正当防卫的要件。并且,尽管两个暴力行为在时间上、地点上是连续的,但在乙实施的侵害的持续性以及被告人防卫意思之有无这一点上,显然性质不一。鉴于被告人……对乙实施了具有相当激烈程度的第二暴力,就应该说,两个暴力行为之间存在间断,因此不能认定,是在针对紧迫的非法侵害持续实施反击行为的过程中,该反击行为在量上变得过当。”亦即,其旨趣显然是,虽对第一暴力认定正当防卫,但对第二暴力认定成立伤害罪,没有成立防卫过当的余地。
平成21年的最高裁判所判例通过对于质的防卫过当,肯定对防卫行为的整体性评价。该案大致案情如下:在拘留所内,被告人甲被被害人乙用折叠桌推倒,被告人甲实施了将该折叠桌推回的暴力(第一暴力),之后,对于撞上折叠桌而摔倒、处于难以反击的状态之下的被害人乙, ①继续数次击打其面部(第二暴力),但只有第一暴力与被害人乙的伤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且,若单独评价第一暴力,完全存在满足防卫行为之相对性的可能。对于该案,最高裁判所判定:“在上述事实关系之下,被告人对被害人施加的暴力,属于针对紧迫的非法侵害行为而实施的一系列、一个整体的暴力,能认定为基于同一防卫意思的一个行为,因此,进行整体性考察,认定成立作为一个防卫过当的伤害罪是相当的。”也就是,对该案而言,如果分别评价第一暴力、第二暴力,则仅限于第二暴力,有成立暴行罪的防卫过当的可能性,但最高裁判所对此是通过整体性评价两个暴力,认定成立伤害罪的防卫过当。但这样理解的不妥之处在于,将第一暴力所引起的伤害结果也作为防卫过当(之结果)包括在处罚对象之内。对此问题,最高裁判所指出:“应该说,作为有利情节予以考虑即可。”
(二)对判例的理解与评价
1.判例的前提性观点
尽管最高裁判所平成20年判例与最高裁判所平成21年判例都属于“事例判例”,但本文认为,通过这两个判例,有关防卫行为的整体性评价的判例立场得以明确:(1)就侵害持续过程中的对抗行为在侵害结束之后仍持续实施的情形,最高裁判所平成20年判例的前提在于,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防卫行为,有成立量的过当的余地; ②(2)如果第一暴力、第二暴力能被评价为一系列的行为,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防卫行为,就认定成立防卫过当;(3)无论是侵害持续过程中实施数个暴力的情形(最高裁判所平成21年判例)还是侵害结束之后暴力行为仍然持续的情形(最高裁判所平成20年判例),这一点均无变化; ③(4)对于能被整体评价为一系列行为的情形,应该贯彻这种整体性评价,而不得根据具体案情分别评价这两个行为,若出现某种不均衡,只要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即可(最高裁判所平成21年判例)。
作为这种判例理论之背景的基本观点是,防卫行为的整体性原本属于刑法上的行为个数的评价问题,属于构成要件阶段或者构成要件之前的评价问题。明确提出这一点的是永井敏雄裁判官。永井敏雄裁判官认为,“对于作为社会上的一个‘插曲’(episods)而存在的事态,采取整体性评价的手法是合适的”。并且,在探讨犯罪的成立与否之际,首先,有必要确定“一个行为”的内容,这一点先行于对构成要件该当性以及违法阻却事由的探讨;其次,在认定存在这种“一个行为”的场合,对“一个行为”的整体进行构成要件该当性与违法阻却事由的判断,就是理所当然。 ①因此,对于由第一行为造成了重大结果的情形,割裂已经确定的“一个行为”,“将其分开评价是不合逻辑的,因此,当然应贯彻整体性评价” ②。
2.评价
此类判例理论的要点可以归纳为:(1)对于防卫行为之整体性的判断,不是在违法阻却阶段,而是在构成要件阶段或者构成要件的先行阶段进行;(2)在该阶段被评价为“一个行为”的,违法阻却的判断也应贯彻整体性评价。但本文以为,这种理解未必有充分理由。
首先是行为的整体性判断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定位问题。在判断防卫行为的整体性之际,最高裁判所平成20年判例重视的是,是否存在侵害的持续性与防卫意思。这一点正好反映出,行为的整体性判断,不是构成要件阶段或者构成要件的先行阶段的问题,而属于对防卫行为的评价,亦即,属于违法阻却阶段的判断。 ③对于本文的这种观点,持判例观点者提出了反驳:对于单纯的行为本身的整体性判断,重要的是动机内容与意思决定;而在量的过当成为问题的前提下,由于第一暴力是出于防卫的意思而实施,有无动机内容、意思决定的连续性,这事实上只能根据防卫意思的连续性来判断,而不能以正当防卫的要件本身作为判断标准。 ④然而,如果像该反驳意见那样,认为重要的是脱离正当防卫要件的原初的意思内容本身,那么,即便是出于防卫动机而实施的第一行为(因不满足其他要件)不成立正当防卫的情形,第一暴力、第二暴力仍应作为完全不同的行为来评价吗?例如,在由被告人的先行暴力而招致了被害人的侵害行为之后,被告人实施了与最高裁判所平成20年判例完全相同的第一暴力、第二暴力的情形下,第一暴力势必不成立正当防卫,那么,对于在时间上、地点上连续实施的第一暴力、第二暴力,当然也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评价,连试图分开评价这种问题的意识也不会产生。 ⑤正是因为第一暴力被评价为防卫行为,对于第二暴力是否也能作为“一系列的防卫行为”来评价这一点才会成为问题,因而这正是在按照正当防卫的要件进行判断。
进一步深究判例观点,最终结果就是,对于防卫行为的整体性评价的问题,单纯一罪与概括一罪的区别就具有决定性意义。也就是,在先行于构成要件评价的行为能认定具有“行为的一个性”的场合,既然行为是一个,就构成单纯一罪;反之,在否定作为防卫行为的单一性的场合,也可能出现数个暴力行为的罪数评价的问题。在最高裁判所平成20年判例中,由于第一暴力是成立正当防卫的行为,罪数问题还没有显现出来,但如果第一暴力本身属于质的防卫过当,那么,第一暴力就成立属于防卫过当的伤害致死罪,第二暴力成立属于完全的犯罪的伤害罪。但是,在同一机会之下、针对同一被害人实施的两个暴力也许会被评价为包括的一罪。 ①为此,在同一机会之下实施的暴力行为是作为单纯一罪来评价,还是作为包括的一罪来评价,在防卫行为的整体性判断中,事实上就会出现决定性不同。 ②但原本来说,有可能严格区分单纯一罪与包括的一罪吗?例如,每隔几分钟就对同一被害人实施同样暴力的,一般是认定成立作为单纯一罪的暴行罪,但对此情形,做下述理解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在成立数个暴行罪的基础上,整体处于包括的一罪的关系。总的来说,单纯一罪与包括的一罪之间的区别是流动的,理论上根本就不存在严格的区分标准。 ③相反,在本文看来,为什么仅限于有关量的过当的案件,对于防卫行为的整体性判断,这种区别才属于决定性标准呢?这不仅没有太多说服力,作为判断标准也是不合理的。
由上可见,即便是所谓构成要件阶段的整体性评价,但这种判断也并非牢不可破,如果认为,与包括的一罪之间的区别仅片纸之隔,那么,即使是在构成要件阶段能被评价为一系列的暴力行为,也并非必须总是贯彻这种评价,在防卫行为的判断中,也完全有可能被分别评价。 ④对于这种理解,也许会存在这样的疑问:在单纯一罪的类型中,也存在原本在自然观察上只能认定为一个行为,几乎不可能进行分别评价的情形。也就是,即便是所谓分别评价,也当然存在界限。例如,为了制止紧迫的非法侵害,持续猛烈压住侵害者的身体,侵害者途中因此失去知觉,其侵害行为也随之完全结束的,疑问就在于,由于该案中仅存在一个暴力行为,因而无法作为防卫行为分别评价。的确,所谓分别评价,也不可能对单一行为进行进一步的分解,因而当然存在一定界限。然而,在该案中,倘若行为人完全意识到被害人已失去知觉,但由于平素的愤懑之情爆发,仍继续压住被害人的,将持续的暴力行为分为侵害结束之前的行为与侵害结束之后的行为分别进行评价,这也不是不可能。
如果非要举出反证例子,即便在构成要件阶段明显属于不同行为,也许仍有可能作为防卫行为予以整体性把握。例如,为了排除紧迫的非法侵害,一边用凶器对准侵害者一边实施胁迫行为,侵害者因此丧失侵害态势并摔倒,也就是在侵害结束之后,行为人因过于亢奋,又使用该凶器对被害人实施暴力行为的,在构成要件阶段,第一行为与第二行为分别被评价为胁迫罪、暴行罪(或者伤害罪),看上去似乎难以进行整体性评价,但在作为防卫行为而评价这两个行为之时,就有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将行为整体评价为“一个防卫行为”,对暴行罪(或者伤害罪)也应认定成立防卫过当。 ⑤
三、防卫过当的刑罚减免根据
(一)一般性理解
由上可见,对于防卫过当的整体性判断,完全有必要作为防卫过当的要件论进行探讨。那么,将侵害持续过程中的对抗行为与侵害结束之后的追击行为作为“一系列的防卫行为”进行概括性评价,对行为整体适用第36条第2款,这是否有可能呢?下面想结合防卫过当的刑罚减免根据一并探讨。
众所周知,对于防卫过当的刑罚减免根据,存在下述三种观点之间的对立:(1)责任减少说以处于紧急状态之下的被侵害人的恐惧、惊愕等心理性压迫为根据,认为减少了责任; ①(2)违法减少说认为,即便是防卫过当,仍然是为了保护正当利益,因而减少了违法性; ②(3)违法·责任减少说则以既减少了违法性也减少了责任为根据。 ③并且,按照责任减少说,侵害结束之后心理性压迫仍有可能持续,因而对于量的过当也可适用第36条第2款;而按照违法减少说,对于侵害结束之后的追击行为,基本不能认定存在防卫效果,因而无法设想违法性的减少,从而一般会否定适用第36条第2款。而按照违法·责任减少说,根据究竟是仅限于同时减少了违法性与责任的情形才适用第36条第2款,还是只要减少了违法性或者责任即可适用第36条第2款,其结论亦会不同; ④若是前者,其最终结论与违法减少说相同,若是后者,则其最终结论与责任减少说无异。 ⑤
笔者一直认为,第36条第2款终究是以实际实施了针对紧迫的非法侵害的客观的防卫行为为前提,行为具有排除侵害的性质是适用第36条第2款的前提。基于这种理解,违法性的减少就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在实际判断是否减免刑罚之际,还应在违法性减少的基础上再考虑责任减少的程度。 ⑥按照笔者的这种理解,似乎对于量的过当会否定适用第36条第2款。但正如山口厚教授指出的那样, ⑦即便是以违法性减少为前提,如果侵害持续过程中的对抗行为与侵害结束之后的追击行为是基于同一意思决定而实施,能够概括性地将二者评价为“一系列的防卫行为”,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防卫行为,就有可能认定违法性的减少,基于要求违法性减少的立场,也有承认量的过当的余地。笔者亦赞同山口厚教授的这种观点。
(二)违法性减少与责任减少的含义
不过,对于本文的这种理解,佐伯仁志教授立足于要求违法性减少的立场提出了批判:对于整体性地评价防卫行为这一点,尚缺乏合理根据。 ⑧也就是,以违法减少说为前提,原本来说,侵害结束之后的追击行为是不能被评价为防卫过当的,正是因为行为整体能被评价为“一系列的防卫行为”(包括了原本不属于防卫行为的部分),对于行为整体就能认定违法性的减少,对于量的过当的类型亦能适用第36条第2款。如果像判例那样,立足于一旦在构成要件阶段确定为“一个行为”就不能再在违法性阻却的层面分别评价这一前提,佐伯仁志教授的观点也是完全能够成立的。但是,如前所述,应该这样来理解:即便在构成要件上作为一个整体接受了评价,但那种判断也不过是相对的,也有可能从违法性阻却事由的角度分别评价。按照这种前提,就不属于构成要件阶段的判断,最终仍有必要按照防卫过当的要件论,提出将防卫行为作为一个整体予以评价的根据,但对于侵害结束之后的追击行为,无法找到减少违法性的契机。这样的话,仅仅从违法性减少的角度,就无法推导出允许对防卫行为进行整体性评价的标准,最终只得再纳入其他视角。本文以为,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佐伯仁志教授的批判是正当的,也只能接受这种批判。
但这并不是说,作为导出防卫行为之整体性的标准,责任减少说就是妥当的。对于可否就防卫过当减免刑罚,既然第36条第2款规定的是刑罚的任意性减免,就有必要区别(1)原本能否适用该款的问题、(2)对于具体案件是否应减轻或者免除刑罚的问题,而有关防卫过当的法律性质的问题属于第(1)个层面的问题。并且,对于质的过当的类型,(如果属于能认定存在防卫意思的案件)不管是出于何种心理状态实施了对抗行为,都当然已经解决了第(1)个层面的要件问题。因此,对于个别案件认定责任减少,即便是在第(2)个层面予以考虑,也不得不认为,在第(1)个层面,这一点并非必须要件。
对于量的过当,也有观点基于责任减少说的立场提出,在侵害结束之后心理性动摇仍在持续的场合,由于责任减少仍在继续,因而可以适用第36条第2款。 ①但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混同了第(1)与第(2)这两个层面的问题。第36条第2款并非是对于存在心理性动摇状况的情形,一般均承认刑罚减免的规定,而仅仅是针对那些能认定具有防卫行为性的案件的规定,因此,就不能认为,“若能认定责任减少就能适用该款”。概言之,若具有作为防卫行为的性质,就可以说,会一般性、类型性地减少责任,但并非是对个别具体的案件,总是要求存在责任减少。换言之,并非是说,如果存在减少责任之状况,仅此即可准用第36条第2款。这样考虑的话,就可以说,责任减少说本身未能提出承认量的过当的合理根据。
这样看来,违法减少说、责任减少说虽然以一般性、类型性的形式说明了防卫过当的性质,但对于界限案件并不能推导出具体的判断标准。 ②最终,对侵害持续过程中的对抗行为正是“乘势”在时间上达到了过当的情形,对能认定存在行为样态的连续性的情形,也有就行为整体认定具有过当防卫的性质的余地,在此限度之内,就不得不认为,对于作为整体的防卫行为,有适用第36条第2款之可能。“乘势”达到量的过当的场合,多类型性地减少非难可能性,而且,对于作为整体的对抗行为也能认定违法性的减少,因此,适用第36条第2款,也有充分的合理性。尤其是,扩张适用第36条第2款之所以能被正当化,作为其实质性根据,下面两点尤为重要:(1)量的过当这一设想,属于通过对一系列的防卫行为认定存在减免刑罚的余地,而有利于处于紧迫状况之下的行为人的制度;(2)侵害的结束时间的认定,事实上包括非常微妙的内容,质的过当与量的过当之间的区别也只能是相对的。
四、量的过当的整体性
(一)整体性的判断标准
1.侵害结束之后的防卫意思
那么,对于量的过当,基于什么要件才能肯定防卫行为的整体性呢?这里想重新比照最高裁判所平成20年判例进行具体探讨。正如大家所见,作为认定第一暴力与第二暴力已经隔断的根据,该决定重视的是,是否存在侵害的持续性与防卫意思,但既然是对于量的过当也以承认防卫过当为前提,不存在侵害的持续性这一点就不能成为直接否定整体性的理由。这样的话,就可以认为,该决定否定整体性的决定性理由在于,在第二暴力阶段已经不再存在防卫意思。学界的有力观点也认为,在能肯定防卫意思的连续性的限度之内,对于侵害结束之后的追击行为,仍能认定维持着防卫性质,从而以此为由支持判例结论。 ①虽然原则上能支持这种观点,但对于这里所谓防卫意思的内容,仍有深入探究之必要。
对于防卫意思的内容,判例并未明确进行定义,但按照一般的理解,即便与其他意思内容并存也没有关系,只要认识到紧迫的非法侵害,具有排除该侵害的意思内容(侵害排除意思)即可。这样的话,在侵害结束之后,虽认识到这一点却仍然实施追击行为的场合,由于原本已经认识到不再存在侵害,因而难以认定具有侵害排除意思。为此,倘若严格要求具有防卫意思的连续性,在行为人对侵害已结束却并无认识的场合,换言之,限于行为人误以为侵害仍在持续的场合,能认定行为人对于追击行为具有防卫意思。但是,对于这种情形,由于能认定存在有关侵害的持续性的错误(误信),对于追击行为,就能认定成立假想防卫或者假想防卫过当。为此,特意承认量的过当这一概念,也便失去了实际意义。 ②这样,学界就有观点基于这种理解而主张,在没有认识到侵害已经结束的场合,作为假想防卫或者假想防卫过当处理即可,没有必要特意承认量的过当这种类型。 ③然而,例如,行为人虽未必认识到侵害已经结束,但处于对方说不定还会再次攻击这种不安之中,从而实施了追击行为的,由于对于侵害的持续并无错误(误信)(即已经正确认识到侵害已经结束),对于其实施的追击行为,势必要认定成立完全的犯罪,但对行为人而言,这种结论未免过于残酷。毋宁说,即便行为人认识到侵害已经结束,但由于过于兴奋或者狼狈,不自主地继续实施了追击行为的,对此就应该整体性地把握整个防卫行为,认定存在适用第36条第2款的余地。 ④这样理解的话,虽然要求的是防卫意思的连续,对于侵害结束之后的追击行为,也并非是要求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防卫意思(亦即,认识到侵害,并试图排除该侵害的意思),只要能认定,与侵害持续过程中的对抗行为的主观方面存在一定的连续性,即已足够。 ⑤对于正当防卫的成立要件,也有观点主张不以防卫意思为必要,我本人也一直认为这种观点要更为妥当。 ⑥按照防卫意思不要说,作为防卫行为整体性的标准,就不能要求存在防卫意思的连续性, ⑦但按照上述理解,将主观上的一定的连续性作为量的过当的要件来理解,这仍然是有可能的。 ⑧
2.防卫行为的客观连续性
除了这种主观方面的连续性之外,是否还应要求存在行为样态的客观连续性与同质性呢?因为,正如前面反复提到的那样,对于量的过当,要适用第36条第2款,对于侵害结束之后的追击行为,也要求作为防卫性质的行为仍然在持续(即要求该追击行为仍具有防卫行为性)。首先,当然以对抗行为与追击行为之间存在时间上、场所上的连续性为必要。并且,还以行为样态保持了一定的连续性为必要。 ①即便是所谓行为样态的连续性,想必也不是要求达到严格的同一性的程度,但对于所使用的凶器、侵害的程度等存在很大不同的例外场合,就应否定存在连续性。而且,在侵害结束之后,防卫行为“乘势”仍在持续,这种关系是很重要的,为此,对于侵害结束之后仍执拗地继续实施追击行为的情形,很多时候,想必难以将该追击行为与(针对侵害的)对抗行为一并进行整体性评价。
作为对最高裁判所平成20年判例的解释,存在强调防卫意思的连续性这种倾向,但由于该决定虽认定第一暴力与第二暴力之间存在时间上、场所上的连续性,但仍然提出缺少防卫意思(以及侵害的持续性),因而难以否定的是,在没有这种连续性就当然应否定量的过当这一意义上,两个暴力在时间上、场所上的连续性仍属于重要标准。而且,本决定进一步鉴于被告人对被害人“实施了相当激烈的第二暴力”,否定成立量的过当。为此,也许还有可能存在这样的理解:第二暴力的程度激烈,这不过是用于认定在该阶段不具有防卫意思的间接事实。但是,该决定在明示第二暴力阶段缺少防卫意思的基础上,又特意提到了第二暴力的行为样态,鉴于此,就可以理解为,判例是以下面这一点作为前提的:对于客观的行为样态的同质性,作为独立于防卫意思的要件,在对整体性进行评价之际,也有可能予以考虑。
(二)整体性评价是绝对的吗?
由上可见,在能够将对抗行为与追击行为评价为主观上、客观上的连续行为之时,就可以整体性地把握二者,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防卫行为,适用第36条第2款。为此,对于最高裁判所平成20年判例,如果在第二暴力阶段,被告人的防卫意思仍在持续,且暴力的行为样态也并非如此激烈,就能肯定量的过当,整体性地评价这两个暴力行为,成立作为防卫过当的伤害致死罪。但是,在第二暴力阶段不能认定存在防卫意思,且两个暴力行为已经隔断(分离)的场合,由于对造成死因的第一暴力已肯定成立正当防卫,那么,最高裁判所平成20年判例中的被告人(尽管不成立防卫过当)就不过是承担伤害罪的罪责。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不均衡:对于第二暴力,防卫意思仍在持续,毋宁说本应从轻处罚的案件,反而处断刑更重。
对于这种“逆转现象”,负责调查最高裁判所平成20年判例以及最高裁判所平成21年判例的调查官松田俊哉裁判官认为,这些都可以在量刑的层面应对,因而不是问题。 ②但是,如果认为只要在量刑判断中能够应对,罪名是什么都没有关系,那么,刑法解释论就几乎变得没有任何意义(果真如此的话,吾等学人也就没有立身之所了)。而且,造成死因的第一暴力本身被评价为正当防卫行为,死亡结果的引起也一旦被正当化,因此,是否可将死亡结果归责于被告人,其结论受其后的第二暴力的主观、客观的样态所左右,就显然不当。对此,松田俊哉裁判官提出了反论:如果第一暴力与第二暴力作为一个整体该当于一个伤害罪的构成要件,第一暴力就不过是该整体行为的一部分,不可能就一个行为的一部分终局性地判断是否成立正当防卫,因而第一暴力终究不过是“正当防卫性的行为”。 ③然而,这种反论只有在下述前提下才可能成立:对于被评价为“一系列的防卫行为”的行为,几乎不可能在违法性层面予以分离。但如前所述,这种前提本身就是不妥当的。
原本来说,对于量的过当这一概念,之所以对防卫行为采取整体性评价,其出发点就在于做有利于行为人的解释。也就是,对于趁势继续实施了追击行为的情形,认定成立完全的犯罪,对行为人而言过于残酷,因此,对于那些可以与侵害当时的对抗行为进行整体性评价的案件,通过承认就整体行为成立防卫过当,给予被告人以减免刑罚的可能性,就属于主要的问题意识。这样的话,如果作为量的过当进行整体性评价,反而会给被害人带来不利益,这种事态的出现就与进行整体性评价的本来旨趣正好相反,显然难以无视这一点。对于这种情形,即便属于可以作为量的过当进行整体性评价的案件,也应该允许存在分别评价第一暴力与第二暴力的可能性。就最高裁判所平成20年判例而言,即便在第二暴力阶段防卫意思仍在连续,也还是应该通过分别评价第一暴力与第二暴力,而排除成立伤害致死罪。对此情形,山口厚教授肯定成立伤害罪的防卫过当。 ①将由第一暴力引起的死亡结果排除在归责范围之外,限于成立伤害罪,笔者对这一点当然是赞成的,但问题在于,如果将第一暴力与第二暴力分离开来,就无法将第二暴力本身评价为防卫行为。按照这种理解,在进行分离式评价的场合,就会与平成20年最高裁判所的判例一样,成立作为完全的犯罪的伤害罪。
慎重起见,这里对本文观点做些梳理。在侵害当时的第一暴力与侵害结束之后的第二暴力能认定存在主观上的连续性、客观上的行为样态的连续性的场合,就可以将整体行为评价为一系列的防卫行为,对于整体行为认定成立防卫过当。不过,如果整体性评价二者,反而会在处断刑上造成行为人之不利的,就可以分离二者,就第二暴力认定成立完全的犯罪(实际限于那些由第一暴力引起了重大结果的案件)。反之,在两个暴力之间存在很大分离的场合,由于原本就不存在进行整体性评价的基础,因而起始就应分别评价二者。
下面结合两个案例确认本文观点。第一个案例是,如果单独评价第一暴力能成立正当防卫,但侵害结束之后行为人又实施了第二暴力,而且,第一暴力造成了死因,且通过第二暴力有意提早了死亡时间。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属于像最高裁判所平成20年判例那样,由于在第二阶段不能认定存在防卫意思等,两个暴力之间存在分离的案件,那么,就分别评价两个暴力行为,成立作为完全的犯罪的伤害致死罪。这是因为,虽然第二暴力并未形成独立的死因,但只要施加了提早死期这种影响,即便单独评价第二暴力,也能认定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反之,在第二暴力也是基于防卫意思的行为,能够整体性地评价二者的场合,就应对两个暴力进行整体性评价,成立伤害致死罪的防卫过当。如果对这种场合进行分离式评价,第二暴力反而会丧失减免刑罚的余地的,那么,对于这种场合就应该贯彻整体性评价。 ②
第二个案例是,第一暴力与第二暴力的具体状况完全是相通的,但究竟是由哪一个暴力造成了属于死因的伤害,这一点并不明确。在该场合下,两个暴力之间存在分离的,就限于第二暴力,仅成立作为完全的犯罪的伤害罪(当然不成立伤害致死罪)。另外,对于那些因存在连续的防卫意思等而可以对两个暴力进行整体性评价的案件,就整体行为认定成立伤害致死罪的防卫过当,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即便是这种场合,也仍然应该承认有分别评价二者的余地。而且,在分别评价二者的场合,第二暴力就限于成立作为完全的犯罪的伤害罪,为此,就应朝着有利于被告人的方向,优先进行分离处理。对于本文的这种理解,批判意见指出,明明是由被告人的行为造成了死亡结果,却不能将死亡结果归责于被告人,这显然不妥。 ③但既然相当于正当防卫的行为存在引起死亡结果的可能性,不将死亡结果归责
于被告人,毋宁说,这是理所当然的。 ①
五、质的过当的整体性
最后,想就侵害持续过程中实施了数个防卫行为的场合的整体性评价的界限,简单做些探讨。这里的问题在于,在一系列的防卫行为之中,既有满足相当性要件的防卫行为,也有僭越了相当性要件的防卫行为,那么,究竟是就整体防卫行为认定成立防卫过当,还是仅限于就后一行为认定成立防卫过当呢?
作为是否应整体性地评价第一暴力与第二暴力的标准,前述最高裁判所平成20年判例尤其重视侵害的持续性与防卫意思的连续性。在侵害持续过程中实施了数个防卫行为的场合,满足了前一要件(侵害的持续性),这是当然的前提,因而后一要件即防卫意思的连续性就成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标准。实际上,最高裁判所平成21年判例也认为,“属于针对紧迫的非法侵害的一系列、一个整体的行为,能够认定为是基于同一防卫意思的一个行为”,以此作为认定一个行为(行为的单个性)的要件,重视防卫意思的连续性。不过,从上述引用中显而易见,最高裁判所平成21年判例是以数个暴力行为属于“一系列、一个整体的行为”为前提,进一步谈到了防卫意思的连续性,因此,对于行为能否评价为“一系列、一个整体的行为”,就不仅仅是对防卫意思的判断,还一并考虑了时间上、场所上的连续性以及行为样态的共通性。由此可见,重视非法侵害的连续性、防卫意思的连续性,同时一并考虑其他客观情况,在这一点上,可以认为,最高裁判所平成21年判例采取了与最高裁判所平成20年判例相同的判断结构。
并且,按照判例观点,对于肯定防卫行为的整体性的案件,这种整体性评价应该一以贯之。为此,若单独评价引起了伤害结果的第一暴力,可以评价为正当防卫,而与伤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的第二暴力僭越了相当性要件,即便是这种情形,对于整体的防卫行为,也能认定“成立作为一个防卫过当的伤害罪”。当然,在该情形下,分别(分离式地)评价两个暴力行为,会得出有利于被告人的结论(止于成立暴行罪的防卫过当),但这种不均衡“只要作为有利情节加以考虑即可”。在以判例的这种理解为前提的场合,如果属于在本案的第二暴力阶段被告人丧失防卫意思而完全是出于攻击的意思而实施了对抗行为的场合,两个暴力行为之间就失去连续性,被分别评价(分离式地进行评价),因此,第一暴力就作为正当防卫阻却违法性,只有第二暴力作为完全的犯罪成立暴行罪。 ②为此,对于出于防卫意思而实施了第二暴力的被告人,与完全出于攻击意思而实施了第二暴力的情形相比,最高裁判所平成21年判例反而在处断刑的层面得出了不利于被告人的结论。
正如前面反复阐述的那样,按照本文立场,防卫行为的整体性评价并不是绝对的,即便是那些防卫行为的内容仍在持续、可以整体性地把握数个暴力行为的场合,仍应认定具有进行分离式评价(分别评价)的余地。并且,在整体性评价反而会给行为人带来不利益结论的场合,更应优先采取分离式地评价(分别评价)这种处理方式。不过,需要慎重探讨的是,本案不是量的过当的类型,而属于质的过当的类型。也就是,对于量的过当,侵害持续过程中的对抗行为与侵害结束之后的追击行为,原本具有不同的性质,因而完全有可能对二者采取分离式地评价(分别评价);但质的过当的类型则是为了排除同一个非法侵害而连续实施了对抗行为,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防卫行为,毋宁说,原则上应采取整体性评价。 ③“对于紧迫的非法侵害,不是就各个瞬间进行微评,而是以开始时点为起点在一定幅度之内承认侵害行为的持续,因而对于应对该侵害行为的反击行为,也是自侵害开始之时直至侵害结束之时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评价” ①,从直觉上看,这种观点中的某些内容是具有说服力的。这样,难以否定的是,在质的过当的类型中,总是就对抗行为进行整体性地评价,这种理解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非法侵害被整体性地评价,因而防卫行为也有必要进行整体性评价,这种理解是否真有充分的根据呢?虽说是侵害行为被整体性评价,那也不是指自然意义上的单一侵害在持续进行,而是指虽实施了数个侵害行为,但对于这些侵害行为之整体能够肯定侵害的持续性,而不是说,这些侵害行为属于一个不可分离的实体。并且,所谓正当防卫,是为了排除时间上紧迫的侵害的手段,只要无法想象到针对已经实施的侵害的排除行为,由于已经实施的侵害的结束时点与此后就要实施的侵害的开始时点事实上是重合的,为此,侵害的持续性这一概念就不过是,不是为了分离二者(已经实施的侵害与就要实施的侵害),而是为了将整体侵害评价为一系列的“持续的侵害”的概念而已。 ②也就是,作为侵害行为,持续实施了第一侵害行为与第二侵害行为之时,在第一侵害行为结束的阶段,就已经能认定有关第二侵害行为的时间上的紧迫性,因此,原本来说,是包括性地评价数个侵害行为,是对整体侵害认定具有侵害的持续性。这样考虑的话,侵害的整体性这一评价(与防卫行为的整体性评价一样)就不是绝对的标准,对数个侵害进行分离式考察(分别考察)的可能性,也并非是被完全排除。这样的话,就不应该将侵害仍在持续这一事实予以绝对化,对于这期间的防卫行为,仍应认定具有进行分离式评价(分别评价)的余地。例如,像侵害行为一旦中断之后,其后的侵害及其程度发生很大改变的场合那样,对于那些侵害行为的内容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形,由于可以理解为,先行的第一侵害行为已经结束,与此同时,新的第二侵害行为又已经迫近,因此,根据各个不同的情形(局面),分离式地评价(分别评价)防卫行为,也应该是有可能的。按照这种理解,对于最高裁判所平成21年判例的案件,在第一暴力阶段与第二暴力阶段,正可谓侵害行为的局面已经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化,因而完全有可能将两个暴力行为分离开来分别作为评价对象,作为分离式评价(分别评价)之结论,就应该仅限于对第二暴力行为认定成立暴行罪的防卫过当。 ③
事实上,就最高裁判所平成21年判例的案件而言,被告人将折叠桌推回,被害人因撞上折叠桌而摔倒,由此被害人的侵害行为一旦已经结束,那么,在第二暴力阶段,能否认定存在侵害的持续性,在事实认定上就仿佛只是片纸之隔。当然,如果彻底贯彻判例立场,对本案来说,无论第二暴力阶段侵害行为是否持续,不管如何,从防卫意思的持续性的角度来看,对于一系列的防卫行为均能认定成立防卫过当,因而这一点(是否存在侵害的持续性)并不重要。但是,如前所述,对于量的过当的案件,即便是处于能够肯定整体性的状况之下,以为了行为人的利益考虑这一形式,仍有分别评价二者的可能,如果立足于这一前提,那么,一旦认定存在侵害的持续性,就几乎将分离式评价排除在外,这种区分就不具有合理性。总之,对于质的过当的类型,也还是应该承认,在一定范围之内仍然有进行分离式评价的余地。(※下次的论题分别是“构成要件性符合的界限”、“构成要件的推迟实现与构成要件的提前实现”)
(责任编辑:钱叶六)
日本刑法第36条〔正当防卫〕:为了防卫自己或者他人的权利,对于紧迫的不法侵害不得已实施的行为,不处罚(第1款)。超出防卫限度的行为,可以根据情节减轻或者免除刑罚(第2款)。——译者注
对此,佐伯仁志也认为,有关正当防卫的判例“在所有判例理论中,是最为缜密的理论之一”(参见佐伯仁志:《裁判員裁判と刑法の難解概念》,载《法曹時報》第61卷第8期〔2009年〕,第16页)。笔者有关这一点的理解,参见橋爪隆:《裁判員裁判のもとにおける刑法理論》,载《法曹時報》第60卷第5期(2008年),第15页以下。
例如,香城敏麿:《正当防衛における急迫性》,载小林充、香城敏麿编:《刑事事実認定――裁判例の総合的研究》(上),判例タイムズ社1994年版,第261页以下;佐藤文哉:《正当防衛における退避可能性について》,载《西原春夫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第1卷),成文堂1998年版,第236页以下;波床昌則:《正当防衛における急迫不正の侵害》,载大塚仁、佐藤文哉编:《新実例刑法》(総論),青林書院2001年版,第79页以下;中川博之:《正当防衛の認定》,载木谷明编著:《刑事事実認定の基本問題》,成文堂2010年第2版,第121页以下;遠藤邦彦:《正当防衛判断の実際》,载《刑法雑誌》第50卷第2期(2011年),第303页以下;安廣文夫:《正当防衛·過剰防衛》,载《法学教室》第387期(2012年),第14页以下;和田真、野口卓志、增尾崇:《正当防衛について》(上),载《判例タイムズ》第1365期(2012年),第46页以下;栃木力:《正当防衛における急迫性》,载小林充、植村立郎编:《刑事事実認定重要判決50選》(上),立花书房2013年第2版,第71页以下;等等。
参见橋爪隆:《正当防衛論の基礎》,有斐閣2007年版,第88页以下、305页以下。
参见大判昭和7年(1932年)1月25日刑集11卷1页,等等。
此后的最判昭和32年(1957年)1月22日刑集11卷1号31页就是以与本文相同的旨趣解释了最高裁判所昭和23年判例,最终撤销了否定成立正当防卫的二审判决。
对有关侵害的开始时间、结束时间的学说的详细探讨,参见明照博章:《正当防衛権の構造》,成文堂2013年版,第24页以下。
实际上,最判昭和59年(1984年)1月30日刑集38卷1号185页判定,对于被害人实施的攻击,“被告人对此并无预期,应该说,那属于针对被告人的紧迫的非法侵害”,而完全没有言及被告人是否存在积极的加害意思。松浦繁对此的理解是,该判决是要求对侵害存在切实的预期(松浦繁:《判解》,载財団法人法曹会编:《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昭和59年度〕,第241页)。
参见香城敏麿:《判解》,载財団法人法曹会编:《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昭和52年度),第246页;栃木力:《正当防衛における急迫性》,载小林充、植村立郎编:《刑事事実認定重要判決50選》(上),立花书房2013年第2版,第81页;等等。
安广文夫裁判官将积极的加害意思理解为,“起始便决意向对方实施同种同等的反击……这种激烈行为,但根据事态发展,也不放弃实施超出防卫程度的过当行为的意思”,而并非是以意图实施的加害内容本身是积极的(过激)行为这一点作为其本质性内容。参见安廣文夫:《判解》,载財団法人法曹会编:《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昭和60年度),第149页。
参见安廣文夫:《判解》,载財団法人法曹会编:《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昭和60年度),第150页。
判例尽管认为必须存在防卫意思,但即便是因愤慨、盛怒而实施的反击行为,也并未由此便直接否定防卫意思(最判昭和46年〔1971年〕11月16日刑集25卷8号996页),而是认为即便同时存在攻击的意思亦可(最判昭和50年〔1975年〕11月28日刑集29卷10 号983页)。为此,在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即便只是稍微能认定存在试图防卫的意思,就会被评价为“为了防卫”而实施的行为,因此,在正常的正当防卫状况之下,几乎很难想象出缺少防卫意思的案件。在审判实务中,否定防卫意思的案件,也是限于(1)针对鲜有危险性的侵害行为,有意识地选择了危险的防卫手段的情形,以及(2)虽已认识到侵害已经结束,仍实施追击行为的情形。由此可见,事实上,不过是针对那些客观上有可能相当于防卫过当的行为,起到了排除适用刑法第36条第2款的功能。关于这一点,详见今井猛嘉等:《刑法总论》,有斐閣2012年第2版,第207页以下(桥爪隆执笔)。
参见香城敏麿:《判解》,载財団法人法曹会编:《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昭和52年度),第247页。
参见香城敏麿:《正当防衛における急迫性》,载小林充、香城敏麿编:《刑事事実認定——裁判例の総合的研究》(上),判例タイムズ社1994年版,第263页。
需要提请注意的是,既然承认由第三者实施的防卫行为,就势必出现防卫行为人与被侵害人不相一致的情形,进一步考虑的话,是否存在状况紧迫性,就应以被侵害人(而非防卫行为人)的情况作为判断标准(参见橋爪隆:《正当防衛論の基礎》,有斐閣2007年版,第328页以下)。不过,本文设想的是防卫行为人与被侵害人一致的典型案情。
参见安廣文夫:《判解》,载財団法人法曹会编:《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昭和60年度),第149页。
井田良教授等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参见井田良:《講義刑法学·総論》,有斐閣2008年版,第276页;波床昌则:《正当防衛における急迫不正の侵害》,载大塚仁、佐藤文哉编:《新実例刑法(総論)》,青林书院2001年版,第84页;等等。
参见橋爪隆:《正当防衛論の基礎》,有斐閣2007年版,第155页以下。
例如,仙台高秋田支判昭和55年(1980年)1月29日判タ423号148页、大阪地判平成3年(1991年)4月24日判タ763号284页,等等。
例如,大阪高判平成7年(1995年)3月31日判タ887号259页、东京地判平成10年(1998年)10月27日判タ1019号297页,等等。
例如,大阪高判昭和53年(1978年)6月14日判タ369号431页、札幌高判昭和63年(1988年)10月4日判时1312号148页,等等。
例如,东京地判平成8年(1996年)3月12日判时1599号149页,等等。
例如,大阪高判平成14年(2002年)7月9日判时1797号159页。对该案的评释,参见齊藤彰子:《判批》,载《判例評論》第538期(《判例時報》第1834期)(2003年),第43页以下;橋爪隆:《判批》,载《刑事法ジャーナル》第8期(2007年),第126页以下。
关于这一点,参见香城敏麿:《正当防衛における急迫性》,载小林充、香城敏麿编:《刑事事実認定——裁判例の総合的研究》(上),判例タイムズ社1994年版,第273、283页;等等。
对此,町野朔教授指出,所谓积极的加害意思,就被理解为,不过是对于所预期的侵害,“在能够避免却不避免、能够逃避却不逃避的情形下,行为人事实上才会出现的意思”,应该说这是一种正确的意见。参见阿部純二、中義勝等:《刑法総論の現代的課題》,载《Law School》第42期(1982年),第15页(町野朔执笔)。
?
参见遠藤邦彦:《正当防衛判断の実際》,载《刑法雑誌》第50卷第2期(2011年),第309页以下。
参见大阪高判昭和56年(1981年)1月20日判时1006号112页、大阪高判平成13年(2001年)1月30日判时1745号150页、东京地判平成14年(2002年)1月11日(公开刊物未刊登,参见裁判所HP),等等。例如,大阪高判平成13年判决判定,“基于被告人等平常就一直采取的警卫态势而实施的迎击行为,这本身就属于带有违法性的行为;并且,本案袭击行为的性质、程度也并未超出被告人等的预想。比照这些情况,本案犯罪行为就不具备侵害的紧迫性要件,不属于应认定成立正当防卫的紧迫状况之下的行为”。
包括自招侵害的情形在内,对于规范性考虑先行事实这种做法持否定态度的观点,参见浅田和茂:《刑法総論》,成文堂2007年补正版,第235页。另外,除了自招侵害的情形之外,立足于相同前提的观点,参见松宮孝明:《刑法総論講義》,成文堂2009年第4版,第137页以下;塩見淳:《侵害に先行する事情と正当防衛》,载《法学教室》第382期(2012年),第79页以下;等等。
参见塩見淳:《侵害に先行する事情と正当防衛》,载《法学教室》第382期(2012年),第80页;照沼亮介:《侵害に先行する事情と正当防衛の限界》,载《築波ロー·ジャーナル》第9号(2011年),第133页以下(不过,该文第153页指出,对于准备凶器前往现场的案件,也有否定防卫行为性的余地);等等。
进一步而言,如果认为,即便防卫人已经对侵害存在预期,其本人也存在加害意思,同样也不能成为限制正当防卫的根据,那么,这样的话,防卫人也理应没有为防卫进行事前准备之必要。也就是,该观点认为,即便事先已经对侵害存在预期,由于没有避免(回避)侵害的义务,因而并不影响对急迫性的判断;不过,由于事先存在预期,无疑会扩大针对这种侵害的防卫可能性,因而在判断有无防卫行为的相当性之时,事实上会更加严格。但在本文看来,如果没有避免(回避)侵害的义务,势必也没有通过事先准备工具等而应对侵害的义务,既然如此,就不可能期待防卫人事先进行防卫准备,更不能赋予其这种义务。在此意义上,就可以说,对于事先准备这种机会,防卫人也没有加以适当利用的义务。因此,是否真的能够说,可供选择的防卫手段的范围会更大,对此就不无怀疑的余地。
参见曽根威彦:《刑法総論》,弘文堂2008年第4版,第102页;高山佳奈子:《“不正”対“不正”状況の解決》,载《研修》第740期(2010年),第6页以下;照沼亮介:《侵害に先行する事情と正当防衛の限界》,载《築波ロー·ジャーナル》第9号(2011年),第124页以下;等等。
关于这一点,参见遠藤邦彦:《正当防衛判断の実際》,载《刑法雑誌》第50卷第2期(2011年),第314页。西田典之此前就已经指出同样的问题(参见西田典之:《現代刑事法学の視点》,载《法曹時報》第61卷第13期〔1989年〕,第104页)。
关于这种理解,参见山口厚:《刑法総論》,有斐閣2007年第2版,第130页以下;佐伯仁志:《刑法総論の考え方·楽しみ方》,有斐閣2013年版,第148页;桥爪隆:《正当防衛論の基礎》,有斐閣2007年版,第353页以下;等等。作为防卫行为的相当性的要件,判例也要求“作为防卫之手段,是最小必要限度的手段”(参见最判昭和44年〔1969年〕12月4日刑集23卷12号1573页)。
当然,考虑到有免除刑罚的可能性,认定成立防卫过当也还是有相当意义的,但因防卫过当而免除刑罚的,仅限于那些特别罕见的情形;而且,在以斗殴、自招侵害作为问题的案件中,几乎很难想象会有适于免除刑罚的情况。
例如,大谷實:《刑法講義総論》,成文堂2012年新版第4版,第275页;山中敬一:《刑法総論》,成文堂2008年第2版,第453页以下;曽根威彦:《刑法総論》,弘文堂2008年第4版,第101页;等等。
例如,大塚仁:《刑法概説(総論)》,有斐閣2008年第4版,第383页注4;大谷實:《刑法講義総論》,成文堂2012年新版第4版,第276页;等等。
当然,在判断被侵害者所处的利益状况时,也要考虑行为人的目的等主观方面的情况,但被侵害者所处的利益状况,不应为积极的加害意思这种纯粹的心情要素所左右。也有学者表达了同样的态度(参见佐伯仁志:《刑法総論の考え方·楽しみ方》,有斐閣2013年版,第134页;塩見淳:《侵害に先行する事情と正当防衛》,载《法学教室》第382期〔2012年〕,第79页;等等)。反之,山口厚教授则将事前的积极加害意思作为否定被侵害者的正当利益的要保护性的要素而予以正当化(参见山口厚:《正当防衛論の新展開》,载《法曹時報》第61卷第2期〔2009年〕,第33页);林干人教授也认为,若存在积极的加害意思,就能认定存在主观上的高度违法性(参见林幹人:《判例刑法》,東京大学出版会2011年版,第55页)。
参见安廣文夫:《判解》,载財団法人法曹会编:《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昭和60年度),第151页。
参见橋爪隆:《正当防衛論の基礎》,有斐閣2007年版,第305页以下。作为主张这种侵害避免义务的先驱性观点,参见佐藤文哉:《正当防衛における退避可能性について》,载《西原春夫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第1卷),成文堂1998年版,第242页以下。另外,对笔者观点做了概要性阐述的资料,参见橋爪隆:《急迫不正の侵害》,载西田典之等编:《刑法の争点》,有斐閣2007年版,第41页。
为此,对于前述最高裁判所昭和52年决定的案件,为了召开集会而停留在现场,这原本就已经只是名义上的目的,而且,(本人等是否提出了请求,这另当别论)如果处于警方的救助完全来得及的状况之下,就应支持否定紧迫性的结论。反之,松原芳博教授则重视对被告人等的集会自由的保护(参见松原芳博:《刑法総論》,日本評論社2013年版,第162页)。
例如,西田典之:《刑法総論》,弘文堂2010年第2版,第167页;前田雅英:《刑法講義総論》,東京大学出版会2011年第5版,第365页;佐伯仁志:《刑法総論の考え方·楽しみ方》,有斐閣2013年版,第154页以下;栃木力:《正当防衛における急迫性》,载小林充、植村立郎编:《刑事事実認定重要判決50選》(上),立花书房2013年第2版,第76页以下;等等。还有学者从事前负担的要求可能性的角度,探讨是否存在侵害避免义务(参见高橋則夫、杉本一敏:《正当防衛における負担要求可能性》,载《法学セミナー》第692期〔2012年〕,第116页以下)。另外,以“侵害避免义务论”为根据的判例,参见奈良地判平成19年(2007年)3月27日(公开刊物未刊登,参见裁判所HP)、大阪地判平成20年(2008年)9月19日(公开刊物未刊登,参见裁判所HP)、东京高判平成21年(2009年)10 月8日判タ1388号370页;等等。
例如,林幹人:《刑法総論》,东京大学出版会2008年第2版,第189页;照沼亮介:《侵害に先行する事情と正当防衛の限界》,载《築波ロー·ジャーナル》第9号(2011年),第130页;等等。
例如,虽应避免侵害却不避免而是选择直接面对侵害,但侵害程度轻微远超出当初的预想,于是行为人放弃防卫行为而甘愿承受侵害的,就当然不能处罚行为人。
例如,塩見淳:《侵害に先行する事情と正当防衛》,载《法学教室》第382期(2012年),第81页。
对此,有学者指出,两者的问题领域“处于存在部分交叉的两个圆那样的关系”。参见的場純男、川本清厳:《自招侵害と正当防衛》,载大塚仁、佐藤文哉编:《新実例刑法》(総論),青林书院2001年版,第111页。
关于这一点,参见前田雅英:《刑法講義総論》,東京大学出版会2011年第5版,第371页。
对此,高山佳奈子认为,自招侵害属于“彼此彼此”的关系,即所谓“不法”对“不法”的关系,进而否定侵害的非法性,而主张在紧急避险的限度之内将对抗行为予以正当化。参见高山佳奈子:《正当防衛論》(下),载《法学教室》第268号(2003年),第70页以下。
参见山本輝之:《自招侵害に対する正当防衛》,载《上智法学論集》第27卷第2期(1984年),第211页以下;山中敬一:《正当防衛の限界》,成文堂1985年版,第96页以下;齊藤诚二:《正当防衛権の根拠と展開》,多賀出版1991年版,第197页以下;吉田宣之:《違法性の本質と行為無価値》,成文堂1992年版,第61页以下;川端博:《正当防衛権の再生》,成文堂1998年版,第73页以下;岡本昌子:《自招侵害について》,载《同志社法学》第50卷第3期(1999年),第285页以下;等等。
此类判例参见东京高判昭和60年(1985年)6月20日判时1162号168页、东京高判昭和60年(1985年)8月20日判时1183号163页、札幌地判平成元年(1989年)10月2日判タ721号249页;等等。“侵害避免义务论”也认为,虽预期到反击仍实施挑衅性言行的,在对此不能认定存在正当利益的情形下,就有义务不实施该言行,尽管如此,侵害仍然被现实化的,就应否定存在侵害的紧迫性。
例如,福冈高判昭和60年(1985年)7月8日判タ566号317页、仙台地判平成18年(2006年)10月23日判タ1230号348页;等等。后述平成20年的最高裁判所决定的二审(东京高判平成18年〔2006年〕11月29日刑集62卷6号1802页)也做出了同样判断。有关下级裁判所判例的详细介绍,参见明照博章:《正当防衛における“自招侵害”の処理》(3),载《松山大学論集》第21卷第3期(2009年),第101页以下。
以该决定为契机,研究自招侵害的文献,参见吉田宣之:《“自招侵害”と正当防衛の制限》,载《判例時報》第2025期(2009年),第3页以下;照沼亮介:《正当防衛と自招侵害》,载《刑事法ジャーナル》第16期(2009年),第13页以下;橋田久:《自招侵害》,载《研修》第747期(2010年),第3页以下;岡本昌子:《正当防衛状況の創出と刑法36条》,载《大谷實先生喜寿記念論文集》,成文堂2011年版,第403页以下;木崎峻輔:《自招防衛の処理について》,载《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法研論集》第143期(2012年),第101页以下;等等。
对于本案案情事实也有学者提出了疑问:在被告人试图实施第三暴力之际,原本能否谓之为,第二暴力(非法侵害)仍处于持续状态之下。参见安廣文夫:《正当防衛·過剰防衛》,载《法学教室》第387期(2012年),第18页;橋田久:《判批》,载《名古屋大学法政論集》第244期(2012年),第133页。不过,由于裁判所是以侵害仍在持续为前提,对自招侵害做出了判断,因而这里不讨论此问题。
所谓“事例判例”,是指该判例是仅就能认定存在一定事实关系之时所做出的具体判断,不具有一般适用性。例如,采取诸如“对于能认定存在这种事实的本案而言,应判定满足了某要件”等形式,是以存在一定的事实关系为前提而做出的判断。如果事实关系不同,结论也自当不同。反之,如果以“对于某条的某要件应该解释为……”这种形式做出判断,显示的就是判例的一般态度,即便脱离相应事实关系,判例就该条的解释也属于一般性指针,对于其他案件,该判例解释也同样适用。——译者注
对于该决定,佐伯仁志重视的是,这可以成为应对裁判员裁判制度的客观标准(参见佐伯仁志:《裁判員裁判と刑法の難解概念》,载《法曹時報》第61卷第8期〔2009年〕,第21页)。关于这一点,另见川瀬雅彦:《判批》,载《慶應法学》第20期(2011年),第305页以下。
详见橋爪隆:《判批》,载《ジュリスト》第1391期(2009年),第159页以下。
关于这一点,详见三浦透:《判解》,载財団法人法曹会编:《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平成20年度),第432页以下;山口厚:《正当防衛論の新展開》,载《法曹時報》第61卷第2期(2009年),第20页以下。
参见塩見淳:《侵害に先行する事情と正当防衛》,载《法学教室》第382期(2012年),第84页;橋田久:《判批》,载《名古屋大学法政論集》第244期(2012年),第141页。
参见三浦透:《判解》,载財団法人法曹会编:《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平成20年度),第439页。
山口厚认为,两个暴力之间的均衡性要件可以对行为赋予“作为非法的相互斗殴行为之一环而实施”的性质(山口厚:《正当防衛論の新展開》,载《法曹時報》第61卷第2期〔2009年〕,第22页)。但既然相互之间的斗殴有可能会升级,就未必能推导出均衡性。
桥田久的文章中也暗示,在本决定举出的客观要件之中,已包含着有意识地避免由不考虑主观要件所引起的结论不当这种意图。参见橋田久:《判批》,载《名古屋大学法政論集》第244期(2012年),第137页。
例如,如果对方性格很暴烈,或者对方手中正好持有危险性程度很高的凶器,就完全能想到这种情况。
参见橋爪隆:《正当防衛論の基礎》,有斐閣2007年版,第322页以下。
同样的观点参见山口厚:《正当防衛論の新展開》,载《法曹時報》第61卷第2期(2009年),第18页。
参见橋爪隆:《判批》,载《ジュリスト》第1391期(2009年),第163页。要求存在预见可能性的观点,参见栃木力:《正当防衛における急迫性》,载小林充、植村立郎编:《刑事事実認定重要判決50選》(上),立花书房2013年第2版,第85页;塩見淳:《侵害に先行する事情と正当防衛》,载《法学教室》第382期(2012年),第83页;等等。另外,小林宪太郎基于限制正当防卫的成立是对自招侵害者的制裁这一立场,要求在自招行为的阶段存在责任(参见小林憲太郎:《自招防衛と権利濫用説》,载《研修》第716期〔2008年〕,第7页以下)。
参见佐伯仁志:《刑法総論の考え方·楽しみ方》,有斐閣2013年版,第158页;三浦透:《判解》,载財団法人法曹会编:《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平成20年度),第433页以下。
参见三浦透:《判解》,载財団法人法曹会编:《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平成20年度),第440页;中川博之:《正当防衛の認定》,载木谷明编著:《刑事事実認定の基本問題》,成文堂2010年第2版,第137页;等等。
参见遠藤邦彦:《正当防衛判断の実際》,载《刑法雑誌》第50卷第2期(2011年),第196页。
对于量的防卫过当的定义,也有观点认为,不仅是像本文那样限于侵害结束之后实施追击行为的情形(时间上的过当),侵害持续过程中实施数个对抗行为的情形下,对抗行为途中超越了相当性限度的情形也包括在内。不过,对于后者成立防卫过当并无异议,因而本文根据本文的定义区别这两种情形。
关于此问题的最近的文献,参见山口厚:《正当防衛と過剰防衛》,载《刑事法ジャーナル》第15期(2009年),第50页以下;橋田久:《量的過剰防衛》,载《刑事法ジャーナル》第16期(2009年),第21页以下;前田雅英:《正当防衛行為の類型性》,载《研修》第734期(2009年),第3页以下;長井圓:《過剰防衛の一体的評価と分断的評価》,载《立石二六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成文堂2010年版,第215页以下;安田拓人:《事後的過剰防衛について》,载《立石二六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成文堂2010年版,第243页以下;原口伸夫:《量的過剰防衛について》,载《立石二六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成文堂2010年版,第271页以下;植田博:《量的過剰防衛の周辺問題》,载《修道法学》第33卷第1期(2010年),第55页以下;小野正晃:《防衛行為の個数について》,载《阪大法学》第60卷第6期(2011年),第83页以下;井上宜裕:《量的過剰防衛》,载松原芳博编:《刑法の判例》(総論),成文堂2011年版,第75页以下;林幹人:《量的過剰について》,载林幹人:《判例刑法》,東京大学出版会2011年版,第67页以下;佐藤拓磨:《量的過剰について》,载《法学研究》第84卷第9期(2011年),第173页以下;山本輝之:《量的過剰防衛についての覚書》,载《研修》第761期(2011年),第9页以下;成瀬幸典:《量的過剰に関する一考察》(1)(2·完),载《法学》第74卷第1期(2010年)第1页以下、第75卷第6期(2012年)第48页以下;仲道祐樹:《行為概念の再定位——犯罪論における行為特定の理論》,成文堂2013年版,第213页以下;滝谷英幸:《量的過剰とその周辺問題》,载《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法研論集》第145期(2013年),第187页以下;高橋直哉:《複数の反撃行為と過剰防衛の成否》,载《駿河台法学》第26卷第2期(2013年),第45页以下;照沼亮介:《『防衛行為の一体性』に関する判例》,载《法学セミナー》第705期(2013年),第5页以下;等等。另外,作为笔者此前的探讨,参见橋爪隆:《防衛行為の一体性について》,载《三井誠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有斐閣2012年版,第95页以下。本文正是以该论文内容为前提,做进一步探讨。
反之,山本輝之教授则认为,本案也属于质的过当的类型。参见山本辉之:《量的過剰防衛についての覚書》,载《研修》第761期(2011年),第11页以下。
安广文夫裁判官认为,对于量的过当,“通过整体性考察认定防卫过当,是业已确立的判例立场”(参见安廣文夫:《正当防衛·過剰防衛に関する最近の判例について》,载《刑法雑誌》第35卷第2期〔1996年〕,第88页以下)。最判平成6年(1994年)12月6日刑集48卷8号509页也判定,尽管是以共同实行者之间的共谋的射程成为问题的案件,但“在侵害当时的暴力能被评价为正当防卫的场合,对于侵害结束之后的暴力……应该探讨是否重新成立了共谋,只有认定成立共谋,此时才应将侵害当时以及侵害结束之后的一系列行为作为整体来考察,探讨作为防卫行为的相当性”。对此,一般认为,该判决的当然前提是,对于量的过当适用刑法第36条第2款。
二审(大阪高判平成20年〔2008年〕10月14日刑集63卷2号15页)认为,在该阶段,被害人乙也并未失去攻击意思,“马上调整态势再度实施攻击,客观上也是可能的”,从而认定不法侵害仍在持续。想必最高裁判所的判断也是以该事实评价为前提,为此才会判断第二暴力属于质的过当的类型。另见松田俊哉:《判解》,载財団法人法曹会编:《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平成21年度),第8页。
如果认为,最高裁判所平成20年判例重视的是,在第二暴力阶段,既不能认定存在侵害的持续性也不能认定存在防卫意思,因此,要肯定整体性评价,侵害的持续性就是不可或缺的要素,那么,就并非没有这样解释的余地:对于侵害结束之后的追击行为,原本就没有认定成立防卫过当的余地(在该情形下,就可以认为,该决定中的“量的过当”的含义就属于,前面有关“量的过当”的定义的注释中的后一种情形,即“侵害持续过程中实施数个对抗行为的情形下,对抗行为途中超越相当性限度的情形”)。但是,若以此为前提,要推导出该决定的结论,则只要显示在第二暴力阶段侵害并未持续这一事实即可。然而,鉴于最高裁判所平成20年判例还具体提到了其他事实关系,就不得不认为,仍然是以对于量的过当也有适用第36条第2款的可能性为前提。
对于前一类型,有可能因为作为整体的防卫行为满足了相当性要件,而存在成立正当防卫的余地;对于后者,则没有认定成立正当防卫的余地。
参见永井敏雄:《量的過剰防衛》,载龍岡資晃编:《現代裁判法大系(30)刑法·刑事訴訟法》,新日本法規出版1999年版,第134页以下。
参见永井敏雄:《量的過剰防衛》,载龍岡資晃编:《現代裁判法大系(30)刑法·刑事訴訟法》,新日本法規出版1999年版,第146页(不过,永井敏雄在该文第145页指出,能采取整体性评价的仅限于此类案件这种限制性观点也是有可能的)。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松田俊哉:《判解》,载財団法人法曹会编:《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平成21年度),第9页以下。
关于这一点,参见高橋則夫:《犯罪論における分析的評価と全体的評価》,载《刑事法ジャーナル》第9期(2009年),第43页;佐伯仁志:《刑法総論の考え方·楽しみ方》,有斐閣2013年版,第172页。
参见和田真、野口卓志、増尾崇:《正当防衛について(下)》,载《判例タイムズ》第1366期(2012年),第50页。
也许还会有这样的反驳:在自招侵害的场合,第一暴力也不是出于防卫的动机而实施。然而,即便先行实施了自招行为,但仅此尚不能否定在第一暴力阶段存在防卫意思。但是,如果不能认同该假定案件,第一暴力(尽管能认定存在防卫意思)就会成为抢占先机的对抗行为。在该阶段不能认定存在侵害的紧迫性的案件也是如此。
关于这一点,参见松尾昭一:《防衛行為における量的過剰についての覚書》,载《小林充先生·佐藤文哉先生古稀祝賀刑事裁判論集》(上),判例タイムズ社2006年版,第143页以下;遠藤邦彦:《正当防衛判断の実際》,载《刑法雑誌》第50卷第2期(2011年),第200页;等等。另外,对于第一暴力也属于质的过当的情形,安田拓人教授认为,既然第一暴力与第二暴力都属于违法行为,即便是最高裁判所平成20年判例那样的案件,也没有必要对两个行为分别进行判断(参见安田拓人:《過剰防衛の判断と侵害終了後の事情》,载《刑法雑誌》第50卷第2期〔2011年〕,第182页以下)。如果其旨趣在于,显示包括罪数判断在内的结论,就能予以赞同。
长井圆教授也认为,单纯一罪与包括的一罪的区别很重要。参见長井圓:《過剰防衛の一体的評価と分断的評価》,载《立石二六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成文堂2010年版,第234页以下。
山口厚也指出了同样的问题。参见山口厚:《判批》,载《刑事法ジャーナル》第18期(2009年),第82页。
关于这一点,参见高橋則夫:《犯罪論における分析的評価と全体的評価》,载《刑事法ジャーナル》第9期(2009年),第43页;仲道祐樹:《行為概念の再定位——犯罪論における行為特定の理論》,成文堂2013年版,第238页;成瀬幸典:《量的過剰に関する一考察》(2·完),载《法学》第75卷第6期(2012年)第67页;等等。
在该情形下,也许会认为,即便不将第一行为与第二行为勉强评价为“一系列的防卫行为”,只要直接将第二行为评价为防卫过当即可。但是,在对第二行为进行单独评价的场合,由于该行为不过是侵害结束之后的追击行为,如果不与第一行为进行整体性评价,将二者整体评价为“一系列的行为”,就无法赋予该行为以防卫行为的性质,因而也难以适用第36条第2款,自然也不可能是防卫过当。
参见平野龍一:《刑法総論Ⅱ》,有斐閣1975年版,第245页;西田典之:《刑法総論》,弘文堂2010年第2版,第177页以下;佐伯仁志:《刑法総論の考え方·楽しみ方》,有斐閣2013年版,第175页;等等。
参见町野朔:《誤想防衛·過剰防衛》,载《警察研究》第50卷第9期(1979年),第52页;山本輝之:《優越利益の原理からの根拠づけと正当防衛の限界》,载《刑法雑誌》第35卷第2期(1996年),第209页;林美月子:《過剰防衛と違法減少》,载《神奈川法学》第32卷第1期(1998年),第7页以下;等等。
参见大谷實:《刑法講義総論》,成文堂2012年新版第4版,第291页;山口厚:《刑法総論》,有斐閣2007年第2版,第134页;井田良:《講義刑法学·総論》,有斐閣2008年版,第294页;等等。另外,山中敬一通过将违法减少与责任减少联动,而重视双重的责任减少(参见山中敬一:《刑法総論》,成文堂2008年第2版,第498页)。
松原芳博教授在明确指出两者之区别的基础上,认为总是要求既减少了违法性又减少了责任并不妥当,从而采取后一观点(命名为“择一的并用说”)。参见松原芳博:《刑法総論》,日本評論社2013年版,第165页。
也有学者基于违法·责任减少说,通过严格要求违法性减少,而否定量的过当。参见橋田久:《外延的過剰防衛》,载《産大法学》第32卷2=3号(1998年),第227页以下;松宫孝明:《刑法総論講義》,成文堂2009年第4版,第145页;等等。
参见橋爪隆:《防衛行為の一体性について》,载《三井誠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有斐閣2012年版,第97页以下。此前,内藤谦就已经立足于违法·责任减少说,强调违法性减少是成立防卫过当的前提(参见内藤謙:《刑法講義総論》(中),有斐阁1986年版,第351页)。
?
⑧参见佐伯仁志:《刑法総論の考え方·楽しみ方》,有斐閣2013年版,第175页。
参见山口厚:《正当防衛と過剰防衛》,载《刑事法ジャーナル》第15期(2009年),第56页;等等。
参见西田典之:《刑法総論》,弘文堂2010年第2版,第180页;等等。
也有学者已经指出,防卫行为的整体性评价与防卫过当的法律根据论没有关系。参见深町晋也:《『一連の行為』論について》,载《立教法務研究》第3期(2010年),第128页以下;成瀬幸典:《量的過剰に関する一考察》(2·完),载《法学》第75卷第6期(2012年),第54页以下。
作为明确采取这种判断标准的观点,参见安田拓人:《事後的過剰防衛について》,载《立石二六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成文堂2010年版,第258页以下。
关于这一点,参见西田典之:《刑法総論》,弘文堂2010年第2版,第180页。另外,远藤邦彦认为,量的过当的类型,“是将理论上被认定为假想防卫的一种情形,比照事态的连续性,仍作为防卫过当来处理”(参见遠藤邦彦:《正当防衛判断の実際》,载《刑法雑誌》第50卷第2期〔2011年〕,第180页)。
参见佐藤拓磨:《量的過剰について》,载《法学研究》第84卷第9期(2011年),第176、202页。
关于这一点,参见西田典之:《刑法総論》,弘文堂2010年第2版,第180页;高橋直哉:《複数の反撃行為と過剰防衛の成否》,载《駿河台法学》第26卷第2期(2013年),第48页。平成20年最高裁判所判例认定的是,行为人虽“充分认识到”侵害已经结束,却仍然实施了追击行为。为此,对于该判例,仍有这样理解的余地:在认识到侵害已经结束的场合,也并非一律排除成立量的过当。
参见橋爪隆:《防衛行為の一体性について》,载《三井誠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有斐阁2012年版,第101页;佐伯仁志:《刑法総論の考え方·楽しみ方》,有斐閣2013年版,第169页注(23)。成瀬幸典也以“防卫性心理正在持续的状态”作为问题(参见成瀬幸典:《判批》,载《論ジュリ》第1号〔2012年〕,第221页)。
详见橋爪隆:《正当防衛の基礎》,有斐閣2007年版,第242页以下。
有力观点立足于有关防卫过当的责任减少说,虽对正当防卫采取防卫意思不要说,但对于防卫过当,作为责任减少之根据,仍要求存在防卫意思(参见平野龍一:《刑法総論Ⅱ》,有斐閣1975年版,第242页;西田典之:《刑法総論》,弘文堂2010年第2版,第177页;等等)。按照这种观点,由于对于防卫过当要求存在防卫意思,就完全有可能采取与判例一样的问题解决方式。不过,第36条第2款要求,“为了防卫”的行为“超过了防卫限度”,既然如此,作为对“为了防卫”这一用语的解释,能否像该有力观点那样理解,是存在疑问的。毋宁说,对于不能认定存在防卫意思的积极的加害行为,虽然承认有适用第36条第2款的可能,但在实际判断中,不予刑罚减免,这样理解要更为合适。
关于这一点,参见深町晋也:《『一連の行為』論について》,载《立教法務研究》第3期(2010年),第125页。
提出同样要求的,参见曽根威彦:《侵害の継続性と量的過剰》,载《研修》第654号(2002年),第10页以下;佐伯仁志:《刑法総論の考え方·楽しみ方》,有斐閣2013年版,第169页以下;等等。
参见松田俊哉:《判解》,载財団法人法曹会编:《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平成21年度),第14页。
参见松田俊哉:《判解》,载財団法人法曹会编:《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平成21年度),第9页以下。
参见山口厚:《正当防衛と過剰防衛》,载《刑事法ジャーナル》第15期(2009年),第57页;西岡正樹教授也是同样旨趣(参见西岡正樹:《判批》,载《法学雑誌》第74卷第2号〔2010年〕,第149页)。
佐伯仁志教授批判这种处理方式“过于讨巧”(参见佐伯仁志:《刑法総論の考え方·楽しみ方》,有斐閣2013年版,第175页)。但笔者以为,对于侵害结束之后的追击行为,要认定存在作为防卫过当而减免刑罚的余地,与侵害持续过程中的防卫行为进行整体性评价,就不可或缺,因此,根据是否有利于被告人,分别采取整体性评价或者分离式评价,也具有一定合理性。
例如,松田俊哉:《判解》,载財団法人法曹会编:《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平成21年度),第10页。另外,深町晋也与成瀬幸典也基本上是持同样批判旨趣(参见深町晋也:《『一連の行為』論について》,载《立教法務研究》第3期〔2010年〕,第128页以下;成瀬幸典:《量的過剰に関する一考察》(2·完),载《法学》第75卷第6期〔2012年〕,第64页)。
参见山口厚:《判批》,载《刑事法ジャーナル》第18期(2009年),第83页;林幹人:《量的過剰について》,载林幹人:《判例刑法》,東京大学出版会2011年版,第77页;佐伯仁志:《刑法総論の考え方·楽しみ方》,有斐閣2013年版,第173页;等等。
当然,在这种暴力行为持续实施的场合,在第二暴力阶段丧失了防卫意思,这种情况几乎很难想象。如果有可能存在这种情况的话,就可能是下面这样的情形:尽管在第二暴力阶段侵害仍在持续,但被告人确定地认识到被害人已经处于下风、侵害已无法再持续,却仍然不管不顾地继续实施暴力。
参见西田典之:《刑法総論》,弘文堂2010年第2版,第181页。
参见佐藤拓磨:《量的過剰について》,载《法学研究》第84卷第9期(2011年),第203页。
关于这种理解,参见橋爪隆:《判批》,载《ジュリスト》第1154号(1999年),第134页以下。
支持该结论的观点,参见山口厚:《判批》,载《刑事法ジャーナル》第18期(2009年),第84页;林幹人:《量的過剰について》,载林幹人:《判例刑法》,東京大学出版会2011年版,第77页;佐伯仁志:《刑法総論の考え方·楽しみ方》,有斐閣2013年版,第174页;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