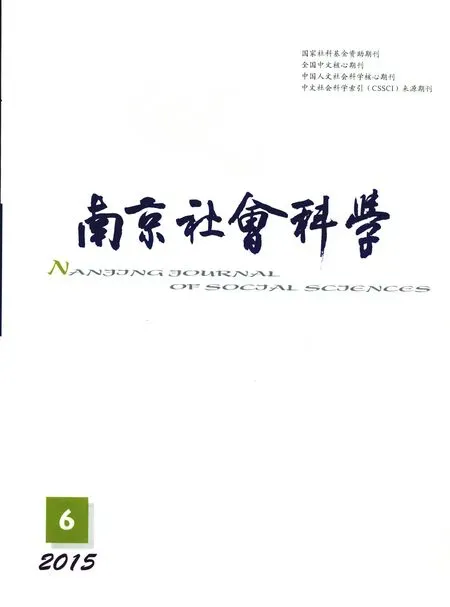从存在论视域看哈贝马斯与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
2015-04-01夏巍
夏巍
从存在论视域看哈贝马斯与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
夏巍
资本作为感性的社会权力,是一种强制性的社会关系,它昭示了现代社会普遍异化的文明危机。对资本的批判使哈贝马斯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发生了最切近的关联。马克思赋予劳动以存在论内涵,认为劳动确立起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是人们之间的感性交往,因而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资本是二而为一的关系,社会关系的异化由劳动的异化所造成,扬弃异化需通过劳动。哈贝马斯依循社会关系由理性建构的传统,遮蔽了生产关系的感性起源。基于对劳动、生产关系的知性解读,生活世界剔除了经济系统。因此他认为脱离劳动的交往关系的扭曲是异化的表现,从生活世界与系统二元架构分析资本起源并寻求摆脱异化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把握了资本的实质,构成了对资本的本质意义的批判。
哈贝马斯;资本;批判;生产关系;劳动
现代文明在本质上是资本为其奠定基础并确定的发展方向,因此资本是一把解开现代社会秘密的钥匙。自资本诞生以来,它给人类带来的不只是物质财富的空前繁荣和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也将人类禁锢于现代性统治的困境之中。不仅如此,只要这种统治存续下去,资本原则就必然作为支配一切的普遍力量而主导着现代世界。因而,如何开展对资本的批判以摆脱文明的危机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这其中,曾一度陷入理论与现实困境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资本批判理论在学界再度复兴,国内外学者普遍首肯,就今天的资本研究而言,马克思是不可回避的思想家。
事实上,作为一种从对资本主义社会鞭辟入里的分析与批判中形成的全新的思想视域——存在论新视域,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明成果。它为今天人类所遭遇的文明危机的本质来历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深刻的阐释。然而,极为遗憾的是,这一学说长久以来被遮蔽在对它的近代知性解读当中。这种解读从经济决定论与自然主义的立场阐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流于历史实证主义与历史客观主义的倾向。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领袖人物,哈贝马斯同样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读和歪曲,但他并未延续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在理论视角的创新中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做法,而是选择了重建它。他的理论旨趣在于深入挖掘历史唯物主义最本真的意蕴,使它在现时代依旧洋溢着旺盛的生命力。虽然哈贝马斯最终也未能彻底走出近代知性解读的阴影,但对资本的批判却使哈贝马斯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发生了最切近同时也是最本质的联系。本文将致力于从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视域分析与比较两者的这一批判,以期更深入地把握资本的本质和现时代人类困境的根源,并辨明究竟哪一种理论构成了对资本的本质意义的批判,找到了摆脱文明危机的有效路径。
一
现代世界中的资本,就其本质而言,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感性的社会关系。它作为社会的类力量,同时意味的是一种社会权力,因为资本本身是一种强制性的社会关系。它昭示了现代社会普遍异化的文明危机。
哈贝马斯指出,人们交往关系的扭曲是这一异化状况的最突出的表现。但这并不是由马克思所断定的劳动的异化所导致的,而是生活世界被系统殖民化的结果。生活世界与系统的二元区分架构,是哈贝马斯为分析与诊治时代状况而提出的一种社会发展模式。借助这一模式,他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陷入异化境地的过程。在他看来,生活世界的结构因素随着传统生活方式的解体而呈现出高度的分化,主要表现为科学、道德、艺术等领域的分化,这即是生活世界的理性化进程。伴随这一进程的展开,生活世界中逐渐释放出目的合理性行为,由此,系统的复杂性开始逐步地增强,系统自身的融合机制形成了相对的自主性,不再受到生活世界的规范的约束,最终从生活世界中分离了出来。这样,现代社会就出现了以语言为媒介并依赖于生活世界相互理解的资源的和通过系统的操控媒介——金钱与权力建立的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融合机制。作为两个不同的社会领域,生活世界与系统因为融合机制的不同而保持着正常的互动关系,生活世界为系统提供符号再生产的成就,系统的物质再生产同时制约着生活世界。但是,当出现金钱和权力取代语言充当了生活世界的整合媒介,两种融合机制发生混淆的状况时,生活世界便沦为了系统控制的对象。生活世界的再生产原本通过交往行为来完成,但是在系统的强制下就无法持续进行下去,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呈现出异化的状况,现代性的各种病态现象也都由此引发。这被哈贝马斯称之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哈贝马斯提出社会发展的二元模式,是由于他并不认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从劳动系统的一元角度解读社会异化状况的做法。当然他也并不否认,生活世界与系统的区分的确也曾出现在马克思的思想当中,在《现代性哲学话语》一书中,他就曾作过如下评论:“马克思第一个用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辩证法形式分析了系统命令与生活世界命令之间的这种冲突,并根据社会史材料描述了现代生产方式进入传统生活世界的过程。”①尽管如此,他认为马克思并未论证这种区分是正当的,所以马克思的角度仍然是一元的,他从根本上缺失了一种区分经济与文化维度的标准,并且忽视了经济之外更多其他因素的影响,这导致了他的理论存在着学理上的缺陷。具体分析,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二,马克思缺乏一个区分传统生活方式的衰落与后传统生活世界物化的标准。随着具体劳动向抽象劳动的转变,马克思的异化概念由于丧失了历史情境而缺乏确定性。青年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是一种具有规范性的社会实践,劳动的对象化或自我表现模式是批判异化劳动的基础,但是当劳动变得抽象化,异化就不再能指涉那种从实践典范之中的分化。而且马克思只是关注劳动和工资间的交换,发现的仅仅是社会劳动领域的物化症状,看到的只能是历史上特定的异化类型。在后传统的生活方式中,社会、个性和文化的分离所带来的痛苦同样也会使得那些在现代社会中成长起来而且获得了其同一性的人们完成其个体化的过程而并不是异化。②
其三,马克思对系统控制下的生活世界的特殊状况进行了抽象的概括。即使将社会冲突的动力归结为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根本矛盾,物化的过程也未必一定会出现在它们被引发的领域。马克思泛化了劳动领域的物化问题,因而对于其它的物化就并不敏感。
哈贝马斯进一步分析指出,造成马克思这一理论困境的根本原因是他的思想与黑格尔的一元论哲学有着潜在的联系。尽管马克思以感性劳动的主客体取代了黑格尔的理性的主客体,但仍旧是一种主体哲学:“他们都把主体哲学作为前提,因而低估了通过系统实现一体化的行为领域的特殊意义。由于这些行为领域从主体间性结构中彻底分离了出来,所以,他们再也无法为在生活世界内部发生分化并完成了社会一体化的行为领域找到任何结构相似物。”③
马克思并未准确诊断出文明危机的根源,那么他所提供的藉由劳动达到生产力的解放以致最终实现人类彻底解放的方案是否能实现呢?哈贝马斯的答案也是否定的。他认为,解放的旨趣指向人们的自由、独立和主体性,它的根本目标是将主体从依附于对象化的力量当中解放出来,劳动蕴含的却是人们通过技术占有或支配外部世界的与之完全不同的旨趣,更何况劳动已经异化,它更无法担负起实现解放的重任。另外,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创造了可观的物质财富,人类解放的旨趣也不再通过经济表达表现出来。
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如何陷入异化境地的探讨和对马克思的理论困境的两方面的分析,哈贝马斯主张,只有在生活世界与系统的二元区分架构中方可揭示出资本文明危机的根源。
沿着这一思路,哈贝马斯认为找到了走出文明危机的路径。他发现解决当下问题的关键不是依赖经济系统或是政治系统进行社会的整合,因为社会同一性的形成实质上根本无法由系统代替生活世界来完成。系统发挥整合的作用只是保存生活世界进行社会整合的成果,它根本无法应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问题。哈贝马斯的观点是:“关键是要在生活世界和系统之间形成一个防护体系和传感设备。”④这个防护体系和传感设备即是哈贝马斯所说的“自主的公共领域”,它是由无数交往行为交织成的处于离散状态的领域,具有更高层次的主体间性并能够形成对整个社会的反思知识。
在历史上,中华民族就有非同寻常的成就。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技史有深入的研究。英国学者坦普尔根据李约瑟的研究,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我们生活的‘现代世界’是中国和西方种种成分的独特综合而成的。‘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基本创造发明和发现可能有多一半来自中国。”①这个判断肯定了中国文化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创造作用,符合历史事实。
在自主的公共领域中,交往行为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互动关系中,虽然生活世界遭遇了殖民化,却依然保有对系统进行反扑的潜力,存在这种潜力的根本原因在于理性本身的丰富性,它仍有尚未衰竭的内涵,这个内涵就是交往理性,它蕴含在交往行为之中。因而交往行为就成为推进社会合理化进程的新的实践力量。它主要借助于文化的资源,使人们达成相互理解并形成反思性的规范意识,抵挡来自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冲击,从而保持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平衡状态,就如哈贝马斯所言,其“目的不再是‘消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官僚统治体制,而是以民主的方式阻挡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式干预。这样,我们就告别了实践哲学中异化和有客观本质力量的观念。合理化过程转向激进民主,其目标是,在社会整合的种种力量之间达成新的均衡,以求在面对金钱和行政权力这两种‘暴力'时,使团结这一社会整合力量——‘交往的生产力’——得以贯彻,从而使以使用价值为转移的生活世界的要求得以满足。”⑤
二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同样落入了近代知性解读的窠臼,这是由于他首先误读了劳动。他眼中的马克思的“劳动”只是人类制造和运用工具从事改造自然的活动,其意义只是生产出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这种理解仍然停留在知性科学的层面上,未曾领会到马克思的原意,因此哈贝马斯也就无法理解马克思是如何揭示出资本这一感性的社会权力关系是从劳动的异化中产生出来并且同样需要由劳动来加以扬弃。
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视域下,劳动突破了工具理性活动的知性规定而获得了感性活动这一存在论本质的澄明:感性与生产一同构成了劳动的基本内涵。马克思认为,生产中充盈着感性意识,它是领会自然界的社会性质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展开中直接构建起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交往意识。感性活动的根本动力,来自于要求实现内涵在它自身中的感性意识的对象化,因而感性决定了生产。但另一方面,感性又必须经过生产劳动才能展开自身,所以感性直接是生产的结果,这是马克思赋予劳动的存在论内涵。哈贝马斯脱离了感性谈论生产,就无法领会劳动的感性的现实性的一面,只能在知性科学意义上认识劳动。
正是建立在对劳动的存在论的理解的基础上,马克思得出了是人类的劳动生产出社会关系,劳动的异化导致了社会关系的异化,劳动的异化又是由分工所导致的论断。
历史的前提是从事感性活动的个人是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点,他说:“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⑥这些现实的个人的生活过程就是生产,生产包括了物质条件和分工(活动),感性包括了交往意识和交往形式。物质条件是交往意识领会到的他人与他物之间的感性联系,它并不是实体意义上的脱离交往意识的物质条件,而是人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它所呈现的是社会力量而非纯粹的物质力量,生产力是其经验化的形式。只有在物质条件中呈现出来的才是交往意识,如果撇开物质条件谈论交往意识,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就成为只是在思维中把握到的人格关系。因此,物质条件与交往意识的相互规定才规定出生产活动。生产从一开始就包含了分工,所以活动同时是分工。交往意识决定了分工的方式,因而分工是个人感性活动的交往方式。感性活动之劳动之所以发生,其前提是原始共同体及其意识的形成,因为共同体自身的再生产需要通过劳动来完成。如果人们要扩大共同体的规模,就必须进行积累,从而将获得的新文明成果存留下来。旧有的社会关系形式继续存在下去会导致新文明成果的丧失,因此在旧有的社会关系形式中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便要求新的分工,分工就承担起了积累的使命,它的实质即是积累的劳动与活劳动的关系。当积累的劳动开始支配活劳动时,就诞生了社会权力。换言之,分工固定下来是交往形式,这种交往形式的实质是范畴规定前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性交往的生产关系。当对象性本质力量从个人的生存活动中异化出去时,在分工所规定的感性活动的特定的交往形式中就凝聚成一种人们彼此冲突与对抗的类力量,作为支配着每一个感性个人存在的外部力量,这种类力量即是社会权力。
正是分工造成了劳动的异化,分工决定了交往形式就表明了人与人之间统治与被统治的权力关系源自物质生活关系领域,这是一个感性的领域,惟有感性才能真正理解它。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⑦这里的“社会生活条件”指的即是物质生活关系领域里所发生的“个人的活劳动”与“被积累起来的社会劳动”之间的关系。在资本的世界当中,积累起来的劳动以一般交换价值的形式实现了其对现实的活劳动的统治,换言之,抽象劳动获得了对具体劳动的统治之时,一种新型的社会权力关系就诞生了,它就是资本。在这个世界中,如果个人的感性活动不能对抽象劳动的积累作出应有的贡献,就绝不可能被承认为劳动,或者进一步说,对他人存在具有一定的意义。⑧海德格尔将这种时代状况归结为“进步强制”,他说:“是什么通过规定了整个大地的现实而统治着当今呢?[是]进步强制(progressionszwang),这一进步强制引起了一种生产强制。……在这一天命中,人已经从对象性的时代进入了可定造性(bestellbarkeit)的时代。”⑨
三
西方自苏格拉底开始就有这样的观念:理性思维建构社会关系。苏格拉底的名言“美德即知识”表达的是根据理性区分善恶、将间接的理性推理之后的结论作为道德的基础的意图。康德认为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是抽象人格间的关系。这样,他事实上将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抽象劳动主体化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理解为一种纯思的观念的社会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所开启的存在论新视域首次打破了这一传统。马克思论述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在感性活动之劳动中确立起来的,理性仅仅是对这种关系加以确认并且通过制度框架将其表达出来而已。这样,社会关系即是生产关系本身。生产关系是人的理性前的社会存在,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性交往,是个人原始地身处于其中的“社会生活条件”,它就是马克思的“生活世界”。资本主义生产中生产出的生产关系,并不是通常认为的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关系,而是全部社会关系意义上的生产关系,质言之,生产关系与资本是二而一的关系,这绝不是经济决定论意义上的观点,而是感性的社会关系与社会权力的存在论论断。
哈贝马斯依循了社会关系由理性建构的传统。他将生产关系定位为一种没有交往意识的交往形式,并且是脱离生产过程的制度和社会机制(institution and social mechanism):“生产关系则指这样一些制度和社会机制,它们决定着(在某种给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劳动力量与可利用的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方式。”他认为生产关系并不是生产过程的要素,而是生产过程的先在条件。它规定了生产手段的使用权和支配权,并且决定了社会整合的形式。原始社会由亲族系统执行生产关系的功能,文明社会则由统治系统来承担,当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同它的操纵功能一起被假设为能够使阶级关系稳定化时,生产关系才采取了纯粹的经济形式,所以生产关系并不像马克思所界定的那样,只能是一种经济形式。哈贝马斯还指出,生产关系的感性源头并不是劳动,因为生产还有一个前提即“前经济事实”,而这些前经济事实“以符号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联系基础上的。”因此,尽管哈贝马斯同马克思一样,认为作为生产关系之制度框架的确立不是理论建构的结果,它确实需要汲取感性的力量方可建立起来,他说:“制度框架长期的结构变化不是有计划的目的理性的和后果受到监督的行动的结果,而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但是,与马克思不同的是,他认为这个感性力量的源泉是交往而非劳动。
这样,哈贝马斯是在脱离生产的交往为前提的构想中得出了生产关系即是建立在这种交往基础上的制度框架的论断。这种观点遮蔽了生产关系的感性起源。哈贝马斯和马克思曾批评的经济学们一样,最终也落入了依据理性建构社会关系的窠臼。马克思曾这样说道:“经济学家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条件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但是既然我们忽略了生产关系(范畴只是它在理论上的表现)的历史运动,既然我们只想把这些范畴看作是观念、不依赖现实关系而自生的思想,那么我们只能到纯理性的运动中找寻这些思想的来历了。”基于对生产关系的这一理解,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剔除了经济系统,突显了语言或符号互动构成的沟通关系,成为交往理性大展身手的场域。同时它也是维持文化的再生产、社会的稳定和个人同一性的能力机制。哈贝马斯诊断出生活世界中脱离劳动的交往关系的扭曲是现代社会普遍异化状况的突出表现,要求扬弃异化当从交往行为入手。但是,这种脱离了劳动的交往行为能够建构出的社会关系也只能是一种纯思的社会关系。
由于系统的媒介——金钱与权力侵入生活世界取代语言成为生活世界的融合机制,从而造成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是哈贝马斯的基本观点。但是,金钱和权力究竟是什么?我们是否无须再对它们作进一步地考量呢?是否阻挡住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式干预就可以“告别了实践哲学中异化和有客观本质力量的观念。……从而使以使用价值为转移的生活世界的要求得以满足。”
要回答以上这些问题,必须深入把握金钱与权力的本质,而非其表象。这两个系统的媒介,实际上是社会权力的制度化,其本质分别是法的权力和政治权力。哈贝马斯并未追问这两种权力机制的来历,换言之,这两种交往形式是如何扭曲变形为权力机制的。取而代之的方式是,直接用政治理性将它们设定为理所当然的既定前提。这样,他就首先确认了交往形式,而事实上交往形式自身还要由分工来决定。法所规定的权利倒是对已经形成起来的资本的生产关系的确认和表达,一切法的权力与政治权力归根结底都源于人的感性存在的历史方式,哈贝马斯并不认为金钱和权力只是对资本这一社会权力关系的事后的确认和表达,而是倒果为因,认定金钱和权力对生活世界的干预导致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哈贝马斯以生活世界与系统二元区分架构诊断社会异化状况,并且指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因为诸多局限性不足以探明社会异化的根源,也无法指出一条真正摆脱异化状况的有效路径。而事实上,只有揭示出资本这一异化的社会关系的真实起源,才能真正消除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由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牢牢抓住了资本的实质,因而构成了对资本的本质意义的批判。哈贝马斯在对资本深入批判的同时,事实上只是在承认资本原则的前提下试图改良社会秩序。在资本批判的原则之下,马克思的理论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注:
①③④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93、395、400页。
②Habermas.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ⅠⅠ,Beacon Press,1987,pp.341-342.
⑤⑭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第21—22、21—22页。
⑥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37页。
⑧王德峰:《论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的原则高度》,《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⑨F.费迪耶等:《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丁耘摘译,《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
〔责任编辑:金 宁〕
Habermas and M arx's Critique of the Capital from a Perspective of Ontology
Xia Wei
As a sensuous social power,capital is a kind ofmandatory social relations.Ⅰt shows modern society is caught in the civilization crisis of alienation.Criticism of capitalmakes Habermas have the closest connection with Marx's historicalmaterialism.Marx endows labor with ontological meaning and thinks labor establishes social relations.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s the sensuous communication of people,therefore social relation is relations of production.Capitalism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s same as capital.The alien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caused by the alienation of labor,we should sublate alienation through labor.Following the rational 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social relations,Habermas has covered the sensuous origin of production relations.Based on the intellectu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bor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the life world is cut out of the economic system. Therefore he thinks the distortion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relationship apart from labor is usually the sign of alienation and we should analyze capital origin and look forways to get rid of alienation based on the dual structure of the life world and system.Historicalmaterialism grasps the essence of the capital,therefore constitutes the essential critique of capital.
Habermas and Marx;capital;critique;relations of production;labor
B03
A
1001-8263(2015)06-0045-06
夏巍,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剑桥大学访问学者 济南250100
* 本文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研究”(11JZD00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生产范式与交往范式——哈贝马斯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论研究”(10YJC72004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