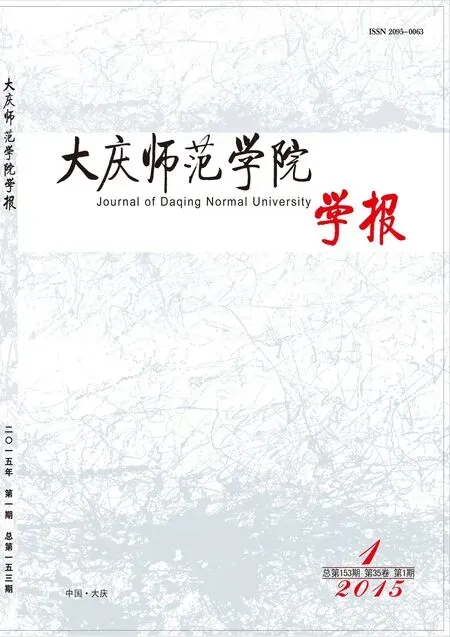刘勰“神思”说新探——从比较文化的角度
2015-03-30胡健
作者简介:胡健(1954-),男,江苏沭阳人,教授,主要从事美学研究。
DOI 10.13356/j.cnki.jdnu.2095-0063.2015.01.018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美学史上“文的自觉”时期,也是“美的自觉”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摆脱了政治功用的束缚,开始了“为艺术而艺术”,这时的文论对艺术美的规律多有探讨,而南朝刘勰“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则更是对这一时期艺术美探讨“集大成”著作。《神思》是刘勰《文心雕龙》中的重要篇章,它既是创作论的首篇,也是创作总论,所以向来为研究者所重,本文试图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对刘勰《神思》篇中的艺术想象问题作一些新的探讨。
一、“思理为妙,神与物游”
何为艺术想象?刘勰在《神思》篇的开首就为它下了定义:“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语出于《庄子·让王》篇,刘勰借此来定义艺术想象。在刘勰看来,艺术想象是艺术家的一种奇特的能力,它可以让思想情感超越具体的时空限制,而去把握生活中更为重要更为本质的精神性的东西。刘勰把艺术想象称为“神思”,还因为艺术想象作为一种“思”,它具有着“变化莫测”的“神”的特点。《易传·系辞》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刘勰用“神”来强调艺术想象的特点,突出了艺术想象那种变化多端的特点。在刘勰看来,艺术想象对艺术创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称它为“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在西方,美学家们对艺术想象也有类似的说法,黑格尔在《美学》中就主张:“如果说到本领,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 [1]348还说:“真正的创造就是艺术想象的活动。” [1]50这与刘勰是不谋而合的,道出了艺术想象在艺术创作中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上面刘勰对艺术想象的定义看,他是从在场(“江海之上”)与不在场(“魏阙之下”)关系的角度去对艺术想象加以解说的。在他看来,艺术想象可以具有突破时空的局限,使艺术家由在场进入不在场,由有限进入无限,从而把在场与不在场、有限与无限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创造出新的“象中有意,意中有象”的艺术意象。所以,刘勰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在他看来,艺术想象也就是艺术家所具有的超越在场、超越时空、超越思维、创造出新的审美意象的特殊能力。
那么,在刘勰看来,艺术想象的运行机制又是如何呢?《神思》中说:“思理为妙,神与物游。”艺术想象的最高明之处就在于它能“神与物游”。由此可见,艺术想象并不等于完全任意的胡思乱想,艺术家头脑中那些变动着的形象与情思是随着对生活(物)的不断理解而逐渐地自由地展开的。形象与情思随着“物”的自由展开的过程,是微妙的存在被逐渐渐显现出来的过程,是艺术家所创造的审美意象逐渐明晰丰满的过程。这样的艺术想象,才称得上是“神与物游”。
对于“神与物游”,《神思》篇中还曾有更具体的解说:“神用象通,情变所孕。”在艺术想象中,形象与情思之所以能随“物”一起展开,是因为艺术想象具有“神用象通”与“情变所孕”的特征与功能。先看“神用象通”,这里的“神”指的是生活中的那些难以言传的情理,生活中的情理本来十分微妙,用一般性的概念是无法传达出来的,所以只能借助一些具体生动的形象来暗示与表达,这也就是《易传》中说的“以象出意”,以“象”来“类万物之情”,“类”就是“通”。再看“情变所孕”,在刘勰看来,推动着艺术想象活动的动力,就是艺术家在生活中所孕育而生的内在充沛的情感;艺术想象活动不是冰冷冷的理智活动,而是充满了情感的创造性活动。所以《神思》篇中说:“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艺术想象不但是为艺术家的情感所孕育所推动,而且它还要显现出一种不同于一般“思想逻辑”的“情感逻辑”(合情合理)。过去理论界有种“形象思维”的说法,其实艺术想象在本质上不是思维,而是超逻辑与超思维的。以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为例:“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首诗表达的是远在异地的一种对亲人之思。这首诗之所以好,就在于它没有用概念性的语言来对这种情感加以直白地表白,而是十分重视画面的巧妙安排,“以象出意”,重视情感“逻辑”的生动显现,所以它才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从而使“在场”与“不在场”构成意象,联成无限,因而它给人的不是概念的知识而是存在的真理。从而完全达到了刘勰所说的“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的境界。
关于艺术想象问题,西方古典美学家也有些精到的见解,可以与刘勰的见解相互对话。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也曾对想象力定义:“想象是在直观中表象出一个本身并不出场的对象的能力。”“想象力(作为生产的认识机能)是强有力地从真的自然提供验它的素材里创造一个相似另一自然来。” [2]160康德把想象当作主体的综合能力,是介于概念与直观之间的中介。他的这个定义与刘勰的定义是十分相像的。黑格尔在《美学》中对艺术想象也作过探讨,他同样强调艺术想象“神用象通”的特点:“在艺术与诗里,从‘理想’开始总是靠不住的,因为艺术家创造所依靠的是生活的富裕,而不是抽象普泛的观念的富裕。在艺术里不像在哲学家里,创造的材料不是思想而是现实的外在形象。” [1]348同样,他对“情变所孕”也有强调:“有了这种对外部世界形状的精确知识,还要加上熟悉人的内心生活,各种心理状态中的情欲以及人心中的各种意图;在这双重知识之外,还要加上一种知识,那就是熟悉心灵内在生活通过什么方式才可以表现于实在界,才可以通过实在界的外在形状而显现出来。” [1]348在黑格尔看来,艺术想象的最高境界同样是“神与物游”:“艺术家所选择的某对象的这种理性必须不仅是艺术家自己所意识到的受到感动的,他对其中本质的真实的东西还必须按照其整个的广度与整个的深度加以彻底体会……轻浮的想象决不能产生有价值的作品。” [1]349由此可见,黑格尔对艺术想象的见解与刘勰对艺术想象的见解,完全是可以相互对话的。
尽管如此,中、西方美学家对艺术想象的理解还是存有差异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艺术型的文化,对想象的重视是很自然的,而且,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前科学的文化,没有出现用思维压想象的现象。西方文化则是一种科学型文化,西方的美学家虽然也很重视艺术想象,并对艺术想象有很好的理解,但由于受其文化传统的影响,长期存在着“想象是低于思维”的哲学偏见。古希腊的柏拉图就重理智而轻想象,认为前者所对应的是理念,而后者对应的是“影子”,前者是理性认识,后者是感性认识。康德与黑格尔虽然对想象力有一定的重视,但他们最终还是把思维看作是高于想象的,这也是黑格尔贬艺术而抬哲学的原因。到了现代,西方美学家的看法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尼采、海德格尔都认为科学只是知识,艺术才揭示存在,因而认为想象比思维更为重要,艺术比科学更为重要。因为“思维以把握事物本质相同性(同一性与普遍性)为己任;想象以把握不同事物间即在场的呈现的事物与不在场的隐蔽的事物之间的相通性为目标,对后者的追求不排斥对前者的追求,只是后者超越了前者” [3]109。这也就是说想象是从思维的终点处开始的,它具有超概念超思维的特点。西方美学家对艺术想象理解的变化对我们重新理解刘勰的“神思”,重新认识“想象”,会不会有些启迪呢?
二、“陶钧文思,贵在虚静”
艺术想象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精神活动。灵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在艺术创作中,有灵感时,艺术家往往浮想联蹁,“犹有神助”;而无灵感时,则常常一筹莫展,一无所获。陆机在《文赋》中就曾谈及这一问题,“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陆机对此难以作出解答。刘勰在《神思》中则对艺术灵感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这里的“志气”指的是思想情感,它是艺术家想象活动的导引者;这里的“辞令”指的是文字语言,它是艺术家想象活动的枢机。在刘勰看来,灵感现象就是艺术家进行艺术想象时,思想情感处于充沛自由与文字语言处于得心应手的一种极佳状态。难能可贵的是,刘勰还指出,艺术想象活动中的灵感状态与艺术家的“虚静”心态有关。所以他说:“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沦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这里“积学”“酌理”“研阅”“驯致”或属于前期准备或次要状态,而灵感的关键则在于艺术家心态的“虚静”。老子讲过:“惟道集虚。”因为不可言传的道是“虚无”的,所以只有虚静的心态才能容纳或体会到这种玄之又玄的道,亦即神奇的“意象”。从这个角度讲,灵感也就是艺术家在想象时超出了庸常而达到了“与道合一”的最佳境界。“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相反,如果艺术想象时,艺术家不能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只拘泥于一些“小成”,那他劳心费神也只能与灵感状态没有缘份。
西方的一些美学家也谈过灵感。柏拉图在《伊安篇》中就认为,好诗都有是灵感的产物,获得灵感的诗人可以超出庸常而说出“响彻千年的话”,可见他对灵感现象与灵感的作用是很早就注意到了。但是他对灵感产生的解释却是荒谬的,诗人之所以获得灵感,是因为神夺去了他平常的理智,凭附在诗人身上,诗人在迷狂中获得灵感,成为神的代言人。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美学》中也讨论过灵感。黑格尔指出:“煸起真正的灵感必须先有一种明确的内容,即想象所抓住的并且要用艺术方式所表现的内容。灵感就是这种活跃地进行的构造形象的情况本身(这一方面是就主观的内在的创作活动来说,另一方面也是就客观地完成作品的活动来说,因为这两种活动都必须有灵感。)” [1]355那么,灵感从何而来呢?黑格尔指出,有时灵感的到来好像是十分偶然的,创作的推动力好像是外在的,但他认为对艺术家唯一的重要的要求是:“艺术家应该从外来材料中抓住真正有艺术意义的东西,并且使对象在他心里变成有生命的东西。” [1]355-356所以灵感在他看来,“它不是别的,就是完全沉浸在主题里,不把它表现为完美的艺术形象时决不罢休的情况” [1]356。黑格尔这里的“真正有艺术意义的东西”“明确的内容”不是有些类似于刘勰所说的或“道”或“意象”吗?那么,艺术家要在创作中真正获得灵感,就必须排除对“真正有艺术意义的东西”“明确的内容”的干扰而完全沉浸在其中,这不很像“与道合一”吗?而这种对干扰的排除,与对“道“或“意象”的沉浸”,在刘勰那里也就是“虚静”。艺术家只有“虚静”时,“真正有艺术意义的东西”“明确的内容”才能在他的想象中真正浮现出来,活跃起来,从而达到一种神奇的灵感状态。
三、“杼轴献功,焕然乃珍”
经由艺术想象,艺术家创造出不同于生活表象的艺术意象。艺术意象是一种“象中有意”或“意于象中”的艺术形象。“窥意象而运斤”,“意象”可以说是艺术想象的最终成果,“意象”在心为“心象”,表达于文字则为客观化了的“心象”。对于生活表象与艺术意象的性质与关系,刘勰作了个十分形象而又传神的比喻:“视布于麻,虽云未费;杼轴献功,焕然乃珍。”这里的“麻”指的就是平淡无奇的生活表象,“布”即指美丽的丝绸,这里则是指形象生动的艺术意象。平淡无奇的生活表象之所以能变为形象生动的艺术意象,是因为“杼轴献功”——艺术家运用了艺术想象对“麻”进行了创造或加工,这才使得平淡无奇的“麻”变为了美丽的“布”,也就是刘勰所说的“焕然乃珍”。“杼轴”原本指织布的机器,刘勰借用它来比喻艺术家具有创造性质的艺术想象。为了更好地理解刘勰的思想,以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为例,如果把这首诗的意象还原为生活表象,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天涯”……它们显然是不能感动人的,但是这些生活表象经由诗人的创造性想象,变成艺术意象时,它们就变得充满审美的生命与情味,从而它就能让人感受到了飘泊天涯的断肠人的触景生情,感受到一幅让人回味不尽的羁旅荒郊图。这就是所谓的“杼轴献功,焕然乃珍”。
有趣的是,刘勰把生活的表象比作“麻”、把艺术的意象比作“布”,而古希腊的柏拉图则把前者比作“水”、把后者比作“蜜”。柏拉图在《伊安篇》中说:“……抒情诗人在做诗时也是如此,他们一旦受到音乐与韵节力量的支配,就感到酒神的狂欢,由于这种灵感的影响,她们正如酒神的女使徒们受酒神的凭附,可以从河水中汲取乳蜜,这是他们在神智清醒时所不能做的。” [4]7去掉其神秘的成分,柏拉图所说的“水”与“蜜”的关系,与刘勰说的“麻”与“布”关系可谓十分相像,“麻”能变“布”,“水”能变“蜜”,都是因为艺术家的艺术想象发挥了作用,可见艺术想象具有非常神奇的作用。德国美学家黑格尔的一些说法同样值得注意。黑格尔在《美学》中说:“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艺术美高于自然美,因为艺术美是心灵产生与再生的,心灵和它的产品比自然和它的现象高多少,艺术美也就比自然美高多少。” [1]2“只有心灵才是真实的,只有心灵才涵盖一切,所以一切的美只有涉及这较高境界产生出来时,才真正是美的。就这个意义上说,自然美……是一种不完全、不完善的美。” [1]3或许,崇尚“天人合一”、具有“自然主义传统”的刘勰未必同意黑格尔对自然美的贬低,但是在“视布于麻,虽云未费;杼轴献功,焕然乃珍”的层面上,他们关于自然美与艺术美见解却完全是可以相通与对话的。
艺术家运用“神思”即艺术想象所创造出的精神产品就是艺术意象。关于艺术意象,刘勰在《神思》篇中还说:“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也就是说,艺术意象是非常奇妙的,它具有意在言(象)外的特点。刘勰在《隐秀》篇中对艺术意象还曾作过更为细致的探讨:“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他认为艺术意象是“象”的“秀”与“意”的“隐”的有机统一,是“象”的直接性、鲜明性与“意”的间接性、多义性的统一。所以刘勰强调:“晦塞为深,虽奥非隐;雕削取巧,虽美非秀矣。”他的隐秀论确实是道出了艺术意象的本质特点。刘勰之后,意象成了中国诗学中的最重要概念之一,受到历代诗论家们的普遍重视,而明代王廷相的解说最为透彻:“夫诗贵意象透莹,不喜事实粘著,古谓水中之月,镜中之影,难以实求是也……言征实则寡余味也,情直致则难动物也。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之,邈哉深矣。此诗之大致。” [5]652在王廷相看来,艺术作品之所以能打动人,就在于有审美意象,审美意象就是艺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审美形态。有此则美,无此则必不美!德国哲学家康德对艺术意象也曾发表过十分精到的见解。他在《判断力批判》中指出:“审美意象是由想象力形成的那种表象。它能引起许多思想,然而却不可能有任何明确的思想,即概念与之完全适应。因为语言不能充分表达它,使之完全令人理解。很明显,它是和理性观念相对应的。理性观念是一种概念,没有任何直觉(即想象力形成的表象)能够与之相适应。” [6]563这一见解与刘勰对意象的理解也是相通的,确实道出了艺术意象超越一般概念的本质特点。
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7]或许“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更为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