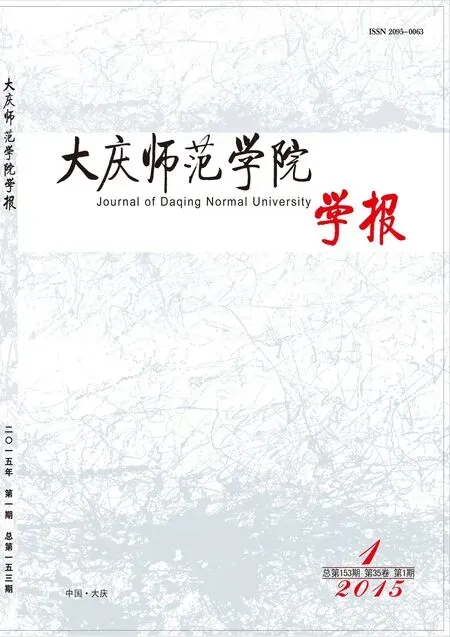宋金对峙在清初的文学重写——以《续金瓶梅》为中心
2015-03-30杨剑兵,郁玉英
作者简介:杨剑兵(1970-),男,安徽桐城人,副教授,文学博士,从事古代小说戏曲、元明清文学研究;郁玉英(1973-),女,江西萍乡人,副教授,文学博士,从事词学、唐宋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八股文与明清小说相互关系研究”(12CZW034) ;三峡大学科学基金项目“遗民意识与清初小说”(KJ2011B057)。
DOI 10.13356/j.cnki.jdnu.2095-0063.2015.01.013
清初章回体小说以宋金对峙为历史背景的主要有《后水浒传》《水浒后传》《续金瓶梅》等,它们均为续书。这些小说作家选择宋金对峙为历史背景来创作续书的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续书对原书在时代背景上的连续性。《水浒传》的历史背景主要是北宋徽宗宣和元年至三年(1119—1121)的宋江起义。据《宋史·徽宗本纪》载:
(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1]407
再据《宋史·侯蒙列传》载:
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 [1]11114
与这次起义相关的是朝廷奸臣当政,如四大奸臣蔡京、童贯、高俅和杨戬,还有宋徽宗的奢华生活,如到全国各地搜集奇花异石的“花石纲”。作为由《水浒传》故事生发出来的《金瓶梅》,其历史背景主要也是在宋徽宗宣和年间,从小说中不断出现的四大奸臣,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一点。不过,上述两部小说在结尾处亦涉及北宋灭亡与南宋建立的历史,但显然只是作为小说的尾声而已。而作为《水浒传》《金瓶梅》的续书,在历史背景上恰好可以将原书尾声的历史当作小说的主要历史背景。《后水浒传》诸多人物是由《水浒传》中的人物转世而来,特别是由宋江转世的杨幺、由卢俊义转世的王摩。笔者疑为作者借续书之名,反映南宋建炎四年至绍兴五年(1130—1135)发生于洞庭湖地区的钟相、杨幺起义,并结合宋金对峙的历史背景来表达自己在乱世中的渴望忠义、痛斥外族入侵的遗民情怀。《水浒后传》亦将《水浒传》的宣和历史背景,移至两宋之间的历史背景,出现了金兵残酷掠杀北宋民众、燕青冒死拜见北狩的宋徽宗等情节,这与作者自称“古宋遗民”是完全相符的。《续金瓶梅》更是较为详细地展现了金兵南下给百姓带来的无尽苦难以及在这一苦难中的众生百态。所以,这些小说作家在续书创作时,选择宋金对峙为背景,既是对原书在时间上的必然要求,又是作家遗民心态的必然选择。
其次,金朝与清朝具有历史渊源关系。金朝与清朝均由女真族建立。女真本是散居于东北松花江流域与黑龙江流域的游牧民族,古为肃慎氏。元魏时,有七部。隋时称为靺鞨,而七部并同。“唐初,有黑水靺鞨与粟末靺鞨,其他五部无闻” [2]1。“五代时,契丹尽取渤海地,而黑水靺鞨附属于契丹。其在南者籍契丹,号熟女直;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号生女直” [2]1-2。在辽朝中期,女真族完颜部崛起,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按:汉名完颜旻)于收国元年(1115)正月称帝,建都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称上京。金太宗(完颜晟)天会三年(1125)宋金联军灭辽。天会五年(1127)金灭北宋,势力进入中原地区。海陵王(完颜亮)天德五年(1153),金迁都至中都(今北京)。在金章宗(完颜璟)后期,金朝开始衰落,北方蒙古族开始崛起,并于金哀宗(完颜守绪)天兴三年(1234)灭金。金朝经10位皇帝共119年走向灭亡。蒙古族建立元朝后,女真原居住地归合兰府水达达等路管辖。明初,女真族分为建州、海西、野人三部。建州女真到努尔哈赤时,逐渐强大,并在其领导下统一了女真各部。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称汗,国号“大金”,建元“天命”,建都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史称“后金”。清太宗皇太极于天聪九年(崇祯八年,1635)改“女真”为“满洲”,并于次年改国号为“清”,改元“崇德”。顺治元年(崇祯十七年,1644)清朝入主北京,康熙元年(永历十六年,1662)灭南明永历政权,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了吴三桂等三藩叛乱,康熙二十二年(1683)郑克塽降清。至此,清朝完成了全国统一。女真族在发展过程中虽与契丹、汉、蒙古等民族有过融合,民族称谓上亦有多次更易,但仍然保持着本民族的特性。所以,金朝与清朝在民族上是同根同源。正是这一内在联系,这些小说作家在小说创作时,选择宋金对峙为历史背景是有所喻指的。
除上述两点主要原因外,南明与南宋有诸多相似点,如它们最初都建都于南京,都与入侵的少数民族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并涌现了众多可歌可泣的抗敌人物与故事等,或许亦是上述小说作家选择宋金对峙的历史背景的原因。比如《水浒后传》中李俊在海外建立的“暹罗国”,众多学人即认为是作者暗喻南明的郑氏政权。
总之,《后水浒传》《水浒后传》《续金瓶梅》选择宋金对峙为历史背景,一方面是续书特点使然,另一方面是作者以金喻清的遗民心态使然。而《续金瓶梅》又是这两方面代表之作,下文以其为例,探讨其与明清之际现实的关联以及作者的遗民心态。
一、金兵的残暴与清兵的屠城
金兵的掠杀在《续金瓶梅》中多有表现,其中重点描写了金兵在山东(包括东昌府的清河县)及扬州的屠杀。如小说第一回描写了金兵掠杀兖东一带,筑成十几座“京观”而去。再如第二回描写金兵血洗清河县所造成的惨象,第十三回描写了金兵于清河县的屠城。小说突出描写金兵在山东的残暴,与作者故里诸城遭清兵屠城有关。丁耀亢在《出劫纪略》里记载了崇祯末年清兵在诸城的屠杀:
是夜,大雨雪,遥望百里,火光不绝。各村焚屠殆遍。……白骨成堆,城堞夷毁,路无行人。至城中,见一二老寡妪出于灰烬中,母兄寥寥.对泣而已。……城北麦熟,欲往获而市人皆空。至于腐烂委积,其存蓄不可问类如此。时县无官,市无人,野无农,村巷无驴马牛羊,城中仕宦屠毁尽矣。 [3]278-279
这次清兵在诸城的屠城,丁耀亢的家人亦惨遭不幸:
丁耀亢弟弟耀心、侄儿大谷守诸城殉难,长兄耀斗、侄儿豸佳受伤致残,二兄耀昴全家战亡,只有丁耀亢携老母、孤侄逃入海岛而幸全。 [4]6
从其《哀九弟见复》《哀大侄如云》《海中寄乡信兼慰长兄》《兵退后再答大兄》等诗作中可感受到作者对家人惨遭不幸的痛心。另外,丁耀亢的诗作亦反映了清兵的屠杀,如《冬夜闻乱入卢山》云:
乱土无安民,逃亡乐奔走。岂无饘粥资,急命轻升斗。自遭囗(按:本字被挖版,疑为“虏”字)劫后,男妇无几口。日暮还空村,柴门对古柳。白骨路纵横,宁辨亲与友。昨闻大兵过,祸乱到鸡狗。茅屋破不补,出门谁与守?但恐乱日长,零落空墟薮! [5]659
小说第五十三回又描写金兵攻陷扬州城后大肆掠杀。这段描写虽蕴含着因果报应的思想,但金兵的残暴还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清兵在扬州的屠城:
数十人如驱牛羊,稍不前,即加捶挞,或即杀之;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籍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行过一沟一池,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 [6]232
小说中的金兵与明清之际的清兵虽然不能划等号,但是小说突出描写了金兵在山东与扬州的屠杀,这无疑在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作者试图将自己的经历与耳闻融入自己的创作中,并试图让读者通过这些地点的提示而联想到明清之际的社会现实。这种隐晦曲折的表达方式,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清军南下时犯下的种种罪恶的痛恨,对大明国土遭到践踏、大明子民遭遇涂炭的哀痛。这是作者创作匠心之所在,更是作者强烈遗民意识的表现。
二、北宋的灭亡与明亡教训的总结
靖康二年(1127),宋徽宗、钦宗二帝北狩,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耻”。《续金瓶梅》在描写北宋灭亡的过程,着重突出了君主荒淫、奸臣当权、边将投降、党争不断等方面,而这些恰恰与明亡原因有其相似的地方。
(一)宋徽宗的荒淫与晚明君主的昏庸
《续金瓶梅》在描写宋徽宗时总体上与史书记载相一致,即均有表现其荒淫的一面。这种荒淫主要表现在:
(1)醉心花石。宋徽宗喜好花石,史书多有记载,小说亦多有表现。第六回描写了宋徽宗遇上好的虎刺,常常赏赐白银三五百两。第十三回又描写了宋徽宗嫌宫廷阁楼“太丽”,“移了口外乔松千树、河南修竹十亩”,营造了一座风流典雅的艮岳山。
(2)不问朝政。小说第十三回描写道:
这道君把国政交与蔡京,边事付与童贯,或是召林灵素石上讲经,或是召蔡攸来松下围棋,选几个清雅内官,捧着苏制的榼盏,一切金玉杯盘、雕漆宫器俱不许用,逢着水边石上,一枝萧笛,清歌吴曲。
真所谓“清客的朝廷,仙人的皇帝”。
与宋徽宗相似的晚明君主主要有万历帝、天启帝与弘光帝。万历帝在位四十八年,而“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 [7]246。《明史》曰:“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8]295孟森亦云:“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 [7]246天启帝嗜好木工,人所皆知,最后权力被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所掌控。《明史》评曰:
明自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有刚明英武之君,已难复振。而重以帝之庸懦,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 [8]306-307
弘光帝作为南明的第一个皇帝,不思恢复国土,而倾心于选淑女、观戏剧,最后落得国破身亡。《南明史》评曰:
上燕居深宫,辄顿足谓士英误我,而太阿旁落,无可如何,遂日饮火酒、亲伶官优人为乐,卒至触蛮之争,清收渔利。时未一朞,柱折维缺。故虽遗爱足以感其遗民,而卒不能保社稷云。 [9]55
总之,小说在描写宋徽宗时在一定程度上观照了晚明君主。换言之,从作者对北宋晚期的乱政描写来看,与其说在为北宋之亡的教训作总结,不如说在为明亡教训作总结。
(二)徽宗时的奸臣当道与晚明时的阉党专权
大凡一个朝代或政权的晚期,常常会出现奸臣当道的现象。这与君主的昏庸荒淫有关,又与奸臣善于钻营逢迎有关。北宋与明朝亦没有逃脱这一历史魔咒。《续金瓶梅》虽对宋徽宗朝政描写不多,但明显突出了“四大奸臣”(蔡京、童贯、高俅、杨戬)中的蔡京与童贯。蔡京主要是在朝廷里掌控权力,过着奢靡的生活,如小说第十七回描写道:
说那徽宗朝第一个宠臣、有权有势的蔡京,他父子宰相,独立朝纲,一味谄佞,哄的道君皇帝看他如掌上明珠一般。不消说,那招权揽贿,天下金帛子女、珠玉玩好,先到蔡府,才进给朝廷,真是有五侯四贵的尊荣、石崇王恺的享用!把那糖来洗釜,蜡来作薪,使人乳蒸肉,牛心作炙,常是一饭费过千金,还说没处下箸。
如果说蔡京在朝廷里败坏朝纲,那么,童贯则在边疆有损北宋安危,如小说第十九回描写道:
却说宋徽宗重和七年,童贯开了边衅,密约金人攻辽,后又背了金人收辽叛将张瑴,金人以此起兵责宋败盟。童贯无力遮挡,只得把张瑴杀了,送首级与金,因此边将一齐反叛。
如此奸臣当道,徽、钦二帝北狩,实在是在所难免。诚如小说描写道:
这上皇父子垂头长叹,才悔那艮岳的奢华、花石的荒乱,以至今日亡国丧身,总用那奸臣之祸。(第十九回)
晚明时的阉党专权与徽宗时的奸臣当道颇有几分相似之处。明天启时,魏忠贤通过与天启帝乳母客氏的勾结,又与崔呈秀、田尔耕、许显纯等人的结党,形成庞大的阉党集团,赶杀东林清流,掌控朝廷内外权力。《明史》谓“明代阉宦之祸酷矣” [8]7833,魏阉盖首当其冲;又谓阉党专权给明朝带来严重影响,曰:“其流毒诚无所穷极也!” [8]7833谷应泰甚至将魏忠贤与蔡京相提并论,曰:
呜呼!自予考之,神、光二庙,朝议纷争,玄黄溷淆,朋徒互揣,至此则钩党同文,得祸斯酷矣。然封谞事发,始知顾、及之贤,蔡京事败,益信元祐之正,身虽荡灭,名义所从判尔。 [10]1172
到弘光时,马士英、阮大铖等阉党余孽掌控着朝廷内政和边疆大权,从而使其仅存续一年即告寿终正寝。孟森谓马(士英)阮(大铖)“亡国大罪人” [7]343,似乎并不为过。
总之,《续金瓶梅》对徽宗时奸臣当道的描写,无疑是对北宋灭亡原因的一种探究,这种探究为我们提供了阉党专权导致明亡的思考。由此可见,作者在探究历史的同时,又渗透着对现实的关注。
(三)郭药师的降金与晚明边将的降清
《续金瓶梅》描写了众多降金者,如张邦昌、刘豫、郭药师、蒋竹山、苗青等。作为边将降金者,小说着重描写了郭药师。郭药师为历史真实人物。据《宋史》《金史》载,郭药师曾为辽将,叛辽归宋后,受“徽宗礼遇甚厚,赐以甲第姬妾” [1]13738,后因与其一起镇守燕山的副将王安中杀张觉事,而“深尤宋人,而无自固之志矣” [2]1834。最后,因童贯处理边事不当,郭药师率兵降金,并引金将斡离不入东京,徽、钦二帝蒙尘,北宋遂亡。这一人物仅在《金瓶梅》第十七回中出现过一次,而在《续金瓶梅》中则多次出现,如第十回、第十六回、第十九回中对降将郭药师的描写,可以看出,其降金行为给北宋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降金后对徽、钦二帝颇为不敬,彰显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同时,又以权谋私。从作品中对郭药师充满痛恨与厌恶之情,又可看出作者总结了北宋灭亡的历史教训。
北宋的灭亡与郭药师的降金有直接关系,而晚明时期的边将降清,又何尝不关乎着明廷的灭亡呢?崇祯时的洪承畴、吴三桂等边将的降清,对明廷边疆形成了致命的打击。洪承畴曾在镇压李自成起义中有过汗马功劳,得到崇祯帝的重用,并委以蓟辽总督之任。但在松山之战(1641—1642)中,洪承畴被俘降清,辜负了崇祯帝的一片苦心。《清史稿》载:
庄烈帝初闻(洪)承畴死,予祭十六坛,建祠都城外,与邱民仰并列。庄烈帝将亲临奠,俄闻承畴降,乃止。 [11]9468
降清后,洪承畴又成为清廷的一位得力干将,“江南、湖广以逮滇、黔,皆所勘定;桂王既入缅甸,不欲穷追,以是罢兵柄” [11]9488。洪承畴对清廷一片赤诚,换来的却是归入《清史列传》中的《贰臣传》。这或许是其始料未及。吴三桂相对于洪承畴,有过之而无不及。吴三桂曾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受封平西伯,但却借驱赶大顺军之名,乞师清廷。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使清廷顺利入主北京。就此观之,吴三桂颇似郭药师。另外,南明时期的高杰、刘泽清、刘良佐、李成栋、郑芝龙等边将的降清,压缩了南明的生存空间与时间,甚至有些降将将屠刀直指自己曾经效忠的王朝的百姓,如李成栋一手制造的“嘉定三屠”等。由此观之,明朝的灭亡不仅与这些降将有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说,大明江山就断送在他们手中。
总之,《续金瓶梅》在降金将领中拈出郭药师与《金瓶梅》有所涉及有关,更为重要的,他是直接导致北宋灭亡的重要人物,从小说中多次提及可窥之。这或许即作者痛感晚明边将的降清给明廷带来的厄运,而在历史人物身上找到了寄托。
(四)两宋之际的党争与晚明的党争
党争在《金瓶梅》中未曾涉及,而《续金瓶梅》第三十四回则进行了集中描写。此回首先描写了宋高宗时的党争。这一党争主要是因战和之论引起的,其中汪国彦、黄潜善等主和,李纲、张浚、岳飞、韩世忠等主战。主和派为打压主战派,一方面“重修神宗、哲宗实录,把那元祐党人碑从新印行天下,把王安石、蔡京、章惇、吕惠卿一班奸臣说是君子,把司马光、苏轼、程颐、刘挚等一班指为党人”;另一方面,又指控“李纲等一起忠臣是沽名钓誉,专权误国”。最后,主和派战胜主战派,李纲遭贬,又“将谪贬的、正法的这些奸臣们,一个个追封的、加谥法的、复职的”。接着,此回还追溯了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及唐宪宗时的牛李党争。此回可谓描绘了一幅自汉至宋的党争图。但是,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党争的简单叙述上,而是重点强调了党争带来的严重后果,如东汉末年的钩党之争“丧了汉朝”,中唐时的牛李党争导致“藩镇分权,唐室衰微”,元祐党争产生“金人之祸”,南渡初年的党争使恢复国土的宏愿付诸东流。
作者在小说中并未涉及晚明党争,但通过对南渡初年的党争描写及东汉末年、中唐时期、北宋中期的党争追溯,可以感受到作者对晚明的党争是深有感触的,尤其是党争给朝廷与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如作者所议论道:
这个党字,贻害国家,牢不可破,自东汉、唐、宋以来,皆受“门户”二字之祸,比叛臣、阉宦、敌国、外患更是厉害不同。即如一株好树,就是斧斤水火,还有遗漏苟免的,或是在深山穷谷,散材无用,可以偷生;如要树里自生出个蠹虫来,那虫藏在树心里,自稍吃到根,又自根吃到稍,把树的津液昼夜吃枯,其根不伐自倒,谓之蠹虫食树,树枯而蠹死,奸臣蠹国,国灭而奸亡。总因着个党字,指曲为直,指直为曲,为大乱阴阳根本。(第三十四回)
另外,王桐龄在《中国历代党争史》中总结历代党争的七大特点:一是“中国全盛时代无党祸”;二是“士大夫与宦官竞争时,大率士大夫常居劣败地位,宦官常居优胜地位”;三是“朝臣分党竞争时,则君子常败,小人常胜”;四是“竞争者之双方皆士大夫时,则比较品行高尚者常败,品行卑劣者常胜”;五是“新旧分党互相竞争时,适合于国民心理者胜,否则败”;六是“学术分派对峙时,时常带有地方彩色”;七是“学术分派对峙时,时常含有门户之见”。 [12]227-242这些特点未必完全符合历代党争,但至少为我们提供了对历代党争的思考。
总之,《续金瓶梅》作者在描写两宋之际的党争及追溯宋前党争时,饱含着对党争误国、亡国的痛切之情。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也是对明朝亡于党争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
从以上四个方面的对比可以看出,小说作者表面上总结的是北宋王朝灭亡的教训,而实际上总结的是大明王朝灭亡的教训。总结明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是明遗民在清初深刻思考的重要问题之一,小说作者以文学的形式向读者展示自己对明王朝灭亡的思考,恰恰又是其浓郁的遗民意识的体现。
三、金代流人与清初宁古塔流放
流人者,流放之人也,主要包括因犯罪、战争、政治斗争等而遭流放者。流人自古有之,如姬昌遭商纣王的流放,越王勾践遭吴王夫差的流放,屈原遭楚怀王的两次流放等。《续金瓶梅》第五十八回对金代流人有较为充分的描写。这些流人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因东京陷落而被掳的徽、钦二帝及其嫔妃宫女;二是因出使金朝而遭扣押的洪皓;三是因战争失败而被掳的北宋百姓。流放地主要有两处:一是五国城(今属黑龙江省依兰县),徽、钦二帝等流放在此;二是冷山(今属黑龙江省五常市,一作今吉林省舒兰市),洪皓、北宋百姓等流放在此。
小说一方面描写了流放地恶劣的自然环境及与中原迥异的生活方式,如五国城:
那是穷发野人地方,去狗国不远,家家养狗,同食同寝,不食烟火,不生五谷,都是些番羌,打猎为生,以野羊野牛为食。到了五月才见塞上草青,不到两月又是寒冰大雪。因此都穿土穴在地窖中居住,不知织纺,以皮毛为礼。
又如冷山,“去黑海不远,也是打猎食生,却是用鹿耕地”,冬天是“冰天、雪窖”。
另一方面,小说重点描写了这些流人在流放地的生存状态。描写徽、钦二帝时,小说强调他们的精神孤寂,“徽钦父子不见中国一人,时或对月南望,仰天而叹”。不仅如此,他们在生活上亦颇为艰苦,“连旧皮袄也是没的”,还“随这些野人们吃肉吞生”。最后父子相继病逝于流放地。作者不禁感叹:“可怜这是宋家一朝皇帝,自古亡国辱身,未有如此者。”
(1)描写北宋百姓流放时,小说强调了他们遭受的非人待遇:
那些北方鞑子……将我中国掳的男女,买去做生口使用。怕逃走了,俱用一根皮条穿透拴在胸前琵琶骨上。白日替他喂马打柴,到夜里锁在屋里。买的妇人,却用一根皮条使铁钉穿透脚面,拖着一根木板,如人家养鸡怕飞的一般。
他们“十人九死,再无还乡的”。百姓遭亡国之苦,由此可见一斑。
(2)描写洪皓流放时,小说强调了他在流放地不屈而坚强的生活:
(洪皓)把平生记得四书五经写了一部桦皮书,甚有太古结绳之意。却将这小番童们要识汉字的,招来上学。……有一日,做了一套北曲,说他教习辽东之趣。
就此而言,洪皓在流放地充当了传播汉民族文化的角色。同时,洪皓对北宋怀有一颗赤诚之心,闻徽、钦二帝驾崩后,又:
换了一身孝衣,披发哀号,望北而祭。自制祭文,说二帝播迁绝域,自己出使无功,以致徽钦魂游沙漠。
最后,洪皓流放十三年(按:史载为十五年[1129—1143])得以归国,犹如当年苏武一般,完成了一位忠臣应有的气节,诚如作者评价曰:
那时公卿大臣,受朝廷的恩荣爵禄,每日列鼎而食,享那妻妾之奉,不知多少,那显这一个洪皓,做出千古的名节来。
(3)小说在描写金代流人时,总体上与史书记载相吻合,特别是洪皓哭祭徽、钦二帝事,尤为感动天人,而这一情节与诸多入清士人哭祭崇祯帝的情况颇有类似之处。笔者疑作者借历史人物,表达故明情怀。
小说不仅对金代流人的生活状态有较为详细的描写,还两次提及清初重要流放地——宁古塔(按:小说作“宁固塔”)。第一次是在小说第二回:
休说是士大夫宦海风波不可贪图苟且,就是这些小人,每每犯罪流口外,在宁固塔,那一个衙蠹土豪是漏网的?
第二次是在小说第五十八回:
洪皓……后来事泄,几番要杀他,只把他递解到冷山地方——即今日说宁固塔一样。
小说虽仅两次提及宁古塔,但还是明确无误地传递了清初流放的信息。关于宁古塔的由来,清初流人方拱乾《绝域纪略·流传》称:“宁古塔,不知何方舆,历代不知何所属。数千里内外,无寸碣可稽,无故老可问。相传当年曾有六人坐于阜,满呼六为宁公,坐为特,故曰宁公特,一讹为宁公台,再讹为宁古塔。固无台无塔也,惟一阜如陂陀,不足登。” [13]1175除宁古塔(按:旧城为今黑龙江海林、新城为今黑龙江宁安)外,盛京(今辽宁沈阳)、尚阳堡(今辽宁开原)、卜魁(今黑龙江齐齐哈尔)等也是清初重要流放地。 [14]
在《续金瓶梅》成书前,有几位重要汉人流放到宁古塔,如陈嘉猷、郑芝龙、方拱乾、吴兆骞等。其中陈嘉猷(字敬尹)于顺治十二年(1655)流放到宁古塔,亦是有史料记载的第一位汉人流放至此地 [15]57;郑芝龙及其子世忠、世恩、世荫、世默等于顺治十四年(1657)流放至此;方拱乾、吴兆骞等丁酉(顺治十四年,1657)科场案牵连者及其家人,于顺治十六年(1659)流放至此。在这些宁古塔流人中,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降清者的流放,如郑芝龙及其家人;一类是无辜者的流放,如方拱乾、吴兆骞等。丁耀亢在小说第二回与第五十八回提及宁古塔时,表达了对不同流放者的态度,而上述两类宁古塔流人恰好符合作者的不同态度。
在小说第二回提及宁古塔时,作者显然是对那些因“犯罪”而流放者感到理所当然,亦是对他们“犯罪”的一种惩罚。按小说的叙述,“犯罪”者主要是指“衙蠹土豪”。但笔者认为那些“犯罪”者不仅包括“衙蠹土豪”,还包括那些变节投降者。苗青曾在《金瓶梅》里杀主劫财,理应受到惩罚,但在西门庆的庇护下安然无事。他在《续金瓶梅》里又投降金朝,为害一方。在作者看来,像苗青这样一个杀主劫财、变节投降者,理应得到流放的惩罚。不过,在苗青的结局上,作者最终选择了剐刑,让其得到应有的惩罚。然而,小说第二回对流放者的态度似乎在告诉我们,像郑芝龙这样降清者流放到宁古塔,是罪有应得。
小说在第五十八回在描写洪皓时再次提及宁古塔。作者对于洪皓这样无辜流放者饱含了深切的同情。这种同情态度如果移植到因丁酉科场案而流放的方拱乾、吴兆骞等人身上,也是比较恰当的。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共发生五起科场案,其中以顺天乡试案(又称北闱科场案)、江南乡试案(又称南闱科场案)影响最大,孟森称:“丁酉狱蔓延几及全国,以顺天、江南两省为巨,次则河南,又次则山东、山西,共五闱。” [16]24在这影响最大的两科场案中,又以江南乡试案最为酷烈。“两主考斩决,十八房考除已死之卢铸鼎外,皆绞决” [16]43。另外,方章钺(按:方拱乾第五子)、吴兆骞等“俱著责四十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 [17]942。孟森如是评价江南乡试案道:
夫行不义杀不辜,为叔世得天下者之通例。不从弑逆者,即例应以大逆坐之。 [16]43
这实际上揭示了整个丁酉科场案的实质,那就是清廷试图借此来打击与控制汉族士人。所以,在科场案中牵涉到的人物多为无辜者,如颇有影响的方拱乾、吴兆骞等。这些无辜者,犹如出使金朝遭扣押而被流放的洪皓。按照这一逻辑,从小说中作者对洪皓这样无辜流放者的同情,可以推测出作者对宁古塔那些无辜流放者亦抱有同情之心。
总之,小说通过对金代流人凄苦生活的描写,表达了对他们深深的同情,又通过描写洪皓在流放地坚强不屈的精神与不忘故国的气节,表达了作者对其崇敬之心。同时,小说在涉及流放时,两次提及宁古塔,表达了作者对不同流放者的不同态度。这些描写及作者的不同态度,实际上反映了作者对清初宁古塔流人的思考,也反映了作者的遗民意识,特别是对洪皓的描写,更是将自己内心深处的遗民情怀诉诸其中。
四、结语
《续金瓶梅》在创作时以《金瓶梅》为依托,以宋金对峙为背景,表现了作者对金兵的残暴、北宋的灭亡、金代的流人等方面思考。而小说中又不断出现明清时期特有的名词,如“宁古塔”(第二、五十八回),“锦衣卫”(第六、十九、二十一、六十三回)“蓝旗营”(第二十八、五十六回)、“鱼皮国”(第五十八回)等,甚至出现“大明”(第十三、三十回)字样。作者在小说创作时,确实蕴含着对明清易代的现实的考量,表达了自己的遗民情怀,如对清兵屠城的愤怒、对明亡教训的总结、对宁古塔流放的态度等。这或许即是《续金瓶梅》案的出现及《续金瓶梅》遭禁毁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