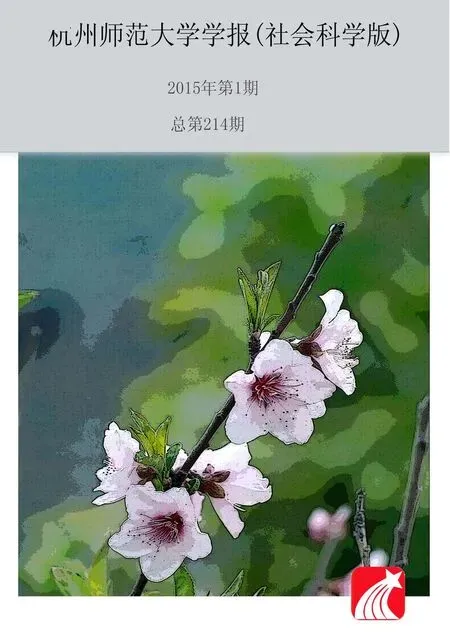中国城市政府管理体制的结构性突破——以上海市“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作为研究对象
2015-03-29张冬冬
张冬冬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思政部,上海 201209)
中国城市政府管理体制的结构性突破
——以上海市“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作为研究对象
张冬冬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思政部,上海 201209)
摘要:新的社会治理格局和社会治理体系的建立,要求实现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以公共服务提供为主要方式的、以安全与和谐为主要体现的新的社会治理格局。在这个过程中,以往“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城市政府管理体制逐渐暴露出层级过多、效能低下、活力不足、公共服务能力较差等缺陷。而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要求进一步减少政府层级、明确各级政府层级的职责和功能、强化条块之间的协调合作、激发多元参与主体的活力等,从而构建一个“层级合理、职能融合”的现代政府管理体系。
关键词:政府管理体制;社会治理创新;政府职能
在市场化、全球化、网络化的社会条件下,面对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如何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党和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其实就是如何以治理的理念和手段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实现社会治理主体和参与方式的多元化、治理效果的有效化、社会公共服务提供的合理化以及社会环境的和谐化和安全性。那么,在政府管理体系的构建和创新中,在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的定位下,就是如何合理界定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职能问题,形成“层级合理、职能融合”的政府管理体系,从而成为社会治理是否能够达到目标的一个重要保障。
一、以社会治理逻辑优化城市管理体制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求在今后的发展中加强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就更多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进一步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就是社会治理能力的提高。在新的治理体系构建中,对社会治理体系构建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其基本使命主要体现在四重定位:以多元构成治理,以服务创造治理,以和谐优化治理,以安全体现治理。
(一)以多元构成治理
所谓多元构成治理,意味着社会治理体系必须将多元的社会主体纳入到一个整体的治理网络结构中。也就是说,在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就参与主体而言,政府只是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社会治理已经从一元的、基于科层制的政府为管理主体,转变为包含政党组织、政府、企业、第三部门和公民等的多元化的治理参与主体①;就治理体系的构建来说,从以往只有党和政府单线的、自上而下的、条块的行政管理体系,转变为党、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所构成的多线条的、扁平化的、网络状的多元治理体系;就治理模式的塑造而言,从政府单一的、固化的行政管理模式,转变为政党组织、政府部门、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所提供的多元的、灵活的社会治理模式,从而促进社会治理主体、模式、体系的多元化和网络化。
(二)以服务创造治理
所谓服务创造治理,意味着通过社会治理体系构建,必须能够提供有效、高质量的社会公共服务,以服务体现和优化管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多元化服务需求。因而,在创新社会治理中,就治理手段而言,必须从计划经济式的行政命令和单一指令,转变为政党组织、政府、企业、第三部门和公民共同提供的复合的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公共服务。不仅政府部门要为公民提供服务,代表社会的企业和第三部门也要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服务,公民作为服务的受益者,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也要同政府、企业和第三部门合作,打造公共服务提供的网络体系,共同促进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和完善。随着从行政管理逐渐过渡到社会治理,就政府而言,从以往计划经济时代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提供者,到市场经济的掌舵者,再到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转变的不仅仅是政府部门提供公共物品的方式,而且包含了公共物品提供者的多元化和公共服务内容的多元化。以服务创造治理,正是通过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和社会组织的不断萌芽发展,为公民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产品,并且以服务体现和优化管理,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三)以和谐优化治理
所谓和谐优化治理,意味着社会治理体系的主体之间要形成扁平化、协同力的治理关系,以及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更加注重社会矛盾的化解,促进社会和谐。也就是说,就治理绩效而言,突出在治理过程中,各个参与主体之间如何达成合作,以及在效率之上,更加注重公平公正和促进社会和谐;在治理结构上,体现在多元治理的结构下,各种治理主体之间如何达成合作与和谐,这包括:1.社会治理是全社会的共同行动,创新社会治理,必须在政党组织、政府部门、企业组织、第三部门和公民个体之间,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企业、第三部门和公民等社会各方面参与,激发社会活力,从传统的社会管理转向时代发展的社会治理,努力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解、居民良性互动上取得合作共赢、和谐有效。2.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治理的优化更体现为在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要建立畅通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心理机制和矛盾调处机制,从而更有效地保障人民群众的权益和促进社会和谐。
(四)以安全体现治理
所谓安全体现治理,意味着在不同的维度和层级上,通过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建,必须要实现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的稳定和安全。也就是说,就治理目标而言,在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面前,注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要更加强调社会安全、稳定,为居民安居乐业创造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治理创新过程中,要进一步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完善安全生产监管制度,健全防灾减灾救灾机制,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增强全社会的安全防范意识,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预警响应和救援保障能力,提高城市安全防范水平,为居民的工作、生活和出行创造安稳的经济社会环境。
即未来社会治理的基本使命是,通过一定时期的社会建设,未来要实现一个具有安全感、服务性、和谐度、协同力的社会治理体系。即与传统政府管理理念和方式相比,未来的社会治理中,政府不再是唯一的价值存在和治理主体,市场化的组织、社会非营利性组织等同样可以成为进行社会管理、提供社会服务的价值主体;各个社会治理主体在协作的基础上彼此互相拾遗补缺,形成相互补充、共同治理的网络化社会治理格局;多元的主体、网络化的治理结构,突破传统的公共物品的供给,更多的以多元化的公共服务的形式提供给公民以安全为主要表现的社会和谐和安居乐业。在这个过程中,城市政府管理体系要发生很大的变化,政府的职能也要发生很大的改变。
二、“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由来、现状及其弊端
(一)“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的由来
我国现行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是针对我国计划经济时代沿袭下来的条块分割、职责同构的城市管理体制的弊端所提出的新的城市管理模式创新,作为试点城市,上海率先进行了改革试验。作为一种新的管理体制创新,“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政府管理体系其主要作用是划清了市与区之间的职能,并将街道作为一级准政府而纳入城市管理体制中。“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实行以来,市、区两级政府简政放权,城市管理重心下移,社区事业蓬勃发展,中国的城市行政管理体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的问题,其核心是城市政府管理体制中政府职能定位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区与市之间的协调问题、作为一级准政府的街道职责界定问题,以及作为基层自治组织的社区居委会活力激发问题等,给城市社会治理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障碍。
(二)“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的发展现状
随着个体化进程的推进,从传统阶级、地位、家庭的束缚之下抽离出来的个体,不断融入以平等、独立、自主为原则的现代社会之中。 在中国,个体化进程则与改革开放的推进亦步亦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公社制度的解体、城市国有企业的重组,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大包大揽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 个体自愿或不自愿地摆脱了原先“集体人” “单位人”的身份限制,投身市场经济的浪潮之中,开始一种自主选择、自我负责的生活。 摆脱了集体依附状态的个体,开始重新认知自身,追寻自我意义和生命价值。
“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的特点是将权力重心下移至街道,强化街道办事处的权限和职能,旨在充实、强化街道办事处的管理职能,减轻市、区两级政府的城市管理任务。街道办事处被授予部分城区规划的参与权、分级管理权、综合协调权、属地管理权等四项权限,并采取了理清条块关系、建立综合执法队、扩充街道和居委会编制、完善财力机制等一系列措施,以对这些权限进行落实。
“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建立后,在短时间内提高了城市管理效率,推动了社区发展。它改进了街道办事处管理上的条块协调,在街道办事处内建立了全面应对于区政府派出机构的部门设置,实行对派出机构的双重领导,这样就形成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机构组合,克服了原有的“条块分离、各自为政”的弊端,对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城市管理重心下移和提高城市管理效率都有重大作用。在实践中,这种“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新体制有机地整合了纵向联系的行政体系和横向联系的自治组织,提高了政府整合社区资源和行政资源的能力,“条块关系”初步理顺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事、政企、政社的分离,建立起了新的社区管理框架,在一定时期内推动了社区建设,加快了社区发展。
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环境发生变化,传统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的弊端也不断暴露出来,问题的核心集中于“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中,各级政府管理主体,尤其是区、街道办事处的定位、职能、构成和权限混乱所引起的财权和事权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条块不顺、职能错位的问题。
(三)“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的问题与根源
1.体制设计与运行上的弊端
所谓“两级政府”是指市级政府和区级政府,街道办事处是区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内含于“两级政府”之中,它既是政府各项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又是调节社区社会、经济、文化等活动的中枢。“三级管理”是指市级政府、区级政府、街道办事处三者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从而,在“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中,街道办事处具有两重角色:一是上级机关的派出机构,是上级政府各项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二是作为一级管理机构,管理着居民委员会,并通过它来处理大部分具体的社区事务,即在“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模式下,“街道办事处成为以职能转变为核心的自上而下的行政体制改革和以居民自治和社会自治为核心的自下而上的社区体制改革交汇点”。[1]“两级政府、三级管理”模式,旨在强化街道办事处的权限和职能,充实街道办事处的管理职能,减轻市、区级政府的城市管理的压力。
然而,在将城市管理重心下移、减轻市区层面行政管理压力的同时,作为区政府派出机构的街道办事处在社区建设和城市基层管理中的功能和地位日益突出,致使其发挥了相当于一级政府的功能,街道的职能存在严重错位。作为上级政府的派出机构,街道并没有税收征管、行政执法的权力,也不具备人事任免权,因而面对大量招商引资任务,以及上级条线部门下派的大量行政任务,街道有心而无力,流于应付。另外,纵观街道的部门安排,完全是上级政府职能部门的“缩影”,在权力没有法定、职能无法发挥的情况下,如此一应俱全的、琐碎的部门设置对于行政管理过程是无效和浪费的,只能流于跟上级部门的盲目对口中。
2.体制活力和能力上的弊端
在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过程中,政府能力的强化与社会自身的成长是极其不对称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最大限度地释放出了政府的管理范围和控制力度。但是,任何事情都是一体两面的,政府管理范围的扩展和控制力度的强化却弱化了“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改革活力,直接导致了当所有社会问题被推至政府这最后一道底线时,政府的调控能力、解决能力和管理能力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问题反而捉襟见肘、爱莫能助。在一些学者看来,以上海为始所进行的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不是西方政治学中的地方自治体制,而是比较符合黄宗智所说的“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的属性,即居委会作为由国家为主导建立的城市基层民主自治组织,其接受街道层面的党工委和行政中心的领导,通过这种领导,党和国家“柔性地”体现了自己的意志。[2]也就是说在“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下,街道办事处作为一级政府,成为社区管理的唯一主体,而作为城市基层治理组织的居委会却在很大程度上缺乏自主性,依靠于街道财政拨款的居委会,其职能的发挥仅限于街道办事处的指示,而非按照居民的自主意愿安排社会服务,在街道流于应付上级政府工作任务的困境下,居委会作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功能基本名存实亡。
从数量上来看,上海市的社会组织发展,一是数量较少,社会组织的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二是社会组织的作用能力有限,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的程度在短期很难有所改变。社会组织作为从社会中自发形成的组织体系,更多的时候需要挂靠在一级政府或其职能部门之下,其财政、人事都受到主管部门和上级部门的制约,因而社会组织作为自发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功能存在很大局限。三是社会组织发展的支持体系没有建立。虽然挂靠在政府职能部门之下,绝大部分社会组织在募集资金和推进项目的过程中依然面临着很多掣肘和障碍。
3.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上的弊端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上海长期实行财权、财力下放的分权财政体制。这种体制激励市区两级政府将主要精力和资源用于经济建设,从而对上海市区两级财政收入和财政能力的增加多有助益。但这种体制也具有极大的局限性:由于不同区之间财政能力的差异,各区之间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也存在很大差异,造成上海市级层面公共服务的提供存在较大差异。调查研究显示,“现在上海各个区的财力差距相当大,人均财政开支2009年最高的区和最低的区是5.06:1,也就是说缺乏公平保障机制”。[3]譬如教育资源的提供等,教育资源众多的中心城区,与教育资源缺乏的远郊地区存在着资源分配不均的严重问题——“人均教育公用经费幼儿园是6.31:1,小学是9.04:1,初中是7.67:1,高中是6.80:1”。[3]
另外,在现行“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下,区域经济强化,助长了地区本位主义思想,市级政府的权威性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一方面,市辖区作为城市整体的基本组成部分,相互之间在发展目标、战略定位、土地利用、结构调整等方面要统筹考虑,并受到城市发展整体性要求的制约。另一方面,各区作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又必然以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宗旨,在资源争夺、土地规划、区域发展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和矛盾。因此,区级政府的双重身份,导致在其利益驱动机制和行为约束机制发生矛盾时,结果往往是利益驱动占据上风,而以城市发展全局整体性受到破坏为代价。
三、“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的变革走向
针对“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城市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学界普遍存在三种观点:一是变“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为“三级政府、三级管理”,即将街道的“准政府”定位变为真正的一级地方政府,成为市、区下辖的一级地方政府层级,赋予街道彻底的行政管理和财政征收权力;二是重构“两级政府、两级管理”体制,即将现有的街道适当合并,扩大区域后设立一级政府,而将现有的区政府改为市政府的派出机关,代表市政府负责指导、联系、监督各街道政府,适当减少其行政职能,实行“虚区实街”的管理体制;三是取消街道办事处,直接由区政府和基层居委会打交道,同时积极营造第三部门发展所需的环境,促使居委会基层自治功能的正常发挥。[4]
针对这三种方法,纵观国际上大都市的城市治理,尽可能减少政府行政层级既是管理的便利也是国际的惯例。根据目前世界上191个国家和地区的初步统计,地方政府行政层级为二级与三级的占67%,超过三级的只有21个国家,占11%,世界上主要的发达国家中,联邦制的美国实行州政府和22000多个县、乡、城镇的两级制,日本实行都、道、府、县和市、町、村两个层级,法国实行大区、省和市镇三个层次。[5]那么,在上海的城市管理体制和政府体系改革创新中,在变化了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将街道作为一级行政机关的做法显然是不合时宜的。除此之外的两种方法,要么是弱化区的权力,要么是弱化街道权力,这是我们在接下来的行政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中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然而,不管是哪种途径,在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过程中,减少政府层级、明确各级政府层级的职责和功能、强化条块之间的协调合作、激发多元参与主体的活力等却无疑是未来上海城市管理体制的大方向。
1.科学合理界定条块之间的界限,明确各级政府管理主体的职能,合理确定事权财权
在城市治理过程中,对于城市相关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领域所涉及的各项事权和财权进行合理划分和界定,市、区和街道之间要实行错位管理——决策权和监督权进一步向市政府集中,执行权则分类分配于区和街道,而居委会则主要是服务群众,承担起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基层自治功能;各级政府管理主体职责明确,并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严格按照宪法所赋予的各个主体的职责,在城市治理中理顺条块关系,条重管理,块重自治,建立和谐高效的政府间关系。
2.树立新的地方治理观,激发多元参与主体活力
与传统政府管理理念和方式相比,未来的社会治理中,政府不再是唯一的价值存在和治理主体,市场化的组织、社会非营利性组织等同样可以成为进行社会管理、提供社会服务的价值主体;各个社会治理主体在协作的基础上彼此互相拾遗补缺,形成相互补充、共同治理的网络化社会治理格局;多元的主体、网络化的治理结构,突破传统的公共物品的供给,更多的以多元化的公共服务的形式提供给公民以安全为主要表现的社会和谐和安居乐业。因此,要大力推进居民自治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简政放权,将更多的适于社会管理和服务的事务,交给居民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大力推进业委会的健康发展,积极培育社会中介组织和行业协会的发展,激发社会组织和公民在城市管理中的主体地位意识和参与积极性。
3.厘清政企关系,创新政社关系,理顺政事关系
与传统城市管理不同,在城市治理的发展中,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企业、第三部门和居民逐渐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等公共服务提供组织以及政府采购、政府服务外包等的兴起,都是在城市治理创新的过程中,不同的社会参与主体切实加入治理的具体表现,城市政府不是城市治理的唯一主体。因而,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城市管理的主体之一,政府要进一步厘清政企关系,创新政社关系,理顺政事关系,要处理好各个层级之间的关系,在城市治理过程中合理界定不同层级自身职能,划分职权分配,合理界定财权事权;在社会的治理创新中,进一步挖掘企业、社会组织的功能,将市场能够承担的社会治理功能进一步交还给市场和社会,进一步发挥社区居委会和居民的自治功能,建立“行政、自治、社会”三位一体的治理结构,以期集合来自党、国家、社会的各种力量,在城市治理创新中实现各个主体相互协调、相互合作、相互补充的和谐治理局面。
4.强化市级调控能力,建立扁平化的公共财政体制
在区与区之间资源分配、公共服务不均衡矛盾的情况下,要强化市一级的调控能力,提高市级财政收入比重,进一步加强市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建立扁平化的公共财政支付制度。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在城市化水平高、经济发展快的现代化形势下,需要市级政府层面有更大的宏观调控能力,增加市一级的权力,统一规划、集中管理,平衡区域财力和资源分配,使市级职能更多的集中于经济管理、宏观调控和统一协调,而弱化区级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更多地承担起社会建设和公共管理服务职能,街道和居委会则更多地承担起服务居民和服务自治的工作上去。另外,要建立基本的公共服务支出水平标准,确定社保、医疗和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区级之间的合理分配和平等对待,弱化区与区之间的不平等资源分配和公共服务支出水平,使上海在进一步的城市发展中实现各个区域的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5.借鉴国际大都市的管理体制,创新城市管理体系
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的社会治理创新总是走在整个国家治理创新的前列,在逐步同国际大都市接轨的过程中,要积极学习和借鉴国际大都市的政府关系设置模式、政府组织的规模标准、公共组织的管理模式、城市社会治理体制等,进一步学习和吸收符合我国国情和上海市情的有效做法,在接下来的社会治理创新中走出更为扎实的步骤。
参考文献:
[1]杨艳文.街道治理的结构、动力及其逻辑[J].学术论坛,2013,(12).
[2]郭伟和.街道公共体制改革和国家意志的柔性控制——对黄宗智“国家和社会的第三领域”理论的扩展[J].开放时代,2010,(2).
[3]江建全.以扁平化管理为突破口,完善上海现行“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J].理论与改革,2011,(1).
[4]浦兴祖.特大城市城区管理体制的改革走向——兼谈“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之提法[J].政治学研究,1998,(3).
[5]洪智明.深圳市“一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研究[D].兰州大学,2011.
(责任编辑:吴芳)
Reasonable Levels and Syncretic Functions
—A Study on Shanghai’s Government Management System
in a New Governance Context
ZHANG Dong-dong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Shanghai Second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
Abstract:New social governance means multiple subjects, including people,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government, should provide public services and make a security and harmonious social environment to each other. During the process, the government system characterized by “two-leveled government, three-leveled management” has gradually displayed its flaws in practice, such as excessive levels, low efficiency and vitality, and poor public service capacity, etc. In dealing with it, we need to make an innovative social management system as follows: first, the government level should be decreased and the function of each hierarchic level be clarified. Second, the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levels and parts should also be strengthened. Third, the vitality of the participating subjects should be stimulated. In this way, we are likely to build a modern government management system with reasonable levels and syncretic functions.
Key words:Government management system; innovative social governance; duties of the government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5.01.016
中图分类号:C9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5)01-0110-06
作者简介:张冬冬(1985-),女,河南南阳人,政治学博士,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思政部讲师,主要从事政党制度、城市政治等研究。
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要“坚持系统治理,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从十八大的“政府负责”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导”,表明政府只是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之一。
城市学研究城市管理研究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