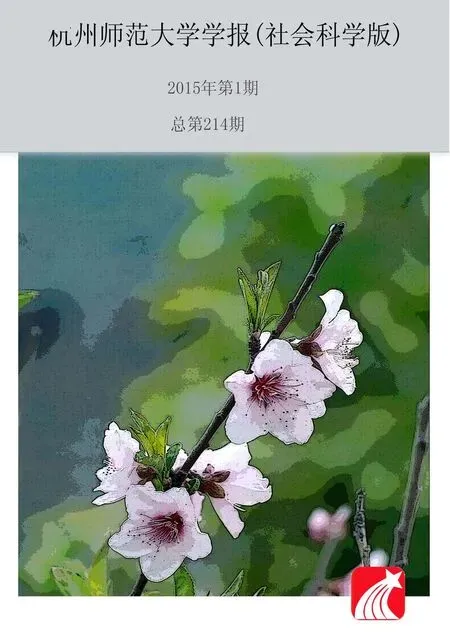马一浮、牟宗三对朱熹“性即理”的不同解读
2015-03-29乐爱国李志峰
乐爱国,李志峰
(厦门大学 哲学系,福建 厦门361005)
朱熹因言“性即理”,其学术被不少学者界定为“理学”,与陆九渊、王阳明言“心即理”,其学术被界定为“心学”相对立。然而,对于朱熹“性即理”及其与陆王“心即理”之关系,马一浮与牟宗三有着不同的解读,因而对于朱学及其与陆王学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解。分析比较马一浮与牟宗三对于朱熹“性即理”的不同解读,不仅有助于把握朱熹“性即理”的内涵,而且对于深入理解朱学,不无裨益。
一、问题的提出
把“性即理”与“心即理”分别看作朱学与陆王学的根本分歧,可以追溯到1931年出版的吕思勉的《理学纲要》。该书指出:“朱陆之异,象山谓‘心即理’,朱子谓‘性即理’而已。惟其谓‘性即理’,而‘心统性情’也,故所谓性者,虽纯粹至善,而所谓心者,则已不能离乎气质之累,而不免杂有人欲之私。惟其谓‘心即理’也,故万事皆具于吾心,吾心之外,更无所谓理,理之外,更无所谓事,一切工夫,只在一心之上。二家同异,后来虽枝叶繁多,而溯厥根源,则惟此一语而已。”[1](P.117)
1932年,冯友兰发表《宋明道学中理学心学二派之不同》,指出:“朱陆之不同,实非只其为学或修养方法之不同;二人之哲学,根本上实有差异之处。……若以一、二语以表示此种差异之所在,则可谓朱子一派之学为理学,而象山一派之学,则心学也”,“朱子言‘性即理’,象山言‘心即理’。此二言虽只一字之不同,而实代表二人哲学之重要的差异”,[2](P.1)“朱子言‘性即理’;阳明言‘心即理’。此为理学与心学不同之处。”[2](P.9)该文还说:“盖朱子以心乃理与气合而生之具体的物,与抽象之理,完全不在同一世界之内。心中之理,即所谓性;心中虽有理而心非理。故依朱子之系统,实只能言‘性即理’,不能言‘心即理’也。”[2](PP.1-2)这些观点后来被纳入1934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对民国时期乃至后来的学术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然而事实上,一直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1935年,张荫麟《评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下卷》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有关朱陆异同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讲朱陆哲学上的重要差异在于朱子言“性即理”、象山言“心即理”,并不能推演出在修养方法上朱子注重“道学问”与象山侧重内心自知的差别:“朱陆同以为‘人之所应然的道理’是具于各人心中。那么,他们应当同以为:欲知道怎样做一个理想的人,欲明‘心之全体大用’,反求诸其心就够了。何以朱子于此更注重‘道学问’呢?更注重对外物‘用力之久’呢?”[3](P.723)
同年出版的李石岑《中国哲学十讲》认为,朱熹“特别尊重‘心’与‘理’的合一”,因而专题阐述了朱熹的“心即理说”,[4](P.287)并且还说:“晦庵是站在心的立场上去说明理”[4](P.288),“晦庵认心和理是同一的东西”[4](P.297)。
1938年,贺麟在一篇讨论朱熹太极说的论文中说道:“朱子之太极有两义:(一)太极指总天地万物之理言,(二)太极指心与理一之全体或灵明境界言。所谓心与理一之全,亦即理气合一之全(但心既与理为一,则心即理,理即心,心已非普通形下之气,理已非抽象静止之理矣)。”[5](P.129)这里把朱熹所言“心与理一”解说为“心即理,理即心”。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马一浮于1939至1941年任四川乐山复性书院院长兼主讲期间,在讲学中也涉及了对于朱熹“性即理”的解读。
二、马一浮对朱熹“性即理”的解读
朱熹讲“性即理”,但又认为“性”与“心”是不同的,“性便是心之所有之理,心便是理之所会之地”,“性是理,心是包含该载,敷施发用底”。[6](P.88)所以,“谓性便是心,则不可;谓心便是性,亦不可”[6](P.411)。与此同时,朱熹又明确讲“心具众理”。《孟子集注》指出:“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7](P.349)由此可见,在朱熹那里,“性即理”与“心具众理”是统一的。而且,朱熹对《大学》“格物”解说,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与朱熹不同,王阳明讲“心即理”,并强调“心外无事”,“心外无理”。他说:“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8](P.15)又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8](P.2)王阳明尤为反对朱熹把《大学》“格物”解说为“即物而穷其理”,指出:“朱子所谓‘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即物穷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而为二矣。”[8](PP.44-45)
马一浮赞同朱熹所谓“性即理”,而且认为,朱熹对《大学》“格物”的解说,并非把“心”与“理”分为内外。他说:“朱子释‘格物’为穷至事物之理,‘致知’为推极吾心之知。知者,知此理也。知具于心,则理不在心外明矣,并非打成两橛。不善会者,往往以理为外。……今明心外无物,事外无理,即物而穷其理者,即此自心之物而穷其本具之理也。此理周遍充塞,无乎不在,不可执有内外。”[9](PP.110-111)马一浮甚至还说:“今明心外无物,事外无理,事虽万殊,不离一心。……一心贯万事,即一心具众理。即事即理,即理即心。心外无理,亦即心外无事。理事双融,一心所摄,然后知散之则为万殊,约之唯是一理。”[9](P.111)显然,在马一浮看来,朱熹所谓“即物而穷其理”,就是即心中之物而穷其所具之理;所谓“心具众理”,就是“即事即理,即理即心”。
但是,马一浮并不赞同王阳明所谓“心即理”。他说:“阳明谓心即理,不如宋儒性即理之说为的当。”[10](P.1142)又说:“心兼理、气,统性、情。出于性、理,谓之道心;发于情、气,谓之人心。宋人性即理之说最为谛当,若阳明心即理,未免说得太易了。”[10](P.1166)“阳明‘心即理’说得太快,末流之弊便至误认人欲为天理。心统性情、合理气,言具理则可,言即理则不可。”[9](PP.591-592)“心统性情,即该理气。理行乎气中,性行乎情中。但气有差忒,则理有时而不行;情有流失,则性隐而不现耳。故言心即理则情字没安放处。”[9](PP.672-673)
由此可见,马一浮一方面把朱熹“性即理”与王阳明“心即理”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以朱熹“性即理”涵摄“心即理”,以朱熹“心具众理”涵摄王阳明的“心外无事”、“心外无理”,以“最为谛当”的朱熹“性即理”涵摄“说得太易”、“说得太快”、“情字没安放处”的王阳明的“心即理”,而不是将二者对立起来。
三、牟宗三对朱熹“性即理”的解读
牟宗三对于朱熹“性即理”的解读,着重于将“性即理”与“心即理”区别开来。他说:“在伊川朱子,性只成存在之理,只存有而不活动,心只是实然的心气之心,心并不即是性,并不即是理。故心只能发其认知之用,并不能表示其自身之自主自决之即是理,而作为客观存有之‘存在之理’(性理),即在其外而为其认知之所对,此即分心理为能所,而亦即阳明所谓析心与理为二者也”[11](P.93),认为朱熹讲“性即理”是“析心与理为二”,完全不同于王阳明的“心即理”。
至于朱熹讲“心具众理”,牟宗三认为,在朱熹学说的系统中,“心具”与“性具”并不相同,“‘性具’是分析地具,必然地具,性即理。而‘心具’则不是分析地具、必然地具,心不即是理。‘心具’是综和地关联地具,其本身亦可以具,亦可以不具。其具是因着收敛凝聚而合道而始具,此是合的具,不是本具的具。……其底子是心性平行为二,心不即是理,故心体亦不即是性体”。[12](P.135)在牟宗三看来,朱熹的“心具众理”,实际上是“心不即是理”。所以他还说:“朱子所想之心只是心知之明之认知的作用,其本身并非即是‘心即理’之实体性的心。彼虽亦常言‘心具万理’,但其所意谓之‘具’,是认知地、管摄地、关联地具,并非是‘心即理’之实体性的心之自发自律地具。”[12](P.338)
朱熹既讲“性即理”、“心具众理”,又讲“心与理一”,指出:“心与理一,不是理在前面为一物。理便在心之中。”[6](P.85)对此,牟宗三案曰:“此‘心与理一’是认知地摄具之一,不是本体论地自发自具之一。”[12](P.426)如前所述,贺麟曾认为,太极既指总天地万物之理,又指心与理一之全体,就后者而言,“心与理一”,则“心即理,理即心”。显然,贺麟是从本体意义上解读朱熹的“心与理一”,并进一步解读为“心即理,理即心”。可见,牟宗三对于朱熹“心与理一”的解读不同于贺麟。
应当说,牟宗三对于朱熹“性即理”与“心即理”的区别,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但是,他做出这些区别,旨在说明朱熹“性即理”及其相关的“心统性情”所蕴含的心、性、情之三分之格局,“与孟子‘本心即性’之本心义不相应”[11](P.50)。因此,牟宗三说:“朱子实非孟子学,亦实非象山、阳明学”[12](P.175),“朱子自是伊川学,而非孟子学”[12](P.431),并进而认为“伊川是《礼记》所谓‘别子’,朱子是继别子为宗者”。[11](P.49)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以朱熹“性即理”与陆王“心即理”区别出“理学”与“心学”,只是就宋明理学中的学派分立而言,而牟宗三则不仅限于学派的分系,而且进一步从中分析出“朱子实非孟子学”,“朱子是继别子为宗者”,朱熹“性即理”与陆王“心即理”的对立愈加尖锐。
四、朱熹“性即理”与陆王“心即理”的相互联系
无论是马一浮还是牟宗三,他们都认为朱熹的“性即理”与陆王“心即理”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别,需要指出的是,与牟宗三不同,马一浮不是把这种差别看作是对立,而是强调二者的相互联系,并以朱熹的“性即理”涵摄“心即理”。
事实上,朱熹在讲“性即理”、“心具众理”的同时,还具有“心外无理”的思想。他说:“夫心之体具乎是理,而理则无所不该,而无一物不在,然其用实不外乎人心。盖理虽在物,而用实在心也。”[6](P.416)又说:“理不是在面前别为一物,即在吾心”[6](P.155),“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也,不是心外别有个理,理外别有个心。”[6](P.4)需要指出的是,这里通过“心固是主宰”,而内涵了“心即理”。朱熹还明确说:“仁者心便是理”,“仁者理即是心,心即是理。”[6](P.985)另据《朱子语类》载,朱熹门人说:“……千言万语,只是欲学者此心常在道理上穷究。若此心不在道理上穷究,则心自心,理自理,邈然更不相干。……今日明日积累既多,则胸中自然贯通。如此,则心即理,理即心,动容周旋,无不中理矣。……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朱熹说:“是如此。”[6](P.408)应当说,这里讲“心即理”涵摄于朱熹的“性即理”之中。
而在陆九渊那里,讲“心即理”但并不否定“理”为宇宙所固有。他说:“此理在宇宙间,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损”[13](P.26),“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岂可言无?”[13](P.28)还说:“宇宙间自有实理,所贵乎学者,为能明此理耳。”[13](P.182)同时,他又认为,“心皆具是理”。他说:“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13](P.149)可见,陆九渊既讲“理”为宇宙所固有,又讲“心皆具是理”,并进一步讲“心即理”。显然,无论在朱熹还是在陆九渊,“性即理”与“心即理”多有重合之处,可以并行不悖。
王阳明虽然讲“圣人之学,心学也”,“陆氏之学,孟氏之学也”,而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讲格物致知是“析心与理而为二”而与“心学”相对立,但是却接受《大学章句》所谓“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指出:“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8](P.15)王阳明在《紫阳书院集序》中指出:“君子之学,惟求得其心。虽至于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孟氏所谓‘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学者,学此者也;审问者,问此者也;慎思者,思此者也;明辩者,辩此者也;笃行者,行此者也。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故心外无学。”[8](P.239)这显然接受了朱熹《中庸章句》注“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所言“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王阳明甚至也说:“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8](P.79)由此可见,阳明学讲“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朱熹《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中引申出来的。因此,王阳明所撰《朱子晚年定论》自谓“自幸其说之不谬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8](P.128),并非虚言。由此可见,马一浮以朱熹的“性即理”涵摄“心即理”,确有一定的道理。
与此同时,王阳明不仅讲“心即理”,而且也讲“性即理”。他说:“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元不动,理元不动”[8](P.24),“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穷仁之理,真要仁极仁,穷义之理,真要义极义:仁义只是吾性,故穷理即是尽性。”[8](PP.33-34)尽管在牟宗三看来,“性即理”与“心即理”大相径庭,但在王阳明那里,“性即理”与“心即理”似乎并非截然对立。王阳明还说:“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邪?晦庵谓:‘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8](P.42)在这段对于“心即理”的阐述中,王阳明却插入了“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显然是把“性即理”与“心即理”调和起来。
其实,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把朱熹“性即理”与陆王“心即理”对立起来之后,除上述张荫麟、李石岑、贺麟以及马一浮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将二者调和起来。
1945年,张东荪发表的《朱子的形而上学》认为,朱熹既讲“性即理”,又讲“心即理”,同时又认为,在朱熹的学术思想中,“性即理”与“心即理”是相互联系的。该文还引朱熹所言“心与理一,不是理在前面为一物,理便在心之中”,指出:“心之所以能具理,只是由于性使然。须知性即理也。由理造成的性则当然可使心能与理打通。……故明心即是尽性;尽性即是穷理;穷理即是理之自己完成。说心、说性、说理乃完全是一回事。因而有‘心即理’与‘性即理’之言。”[13](P.20)
1947年,钱穆的《朱子学术述评》认为,朱熹讲“性即理”,同时也“颇有主张心即理说之倾向”,“但从朱子思想之大体看,则朱子只肯明白说性即理,又说性是一物在心中,不肯说心即理”。[14](P.18)该文又说:“他虽说心具众理,而实心外有理,因此他不肯说心即理,或心生理,而只说心具理,于是说成一个道理在心中之性。”[14](P.19)还说:“既认万理在我心中而又要向外寻求,此何以故?因理非气则无可安放故。理安放在气上,故穷理必须格物。物无穷,斯理亦无穷,但却又全在你心里,此何以故?因性即理,性不能在心外,则理亦不能在心外故。此是朱子思想。”[14](P.19)1948年,钱穆发表的《朱子心学略》则说:“程朱主性即理,陆王主心即理,学者遂称程朱为理学,陆王为心学,此特大较言之尔。朱子未尝外心言理,亦未尝外心言性,其文集语类,言心者极多,并极精邃,有极近陆王者……”[15](P.1)钱穆的这些观点,后来被纳入他的《朱子新学案》。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牟宗三强调朱熹“性即理”与陆王“心即理”的截然不同,但与他师出同门的唐君毅却认为,“求心之合乎理,以使心与理一,亦程朱陆王共许之义”,并指出:“朱子果有以心与理为二之言,则初是自人之现有之心,因有气禀物欲之杂,而恒不合理;故当先尊此理,先有自去其气禀物欲之杂之工夫,方能达于心与理一上说。”[16](P.349)唐君毅还引朱熹所言“读书须是以自家之心,体验圣人之心。少间体验得自家之心,便是圣人之心”,“圣人之言即圣人之心,圣人之心即天地之理”,指出:“此未尝不归宿在见心之即理、见己之心同于圣人之心,而通于象山之发明本心之旨。”还说:“然以朱子观象山之言,‘说心与理一,不察乎气禀物欲之私,是见得不真’。此即谓必须先见及此气禀物欲之杂,足使心与理宛然成二,然后吾人方能实有去此难之工夫,以实见心与理之一。以象山观朱子,则先见有此气禀物欲之杂,即不能直下见及心与理之一,而未能本此见,更以‘自信此心与理一’为工夫。所见者既是有此‘杂’,以使心与理不一者,则此所见者,非心与理一,乃心与理二。则由工夫之所成,而见及之心与理一,即只属修成,非真本有。然若非本有,则修无可成,而亦可不修。于此心与理一之为本有一义上,则朱子在其心性论,虽亦向之而趋,而未能圆成。”[16](P.418)显然,在唐君毅看来,朱熹讲“性即理”,似乎是使心与理为二,但那是由于朱熹认为心为气禀物欲所杂而不合理,需要先去其气禀物欲之杂,方能达到心与理一;这虽然是由工夫所成的心与理一,但说明朱熹在本体论上具有心与理一的趋向,只是没有能够圆满地解决“性即理”与“心即理”的关系;所以,唐君毅明确指出:“朱子之学,既未尝不归在见心之即理、己之心即圣人之心,则亦即未尝不与象山同旨。”[16](P.418)
五、结语
现代对于朱学与陆王学的研究,大都以“性即理”与“心即理”区分朱学与陆王学。冯友兰将二者对立起来,而把朱学界定为“理学”,把陆王学界定为“心学”。与此不同,一些学者反对把“性即理”与“心即理”对立起来,甚至通过强调二者的相互联系,把朱学与陆王学调和起来。马一浮虽强调“性即理”与“心即理”的不同,但是以朱熹“性即理”涵摄“心即理”。牟宗三则进一步分析朱熹“性即理”与陆王“心即理”的截然不同,并以为“朱子实非孟子学”,而与陆王学对立。
重要的是,这些莫衷一是的学术观点是进一步研究朱熹“性即理”及其与陆王“心即理”之关系的学术基础和可供参考的学术资源。借助于这些资源,重新审视朱学与陆王学可以看出:关于“性即理”与“心即理”,在朱熹那里,二者虽然不同,但可以并行不悖;而在陆九渊那里,讲“心即理”时又讲“心皆具是理”,因而与朱熹讲“性即理”时又讲“心具众理”多有重合;王阳明则在讲“心即理”时又讲“性即理”,不仅把二者调和起来,而且可以看出王阳明讲“心即理”与“性即理”或有某种渊源关系。
由此可见,虽然在今天看来“性即理”与“心即理”有较多的不同,但在朱学和陆王学中,不仅没有就二者作出明确的区分,而且不同概念交互使用,并行不悖。所以,以此二者作为朱学与陆王学的区别,恐有不妥;即使通过各种方式把朱学归于“性即理”,把陆王学归于“心即理”,并强调二者的对立,可能也并非朱熹和陆王所能够接受的。
[1]吕思勉.理学纲要[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2]冯友兰.宋明道学中理学心学二派之不同[J].清华学报,1932,8(1).
[3]张荫麟.《中国哲学史》下卷[J].清华学报,1935,10(3).
[4]李石岑.中国哲学十讲[M].上海:世界书局,1935.
[5]贺麟.与张荫麟先生辩太极说之转变[J].新动向,1938,1(4).
[6]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9]马一浮.马一浮集:第一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
[10]马一浮.马一浮集:第三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
[11]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3.
[12]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3.
[13]张东荪.朱子的形而上学[J].中大学报,1945,3(1-2).
[14]钱穆.朱子学术述评[J].思想与时代,1947,(47).
[15]钱穆.朱子心学略[J].学原,1948,2(6).
[16]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