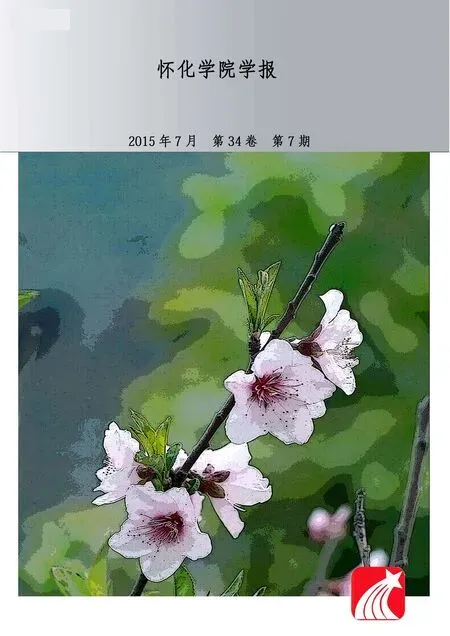苗族理词生态伦理法治思想之管窥
2015-03-29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 马列部,贵州 铜仁554300)
引言
2008年,由贵州省黔东南苗族申报的《苗族贾理》通过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苗族贾理在苗语生活世界里称为Jax (音译贾、加或枷),是指苗族人民用来阐明宇宙及天地万物的产生和发展、苗族各类案件例举以及从事巫事活动所吟诵的民间口头文学。经众多搜集者整理后,迄今苗族理词已出版了5个文本。尽管不同异文在细节上略有差异,但其大致内容基本相似。
苗族理词与苗疆民众生活密不可分,在苗族理词的吟诵中,听众不仅得以认识苗族理词所构筑的宇宙观、世界观和生命观,了解到苗族理词所承载的历史,如旷日持久的战争、奔波流离的迁徙与苗族姓氏的大致分布,更为重要的是维系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截至当下,在广大的苗疆,苗族理词依然成为维系苗族族源记忆、族群意识和族属认同的重要依据,并以此深远影响到审判、宗教、婚丧嫁娶等生命活动有序进行,包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法治思想。
生态伦理法治思想缘起于西方工业革命负面影响的积极探索。人类自从进入工业文明后期,在创造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也把人类推向了危险的境地:水体污染、酸雨、温室效应、植被破坏、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环境危机、生态破坏等问题犹如人间瘟疫,历史与现实中鲜为人知的事例不断告诫我们在发展的同时不得不考虑、解决环境问题[1]33-40。正如恩格斯所告诫我们不要过分沉溺于对自然的征服,我们每一次胜利自然都对我们有过报复。我们已经进入了环境时代,解决环境问题将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于中国而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对于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所需的物质基础还是远远不够的。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仍然是发展经济,然而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党的十七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布局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建设;十八大指出应该突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把生态文明建设融进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的各领域和各方面,建设美丽中国。
在此社会语境下,研究苗族理词的生态伦理法治思想,对于建设美丽苗疆甚至于美丽中国都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具体而言,苗族理词的生态伦理法治思想包括代际公平、相生相克与心存敬畏三个角度,下文将详细论述。
一、代际公平:苗族理词之灵魂不灭
苗族无文字,苗族理词的传承依靠口耳相传。在苗族理词序贾篇中写道:“弹墨线才造成屋,懂贾理才做成人”;“汉族不离书,苗家不离贾”;“传《贾》勿丢失,承理勿遗忘,牢如身上瘤,固如肉中刺,跌倒也不掉,至死也不落”;“施饵自岸上,获鱼于水中;施《贾》于人心,获益于社会”[2]2-9。
从上述贾理的叙述中,我们不难发现,苗族虽然没有文字版本的法律,却有口耳相传的贾理。换而言之,贾理有如苗族宪法一样规约着苗族民众的日常生活:苗族贾理像弹墨线一样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人懂得做人的道理;维护整个苗疆的社会秩序与和谐,所以贾理又称为道理歌。这些贾理在苗族人民身上如身上瘤、肉中刺一样深刻,这对于塑造苗族人民的群体心理、行为模式、价值观念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从上述论述更可以看出苗族理词强调传承的重要性,具有数典不忘祖的特质。苗族文化中认为先人虽然去世,但是灵魂不灭,强调要继承和发扬祖先的智慧和法则。如贾序篇中说道:“今天咋循祖先经典,遵行祖先范例。随母足跟走,循父指尖行。”[2]586表明了先人的垂范作用。
正是因为敬祖尊祖的影响,苗族理词在丧葬仪式中大量运用。在丧葬仪式中,苗族文化认为人去世之后,苗族巫师要将其灵魂与先人相聚,这说明代际之间在阳间的分离只是暂时的,必然将在另外一个世界相聚,故而生前所作所为应该无愧于祖先,无愧于后人。正是“江山是主千年在,人在世上如过客”的生命伦理,故而苗族认为死亡仅仅是肉体生命的终止,其灵魂生命不灭,既要认祖归宗,又要庇护后人。正是因为将个体生命视为生生不息的生命链,故而传统苗区没有挥霍性地掠夺资源为个人所用,其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则举行周期性的祭拜祭祀活动。外族人言及苗族社区“有强弱无贵贱,有众寡无贵贱”,虽然不是世外桃源,但长幼有序、众生和谐,这些对生态环境意识的自觉显然有着有较大的借鉴作用。
今天,随着布兰特伦夫人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认可,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代际公平的问题,苗族贾理为我们处理代际公平提供了强有力的个案。
二、相克相生:苗族理词之生命共处
我国的法律部门的划分以调整的社会关系类型和调整方法为标准,现行法分为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和诉讼法与非诉讼程序法七个法律部门组成,由这些法律部门组成我国的法律体系。2011年3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中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党的十五大提出的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如期实现。”[3]
纵观我国现行法我们发现,这里所称的法律指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体系,而没有包括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规范。苗族理词既调整社会关系,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由当时特定的社会物质生产条件所决定,区别于人类中心主义指导下的工业文明的法律体系,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有着十分丰富的时代价值。
在苗族理词的叙述中,体现了事物相克相生的思想,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如苗族理词《创世篇》中的宝瑙妈妈迎风受孕,生下十二蛋,然后询问各种动植物如何生育孩子。“请岩鹰来抱,托山鹄来孵,岩鹰就开口,山鹄就出言……要点牛工钱,要点马工钱”。“宝瑙妈妈讲,宝月妈妈说……冷季留咱用,暖季你再要”[2]。宝瑙妈妈所生的十二个蛋也包括了人、动物、植物、疾病和鬼神。从这些理词中体现了万物相生相克,以此来维护生态平衡,体现出了苗族先民的生态智慧。
苗族理老(lix lux)为人们定纷止争。处理人们纠纷的寨头理老既可以是律师,也可以是法官,而他们处理争议的根据即苗族理词。理老正是这些理词进行口耳相传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他们不是通过选举产生,而是由威望较高的人担任。苗族理老处理纠纷的案件理词较多,并且各个地方的也有差别。年代较为久远而有比较典型事物相克相生的案件包括“蛇和蛙”、““牛和虎”、“猪和狗”、“杨梅树和竹”。鉴于苗族贾理不同于现行国家法律的条款式规定,更多地以寓教于乐的故事为载体,故而下文列举几个较有典型的案例故事。
苗族理词案件篇“蛇与蛙”:青蛙以和蛇用鼓的时节不同特向蛇借鼓。用鼓上瘾之后不想归还,决定把鼓砍成三个吞进肚子,于是谎称被盗。当三月春耕生产时节,蛇听到吹敲鼓响彻大地,因此气急败坏,发誓遇见青蛙就要吞食之。青蛙却说我子孙上千,你吃不完。青蛙齐鸣,似万鼓齐敲,响彻天地,故民间把青蛙看作鼓神,在苗疆出土的许多铜鼓有青蛙的造型。
“牛和虎”理词:水牛在早晨出生,水牛是大哥。用来为人犁田拉耙,来养父母儿孙。老虎在夜里出生,他是小弟。虎笑牛身魁力猛,踩岭岭抖,行坡坡崩,却要为人犁田拉耙。牛回答说我为人犁田拉耙本为神仙所定,枉你身魁力大,用你来穿鼻子犁田。结果虎犁田失败,鞭子打烂了虎皮,因此形成了斑纹。犁拖差点断,虎最后不得不逃回山岭。牛笑了老虎的态,笑掉了牙齿,因此牛的上前牙是没有的。
“猪和狗”理词:猪和狗都来到人的家里都想吃饭,不想喝糠。人说谁开垦田勤快谁就能吃饭,猪勤快地去了,回来要求吃饭。一直睡觉的狗趁机在田里踩满了自己的脚印,也要求吃饭。人无奈只好相约第二天早上去确认,最后发现确实是狗的脚印。狗最终得到饭吃,而猪得喝糠。理老出言口封,猪睡圈吃糠而肥,用来发财发福;狗睡门边吃饭不肥,狗还吃猪剩下食物,并用来防盗和驱邪。
“杨梅树和竹”案例:树木和荆棘都为人来当材火煮饭,结果米汤流出烫伤了滑皮榔树(含白浆,有如米汤状,传说因此事而遗留下来),也烫伤了毛竹。杨梅树充当理老来断案,责令树木和荆棘回家,人需要的时候自己来砍。此外为竹子疗骨伤(落下竹节伤痕)后,留其作为自己的助手,共同宣扬贾理,竹也因此被作为贾签理片。
纵观正式出版的苗族理词,我们会发现苗族理词许多案例通过动植物之间的特征和习性来寓理于物。这样的表述既通俗易懂,有利于记忆与传播,同时阐明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生态法则。
十八大提出要建设“美丽中国”,这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号召和促人反思的主题。而在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形势严峻,对这些问题的法律应对需要环境资源生态法联合诸部门法一起发力,即法律体系的生态化。法律体系生态化是指用生态文明的理念和生态学方法指导我国法律体系的发展与建全,把生态文明观和生态文明建设贯彻到我国相关法律制定、修改和健全的全过程。
根据苗族理词已公开发表的案例,以及笔者生活在苗疆的体会,苗族理词“案件篇”实为苗族习惯法,是苗族判例式的习惯法。上述提及的“蛇与蛙”、“牛与虎”、猪与狗”、“杨梅树和竹”等,以动植物之间的特征与习性来阐释人与人纠纷的法律解决规则,这就是运用生态法的典型。
三、心存敬畏:苗族理词之神明裁判
苗族原始宗教包括了宇宙神灵观、万物有灵观、灵魂不灭观。据口传的《苗族理词》叙述:从天上的日月星辰、风云雷电,地上的花草树木、龙虎蛇兔等万事万物都会说话,苗族人民认为他们都是神灵的化身。这些宗教文化体现了对自然环境的“惧感”特征,蕴含了苗族人民对万事万物的敬畏精神。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曾提到与西方罪感文化不同的是日本文化属于耻感文化,两者之不同在于耻辱感文化靠外部的约束力来行善,而不像罪感文化那样靠内心的服罪来行善[4]160。笔者认为苗族文化与这两者既区别又联系,属于惧感文化,它固然包含外部评价之善恶与内心判断之正误,但其实质源于万物有灵的敬畏之感。这一方面是其相对封闭的自治格局,另一方面与其长期以来重鬼尚巫的传统息息相关。
惧感文化与之相应的是神治思想。与礼治和法治不同的是,苗族社会虽然具有理老、议榔和鼓社的礼治传统,但由于没有相应的军队、国家等法治实施手段,上述提到的苗族社会的三大支柱其实没有国家的权力来推行和实施,故而苗族的最高裁决方式是神判即沈从文所言:“地方统治者分数种,最上者为天神,其次为官,又其次才为村长同执行巫术的神的祀奉者”;“这原因只是那边为皇帝所管,我们这边却归天王所管……我们这里多少事皆由神来很公正的支配,神的意思从不会和皇帝相同的。”[5]107
传统的苗族社区尤其是苗疆腹地,苗族理词的裁决虽然也起着法律判决的作用,但假如对方不服,其最高判决取决于神判。正是因为苗族社会由于惧感文化带来的神判裁决方式,这也是众多巫师或理老吟诵苗族理词的原因。理老在重大疑难案件中,经过裁决双方当事人不服或者案件无法查明事实真相,这时往往经过神明裁判的方式结案。
典型的案例如中部方言区的《烫粑理词》和东部方言区的《喝血酒词》,这两个地方的神明裁判具有区别又有联系。其中《烫粑理词》叙述原告被盗,被告认为纯属诬陷。由于双方坚持不下,只好用神明裁判来解决:“各方各包粑,粽子四斤米,同入一锅煮,看谁的粽子熟,看谁的粽子生;谁的熟谁胜,谁的生谁负”[2]。而在东部方言区中的《喝血酒词》,当无法查清事实时也是诉诸于神明,但是血酒词咒得太凄惨,双方当事人往往听从理老的劝解而不再喝血酒,理亏方往往也会自行招认。《喝血酒词》中说:“这个要喝血酒的,如果他是个真正的人,假如他是一个憨汉子,他是不沾不应誓,他是不受罚受惩的;假如他是个心肠歪曲的话,他喝了血酒誓,他就会断子绝孙,他喝了血酒誓,他就会死尽死绝,他就会死得精光,死得一个不剩,死得一个留。”[6]153这些神明裁判虽然属于迷信,但是苗族人民尚鬼崇巫,因此往往具有强制力,当事人因此作出相应的让步。这些对未知事物的敬畏精神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时至今天,工业文明把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我们发现人类中心主义的人定胜天的思想在解放人性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我们无法完全认清整个生态系统的规律。在苗区如今也受到工业文明的冲击,这对苗疆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实践中,宗教文化的影响力在逐步弱化,但是还将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这种宗教惧感文化与如今提出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人与天调理念不谋而合。因此,这种宗教惧感文化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人类文明发展史大致经过了十几万年的悠久的原始文明,几千年的漫长农业文明,几百年的工业文明和当今的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和谐双赢的文明。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包括非常丰富的内容和任务,涉及诸多的部门学科和工作领域,其中生态伦理和生态法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领域。苗族理词为苗疆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利用的伦理法治资源。换而言之,我们在吸收传统儒家的礼治思想和西方的法制思想的基础上,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有地方性知识的加入,只有立足于古今中外并纳入本土性文化的兼收并蓄,才能构筑神治、礼治、法治三江并流的多元文化。
结语
生态系统具有区域性,而这些区域性不同于行政区划。在我国西南喀斯特地貌的苗疆中形成的苗族理词,对生态文明的建设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对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苗族地区的影响远远不如苗族理词的影响力。苗族理词深入人心,融入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泛泛地期望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来谈全国范围内的生态文明建设,在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家现代化的战略思想、作为系统工程的建设的今天是远远不够的。
在乡土社会中,国家法之外还存在着活生生的社会规范,就如我们苗族理词中的习惯法,这些规范无时无刻影响着人们的行为[7]12-14。研究这种习惯法对于生态法治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符合了法律人类学和法律社会学家的观点。使得我们的研究把目光从静态的法转向了动态的“活法”,从立法层面转向了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
[1]陈泉生.环境法学基本理论[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
[2]王凤刚.苗族理词[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
[3]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03-10/2895965.shtml
[4]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
[5]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七卷·凤子[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
[6]石如金.湘西苗族理词[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
[7]胡卫东.黔东南苗族山林保护习惯法研究[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