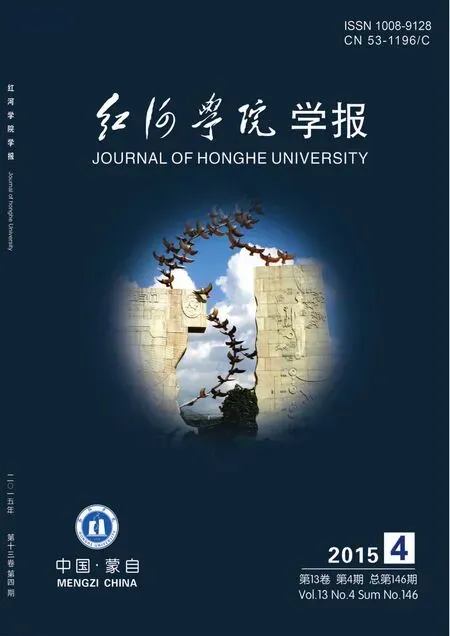《水云》:一种符号学研究
2015-03-28刘文涛
刘文涛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昆明 650000)
《水云》研究,是沈从文研究中的异类,很多研究者都试图去揣摩作品的内涵,试图为研究沈从文及其创作的《八骏图》、《边城》、《长河》等小说找到钥匙。金介甫认为《水云》是“沈从文婚外恋情作品”,[1]大多作者从沈从文对生命的认知去研究《水云》,还有通过它来研究沈从文的创作模式的。笔者认为,《水云》在某种程度上是沈从文对自我的认知,是对人生的态度。《水云》中提到的“偶然”与“情感”、人与神、生命与死亡、近乎于白日梦的幻想以及“水云”这个题目,如果放在符号学的视野中来考察,或可以明晰《水云》之于沈从文的重要性。
一 “水云”的符号信息
阅读《水云》,最深切的感受便是某种未知的因素在偶然间出现,却改变着一个人的人生轨迹。符号是有意义的,“意义就是一个符号可以被另外的符号解释的潜力,解释就是意义的实现。”[2]“水云”作为一个语言文字符号,肯定是可以解释的。
水,无形、无相。有时静若处子,有时动若脱兔。因形赋形,外在给予它什么,它便是什么,可以说随遇而安,也可以说受困于己,没有选择的余地。云,其成分主要是水,但是却又与水相差甚远,它靠风而动,姿态变化万千,没有人会知道下一秒云是什么样子。“水云”,若指示的是某种物,便是统一的,相伴而生的,但这个事物却又传达着某种不确定,预示着某种偶然。从文本的写作来看,作者用了两万字的篇幅,以时间为线索,展示了日常生活的某些侧面,小到草丛中的野兔大到自我分裂的人生对话,看似必然,其实都是偶然得之。
“水云”作为符号传递的信息,副标题“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或也可以作为它的解释项。作者在文中提到,关于小说《八骏图》、《月下小景》、《花城》、《长河》的创作,都是偶然得之,或是因为人生的叹息,或是因为想要留住美好,都是生活推着他去写作,不过必须加入抒情(情感)罢了。他也曾说过,文学等等“其本质不过是一种抒情”[3]12。作者是怎么创造故事的?或可以说“偶然”+“情感”创造了故事。反过来,是不是说“偶然”+“情感”创造了“我”呢?答案是肯定的。作者作品中所描述的日常生活是那么自然,但都不是刻意追求刻意为之的,而是自然自在,顺其自然的。笔者在这里以一种推理的方式填补了副标题的空缺,是与上文对于“水云”的解释相通的。这也就是说,整个文章的题目,解决了作者的人生轨迹变化的问题。分析“水云”这个符号,便不难看出作者在文章中所要表达的意思。
二 非标出项:“偶然”与“情感”
文本中叙述了自我的分裂,一个是“对生命有计划对理性有信心的我”,一个是“宿命论不可知论的我”[4]271,那个宿命论者说“我们生活中到处是‘偶然’,生命中还有比理性更具势力的‘情感’。一个人的一生更可以说即由偶然和情感乘除得来。”[4]267纵观整个文本,可以发现,作者的行文都是围绕生命中的“偶然”和“情感”展开的。笔者认为,可以把“偶然”与“情感”作为整个语言文字文本的非标出项来看待,与文本的所有文字符号进行比较。笔者发现,“偶然”与“情感”在文本中出现的频次最高。非标出项是指在符号系统中“对立的使用较为多的那一项,……就是正常项”[2]279。对于研究文学文本的研究者来说,更愿意去研究标出项,也就是出现次数较少的一项,因为它更有可能反应作者的真实意图。但是对于《水云》而言,非标出项才是更接近作者真实意图的符号项。
非标出项属于正常范畴,也就是说属于意料之中的符号。但是笔者认为,在《水云》中,或可以扩大范围来比较,它同沈从文其他的作品有着很明显的差异。它的叙述方式,人格分裂式的哲学思辨性质的对话写作形式,都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偶然”与“情感”这对非标出项的符号价值。文本中,那个宿命论者说:“(偶然)名字有点俗气,但你并不讨厌它,因为它比虹和星还固定性,它无再现性。它过身,留下一点什么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的心上;它消失,当真就消失了,除了留在心上那个痕迹,说不定从此就永远消失了。这消失也不会使人悲观,为的是它曾经活在你心上过,并且到处是偶然。”[4]268宿命论在这里并不迷信,“偶然”构成了整个文章最具魅力的一部分,偶然之间遇到的事,便可以下笔写成文章,这篇《水云》想必也是作者偶然得之。生活在偶然之中,人就不用过多承担外界符号给与个体的修饰,活得就更加自然。“人的符号活动越多,物理实在的范畴似乎也就相应变得缩减” ,[5]如果人的身上布满了符号,人是否还是人就需要打上一个问号。在“偶然”之中的人,是自在的,安静的,是真实的。
情感是与理性相对的。理性的人,有着自己对于世界的一套既定标准,不论做什么事都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有计划,有信心,缜密的思维使得他们生活过于单调。而情感,是个体的本能,它出于个体在生活中的经验,是要做什么必定能做什么,是对美的认知。“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些!丑的东西虽不是罪恶,可是总不能令人愉快。”[4]276情感需要积累,同时也需要释放。针对理性的宣战,分裂的我似乎更倾向情感。文中叙述的名叫“偶然”的女子,不正是一种情感的自然表达么!因为有情,所以沈从文说:“事实上如把知识分子见于文字、形于语言的一部分表现,当作一种‘抒情’看待,问题就简单多了。”[3]13也因为有情,才能使作者在文章的书写中感情平稳而且文字表述细腻,虽然看似琐碎,但却能打动读者,传达出自己的意图。
“偶然”和“情感”作为这篇语言文字文本的非标出项,其重要性不是在于他们出现的次数较多,而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传递了作者写作文本时所要传达的真正意图意义,也能使接收者在解释过程中更加便利,但又能一语中的。
三 刺点:安静与思辨
刺点这一概念,是巴尔特在分析摄影的专著《明室》中首次提到的。它指的是:“一个‘细节’,即一件东西的局部,并非有意为之。”[6]符号学在讨论众多符号中比较特别且有重要作用的符号项时借用了这一概念。在庞杂的符号系统中,接收者要找出解释发出者意图的符号并不是手到擒来的,必须依靠个体以及外在因素的帮助,才可以完成。与刺点相伴的常常是意趣,也就是能使接受者感到愉悦的事物。
在整个文本中,从作者叙述的节奏来看,是舒缓的,感觉不到太多节奏比较强的叙述,就如同湖面的水体,明知道它有入口和出口,但是感觉却是安静的,平和的。作者在文章中写到春游,便是一种极安静的表达。他远离了能够欣赏樱花的地方,来到一个很少有人迹到达的所在,意外地看到了草丛中的野兔。他能靠在树下远眺大海,也能凝神注视来来往往的行人。在这种极安静的环境中,分裂的自我便开始了思辨性的辩论。起先,有计划有信心的那个“我”颇有气势,他认为人生必定是有计划的,人必须要有信心,有理想,那样才能完成一些事,给后人留下可供参考的东西。但是宿命论的“我”不这样认为,他觉得,人生是偶然与情感的乘除,越是刻意去做,越得不到,千千万万个偶然塑造了完整的自我。这种具有哲理色彩的对话,若不是有一个安静的环境,恐怕很难发生。
第二次,分裂的自我的对话,是“我”独自在“一列梧桐树下散布,太阳光从梧桐大叶空隙间滤过,光影印在地面上,纵横交错,俨若有所契,有所悟,只觉得生命和一切都交互溶解在光影中。”[4]272这样的环境,营造了让人开悟的氛围,于是,思辨性的声音又跑了出来。这次他们依旧在讨论偶然和情感,不过更偏重情感。结果却不了了之。“这似乎太空虚了点,正像一个人在抽象中游泳,这样游来游去,自然不会到达那个理想或事实边际。”[4]274辩论的结果似乎使作者不满意,他似乎更倾向于偶然,但却被理性占了上风。一个名叫“偶然”的女人被叙述,虽可以看出暧昧,但在叙述中却并不显紧张,还是依旧比较平稳。而后,当我每天早晨在院落中写作的时候,分裂的自我又出现了,这一次,讨论的问题更具思辨性、哲理性。生命、命运都来了,人也成为了讨论的重点。那个宿命论者说“你打量用这些容易破碎的东西稳定平衡你奔放的生命,到头还是毫无结果”[4]281生命到底是什么,人到底是什么?
最后,平稳的叙述中,安静的环境里,思辨达到了高潮,那就是“人”。用人教育我,教育的是自己。偶然和情感安排了人的一生,但是到头来我们接触的还是人,在偌大的繁华世界中,人在教育我。这里的人与其说是外部的无关紧要的人,不如说是“我”在感受了“偶然”之后的开悟。这种状况把“我”带到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境地,以至于最后的发问:“我关心的是一株杏花还是几个人?是几个在过去生命中发生影响的人,还是另外更多数未来的生存方式?”时,竟出现了“没有回答”[4]298这样的尴尬。这是“我”不愿看见的,可是讨论就这样戛然而止,叙述也到这里停止,留给接收者许多疑问。笔者认为,这样的戛然而止,正是文章的魅力所在,前文的叙述是那么明晰,留给接受者的不过是一个有答案的疑问而已。
笔者在这里讨论刺点:安静与思辨。实则是想通过这样一个符号学的概念,来展示沈从文在叙述过程中对于生命、对于人的思考,这种思考在他创作的很多作品中都有所表现。而在《水云》中,他把这种思考独立了出来,走得更远。
四 符号溢满:人与生命
作为语言文字文本,文字承载着符号的意义。在众多的文字中,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值得研究的,必须靠接收者去发现。在一篇语言文字文本中,符号溢满成为可能。而《水云》作为一篇相当有特色且具有很大研究价值的文章,其中充斥着的符号便也很多。所谓符号溢满,指的是在符号体系中,有某一种符号特别多,并且不断出现。这时候,这种符号就像水杯中的水一样,溢出来,被接受者所大量掌握。符号溢满是不动声色的,它在符号传达意义的过程中自然生发,只有接收者才能把它变得有意义。如果这种符号不被接受,那它所具有的溢满性也得不到充分的认知。
沈从文的文章,不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在写人,人是他最为看重的。《水云》中叙述人,并不刻意,舒缓的叙述节奏之下,人的天性被一次次提及。“但觉人生百年长勤。所得于物虽不少,所得于己实不多。”[4]274这是在分裂的自我讨论完情感的话题之后,叙述者所说的话。当叙述者看到看樱花的人往来不息,一起用餐的小姐实为大上海的产物,每个人都在为别人而生活,外在的符号附加于个人的意义过多时,人便不再拥有人的天性,活着只是为了满足他人的眼光。
“我懂得‘人’多了一些,懂得自己也多了些。”是什么让沈从文有了这样的变化?通过叙述,应该是名叫“偶然”的女子,以及生活中遇到的种种事情,使他认识了“人”,也渐渐认识了自己。他说:“在‘偶然’之一过去所以自处的‘安全’方式上,我发现了节制的美丽。在另外一个‘偶然’目前所以自见的‘忘我’方式上,我又发现了忠诚的美丽。在第三个‘偶然’所希望于未来‘谨慎’方式上,我还发现了谦退中包含勇气与明智的美丽。”[4]287这是怎样的情怀,偶然构筑了我的世界,我用他们来思考我自己。人,实质上就是在不断地失去中总结自己,缺点也好,优点也罢,在种种经验中便慢慢地认识了自己。
“若想在让人生命中保有‘神’的势力,即得牺牲自己一切‘人’的理想。若希望证实‘人’的理想,即必须放弃当前唯‘神’方能得到一切。”[4]291人与神,神与人,哪个更可贵?笔者认为,人最可贵。不论是当人当神,前提是首先得是个“人”。人所具有的天性,是要用美来激发的,成就人的是人自己,毁灭人的也是其自身。在叙述的过程中,沈从文从头到尾都在强调人的无限性,不论这个人是理性的还是宿命论者,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认识人,本身就是困难的,但是只有认识人,才能认识自己。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充斥着符号的所在,在沈从文的时代,战争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但文章中却丝毫没有用过多地笔墨去表现,而是以一种平稳的叙述凸显了人,也使得对人的思考充溢着整个文本。
五 结语
皮尔斯说:“每一个思想是一个符号,而生命是思想的系列,把这两个事实联系起来,人用的词或符号就是人自身。”[2]4沈从文在《水云》中所展示的正印证了皮尔斯的话。他用每一个语言文字符号来诠释自我对于人生的看法,偶然与情感创造着他,同时也创造了他的故事。而他似乎就是一个较少与外部符号世界相关联的个体,这种微关联性使他对生命和人有了自我独到的见解。笔者在这里用符号学的若干概念与文本中的几个关键词相联系,来论述《水云》这篇独具色彩而且颇有争议的文本,未免有些以偏概全,但也是一种思路,同时也获得了沈从文在这篇文章中想要表达的若干意义。
[1]金介甫.沈从文传[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248.
[2]赵毅衡.符号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2.
[3]沈从文.沈从文别集:抽象的抒情[M].长沙:岳麓书社,1992.
[4]沈从文.水云[M]//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十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
[5]卡西尔.人论[M].李琛,译.北京:光明时报出版社,2009:025.
[6][法]罗兰.巴尔特.罗兰.巴尔特文集[M].赵克非,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