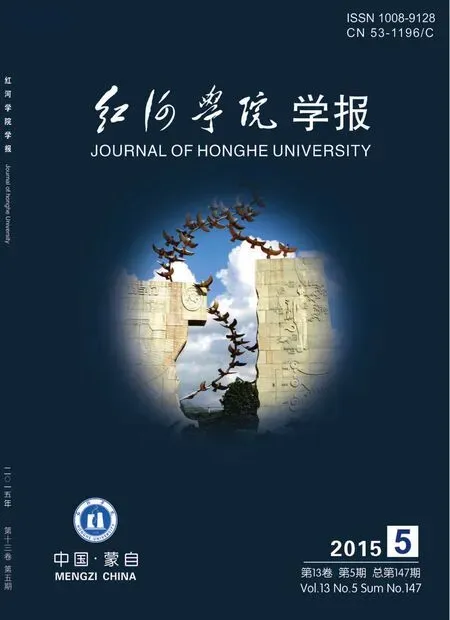普洱茶的社会生命史及其意义研究
2015-03-28马祯
马祯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081)
普洱茶的社会生命史及其意义研究
马祯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081)
“物的社会生命”是认识物及其社会文化意义的有力视角。该篇通过梳理历史资料和相关文献,为普洱茶书写社会生命史。文章认为普洱茶经历了从明朝以前的“异类茶”转变为清朝贡茶,并在清朝之后经半个多世纪的沉寂再商品化的生命历程。在这个过程中,普洱茶的生命与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密切相关,体现了物的社会意义。
普洱茶;物的社会生命;贡品;商品
引言
普洱茶产于云南,是傣族、哈尼族、布朗族、拉枯族、德昂族、佤族等民族栽培、使用、交易的茶叶品种。早在唐朝时,普洱茶就成为民间交易的商品,但在相关文献记载中,普洱茶被理解为“茶中异类”,其品质并没得到认可。随着民间交易的不断扩大,普洱茶在明朝时期逐渐得到肯定,并在清朝雍正年间成为贡茶。之后,普洱茶具有了双重身份:它一方面是王朝纳贡体系中的贡品,另一方面是市场交易中的商品。清朝灭亡后,纳贡体系随之崩溃,普洱茶由贡品和商品的双重身份变成商品,但它的流通只限于对普洱茶有特殊需求的藏区、香港和台湾。直到20世纪90年代,普洱茶以“能喝的古董”、“原生态”、“减肥茶”等多重标签再次进入市场,掀起一股饮普洱之风,并持续到现在。
将普洱茶作为一种“物”来理解,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物的社会生命史”视角提供了有效的分析路径。阿帕杜萊在《物的社会生命——文化视野中的商品》中,认为物与人一样具有社会生命。物的生命指的是物经历商品化、去商品化,甚至循环往复的过程。阿帕杜萊将物从“无活力、沉寂的”[1]4西方式理解中解救出来,将其视为本身具有生命的存在,讨论物在生命历程中呈现出的不同生命形态。通过对物的制作、流动、使用的讨论,串联不同的空间、时间和人群。因此,书写特定物的生命史,不仅可以理解物及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流通,还可以理解社会文化,即以“物的生命史”[1]64为社会文化作传。
纵观普洱茶的历史,它经历了多重身份的转变,蕴含着丰富的历史过程。正如余舜德所言“少有其他物品如普洱茶经历如此丰富的社会生命史”。[2]365普洱茶多重身份转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与政治、经济和文化有何关系?社会有何意义?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且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可以理解普洱茶本身,还有益于理解它负载之上的社会历史和现实。本文运用阿帕杜萊“物的社会生命”的视角,通过梳理汉文典籍中的普洱茶,在论述它从“茶中异类”到贡茶;从作为认识边疆“蛮夷”风俗的媒介到具有自身主体性,以及近年来对普洱茶的再次商品化,讨论它在历史语境中的演变,及背后的社会文化逻辑。
一 从茶中异类到普茶
对物的意义、物的用途及其生命轨迹的理解,要通过追寻物的历史性流通来实现。[1]5在明代以前的历史文献中,普洱茶经历了从茶中异类到普茶的演变,名称的确立也是普洱茶本身价值凸显的过程。它从最初作为说明西南夷风俗的“脚注”,变成具有独立价值的物。
(一)明以前的异类云南茶
对普洱茶的记载散见于历史文献中。明朝以前,关于普洱茶的记载与云南少数民族联系在一起。出产、交换普洱茶的社会与这一物本身被相互界定。由于中央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表述带有歧视性,因此普洱茶也脱不了“蛮”气,是茶中异类。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茶在史书中出现很早,唐人樊绰在《蛮书》中写道:“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3]
宋朝李石所著《续博物志》第七卷中也有类似的记载。[4]“银生城”指的是南诏所设“开南银生节度”管辖的区域。银生是当时节度使驻地之一,管辖范围相当广泛。“银生城管辖的范围还有奉逸城和利润城,奉逸城在普洱县,而利润城在今天勐腊县的易武乡。”[5]305从地名的梳理中可以看出,银生城指的是今天普洱市和西双版纳地区,“银生城界诸山”就是普洱市和西双版纳境内的各大茶山,即如今普洱茶的主要产区。这些地区主要是傣族、哈尼族、布朗族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历史上西南诸族属“蛮夷”,因而其地所产的茶也与中原地区大不相同。不仅缺乏茶叶制作上的“采造法”,从其使用方式来看,它更像一种蔬菜,并不具有茶的物质属性。
明朝谢肇淛在《滇略》中写道:“土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6]这是“普茶”第一次出现在历史文献中,对此,历史学家林超民也有相同的看法。[5]305但是,谢肇淛对“普茶”的评价十分负面。谢肇淛认为:“滇苦无茗,非其地不产也,土人不得採取制造之方,即成而不知烹淪之節,犹无茗也。”[6]在他眼中,滇茶由于太苦、且制作方法不当,品质好的又太贵,以致“滇苦无茗。”土庶所用的普茶也是“淪作草气,差胜饮水耳”。[6]从以上这些文献中可以看出,云南茶品质低劣,喝云南茶还不如喝水。而且,文献中的云南茶与少数民族的形象结伴出现。普洱茶本身并不具有物质独立性。它彰显的是云南诸民族生产、生活、交易风俗,是文化的注释。在此意义上,云南茶是外界认识产地社会的媒介物,不具有独立的价值与重要性。
(二)普茶与其价值的凸显
方以智的《物理小识》第一次提到“普洱茶”:“普洱茶,蒸之成团,西蕃市之,最能化物,与六安同。”[7]138方以智不仅介绍了普洱茶的消食作用,还介绍了普洱茶的贸易地点,并将其与六安茶做了对比。这是对普洱茶的第一次积极评价。方以智肯定了普洱茶的化食效果,使普洱茶作为茶的物质意义得以显现。从他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普茶在明代无论对于滇人的日常生活,还是贸易,都十分重要。普洱茶从地方性的食物变成被交换的商品。文献对它的描述渐渐从产地社会剥离,成为具有自身价值的物,普洱茶这一名称也逐渐得以确立。
伴随着名称的确立,普洱茶的特性被细化,这对于普洱茶在历史中凸显自身价值具有特殊意义。普洱茶作为被描述的主体出现在文献中。吴大勋在《滇南见闻录》中有“其茶能消食理气,去积滞,散风寒,最为有益之物。煎熬饮之,味极浓厚,较他茶为独胜。”[8]36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中有写道:“普洱茶味苦性刻,解油腻牛羊毒,虚人禁用。苦涩,逐痰下气,刮肠通泄。……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犹大也。”[9]205由于其自身的特色,此时的普洱茶还被当做一种药物来使用,其意义经超出了产地社会的风俗,成为具有多重效用的有益之物。
二 普洱茶的贡品、商品身份及其变迁
(一)普洱茶的商品、贡品身份
早在元代,云南茶就是物物交换中的商品,但此时交易范围较小。李京的《云南志略诸夷风俗》中说“金齿、白夷(指傣族),交易五日一集,以毡、布、盐、茶互相贸易。”[8]129清朝时期,普洱茶贸易频繁,并最终确立了其商品与贡品的双重身份。普洱茶作为一种物,本身的重要性在此时得以彰显。作为商品的普洱茶在特征上被严格细分。如张泓的《滇南新语》:“普茶珍品。则有毛尖、芽茶、女儿之号。毛尖即雨前采者,不作团,味淡香如荷。新叶嫩绿可爱。芽茶较毛尖壮。采制成团。以二两四两为率。滇人重之。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前后。以一斤至十斤为一团,其余粗普叶。皆散卖滇中。最粗者熬膏成饼模印。”[10]141对于普洱茶的分类描述是探究它物性的过程,这种物性是普洱茶作为商品被细化的结果。广泛的贸易使普洱茶名扬天下:“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11]10。随着普洱茶的物性被逐渐发掘,它美名远播,最终成为清朝皇室贡茶。
普洱茶成为贡茶的确切时间已无法考证,但至迟为公元1659年。[12]175成为贡茶之后,普洱茶的价值生成有了政治的参与。由于物的价值政治在很多时候就是知识的政治。[1]6因而文献记载作为一种知识的生成,对普洱茶的描述也越来越具体和详细。《光绪普洱府志稿》卷十九食货志六中记载:“茶有六山,倚邦、架布、熠岭、曼砖、革登、易武……气味随土性而异,生于赤土或土中杂石者最佳,消食散寒解毒。于二月间采蕊极细而白,谓之毛尖,以作贡,贡后方许民间贩卖。采而蒸之,揉为圆饼。其叶之少放而嫩者,名芽茶。”[13]从中可以看出,此时的普洱茶不仅是商品,还是贡品。普洱茶的商品和贡品双重身份,是在同一历史时期其在社会生活中不同位置的显现。
(二)普洱茶的去贡品化和再商品化
清朝时期,普洱茶贡品和商品的双重身份具有政治和经济意义。清朝末期国力衰退,纳贡体系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崩溃,普洱茶的贡品身份消失。由于政权动荡,外敌入侵,茶叶贸易也因此受到严重影响。虽然民间普洱茶交易在民国时期依旧继续,
但大部分产区处于“满山茶树头光光,茶农茶工泪汪汪,两手空空无出路,卖儿鬻女去逃荒”[12]173的景象。新中国成立之后,普洱茶在公社化运动、以粮为纲等社会运动中又遭到破坏。一直到1973年以前,云南发展红茶和烘青绿茶,普洱茶很少被提及。
普洱茶的再商品化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以台湾为地理中心,以商人、文艺界人士、学术团体为主导。这一过程是对历史和知识的运作。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收藏在香港和台湾的一些陈年普洱茶被发现,并在两地得到极大追捧。1988年12月13日到1989年1月1日,台湾茶艺观光团来到昆明植物研究所,意在调查云南是否还在生产普洱茶。研究所的生物学家说他们没有听说过普洱茶,即使历史上有,现在也不存在了。[14]109-131台湾考察团接着到了六大茶山地区,他们发现在这些地区,普洱茶依旧还被种植,且在六大茶山留存着很多古茶树。台湾和香港对于普洱茶的追捧使云南重新重视普洱茶。1989年,云南“云茶苑”茶艺表演队在北京参加“中国首届茶与文化展示周”。“云茶苑”的茶艺表演轰动京城,云茶第一次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12]185从此,普洱茶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被再商品化。
在赋予普洱茶新的意义时,正如阿帕杜萊所讨论的,“较长的社会历史造就了在较短时期内物的轨迹、意义以及结构。”[1]36普洱茶的再商品化,正是以追寻历史上它的贡品、商品身份开始的。对普洱茶历史的回顾包括两个方面:(1)梳理普洱茶的历史以建构其贡茶身份;(2)探寻古茶树并以确立树龄的方式彰显其历史悠久性。1988年11月,《版纳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西双版纳茶叶专辑)》中收集了普洱茶历史文献。此后,关于普洱茶历史的著作和文章大量涌现。这些文献借用历史语境强调其独一无二性。与梳理历史同步的是普洱茶研究学术会议的不断召开,如1993年、1994年、2001年国际茶文化研讨会,以及每一次学术会议之后,与会专家进行的普洱古树考察、膜拜活动。[12]187以上这些建构行为经过媒体传递,再加上对普洱茶抗癌、降低血压、减肥等效果的宣传,普洱的知识体系被迅速建构起来。同时,由于从民国时期到1990年代,普洱茶的沉寂造成市场和社会对普洱茶知之甚少。学者、媒体、市场建构的知识很快被大众吸收,“知识和无知之间形成的张力是商品流通的一个决定性因素。”[1]41普洱茶被成功商品化。
三 普洱茶社会生命的意义
普洱茶成为皇室贡茶,是政治介入物的价值生成过程的体现。物的消费成为社会控制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通过以政治手段对物的流通进行限制性规定来实现。[1]22两种身份的叠加,体现着普洱茶社会生命的内涵:作为贡品,它反应了清朝以物为媒介,在朝贡体系中加强中央与地方社会联系的实际行为;作为商品,它反应着中央王朝通过物对其产地和消费地的管控。普洱茶在1990年之后被再次商品化,则是历史话语和知识建构的结果,作为商品的普洱茶在现代社会是多重标签的叠加。
(一)普洱茶作为贡品的意义
成为贡茶之后,清政府对普洱茶的采摘、形制、规格等都做了严格的规定。贡茶普洱在此意义上脱离了流通领域,其主要功能是皇家“保证其用品的独一无二性”。[1]22实质是物的“去商品化”过程。恰恰是这一过程,使得普洱茶最终具有其自身特性。“干茶每年备贡者,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又瓶盛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共八色。”[11]10又光绪《普洱府志稿》记载:“雍正十三年,题准云南商贩,茶系每七圆为一筒,重四十九两,征收税银三钱二分。”[13]在贡品的制作规格要求下,普洱茶团茶和圆茶(即七子饼茶)的形制被固化,成为普洱茶最鲜明的特征,并延续至今。
成为贡茶之后,普洱茶得到多位皇帝的赏识,反过来又加固了其在社会中的意义。如:乾隆皇帝曾写诗称赞:“唯有普洱号钢坚”。除了乾隆之外,道光、光绪皇帝对普洱茶也有很高的评价,并经常赏赐给后妃、太监、宫女。“在清代宫廷,上至皇帝、皇后、下到宫女,苏拉等杂役都会有一定的宫份茶,这些茶叶通常会以‘月例’或‘年例’的形式发放,宫中使用的普洱茶数量之大,我们可以从例份上看出来。”[15]314-319普洱茶不仅是宫中日常生活的必需,体现着皇帝对于妃子、皇后、太后以及大臣的宠幸程度,它还作为清朝的象征被赐予各国使节,成为权力的象征、关系的媒介。从史料记载来看,清朝时期皇帝定期或不定期赏赐出去的普洱茶数量十分可观。如赏安南国使者五次,五次均赏普洱茶;英国马嘎尔尼使团也得到了乾隆皇帝大量的普洱茶赏赐;此外还有朝鲜国、琉球各藩亲王等。[15]314-319同时,从康熙皇帝开始,朝廷以普洱茶为主体组织大型集会活动。如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年、康熙六十年(公元721年)、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举行的大型的“千叟宴”,参加的人数最多达到五千人。[15]314-319除了大型的千叟宴之外,乾隆八年之后,几乎每年都要举行一次茶会。跻身王朝权力中心的贡品普洱体现着君臣、内外等关系。它已经不仅仅是饮品,
作为礼物与,它是王朝中心关系的纽带、交流的媒介。
(二)普洱茶作为商品的意义
普洱茶在清朝时的鼎盛除了其贡品身份,还与其作为商品的身份相关。清王朝通过加强对普洱茶贸易的管理,不仅使产地与消费地紧密联系,还使中央王朝对二者的管理落实在对物品的管控上。在此基础上,普洱茶成为中央王朝控制地方社会的媒介之一。
雍正七年,即公元1729年,清政府派云南总督鄂尔泰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16]184-233出产普洱茶的地区,成为改土归流政策实施中的重点。光绪《普洱府志》记载,雍正七年在普洱设置了普洱府治。在攸乐山,即今天的基诺山设置“攸乐同知”,驻守军队达到500人之多,其主要目的是防守茶山,征收茶捐。[13]产地社会因普洱茶被进一步纳入王朝贸易管理体系,普洱茶体现着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而且,对普洱茶的贸易管控一直在加强。光绪《普洱府志稿》记载:“于十三年为始,颁给茶引三千饬,发各商行销售办课作为定额、造册题销。”[13]通过规定普洱茶的采摘、制作规格,保证了国家茶叶税收的稳定。同时,管理茶叶的机构成为地方社会的实际管理主体。对普洱茶贸易的管理反过来也塑造了普洱茶本身。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清政府撤销“攸乐同知”,设置“思茅同知”,并在思茅设官茶局,在六大茶山分设官茶子局,负责管理茶叶税和收购,[17]25并设宁洱为普洱府府第所在地。至此,普洱府的行政范围基本确立下来,普洱茶名因此渐渐确定。
普洱茶成为王朝体系中的管理媒介,不仅体现在产地,还体现在对消费地的控制上,如通过边销茶对西藏的控制。《云南省通志稿》卷六十二,食货志四课程《皇朝通志》中记载:“顺治十八年,准达赖喇嘛及根都台吉于北胜州互市,以马易茶。”[18]728藏族商人每年自夏历九月至次年春赶马到丽江领“茶引”,再到普洱购买茶叶,运送回西藏。“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朝廷议准云南茶引,颁发到省,转发丽江府,由该府按月给商赴普洱贩卖,运往鹤庆州之中甸各番夷地方行销,其稽查盘验,由邛塘关金沙江渡口照引查点,按例抽税。其填给部引赴中甸通判衙门呈缴,分季汇报,未填残引,由丽江府年终缴司。”[13]普洱茶贸易制度成为王朝管控西藏的有效手段之一。云南和西藏之间的茶叶贸易在清朝时十分发达,这不仅联系了云南和西藏的文化交流,还使得国家统一。茶叶贸易圈与国家的疆土的密切相关性,也是自明朝以来“以茶制夷”观念的延续。“茶叶慢慢演变成特别供给物资,而不仅仅是茶马贸易的品种,但其作为国家战略物资的属性没有变。”[19]32
普洱茶以贡品、商品形式跨地区、跨文化的流动,对王朝统一具有重要意义。对物的控制成为对地方社会的重要控制手段之一,对物依靠成为人、地域之间的连接。物,成为王朝贯彻其意志的媒介。清朝后期,英国注意到茶叶在藏族人生活中的重要意义,认为只要能控制西藏的茶叶贸易,就会切断西藏与中国其他地区(这里主要指云南和四川)的实际联系。[20]28英国以茶作为侵略手段,想尽一切办法将印度出产的茶叶运送到西藏销售,中国境内的茶叶贸易受到严重的打击。[18]128茶叶的销售地理成为英国权力地理的一部分。茶叶贸易的争夺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国家疆域的争夺。虽然英国人将印度茶卖到了西藏,但因口味不对而遭到西藏人民的拒绝。[21]10-17英国人以茶叶作为入侵西藏的计划最终没有得逞。
(三)普洱茶再商品化的意义
普洱茶的再商品化从台湾开始,进而扩展到香港、广东及产地云南,而至日本、韩国甚至欧美国家,[2]356一股普洱茶风潮在茶叶市场兴起。普洱茶的再商品化是建构历史话语、知识,以及市场运作的结果,主要体现了一下三个方面的意义:(1)普洱茶具有多重标签。它被界定为“原生态”、“能喝的古董”等具有鲜明特征的商品。“原生态”,是指普洱茶生长于云南普洱、西双版纳、临沧、德宏、大理等地区的高山之中。由于社会历史原因,这些地区经济开发较晚,保持了较为传统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出产自这些地区的普洱茶被理解为原生态。“能喝的古董”指的是陈年普洱茶,及保存十几甚至几十年以上的普洱茶其味道更佳。对绿色、生态、奇特、稀少、传统等“特性”的强调,使普洱茶在众多茶品中具有独具特性。(2)在普洱茶商品化过程中,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被标签化,成为远离现代工业污染、“异文化”的代表。产地社会的自然景观、风俗习惯等成为推广和包装普洱茶这一商品的重要因素。最后,普洱茶成为促进产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物。普洱茶品种多样,如台地茶和古树茶、栽培茶和野生茶、普洱茶生茶和熟茶、陈年普洱茶等,它在茶叶市场上的价格也参差不齐,具有很大的商业利润空间,且对随着普洱茶消费市场的不断扩大,政府支持茶农扩大普洱茶种植使产地脱贫致富,普洱茶成为产地社会发展的动力。产地社会因普洱茶而被整合、变迁。“少数民族社会在这一过程中处于传统和现代这一矛盾中”。[22]178-188一方面市场需要清洁、规范的普洱茶,同时又需要普洱茶保持其古老和传统性;一方面,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现代化建设,促进其发展;同时又希望其保持
原有文化特色不变。普洱茶作为一种物,在新的语境下塑造着社会。
结语
普洱茶只是一种饮品,是普通的食物。它因自身的物性以及历史境遇,卷入了政治、市场以及知识的历史洪流中。它代表着复杂的社会形势、价值与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循着普洱茶的历史轨迹,不仅可以理解普洱茶本身,还可以看到物与政治、经济的相互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普洱茶有着不同的社会生命,它表征着明朝以前主流话语对于西南族群的理解;作为贡品和商品,体现着纳贡体系、商品流通、贸易管控中王朝与地方的关系;普洱茶的再商品化过程,体现着知识对商品的意义再造,也反应了物对社会的塑造。如今,普洱茶的标签化,使产地社会在获得经济发展的同时被进一步“他者化”,成为原生态、传统等的代名词。就此意义,本文仅是抛砖引玉。物与社会的互相界定何以成为可能?这一过程对社会有何影响?不同身份的行为者如何体现各自的主体性?对物本身又有何意义?都将是值得深究的话题。
[1]Arjun Appadurai.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2]余舜德.体物入微:物与身体感的研究[C].台北:“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3][唐]樊绰.蛮书[M].武英殿聚珍版原本:卷七·云南管内物产.
[4][宋]李石.续博物志[M].武汉:湖北崇文书局,1875.
[5]林超民.林超民文集:第二卷[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
[6][明]谢肇淛.滇略:卷三[M].四库全书·史部十一,文渊阁本.
[7][明]方以智.物理小识:卷六[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
[8]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十二卷[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9][清]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M].闫志安,肖培新,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
[10][清]张泓.滇南新语[G].边疆史地研究资料文库编委会,边疆史地研究资料文库·边疆史地文献资料初编:第三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11]王美津.普洱茶经典文选[C].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5.
[12]云茶大典编委会.云茶大典[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
[13][清]陈宗海,等.光绪·普洱府志稿[M].(卷十九·食货志六).
[14]Janet C.Sturgeon,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thnic Identity in Xishuangbanna,China:Tea and Rubber as“Cash Crop”and“Commodities”[J].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Vol. 41),2012:109-131.
[15]万秀峰.普洱贡茶在清宫中的使用考述[J].农业考古,2012(5).
[16]黄桂枢.云南普洱茶史与茶文化略考[J].农业考古,1992(2).
[17]张顺高.中国云南普洱茶古茶山文化研究:纪念孔明兴茶1780周年即中国云南普洱茶古茶山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5.
[18]吴觉农.中国地方志茶叶历史资料选辑[C].北京:农业出版社,1990.
[19]周重林,太俊林.茶叶战争——茶叶与天朝的兴衰[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
[20]方国瑜.方国瑜文集:第四辑[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21]陈一石,陈泛舟.滇茶藏销考略[J].西藏研究,1989(3).
[22]Po-Yi Hung,Tea Forest in the Making:Tea production and the ambiguity of modernity on China’s southwest frontier,Geoforum(47),2013:178-188.
[责任编辑张灿邦]
The Social Life of Pu’er Tea
MA Zhen
(College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81,China)
The perspective of"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provides a useful view in understanding the significances of matters in social and culture.This paper,guiding of the theory of"social life of things",to discuss the biography of Pu’er tea on the basis of historical data and related literature.Pu’er tea became tribute tea in Qing dynasty after experiencing a life of"heterogeneous tea"before Ming dynasty,and then became a high-quality product of minorities in Yunnan,Southwest of China.Pu’er tea’s life demonstrates the social meaning of things with its significances of political,economic and cultural in historical periods.
Pu’er tea;social life of things;tribute;goods
C91
A
1008-9128(2015)05-0078-05
2015-01-23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014年中央民族的大学博士研究生自主科研项目(10301-01402902)
马祯(1988-),女,甘肃会宁人,博士生,研究方向:南方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物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