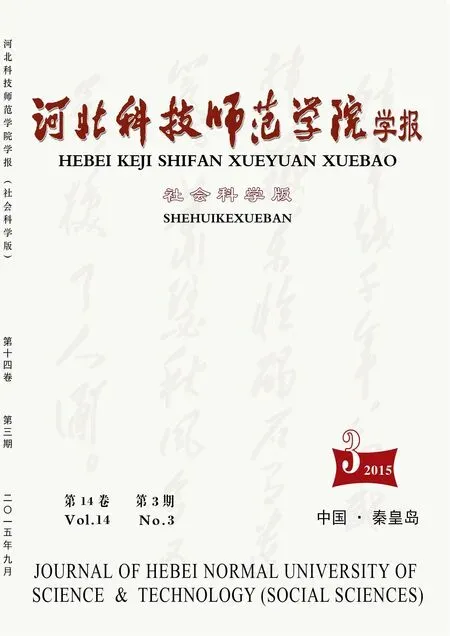从《庄子》析伯夷形象
2015-03-27葛炜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991( 2015) 03-0034-06
DOI:10.3969/j.issn.1672-7991.2015.03.007
收稿日期:2015-04-22
作者简介:葛 炜( 1988-),男,河北省石家庄市人,硕士,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
Analysis on Boyi’s Image in the Analects of Zhuangzi
Ge Wei (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Hebei Normal University,Shijiazhuang Hebei 050024,China)
Abstract:Boyi image in Zhuangzi is disruptive and sophisticated,on the one hand,Zhuangzi recommend Boyi dismembered dog,hog and vagrant,on the other hand,it seemed to sing high praise for him.The reasons could be attributed to posterity’s modification on the Zhuangzi,and most importantly,it because the Tao thinking of Zhuangzi.It can be said that the image of Boyi in Zhuangzi is praised and criticized because of Tao.
Key words:Zhuang zi; Boyi; images
庄子是战国时期对伯夷形象做出深刻评价的思想家。虽然庄子的实际言论我们已不能听到,但仍能从《庄子》一书中看到庄子思想的内涵。因此,若要考察庄子对伯夷形象解读,则不得不立足于《庄子》。
一、伯夷之“义”
《庄子》一书中的伯夷形象极具颠覆性和复杂性,这也就意味着《庄子》一书中的伯夷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形象,而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庄子》内容的复杂性外,还与庄子“道”的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庄子之“道”在这里既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又起着催化剂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量变是质变的前提,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因此在发生转变之前,还需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准备,这个准备也就是伯夷之“义”。
对于“义”这个字的内涵,《说文解字》载:“义,己之威仪也。” [1]而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中载:“古者威仪作义,今仁义字用之。仪者,度也,今威仪字用之。谊者,人所宜也,今情谊字用之。” [2]而《中庸》第二十章中载:“义者宜也” [3]28,并且用“宜”来解释“义”最早已从西周就开始了。此外朱熹在《中庸章句》中说:“宜者,分别事理,各有所宜也。” [3]28相比之下,朱熹的解释更为通透,即在不同的情形下,达到合理就是“宜”。而《庄子》一书中,对于伯夷之“义”也是有过明确提及的。据《庄子·外篇·秋水》载:“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 [4]561首先,这其中的“我”指的就是“河伯”,也可以说指代的是庄子本人。而张恒寿老先生认为,该篇中的这一章“肯定是庄子后学所作” [5]191。因此,该篇中的这一章是可以体现庄子思想的。故而,从这里可以看出庄子对伯夷之“义”是认可的。但这里也仅仅只是单纯地提出了伯夷之“义”,却没有进一步说明伯夷之“义”的内涵,因此若要理解伯夷之“义”,还需要从其他角度入手。
据《庄子·杂篇·让王》载:
“昔周之兴,有士二人处于孤竹,曰伯夷叔齐。二人相谓曰:‘吾闻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试往观焉。’至于岐阳,武王闻之,使叔旦往见之,与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视而笑曰:‘嘻,异哉!此非吾所谓道也。昔者神农之有天下也,时祀尽敬而不祈喜;其于人也,忠信尽治而无求焉。乐与政为政,乐与治为治,不以人之坏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时自利也。今周见殷之乱而遂为政,上谋而行货,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为信,扬行以说众,杀伐以要利,是推乱以易暴也。吾闻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乱世不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并乎周以涂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洁吾行。’二子北至于首阳之山,遂饿而死焉。若伯夷叔齐者,其于富贵也,苟可得已,则必不赖。高节戾行,独乐其志,不事于世,此二士之节也。” [4]987-988
首先,对于该篇,“自向、郭以来,都不加详注。自苏轼开始认为伪作以来,多数学者都有较为相同的看法” [5]286,并且张恒寿老先生在此基础上认为该篇是:“秦汉人抄袭《吕氏春秋》而成的文字,绝无可疑。” [5]291其次,虽然本篇源自于《吕氏春秋·诚廉》篇,但“似也并非全无原由” [5]291,而是该篇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庄子学派的思想,故而后人才将其引入《庄子》书中。因此,该篇在对于解读前文中提到的伯夷之“义”的内涵的过程中,还是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的。
首先,《庄子》一书中该篇名为“让王”,顾名思义,背后所暗示的正是伯夷、叔齐兄弟让国的故事,因此这里所突出的正是这个“让”字。而《吕氏春秋》一书中,该篇却以“诚廉”为名,并且篇尾还进一步说到“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轻” [6]269,对于此,正如高诱所说“莫不有重,于天下也。莫不有轻,义重身轻也” [6]269,而以天下为重,以自身为轻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廉”,因此可以看出,这里的“义”还表现为“廉”。
其次,《庄子》中的《让王》篇的主要讲述的是伯夷、叔齐兄弟耻食周粟而饿死于首阳山的故事。前文中已说过,虽然此篇承袭于《吕氏春秋》的《诚廉》篇,但后人将其掺改入《庄子》书中,并非是毫无缘由的,而是其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庄子的思想。开篇中,伯夷、叔齐兄弟认为“吾闻西方有人,似有道”,可到了之后得到的答案却是“加富二等,就官一列”,由此二人认为“今天下闇,周德衰,其并乎周以涂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洁吾行”,最后当时的作者给出“若伯夷叔齐者,其于富贵也,苟可得已,则必不赖。高节戾行,独乐其志,不事于世,此二士之节也”的评价,尤其是后面的“二士之节”可以说是《庄子》一书中对伯夷的较高评价了。通过前文的论述不难发现,该篇内容明确,主旨鲜明,无需做过多的说明。“让王”二字的篇名所体现的是伯夷兄弟让国的行为,而拒绝周公旦的“加富二等,就官一列”,则是不贪图富贵,也就是本文前半部分提到过的“轻富贵”,再结合耻食周粟而饿死于首阳,这所体现出的恰恰是以天下为重和以自身为轻的思想,也就符合了《吕氏春秋》中的“诚廉”篇名,由这两个方面也就组合成了庄子眼中的“二士之节”。可以说,正是该篇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庄子的思想,故而“让”、“廉”二字,以及由此所表现出的“二士之节”,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概括庄子眼中伯夷之“义”的具体内涵,并且这也正是本篇作者将其加入《庄子》书中原因之一。此外,既然该篇作者认为伯夷的行为符合了庄子的思想,并且庄子思想的出发点皆源于“道”,故而也可以说伯夷的这种行为也是一个向“道”的过程。
二、伯夷之“道”
《庄子》一书虽非全部出于庄子之手,但其与庄子思想却是息息相关的,由于“道”是庄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庄子》中对伯夷形象的解读以及庄子对伯夷的任何评价都是与“道”密不可分的。前文中的“二士之节”所折射出的伯夷之“义”,就是源于伯夷的行为迎合了庄子心中的“道”,因此这也可以说是伯夷向“道”的过程。何以如此?
首先,伯夷没有贪利之心。庄子认为,世人相残、社会黑暗的主要原因,一是统治者的罪恶,二是世人的贪利之心。据《庄子·杂篇·庚桑楚》载:“民之于利甚勤,子有杀父,臣有杀君,正昼为盗,日中穴阫。” [4]775从中不难看出,由于人人争利,以致相互仇杀,世人生存于社会中,犹如生存于“羿之彀中”,也就是时刻出于后羿神箭的射程范围内,毫无安全可言。而伯夷却不是这样,《庄子》中所记述的伯夷拒绝“加富二等,就官一列”的条件,本身就可以体现出其没有贪利之心,并且“其于富贵也,苟可得已,则必不赖。高节戾行,独乐其志,不事于世”一句,则更是对此的明确说明,这既贴近于庄子的“道”,也是该篇作者对伯夷的赞赏之处。
其次,伯夷无占有之心。“现实世界中的行为方式,核心是追求个人目标,个人目标形形色色,庄子皆称为‘物’(“物”包括功业名声)” [7]275,而这个“物”包括功名利禄等内容。而世人追逐“物”,无非是因为此“物”对自己有用,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占有之心。据《庄子·内篇·齐物论》载:“圣人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求喜,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 [4]97从中不难看出,庄子认为,作为圣人,就应当“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求喜,不缘道”,而“不缘道”可以说是对此的一个高度概括,正如成玄英的《庄子疏》所说:“固不以攀援之心行乎虚通至道者也” [4]98,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不怀着占有之心行事。在庄子看来,道与非道的根本区别就是在于是否怀有占有之心。
对于此,《知北游》篇中的记述,解释得更为准确。据《庄子·外篇·知北游》载:“舜问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汝何得有夫道?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孙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故行不知所住,处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强阳气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4]739从中可以看出,对于舜所问的道是否可以据为己有的问题,丞的回答很直接,即“汝身非汝有,汝何得有夫道”,连自己的身体、生命都不属于自己,又怎么能去占有道呢?这所反映出的是一种彻底的、非占有的心态。而对于伯夷来说,从“让王”所反映出的兄弟让国一事,再到拒绝“加富二等,就官一列” [4]987,最后因耻食周粟而饿死于首阳山,这反映出的正是一种非占有的心态,这不仅是后人将其掺入《庄子》一书的原因,这也恰恰是伯夷得“道”的一种表现。
但这显然不是《庄子》一书对伯夷的最终评价。前文提到,《庄子》中的伯夷形象出现了极大的转折,而这个转折正如前文所说,是在“道”的思想的影响下和内容掺杂的作用下形成的。但笔者认为,后者的影响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这也正是后面所要论述的伯夷非“道”之处。
三、伯夷非“道”
本节开头时曾提到,若要理解《庄子》一书中伯夷形象的巨大转折,就要从两个方面入手进行考察,但内容的掺杂所引发的转变是在庄子“道”的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故而笔者认为庄子“道”的思想在这里应当起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笔者将《庄子》一书中伯夷形象转变的表现罗列如下:
《庄子·内篇·大宗师》载:“若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箕子、胥余、纪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 [4]232
《庄子·外篇·骈拇》载:“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是而盗跖之非乎!天下尽殉也。” [4]323
《庄子·杂篇·盗跖》载:“世之所谓贤士,莫若伯夷叔齐。伯夷叔齐辞孤竹之君而饿死于首阳之山,骨肉不葬。……此六子者,无异于磔犬、流豕、操飘而乞者,皆离名轻死,不念本养寿命者也。” [4]996
此三段材料为《庄子》一书中对伯夷形象的负面评价,也可以说是伯夷形象出现转折的表现。而此三段材料根据张恒寿老先生的考证,都并非为庄子派后学所作。第一,对于《大宗师》篇,张恒寿老先生认为:“此节是有意抄袭了《骈拇》篇对伯夷、盗跖的评语,从而节取了韩非评论的一部分人物加以批评,以表示对当权派的接近。它产生的时代似乎在秦汉时或战国末期,不能比《骈拇》和《韩非子》为早。” [5]59第二,对于《骈拇》篇,张恒寿老先生认为该篇虽不是庄子派嫡系所作,但与道家思想还是有一定的联系,该篇大体成书于秦统一前夕。第三,对于《盗跖》篇,“多半是攻击圣哲的言论,向来都认为不是庄子的作品” [5]292,据张恒寿老先生的考证,该篇大体成于战国末期。由此可以看到,《庄子》中对于伯夷形象评价的材料,大多并非出自庄子派的嫡系后学之手,而是后人将其掺杂进去的,可以说这是造成《庄子》一书中伯夷形象出现转折的直接原因。但笔者认为,这其中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或者联系。
《庄子》一书中对伯夷通过“让”和“廉”所表现出来的“义”,并由“义”体现出来的向“道”是颇为赞赏的,这由“二士之节”一句即可看出。但从前文所罗列的记述中,诸如“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 [4]232、“离名轻死,不念本养寿命” [4]996、“无异于磔犬、流豕、操飘而乞者” [4]996等等,则又表现出了对伯夷的讥讽,这些内容表面上看似只是简单的后人的一种掺杂行为,但其与庄子“道”的思想是大有渊源的。大致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剖析。
第一,伯夷对生命的漠视。后人所掺杂的伯夷对生命的漠视批判的内容,源于庄子对生命的尊重,而庄子对生命的尊重,又是源自于其对生命脆弱的认识。庄子生活的时代,正是社会急剧动荡的年代。一方面,列国都积极招揽人才力图变法革新,这不仅给当时的士人获取功名提供了机会,并且也为社会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的剧烈动荡,使得列国间的兼并战争不断,几场战争下来,动辄就有数十万人命丧黄泉,正如屈原在《国殇》中所记述的“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8]一样。进而从庄子的角度出发可以体会到,“生命在天地间不应当是随随便便的东西” [7]60。何以如此?据《庄子·杂篇·则阳》载:“(柏矩)至齐,间辜人焉,推而强之,解朝服而幕之,号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灾,子独先离(罹)之,曰为盗贼!莫为杀人!荣辱立,然后睹所病;财货聚,然后睹所争。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争,穷困人之身使无休时,欲无至此,得乎!’” [4]901从这段材料中可以看到,柏矩(老聃的弟子,在这里代表庄子)并没有明确说出死囚所犯的罪,而是将死囚的死因归结为“荣辱立”、“财货聚”以及“穷困人之身使无休时”的社会环境。在庄子看来,死囚被杀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他本身所犯的罪,而是促使他犯罪的社会环境,这种社会环境就好比一只巨大的、无形的黑手随意地操纵着人的生死,因此在庄子看来一个生命的结束变得毫无理由,而柏矩为死囚“号天而哭”,哭的也正是这种毫无理由的死亡。正是由于此,庄子才认为生命不应当是随随便便的东西,故而更不应被随随便便地抛弃。
但很显然,在前面诸篇的作者看来,伯夷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如《庄子·外篇·骈拇》载:“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 [4]323《庄子·外篇·骈拇》也载:“伯夷叔齐辞孤竹之君而饿死于首阳之山,骨肉不葬。……无异于磔犬、流豕、操飘而乞者,……不念本养寿命者也。” [4]996从材料中可以看出,在该篇作者看来,伯夷守义饿死于首阳山的行为是一种“残生伤性”的行为,这种行为使得伯夷“骨肉不葬”,最后作者给出“无异于磔犬、流豕、操飘而乞者”的最终评价,可以说这是当时对伯夷众多评价中最低的一个。何以如此?这正是前文中所论述过的,庄子对生命的尊重。从《庄子·杂篇·则阳》中所记述的柏矩游齐时的所见所闻,可以看出,人的生命是被外在的一个巨大的黑手所操纵着,而这个黑手可以随心所欲地吞噬生命,但庄子却认为任何生命都有着其独特的存在价值,故而不该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东西,更不该被随随便便的抛弃,这从“号天而哭”中就可以体会到。而伯夷却不是这样,为了所谓的“名”或“义”而伤残自己的生命,最终使得“骨肉不葬”,这显然与庄子敬畏生命的态度是背道而驰的,以反喻正,其中所表现出的深意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伯夷的自我中心意识。“无异于磔犬、流豕、操飘而乞者”,无疑是众士人对伯夷评价中最低的一个,而该篇作者何以会给予伯夷这样的评价,该句前面一句,即“伯夷叔齐辞孤竹之君而饿死于首阳之山,骨肉不葬”已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但笔者所要强调的是,虽然这里说的是“伯夷叔齐辞孤竹之君而饿死于首阳之山”,但导致“骨肉不葬”进而让作者给出“无异于磔犬、流豕、操飘而乞者”评价的原因并非是“伯夷叔齐辞孤竹之君”,而是耻食周粟这件事。对于此,《庄子·杂篇·让王》中“今天下闇,周德衰,其并乎周以涂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洁吾行”就是最好的例证。联系《让王》、《盗跖》两篇来看,伯夷是认为“今天下闇,周德衰”,进而担心“并乎周以涂吾身”,所以才选择“避之以洁吾行”,进而最终导致前面“饿死于首阳之山”的结果。但对于此,笔者认为,这已不再是如前文所述一般,表现为一种向“道”的“义”,而是表现为以一种追求名的行为。而这种行为,也正如《庄子·外篇·骈拇》中所言“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残生损性,则盗跖亦伯夷已,又恶取君子小人于其间哉” [4]323,二人的死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都是在追求“物”的过程中死的,只不过是所追求的内容不同罢了。
这是一种自我中心意识,也可以说是一种自私的行为,恰恰也正是庄子所极力批判和反对的。何以如此?笔者认为,若要搞清楚原因,则必须要搞清楚庄子眼中的自我中心意识到底是什么。据《庄子·外篇·知北游》载:“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正获之问于监市履豨也,每下愈况。汝唯莫必,无逃乎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遍咸三者,异名同实,其一指也。’” [4]749-750从该段中可以看到,东郭子问:“所谓道,恶乎在?”庄子的回答分别是“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而最后的总概括就是“无所不在”。而东郭子似乎对这个回答不是很满意,他认为庄子没有认真地回答他的问题,而庄子的态度恰恰相反。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庄子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也正是他的认真,以至于对某些事的态度近乎于偏激。因此,庄子是很认真地回答了东郭子的问题,并且庄子还尖锐地指出“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也就是说东郭子的问题没有问到实质上,而实质是什么?也就是文中所说的道“无所不在”,换句话说也就是“道在自然”。
在这里,庄子似乎只是在单纯地强调“道在自然”,但笔者认为其实不然。从“蝼蚁”到“屎溺”是一个层层递下的过程,这也正是东郭子感到惊讶而又不可思议的原因,而庄子何以会层层递下呢?笔者认为,庄子在这里所暗示的应当是,道并非是什么高尚的东西,道本身就是自然的一种再现,简单点就是前面提到的“道在自然”。因此,自然界的万物之间也就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东郭子对于庄子的回答感到惊讶,反应的是东郭子显然是以一种固有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具有贵贱等级的眼光去看待外部世界的结果,而庄子的回答,道“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则恰恰说明自然万物都有着其独特的存在价值,都应当受到尊重。因此,从这段材料中不难看出庄子对于这种自私的、自我为中心评价外物的态度的不耻。
而在前文中所列《大宗师》、《盗跖》章节的作者看来,伯夷恰恰是这样一个自我中心的人,而伯夷的自我中心意识,又是由其“占有之心”所表现出来的。前文中曾提到伯夷无占有之心,这从“让王”以及拒绝“加富二等,就官一列”就可看出,而此处又提到“伯夷的占有之心”,而这似乎属于相互矛盾。但笔者认为其实不然。前面的无占有之心,是基于兄弟让国以及轻富贵而言的,这也是迎合庄子“道”的思想之处;而现在的占有之心,则是相对于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而饿死于首阳之山,骨肉不葬”而说的,二者之间性质相同,但结果不同。前者伯夷“让王”以及拒绝“加富二等,就官一列”是顺应了自然的本性、向“道”的过程。而后者伯夷“饿死于首阳之山,骨肉不葬”是一种追求仁义的、具有目的性的行为。因为从庄子的角度出发,仁义也属于“物”的一种,因此伯夷追求这种“物”并想要将其据为己有的行为,就是一种占有之心,而这显然与庄子的“道”是背道而驰的。这里与前文一样,依然是以反喻正,从侧面来说,是迎合庄子的思想的。
此外,还需要格外强调一点,这就是庄子的“认真”。前文提到,庄子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对于为何认真,由于与本文无关,故而不在此赘述。而庄子的认真却达到了一个非常苛刻的程度,这种苛刻有时近乎于偏激。如《庄子·外篇·天地》所载的“博学以拟圣,于于以盖众,独弦哀歌以卖名声于天下” [4]435,是庄子借助隐者对孔子师徒的批评。还有《庄子·外篇·山木》所载的“饰智以惊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 [4]680,也是庄子对孔子的批评。由此不难看出,庄子不允许所谓的道德圣贤有一丝一毫的自我显示成分,一旦被看出有这样的成分,那么他们倡道或者殉道的正面意义就会被全盘否定。何以如此?这依然源于庄子的“道”。在庄子看来,“合于道的行动,简单地说,就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行动,就是以一个人天性中的认真善良去做各种本分之事,却不含求取回报之心,更不含炫耀卖弄之心。” [7]279如《庄子·外篇·山木》中所记述:“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之国。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乐,其死可葬。” [4]671-672就是一种朴实的、不含占有和卖弄之心的状态。而之前,伯夷对于富贵,“苟可得已,则必不赖。高节戾行,独乐其志,不事于世” [4]988的做法,就是依照自身的天性所作的本分之事,这既不含占有之心,也不含卖弄之心,故而《庄子》中的伯夷形象是正面的。
但是,由于庄子近乎偏激的认真,并且伯夷自身也显示出了自我显示的成分,这也就给予了后人进行附会的条件,如《庄子·外篇·骈拇》所载:“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残生损性,则盗跖亦伯夷已,又恶取君子小人于其间哉。” [4]323从这段话不难看出,伯夷不能顺从自己真实的性情,而被所谓“名声”牵着走,最终该篇作者给出了“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 [4]232的结论,这也正如成玄英所说:“悦乐众人之耳目,焉能自适其性情耶!” [4]234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庄子》一书中的伯夷形象是深刻而又复杂的,并且处处都显露着庄子“道”的思想印记。前者,伯夷“让王”以及拒绝“加富二等,就官一列” [4]987-988的行为所体现出来的“义”,契合了庄子的道,因为在后人(指掺杂文章者,下同)看来,这里的“义”并不是伯夷所刻意追求的。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没有丝毫自我中心意识的,不含目的性、卖弄炫耀之心的,一种顺应自然本性的行为。而后者,由伯夷耻食周粟所导致的“饿死于首阳之山,骨肉不葬”,在后人看来是一种“皆离名轻死,不念本养寿命” [4]996的行为,也就是为了名声而不顾及生命的意义的行为,这是有悖于庄子的“道”的,也正是基于此,后人才给予了伯夷“无异于磔犬、流豕、操飘而乞者” [4]996的最终评价,而这也是先秦时期众士人对伯夷评价中的最低。虽然这些人对伯夷的评价很低,但这并没有影响伯夷在后世人心目中的地位。如《庄子·杂篇·盗跖》载:“世之所谓贤士,莫若伯夷叔齐。” [4]996对于此篇,“多半是攻击圣哲的言论,向来都认为不是庄子的作品,毋烦再述。” [5]292虽然该篇并非庄子派的东西,但仍可以从中看出当时世俗对伯夷的看法,也就是“世之所谓贤士”。虽然《庄子》一书中的伯夷形象出现了一个低谷,但这只是后人为了迎合庄子思想而做的掺杂,总体上并不能影响伯夷形象所反映出的伯夷精神依然按照既定的、向上的轨道继续沉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