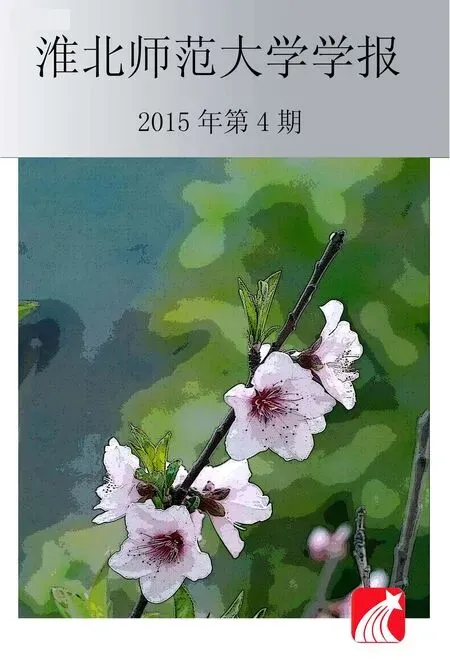幽冥中的权力探究
——一种当代中国美术考古的新观念
2015-03-27李金凤陈志峰
李金凤,陈志峰
(1.淮北市博物馆,安徽淮北235000;2.天津商业大学艺术学院,天津300134)
幽冥中的权力探究
——一种当代中国美术考古的新观念
李金凤1,陈志峰2
(1.淮北市博物馆,安徽淮北235000;2.天津商业大学艺术学院,天津300134)
从中国文化的基础层面出发,探求以农耕为主的民族在看待世界的心理的特征以及这种特征出现的客观条件。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中国陵墓中的视觉特征从最初对群体性祖先的崇拜表达,开始转向对家族个人的社会权力崇拜表达,这种转向可以说是一种视觉形式在陵墓形制中对于社会权力结构的视觉建构。从美术考古的层面出发,对陵墓形制的权力崇拜的历史挖掘有利于美术考古学科的发展。
美术;考古;权力;陵墓
一、从大框架到小框架——中国人的时空心理以及“土”情节
历史的选择似乎特意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和空间为基础的一种磅礴舞台,在时间层面上不仅造就了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延续,而且也在空间层面上保留了这一文化的特有形式。中国地处东亚大陆的近端,在地缘上从四方位的概念出发,可以发现在中央文明扩散到一定程度之后,便会因地理气候等客观因素而限制住这种蔓延性的文化发展:河套以北的极寒地区、西方的沙漠和高原地带、东方的一片汪洋以及南面的茂林烟瘴之地等,这些边缘性的障碍控制住了中华文明的边界,但同时也塑造了中国人对于空间认知的一种习惯性心理意识。在这种版图地理呈现“中央——扩散——四方——限制”的客观条件下,中国人在先天的环境存在中得到了一种“限定”的意识,使得自身的发展牢牢扎根于中原地带,在这种大框架的地理版图层面上,实现了人们心里中一种相对封闭的文化观念。这也可以说明为何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国人始终没有把眼光投向东边的海洋区域。大框架的自然限制导致了每个个体所组成的整体性文化的小框架上的心理限制,所以中国人便“得到”了一种自为式的时空理解,而且也先天性地把自身作为了宇宙的中心而看待周遭的环境。
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对于中原故土的依赖性,导致了农耕文明的高度发展,对于土地的民族心理相比其他民族而言就显得异常深厚,而且这种对于土地的依赖性不仅体现在社会现实生活的诸多领域中,在想象层面的去世后的时空中也同样得到了彰显。土葬的习俗在“古代东亚,特别是在古代中国有着数千年的持续发展的历史,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1]76在这一相对比较独立的死后时空中,中国人建构出了一套全面有机繁复而又统一的视觉系统和形式存在,蕴含了一套独特的视觉语汇以及特有的形象思维和生死观。并且这种状态还在统一稳定的基础上,随着现实社会中的权力变迁而出现相应的视觉形式的变化,这就为中国美术考古的发展提出了一种崭新的研究思路:在视觉和权力交织的历史范式中,找到一种能够体现文化意义上崇拜对象的转移对美术以及美术之上的各种上层建筑的影响的视觉逻辑。
二、幽冥中的磅礴——整体观念对于中国美术考古的意义
一般意义上,对于美术考古而言,西方引进的传统多以某个层面或某一个专题器物的演变发展为主,或者把其精力投入到视觉形式的更迭和其背后所反映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等现实意义之上。但中国的墓葬无论从具体的模拟地上建筑的文脉形式,还是从内部的壁画浮雕以及明器摆设等,都是一个视觉的综合体,也是一种有机的整体性历史存在,所以作为具有科学意义的现代考古应该从遗址整体性挖掘墓葬的诸多层面上的遗留物,并揭露和记录遗址中的全部情况,只有充分了解这一系列的视觉系统中的各种因素和其背后的变迁历史,才能从宏观的层面上把握和理解中国艺术的美学价值和形态必然性问题,才可以从考古的角度去把握当时历史社会中的伦理价值、礼制形式、社会整体价值观、信仰以及背后的权力结构问题。一般说来,一种社会具有某种稳定的社会权力结构形态,这种形态会因固化之后的社会惯性而从“生之教育”到“亡之墓葬”等等诸多环节加以巩固和发展。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就需要从整体性出发,在权力与视觉共同搭建的这种冥界时空中找寻中国特有的社会伦理建构,以便避免因单一化的器物或美术类型学层面的研究而失去这种和社会结合比较紧密的新型美术考古方法。
中国人对于土地的依赖性导致了极其明显的丧葬文化的形成,但在这种丧葬形式中,除了在土地下建有宏伟的模拟地上建筑群的墓室系统之外,在地面之上也相对地建有各种明堂、祖庙。而且一定时期内还演化成了社会群体必不可少的依赖性的祭拜空间。在历史性地形成的祭拜空间中,往往组合特定空间形式演变为一种类似宗教用途的综合性艺术系统,包括各种视觉因素和装饰性器物、雕塑等,但这种整体性的艺术系统是按照一定的观看心理模式设计而成的。主要体现的并非现世当今的考古者所体会的一种非墓主人的视觉经验,而是完全按照一种墓主人灵魂游离于躯体之外而再次来到现世时空中之后的视觉经验而设计出的典型空间形式。所以对于在地面上进行墓葬礼仪朝拜的个体而言,这种视觉经验就影响了在世之人的心理,从而体现出一种神秘的类宗教仪式的感觉。值得指出的是,这种神秘的时空经验不但指涉了幽冥世界的集体幻想,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架构出亦或延续性地架构出了现实中的社会权力结构。
三“、另一个世界的反映”——墓葬形式对于现实社会权力结构的视觉化二次建构
如上所述,中国的墓葬形式不仅是幽冥世界的一种载体,而且也架构了现实中的权力结构,因国人历史性地产生了祖先崇拜的文化习俗,所以在墓葬形式中也会历史性地安插这一文化结构类型的礼制系统,最重要的应该为“庙”与“墓”同时并行的存在。“早在三代,庙与墓已同为祖先的崇拜中心,但二者的宗教含义和建筑形式则大相径庭。庙总是集体性的宗教中心,而单独墓葬则属于死者个体或连同其家庭成员。庙筑于城内,实际上形成城市核心,而墓则多建在城外旷地。庙与墓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二者崇拜对象的不同:前者的主要崇拜对象是远祖,而后者则奉献给近亲。”[2]551为何会在社会构成的视觉和形式层面上出现这类变化?这其实应该结合社会的整体精神价值变化以及这种变化背后的社会关系的变化来分析。在更加古老的时期,社会整体性的价值崇拜更多地侧重于对于祖先的整体性崇拜,而西周之后以及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单位逐渐演变为从“族”的整体分裂出的“宗”这一形式的出现,社会整体的价值崇拜开始变为对于在社会中渐为强势的独立宗族的权力崇拜。而且以这种社会转变为基础的形式制度也在发生转变,这也正是美术考古所重点探究的内容。人们对于郊外的墓室形式的重视程度超过了城中的宗庙建筑,旧有的对于宗庙的兴趣开始转向到了城外的墓葬。“旧有的宗教和艺术形式无法反映和支持新的社会结构而逐渐为新出现的宗教和艺术形式所取代和补充。其后果则集中地表现为宗族祖庙地位的急剧下降和象征家庭个人权势的墓的重要性的日益增长。”[2]561可以说在当时社会整体经济结构以及文化结构发生整体变迁的阶段,在墓葬和宗庙崇拜层面的转变也反映了人们从单纯的祖先崇拜变为对于权力崇拜和掌握权力的单个宗族的近亲崇拜的模式。当时对于死者的身份界定也开始出现了同墓葬的视觉等外在形式相对等的设计建构。“死者的身份和爵等并非由其在宗族内的地位而定,而是根据他生前的任职和贡献。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东周时期庙与墓截然不同的社会意义:庙代表了宗族的世袭,而墓象征着个人在新的官僚系统中的位置成就。”[2]561这说明,当时的墓葬已经从单纯意义上的近世祖先的祭拜意义逐步加进了对于这些近世祖先的显赫社会地位和权力的崇拜,以及对于这一权力在社会结构中所占地位的象征性建构的诸多附属内容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因素。特别是在设计的视觉化形式上,这种转变尤为明显:以前的庙堂建筑空间一般采取平面化的布局,而权力崇拜反映在墓葬形式上的结果便是视觉化的三维形制的突显,设计的主攻方向不再停留在二维平面的纵深扩张,而且也同时向三维空间的高度方向发展。在距离墓葬极远的地区就可以看见类似纪念碑一样的大型墓冢结构。突出于地面的高大陵墓从心理和视觉上体现了死者生前享有的社会地位,而且也为在世的人们提供了一种现实世界中权力层位的有力象征。可以说这种视觉的形式就是为在世的人们搭建一种权力结构的物质再现,在这种再现中,权力结构发生变化的宗族把庙堂形式所代表的祖先崇拜变为了墓葬形式所代表的近世祖先的权力崇拜,庙堂的形式也随之一点点“进入”到了墓葬的整体系统形制之中,“文献载古代宗庙中两个最重要的部分是庙和寝,庙得名于朝,是举行典礼的地方,寝则象征死者生前休息闲晏之处。秦汉时期,寝首先被移至陵园内,庙也随之附着于墓地。”[2]564可见,随着历史的发展,包括视觉系统在内的陵墓设计不断地融和接纳了以前作为价值崇拜的因素,而把所有因素的重心重组为一个代表权力结构的视觉系统,在一定意义上,这不仅只是为了死者而定的幽冥等级原则性视觉再现,而且更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现世当中权力结构的原则性再现。
结语
综上所述,美术考古在今日看来,不仅是一种具体到视觉形式的类型学考古工作,也必须和历史社会变化发展的大趋势联系在一起,并且其作用不仅局限于美术形式的变迁和发展,更应该通过美术形式和设计形式等诸多社会视觉因素的考察,提炼出社会意义的变革,诸如权力更迭、阶层变化等隐含的历史因素。美术考古的任务在当今时代已然顺应发生学科的拓展,才能把其真正的能力和意义体现出来。如上文所述,考古中重视从视觉因素中找寻权力在社会中的崇拜,并且这种崇拜反向影响了美术在这些反映权力的设计形制中的表现形式和造型变化。此种考古的新路径应该具有一定学术意义和价值。其实陵墓是对权力的关系的一种映射,历史上很多实例证实了这一点,例如东汉的祠庙为灵魂的居处,所以重视程度相比后世为高,因此画像石艺术表现的比较兴盛;东汉灭亡之后魏文帝曹丕下诏废黜上陵礼,这种权力更迭中的社会突变就会影响到陵墓的形制,以致当时的画像石艺术又归于沉寂。如此种种都说明了考古在美术领域中不仅可以帮助美术史的研究形成实物例证的作用,还可以帮助社会学家进行社会权力的变迁验证,这就必然拓宽了美术考古的作用和范围,为学科发展迎来新的空间。
[1]巫鸿.美术史十议[M].北京:三联书店,2008.
[2]巫鸿.礼仪中的美术[M].北京:三联书店,2009.
责任编校 谢贤德
J209
A
2095-0683(2015)04-0125-03
2015-06-16
李金凤(1982-),女,安徽巢湖人,淮北市博物馆三级美术师;陈志峰(1977-),男,安徽萧县人,天津商业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