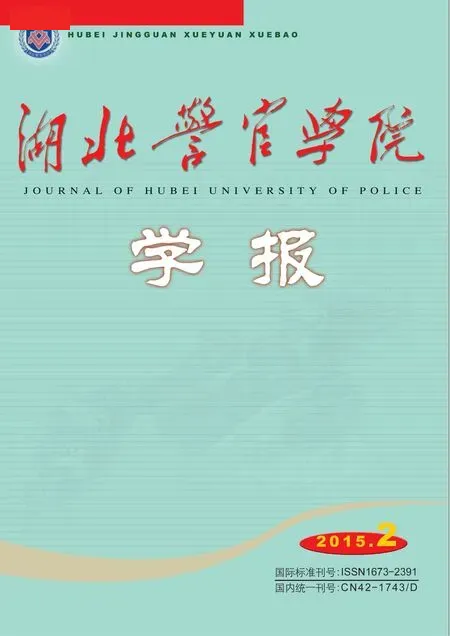论扒窃入罪的合理范围——兼评“两高”关于扒窃的限制性解释
2015-03-27
论扒窃入罪的合理范围
——兼评“两高”关于扒窃的限制性解释
吴卫
(惠东县人民法院,广东惠东516300)
【摘要】《刑法修正案(八)》适时地将扒窃纳入刑法范围予以规制,但在维护社会秩序与保障人权之间存在激烈矛盾,加之无数额、无情节限制,因而引发了较大的争议。尽管两高的司法解释作出了公共场所与随身携带的限制,但处罚的范围仍然过大,与扒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相称,还是存在不足之处。以限制入罪为视角,通过厘清扒窃的行为性质,区分既遂与未遂,合理适用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圈定扒窃入罪的合理范围。
【关键词】扒窃入罪;刑法谦抑性;罪行相适应;限缩解释;刑法第13条但书
扒窃本为公安机关在日常反扒活动中使用的术语,其含义无定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在刑法领域,扒窃最早出现于司法解释之中,即1997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对于1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3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以盗窃罪定罪处罚。”2011年5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作为盗窃罪的一种特殊形式正式引入刑法。
一、扒窃入罪的理由
扒窃入刑前,理论界与实务界争论十分激烈,最终赞成论者获胜,以修正案的方式将原本由治安管理处罚的行为纳入刑法。主张扒窃入罪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在人口密度大、流动性强、出行频繁的当下,扒窃行为不仅使直接受害者蒙受财产损失,客观上还扰乱社会秩序,损害国民的公共安全感,导致了民众出行的安全感下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削弱等危害。扒窃常常需要接触被害人的身体,而人的身体也是一种法益,未经权利人同意他人不得故意触碰,因此,扒窃在侵犯财产权利的同时还侵犯了人身权利。扒窃者通常携带刀片等作案工具,为强取财物或抗拒抓捕而转化为人身伤害的可能性大于普通盗窃罪。此外,在众目睽睽之下(不排除被害人知情)实施扒窃行为,是对公平正义观念的践踏和对国家公权力的挑战,情节恶劣,必须依法严厉打击。综上,扒窃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二)特殊预防必要性大
扒窃者多为惯犯、常习犯,人身危险性大,再犯可能性大。《三年来北京市公交系统扒窃案件实证分析》显示,2008年3月至2011年11月,北京市检察机关共办理公交扒窃案件433件530人,涉案嫌疑人大都为惯犯、职业犯、常习犯,其中因盗窃受过行政或刑事处罚的有348人,约占总数的70%,其中构成累犯的有156人,约占总数的30%,没有前科劣迹的仅30%。[1]随着人口集聚场所监控设施的逐渐普及以及人们反扒意识的增强,为更易实施扒窃行为和提高反抓捕、反侦查能力,扒窃出现团伙化趋势。扒窃者往往利用同乡关系或未成年人、聋哑人等特殊群体组成扒窃团伙,内部分工精细,结构紧密,掩护、扒窃、转移、销赃一条龙,查处难度大,因此需要刑法予以特殊预防。
(三)案件多发且取证难
扒窃通常发生在人流量大、比较拥挤的场所,且扒窃过程十分短暂,短则瞬间,长也不过一两分钟,加之多为团伙作案,造成了取证难的问题。此外,由于财产损失小,担心被打击报复等原因,被害人往往不愿意作证,增加了打击扒窃的难度。由于金融业的发达以及安全意识的提高,人们出行很少带大量现金,通常扒窃涉案数额较小。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之前,由于往往达不到盗窃罪的入罪标准,也无证据证明扒窃者一年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刑法难以规制扒窃,往往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扒窃者处以罚款、拘留等行政处罚。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并罚最多行政拘留20天,代价相对不高昂,威慑作用较小,难以遏制扒窃的高发态势,需要发挥刑法的威慑作用。
正是由于扒窃频发,侵犯财产与人身权利,同时损害公众的安全感,社会危害性严重,达到了用刑法规制的程度,加之《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扒窃规制不力,为严厉打击扒窃和维护社会秩序,《刑法修正案(八)》适时引扒窃入刑,并且无数额和情节限制。
二、扒窃一律入罪的弊端
诚然,扒窃入刑是刑法回应群众呼声、满足时代要求以及适应城市化迅速发展、人口密度增大国情的体现,但“扒窃的,处……”寥寥数字的规定无疑过于简单。尽管存在如“故意杀人的,处以……”的规定,但无论裁判者还是公众,对杀人行为的理解均十分接近,扒窃系首次入刑,亦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即便是裁判者对其内涵究竟为何争议也颇大。可能正是由于扒窃频发,通常数额不大,取证难等原因,才未对扒窃入罪予以数额或情节限制。这种无任何限制在司法实践中引发了极大争议:是一律入罪,还是考虑涉案数额、作案情节等因素提高入罪的门槛。如2011年6月1日,成都市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召开会议,对适用《刑法修正案(八)》办理扒窃案件进行研究,并形成《会议纪要》,对公安机关办理扒窃案件可提请批捕的9种情形进行了限制性的规定。[2]本文认为,扒窃行为一律入罪并不科学,应予以一定的限制,如此方能在维护社会秩序与保障人权之间实现平衡。具体理由如下:
(一)扒窃一律入罪,有违刑法谦抑性
刑法的谦抑性,即刑法并不适用于所有的违法行为,而只能慎重、谦虚地适用于必要的规范内,其内容包括刑法的补充性、不完整性与宽容性。[3]刑法并非万能,在一定程度上,刑罚是以恶对恶,有一定的副作用。当扒窃者刚接触被害人裤兜即被抓获;扒窃者将手伸进被害人兜里,但里面空无一物;扒窃者仅扒得价值与使用价值均微小的物品如一张餐巾纸;等等。根据一律入罪的观点,前述行为均构成犯罪。但根据法益侵害说,违法性的实质是对法益的侵害与威胁。[4]而且,当行为只侵犯微小法益时,刑法应让位于其他法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法谚云:“法律不理会琐碎之事。”[5]刑法更应如此。此外,刑法第13条但书明文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所以,扒窃不应一律入罪。
(二)扒窃一律入罪,有违罪刑相适应
罪刑相适应或罪刑均衡是各国刑法的基本原则,轻罪轻判重罪重判是国民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在刑法中的体现。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故意伤害需达到轻伤以上才追诉;根据司法解释,通常非法拘禁要超过24小时才追诉。而扒窃伴有的人身伤害危险性很小,却仅因为以扒的方式窃取财物就一律入罪,与人身伤害型犯罪之间明显罪刑失衡。由于抢劫罪是以暴力、胁迫等方式强行夺取财物,被害人遭受人身伤害的可能性大(最高法定刑为死刑),因而并无数额要求;抢夺罪是明目张胆地强行夺取他人财物,且造成他人人身伤害的可能性较大,但只有在满足数额较大的前提下才追诉,根据2013年11月18日起施行的“两高”《关于办理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数额较大是指1000至3000元以上。扒窃即使伴随人身伤害,通常也是轻微的,扒窃一律入罪,会造成与财产型犯罪之间罪刑失衡。此外,我国只存在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并无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根据一律入罪的观点,只要一次轻微扒窃就会终身被打下“罪犯”的烙印,犯罪记录影响就业等,妨碍回归社会,与公平理念不符。
(三)扒窃一律入罪,耗费有限的司法资源
盗窃罪在刑事案件中占相当大的比重。据统计,2004至2008年全国公安机关关于盗窃的立案分别为3212822、3158763、3216293、3260966、3399600件,全国公安机关办理的盗窃案件占总侵财案件的79.8%,占所有刑事立案数的68.3%;全国法院盗窃案件结案分别为167529、178421、180329、190866、202475件,审结的盗窃案件占侵财案件的59.5%,占所有刑事案件的26.1%。[6]尽管不是最新数据,但最近几年经济社会状况并未急剧变化以及根据菲利的犯罪饱和论,此数据仍有参考价值。不论数额、情节一律入罪,会明显增加公检法的工作量。因为一律入罪降低了盗窃罪的入罪门槛,几乎将此前由《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理的案件全部纳入司法程序,经过立案至执行程序。例如,2013年某日14时许,王某窜至延庆县延庆镇某市场水产厅肉食摊前,扒窃事主康某上衣兜内现金两元五角,被正在执勤的便衣民警当场抓获。后王某被逮捕,并因盗窃罪被法院判刑。[7]仅因扒窃2.5元钱,王某经历了完整的刑事追诉程序,而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前可能只需治安处罚即可。扒窃一律入罪造成追诉大量微小扒窃的现象。目前,全国法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积案,扒窃一律入罪的做法无疑加剧了案多人少的矛盾,是对司法资源的一种浪费。此外,扒窃一律入罪将导致《治安管理处罚法》关于盗窃的规定形同虚设,造成法律资源的浪费。
三、对两高限制性解释的评析
2013年4月4日正式实施的“两高”《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应当认定为扒窃。”这是扒窃的官方定义,须满足“公共场所或公共交通工具”和“随身携带”条件才能构成扒窃,而且根据“应当”,只要符合这两个条件就构成扒窃。司法解释通过对地点与对象的限定来限制构成扒窃的入罪范围,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对统一司法裁判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这两个核心条件的含义为何,未作进一步解释说明,不利于正确认定扒窃,下文将对此进行讨论。
(一)对公共场所的正确理解
“公共场所或公共交通工具”是对扒窃型盗窃罪地点的限制。公共场所即不特定人可以进入、停留的场所以及有多数人在内的场所。[8]刑法仅有第291条“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有关于“公共场所”的规定,即“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列举式规定不可能穷尽公共场所,其实只要满足不特定人可以随时进入、停留或多数人在场的条件,基本就可以认定为公共场所。但是,企业或机关封闭的办公区域以及有严格门禁的学校等严格限制为“内部人员”的不属于公共场所,机关的服务大厅由于对外开放,则属于公共场所。
司法解释出台前,往往认为扒窃发生的场所仅限于公共场所,并没有单独提出公共交通工具这一场所限制条件。根据一般社会观念,公共交通工具就是指公交车、地铁、轻轨、火车等为公众提供搭乘服务的运输工具。其实,公共交通工具具有前述公共场所人员不特定、流动性强、人数较多等特点。通常而言,公共场所包括公共交通工具。当然,出租车等人数少、人员流动性小的交通工具不属于公共交通工具的范围。本文认为,司法解释如此规定是为了提示司法人员注意公共交通工具是扒窃的多发性场所,属于注意规定,而且如此理解方能合理解释“两高”为何将两个具有包含关系的概念并列规定。
(二)对随身携带的准确认定
关于随身携带,有学者认为指他人带在身上或置于身边附近的财物。[9]也有学者认为,扒窃的对象仅限于“贴身财物”,排除任何不接触身体的情况。[10]从字面意思理解,随身携带当然包括贴身财物,但是否仅限于此?甲乙二人在流动性较强的餐厅吃饭,甲将其衣服挂在坐倚上,二人交谈甚欢,丙趁甲不注意将其衣服兜里的钱包盗走,钱包内有身份证、银行卡及现金100元。衣服挂在坐椅上肯定不属于“贴身”,根据第一种观点那就属于扒窃。显然,身体随时可以触摸、检查的情形应属于随身携带。对于第一种观点的“身边附近”应如何理解?有学者主张现代法治是“常识、常理、常情之治”,强调在制定、理解、适用具体法律的过程中,绝对不能把法律与民众普遍认同的基本道理对立起来,绝对不能对法律规定做出明显违情悖理的解释。[11]本文认为应作常识性理解,扒窃主要是强调主人对财物的随时可控性、紧密联系性,符合这种特征即可成为扒窃的对象。所以,如他人放置在自行车车筐里、挂在自行车把上的财物,乘坐火车时放在行李架上的行李,乘公交、地铁时置于椅子旁的物品,公园休息时暂放在旁边的照相机等情形,均可认定为随身携带。当然,如果扒窃者确认(需证据证明)特定行李的主人暂时离开了,此时主人虽然仍占有行李,但对行李的随时可控性严重下降、与行李的联系松懈,则不得认定为随身携带。总之,何为随时可控性、紧密联系性,需结合具体案情根据随身携带的可能含义进行具体判断。
四、扒窃入罪的合理范围
尽管“两高”试图通过“公共场所或公共交通工具”与“随身携带”两个条件对扒窃入罪的范围予以限制,但在本文看来扒窃入罪的范围仍然过大,需要进一步限制方能划定扒窃合理的犯罪圈。
(一)扒窃行为性质辨析
《刑法修正案(八)》、“两高”司法解释均未对扒窃予以数额、次数限制,因此部分学者认为扒窃为行为犯,只要实施扒窃行为即可构成扒窃型盗窃罪;但另一部分学者主张扒窃为结果犯,仅扒窃行为不能构成扒窃型盗窃罪。[12]根据我国刑法通说,行为犯是“以法定行为完成为既遂标志的犯罪”,结果犯则是“必须发生法定的犯罪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13]本文认为,认定扒窃为结果犯更妥当。理由如下:
1.扒窃不符合行为犯的本质。行为犯的本质是只要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危害行为即成立犯罪并构成犯罪既遂。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仅实施危害行为即已侵害法益,应受到刑法的规制。行为犯的这种本质表现为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同时发生,即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无时间间隔,而结果犯本质特征为危害行为终了与危害结果发生之间具有时间上的间隔。显然,扒窃行为与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之间具有时间间隔,因此扒窃不为行为犯。
2.扒窃与盗窃罪的关系。众所周知,盗窃罪为财产型犯罪,是典型的结果犯,以获得财产(控制说)或丧失财产(失控说)为既遂标志。扒窃是盗窃罪的表现形式或行为方式之一,这种包含关系决定了扒窃的性质应从属于盗窃罪的性质,即扒窃应为结果犯。否则,同一罪名既包括行为犯又包括结果犯(亦不满足结果加重犯的条件),在逻辑上必定引发混乱。当然,如果为危险犯与实害犯关系如刑法第114条与115条之间的关系时则可同罪名,但扒窃与盗窃的关系并不符合。
3.扒窃与“两抢”的对比。根据司法解释,抢劫罪只有在造成被害人轻伤以上或夺取财产的才构成既遂。根据前述关于抢夺的最新司法解释,抢夺的入罪标准为夺取的财产在1000-3000元以上。而抢劫罪、抢夺罪在人身伤害方面明显要比扒窃严重,通常在财产损失方面也要大于扒窃。如果认定扒窃为行为犯则严重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不妥当。
(二)既遂未遂的区分
如果采行为犯说,则扒窃一律构成盗窃罪,无所谓既遂与未遂之别。本文采结果犯说,则应区分扒窃未遂与既遂。扒窃的着手应该是行为人接触被害人装有财物的包的外侧,以是否产生使被害人丧失财物的紧迫危险为标准。何为扒窃型盗窃罪既遂?本文认为,被害人丧失对财物的占有即既遂,即采失控说。因为丧失对财产的占有即原有的占有关系被破坏,此时法益就已遭到侵害。当然,应根据具体情况予以认定。根据司法解释,只有存在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盗窃目标等情节严重的情形时才处罚盗窃未遂。
(三)第13条但书的理性调适
通常而言,扒窃的财产具有随机性,涉案金额可大可小,且不受扒窃者控制。正是由于该特点,不应严格规定扒窃入罪的数额,但也不能认为只要扒窃到物品即认定为既遂。作为扒窃对象的物品应具有一定的价值或使用价值。如果扒窃的是一颗普通糖果、一张名片等价值与使用价值均十分低的物品,就可以运用刑法第13条但书“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予以非犯罪化处理。这样,就不会出现因扒窃2.5元钱而被判刑的现象。否则,既浪费宝贵的司法资源,也无法实现刑罚目的,因为刑期过短,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目的均难以实现,还可能因短期自由刑导致交叉感染,增加人身危险性。当然,非犯罪化并非不处罚,可以利用《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行政处罚,同样能收到处罚效果。
综上所述,通过对“公共场所或公共交通工具”、“随身携带”的准确理解,扒窃不以携带凶器为必要,不要求技术性、惯常性,财物不限体积微小但应有一定的价值或使用价值,将扒窃认定为结果犯并严格区分为既遂、未遂,合理利用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方能划定扒窃型盗窃罪的合理范围,从而实现维护社会秩序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参考文献】
[1]肖中华,孙利国.“扒窃”犯罪成立要素的合理界定——侧重于行为无价值论的基本立场[J].政治与法律,2012(9).
[2]李寒劲,冯杨勇.“扒窃入刑”的司法困境及出路[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3(10).
[3]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7-8.
[4]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11.
[5]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98.
[6]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关于盗窃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调研报告[J].山东审判,2010(5).
[7]李照君,鲁石林,侯瑞盈.论扒窃行为入罪的标准——从王某某扒窃案谈起[J].法制与社会,2013(11中).
[8]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881.
[9]张明楷.盗窃罪的新课题[J].政治与法律,2011(8).
[10]车浩.“扒窃”入刑:贴身禁忌与行为人刑法[J].中国法学,2013 (1).
[11]陈忠林.常识、常理、常情:一种法治观与法学教育观[J].太平洋学报,2007(6).
[12]谢婷.扒窃司法适用新论——以两高最新司法解释为视角[J].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3).
[13]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59.
收稿日期:2014-10-23责任编校:陶范
【文章编号】1673―2391(2015)02―0074―04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D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