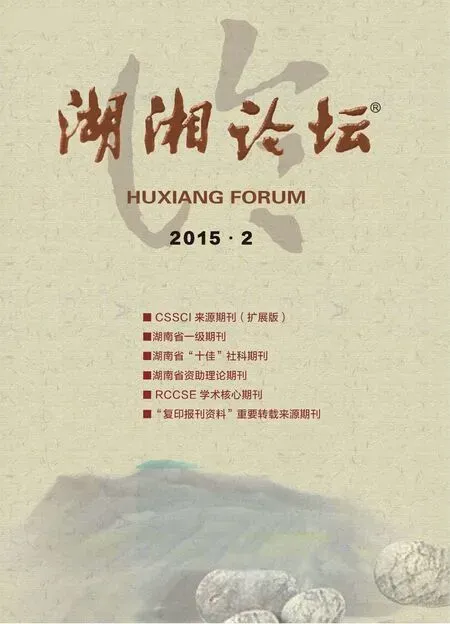论从知识到智慧的转向——兼析庄子“齐物论”篇的内在意蕴
2015-03-26代训锋
代训锋
(忻州师范学院,山西 忻州 034000)
庄子的“齐物论”篇一直以来被国内学者看做庄子思想中最具哲学韵味的核心内容,加之国学大师章太炎的一篇颇具分量的“齐物论释”,更显得此篇文本的重要性。但是,综合众多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其阐释“齐物论”大致有三种指向。一种是注重从“齐物论”整篇上来把握“齐物论”的思想,认为庄子阐述万物齐一于道,泯灭是非生死的思想,体现的是庄子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这一观点至今还有影响;另一种是从庄子“内七篇”、甚至从整个庄子文本出发来理解“齐物论”的思想,目的是为了阐明为实现自由逍遥的境界而必须走“齐物”的路径,这一观点也得到众多研究者的认可;第三种则是从“齐物论”中的个别关键词句来理解庄子“齐物论”的思想,如对“吾丧我”、“以明”、“物化”等词句的解释,体现的是对庄子“齐物论”思想脉路的把握,这有助于从整体上理解庄子的齐物论思想。
我不否认庄学研究者在“齐物论”的阐释上的累累成果和重要价值,而且,正是他们的研究成果,搭起了后学之辈向上攀登的阶梯。但是,我又不能不说,这些研究忽略了“齐物论”文本所表达的一种思想的重要转向,即:从知识到智慧的转向,具体地说就是,从“齐是非、齐生死、辩无胜”等这种对世界的认识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样的人生境界,它表达的是从“世界是什么和世界怎么样”到“人应该怎么活”的智慧追问和转向。冯契先生曾用“转识成智”来表达中国传统哲学的这个特点。那么,在“齐物论”中,这样的智慧追问和转向是怎么展开的呢?当然是从齐物开始的。
一、何谓齐物
作为篇名的“齐物论”,历代学者各抒己见,对这一题目做了大量的诠释,虽然对篇名诠释观点的差异显示了对“齐物”思想理解的不同,但是,从拘泥于篇名的理解来把握“齐物论”整个文本却是没有多少意义和价值的事情。因为重要的是如何理解和把握“齐物论”的整体思想,而不是“齐物论”这个题目表达了什么意思。不过,既然庄子在“齐物论”中表达了一种智慧的追问和转向,而且这种追问和转向又是从齐物开始的。所以,对“齐物论”这一题目的分析难以避免。
概括地说,对于“齐物论”这一题目,单从汉字的组合结构上来看,大体有两种说法:一是“齐物”论;二是齐“物论”。这两种理解都可以在庄子的“齐物论”文本里找到支持的根据。但是,对“齐物”论的认可度可能会更高。因为物而不是物之论才是庄子在“齐物论”中所要解决的问题。物之论是可以逃避的,你只要不参与物之讨论就行了。但是,物是无法逃避的,因为你生活在物的世界里,所以需要给予解决。这个解决当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解决,物理意义上的解决一般是指在物的形态上做出改变,譬如放大或缩小,甚至毁灭。这也不是心理意义上的解决,在某种心理状态下,你可以重视或者忽视某些事物,但这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上的心理活动,而与思辨和推理无关。也许,我们可以把庄子的解决称为哲学意义上的解决,它是通过思辨和推理的方式,经过对物的某种理解,在心和物之间达成某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物不足以为心累,心不至于为物役。
这种对物的理解,就是所谓的齐物。也许这是一个在常识看来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孟子所言:“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1]p114,你又如何去齐宇宙中这不齐的万物呢?其实,庄子就是在破常识,你当然不能以常识去理解庄子。以常识去理解庄子恰恰说明你不理解庄子,自然不能理解庄子怎么去齐物。在这里,庄子齐物的关键其实不是在于物,而是在于心。如孟子所言“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物是不齐的,各种各样,千差万别,但是,如果无心于不齐的话,这不齐的万物于我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以心来齐物,这是庄子的思路,那么,庄子又是怎样以心齐物的呢?
二、如何齐物
1.“吾丧我”与破成心
“齐物伦”的篇首就是从心开始的:“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2]p23-24在颜成子游的问话中,南郭子綦的特异之处就在于心如死灰状而不是形如槁木。形如槁木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做到,但是,心如死灰则非常人所能及,因为它意味着心的所有活动的丧失,意味着外物对于心不发生任何的影响。心当然存在,但是,又好像不存在一般,这就是“无心”,南郭子綦称之为“吾丧我”的状态。
什么是“吾丧我”?“吾”不就是“我”吗?在常人看来,这就是个文字游戏。其实不然,那么,“吾”和“我”究竟是什么呢?如果说“吾”是个整体的话,那么,“我”就应该是整体的“吾”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部分又是什么呢?显然不是形体,因为,没有了形体的“我”,“吾”也不存在了,那会是什么呢?是“心”吗?不错。那确实是一颗心,从颜成子游关于“心固可使如死灰”的问话中可推知。但是,它是一颗“成心”。从庄子的“人间世”篇中“心斋”的要求来看,“心”应该是虚的,虚室方能生白。但是,“成心”却是实的,它里面充满了善恶是非,它把世界区分为自己和他人或者他物,在这样的“成心”中,“我”就出现了,相应地,“你”和“他”也出现了。于是,在“我”、“你”和“他”之间就有了对立、紧张和冲突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我”就是一种执著于己的自我意识,一颗执著于己的“成心”,而“吾丧我”就是要破掉“成心”。
为什么要“吾丧我”?我们可以简单地说是为了齐物的需要,进一步地说,“我”的存在一定是对这个世界和自己都构成了某种伤害,因此才要去除。世界有“我”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世界会以“我”的方式被切割和划分,意味着“你的”、“我的”、“他的”等不同的“我”在不停的争斗着、冲突着、对立着。此种争斗和焦虑的状态正如庄子所言:“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其发若机栝,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其杀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之也;其厌也如缄,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2]p27-28大知是闲淡的,因为无“我”“无己”,小知不停的算计着、争斗着,因为有“我”有“成心”。在“成心”的状态中,生命真正的意义和价值被蒙蔽和淹没了,“成心”的活跃意味着真心的死亡,当世界被不同的“我”所包围时,呈现出来的是种种假象,而真实的世界却被隐藏。如同庄子所说的“人籁”、“地籁”和“天籁”。人们往往会陶醉于人籁,却忘记了它的所从出。但是,对庄子而言,再好的人籁他也不喜欢,因为里面有“我”有“成心”。
2.齐是非与辩无胜
世界就是世界,万物就是万物,原本无所谓是非的,只是在不同的“我”的眼中是不同的。这并不是说万物善变或者多变,更多的时候是因为人心的差异以及不同的“我”的存在。当时不是有儒家和墨家吗?儒家主张命,墨家就主张非命;儒家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墨家就主张明鬼;儒家主张乐,墨家就主张非乐……同样一个世界,同样一件事情,竟会有如此相反的主张,而且每个人都以为“我”是对的。这不禁让人疑惑:天下真的有这么多是非吗?到底谁的是非是真是非呢?
其实,世界原本无所谓是非的,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的特点和用途。这些特点在构成它们的优点的同时也构成了它们的限制。庄子说得对:“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2]p38。在物的世界里,万物实际上是互为彼此的,“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2]p35。万物如果从自己的角度来看,都是“此”,而他者都为“彼”;从他者的角度看,则他者为“此”,他者之外的事物都为“彼”。如此看来,彼此的区别都是相对的,如果互为彼此的万物执著于彼此间的区别,就如同狙公所养的猴子:同样七颗果实,朝三暮四则怒,朝四暮三则喜。猴子只看到彼此的区别,却没有看到彼此之间的相通,岂不悲哉!
人当然不是猴子,但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2]p35的道理,难道就一定明白吗?庄子的“方生之说”进一步揭示这个道理。“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2]p35-36这个世界时不分彼此的,此事物的“生”在彼事物看来就是“死”,此事物的“死”在彼事物看来就是“生”;我以为“可”的他以为“不可”,我以为“不可”的他以为“可”。究竟是“生”还是“死”?到底是“可”还是“不可”?单纯拘泥于物的立场,也许永远没有一个定论,也许永远会陷入纷争之中。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即“照之于天”,也就是以天观之,那么,生与死、可与不可、是与非之间的对立和争论立刻消失于无形,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没有分别的世界。
庄子不仅以“照之于天”来泯灭生死和是非的界限,而且又给出了一个停止纷争的理由,这就是所谓的“辩无胜”。庄子认为,辩论是无法决定胜负的。“即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闇,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2]p57-58对于喜欢辩论的人来说,这是一段既精彩又无法回避的文字。它告诉我们辩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与若不能相知也”。这意味着彼此之间永远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理解。在“我”之外,有着另外的众多的“我”,你必须承认他们的存在,这样,不同的“我”并存着,而且各自坚持着自己的立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岂止是“辩无胜”,恐怕辩论本身都失去了意义。
辩无胜的态度尽管揭示了辩论的相对性和无意义,但是,不管怎样,“辩”总是与“齐物”的态度是冲突的。那么,“齐物”需要什么样的态度呢?需要的是“相蕴”和“和之以天倪”。
3.“以相蕴”与“和天倪”
在长梧子回答瞿鹊子的对话中,庄子写道:“且女亦大早计,见卵而求时夜,见弹而求鸮炙。予尝为女妄言之,女以妄听之。奚旁日月,挟宇宙,为其吻合,置其滑涽,以隶相尊?众人役役,圣人愚钝,参万岁而一成纯。万物尽然,而以是相蕴。”[2]p52-53在这里,庄子提到了两种态度,一种是瞿鹊子的,看见鸡蛋就想到报晓的鸡,看见弹丸就想吃烧烤的鸟,未免算计得太早,这是“辩”的态度。另一种是与日月为伴,与宇宙为伍,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合万物为一体,置各种是非争论于不顾,无尊贵卑贱。这就是“相蕴”。前者属于众人的态度,因为无休止的争论,所以终身役役而不得解脱;后者是圣人的,因为万物相蕴,所以能合万物为一体。在万物相蕴中,所有的差别和是非都不存在了,心归于混朴和纯粹,在澄明纯粹的素朴之心中,万物彼此相蕴,没有绝对的界限,也没有绝对的对立,庄子把这个境界叫做“寓诸无竟”,这是一个没有差别和是非的境地,是世界本来的样子,这也才是心灵应该居住的地方,或者说,是心灵应该保持的状态。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值得向往的境界,但是,我们的心灵应该怎么努力才能拥有这样的境界呢?庄子认为必须要“和之以天倪”。“‘何谓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则是之异乎不是也亦无辩;然若果然也,则然之异乎不然也亦无辩。忘年忘义,振于无竟,故寓诸无竟。’”[2]p58-59天倪是自然的分际和界限,它不是人为设置的。是或不是,然或不然,不是凭借人的辩论来区分的,“是”如果真的是“是”的话,它和“不是”的区别是根本无需辩论的,“然”如果真的是“然”的话,它和“不然”的区别也是根本无需辩论的,“是”与“不是”、“然”与“不然”的分际是自然的,这就是“天倪”;由辩论所确定的“是与非”和“然与不然”的界限是人为的,是人倪,是“成心”。在这里,庄子通过对天倪和人为的界限的揭示来去除辩论和纷争,而去除辩论和纷争的方式就是“和”。这里的“和”绝不是在天倪和人为之间“和稀泥”。“和稀泥”是把自己作为第三方加入到辩论和争执当中,以中立者的身份在对立着的双方之间进行调和。而庄子的“和”则是和对立着的双方无关,它只和是非有关,是自己对待是非的一种态度。在“和”中,既没有了“你”、“我”、“他”的分别,也没有了“年”,没有了“义”,没有了彭祖和殇子,剩下的只是顺应万物的流变,即“因之以曼衍”,一切都融入无差别无是非的境地了。如老子所言:“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3]p113。
从整个过程来看,庄子齐物的方法就是“莫得其偶”。“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3]p36从常识来看,万物都是相对待而存在的,有“是”就有“非”,有“生”就有“死”,有“彼”就有“此”,有“我”就有“你”和“他”,但是,当去除了一方,另一方还存在吗?没有了“是”还有“非”吗?没有“生”还有“死”吗?没有了“彼”还有“此”吗?没有了“我”,还有“你”和“他”?当然就不存在了。当处于“莫得其偶”的状态时,万物就没有了区别,辩论也就失去了意义。“莫得其偶”的指向就是“相蕴”与“和之以天倪”。
但是,庄子仅仅是为了齐物而齐物吗?当然不是,其真正的用意是什么呢?其真正的用意就在于:在物的世界里,发现并坚持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说,“如何齐物”是认识层面的问题,那么,“为何齐物”就是智慧层面的问题。从“如何齐物”到“为何齐物”,庄子“齐物论”篇的思想就从关于“世界是什么和世界怎么样”的“知识论”转向了“人生应该怎么活”的“智慧说”。
三、为何齐物
生命的问题一直是庄子思想中的重要问题,对生命的关怀从未曾离开过庄子的视野。在“齐物论”中,庄子主张齐物,其用心同样出于对生命的呵护。因为只有齐物。才能让生命从物的世界里摆脱出来,心才可以“物物而不物于物”[3]p360。“物物”是做“物”的主宰,“物于物”是做“物”的奴隶。我们不能离开这个物的世界,但是,我们可以不在乎这个世界,不在乎这个世界的是非、生死、彼此等之间的区分和争论,在不在乎中,心获得了解放和自由。你有你的是非,他有他的彼此,一切都由它去吧,与我何干!我既不会作为第三者参与其中的纷争,也不会作为中立方做争执的裁判,我只是不在乎,这种态度,庄子称之为“两行”。“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3]p40。“行”包含有走路的意思。在物的世界里,人们在不同的路上竞逐着,彼此间争论着各自的是非,而我则静静地站在中间,站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任由他们争论者是非,我却心静如水。如果说是非之争是一个无穷的循环的话,我却把自己置于环中的位置时,不管环流的多么急促,环中的位置却永远是空灵静默的。这就是“得其环中,以应无穷”[3]p36吧。
在物的世界里行进竞走以至于流连忘返的人是可悲的。庄子说:“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3]p31-32他们在充满是非彼此的物的世界里冲突着、争论者,不死不休;欲望如同无底洞,一生为此疲于奔命,不知成功是何,不知生命归何!他们的心连同他们的形体都成为物的奴隶,活着无异于行尸走肉。也许,更可悲的是,他们并未意识到心的死亡,意识到心的死亡,或许还有重生的希望,意识不到则永无重生之日。难怪庄子叹言:“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3]p377
要使生命返归本真,首先是心的回归,只有破除“成心”,才可以把“心”从物的世界里超拔出来,“心”才不至于成为物的奴隶。“心”应该为自己找一个真正的家园和归宿,这个家园和归宿不是物,物的世界只是客栈,可以一宿不可以久留。真正的家园和归宿不在别处,而在于“道”。游“心”于“道”才可以找到自我,找回真实的生命感觉。这个时候,万物不会再构成对“心”的限制,也不会再成为“心”的负担,当然更不会成为生命的负担。因为和“道”一样,“心”已经与万物为一体了,沉浸在逍遥和恬静之中,这就是“道通为一”[3]p38,这就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3]p44。这个时候,作为“知识论”的“齐物论”被转化为作为“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的“齐物”[4]p90。
“齐物论”最后以庄周梦蝶这样一个美丽的梦来结束是颇有意味的。从知识论的角度看,它表达的是生命有了自觉意识后的理性追问,而追问的对象是:在弃绝一切是非、对待差别后的“我”;追问的问题则是我是谁?我在何处?什么是我?不过,这些问题在齐物之后已经是“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的“其知有所至”[3]p40的问题。但是,从生存的智慧来看,也许,庄周梦蝶旨在告诉我们,所谓的齐物只是一个梦,一个在梦中才可以实现的理想。只要你醒着,你就不得不面对现实世界中各种各样的、实实在在的区分和是非,并且会情不自禁的陷入其中。的确,你生活在一个现实的物的世界里,你不可能逃离被“物化”的命运,所以,我们在庄周梦蝶这个美丽的梦的后面,读出的是深深的无奈。不过,从美丽的梦境和深深的无奈中却透露出一种生存的智慧,那就是“形莫若就,心莫若和”[3]p90。当一个人只想顺应和因循这个世界的时候,任何的区分和是非还有什么意义吗?没有,一定没有。这个时候,齐物不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关于物的知识也在一个美丽的梦醒之后,转向了人生的智慧。
当然,这只是“齐物论”中所表达的一种转向,其目的在于人生的自由逍遥。这是本文最后要说的话。
[1]金良年.孟子译注·滕文公(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庄子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8.
[4]王博.庄子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