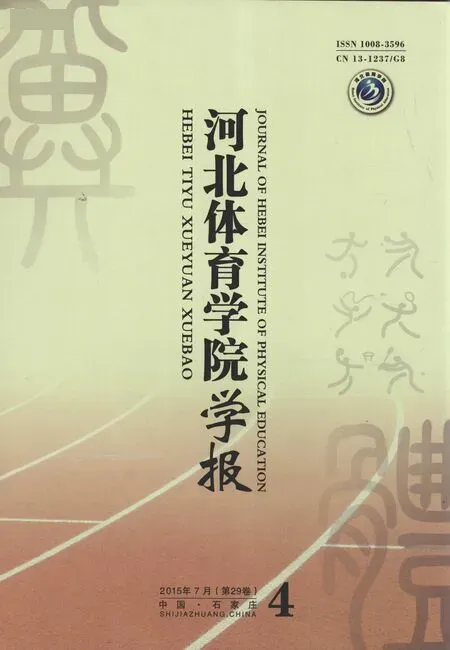物种间体育的动物权利与人类义务
2015-03-26樊东声
樊东声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南京 211188)
在人类的体育活动中会经常出现动物的身影,象征和平的鸽子早在第一届雅典奥运会上就开始展翅飞翔,憨态可掬的熊猫“盼盼”作为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吉祥物名声大噪,2006年多哈亚运会开幕式上的64 匹汗血宝马让人血脉偾张,而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更是将牛、马、羊、鸡、鸭、鹅和狗都搬上了表演舞台。在人类的体育活动中,动物并不仅仅只是负责助兴,也会直接参与人类的体育活动,比较引人注目的有马术、飞盘狗、职业骑牛、西班牙斗牛、垂钓以及已被法律明文禁止的英国猎狐运动等;此外,民间还留存了大量以动物争斗为竞猜对象的休闲活动,例如斗鸡、斗狗、斗蛐蛐等等。有学者将这种人类与动物共同参与的体育活动归类为“物种间体育”,在这类体育活动中,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有和谐的也有冲突的,但起主导作用的都是人类,而动物多是被动参与,这引发了人们对动物权利和人类义务的广泛讨论。
1 物种间体育的主要形式及存在的问题
1.1 物种间体育的主要形式
人类是地球上进化最为成功的物种,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人类逐步掌握了认识自然、发现规律和改变自然的能力,人类运用逻辑思维能力,通过有意识的活动构建了不同于自然界的人类社会,逐步从自然动物界分离出来。体育活动就是人类有意识的活动之一,体育活动有时是生存本能的体现,而更多的时候则是一种文化的展示和传承。动物参与人类体育的形式丰富多样,依据动物在人类体育中所起到的作用或用途,可以分为8个类别:①战斗成员(人类与动物互斗或动物之间的互斗);②猎物(狩猎和捕鱼);③食品(在体育比赛中消耗动物类食品);④用具(使用动物身体部分生产运动或休闲设备,以及以动物作为祭祀品);⑤运输(人与动物组合进行赛跑或技能比赛);⑥吉祥物(动物存在或人模仿动物);⑦被剥夺空间(人类运动空间的延伸侵占动物的生存空间);⑧被动的受体(动物试验)[1]。
物种间体育是人类与动物共同参与的体育活动,强调人与动物“同时在场”的互动竞技,参考上述动物参与体育的形式可以发现,动物充当战斗成员与人类互斗、充当猎物由人类捕获或猎杀、充当运输工具与人类组合进行赛跑或技能比赛这三种形式比较契合物种间体育这一概念的指涉。
1.2 存在的问题
动物参与人类体育的形式有些被视为司空见惯,例如动物充当吉祥物、动物进行运输、破坏动物栖息地修建体育场馆、利用动物身体部分制作体育用具和食品等,这类形式不仅在体育活动中存在,在日常生活中亦非常普遍;而有些动物参与人类体育的形式则产生了强烈争议,例如人与动物互斗、动物之间互斗、以动物为猎杀对象和实验对象等,这类形式受到了动物权利保护机构的强烈谴责,认为这极大地侵犯了动物的权利,特别是人与动物互斗的体育形式和以动物为猎杀对象的体育形式饱受指责。如上所述,物种间体育主要包括人类与动物互斗、人类捕获或猎杀动物,以及利用动物作为运输工具进行赛跑或技能比赛这三种体育形式。在这三种体育形式中,人类都是为了自身欲望而在战略性地使用动物,都是依据自身意图来界定两者的关系,因此存在较为突出的侵犯和伤害动物权利的问题。
2 动物权利的伤害
2.1 什么是权利
权利通常包含权能和利益两个方面,权能是指权利实现的可能性,而利益是权能现实化的结果[2]。权利意味着“有效诉求”,与义务是对立统一的。现实中存在两种权利,即法律权利和道德权利,两者乃实然与应然的关系。权利具有道德意义,即道德权利,道德权利指作为道德主体的人依据道德所应享有的道德自由、利益和对待[3]。道德权利是法律权利的母体,更具普适性,是权利的本质基础。
2.2 动物有权利吗
人类享有道德权利的首要原因在于人是一个生命主体,生命主体都具有某种“固有价值”,这种“固有价值”并不依赖于对他者的有用性与否而存在,具有“固有价值”的生命主体可以成长为道德主体,从而拥有道德权利。人类成长为道德主体并拥有道德权利的原因在于人类超越了简单的“使用与交换价值”的束缚,成为一个拥有复杂价值属性的生命主体,这些复杂价值包括信念、愿望、知觉、记忆、感知、情感、认同、思维和实践能力,以及独立于他人效用的权利。动物和人类一样是一个生命主体,它们的生命也具有“固有价值”,而且这种“固有价值”并不依赖于对人类的有用性与否而存在,同时动物也是拥有复杂价值属性的生命主体,只是在某些价值属性上动物与人类有所不同或有所欠缺,动物与人类的主要差距表现在智力和有效诉求能力方面,然而人类个体间的智力也有巨大差异,人类也有无法进行有效诉求的生命时期,难道我们可以歧视、伤害甚至杀害那些严重智力障碍者和刚出生的婴儿吗?如果依从这样的逻辑,人类的文明将不复存在。因此,如果人类想把权利赋予所有人类,那么相一致的,也必须将权利赋予非人类的动物。
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伦理学家乔尔·范伯格认为,权利产生于利益,最基础的利益包括:可预见的生命存续时间;身体健康和活力;身体的完整性和正常机能;没有承受痛苦和缺陷;情绪稳定性,没有无端的焦虑;正常的社会交往;能够容忍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一定程度上的免受干扰和胁迫的自由,以及其他一些长远的利益[1]。不言自明的是,如果基础权益受到侵害(特别是生命权),必然影响个体更高权益的获得。动物如果拥有道德权利,则也应拥有这些基础权益。
2.3 什么是伤害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道德和理想,是法律的基础和宗旨。公平正义要求尊重每个个体的权利,要求个体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避免伤害其他个体。但何谓伤害?问题看似简单,实则非常复杂。首先,伤害会导致痛苦,但导致痛苦的不一定是伤害,例如医生为病人实施手术会使病人身体痛苦,教师对犯错的学生进行批评也会使学生心理痛苦,但这并不是伤害,而仅仅是“对身体或心理施加的痛苦经历”,这类行为有时不仅无害反而有益。其次,伤害不一定需要“对身体或心理施加痛苦经历”,剥夺某些利益获得的可能性就能够制造伤害,例如安乐死,虽然无痛,但由于是过早地剥夺生命,因此可能是有害的,这也是安乐死还存在争议的原因。第三,伤害有时难以避免。自我防卫就是一个简单的例证,当个体受到其他个体的伤害威胁时,为了避免伤害只能选择伤害侵害者时,他就是在自我防卫,自我防卫有时可以变得极其复杂,例如相对于威胁程度的不同有可能出现防卫过度的问题。因此,在界定伤害时,应从受体境况变化的角度来考量,伤害意味着所做的事情使受体境况变得更糟。
2.4 动物权利受到伤害了吗
对人与动物互斗、人类捕获或猎杀动物以及利用动物作为运输工具进行赛跑或技能比赛这三种物种间体育的主要形式进行分析,物种间体育中人类与动物的关系主要有两种形式:①人类主导动物的行为模式,以获得消遣与娱乐,例如赛马、飞盘狗和职业骑牛;②以猎杀为目的的所谓“血腥体育”,人类歧视、虐待甚至杀戮动物,例如西班牙斗牛和英国猎狐。如果对照乔尔·范伯格的基础权益观点,物种间体育显然是伤害了动物的基础权益。“血腥体育”这种直接剥夺动物生命的体育活动,无疑是最彻底地伤害了动物权利,而人类主导动物行为模式的物种间体育,也由于限制了动物的自由、使其产生焦虑感而被认为是伤害了动物权利。
3 物种间体育中的人类义务
3.1 人类与动物的关系
“二元对立”的观点普遍存在于人类世界,例如自然与社会、科学与传统、人类与非人类。然而人类与非人类动物的关系并非对立的,人类与动物是协同进化、共享空间与资源的关系。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为我们准确理性地认知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拉图尔认为“二元对立”的观点不利于我们认知客观世界,客观世界是一个网络,它融合了自然与社会、科学与传统、人类与非人类,所有的所有都在网络之中,相互依存、共同构建客观世界。拉图尔认为,行动者网络中行动者之间关系是不确定的,每一个行动者都是一个结点,结点之间经通路连接,共同编织成一个无缝之网。在该网络中,没有所谓的中心,也没有主客体的对立,行动者们处于一种平权的地位。主体间是一种相互承认、相互认同、相互依存又相互影响的关系。非人的行动者通过有资格的“代言人”来获得主体的地位、资格和权利,以致可以共同营造一个相互协调的行动之网。虽然没有所谓的中心,但人类在这个网络中是强制性的通道点,因为人类决定了大多数参与联结的各个通道的形式和内容。行动者网络理论强调“人类与非人类在知识的形成中应被对等的看待,人类与非人类在知识的形成过程中都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可见,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消除了人与非人的鸿沟,解除了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为我们客观全面地认识世界网络提供了理论指引[4]。动物在物种间体育网络中也是一个行动者,基于行动者网络的动物与人类在主体权利上不存在差异,但人类作为网络构建的强制性通道点,往往自认为是网络的中心,自认为可以主宰一切,因此人类一直试图构建只对人类有利的道德体系,人类与动物的关系也走向异化。人类在定义道德体系时具有明显的傲慢与偏见,人类可以有意识地伤害动物,而动物却不能伤害人类,即使人类犯错在先。
3.2 物种间体育中的人类义务
体育是在公开的规则下自愿地进行对抗,即“自愿尝试克服不必要的障碍”[5]。大多数体育都呈现出合理性的伤害威胁,而像拳击这类直接身体对抗的体育项目,则是故意造成伤害。但是体育为参赛者提供了选择权利,即参赛或不参赛。在故意造成伤害的体育项目中,参赛者同意承担由于伤害造成的风险,即参赛者放弃了不受伤害的权利,因为他们要追求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东西。物种间体育中剥夺动物生命的行为无疑是对动物权利的伤害,而人类与动物合作完成竞赛的体育项目则在是否伤害动物权利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产生分歧的原因在于动物无法明确表达意愿,无法明确表达是否放弃自己的权利。因此只要人类将动物纳入体育,伤害动物权利的话题就会存在,但根据伤害的定义,物种间体育还是有存在的道德基础,在人类与动物合作的体育中,例如狗飞盘、马术等,动物得到了较好的照顾,动物的境况没有因为参与体育而变得更糟,动物的权利得到了尽可能少的侵害,得到了尽可能多的保护,因而这类物种间体育形式可以毫无争议地存在,所以马术运动就能被奥运会接受,也得到了人们的接纳和认可。
体育的本质目的显然不是伤害,如果体育主动选择伤害,它的代理成本将非常大,早期的角斗士竞技的代理成本就非常大,因此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消亡。人类没有为了体育而伤害动物的道德基础,因为作为一个生命主体,动物也有基础权益,不能因为人类自身不可告人的利益而伤害动物的基础权益,相反人类却有保护动物基础权益的义务。人类难以避免在体育中使用动物,但人类应该尽可能地保护动物的权利,人类在物种间体育中应尽量减少动物遭受不必要的痛苦,杜绝故意剥夺动物生命的行为,这不仅仅是基于动物的权利,更是基于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道德。对动物在体育中的使用,人类应以照顾为主,尽量摈弃不必要的伤害,有时体育规则的些许改变就能达到这些目的。动物权利论的倡导者汤姆·雷根更是进一步指出“每个动物都有不可替代和均一化的固有价值,动物权利是人权的一部分”[6],因此人类非但不能故意伤害动物,反而有主动保护动物的义务。
4 结语
物种间体育是人类与动物融合互动的一种方式,但其中却普遍存在着物种歧视和故意侵害动物权利的问题,其中“血腥体育”尤甚。动物拥有道德权利,人类没有故意伤害动物的道德基础,人类与动物实际上是协同发展的,并共同构建着客观世界的网络。人类在体育中难以避免使用动物,在物种间体育中,人类应尽到保护、照顾的义务,尽量避免使动物遭受不必要的痛苦,更应杜绝故意剥夺动物生命的行为。因此,人类主导动物的行为模式,以动物为运输工具进行赛跑或技能比赛的物种间体育形式可以适当存在,但要注意赛前、赛中和赛后的动物权利保障问题,而以剥夺动物生命为表现形式的“血腥体育”则是不道德的,理应受到谴责和制止,猎狐运动已被明令禁止,但西班牙斗牛运动仍然以民间传统文化为保护伞继续存在着,这场有关动物权利保护的讨论与斗争仍将持续下去。
[1]Gillett J,Gilbert M.Sport,Animals,and Society[M].Routledge,2014:270-275.
[2]唐金凤.从“权利”到“权力”:网络话语权定义的重构[J].新闻研究导刊,2011(2):35-37.
[3]李建华,周蓉.道德权利与公民道德建设[J].伦理学研究,2002(1):16-20.
[4]刘济亮.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06:24-28.
[5]Suits B.The Grasshopper:Games,Life and Utopia[M].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78:73.
[6]彼得·辛格.动物权利与人类义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