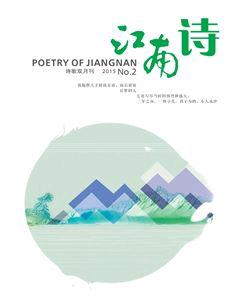“谦卑”是摄影的开始
2015-03-23沈苇ShenWei王寅WangYan
◎沈苇 Shen Wei / 王寅 Wang Yan
“谦卑”是摄影的开始
◎沈苇 Shen Wei / 王寅 Wang Yan
沈 苇:从诗到摄影的跨界,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摄影反过来对诗歌写作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和益处?譬如观察方式、纪实性、物象和瞬息的捕获以及加倍的“凝视”,等等。
王 寅:摄影是突然到来的,就像夏天和爱情一样不可阻挡。直觉就是我的技巧,这和诗歌创作如出一辙。
摄影教会我观看世界的别样方式,就像诗歌教会我歌唱和聆听一样。摄影让我更多地接触到现实世界神秘的部分,我经常在照片的暗处发现那些肉眼没有察觉之物、那些看不见的幽灵:隐藏在黑暗中的人、一道隐秘的光亮。一个不知来自何方的奇怪物体……
诗和摄影采用不同媒介,但两者又有很多共同之处,词语、色彩、韵律和意象,诗歌中有的,摄影中也有。相对而言,诗在表达上更趋于抽象,摄影则要具体得多,摄影看似直接和安静,但也隐藏了更多的隐喻和解读的可能,诗歌的呈现则更为赤裸。
创作经常是盲目和自发的,可以从一首诗出发,也可以从按下快门出发,一切取决于机缘和情绪。我很喜欢曼雷的一段话话,稍稍改动了一下:“我用摄影表达诗歌不能表达的,我用诗歌表达摄影不能表达的。”
加倍的“凝视”,说得非常好!其实不仅是凝视加了好几倍,而且还加大了焦距。摄影对诗歌写作的影响和益处是显而易见的,让我更专注、更细致,这种影响当然也是双向的,我也会把诗歌的手法用到摄影中间去,譬如跳跃、拼贴,好像这也早已经是摄影常用的手法。
一开始,我不太愿意将摄影与诗人的身份联系在一起,但后来发现诗人是无法摆脱的身份,人们总是试图在我的照片里寻找诗意。也有人不相信能同时做好两件不同的事,写诗和做记者、写诗和摄影。为什么不能做好呢?行业的分类是人为的,创造力则是无边界的。
沈 苇:《摄手记》中,许多作品令人过目不忘,如波兰的雪、宏村的大白菜、喀什噶尔的小女孩等,就像出色的诗句一样,直指人心。摄影的极致是否契合诗的境界和追求,或者,变成了一首诗?存不存在一种你心仪的“摄影诗学”,还是亲历与实践更为重要?
王 寅:诗可以是抽象,也可以是具体的,但摄影大多是具体的,你的问题让我想到了对物的关注和表现。由于照片是一个一个瞬间点状构成的,所以摄影的意味往往是靠画面之外延展的信息来传递的,这是摄影的妙处,这一点也与诗的精神极为吻合。
摄影和诗歌的关系,就像左手和右手,有时候它们会在黑暗中互相换位,摄影把不可见的拍给你看,诗歌则是把可见之物变成节奏和音律,这感觉非常奇妙,一切的变化在目光和双手之间、双手和物体之间,意念和时间之间。
沈 苇:你的摄影作品,风格上明亮、干净、温情,在城市纪实摄影中,“穷街陋巷也得到体谅”。而诗歌,你自己说有一种“黑暗基调”。我的理解是“风暴的平生”和“利斧的寂静”的一种交融。为什么差异性会这么大?
王 寅:这个现象有不少朋友也都注意到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我自己也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只能说摄影暴露了我内心的温暖阳光的一面。我诗歌的黑暗基调似乎更符合当下流行的美学观念,人们排斥明亮温暖,更认可黑暗和苦难,但这只是此一时流行的美学而已。明媚也是黑暗的变异,明媚与黑暗,都是现实和想象的一部分,何来高下。
我一向对色彩比较敏感,不会拍黑白照片,也就很难和暗黑风格有缘。在我的那些阳光明媚的照片里,阴影尽管不是主体,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如果没有这些浓重得省略了细节的阴影,这些照片就无法成立。要知道,即使在阴雨天气,也是有阴影的,而且更妙不可言,但无须言明并说出。
沈 苇:我认识的许多诗人,照片都拍得好,有感觉,但缺少你的那种持续和专注。有人说:与其费劲去培养一个摄影家,还不如把一台相机直接交给一位诗人得了。你同意这句话吗?
王 寅:这句话是玛格南摄影师塞尔吉奥·拉莱说的,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是相信诗人会很受用。从买了第一台数码相机开始,拍照至今也已经十一年了,最大的感受并不是拍了多少照片,而是感受到创作的快乐。多拍总是不错的,但我现在按动快门的次数越来越少了,经验告诉我,应该在哪里等待,知道哪些应该拍,哪些会出好照片。
“把一台相机直接交给一位诗人”,有一定的道理。诗人更相信直觉,而非理性。这有助于拍出好照片的。中外诗人作家中,爱好摄影的数量并不少,有些水平还很高,譬如金斯伯格、吉增刚造、安部公房……并不是所有的诗人喜欢拍照,但是好的摄影师一定具有诗人气质,我对诗人气质的理解是爱幻想、纯粹……
沈 苇:你去过30多个国家,在国外,摄影状态与在国内是否有所不同?谈谈最为难忘的一两次经历。
王 寅:我去过的国家并不多,有些去一次足矣,有些你却愿意一去再去,有些则是在你抵达的那一刻就知道一定会再来。我多次提及2005年冬天难忘的波兰之旅,本是应邀参加诗歌节,但却是以摄影完成了旅途中的纪录。去的时候,正逢欧洲十年一遇的奇寒,所有的城市都被大雪覆盖,冻彻肌肤的温度让注意力更集中,除了雪的记忆,还有各种意想不到的奇遇。扫街时实在冻得受不了,就跑进教堂或咖啡馆暖暖身子回回神。有时候咖啡还没喝完,鞋子上融化的雪泥已经在咖啡馆干净的地面留下黑色的水迹,十分尴尬窘迫。在离开卡托维茨的时候,波兰朋友随手一指路边的一座建筑:那是热奈曾经被关押过的监狱。后来,果然在热奈的书里查到了相关信息。
沈 苇:你多次引用波德里亚的话,摄影“有一种把自己委身于幸福的偶然性”。波德里亚同时说,这近乎“催眠状态”。这是怎样的一种状态?
王 寅:我把波德里亚视为摄影的偶像,因为他的业余摄影身份,也因为他的这句话。在陌生的城市漫无目的地闲逛,就是为了拍照。街拍时常迷路,也因此经常有意料之外的发现,有时候出门到了车站,哪一路公车或火车先来,就跟着去哪里的。
我拍的照片中,最受欢迎的还是那些孤立的城市风景,有的被收藏,有的做成了翻译小说的封面——无人的咖啡馆和餐厅、寂寥的街道、空空的长椅,有人生活的痕迹,有移动的光影,却空无一人。
摄影是一次等待,等待合适的光线、物体、构图达到那一个点,其实也是它们在等待我的到达它们面前,站到合适的点上,把所有的偶然集中在一起,完成最后一击。
沈 苇:你曾说,“时间之外的一切,也许只是多余的忧愁”。那么,摄影也是一种忧愁么?因何而忧?忧在何处?我的理解,最终是否会变成“以忧解忧”?
王 寅:摄影确实让人忧愁,但如果不摄影是否会更忧愁?
摄影和季节和光线打交道,简而言之,是和岁月打交道,所以等待、期待都足以产生浓郁的愁绪。
忧愁是各种情绪的代名词,诗人奈丽·萨克斯说过:“在教我们再次生活时,请务必温柔。”摄影就是一个温柔的教师,教我重新学会用心灵观看和倾听,不论是用词语还是用图像。在空白处写下诗行,在储存卡上拍下像素,你正激烈奔跑的时候,表现出的恰恰是相反的宁静。
保留必要的阴影吧,就像保留忧愁,而不是简单地驱逐它。
我并不看重已经拍下的照片,它们太轻巧、太好看、来得太容易,我应该可以拍得更好,现在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即将要进行的主题摄影准备的热身,技术的、心理的和身体的。
沈 苇:我现在出门基本不带相机,手机用的也是非智能的,是个落伍者。因为感到每次旅行拍回来的照片,大多没有意思,更无保存价值。影像的泛滥,让我有点不知所措。如果以忧解忧是可能的,对摄影的热爱,能否可以理解为用影像反对影像、用瞬间反抗瞬间?
王 寅:影像泛滥是数码时代的特征,就像文字在数码时代依然泛滥一样。但是好的照片和好的文字是同样稀缺的。如果不带手机出门,很有可能就会与好照片失之交臂,这是我的经验之谈,我不一定背上大相机,但一定会带上手机,在最短的时间里拍下中意的画面,而不是徒留遗憾。
沈 苇:iPhone你现在用得比较多,与数码相机相比,除了便捷和隐蔽,它还有哪些好处?
王 寅:科技的进步和发展为摄影带来了无穷的可能性。iPhone越来越好用,小巧实用、携带方便,像素也越来越高,也许有一天最终会取代数码相机。最有意思的是它的模样并不像一架照相机。
沈 苇:在这个“显时代”,我理解的摄影是一种“隐”,——摄影家是躲在镜头后面的隐者,尔后变成自己作品中的隐者。这种“隐”,与其说是主体的“低调”,还不如说更接近艾略特所说的“谦卑”(“谦卑是无穷无尽的”)。它,是否就是摄影的一个开始?
王 寅:摄影“隐”的存在方式和作品的呈现方式都非常符合我的气质和个性,这也是我选择摄影的理由之一。摄影是以过去时态存在的,即使是在一秒钟前刚拍下的照片也是过去时的,自然就过滤了时间的杂质。好的摄影不需要文字说明,简单、生动,本身就能说话,而且释义更广阔,多好!“谦卑”是摄影的开始,也应该贯彻始终,直至我们拍下此生的最后一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