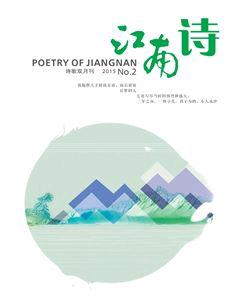《编年体史记》创作手记
2015-03-23谷雨GuYu
◎谷雨 Gu Yu
《编年体史记》创作手记
◎谷雨 Gu Yu
所谓距离产生美,陌生的东西更能带来新鲜的元素。
大约四五年前,出于对历史的喜爱,同时写作也面临雷同的风险,我突然有意识地将目光投放到更久远的从前,试图创作一部更具独特性的作品,重新构建一个新的诗歌写作体系,从而产生了要写一本新诗集的想法,名字就叫《编年体史记》。
一
早在2002年,诗人木朵在一封来信中谈到写作的困惑与焦虑:
天才是强者,他的时代是弱者。他的力量使得步其后尘者——而不是使他自己——精疲力竭。他淹没了他们。每个国家,每一个根本性时代都存在这样的强者,在英国是弥尔顿,在德国是歌德,在美国是爱默生,都是“相信自己完全不可能患上创造性焦虑”的人。然而在中国,是什么使我们精疲力竭?是五千年古代文化,还是无边无际的世界文化,抑或建国以来一个声音的文化?
老实说,我在2010年时选择构思和创作《编年体史记》,主要原因也是因为自己正面临写作的困惑和焦虑。
诗人欧阳江河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人的写作想有多自由就能有多自由,但是,真正有意义的和有价值的写作肯定存在着限制。问题是,对于这限制是什么,在哪里,我们往往茫无所知。
在此之前,我时刻都在求新求变,寄希望于通过语言、意象、结构、技巧等的变革,推陈出新,只为寻求更多的可能性。我们在谈论米沃什,卡瓦菲斯和博尔赫斯们,其实也是在穷究自身,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发音。然则,每到一个阶段末尾,我都面临重复的焦虑,担心“把自己毁掉的危险总是近在眼前”。因而,创造一种新的诗歌语言,一种新的写作体系,于我似乎更迫在眉睫。也是到了这个阶段,我对好诗的标准有了新的定义,我认为一首好诗必须兼备三个核心要素:对事物的命名,和体系的重构;诗歌中蕴藏的情绪,即情感唤起力;作品的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
诗歌就是对万物的命名和重构,所谓的主义和流派之争,到头来不过是对命名之争,体系的重构之争,试图通过主义和流派,在庞大的诗歌语系中确立自己的坐标点,尽管如此,其对命名和重构的价值仍然存在;
情感唤起力不难理解,一切伟大的作品,其核心都必然具备情感的唤起力,在独特的体验中蕴含人类普遍的情感体验和共鸣,很难想象,没有情感的东西如何获得人们的认同?
就像《诗经》,起源于先秦歌谣,这些民间歌谣来自不同地域,不同风格,集结了人类普遍的情感体验,成为一代雅集。
关于诗歌的独特性,我的理解是,要么开创一种新的语言体系,要么形成一种全新的风格,或具备复杂的结构、技巧等,是前所未有的,甚至影响后来者的作品。就像卡夫卡的荒诞,艾略特的玄学,佩索阿的“我之非我”……
而诗歌的不可复制性,试举几例:欧阳江河的《手枪》、伊沙的《结结巴巴》、阿斐的《众口铄金》、唐不遇的《第一祈祷词》(还有目前正被网络炒得火热的诗人余秀华的作品)。
类似这样的诗歌作品必然是不可复制的,是浑然天成的,是在语言或风格或结构上独一无二的。
二
五年前,我鬼迷心窍地开始读《史记》,读《资治通鉴》,读着读着,顿觉豁然开朗。我在想,诗歌可否写史?回顾我所接触到的诗歌作品,惟一能让我想起来的是大师级的诗人卡瓦菲斯。
在黄灿然先生翻译的《卡瓦菲斯诗集》中,卡瓦菲斯写史的诗歌占了整本诗集的三分之一以上,且有着非常独特的语言体系,带给人们全新的阅读感受。
诗人余西说,希腊诗人卡瓦菲斯的诗可以分为两类:当代的和历史的。前者表现诗人的生活,尽管他在诗中所留给自己的位置让人觉得类似于虚构,尽管这种生活对于我们来说更像是一段旖靡而遥远的历史。而在后者,卡瓦菲斯像是一位在古希腊罗马的历史时空中的漫游者,在历史的缝隙间虚构出自足的家园。
到了去年还是前年,我在《读诗》中发现,诗人柏桦也在写史,名字居然就叫《史记》,写了诸多晚清和民国轶事,很有意思,各种材料信手拈来,就像一个拼图游戏,以诗歌的方式完成一个个新拼图,惟一让人美中不足的是,诗人过于依赖其材料,有掉书袋和堆砌材料之嫌。
但是不管怎样,事实证明,以诗歌写史是可行的,但不只是材料,单纯还原历史本真,而是像历史学家杜兰特那样,以一己之力,历时50年,以一种新的体系和架构,创作出11卷本的《世界文明史》。
历史本身足够曲折迷人,足够波澜壮阔。
当然,更迷人的内容或许藏身于历史的阴影和隐蔽之处。对于未知和陌生,我们似乎有更多的想象和推演空间,也容纳了更多可能性。
无论大到国家的政治权力、战争、谋略,还是小到一个黎民百姓的私人生活,我们总能在历史中发现其惊人的相似和不同。
更有意思的是,我们所理解的古人,他们是否和真如史官所记录的那样?或许,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番面貌?作家潘军在中篇小说《重瞳》中写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项羽,是参照历史,对项羽人性的挖掘分析后的重新阐释和解读。
也许,这只是一次误读。就像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谁能保证自己看到的历史就是历史的本真?
……
三
从动念头到落笔,我拖了整整两年时间。我一直在想,作为一个想要超越自我的大工程,《编年体史记》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曾构思过两个版本的解决方案,一个版本是诗集,一个版本是故事体。
故事体不难理解,就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进行,但这个故事不能是单纯的翻译和剪裁,而是在纵览全局的基础上,搭建全新的体系,其中有自己语言和逻辑阐述的故事,有推演和分析,有对未解之谜的可能性带来的疑问……
难的是诗歌体。
我如何用诗歌的方式重新演绎这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2012年4月,我很突兀地写下《编年体史记》的第一首诗,很惭愧,没有按照顺序来写——就像翻一本新书,没看开头,直接跳跃到书中随意的某一章节,开始没有秩序的阅读——而是直接截取陈胜吴广起义的这一章节,并命名曰《苟富贵,勿相忘》,姑且摘取如下:
苟富贵,勿相忘
——公元前208年,陈胜兵败被杀
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
——《史记·陈涉世家》
落魄的人为王,终究不忘草莽的习性
骨子里摆脱不了小人得志的肤浅
和胆怯,就像屋檐下摔倒的孩子
嘴里塞满了泥土。
不问出身、贵贱,出身和贵贱可以更改
就如乌鸦和喜鹊的命运任意置换
占卜吉凶,问卜鬼神
所谓谋略,不过是塞进鱼肚里的朱砂和白绸布
是深夜里的篝火古庙,狐狸混迹于人间的叫喊——
当然,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著书的史官并不知道,那个落魄的王
是我[1]我:陈涉(陈胜)幼时的乡党,像一个掘墓人,以他的视角讲述陈胜的身前身后事,颠覆了史官的溢美之词(譬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是攫取了陈胜称王后阴暗、冷酷,和背信弃义的一面。幼时的乡党,与我曾有盟约:
——苟富贵,无相忘[2]苟富贵,无相忘:如果将来谁富贵了,千万不要忘了对方啊。。
但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曾经的盟约都是狗屁,我被斩杀后
人世噤声。
我与此人再无新仇,惟有背负一生的
耻辱和旧恨。
这个短命的王,这个给了我耻辱的人
有鬼一样的名字,和弹药库的脑袋。
之所以先写这一首,或许和当时的尴尬处境有关。
简单交代一下苟富贵,勿相忘的时代背景,说的是带领农民起义,建立新楚政权的大王陈胜,在此之前曾是农奴,和一乡党做农奴时立下誓言:苟富贵,勿相忘(如果有一天,我们中间谁要是富贵了,千万不要忘了对方啊)。
抱着这个约定,这个乡党辗转找到陈胜,跟陈胜的部下说:我和你们大王以前一起做过农奴,当时曾立誓:苟富贵,勿相忘。我来投奔你们大王来了。
下属向陈胜反馈,此人会坏了大王的名声。
于是乎,陈胜一刀把此人给杀了,斩断曾经所谓的誓言。
而我也看到了大众眼中不一样的陈胜,我看到的不是那个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陈胜,也不是那个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陈胜,是阴暗、冷酷、背信弃义的陈胜,是兵败后被车夫所杀的陈胜。
此后,我相继写下《千古一帝》、《十面埋伏》、《鸟尽弓藏》等。
基本构架搭建完毕后,后续的创作似乎更加流畅。
我从三皇五帝开始写起,而后到夏商周(含春秋战国),写到战国四公子的春申君时暂时告一段落,也赶上更为繁琐的事务,更担心作品出现同质化。只是未曾料到,这一耽搁又是两年时间过去了。
当然,心境和以前又有所不同。我已经不再谈少年心性,不再谈爱憎分明。
四
写下第一首诗后,我开始从宏观的层面构思《编年体史记》的写作体例,就像互联网里的产品经理,通过思维导图,构建一个全新的产品体系。
——既然是编年体史记,毫无疑问,写作上肯定以时间为轴,由古至今;
——人是历史的核心,是惟一具备认知革命的动物,所以,我写的仍然是人,和事;
——历史事实不会改变,也不能改变,能改变的是逻辑的反向推演,是分析和阐述更多的可能性;
——体例上最核心的产品是诗歌,当然也有可能是散文、小说、戏剧、日记、书信,表达形式上也可能是表格、图片等各种可能出现的文字和符号。也就是说,必须是多元素的、有厚度的、有层次感的架构,像一座房屋,不只是有几根木头固定在那里,而是更像一个食物链,彼此互联互通;
——格式上有序言,有引言,有诗歌,有注释。序言是一根线,贯穿始终,成为一个庞大体系中的整体,而不是冷漠的孤岛;引言全部源自《史记》,是对诗歌中人和事主旨的引申和佐证;诗歌无须多言,自然是创作中的主体,是拆卸、分解、重组,是一个崭新的生命体,带着古人的言辞和时间应有的温度,是我在历史长河里的一次自由穿越;注释更好理解,是对古时的人和事的诠释。
……
如上所说,我写到齐桓公时用的是自序,写《史官》时用的是散文,写楚灵王逃亡荒野时用的是日记。
五
人到了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想法和诉求。这符合马斯洛的需求理论。
有时,我甚至一厢情愿地理解为,我的停笔恰恰是在思考,如何规避作品的同质化?如何推倒旧有的风格、修辞和技巧,重建一个新的风格,截然不同味道的诗歌来?
如果创作没有了创新,停留在原地踏步,我想,这是对自身最大的辱没和戕害。
但,旧秩序的惯性总是会把我引入同一片泥淖,让我茫然。
因而,最初希望在半年一年内完成这部《编年体史记》似乎成为一纸空谈。
我一拖再拖,等待不同语言的诞生。
我还想把我分身为另一个我,一个和之前的我完全不同的我,帮我完成《编年体史记》未完成的章节,或是,分身出第三个我,他们分别扮演不同的性格、角色,运用不同的语言和技巧之梁,在宏大叙事的框架规则内,完成各自的使命。
可惜,这只是我的幻想。
如果可能,请允许我在风景深处小睡片刻,在历史最隐蔽的角落观察片刻,寄希望于上帝之手,搬走这浩瀚时间里苍茫的阴影和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