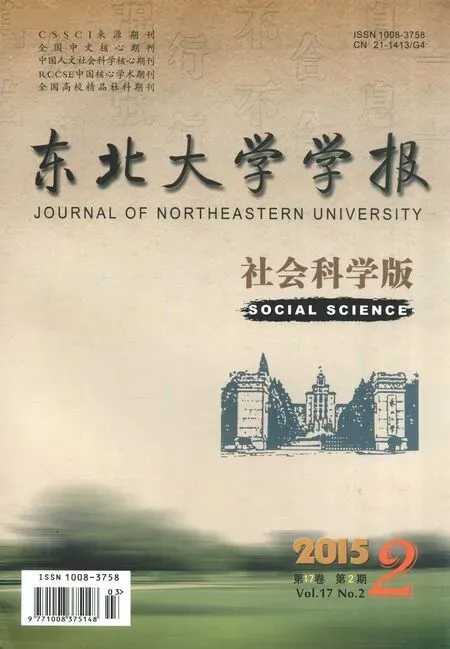苏佩斯成像实验及其哲学影响
2015-03-23杨庆峰
——————————--
苏佩斯成像实验及其哲学影响
杨庆峰
(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上海200444)
摘要:苏佩斯利用现代成像技术对大脑认知活动进行成像实验,这一实验意义重要但是却被忽略。这一实验成立的技术基础是脑电图(EEG)、脑磁图(MEG)、正电子成像术(PET)、功能磁核共振成像(fMRI)等四类大脑成像技术的成熟应用;哲学基础是技术图像的相似性,依赖于图像形状的概率相似;伦理基础是实验者的自愿。前者是外在基础;后两者构成了内在基础。它对整个哲学传统中物与观念之间的区分提出挑战,尤其是对现象学中关于“事物意向与观念意向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分”的命题提出了挑战。所以成为现象学的科学哲学需要面对的问题。
关键词:苏佩斯实验; 现象学; 图像; 意向性
doi:10.15936/j.cnki.1008-3758.2015.02.004
收稿日期:2014-08-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13YJA720021)。
作者简介:杨庆峰(1974-),男,陕西白水人,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技术哲学、图像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15)02-0129-06
Abstract:By using modern imaging technologies, Patrick Colonel Suppes did experiments on the brain’s cognitive activities. Despite great significance, his experiments have been literally ignored. The technological foundation of Suppes’s experiments is the mature application of four types of imaging technology on brain, including EEG, MEG, PET and fMRI;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is the similarity of technological image, which relies on the probabilistic similarity of image shapes; and the ethical foundation is the participants’ voluntariness. They work together to form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foundations. Since Suppes’s experiments pose challenges to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object and concept in the philosophical system, particularly the basic distinction between object intentionality and concept intentionality, they must be confronted in the scientific philosophy of phenomenology.
On Suppes’s Imaging Experiments and Their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
YANGQing-feng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Key words:Suppes’s experiment; phenomenology; image; intentionality
从哲学史上看,物与观念之间的区分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知识论传统从命题来源、命题性质给予了区分分析。现象学传统则从意向行为产出阐述了二者的不同,如胡塞尔从意向体验角度阐述了指向个别的“三角形”与指向普遍三角形观念之间的区分。但是随着脑科学、图像技术的发展,这些科学实验却论证了两种命题相似的结论。美国斯坦福大学科学哲学教授帕特里克·苏佩斯(Patrick Colonel Suppes,1922-)就是非常典型的代表。本文将从苏佩斯成像实验开始,展开分析这一实验成立的基础及其所产生的哲学影响。
一、 苏佩斯实验:科学哲学中未被注意的实验
20世纪90年代,苏佩斯利用现代成像技术记录了大脑认知活动的图像,为了更好地论证其结果,他一共做了三个实验,我们把这三个实验共同称之为苏佩斯实验。这一实验为我们展现了现代成像技术发展对于哲学可能带来的冲击。
在成像技术成熟的基础上,苏佩斯利用核磁共振技术做了三个相关实验。“1996年,特别是在纽约大学师从随萨姆·威廉森和劳埃德·考夫曼刚获得博士学位的吕忠林协助下,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的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做MEG实验。”[1]687他的三个实验情况如下:
第一个实验是指向受试者之间的不变性。这个实验面向9个实验对象,实验者向9个受试者提供48个关于欧洲地理的句子,实验要求受试者判断句子的真假,同时,当受试者听到这些句子或读出一台计算机屏幕上逐词显示的这些句子时,进行脑电图(EEG)记录。其中的一个句子是“意大利的首都不是巴黎,华沙是奥地利最大的城市”[1]694。记录下其中5个受试者的数据求平均,形成这48个句子的原型;记录下其他4个受试者的数据,形成每一个句子相应的平均后的测试样本。实验结果:受试者之间脑电图不变。
第二个实验是向受试者直观呈现100个不同的地理句子。实验关注一个受试者(S32)从100个句子中正确识别出93个句子的显著结果。实验结果:单独一位受试者所达到的最好的识别率是93%,即从100个测试样本中识别出93个。这一结果说明受试者能正确识别出93个句子。
第三个实验是视觉图像实验,测试受试者看到同一句子和听到同一句子脑活动图像的差异。实验结果显示:对简单形状(圆或者三角形)的视觉图像非常类似于相应词产生的大脑图像。
我们把这三个不同的实验统称为苏佩斯实验,这一实验的总体结果是表明“关于表征的必然的、主要的经验结果可能是当前所获得唯一结果”[1]719。就其哲学影响而言,这三个实验最为重要的是实验3。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其一,从实验所关注的问题本身看,实验1主要研究实验者在判断、识别句子真假过程中脑电图的差异;实验2所研究的是实验者正确识别句子的情况,这两个实验所着眼的问题相对小一些,不具备普遍性;实验3所研究的问题是与哲学史上的主要问题相关——物与观念之间的差别。这一问题首先表现在贝克莱,其次体现在胡塞尔现象学中的问题即:当一个人看到一个对象和听到同一个对象的名称的时候,这两个行为之间是否存在着差异?其二,从实验方法看,实验3是采取脑电图对照的方法来研究上述问题,即对比二者心理活动所产生的脑电图图像来得出结论。
所以,本文所指的这一实验的哲学影响是从更大的哲学视域来看的,尤其是借助现象学来分析这一实验对哲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具体分析将在后面展开。在展开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实验3的基本结论:该实验的结果是“简单形状和简单色块产生的脑电图,与它们的口头名称所产生的那些脑电图惊人地相似。这种结论,与听觉记忆和视觉记忆的广泛的心理学研究一起,支持了贝克莱和休谟所猜想的解答”[1]698。苏佩斯所提到的实验所推演出来的结论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基于听觉的脑图像与基于视觉的脑图像之间的相似性所导致的结果是完全冲击了由胡塞尔所确立起来的区分:事物意向与观念意向之间的差异。这一结果意味着当我观察“三角形”事物的东西,定然会在脑部产生相应的认知图像A。同样,当我听到“三角形”这一词语时,脑部也产生了相应的认知图像B,而A与B之间存在很大的相似性。这意味着这一实验不仅没有确证胡塞尔上述命题——二者的区分,反而批判着胡塞尔的命题。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苏佩斯实验本身及其所产生的哲学影响呢?
二、 苏佩斯实验成立的基础
苏佩斯实验之所以成立具备四种基础:技术基础、哲学基础、伦理基础和科学基础。技术基础在于成像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对大脑认知活动给予成像,它可以被称为外在基础。哲学基础在于依赖于图像的相似性,这是内在基础。另外可以称之为内在的是伦理基础,它是建立在受试者自愿的基础上,但是其伦理基础并不牢固,还是存在问题。科学基础主要是来自认知科学的支持。
苏佩斯实验成立的技术基础是现代成像技术,尤其是对大脑有关的成像技术。现代成像技术不仅是能够对自然物形态成像,还可以对自然物内部结构进行成像,最新的技术发展表明可以对思维的载体——大脑的内部甚至脑部认知活动进行成像*比如由浙江大学医学部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情感和记忆的神经环路基础”主要是为了解释大脑记忆与情感活动的神经环路技术,在这一研究中就会采用上述方法来对大脑进行成像。。科学哲学家苏佩斯描述了他的实验所涉及到的四种方法。“当前观察大脑活动的四种主要方法是很容易描述的。第一种方法是已经提到的经典的脑电图(EEG)观察,这一点很重要,它至少有千分之一秒的时间分辨率。第二种方法是现代的磁场观察,而不是电场观察,这是在脑磁图(MEG)的标题下进行的。这种方法也有近似于千分之一秒的相同的时间分辨率。第三种方法是正电子成像术(PET),……这种方法有利于观察大脑活动的定位,但只有一秒的时间分辨率。最后,当前最流行的方法是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它的最大优点是,在大脑中很好定位的地方,观察能量的吸收,但不幸的是,也有不小于一秒的时间分辨率。”[1]186除了这四种方法之外,还有很多如Evoked Potntial、TMS、Lessions、Classical Histology等方法。这些都属于神经系统的测量方法。苏佩斯的实验主要是利用了脑电图和脑磁图两类成像技术。
苏佩斯所提到的脑成像技术是有一定根据的。根据神经生物学家自己的描述,相关的技术也是上述四类,只是他们的强调点略有不同。“在我们转向这一任务之前,我们应该先谈一下使我们能把活人脑的活动景象勾画出来的一些新老技术。这些技术对于考察健康和患病时的意识神经相关物有极大的价值。……这些技术包括脑电图(EEG)和脑磁图(MEG),它们分别测量由几百万个神经元的同步活动所产生的微小的电位和电流;……这些技术有很高的时间分辨率,但要用它们对神经元群作精确定位尚不太胜任。其他一些技术,例如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和功能磁核共振成像(fMRI),虽然时间分辨率差一些,但可以在很高的空间经度得出脑代谢和脑血流的相对变化,因此能为我们提供活脑在工作时的宝贵图像。在我们讨论到许多与意识经验有关的脑区时常常要提到这些技术。”[2]
然而,苏佩斯所采用的脑电图和脑磁图技术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传统扫描技术所获图像展示的大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脑,我们看到的不过是大脑表面的影子。”[3]2012年哈佛大学的加恩·维登教授表示,借助于新型核磁共振技术获取的彩色图像,他们得以第一次真正了解人脑1000亿个细胞的神经通路及大脑如何运转。所以,上述大脑成像技术所遇到的关键问题是:所成像的对象是什么?是大脑本身还是大脑表面的影子?
另外,苏佩斯实验成立的哲学基础是图像相似性。图像相似性如何理解?是否是事物与图像对象之间的相似性?如在上述实验3中,实验者看到蓝色物体和听到“蓝色”的名称、看到三角形和听到“三角形”这个例子中,出现了两份相似的认知图像。如何理解这样的相似性?首先,苏佩斯实验中的图像相似性是统计学意义上相似,而不是直观相似。这一点在他的实验说明中非常明显,这一图像就是统计学的结果。所以科学意义上的相似性取代了直观的相似性。其次,这种相似性是经验主义的相似性的表现。这种相似性是从不同图像的吻合角度看,视觉图像产生的脑图像与听觉形成的脑图像之间近似吻合。但是很明显,这里存在着一个循环论证。不同图像的吻合本身就基于相似性,如果两个图像之间缺乏相似性那么它是无法近似吻合。这种依赖相似性循环论证是苏佩斯实验中问题所在。最后,从本质上看,苏佩斯所提出的图像相似性的问题更多是依赖于图像形状。如果说现象学为我们揭示了“每一个相同性都与一个种类有关,被比较之物隶属于这个种类。……如果两个事物在形式方面是相同的,那么这个有关的形式种类便是同一之物;如果他们在颜色方面是相同的,那么这个有关颜色种类便是同一之物。……相同性是隶属于同一个种类的诸对象的关系”[4]117,那么,“图像形状是同一之物”就成为苏佩斯实验中的现象学设定。缺乏这一设定,他的所有比较的结论都会失去根据。
此外,苏佩斯实验之所以成立的伦理基础也需要给予说明,这恰恰是他本人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安全问题、成像的精确性问题、隐私问题,以及非医学目的应用等是脑成像技术面临的几个重要的认识论问题及伦理问题。当然,在苏佩斯实验中,除了上述伦理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实验之所以可能还有受试者的自愿,这是该实验得以进行的基础,在这一实验过程中会产生很强烈的幽闭恐惧、心理压力和担心,这些心理活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实验的结果并不清楚。伦理基础并不能否定这一实验的结论所产生的影响。此外,要分析这些影响是否有效最好是集中在其内在的逻辑基础上,比如这一实验所依赖的经验主义基础上的图像相似性,而这恰恰是苏佩斯实验的软肋。
最后,苏佩斯实验得到了认知科学上的支持。从认知科学角度看,听与看是两种不同的知觉世界的方式。听觉是“信号在毛细胞和耳蜗的基底膜得到加工,然后耳蜗将这些信息以神经信号的形式输送到下丘和耳蜗核。信息随后被传送到丘脑的内侧膝状体,并达到初级听皮质”[5]175。视觉是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把光线转化为神经信号传送到视皮质。所以这意味着对两种认知方式的比较研究在科学上是站得住脚的,因为只有针对两个不同的对象比较研究才是有意义的。苏佩斯实验恰恰是这样的,它将听觉对象看做是听觉行为的结果,将视觉对象看做是视觉行为的结果,这二者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然而,这也正是他的问题所在,认知科学中的“联觉”(synesthesia)现象给予他极大的挑战。所谓联觉是指可以多种方式体验到一个对象。比如尝到单词。“J.W.和大多数人体验到的世界不一样。他可以尝到词语。例如,单词‘精确地’尝起来就像鸡蛋。……只要一个名叫Derek的常客出现,他就会感到寒毛直竖。因为对J.W.来说,单词Derek是耳垢的味道。”[5]171对于苏佩斯来说,看到三角形与听到“三角形”的观念行为的脑电图图像是相似的;但是,如何比较看到一个三角形与听到一个三角形本身而不是“三角形”观念,这二者是否相似,这显然超出了苏佩斯实验的范围,而成为一个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三、 物与物之观念区分的变迁
柏拉图比较早地确立了“物与物之观念”、“物与物之图像”的区分。在《理想国》第三卷中他曾经对物、物的图像和物的理念之间的关系给予描述。“一种是自然的床,我认为我们大概得说它是神造的。……其次一种是木匠造的床,……再一种是画家画的床,……因此,画家、造床匠、神是这三者造这三种床。”[6]“模仿”成为他描述这三类存在物之间关系的一个概念。我们暂时撇开他的答案,而是从他所提出来的问题入手。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物、物的图像和物的理念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关系问题主要是存在对象意义上的关系,但是上述区分关系在随后的历史过程中并没有被关注到。由于哲学史内在地对观念优先性地强调使得“物与物之观念”之间的区分问题被凸显,而“物与物之图像”的区分则被忽略。中世纪学者关注事物及其观念的关系从而形成了哲学中个性与共性、个别与一般的关系问题,即认识论传统。上述传统中物自身、物之观念都获得了根本的合法性地位。其中海德格尔为我们清楚地揭示了物的合法性问题,如其著作《物是什么》(1937)和《物》(1951);观念的合法性更是如此。整个哲学史就在探讨观念,真理也只是和观念联系在一起。图像却因为柏拉图的“图像是对影像而不是真实的事物的模仿”而滑落出哲学关注的范围。
在具体的解决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方式。如面对事物与观念的关系问题,存在的争议是:事物与观念是否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古代及现代哲学家认为一般真理都是观念,而与事物无关,但是贝克莱在《视觉新论》中批判了这一观点。他指出:“所有的一般真理都是关于普遍的抽象理念的,这确实是现代哲学家和古代哲学家的一个信条;……我在经历了考虑理解三角形的一般理念的反复努力与阵痛之后,我发现,这种一般理念是完全不可理解的。”[1]696休谟接受了这种批判。
现象学诞生以前,物与物之观念的区分都是从本体论意义上作出的,现象学出现以后,改变了这种方向,开始从意向行为本身来区分二者。对象本身与“看”这一知觉活动相关,比如我看到一棵树、看到一个三角形形状;而观念与“听”这一知觉活动相关,如我听到“树”“tree”的不同发音。这就是看到一个对象(物)之意向性与听到一个对象之观念意向的区分。
我们知道,现象学长于区分,尤其是对不同的意识行为直接作出区分。“比较性的考察告诉我们,我们意指种类之物的行为与我们意指个体之物的行为是根本不同的;无论我们在后一种情况中所意指的是整个具体之物,还是意指一个在这个具体之物上的个体部分或个体特征。”[4]113胡塞尔是从直观角度、意向行为等角度对二者的区分给予了论述,从而有效地将存在问题转化为意向分析问题。借助直观类别,他确立了对事物的直观与对事物之理念的直观是不同的直观形式。对事物的直观是感性直观,而对理念的直观是范畴直观。感性直观的特征是简捷,简捷感知的特性在于“它以亲身具体的方式给出它的对象。在这样的一种亲身具体的给出中,对象本身保持自身为同一个对象。在各种不同的明暗层次(这些明暗层次是在各种感知系列里显示出来的)的相互转换中,我看到的是作为‘同一个自身’的对象。”范畴直观则是完全不同的,它经历了从事实到本质的过程。“观念直观构成一种新的对象属性:一般属性。……在感性之物的领域里,观念直观产生出了像颜色一般、房屋一般的这样的对象;在内感官领域则产生了判断一般、希望一般等等这类对象。”[7]92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奠基关系。“范畴化行为是被奠基的行为,就是说所有的范畴之物最终都是以感性直观为基础的。……所有范畴之物最终都是以感性直观为基础的,每一对象化的解析都不是漂浮无根的,而是对已然既与之物的一种解析。”[7]91
但是,现象学对“事物与观念”之间的区分难以理解和把握。相比之下,符号学更加简洁地解决了“事物与观念”之间的区分,索绪尔用符号的所指与能指的问题取代了事物与观念的关系问题。根据符号学理论,符号包括能指和所指两方面,其中能指意味着符号的声音形象,代替传统中的观念;所指意味着符号的概念意义,代替传统中的事物。所以,在符号学语境中,事物与观念之间的区别就变成了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区别。具体到苏佩斯实验中,当我们看到“蓝色”时形成的脑电波图形主要是指作为颜色显现的事物,而非概念意义的显现;当听到“蓝色”的表述,不论这个声音是由电脑发出还是某个人念出,这是与符号能指对应的。这里的表述所存在的问题是无法确认某一行为是否与符号的所指相联系。因为“看”的是符号形象的刺激,而“听”的是符号的能指方面。所以,这里的相似性并没有描述符号(包括概念和声音形象)之间的认知过程,而是集中在声音形象(呈现给听觉)、事物(呈现给视觉)上。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使用“红”的例子来分析一下:现象学家是如何阐述红色的东西、“红”(红色之观念)和红色东西的图像之间的区分呢?在胡塞尔看来,我们可以从红色东西的直观(感性直观)过渡到“红”之范畴(范畴直观)。具体过程是看到一块红布、一条红丝带、一朵红花等等,从这些与红色有关的事物之中,我们完成了从被给予的红色过渡到一系列别的红颜色上,此外我们可以想象红色的丝带、红色的花朵,可以回忆我们刚刚看到的红色的花朵,等等。我们所获得的是随意的变项,更获得了本质的红。此处,从直观过程来看,就是完成了从对感性红之物的直观到本质红的直观,从而所获得的就是本质红。在本质获得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同行为:想象行为、回忆行为。
四、 苏佩斯实验对现象学的冲击
上述描述给我们展示了物与观念之间的区分的简单历程。这一区分经历了从存在对象、意向行为到语言符号等角度进行区分的不同阶段。尤其是在现象学处,它所给予是在我看到“红”色丝带与我听到“红”的词、我想象“红色”之间是差异的关系。这一区分为很多现象学家接受,但是,苏佩斯实验至少从两个方面对现象学提出了挑战:
一是对物与物之观念区分传统提出了挑战。这一实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现象学上的被认可的物之意向与物之观念的意向之间的区分并不是完全有效的。正如上述实验所显示的:我听到“三角形”的观念与我看到“三角形”对象的脑电图图像是相似的,这说明了两种行为的相似性。如何解释这种相似?它是否真的指向了哲学上的物与观念之间的区分?这恰恰是哲学自身需要思考的地方。
二是从图像角度提出了一种利用自然科学方法解决哲学问题的思路*利用自然科学方法解决哲学问题在哲学中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传统。通常表现为借助数学的形式来阐述或分析哲学问题,这一做法在近代哲学就有所体现,如笛卡儿、斯宾诺莎等人就用数学的形式构建其哲学体系;当前,有数学家利用数学方法来验证某些哲学命题,如质量互变规律。随着图像技术的成熟,科学家开始利用大脑成像技术来研究某些哲学问题,如自由意志、伦理选择等。苏佩斯的实验也是这一传统的一种表现。。事实上,苏佩斯并非是孤独地做这件事情。在他之前,自然科学家已经开始利用成像技术来解决哲学问题,如在20世纪90年代左右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杰尔拉德·M.埃德尔曼(Gerald M.Edelman)已经注意到脑电图(EEG)和脑磁图(MEG)等成像技术能够在解释意识起源上提供帮助。同时期,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心理系教授本杰明·李贝特(Benjamin Libet)利用EEG图像验证了“自由意志”,这一实验的结果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实验结果表明,大脑是在个体报告发出动作意向之前几百毫秒就已经产生了相应动作的脑活动,也就是说动作产生的直接原因并不是个体意识当中的意向,而是意识之外的其他脑活动[8]。这些实验的共同之处主要是利用脑图像来验证哲学问题。当然,这三类实验的性质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一种是将某些心理活动(意识的产生)直观化、可视化,如埃德尔曼的实验;另外一种是利用图像来证明某一活动(如自由意志)的有效性,如李贝特的实验。苏佩斯的实验可以归属于第二类,独特之处就在于他比较了两类行为——看某一个对象和听到某一个对象之观念——的脑图像,并且得出了两类行为的相似性。
针对上述实验,我们如何回应?100多年前,胡塞尔批判了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心理主义的倾向。他的批判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他彻底地批判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哲学界所存在的将哲学问题理解为心理活动的趋势。那么,苏佩斯实验是否意味着自然主义-心理主义在100年后的复苏?如果是这样,需要现象学家真正面对这一问题,在胡塞尔批判基础上看清这种复苏背后的本质。所以,这样看来,我们仅仅停留在100多年前胡塞尔的批判是不合适的。我们需要正视自然科学领域所出现的这种做法,或许这背后所隐含的问题实质是:对研究方法的反思。所以,如果不拘泥于苏佩斯实验的结果,至少他的方法是值得关注的:这就是随着认知科学哲学的发展,通过结合大脑成像技术来研究古老的哲学问题。如果这一方法可行,那么现象学的研究甚至整个哲学问题的研究就会出现一种转向:20世纪初哲学问题被看做是语言问题;而当下,哲学问题被转化为技术问题,尤其是借助成像技术来加以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苏佩斯. 科学结构的表征与不变性[M]. 成素梅,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2] 杰拉尔德·埃德尔曼,朱利欧·拓诺尼. 意识的宇宙——物质如何转变为精神[M]. 顾凡及,译.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60.
[3] 新型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绘制惊人大脑图像[EB/OL]. (2012-06-07)[2014-08-30]. http:∥tech.sina.com.cn/d/2012-06-07/07357233783.shtml.
[4] 胡塞尔. 逻辑研究:第2卷[M]. 倪梁康,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
[5] 迈克尔·S.伽兹尼扎. 认知神经科学[M]. 周晓林,译.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1.
[6] 柏拉图. 理想国[M]. 郭斌和,张竹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390.
[7] 海德格尔. 时间概念史导论[M]. 欧东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8] 有一种错觉叫自由意志[EB/OL]. [2014-11-19].http:∥www.guokr.com/article/50325/.
(责任编辑:李新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