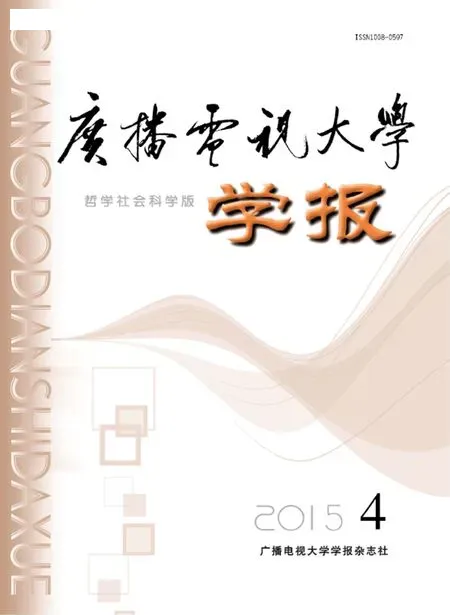走近艺术:在审美实践中追求生命空间的扩展
2015-03-21CometotheArtIntheAestheticPracticeofExpandingSpaceofthePursuitofLife
Come to the Art: In the Aesthetic Practice of Expanding Space of the Pursuit of Life
宋生贵
SONG Sheng-gui
(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Art College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Huhhot Inner Mongolia China 010010)
走近艺术:在审美实践中追求生命空间的扩展
Come to the Art: In the Aesthetic Practice of Expanding Space of the Pursuit of Life
宋生贵
SONG Sheng-gui
(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ArtCollegeofInnerMongoliaUniversity,HuhhotInnerMongoliaChina010010)
[摘要]艺术活动及其审美实践,是人类走向理想的生活与生命形式的重要方式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扩展人的生命空间的意义上来探讨走进艺术世界、开展自觉审美实践活动与实现生活艺术化的关系。这里所讲的人类在艺术审美实践活动中追求生命空间的扩展,包括人以自己具有无限灵性和可逆性的特有机能,寻求与更为广阔而久远的世界对话;从人类为寻求身心的更大自由,为获得生命空间的更加扩展的意义上,探讨人类活动的生成、发展,乃至认识其内在机缘与命意。
[关键词]艺术;审美实践;生活艺术化;生命空间
Abstract:Art activities and aesthetic practice is the ideal of humanity to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of life and forms of lif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xtend the life of people from the space sense to explore into the art world, to carry out the self-conscious aesthetic practical activity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artistic life. Here, the human in the aesthetic practice of expanding space of the pursuit of life, including a person with a unique function of unlimited spiritual and reversibility, From human beings to seek the greater freedom of body and mind, in order to obtain the space more extended sense of life, discusses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activities, and even recognize its internal chance and meaning.
Key words:Art; Aesthetic practice; Living art; Life space
如果我们把关于生活艺术化及相关审美问题的讨论置放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大视野来看,其聚焦点可能落到哪里呢?估计仁者见仁,志者见志。笔者的答案是,视点最终会落到关于人的理想的生命形式上,落到人类发展的大目标上。其中包括人以自己具有无限灵性和可逆性的特有机能,寻求与更为广阔而久远的世界对话;从人类为寻求身心的更大自由,为获得生命空间的更加扩展的意义上,探讨人类活动的生成、发展,乃至认识其内在机缘与命意。
艺术及审美活动是人类走向理想的生活与生命形式的重要方式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扩展人的生命空间的意义上来探讨走进艺术世界与实现生活艺术化的关系。这里所讲的“艺术世界”主要是指传统意义上的民间艺术与艺术家的创作。
一、生命空间:在有限与无限之间
从形而上的最根本的意义上看,追求生命空间的扩展,是人类从事艺术活动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永恒性的心理依据;是人类生命情调中的一个绿色命题。神话故事是人类的第一个智慧之果,其中即表达了先民们为获得心灵自由并扩展生命空间的信息,如中国的神话故事《后羿射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等。《山海经·海外北经》中讲:“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夸父虽然渴死途中,未能实现追逐到太阳的目的,但他死时而留下的那根拐杖化作了大片林木,可以绿阴蔽日。在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过度膨胀时,有人往往把这类故事与所谓的“人定胜天”联系在一起,以突出它的现实鼓舞性;而事实上无论人有什么样的豪情壮志,发表了什么样的豪言壮语,最终“人”还是人,“天”还是天,人通过努力而可以对天有更多的了解,并自觉地研究科学而合规律的应对之策,至于“定胜”与否,如何判定呢?或许这原本就是个伪命题。所以,我们宁肯相信《夸父逐日》等神话故事传递出的是一种关乎精神超越的信息,即,在特定情境中,现实生活尚不能到达目标,可以通过展开精神双翼的奋飞而到达。亚里士多德说:“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因此,神话所编录的全是怪异,凡爱好神话的人也是爱好智慧的人。”[1]神话以其蕴含的哲理、激情、美感成就了人类的梦幻,也催生出丰富灿烂的艺术成果。上古时代是这样,进入21世纪的今天依然是这样,而且可以断定,未来也会是这样,因为无论任何时候,作为独立生命体的人,其所拥有的时空及内涵总是有限的。恩斯特·卡西尔即认为:“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假如必须经历所有那些我们在观看索福克勒斯或莎士比亚的悲剧时所体验到的情感,那么,他不仅会被这些情感的力量压得透不过气来,而且会被这些力量粉碎和消灭。然而在艺术中我们就不会面临这样的危险。我们在艺术中感受的东西即是那种没有物质性内涵的完满的情感生活。我们已从肩上卸下了激情的重负;剩下来的只是我们的激情在摆脫了它们的重力、压强、引力后,那种微微颤动的内在情感。”[2]在艺术活动中,人可以在虚拟世界中所获得某种情感体验,因此会更加自由,并可以到达超越其现存状态的境界。
二、特定情境,找到“上帝”的感觉
人类生命空间的扩展与生命存在形式的完善,首先在于人的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感性世界的扩展与完善。艺术活动的突出特点则是可以使人的生命,尤其是感性世界得以激发与调节。哲学家怀特海曾经说过:“艺术作品是自然的一个碎片,它身上带有一种有限的创造性努力的痕,所以它是独立的,是一件个体事物,它的模糊而无限的背景可以对它进行详尽描述。因此,艺术提高人类的感觉。它使人有一种超自然的兴奋感觉。夕阳是壮丽的,但它无助于人类的发展,因而只属自然的一种流动。上百万次的夕阳不会将人类推向文明。将那些等待人类去获取的完善激发起来,使之进入意识,这一任务须由艺术来完成。”[3]
“艺术提高人类的感觉”,而且是“一种超自然”的“感觉”,可谓一语中的,说到了关键点上。所谓超自然的“感觉”,就是超越外在的生理层面上的感觉,而达到精神境界的感应与交流,特别是可以从中获得精神上的自由与力量。
当我们因焦虑与恐惧所环绕而局促不安、心神不宁,极端痛苦时,莫扎特的《安魂曲》会给我们焦灼而痛苦的灵魂以安顿;当慨叹人生的坎坷、命运的残酷而对人生丧失信念与理想时,我们会从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中重新燃起生命的希望之火;当我们颓废消沉时,传达着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的民歌顷刻间就能让我们充满活泼的生命能量。我坚持认为这是一个永恒规律!如山西民歌中的几段歌词:
想亲亲想得我手腕腕软,
拿起个筷子我端不起个碗。
想亲亲想得我心花花乱,
煮饺子下了一锅山药蛋。
头一回眊妹妹你不在,
你妈妈打了我两锅盖。
二一回眊妹妹你还不在,
你大大劈头打了我两烟袋。
想你想你实在想你,
三天我没吃下一颗米。
茴子白卷心心十八层,
哥哥(妹妹)你爱不爱受苦人。
烟锅锅点灯半炕炕明,
烧酒盅盅挖米不嫌哥哥你穷。
茅庵庵房房土哟炕炕,
烂大了个皮袄伙伙盖上。
雪花花落地化成了水,
至死了也把哥哥你随。
咱二人相好一呀一对对,
切草刀铡头不呀不后悔。
毫不夸大地说,这真是爱的绝唱,因为是用生命在爱,用生命在唱,唱出了爱的生命。这歌是朴素的,但却已经自自然然、大大方方地达到了脱俗的美境!我这里顺便表明一个艺术理论观点,即,我不同意笼而统之地以“俗”来评价民间艺术,因为真正有生命力的民间艺术在精神取向上是很有超越性与穿透力的。
走进并用心体会那些形式朴实无华的民歌,可以发现,由于自然的、社会的,以及其他种种生存条件的原因,生活其中的人们的某些生存愿望、生命意志等受到限制或压抑,于是借助民歌而得以表达。这种表达与交流,除了抒发胸臆之外,也为自己找到了精神寄托,生活因此而丰富。这是处于特定地域的民众营造精神生活的积极方式,无论生存环境有多么恶劣,生活条件有多么艰苦,只要进入表达心声的民歌之中,自己就成了可以挺直腰杆的主人,向上苍祈望,与厚土对话,同心爱的人倾诉衷肠。另外,许多民间艺术活动还表明,人们在特定的情境中走进艺术,还可以从中焕发激情和增强自信。如,画家苗再新创作的两幅中国画《生命的律动》《老腔》,便很生动地表现出了这一点。
举凡艺术创作,都求造出一个独特的境界。这境界,往往是现实生活中所不全有,不可照录而来的。就比如那个“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的《红楼》“大观园”,便只能说在世间的有无之中——既不能说其全有,也不能说其全无,因为那是作家心灵世界对外部世界感应后的升华和重构。艺术家进入他特有的创作情境,“行神如空,行气如虹”,什么设境造屋,人生离合,统统都在他的调度之中。唐代堪称诗画双绝的大艺术家王维(苏东坡说:“品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曾隐居于辋川别业,与山水为邻,过着于自然间优游安适的生活。在这里他可以自由想象,并借助笔墨而创造自己心中所想的意境。假如他想到:最好有重叠的山,并在山的白云深处结一个庐,庐后有松柏参天,庐前面临着深渊,左面挂有瀑布,右面耸着怪石,无路可通;而他自己就坐在这庐中,啸傲或弹琴,与人世永远隔绝。于是,他就展纸研墨,即兴而作,顷刻之间在纸上实现了这个境界,并使自己神游其间。此一时,他就是“上帝”!
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莫言也说过,文学创作让他“饱尝大权在握的幸福”。他说:“我仰面朝天躺在草地上,看着天上的白云缓慢地移动,好像它们是一些懒洋洋的大汉。我想跟白云说话,白云也不理我。天上有许多鸟儿,有云雀,有百灵,还有一些我认识它们但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它们叫得实在是太动人了。我经常被鸟儿的叫声感动得热泪盈眶。”“在这样的环境里,我首先学会了想入非非。这是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许多美妙的念头纷至沓来。我躺在草地上理解了什么叫爱情,也理解什么叫善良。然后我学会了自言自语。那时候我真是才华横溢,出口成章,滔滔不绝,而且合辙押韵。”[4]他又在《福克纳大叔,你好吗?》的讲演中说:“我的高密东北乡是我开创的一个文学的王国,我就是这个王国的国王。每当我拿起笔,写我的高密东北乡故事时,就饱尝到了大权在握的幸福。在这片国土上,我可以移山填海,呼风唤雨,我让谁死谁就死,让谁活谁就活。”[5]当然,这并不是艺术家要在艺术创作中不顾一切地颐指气使,为所欲为,而是可以不受任何既有境遇与生存条件所限,不为任何功利俗念所困,以足够的自信与执着的追求去开创属于自己独有的境界。
无论是艺术家还是欣赏者,通过艺术活动而达到超越现实的某种境界,正是人的想象力的展示与锻炼。正如有美学家所说:“就人类的自我发展而言,人们从事艺术欣赏和创造的过程,也是锻炼和提高自身想象能力的过程。就像儿童的游戏是为了成年后的生产和生活做准备一样,艺术中毫无功利目的的欣赏也为现实中的功利实践做准备。反之,就像先有嫦娥奔月的神话后有阿波罗飞船一样,艺术的想象总是走在生活的前面。因而,艺术不仅是生活的总结,而且是生活的先导。”[6]
三、艺术情思,使不可能与可能融通而化成
做梦是人人都有的经历与经验,有些现实世界中所做不到的事,见不到的境地,在梦中得以实现。例如庄子梦化为蝴蝶:“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无论是庄周化为蝴蝶,还是蝴蝶化为庄周,都是人所空想而求之不得的事,在梦中可以实现。从理想表达的意义上讲,许多艺术即可谓是“梦境”的写真。宋代人苏东坡格外赏识文与可画竹的情境,他以诗赞曰:“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得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疑神。”文与可的墨竹画是宋代文人画中的上品,而使苏氏激赏的正是其“其身与竹化”的神情佳境。清代画家邹一桂曾经记载过宋代画家曾无疑画草虫的体会,文中讲:“宋曾云巢无疑工画草虫,年愈迈愈业,或问其何传,无疑笑曰:此岂有法可传哉!某自少时,取草虫笼而观之,穷昼夜不厌,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复就草间观之,于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笔之时,不知我之为草虫耶?草虫之为我耶?此与造化生物之机缄,盖无以异,岂有可传之法哉!”[7]我们知道,艺术的境界从来就不是现实状况的照搬或实录——包括那些称之为突出“现实性”的作品;因为只要是创作,就必然要表达创作者的精神追求,必然要凭借作品传递其某种理想寄寓的信息。所以,若置放于艺术与人类文明的关系的大视野来看,则可以肯定地说,没有精神指向与理想色彩的艺术,是没有生命力的。
在特定情境中,现实的不可能与理想中的可能,因艺术情思而化成,这是艺术的特殊魅力,也是人类关注并怀着形而上的冲动投身艺术活动的重要原因。中国现代美学家宗白华曾经这样记述他进行艺术创作的动因:“在都市的危楼上俯眺风驰电掣的匆忙的人群,通力合作地推动人类的前进;生命的悲壮令人惊心动魄,渺渺的微躯只是洪涛的一沤,然而内心的孤迥,也希望能烛照未来的微茫,听到永恒的深秘节奏,静寂的神明体会宇宙静寂的和声。一九二一年的冬天,在一位景慕东方文明的教授家里,过了一个罗曼蒂克的夜晚;舞阑人散,踏着雪里的蓝光走回的时候,因着某一种柔情的萦绕,我开始了写诗的冲动,从那时以后,横亘约摸一年的时光,我常常被一种创造的情调占有着。黄昏的散步,星夜的默坐,大庭广众中的孤寂,时常仿佛听见耳边有一些无名的音调,把捉不住而呼之欲出。往往是夜里躺在床上熄了灯,大都会千万人声归于休息的时候,一颗战栗不寐的心兴奋着,静寂中感觉到窗外横躺着的大城在喘息,在一种停匀的节奏中喘息,仿佛一座平波微动的大海,一轮冷月俯临这动极而静的世界,不禁有许多遥远的思想来袭我的心,似惆怅,又似喜悦,似觉悟,又似恍惚。无限凄凉之感里,夹着无限热爱之感。似乎这微渺的心和那遥远的自然,和那茫茫的广大的人类,打通了一道地下的深沉的神秘的暗道,在绝对的静寂里获得自然人生最亲密的接触。我的《流云小诗》,多半是在这样的心情中写出的。”[8]他的《小诗》这样写:
“生命的树上 / 凋了一枝花 / 谢落在我的怀里,/ 我轻轻的压在心上。/她接触了我心中的音乐 / 化成小诗一朵。”
对于艺术家来说,通过艺术表达而使“不可能”与“可能”在艺术情境中化成,而其他人,只要是敏于感受、善于体验、长于想象与联想者,也是极容易使自己与艺术情境相联系,进入自由无碍的精神空间。譬如,一首《春江花月夜》,多少年来不知摇动了多少人的情怀,照彻了多少人的心境,穿越时空,况味无穷。这除去其形式的优美独绝之外,更主要的即是因为在其抒情化的字里行间,艺术地向世人揭示和袒露了诗人于自然人生中所理解到的生命的本原和人生的极致:“……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走进这令人一咏三叹的诗境,那时间在空间中不断延伸的流动意象,可以激活人生形而下的体验,或形而上的冲动,超越现实环境和生命个体的局限,在追寻人类终极命意的高度上,实现人生信念的升值。这也便应了维柯的话:“人们按本性就是些崇高的诗人”。
我们知道,就人的现实存在而言,恰是由一个个悖论或矛盾而构成的,如,物质生命的有限和精神上的无限可能性,个体情性独立与群体意志求同,以及人性与动物性的互逆,等等,都注定了人在许多情况下可能成为尴尬的二元存在的矛盾体。冲突、矛盾,以及实现愿望的现实障碍,既造成人的紧张压抑与心理上的失衡,但也往往又为人提供了生命活力和心理能量。冲突的痛苦,必换来大的生命场和精神场。作为艺术家而言,经历并切身体验冲突与平衡,压抑与反抗,痛苦与欢乐,沉沦与升华等生命存在的洗礼,可以使其领悟到人生的真谛,创作出独有的艺术世界。
美学家桑塔耶纳认为,面对灾难或不幸之时,精神抖擞的人就有一种崇高的意境。他说:“因为我们能够解脱掉偶然穿上的尘世衣物愈多,历万劫而长存的精神就愈袒露而纯朴;它的优越性和统一性就愈臻于美满,从而他的快乐就愈无可限量。”[9]世间无论多么可怕的境遇,都没有不能暂时放开怀抱在艺术情思的融化中求得慰藉的。
是的,如同有一种无言的使命,无论多么可怕的境遇,多么不幸的人生,在那些有责任感的艺术家的创作情思和所缔构的艺术世界中,却绝无沉沦,也绝无退缩和屈从,而有的是殚心竭虑的追寻和创造;同样,无论有多么美好的境遇,多么幸运的人生,在有个性、有追求的艺术家的创作实践中,也绝不会有那种志满意得、左右逢源、八面风光的陶醉,不随声附和,而依然要向着更深远的意义去追寻和创造。这也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心灵所真正追求和崇尚的东西,是自己所创造的东西。只有创造出来的东西,才能给人们带来更大的更经久的乐趣。艺术家之所以以艺术为无上乐事,恰是其精神世界和人生追求的需要,因为他们在自己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中可以实现与理想拥抱。对于艺术欣赏者来说,他们在具有丰富审美意蕴的艺术境界中玩索无穷,个体情趣受到激活,进而去自由选择,自由延伸,同样获得超越现实的自由感。
四、走近艺术,为“生命的化妆”而添韵
“生命的化妆”这个说法,是我从台湾作家林清玄先生的一篇散文中借用而来的。这篇散文的题目就是《生命的化妆》,现将此文抄录如下:
我认识一位化妆师。她是真正懂得化妆,而又以化妆闻名的。
对于这生活在与我完全不同领域的人,使我增添了几分好奇,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化妆再有学问,也只是在皮相上用功,实在不是有智慧的人所应追求的。
因此,我实在忍不住问她:“你研究化妆这么多年,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算会化妆?化妆的最高境界到底是什么?”
对于这样的问题,这位年华已逐渐老去的化妆师露出一个深深的微笑。她说:“化妆的最高境界可以用两个字形容,就是‘自然’,最高明的化妆术,是经过非常考究的化妆,让人家看起来好像没有化过妆一样,并且这化出来的妆与主人的身份匹配,能自然表现那个人的个性与气质。次级的化妆是把人突显出来,让她醒目,引起众人的注意。拙劣的化妆是一站出来别人就发现她化了很浓的妆,而这层妆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缺点或年龄的。最坏的一种化妆,是化过妆以后扭曲了自己的个性,又失去了五官的协调,例如小眼睛的人竟化了浓眉,大脸蛋的人竟化了白脸,阔嘴的人竟化了红唇……”没有想到,化妆的最高境界竟是无妆,竟是自然,这可使我刮目相看了。
化妆师看我听得出神,继续说:“这不就像你们写文章一样?拙劣的文章常常是词句的堆砌,扭曲了作者的个性。好一点的文章是光芒四射,吸引了人的视线,但别人知道你是在写文章。最好的文章,是作家自然的流露,他不堆砌,读的时候不觉得是在读文章,而是在读一个生命。”
多么有智慧的人呀!可是,“到底做化妆的人只是在表皮上做功夫!”
我感叹地说。
“不对的,”化妆师说:“化妆只是最末的一个枝节,它能改变的事实很少。深一层的化妆是改变体质,让一个人改变生活方式、睡眠充足、注意运动与营养,这样她的皮肤改善、精神充足,比化妆有效得多。再深一层的化妆是改变气质,多读书、多欣赏艺术、多思考、对生活乐观、对生命有信心、心地善良、关怀别人、自爱而有尊严,这样的人就是不化妆也丑不到哪里去,脸上的化妆只是化妆最后的一件小事。我用三句简单的话来说明,三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妆,二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化妆是生命的化妆。”
化妆师接着做了这样的结论:“你们写文章的人不也是化妆师吗?
三流的文章是文字的化妆,二流的文章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文章是生命的化妆。这样,你懂化妆了吗?”
我为了这位女性化妆师的智慧而起立向她致敬,深为我最初对化妆师的观点感到惭愧。
告别了化妆师,回家的路上我走在夜黑的地表,有了这样的深刻体悟:这个世界一切的表相都不是独立自存的,一定有它深刻的内在意义,那么,改变表相最好的方法,不是在表相下功夫,一定要从内在里改革。
可惜,在表相上用功的人往往不明白这个道理。
笔者不吝惜篇幅而全篇照录,除了想把这篇美文推荐给更多的读者之外,还认为该文所讲到的事例可以启发我们从一个浅显的层面进入现在所要讨论的问题。
我们强调了“生命空间”的内涵包括生理的与精神的两个层面,无论是由有限而到无限的超越,还是实现“不可能”与“可能”的化成,主要是精神层面上的扩展与延伸。其中,一个人的生命光彩的闪现,同样也是来自于精神世界。因此,对作为生命个体的人而言,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提升自己的精神品格,无疑应该是永远的人生必修课。用林清玄先生文中的话讲,就是“一定要从内在里改革”,才会使一个生命整体有光彩。
那么,一个人怎样才能切实而有效地将自己的精神境界营造得充实而富有光彩呢?令林清玄先生“起立向她致敬”的化妆师认为:“再深一层的化妆是改变气质,多读书、多欣赏艺术、多思考、对生活乐观、对生命有信心、心地善良、关怀别人、自爱而有尊严,这样的人就是不化妆也丑不到哪里去,脸上的化妆只是化妆最后的一件小事。”读到此,我也同样对这位化妆师心生敬意!我除了感慨她的见识不俗外,还认同她所指出的实现“再深一层的化妆”的方法与态度,即“多读书、多欣赏艺术、多思考、对生活乐观”等。其中,“走近艺术”恰是我们在本节中专门讲到的。
我们说“走近艺术,为生命的化妆而添韵”,是因为艺术最具有滋润与调节人的心灵的功效。如丰子恺先生所讲:“我们对着艺术品的时候,心中撤去传统习惯的拘束,而解严开放,自由自在,天真烂漫。这种经验积得多了,我们便会酌取这种心情蒲来对付人世之事,就是在可能的范围内把人世当作艺术品看。”“人生处世,功利原是不可不计较,太不计较是不能生存的。但一味计较功利,直到老死,人的生活实在太冷酷而无聊,人的生命实在太廉价而糟蹋了。所以在不妨害真实生活的范围内,能酌取艺术的非功利的心情来对付人世之事,可使人的生活温暖而丰富起来,人的生命高贵而光明起来。”[10]
不同的人对艺术的感觉是有差异的,有的人天赋中即对艺术很敏感,而有的人则敏感性差些;有的人对此类艺术敏感,而有的人则对彼类艺术敏感。这不是问题,只要注重培养即可,特别是对艺术趣味的培养。毫无疑问,培养艺术趣味的必要途径就是走近艺术。趣味很少有生来就广而博的,所以必须要培养与拓展,好比是开疆辟土,“要不厌弃荒原瘠壤,一分一寸地逐渐向外伸张。”“趣味是对于生命的澈悟和留恋,生命时时刻刻都在进展和创化,趣味也就要时时刻刻在进展和创化。水停蓄不流便腐化,趣味也是如此。”[11]艺术感知的趣味必须是有创造性,应该不断拓展,并能够达到新的境界。这表明,一方面艺术趣味的培养,通过走近艺术得以实现;另一方面,通过走进艺术,在不断丰富与提升艺术趣味的同时,便自然而然地丰富与提升了人的内在修养,亦即以无形之手对自己进行着从“精神的化妆”到“生命的化妆”,以使自己的人生更有韵致。如朱光潜先生所说:“每人所领略到的境界都是性格情趣和经验的返照,……欣赏一首诗便是再造一首诗。”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5.
[2]恩斯特·卡西尔.符号·神话·文化[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111.
[3]A·N·怀特海.观念的冒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89.
[4]莫言.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N].劳动报,2012-10-21.
[5]莫言.福克纳大叔,你好吗?——在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的演讲[J].小说界,2000(5).
[6]陈炎.艺术本质的动态分析[J].文艺理论研究,2013,(3).
[7]邹一桂.小山画谱[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462.
[8]宗白华.艺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192.
[9][美]乔治·桑塔耶纳.美感[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61.
[10]丰子恺.艺术的效果[A].丰子恺著,张卉编.人间情味[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2.
[11]朱光潜.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A].朱光潜.无言之美[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30.
[责任编辑:王雪炎]
DOI:10.16161/j.issn.1008-0597.2015.04.009
[中图分类号]B8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597(2015)04-0055-07
[作者简介]宋生贵,男,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收稿日期]2015-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