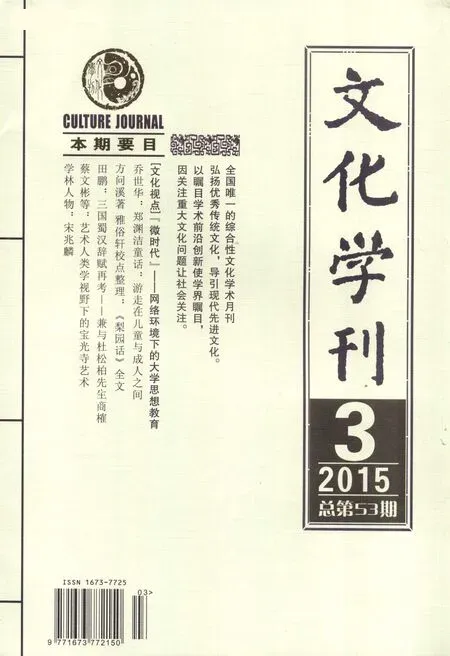系统探究 汪重考辨
——《宋实录研究》读后
2015-03-20张霞
张 霞
系统探究 汪重考辨
——《宋实录研究》读后
张 霞
陈寅恪为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作序时,曾言“中国史学莫胜于宋”[1],反映宋代史学之繁荣。作为宋代史料之渊薮——宋实录,系宋代官修史书的主要体现。宋代历经十八朝,除度宗后四朝没有修实录外,其余十四朝均修有实录,且《太祖实录》《神宗实录》《哲宗实录》经过多次修订,然而仅有《太宗实录》残卷二十卷(原书八十卷)传于世,但这并非说明有关宋实录的记载均已亡佚,而是散落在宋代及宋以后的众多史籍中。学界对宋实录的研究多是以单篇论文或在著述中宏观介绍为主,但是,201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武汉大学谢贵安先生近六十万字的《宋实录研究》,可谓第一部系统研究宋代实录相关问题的专著。
该书共分八章。第一章详考宋代十四朝实录的纂修情况,可谓史料翔实,论析清楚,能够真实再现宋代实录的撰述始末。第二章梳理宋代十四朝实录的写作班子,可谓有理有据。具体体现在通过大量的史料爬梳,缜密辨析,考辨每一部《实录》的修纂人员,且驳正一些记载之误与研究中的不确。尤其是对每一部实录的修纂人员,皆在考辨之后作一简表,使读者可以一目了然。第三章详述《实录》修成后的进呈仪式、参修《实录》者所获得的各种赏赐,以及《实录》的流传情况,读过该章可以了解《实录》修成后的相关事项。第四章论析与宋实录修撰的相关修史机构(崇文院、门下省编修院、秘书省等)、与实录修纂相关的史官制度(国史实录院、秘书省及其他各官)、宋实录修撰机构的相关管理制度(人事管理、修纂管理、后勤管理)以及宋代修纂机构所修其他史书。可谓详考宋代实录修纂机构的设置以及对史官的管理情况。第五章详析宋实录的撰写主题、编纂体例及其与《宋史》列传之间的关系。指出宋代实录的撰写主题是以表彰孝行、美君亲、励忠臣及劝风俗,其体裁是以编年附传的写法,并详考此种体制在纂述实践中的表现。考究“实录附传”与《宋史》人物传记之间的关系,通过众多比照可以看出《宋史》列传与实录之间的关系。第六章详述宋实录对于撰写国史、宋史、编年史、杂史之作用(是其主要的史源之一),从而分析宋实录在宋代史书撰写中的作用。从史源学的角度考察宋代国史、《宋史》、编年史、杂史对宋实录的利用,可谓论之有据,析之有理。第七章从改易之际皇帝实录修撰中之曲笔(史臣秉承帝王意志对实录进行篡改)、宋代党争中对宋实录内容的诬诋、史臣好恶对实录修撰的影响三个层面,分析帝王、执政大臣及史臣皆是有意作伪,引起宋实录记载的曲笔。另外,亦论述了宋实录修撰中无意之讹,即非主观愿望所致而出现的种种错误,诸如缺漏、采择之误、事实之讹及编辑之误等。该章可谓详细梳理宋实录修撰中出现各种错谬的原因及其表现。第八章从宋实录的史料价值、现实功用两个大的方面分析宋实录的价值、地位及其影响。其史料价值体现在实录精神、记事之可靠性、有助于考《宋史》、有助于对其他史籍进行订正、反映宋代之社会历史等方面。另外,从宋实录成为宋代现实政策和行政、朝廷人事任务、军事经济外交活动、文化教育建设的依据,以及对宋代学术研究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宋实录研究》不仅在内容上详细论述考辨了与宋代实录相关的诸多问题,而且在著述态度、著述特点及著述方法方面别具特色。
一、求是求真的著述态度
史学著述不仅是以史料为基础分析史学现象,归结史学规律,同时,在著述中也体现着著者的心态,尤其是对相关研究成果及自己研究内容的态度。
谢贵安先生在《宋实录研究》中,既尊重学界的研究成果,同时又驳正其不妥之处。对于《太宗实录》的修撰情况,谢贵安先生列举王德毅、燕永成两修说,尤其燕永成提出《太宗实录》有“别本”的说法。他经过严密辨证,指出两修说及“别本”之错误,认为《宋太宗实录》仅有一个版本,令人叹服[2]。在论述宋实录能补正方志记载缺漏时,不仅引用宋代周应合《景定建康志》的相关内容,还征引燕永成的论点予以佐证,且对燕氏观点予以很高的评价[3]。罗炳良认为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中《潘武惠公美传》《王中书全斌传》《张文定公齐贤传》在体例方面与其它传有异,因而推测此三传可能源自国史,且《王中书全斌传》有“天禧二年,录其孙永昌为三班奉职”的记载,而《太宗实录》成于天禧元年,不可能有“天禧二年”的记载。《宋实录研究》指出罗氏的观点值得重视,经过辨析,认为“出现天禧二年传主子孙的记载,则有可能是实录传至民间后,由好事者或其后人所加”,且持传统观点,指出这些传记应该视为宋实录的附传[4]。
对于相关研究内容,暂时未能形成定论的,没有勉强为说,均采取存疑的态度。有关《神宗实录》的六修过程,因“史鲜记载,究竟什么时候完成,诚难确定”[5]。秦观参与过《神宗实录》的“增损”,“但其角色究竟是修撰还是检讨,无从考证”[6]对于宋代翰林学士参修实录的具体人数,唐春生《翰林学士与宋实录之修撰》认为是80人[7]。谢先生认为自己“对翰林学士纂修实录的具体人数和情况,尚无更进一步的辨析,不能因为某人担任过实录院的官员,就断定他一定修纂过实录。对此问题,看来有进一步发掘史料和考证史实的必要”[8]。
二、系统完备的著述特点
《宋实录研究》在宏观方面详细完备的考述宋代实录修纂过程、参与修纂人员、修纂的善后流程、修史机构、实录的主题、体裁与体例、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实录中的曲笔与讹误及实录的价值、地位与影响等相关问题。通过对《宋实录研究》的研读,可以了解宋朝历代实录的修撰、传播情况及其对纂修其他史著的影响。
在微观方面,对宋代历代实录的相关问题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述、辨析。诸如对《宋实录》修纂人员的考究。“宋代共进行了26次修纂,纂成14朝实录,有据可考的修纂官员共达253人次”[9]。著者详考每一朝实录的编纂人员及其在编纂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且在考订每一朝实录修撰者之后,将修撰者制一简表,可一目了然地知晓该实录修撰人员的姓名、表字、籍贯、任职等情况。对于论述“宋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著者用史源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宋代实录的史料如何源自奏疏、档案、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及其他史料进行考证,并论析宋实录如何成为诸多国史、《宋史》、编年史以及杂史的史料源泉[10]。此点可谓在史料环节上详究宋实录的渊源及其传播。
三、精于考辨的著述方法
宋实录是宋代相关著述的史料源泉,从国史、《宋史》、杂史、笔记、文集等无不留下相关实录的记载,但这些记载比较分散,且有一定的差异,为更好地探究宋实录的本貌,谢先生对相关记载进行了详细考辨,可谓考证有据,辨析有理。
《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均载曾肇为初修《神宗实录》的检讨官,但《东都事略》及《江西通志》却载其为实录院修撰,经过辨析认为《东都事略》及《江西通志》所载为误[11]。据《宋史·理宗本纪三》及刘克庄《后村集》相关记载,论析刘克庄参修过《宁宗实录》[12],还详细考辨宋代史官制度中监修国史、修国史、同修国史、修撰、同修撰、检讨、直馆、编修、校勘、校正、编校、判馆事、点检文字、书库官、楷书等各个职位的权限与作用[13]。
通过比对《太宗实录》与《宋史》本纪部分内容,从中探究宋实录在体裁方面“编年附传”体之编年特点[14],并根据宋实录相关内容分析其“附传”的特点,进而通过对《二老堂杂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的分析,指出实录中“附传”体当时源自“《日历》附传”[15]。辨析《太宗实录》附传与《宋史》列传之间的关系,诸如后者对前者的因袭、两者之间的差异等,尤其细致分析同一重要人物《太宗实录》无附传而《宋史》有传的原因在于,“可能是《太宗实录》原有而后来散佚的”,也“可能是实录修纂时其人为罪臣而遭到排斥,而易代之后则无此忌讳,故为之立传的。”[16]详细考论宋代党争导致《神宗实录》《哲宗实录》的纂修与改修中的曲笔现象[17]。
另外,著者对实录体史学有系统的研究,在考论宋实录相关问题时,能够纵横捭阖,触及相关实录。论析宋实录的主题时,指出其与《唐实录》的差异[18]。在讨论宋代修纂实录时,认为倘若修纂人员提前离开史馆,朝廷在赏赐纂修者时,将不再予以赏赐,由此联系到与明代纂修实录进行赏赐的差异[19]论析实录焚草制度源于北宋,并指出此种制度对明实录的“蕉园焚草”制度有直接影响[20]。在探讨宋实录的流传时,认为与明代对实录的禁传相比,“宋代实录的阅读和传抄并无特别严格的限制措施”[21]。对于宰相监修国史,认为宋代和唐代一样仅属于业务监修,而明代则以勋戚武官担当,主要是政治把关[22]。论析宋代实录的史料储备及供应制度时,联系到明代修《武宗实录》的情况[23]。
总之,谢贵安先生以翔实的文献资料、严密的考证辨析、严谨的著述态度为学界呈上一部系统研究宋代实录之佳作。
[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3][4][5][6][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谢贵安.宋实录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7]唐春生.翰林学士与宋实录之修撰[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7,(2).
【责任编辑:王 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