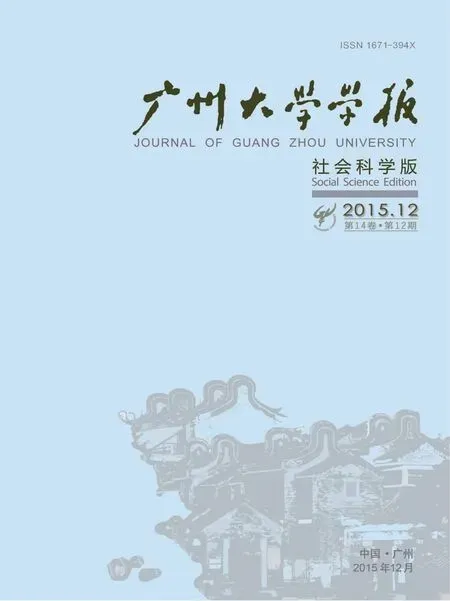语言乌托邦里的自然哲思——沈河生态诗歌论
2015-03-20龙其林钟丽美
龙其林,钟丽美
(1.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2.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200433)
一
沈河(1963—2008),原名赖仕嶂,当代实力派生态诗人,福建省作协会员,福建“三明诗群”成员。虽然沈河创作生态诗歌的时间并不长,却是生态诗坛上一位不可多得的富于灵性的诗人,他的诗歌语言凝练而意象传神,在看似平淡的表现中有着对于自然、生命、神性的细腻揭示。沈河在《人民文学》《诗刊》《星星》等刊物发表了大量诗歌作品,作品入选多种年选,曾荣获《人民文学》《诗刊》等多种诗歌奖项,著有散文诗集《走向你》和诗集《也是一种飞翔》《相遇》等。沈河早期的诗歌清新淡雅,后期诗歌创作则转向于自然生态,创作了以福建青印溪为主要表现内容的众多作品。他的诗歌清朗、单纯而富有生命气息,“与大自然浑然一体,将山作为他的骸骨、森林作为他的皮肤、青印溪作为他的血脉。因此,时而以他质朴的诗句呈现山的美、水的秀和森林的气息。时而也为其唱着哀歌,生命的哀歌。他深知质朴的语言最为精准,有显现的质地、明确的指向,最能直抵其事物特有的本质和精神内核。”[1]246-247
沈河以怜悯之心看待周围的一切事物,正是这种怜悯的视角给了沈河生态诗歌创作以恰当的定位。在沈河的笔下,青印溪就是他尊敬、虔诚和热爱的自然的象征。诗人2002年之后携家带口搬到了城郊居住,在青印溪的岸上安家,对于自然万物有了更为直接的观察和体验,因此他对于现实生态的状况有了清醒的认识。“我生活在闽中,到处是山,山中到处是树,树下是一条条清澈、闪亮的小溪流。对于很多人来说,所看到的只是嫩叶成簇和山花烂漫,对于里面的蠢蠢欲动不会过多地注意。正好我从事的是林业工作,由于职业习惯,不仅仅呆在山外眺望深山,还要深入进去,走上弯曲的山路,近距离靠近飞刀乱斧的声响和鸟兽被惊吓的啼鸣,见识了坡地上吞噬草木的山火,目睹绿色被翻开后漫起的尘土和裸露的石块。特别我把家安在青印溪岸边之后,体会就更深了,青印溪就像大地上的尺子,可以量测山中的微小变化,若浑浊,说明山上暴露了黄色的伤疤;若水少,说明山中的林木在减少;若鱼死,说明有人往河里倒入工业的毒液。”[1]223-224出于对人类毁坏自然生态的愧疚之情和对于自然界事物的怜悯,沈河在青印溪畔用灵动、细腻之笔书写了自己对于自然的疼惜之情,因此,他“写青印溪,写杉木头,写受伤的小鸟,在诗中倾注我的怜悯和关怀”[1]1。
在诗人的眼中,青印溪的生态胜境是那么细腻和值得呵护,不知名的小鸟似乎故意捣乱似地将脚踩进河面,让人不禁联想到它像大人的食指悄悄伸进孩子的腋窝这样一个惹人怜爱的画面。在沈河看来,青印溪的一切事物都是那么鲜嫩、淳朴,让人不忍打搅。于是在《微风扫过青印溪》一诗中,沈河写到了青印溪里的自然与生命,无论是从诗人的掌心跳到血管的小鱼儿,还是将小脚轻轻踩过河面的小鸟儿,在他的眼中都可爱得如同稚儿,浑身散发着盈盈笑语:
在岸边/我静下来,心中的名利/收敛了,不再吵吵闹闹/我在农人挑水前,轻轻把脚放入水中/鱼儿游来,从掌心跳到我的血管,逆流而上/此时,青印溪的私语/停在唇舌间,因为我在这里/以及伸进一只脚/一只不知名的小鸟是故意的/小脚轻轻地踩过河面/像大人的食指悄悄伸进孩子的腋窝/发出的笑像水花/我不仅看到笑,还听到青印溪的声音。[1]4
当诗人置身于岸边,不仅名利心在自然界中被净化了,而且连心也静下来,在静默中感受青印溪的自在与流动。一切都显得自由自在曼妙无比,而自然间的交流也如同人们的私语,似乎也怕惊扰了其中的生命。在这里,人与自然、动物与自然相处得如此静谧。它们之间洋溢着爱的气息、自由的氛围,生命与生命的怜惜、人对动物与人对自然的呵护在此一览无遗。怜悯既是诗人创作的情感出发点,也是他看待自然界一切事物的基本立场。在《小鸟走得轻》中,诗人对工业化时代中生活着的小鸟的生存境遇进行了聚焦,深切地表达了作者对于人类与自然关系越来越对立、紧张的担忧和哀痛:
小鸟走得轻,我在郊外的清晨/听见了。在水泥路上,十几只小鸟/把翅膀收起来,来回走动/轻轻地走/扇不出几缕轻风/我走得更轻。如此轻的脚步/还是被一只走在后面的小鸟听见 /一下子把翅膀发回天空。[1]11
在这首看似平淡、抒情也很节制的诗歌中,诗人的感情隐藏得很深。“水泥路”向人们暗示了田园牧歌时代的一去不返,小鸟们“来回走动”的已经不是乡村田野,这样的开头将鸟与时代的矛盾揭示得十分突出。那么,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作者描写的人与小鸟关系的紧张又表现了怎样的感情呢?著名生态诗人、诗评家华海对这首诗有着精辟的解读:“小鸟在水泥路上小心翼翼地走动,只要有一点轻微的响动,它们就会陡然惊起。诗人的这一个小小发现,却构成了一个大大的问题,我们把它放在一个生态平衡的观念中审视,不得不叹服诗人的敏感和悲悯情怀。他没有主观地站出来发表见解,只是回到事实存在的真相本身。而这真相其实在我们的周围已经较为普遍,但没有多少人去关注,人们的感觉神经是否已在物质的生活中日趋麻木?人们更热衷于物的追求和超前的消费、享受,小鸟们的世界、小鸟们的不安处境似乎与之毫无关联,而这种对野生动物家族的漠然,是小鸟们的不幸,却是人类的悲哀。”[2]3-4在《拜老樟树为干爹》《水向沈河流来》《蛙鸣》《河流》等作品中,诗人也同样以饱蘸悲悯的心境对于生态的现状、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细腻的勾勒,让读者在满腔的挚情中体味到诗人的生态情怀。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怜悯正是沈河诗歌最为感人的地方,他站在怜悯的立场上看待自然与社会,充满了对于现实苦难和生命卑微的同情,对于存在着的生态破坏、社会压迫抱有强烈的厌恶。
迁居到青印溪的沈河,并未在优美的自然中丧失了对现实生态的关注,反而凭借着作家的敏感和专业素养发现了生态危机的急迫,并发出了诗人疾声的呐喊。在沈河看来,“‘生态诗歌’,是指在生命和生存的体验中要有‘生态成份’的进入,也可以说在所处的位置散发隐隐约约的体温和夜深人静时血液的流动,这种体温和流动与生态有关。或许有人会这样认为,在世间多考虑的是生存环境的是否安逸和利益分配的多少,对于周边发生的变化往往熟视无睹,缺少的是投向自然界的视角和进入事物内部的那一瞥锐利的目光。”[1]224在《水向沈河流来》中,诗人通过昔日沈河胜境与今日污染、断流现状的对比,向人们发出了厉声的批判与凄苦的吁求:
沈河,这条小小的河/固定在闽中,鹰喊哑嗓门,/也不能和她一起飞翔。/真是一只鹰,/两片翅膀上压着熟悉的山水,/不想,也不能飞了。/芒刺尖锐,从中逃离,/河面窄小,扔下了一堆破鞋烂袜。/里面的云彩没剩多少,/只能把声音喊得小一点,/把步伐放慢一点。[1]15
如果说沈河的污染和破坏反映的是乡村自然生态的境遇的话,那么城市的生态环境更为恶劣,不仅诗情画意在环境污染中渐渐消失,而且连日常生活的维系与生存延续都成为了一大问题。擅长描写自然胜境、在青印溪中确立了自我艺术个性的沈河,也能够表现出对于工业文明进程的犀利批判。在《雨中》一诗中,诗人发现了生态危机日益恶化的现实,于是借助雨中漫步这一原本饱含浪漫色彩的场景进行表现,从而揭示了生态恶化的恐怖景象:
隔着一层薄薄的布,仅把雨水拦住/脚下,小路沉在水中/鸟粪、工厂上空酸溜溜的烟雾/每时每刻生长的灰尘、从山上冲下的黄泥/从眼窝溢出的泪水、伤口淌出的血液/都融在里面/围住我,围住我。[1]32
凭借着这种进入自然界和事物内部的锐利目光,沈河发现了环境污染的可怕程度,他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入手进行反思,揭示出人类视自然为资源、工具的传统病因。科学技术武装之后的人类表现出了愈来愈强的征服、统治自然的欲望和趋势,自然生态正不断地遭受蚕食。在这种情况下,诗人对于原本蕴含伟力的自然充满了怜悯,丧失了敬畏之心的当代人却在吞噬自然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二
在沈河的生态诗歌中我们能明显地感受到作者的宁静心怀和淡泊之姿,这种淡泊风格与诗人的创作视点关系密切。在诗人看来,“我创作的视点落在三个地方,都在闽中,一是出生地的香林村,二是居住的青印溪,三是与职业有关的山中。与香林村接近,主要关注农业和农民的命运,挖掘童年的记忆;与青印溪接近,试图进入城乡结合部平凡人的喜怒哀乐,看生命如青印溪流淌的行程;与山中接近,站在林业的角度,在所处的位置去创作生态诗歌。”[1]224无论是沈河创作视点中的任何一个,均与喧闹的都市保持了一段距离,而在较为淳朴、安静的环境中去感受自然、品味生活。沈河出生于香林村,“从童年、少年至青年初期的十几年当中,我与那里的草木一同生长,由于沉潜很深,那里许多东西成为我宝贵的写作资源,并且难于用完。”[1]224童年时代在乡村生活的点滴记忆,使沈河在宁静、祥和的环境中完成了对于自然的体认。正如诗人所说,“人生最值得回忆,印象最深刻,最能让你回到从前的岁月的是童年生活”[1]225。童年时代在静谧氛围中感受到的自然生态,在经过长时间的沉淀之后浮现于作家的意识之中,成为他源源不绝的创作资源。“我离开那里已经20多年了,现实中的人和事变得模糊,而记忆中的人和事在夜深人静时显得格外活跃,一次又一次撞击我的心扉,不得不拿起笔,记下,成了诗,我才会平静。”[1]225平静,既是沈河进行诗歌创作后的心灵状态,更是他诗歌本身的存在形式和思想旨趣。
于是,在沈河的诗歌中我们随处可见溢出的宁静、淡泊之态。当诗人置身于青印溪,或是停留在山中,他总是很容易联想起童年时代的时光,成长历程中的这种乡村记忆使沈河保持了对于自然事物的敏感。在诗人看来,他的生命是与童年到青年初期的草木一起成长的,自然已经融入了诗人的身体和心灵深处,成为他的某种潜在意识。于是在表现自然界的事物时,诗人通过对于景物的品味,仿佛回到了昔日的淳朴生活和时光。此刻诗人的心境变得平和,精神也日渐沉稳,流淌在笔下的文字似乎只有宁静。正是在这种心绪下,诗人在创作中完成了精神与自然的融合。在《也是一种飞翔》中,作者以动写静,通过对一只白鹇的动态描绘反衬出青印溪的宁静,揭示出一幅和谐美好的生态图景:
白纸一样,在金色的沙滩/以为是走动的花/水中的影子愈来愈小,一只白鹇/带动青印溪飞起来。水带到空中/落下来就是雨/这只白鹇从沙滩跳到岸上的绿竹/再跳到一棵高大的老樟树/启动的力在短时间酝酿/不是箭/像一只风筝/小小的青印溪养育的白鹇/踏不上往高空的阶梯/也是一种飞翔,在青印溪之上/在农田的上空,一块橡皮/轻轻地擦拭时光表面的黑点。[1]5
在这首诗中,诗人描写了动态的白鹇,将它的走动、跳跃、飞翔一一刻画。同时在这种动态的景象中,在白鹇将整个青印溪带动飞起来的瞬间,我们感受到的却是青印溪的宁静、淡雅。诗人以动写静,相得益彰,在动静关系的转换中生动地再现了青印溪的生态面貌。诗人还擅于捕捉自然中的精微细节,通过对于具体场景的集中勾勒,表现出人对于自然的聆听以及人与自然静谧相处。在《白鹇》一诗中,沈河通过白鹇在水边的生活场景,将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以及动物与自然的关系写得细腻、灵动,在若有若无的音响中勾勒出了一幅自然的胜境:
白鹇出生在青印溪,它鸣叫时,/我带来耳朵。/然后,再看鱼,有的潜入深潭/有的游在浅水中。又高又大的老樟树在水边,/枯落的枝叶在地上。/我搬来一块石头,坐着/比站着能够呆得更长的时间。[1]42
诗人在此并未直接抒发对于破坏自然行为的批判,也没有停留在对于人和自然友好相处的直接呼号,而是通过对于人与白鹇友善、和睦而静谧的相处,向读者传达出了呵护自然环境、无欲无求的淡雅之境,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对于融于自然,在沈河看来是自己诗歌的应有之义:“我始终认为诗歌的‘向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故乡在下面,大地在下面,植物的根在下面,小人物在下面,甚至伤疤也在下面。只有这样,更容易抵达凡人的心灵,更能直达事物的本质。”[1]1在这里,大地成了与自然等同的概念。诗人将自己的笔触深入大地(自然),汲取广阔大地的能量,以此激活诗人的灵魂与情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沈河的生态诗歌中,人只有在自然的深处才能真正地领悟自然、融入自然。这种与自然的真正融入,关键在于诗人身心与周围环境的完美契合,以此实现二者的水乳交融。在《河流》一诗中,诗人在对河流的冥想中,似乎自己也成了一条流动的河流,虽然略显笨拙,却与自然身心合一,诗意盎然:
河流,流过身边。/我翻动荒野,/洗掉墙上的旧标语,/打开事物的门窗,放进水声。/我劳动着,/手臂上出现了一块伤疤。/河流,像一条树枝/伸进我的视野,不缺少春天,/花盛开,花蕊里住着一群蜜蜂。/果园在秋天的深处,/我最先品尝甜蜜。/村庄,在河流的两边,/一排排房子依水而立。/我不去寻找源头和水尾,/只注视它的流淌……我的流动显得笨拙,在无人之境/比如在岸边、乡野、山间/偶尔蹲在沟边,看水如何流过石头。[1]49
如果说《河流》揭示的还是诗人在物我相忘中体验到的融入自然的幻境,在人化河、河映人的关系中表现了人与自然的亲密的话,那么在《投向青印溪》中,诗人则聚焦于融于青印溪之后的精神愉悦和思想启迪,诗人从中感受到了身心的休憩与舒适,还领悟到了自然对人的灵魂的净化。青印溪在诗人笔下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还是一个心灵概念和精神疆域。在这里没有脏累,没有死亡、仇恨,自然消弭了俗世的纷争,所拥有的只是宁静与孤寂:
告示:守在世俗的日子,不得离开半步/我从后门偷溜/身子积累的脏,所渴求的水/在不远处/投向青印溪,伤口现形/靠在浪头上,泡水三天三夜/从伤口还是从五官进去的脏/都要洗净/然后冲刷脑子,并把这些词:/死亡、疾病、仇恨、恩怨……/清除出去。[1]197
在沈河的诗歌中,青印溪成了一个独具魅力的诗歌高地。诗人常常驻足岸边,沉溺于对于青印溪的感悟和遐想之中。沈河曾说,他“常沉溺在岸边,不分早晚,眼睛在望,耳朵在听,鼻子在嗅,脑子在思考,心灵在飞翔。一旦被发现,一旦在精神上清除了遮闭和黑暗,我便获得了一个透亮的世界。”[1]229在这里,青印溪已超越了一个地理名词的范畴,它是沈河对于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的重要发现,是一个予人以诗情画意的精神领域。“中国生态文学作家由于过于贴近现实伦理,更由于缺乏伦理思想观念的生态激活,不少生态文学作品在审视生态伦理问题时往往秉持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准则,从而使原本无限丰富的伦理境遇和精神冲突简单化、机械化。”[3]但从沈河的作品中不难发现其“推崇顺从自然、随缘任运、自由洒脱的人生态度”,当沈河进入青印溪的时间和运转轨道中,他便实现了与这里自然的相互认识、接纳。当沈河的精神在青印溪的映照下逐渐明亮的时候,他获得了一种对于自然的全新认知和体验;而青印溪在诗人的观照下,也不再是一个客观的、毫无情感的普通自然事物,而是焕发出别样的精神光彩,予人以精神的启迪、灵魂的净化与思想的振奋。于是,自然之于人、以及人之于自然在这里实现了完美的沟通,这是一幅难得的生态胜境。
三
沈河追求诗歌的思想、叙事与抒情功能,在他看来诗歌的语言应该是新颖而准确、丰富而简练的,只有这样的语言才能直接深入人类精神深处,获得表述世界的力度。沈河明确地反对诗歌语言的散文化、概念化、粗俗化和随意化,他认为这些问题会从根本上损害一首好诗的产生。诗人认为,真正的好诗应该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能够使读者通过作家的言说方式获得生态感悟。于是,在叙述方式方面沈河“看重细节的力量,当然这些细节经过了朴素平静的心情所照亮的那部分,就不会试图借助华丽词藻的喧闹以显得似乎铿锵有力,不会这么多浓妆艳抹的形容词来削弱诗歌的影响和感染力。诗应该是质朴、直接的,不在感情上摇曳不定。”[1]229在抒情方面,诗人主张节制化的抒情:“我舍弃了语言表面的修饰,大家都知道修饰性的词语主要靠形容词来充当,我很少用形容词,用得多了怕会导致煽情。现在,我觉得不仅仅靠情来感动人,还有在平凡的事物中所采撷到新的发现也能让人感到意外,产生共鸣。抒情化的笔调仍然不能抛弃,但要节制。”[1]231
在思想方面,沈河也有着自己的思考:“思想的内核是诗的主旨,即主题,或诗性意义,对此不能过于狭隘的理解,它可以是一个发现,一个判断,一种倾向,也可以是一种意念,一种感悟,一种直觉,甚至可以是一种潜意识的萌动,一种气韵,一种氛围。当思想的内核出现时,就要调动脑子的各个细胞,把我掌握的词语进行情感的润泽和诗性的组合,为它服务,就像果肉一样围绕着,然后慢慢地形成果子的原形,挂在世人的面前。”[1]231-232关于叙事,诗人坦承:“我更看重细节,如果找到一个好的细节,一首诗可以完成一大半了。诗歌中的细节很重要,要学会用细节讲话。诗歌的细节用得好,比起空洞的抒情和思考要强一百倍。”[1]226
在《目光》中,沈河选择了“目光”作为题眼,对人们滥杀野生动物的行径进行了严厉的谴责:
穿山甲、猫头鹰、雕、巨蜥等野生动物的目光/含有兽性,只扫射在山野/森林越原始的地方其密度越高/他们的炊烟出现/早年,它们敢跑进去/如今只能远远地观看,炊烟依旧柔软/却伸出一双双手/遥控它们奔跑的速度/它们被他们捕获,眼睛还在/目光被掠夺/放入他们的眼睛。[1]190
在这首诗里,叙事的成分十分突出,但作者并非泛泛而叙,而是选择了与“目光”相关的几个场景,一直到结尾处才进行抒情,表达了诗人对人类掠夺自然、屠戮生灵行为的愤懑与控诉。在《一块土地用途变动的过程》中,诗人兼用议论、叙述、抒情的方式揭露了人们对于大地生态的不断破坏:
与祖国不离不弃,只是人民爱动手动脚/凭借一时的兴奋,变动它的用途/它原是一块平坦的山地,砍下的树木/成了棺材,成了门窗,成了柴薪/后来,饥饿难忍,开成一丘丘农田/由青变黄,谷子脱壳,喂养一段岁月/再后来,要上工业产值,一座工厂重重地落地/肥沃烂光,无根出入/现在,兴起房地产开发热,移到这里/铺上水泥地,仅留下几个口/种些草木,泥土要吃力地呼吸。[1]172
诗人以兼容并蓄的目光审视诗歌创作,将传统的抒情、描写生态现实的叙述、直斥国人破坏习性的议论等熔于一炉,使得诗歌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内涵得到了有力的扩充。
沈河的诗歌经验主要来自他对故乡山水、草木的珍爱,缺乏意识形态因素,因而显得更为单纯、更为生态。他既没有“对‘人生究竟’的焦灼追问”,也没有“无情地解剖自己的勇气”,他“不愿深究矛盾的实质及其相互关系,也不愿进行痛苦的思想斗争。”[4]从诗歌观念来看,沈河的诗歌创作追求沉静、简练而又生动、富有张力的诗歌语言:“我追求质朴、简洁的语言和沉静的表述方式,只有这样才能直抵生活的内层,写出独特的生命体验。”[1]2正如沈河所说,“我不想把诗写得过于复杂,偏离众人欣赏的习惯。我坚守‘把复杂的东西用简单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才是最难的事情。这种简单的方式不只是在语言上造成奇妙的效果,而要给读者带来新的感受、新的发现、新的情感,或是新的意象、新的构思角度和新的语言风格,同时要考虑诗的主旨与情感必须取得意象、形式、气韵、节奏、语言的有力合作,和谐融合在一个有机整体之中。当然,诗要留空白,要在时间和空间上转换,在这方面,是我努力的方向。我说过,一首诗不仅要给读者在读后留下‘言尽而意无穷’的感受,而且在读的过程中从每句诗中获取所蕴含的意义和语言组合的快感。”[1]235-236
沈河诗歌风格与思想的形成,除了诗人对于自然的深刻体悟和细致观察,也与他汲取其他诗人作品的养料有着密切关系。沈河毫不讳言,“外国诗歌的言说还是国内诗歌的言说,在我的诗中都会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1]230事实上,在沈河诗歌理念和特色的形成过程中,《诗经》的作品,王维、切·米沃什、加里·斯奈德等诗人都对他的创作具有程度不一的影响。诗人在访谈中承认,很多诗人值得他学习,对其诗歌创作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如果说米沃什的诗歌让沈河领略到了宁静自然的心态、怜悯看待一切事物的视角的话,那么《诗经》则让沈河学到“兴”的手法,使其诗歌意象获得了独立性和丰富性。“《诗经》对人的教育,并不是直接说你要做好人,它教给你一种风度,即温文敦厚,这是中国诗教的特点。我们看《诗经》,它的腔调不是很激烈,在表述上也比较克制,是中庸的、婉转的,最终让你学会一种说话的方式。”[5]诗人“喜欢王维,因为他在诗歌中所表现的人与自然融合的努力,造就我的诗所选取了自然性语言,远离市声,与大自然靠近并进入它们的内部,倾听它们的话语”[1]227。加里·斯奈德“在诗中把禅与道、儒相结合,道提供了对自然界的尊崇,而儒家强调社会组织对保证人与天协调所负的责任。让我知道除了个人顿悟和爱惜一草一木之外,让我的诗歌使利益至上的社会现出人性,寻找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以免导致生态毁灭”[1]227-228。面对来自传统和异域文化的影响,沈河坚持从对外界事物的生命特质的把握和对自然的感悟入手,在对中西精神养料的汲取中不断完善自我的诗学结构、生态思想和艺术形式,从而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激发出更加强烈的原创能力。此中情形,正应验了杨义先生所描述的文化碰撞时代对于创作者主体精神的呼唤:“在中西知识网络大张,知识涡流湍急的近世,应该提倡笑纳八面来风的从容,更不应该忘记树立主体创造的精神支柱。主体应自重,面对中西知识经纬交织而成的张力或弹性,站稳脚跟,挺直腰杆,纵览林林总总的诸般思潮,于思潮中把握思想”[6]71。
对于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批判和对于自然万物的悲悯,在沈河的作品中结合得自然贴切,而其中又以生命体验和自然感悟作为整体创作的底色。这种生命体验和自然感悟,是与作者在生态诗歌中注入“体温”和“血液的流动”的追求是联系在一起的。“诗人在精神和身体上深入自己身处之地,在自然和生活景观写作中融入抒情和哲思。诗人在写作中自觉地探索人与地方的密切关系、思考人类应有的存在方式。在地方剥夺日益加剧的当下,这种创作启发我们对‘生态诗歌’的涵义进行新的思考。”[7]沈河始终是怀着关怀自然的亲切、与自然休戚与共的悲戚之情进行生态诗歌创作的,这种生命特质已经深入到作者的血脉与思想深处,从而在对生态现实和生态胜境的勾勒中均表现出鲜明而持久的存在感,使得读者得以和诗人一起感受自然的疼痛、悲哀与梦想。
[1] 沈河.西安:相遇[M].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
[2] 华海.被惊扰的小鸟[M]∥当代生态诗歌.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3] 龙其林.从他者到本位:中西生态文学伦理的现代转型[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92—97.
[4] 哈迎飞.随缘任运 皈依自然——二十年代作家逃禅现象之一瞥[J].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9(6):68—69.
[5] 陆建德.文学发展的逻辑——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陆建德[J].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4(5):9—13.
[6] 杨义.现代中国学术方法通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
[7] 刘蓓.关于“地方”的生态诗歌——马克·特莱蒂内克作品解读[J].外国文学研究,2013(1):3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