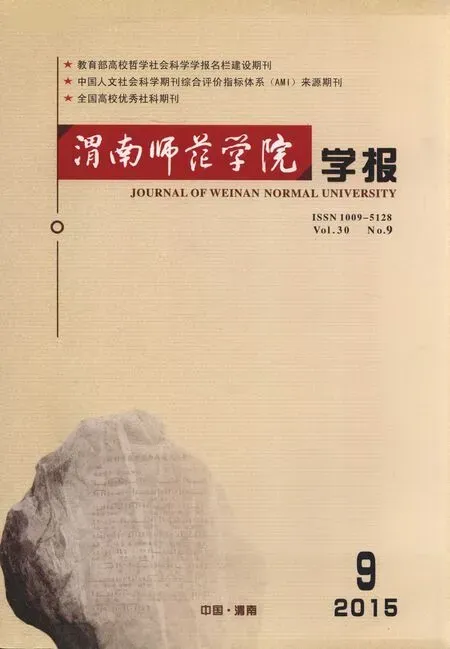刨根问底细检讨云开雾散说长爱
——付兴林、倪超《〈长恨歌〉及李杨题材唐诗研究》读评
2015-03-20蔡静波
蔡 静 波
(渭南师范学院 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秦地文化研究】
刨根问底细检讨云开雾散说长爱
——付兴林、倪超《〈长恨歌〉及李杨题材唐诗研究》读评
蔡 静 波
(渭南师范学院 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及作品所属类别,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付兴林、倪超以充分的论据,严密的论证,否定了传统的“讽喻说”和“双重主题说”,提出了“长爱说”的观点,同时认定该作就是作者生前划分的“感伤诗”而非“讽喻诗”。文章论点突出鲜明,条分缕析,语言流畅,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白居易;长恨歌;主题
近日拜读了付兴林与倪超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的《〈长恨歌〉及李杨题材唐诗研究》一书,不禁对作者增加了一份敬仰之情。说实话,像白居易《长恨歌》这样被无数人翻耕了不知多少遍的作品,期盼能有哪怕一丝新的收获都令人怀疑。但是,该书作者显然做到了,而且破旧立新,是那么的令人不容置疑。
一
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之辩历来众说纷纭,但向以“讽喻说”“爱情说”和“双重主题说”为主,这三种观点各自似乎都有充分论据,彼此谁也不能独占鳌头。《〈长恨歌〉及李杨题材唐诗研究》作者(以下简称作者)以学人特有的理论勇气,大胆质疑旧说,首先从“讽喻说”的缘起、流变进行旁征博引,考据辨析,再通过对作品本身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最终达到否定“讽喻说”建立“长爱说”的立论目的。
首先作者对“讽喻说”的源流进行了梳理。他认为首起《长恨歌》为“讽喻”之作的当是与白居易同时代的陈鸿。因为陈鸿在他的《长恨歌传》中有一段话:“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就是这段话,成为后来坚挺《长恨歌》属于“讽喻”之作的始作俑者。其后明代的唐汝询有“此《长恨歌》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之语;清代沈德潜有“《长恨歌》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者也。以女宠几乎丧国,应知从前之谬戾矣”之论;下诏编纂《四库全书》的乾隆皇帝在《唐宋诗醇》中亦对“讽喻说”推波助澜,认为《长恨歌》“哀怨之中,具有讽刺。……发乎情而不能止乎礼义者戒也”;再后来就是当代学贯古今的陈寅恪,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以翔实的考证,严密的论证对“讽喻说”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发挥;随后作者列举了一系列学人及其论文论著名称和一些主要观点,以及各种版本的文学史,都不同程度地支持或肯定“讽喻说”之观点。
其次,作者对“讽喻说”的缘起和流变逐一进行了据理辨析。这里,他从《长恨歌》和《长恨歌传》的不同文体和作者的立足点、倾向性进行分析对比,进而得出结论:“从作品实际看,《歌》着眼于李杨爱情热烈、凄婉、坚贞,而《传》则瞄准了李杨爱情的荒唐、困惑、淫荡。既然着眼点各别,岂可《传》冠《歌》戴?陈鸿已有自作主张、以己心度他人腹之嫌,强行为《歌》戴上了一顶‘讽喻’的帽子。”这是后代评论家坚持《长恨歌》“讽喻说”的缘起。显然,否定这一缘起观点,实际上等于釜底抽薪,使后继之论难于立脚。
第三,众所周知,白居易曾将自己的作品分为四类:“讽喻诗”“感伤诗”“闲适诗”“杂律诗”。而《长恨歌》是被作者明确划归到“感伤诗”一类的。但因为白居易向来有“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诗歌求讽刺”“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做”等文学观点,所以一些学者就不惜滥用美刺原则,罔顾事实,硬是把白居易按照“情理动于内”的原则创作的感伤类作品《长恨歌》划归到作者后来按照“首章标其目,卒章显其志”的原则创作的讽喻类作品如《胡旋女》《李夫人》一类,仿佛不把白居易放到讽喻诗人的位置,心就不安,不把《长恨歌》的主题定性为“讽喻”,就不贴切。所以作者说:“强自将白居易的诗论主张乱驱遣、贴标签,这是对作者的不尊重;无视不同诗歌的特性,而欲以用一尺度进行剪裁,这是对作品的玷污;试图一厢情愿地拔高作品的思想性,这是对读者的瞒和骗。”
第四,导致对《长恨歌》主题这种认识的不仅仅是陈鸿的主观臆断,也不仅仅是学者们的盲从和滥用,其中也有白居易自身的原因。这一点本书作者也没有回避,而是进行了详细地辩说。譬如,清代乾隆皇帝在《唐宋诗醇》中就有过如下一段议论:“居易诗词特妙,情文相生,沉郁顿挫,哀艳之中具有讽刺。‘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君王掩面救不得’,皆微词也。‘养在深闺人未识’,为尊者讳也。欲不可纵,乐不可极,结想成因,幻缘奚罄,总以为发乎情而不能止乎礼义者戒也。”作者认为这段话包含了三层意思,“第一,《长恨歌》的主旨是讽喻、劝诫。第二,‘汉皇重色思倾国’等句,是对唐玄宗的批评之词。第三,‘养在深闺人未识’是为大唐天子遮掩丑行”。而且他说:“的确,任何试图驳倒‘讽喻说’而主他说者,都不得不认真对待、思考这些令人困惑、费解的棘手问题。或许以前力主‘爱情说’者,未能很有说服力地回答这些问题,或是在未及彻底探实底部的情况下就匆忙立论,因而招致其主张由于缺乏坚实的信心支撑而常不禁风雨,自身难保。”接着,作者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辩证:一是“重色”而非“好色”。持“讽喻说”者都断言诗篇首句“汉皇重色思倾国”为全篇奠定了基调,并成为全篇的纲领,其中,尤为显眼、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重色”“倾国”两词,借用汉武帝、李夫人之典,即代指美艳绝伦的女子,又语含因女色而亡国覆国之意。作者认为,“重色”与“好色”有语义相叠的部分——对女色抱有浓厚的兴趣,但两词的区别也显而易见:“重”是看重、重视、珍惜之意;而“好”是偏重、贪爱、嗜好之意。“重色”与“好色”不仅有程度上的浅深之殊,而且有词义上的褒贬之意,甚至可以说有德行上的高下之分、美丑之别。作者认为,白居易在熟悉的语境中不用“好色”而要选用“重色”一词,是要表露他对唐玄宗、杨贵妃爱情回护、称许、肯定的态度。作者说:“倘若白居易果真要在《长恨歌》中宣扬什么惑君误国的讽喻主题,倘使他确欲在首句中就表明他对李杨的轻蔑态度,那么,通俗现成且颇具讽刺力度的‘好色’一词为何偏偏为他舍弃不取而刻意精选了那么一个温和善意且与‘倾国’一词的走向抵牾的‘重色’一词呢?可见,‘重色’非‘好色’,‘倾国’非‘覆国’。”二是“杨家有女初长成”非为君讳。根据两唐书记载,杨贵妃最初是唐玄宗第十八子寿王瑁的妃子,后唐明皇经不光彩的手段辗转收为自己的妃子。作为谙熟历史的白居易何以要避开历史的真实,曲意替李杨开罪说好话呢?既然白居易要在《长恨歌》中讽刺君王惑色误国,夺儿之妃的事难道不正是最具利用价值的讽刺材料吗?作者认为:“白居易对历史作如此改头换面的美化处理,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一切为诗情、为主题服务。凡是可能损伤主题或与主题相左的材料一概加以‘校正’‘净化’,使之有助于人物灵魂的纯洁,有益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有利于文气的和谐、主题的集中。可以说,对杨贵妃婚史的清纯化处理,与‘重色’而非‘好色’的遣词乃是一脉相承的配套性文学手段,是白居易多方回护李杨形象的主观倾向的客观显现。据此可说,‘杨家有女初长成’非是为君讳恶,而是意在为李杨爱情创造一个纯而又纯的发生背景。”三是李杨之爱非荒淫纵情。作者首先引用传统论者(讽喻说者、双重主题说者)借以引用的《长恨歌》句子及其论点,说明传统论者只不过是用史学的观点来解剖充满奇情遐想的文学作品而已。然后通过对文学与史学不同理念的阐释,证明艺术形象的提炼不是唯一的,而是多维的。同一历史原型,既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描写,也可以从别的角度去描写,只要这种描写不违背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相结合的原则即可。他通过人们对王昭君形象的不同描写与理解,进而证明白居易对李杨爱情时恋、时怨、时恨前后看似矛盾的如此描写,说明帝妃之恋既有超出普通人的自由性又有不及普通人的不便之处,即高出历史生活又超越历史之恋的一对恋人。作者认为,“回眸一笑百媚生”不是对杨贵妃所谓妖姿狐态的摹写,而是对其充满魅力的倩笑的传神描写;“从此君王不早朝”不是对唐玄宗荒于政事的指责,而是对其痴情挚爱的渲染;“三千宠爱在一身”不是对唐玄宗施爱一身、杨贵妃夺尽人爱行为的不满,而是对唐玄宗用情专一的称许;“姊妹兄弟皆列土”不是对杨氏姐妹恃宠皆贵的针砭,而是唐玄宗爱屋及乌“爱心大奉送”的夸饰;“缓歌慢舞凝丝竹,今日君王看不足”不是对李杨只知一味逸乐的讽刺,而是对他们知音互赏的尽态极妍的吟咏;所谓“三千宠爱在一身”,所谓“度春宵”“夜专夜”“醉和春”,正是发生在皇宫里帝妃情爱的特殊印记;所谓“姊妹兄弟皆列土”,所谓“不早朝”“看不足”,正是这对情痴意浓的帝妃沉浸在爱河中的有力佐证。显然,白居易这样描写旨在表达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情深意浓。显然,“从作品中看到,李隆基与杨玉环本意并非要以权谋私,干乱朝政,而是在追求人间至爱”。
二
陈鸿在《长恨歌传》中曾明确交代了《长恨歌》的创作过程:“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作者从这段话中,首先推测出白居易、陈鸿、王质夫三人“相与感叹”的内容既有可能是“讽喻”的角度,也有可能是“爱情”的角度;接着对“希代之事”进行辨析,认为其有三层含义:一是唐玄宗以至尊至贵的身份,居然保不住自己钟爱的妃子,在历代帝王中出现这样的人生悲剧,唐玄宗是第一个;二是杨贵妃作为一个历史上稀有的既美丽又钟情的女神,居然成了宫廷斗争的牺牲品。其被宠极而突然又被毁灭的不幸际遇,开天辟地以来算是头一遭;三是杨贵妃在马嵬坡蒙难之后,曾有贵妃未死、流落乡野、入籍为女冠的小道消息。玄宗曾派人多方寻找,以至出现了方士为贵妃招魂的神话传说,以及赠物托情、盟誓寄怀的情节。王质夫并没有把保留流传于民间的李杨之事的任务,托付于一同感叹且深于史、多于理的史学家陈鸿,而是托付于“深于诗,多于情”的文学家白居易。显然,王质夫的托付与情感寄予也很明白。换言之,从《长恨歌》的创作缘起看,其切入角度是以文学规律、美学规律为利剑,对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李杨之事进行删裁、润色,以生生死死的至情为主线,展现凄恻缠绵、痴情坚贞的帝妃之爱。
当然,单从《长恨歌》的创作缘起看,只能表明白居易有可能按照文学、美学的规律对李杨之事加以再创造,但尚无绝对把握断言白居易定然会摆脱历史的束缚,从正面去讴歌李杨生死不渝的爱情。然而,如果我们对白居易创作《长恨歌》前后,尤其是之前的心境加以考察、研究的话,我们自然会看出《长恨歌》是在白居易特定的心理定势作用下的产物。文学创作中作家的心理定势决定着作品的思想走向。作家从选取题材开始,就以自己的情感体验、经验为过滤器,筛选着与内心情感合拍的、最能打动自己心灵情弦的事情来写。白居易创作《长恨歌》前曾经有过两段恋情,一个是他与符离湘灵姑娘的恋爱,一个是他与长安歌妓阿软的交往。第一段恋情是他在19岁的时候,与邻里一位15岁的湘灵姑娘产生了爱意,并开始初恋。从时间顺序上看,白居易从与湘灵姑娘相识相恋到元和初年他35岁时写《长恨歌》时两人感情已经持续了十五六年,虽然这段感情无疾而终,直到37岁时才在母亲的高压下,与同僚杨汝士的妹妹结了婚。但显然,他和湘灵姑娘的这段情感经历应该是他创作《长恨歌》的情感基础、心理定势。换言之,这段恋情,对他情感经验的储备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第二段与阿软的交往相对晚些,也短些,其情感应不及与湘灵姑娘的,但也不可或缺。
显然,“白居易恋爱时的感受,无论从形式上或从内容上讲,都在《长恨歌》中借李杨故事得以尽情释放。《长恨歌》与其说是在王质夫的促请下创作出来的,不如说是在白居易内心苦情的涵育、作煎下创作出来的。白居易借李杨故事的形式,宣泄了他内心深处悲痛的感受和真挚的爱意,并‘将他对自己的爱情悲剧的认识和情感完全融化在《长恨歌》中了’”。或者说,“这就又有了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旳特点。就遭遇了婚恋的不幸且痛彻肺腑这一点说,白居易是把唐明皇看成了同为天涯沦落人,自然会产生一种惺惺相惜的深切同情,当然也就在《长恨歌》的描写里,倾注了他的全部热情和真情”。
其实,《长恨歌》主题之所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原因除了上述陈鸿的主观臆断及其嗣后学者们的盲从和滥用外,除了《长恨歌》作品本身的描写易于产生误读外,也还有白居易自己的“矛盾性自评”。作者说,所谓“矛盾性自评”是指白居易自己在评价《长恨歌》时所呈现的矛盾性言论和态度。这些表面看起来非常矛盾的评价,使我们在把握《长恨歌》在白居易心目中的地位时产生了左右游移不定的困惑,最为糟糕的是一些论者据此无端发挥。具体缘由有二:一是白居易在《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一诗中写道:“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音》近正声。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莫怪气粗言语大,新排十五卷诗成。”从诗人流露的口吻看,白居易对自己的《长恨歌》充满了自得之意。“讽喻说”者认为,白居易将《长恨歌》与“近正声”的《秦中吟》相提并论,很明显,白居易是在讽喻诗的范围内品评他们的;倘若两者之间没有一致性,白居易是绝难将它们放在一联之中加以对举的;并在此基础上,用《毛诗序》之释阐明白居易的《长恨歌》的有风情和《秦中吟》的近正声与他在《与元九书》中强调的“风雅比兴”相一致。接着,作者又借诗人写于元和十三年的《湖亭与行简宿》一诗进一步证明其“风情”绝非“正声”绝非“讽刺”。作者认为,“风”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与“风情”的含义其实是不同的;并从词性和语义上进行了辨析,认为,“正声”的“正”与“风情”的“风”在词中的功能是相同的,其词性也是相同的,应属名词;“风情”不等于“风”,“风”也不等于“讽”;“风情”就是深情、痴情,就是缱绻、浪漫的恋情,就是男女之柔情、帝妃之真情。再一就是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的两段论述,一段写道:“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这里,白居易把《长恨歌》看得很轻,其低调的评价让人难以置信,进而禁不住怀疑“一篇《长恨》有风情”是不是出自他的口中。一段写道:“日者又问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服判传为准的。……又昨过汉南日,时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没有咏仆诗者。此诚雕虫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作者认为,上述看似矛盾的论述,只是表明了白居易不同的心理和出发点罢了。他说:“无论表面上或骨子里,白居易对《歌》与《吟》均推崇、看重。‘口非’的背后,揣着‘心是’的激动。……大体来说,白居易对自己的作品,无论是讽喻类的《秦中吟》,还是感伤类的《长恨歌》,但从文学的角度去衡量它们的价值,在其深层次意识中,自始至终都持绝对肯定的态度。”
在去伪存真之后,我们看一看白居易真实的态度。他在《与元九书》中,明确将自己此前创作的诗歌划分为四类,即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其中谈到“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这句中将杂律诗和感伤诗的代表作名篇《长恨歌》同提并举的运用中,不难看出感伤诗与杂律诗同处于白居易诗歌分类的最下层。而其本意是“提请社会、读者把讽喻诗、闲适诗与感伤诗、杂律诗以同样喜爱的程度来对待”。作者指出:“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将《长恨歌》归入‘感伤诗’是在距《长恨歌》创作九年之后的元和十年(815),也就是陈鸿为《长恨歌》自定主题后的第九个年头进行的。……试想,如果白居易对陈鸿之说——‘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无甚异议的话,他自然会顺着这根高杆往上爬,让他的《长恨歌》永远戴着那顶似是而非的高帽,徜徉于正统的天衢。然而,白居易并没有那样做,他毅然摘除了陈鸿无端套在《长恨歌》头上的桎梏,以归类的方式重申了他对自己作品的定位、定性。”
三
至此,应该说,作者已经完成了对前贤学者关于《长恨歌》主题诸论的彻底否定。接着,作者通过对《长恨歌》作品本身的详读细解、条分缕析,把《长恨歌》划分为三个部分,即第一部分为“赏美”,从首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到“尽日君王看不足”,共30句;第二部分为“思美”,从“渔阳鼙鼓动地来”到“魂魄不曾来入梦”,共44句;第三部分为“寻美”,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结尾“此恨绵绵无绝期”,共46句。
“赏美”是故事情节的开端,它实际上包含着追求美、欣赏美两个层次。作者从对第一部分的解读中得到如下几点感受:一是赏美的对象是杨贵妃,赏美的主体是唐玄宗。杨贵妃倾城倾国的美貌是这段美满婚姻的首要条件,唐玄宗赏美、宠美是这段美满婚姻的感情基础。因而,他们的相知、相爱不仅是合情合理的,也是无可挑剔的。二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相处的时间概念被淡忘(除去并不能说明时间长度的“春宵”“春游”外),可看成是对他们相爱忘记一切的暗喻,以及他们爱意持久不衰、不变的明证。三是发生在皇宫中的浪漫爱情必然地带有其贵族的印记,但像“华清池”“芙蓉帐”“金屋”“玉楼”“后宫”“骊宫”之类表示空间地名的词不断出现在诗中,除了在其能指层面上代指他们爱的发生地外,在其所指层面上则是以丽词艳字作为李杨相爱的密度、浓度的符号而出现的。四是这第一部曲在全篇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整个曲折、离奇故事的开端,它为全诗定下了以情为主的基调,它为第二部曲爱的变调演奏起着铺路架桥和对比映衬的作用,它为第三部曲爱的主旋律再次对接、奏响起着参照的作用。
“思美”为故事情节的发展,包含着美的陨落和对美的思念两个层次。在第二部曲中,白居易转换了抒情的基调——变快意为悲痛,变浪漫为凝重。主要写了美的毁灭,以及失美以后唐玄宗痛苦不堪的刻骨相思之情。其中的抒情主题,已随杨贵妃之死而直接由唐玄宗一人所扮演。在这一部分里,白居易笔下的唐玄宗,完全是一位忠于爱情、恪守真情的痴情天子。而作者也同样感受到了如下几点:一是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浓郁的追思之情,是第一部曲中痴情、任情的必然结果。二是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具有历久弥坚的长久性。三是唐玄宗的悲伤,是其无计可消除的真情的自然流露。四是这一部分在总体结构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寻美”是借仙山托物寄情,誓言重温再申。在“寻美”这一部分,白居易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塑造了仙界中的杨贵妃形象。其中描写了她崇高的灵魂——她对爱的理解,她对爱的追求,她对爱的坚定信念和对爱的美好祝愿。“蓬莱仙境”的及时出现,好比雪中送炭,使唐玄宗的焦情灼意有了着落,有了回应,使突遭劫难的杨贵妃的命运有了归宿,有了发展;同时,唐玄宗,尤其是杨贵妃的情感、心灵乃至情操在这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展现、提升。可以说,通过对仙界的描述,使杨贵妃的形象最终走向了完美,成为一个既有外表美又有内心美的光辉照人的艺术形象。《长恨歌》的总体构思也于此浑成妙合,主题至此也豁然凸显。
从逻辑关系看,第一部曲主要写李杨之爱。中心人物分别是娇美的杨贵妃和宠美的唐玄宗,皇宫是他俩相爱的游乐园;第二部曲主要写李杨爱情招致毁灭后唐玄宗对杨贵妃长久的思念。李杨由相爱到被迫分离,造成中心人物由二减一。马嵬坡是爱的坟墓,西宫、南内是爱的冷宫;第三部曲主要写杨贵妃对唐玄宗浓情长意的回应以及她坚贞不渝的爱情观。离场已久的杨贵妃成了抒情的中心人物,蓬莱仙山成了示爱的最高境地。作者指出,在全诗中,“蓬莱仙境”对《长恨歌》的情节具有拓展作用,对《长恨歌》的主题具有生成作用,对《长恨歌》的悲剧意识具有消解作用。
总之,作者通过对《长恨歌》主题传统诸论追根溯源式的剖析否定,通过对《长恨歌》“赏美”“思美”“寻美”三个部分的分析论证,达到了“破”“立”之目的,构建了自己关于《长恨歌》主题“长爱说”的论点。诚如作者说:“赏美之短,失美之久,寻美之切,构成了《长恨歌》三部曲的内在运行主线。《长恨歌》之‘长爱’主题正是李杨之爱由发生到发展再到高潮所必然闪现的光环。”
最后,要说的是,此书说理论证,不仅逻辑性强,而且文辞优美,颇值得一读。
【责任编辑 朱正平】
Searching the Details of Chang Hen Ge and Getting the New Theme from the Cloud ——OnChangHenGeandStudyofTangPoetryforLiYangLoveSubjectby Fu Xing-lin and Ni Chao
CAI Jing-bo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einan Normal University, Weinan 714099, China)
The category and the theme of Chang Hen Ge written by Bai Juyi varies in history. Fu Xing-lin, Ni Chao sought the sufficient evidence and had the rigorous reasoning to deny the traditional views such as “Allegory” and “Double Subjects”. They put forward the point of view of “Everlasting Love”, and the poem should belong to “sentimental poem” rather than “allegory poem”. The argument is prominent and bright, the language is fluent, and it is worth reading.
Bai Juyi; Chang Hen Ge; theme
2015-01-22
蔡静波(1957—),男,陕西华阴人,渭南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及秦东民俗文化研究。
I206
A
1009-5128(2015)09-002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