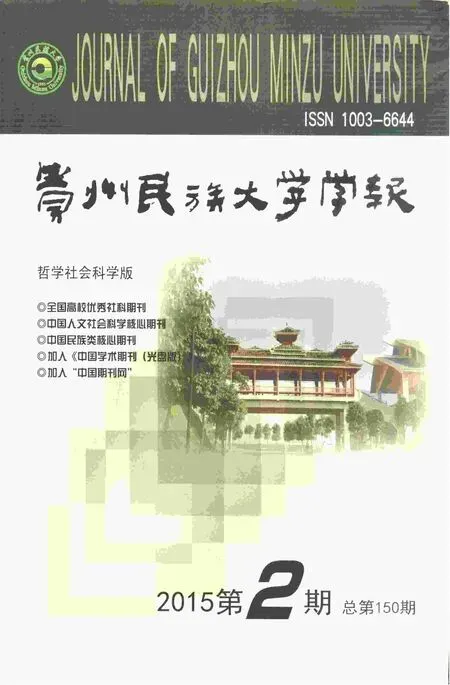祖先庇荫下大理白族传统房屋空间结构与意义解析①
2015-03-20刘朦
刘 朦
(1 复旦大学,上海 200433;2 云南大学,昆明 650091)
一、祖先的庇荫
中国传统的合院式房屋是一个礼的空间,一种新儒学价值观的具体化。它是一座家庙,以祖先的牌位为仪式中心构造而成。房屋庇护着一个家族系统,将生者和死者都纳入父系血缘关系的历史、地缘网络中。作为儒家基本伦理的五伦中的三伦——父子、夫妇、兄弟——都在家院的围墙内表现出来。在新儒家学派最关键的文献《朱子·家礼》,将“祠堂”放置在卷一之首,强调祠堂的中心性和在这里举行的繁多的日常仪式,包括每天的“谒”,一月两次的“参”和在民间节日如新年上的正式供奉。与提供行为举止和治家标准的其它新儒家著述一样,遵守空间界限乃是主调。[1]P49
祠堂是祖先崇拜的物质化反映,祖先崇拜实质是对祖先亡灵的崇拜,它通过祭祀的仪式来表达。我们都知道,一般宗教都有一个可以举行宗教仪式的固定场所,佛教有庙,道教有观,里面有偶像可以供善男信女顶礼膜拜。为了弥补儒教理论构成的缺陷,朱熹将《祠堂》标立于《家礼》之前端,在祠堂内供奉自己的祖先,让人们时常面对自己的祖先而告白内心,借此重振精神,慰藉心灵。[2]P10-14白馥兰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举行典礼的地方,每一个中国家庭传统上都是很讲究礼仪的,体现了宋代理学精神,也就是父权。
徐烺光先生的《祖荫下》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讨论了一个中心问题是:由于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不同,相同的社会行为所产生的结果也就不同。“社会行为”在这里指的是以“祖先庇荫”为中心内容的一切活动。①从喜洲镇的文化看来,在祖先的庇荫下,对人格有着重要影响的两个因素是权威和竞争。第一个因素包括父子同一的关系和大家庭的理想这两个概念。第二个因素包括以下三点:第一,为共同祖先的荣耀;第二,为宗族内某一个支系的荣耀;第三,为祖先们最庇爱,最有才干的后代的社会地位。[3]P8-9许烺光以这两个因素为主要线索,对喜洲的民俗文化、家庭生活、婚姻形式、家族繁衍、与祖先交流学习的方式进行详细讨论,试图描述和分析产生文化个性以及产生喜洲镇其他类型个性的文化背景。
这样的推论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白族人的真实生活,又在多大程度上渗透入了汉族他者的视角?但不可否认,《祖荫下》确实是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在汉化程度极高的白族那里,祖先的庇荫反映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他们的建筑空间结构便是对这一反映的最好诠释。
二、编成密码的父权制
(一)合院式格局:墙与院落
大理白族的民居建筑自明代中后期逐渐形成了“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六合同春”等多种平面布局和组合。院落的生成在于四面围合的理念,围合导致封闭空间、内向空间的产生。这与中国传承几千年的礼制文化有着直接的联系,可以说院落的形成是礼制的外在体现。中国古建筑的“门堂之制”是院落形成的主要原因。院落从构造上来说是由门、堂、廊(廊包括围墙,围墙是廊的一种变形)组成。[4]门堂之制来源于礼制,据说《三礼图》里有关于此的详细说明,说明其是礼制的一部分。
大理白族的居住形式三代同堂、四世同堂较为普遍,甚至叔伯、表亲几辈同住的现象也大量存在。反映的是以父亲血统规则计算的血缘关系,住在宅院里的一家人,由规定严格的父亲血缘关系组成——“我们”。白族社会中父舅权思想十分突出。父亲家长为一家之主,称为“当家爹”。白族的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式民居,是与一夫一妻制的传统父系大家庭相适应的。环绕房子的围墙将里面与外面的世界分开,界定了家的范围及其依附者。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界墙者,人我公私之畛域,家之外廊是也。”围墙是院落大小范围的边界,是私人生活空间的屏障。因此,墙对于院落建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界定因素。
院落的规划意味着秩序的生成,白族建筑中严格遵守长幼有别思想。一是民居布局力求规整,讲究对称,秩序井然,主从分明,重点突出。充分体现了长幼有序、尊卑有定、居中为尊的封建等级制度。比如,《祖荫下》记载道,上了年纪的父母通常和长子住在西房。[5]P47家长住正房,子女按一定秩序分住厢房,客人住楼上。二是内外有别,对外隔绝,自成天地,保持较好的私密性。徐烺光对此分析道,住房分布取决于社会习俗,而并不考虑个人的爱好、房间的舒适和卫生状况等等其他因素。这些习俗强调辈分、性别及年龄的重要性,同时也注重亲属关系。[6]P47伦理意识在平面布局和房屋体量上表现得较为突出,正房作为家居生活的中心,体量比厢房大,表现了白族父权家长制以老为尊的向心结构特征。以院落为中心来组织平面,布局具有明确的中轴线,正房、下房、左右耳房均呈对称布置,充分反映了父子传承的伦理观念,延轴线向纵深延伸的四合院形态与父子延续型的家族制度一致。
在对室内住宅内部舒适性忽略的同时,是对住宅外观装饰的重视。不管是大门、墙壁、照壁还是窗、屋檐等,无一不精雕细琢,精益求精。按照徐烺光的说法是,住宅本身是激烈竞争的代表物。房屋住宅与其说是家庭成员用以栖身的舒适之地,还不如说是整个家庭——包括死去的,活着的,未来的家庭成员——神会威望的象征。[7]P33
(二)家屋的中心:祭坛与炉灶
大理白族的堂屋是一个祖先崇拜的空间,在家里同时住着生者和死者。正如弗兰西斯·何素所说,一家人生活“在祖先的阴影下”。最近的四代祖先的灵魂居住宅子正中,他们的牌位被摆放于祭祖的祠堂中。白族普遍奉行祖先崇拜,认为祖先逝去后,他们的灵魂仍然能保佑后代子孙。对祖先越虔诚,越能受到祖先的庇佑。堂屋供奉着祖先牌位和一个写着家谱的牌子,堂屋正面搁放着三个木制的高约为1.2 米的大柜子,中间是中堂。②墙上挂着刺绣而成的约长2m、宽1.2m 的“福正中悬挂的是寿星图,或是松、鹤之类。两边挂着贺新房或是祝寿时的两三对对联。牌位供奉的地方,是家庭里最神圣之处,也是室内装修最重点的部分。供佛的佛龛一般为并列三间,各细部雕刻都非常精美,不亚于寺庙里的技艺。
对19 世纪和20 世纪的大多数外界观察者来说,中国人的房屋看起来首先是一个家庙,“祭坛特意摆放在主要建筑的主室里,在整个住宅的心脏部分——门面气派地朝向院子。整座宅院围绕着这个屋子而建,朝向和布局都以之为焦点。屋子的数目必须是单数,这样,祖先祭坛就正好处于整座房屋的极点,处于对称的中心,从而保证其支配作用和中心位置”[8]P75。
在大理,通过摆放祖先牌位和写有先人名讳的大纸得以彰显祖先的地位。每年农历七月初一,祖先都要被接回家中,接受食物和香火的供奉。有一些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已把祖先牌位移到堂屋顶上二楼中间的位置,相比一楼来说,这里更为清静。二楼多用木板隔成三间,中间一间靠墙设有神龛。供桌上摆着三类神位:如来佛祖、观音和文昌帝。左边是祖先的神龛,一般摆着四代已逝祖先的牌位。右边供奉着财神。儒、佛、祖先一道享受着房主的香火,常年不断,共同保佑着这家人财福共旺。值得一提的是堂屋的门,白族称为隔扇门③一般有6 扇,每扇宽1 尺5 寸3 或1 尺5寸6,每扇门由两大三小,五块木板合制而成,木板上的雕刻涵盖多种主题,有“二龙抢宝”、“渔樵耕读”、“八仙过海”、“博古陈设”、“稀缺登梅”等内容。隔扇门的最大的特点是由几层浮雕构成,少则二三层,多则五层,层层相连,在二楼,窗户多不能打开,众多的格眼是给二楼透光的仅有通道,据说是因为祖宗不喜欢光线。[9]格子门可以拆卸,比如在“烧包节”当日,所有的“格子门”都要拆去,堂屋和天井只有门槛之隔,祭祀空间增大,主要的祭祀活动还是在堂屋内部举行。
祭祀主要由家里的主人——年长的父系继承人承担。一来表现白族对长辈的尊敬,特别是对男性长辈的尊敬;二来妇女大部分不识字,无法念经文,女性只能制作冥币、贡品、做酒席等。男性继承人每天早晨应问视灵位,焚香、鞠躬。他的妻子作为“主妇”则是所有复杂仪式中的伴礼者。而且,与丈夫一样,出入都要向祖先请示。每天,祖先都要接受家中主人的祭拜。全家人聚集在前厅,男人面东,女人朝西,按照辈分战成排。主人负责举动男性祖先的牌位,主妇负责将女性祖先的牌位从龛位中取出,把它们放在祭桌上享用供奉。家庭成员依次行礼供奉,主人和主妇行最后的跪拜礼。
祭坛位于家庭的中心位置,神龛作为祭坛的具化象征,表明了神龛是一个祭拜的地方。张烺光先生描述了大理的神龛,不论是穷人家还是富人家,他们的住宅内都有一个神龛。家中的神龛一般安放在西厢房里,并且总是安放在二楼中间的屋子里。神龛放在一张木制的台案上。祖先的姓名和亡故的年龄写在木制的牌位上。[10]P51白馥兰认为,祖先不再需要血食,供奉不再被理解成饥饿神灵的食物,而只是一种敬意的符号。对于高层次儒家来说,牌位不是死者神灵的居所,而是繁衍秩序的一种具体符号。[11]P79因此,当儿子离家建立独立的家庭时,他们要建立自己的新神龛。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食物和崇敬是分不开的。因此,灶在家庭中有着至高的地位。而且对于大部分来说,较之神龛,厨房才是住宅真正的中心。白族的灶神与汉族的比较相似,都是天帝派来的“家神”。灶君同祖先的地位一样,被供奉在祖坛附近。一般白族地区的二楼明间中间都供奉“天地国亲师位”,左边供奉祖先牌位,右边供奉“灶君神”位。也有的放在厨房里,通常由一福彩色的木版印刷画表示,张贴在厨房里,旁边是他的妻子,还有其他不同的人和动物形象。至今大理民间流行的经文可以说明灶君在白族地区拥有着广泛的信众。民间流传于灶君相关的经文涉及方方面面,作为符号的灶君逐渐成为家户的象征,甚至是一家的管理者和拯救者。[12]《灶王经》中有这样的语句:“一家之主你为大,一家之主你为尊……”可见,灶君的形象堪比一家之主,体现的是男性的权威乃上天秩序的组成部分,恶行将受到惩罚,带来厄运和短命。如果说祖先祭祀将中国的家庭系入一个更大的血缘群体中,它所促进的价值观念不可动摇,并且它的赏罚产生于内心:一个和谐家庭的心满意足或是良心不安的痛苦。那么灶神体现了家庭与外在世界的一种关系,即使它所促进的价值本质上是儒家式和家长制的,但并非将一个家庭纳入更广大的血缘群体,相反,灶神强调其独立性的意义:“独立的家庭决不与人分享同一个炉灶,甚至兄弟也是如此”[13]P87。
(三)内与外的分界:堂与房
人类最初的空间意识来源于对神圣空间和世俗空间的划分,而世俗空间的最早划分是以性别为依据的。划分的目的是要建立家庭和社会的秩序,特别是父权社会以来,男性在空间中所占的主导地位以空间的约定俗成而被强化。家居生活的内外之别,是自古中国传统住屋的一个必要区分。
男女各行其道,各司其职,内外分明,伦常行为才不至于混乱。许烺光先生通过对喜洲的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家庭中所有其他的亲属关系都可以看成是父子关系的延伸或补充。夫妻关系就只能是父子关系的补充,只能服从父子关系。在喜洲,男女有分床而睡的习俗。新婚夫妇只允许同床七日,七日之后,夫妻虽同房,但并不同床。在公众面前,夫妻之间显得很冷淡。且除了小孩和夫妻以外,男女均分室居住。这样的一些习俗在云南另一些少数民族中也是存在的。
内外的区分,其实也就是堂与房的区分。堂在外,房在内,《曲礼》说:“男在堂,女子在房”。堂属于外的范围,而女子的活动范围没有超过房室一线之外,即堂屋后楣四分之一的空间。这样一来,自然保证了男人的主导权与女人的从属权,同时也置女人于男人的监控之下以保证其对丈夫的忠贞。
门是内外分界的一个重要标志,司马光的《居家杂仪》中就规定:“八岁,女子不出中门。妇人无故不窥中门——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可见汉唐以来男女外内的主要分界线移到中门。在大理,坐月子的女人不能随便出入家中的大门,因为她“不干净”的身子可能冒犯护门神。如果必须出的话,必须带上一顶帽子。另外,有的民居大门外还增设小门,或临街或通向屋后的园子。临街小门有着特殊功能,按白族习俗凡再婚及非明媒正娶者无论出嫁、迎娶均从小门出入,不能通过正面的大门。
三、祖先庇荫下空间结构的意义解读
基于以上对大理白族传统房屋空间结构的描述,以下借用徐烺光先生提出的“权威”与“竞争”两个因素来分析空间结构的意义所在。也就是探讨造成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的原因为何,继而与祖先庇荫的观念模式相印证。徐烺光认为父亲权威越大,祭祀的祖先越久远,家庭观念越重,家族内关系越紧密。然而,竞争的意义却最大可能地破坏了宗族内的团结。这样带来的是分家的必然与维持一个宗族合而不分的困难。对获取权威的渴望,促使白族人不仅仅通过获得财富和权力来拥有权威,而且还通过修建宽大无用的住宅,拥有大片的墓地,以及展示祖先的荣耀来获得众人的尊敬。因此,服从父亲的权威和权威下的竞争,奠定了喜洲人基本个性结构的基础。两者并不冲突,相反,它们互相加强,互相融合。竞争的起点始于家庭内部,兄弟之间不是在各自的道路上奋斗,而是在家中争相获得父亲的恩宠。据此,许先生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结为六大类相对应的等级关系:长辈与晚辈之间、男性与女性之间、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家人与家人之间、大官与小官之间、官家学者与普通百姓文盲之间。
这六个等级可以归纳为三大类别:父子关系(辈分或年龄等级的中心)、男性与女性之间、富裕人家与贫穷人家之间。
那么,借助于对这三种关系的推演,我试着对相对应的空间结构意义做一个解析。
(一)父子关系:原家/分家
父子关系指的是不同辈分,或者不同年龄的其他人的地位或多或少是父子关系的变体。辈分高者代表了权威,而辈分较低者听从命令。在1949年前,大理普遍盛行复合型四代同堂或五代同堂大家庭。合院式的住宅完全满足了这种大家庭式的居住模式,而同时分家又是家庭再生产的基本方式。分家看似与传统文化伦理观念相背离,实则是稳固传统社会结构的一种重要机制。[14]P37在喜洲,大家庭分家之后,小家庭仍然共同住在同一住宅内,人们看见的是大家庭依然存在,小家庭有一定自由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体现在空间结构上便是:每个家庭建筑个体均需服从于宗族的系统。在基本均等的建筑单元空间中,日常生活以厅堂为中心,日用空间的秩序统合诸如祭祖、礼仪、重要的家庭活动等行为。厅堂的中心地位可以将每个家庭成员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作为一个特定的仪式空间,有着“上承先祖、下昭后人”明确的精神象征意义。在形式上,通过墙、庭院的规范,起到了制约内部空间的作用。进而规范地体现社会所强调的“家—族—社会”文化系统。而分家的形式在有的家庭当中是实行家屋穿插分配,正屋二楼一间、西南角正房、西厢房住一户;西耳房住一户;东南耳房住一户;东耳房住一户。祖上这样安排是为了防止外姓入内。按照许烺光先生的理论,分家可以消除导致家庭纠纷的重要因素,也可以使个人相互间的竞争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充分发挥,从而使家庭复合大家庭的理想,在社会意义和传统习俗上保持家庭的体系性。
(二)性别关系:婚出/婚入
在性别关系上,空间体现的是对女性很大程度上的压抑。和男性一样,她们必须服从父母、祖先和传统。然而不同于男性的是,她们还必须服从于丈夫和一些其他相关的男性。和男性一样,她们可以自由地表现出竞争欲,但不同的是,她们竞争的对象是丈夫的姬妾,或是丈夫兄弟的妻子。而就家屋的立场而言,婚姻根本是短暂的关系,是乱伦禁忌的限制下异性同胞关系的替代品。对家屋长远的生命来说,婚出者终究要回归原家,婚入者也终究不是本家的永久成员。家屋真正的成员,是埋在地下、栖在屋顶,世世代代的同胞(祖灵)。[15]P204因此,婚姻关系主要表达两个层面上:一是在家屋内/外,以及由门进入后的横轴结构上;二是各种建筑元素中两性的意涵都在个别家屋透过婚出同胞建立的原家/分家关系上被泯灭。
以上,父子关系是家庭的核心,父亲在家庭里始终保持最高权威,在对同一个祖先寻求庇佑和无法更好地维持大家庭秩序的矛盾上,产生了大理白族独特的分家方式。而分家总是伴随着婚姻关系进行的,对女性而言,很少有属于自己的空间,不管是婚出者还是婚入者,都不是真正的家庭永久成员。在家庭空间中,只有祖灵才是永久的主人。
(三)富裕与贫穷:形制/风水
富裕与贫穷在房屋形制上很容易得到辨识,贫穷的人家居住在寒酸的居室里,一般是平房,茅草为屋顶,没有庭院。整个住宅仅只有一排房屋,而且比庭院住宅的一排还小很多。这样的住宅十分简陋,墙壁甚至没有粉刷,更谈不上诗画装饰了,大门上没有匾额,家中也没有空余房间。整个住宅处处显现出生活的艰辛。富人的住宅通常都是有好几个院落,有二至三道门楼。大门尤其考究,做成三滴水的样式,十分繁复华丽。住宅的大门或中门上通常挂有一块或二块匾额。匾额上刻的是家族成员现在或过去获得的荣耀,获得荣誉者的姓名和获得荣誉的时间。外墙墙壁和内墙墙壁都题有诗画,非常雅致动人。除了围墙以外,院内大门正对的地方还有一堵照壁,在一户住宅里,这样的照壁有两三堵。照壁上题字表明是书香门第。
除了房屋本身的形制竞争以外,最大的竞争还来自于风水的竞争。风水用于确定住宅修建的地点,墓地的选择,墓穴的位置。它被用于选择死人或活人的的居住地。因此,同一宗族内部为直系祖先争夺一块风水好的位置所进行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不论是形制上的还是风水上的竞争,都透露出对祖先庇荫的愿望。不管是阳宅也好,阴宅也罢,都是激烈竞争的代表物。
四、小结
综上,对大理传统房屋空间结构的考察离不开祖先庇荫的观念影响,个人的价值和命运不仅与祖先的命运紧密相连,而且被看成是祖先所作所为的反映。房屋的形制与空间格局可以说是被父权密码所操控,父与子的关系是家庭中最核心的关系,伦理意识在平面布局和房屋体量上表现得较为突出。许烺光先生的《祖荫下》帮助我们加深了对这一点的认知,许先生把大理喜洲镇人们的一切活动置于祖先庇佑之下进行考察,旨在寻找一种基本个性结构与普同的文化模式。借鉴许先生的民族志结论对于了解大理白族传统家屋的布局结构是很有裨益的,可以发现存在于空间安置背后的观念系统,且在“权威/竞争”双重视角下认识空间结构的意义所在,是值得去体味的。
注 释:
①庇荫一词是比喻用法,在徐烺光的书中意指,个人离开了祖先是不能够生存的。他的价值和命运不仅与祖先的命运紧密相连,而且被看成是祖先所作所为的反映。从这个角度来说,任何人可以说是祖先的庇荫下生存的。
②中堂,是白族人自己的称呼。三个堂屋中的柜子将堂屋的空间分为三个部分,中间的墙壁和柜子以上的部分构成了这个空间就是所谓的“中堂”,是堂屋的中心位置。“禄寿”像,两边两幅长2 ×0.3m 的对联。中堂刺绣挂像一般是建房时,媳妇的娘家人当贺礼送来的。
③隔扇门由外框、隔扇心、裙板及绦环板组成。外框是隔扇的骨架,隔扇心是安装于外框上部的形屉,裙板是安装在外框下部的隔板,绦环板是安装在相邻两根抹头之间的小块隔板。
[1][8][11][13][美]白馥兰. 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利经纬[M].江湄,邓京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2]郑春.《朱子》家礼与人文关怀[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
[3][5][6][7][10]许烺光. 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M]. 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2001.
[4]吴正旺,关瑞明.天井与院落[J]. 福建建筑,2000,(4).
[9]黄雪梅. 云南大理白族祖先崇拜中的孝道化育机制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08.
[12]张海超. 建筑、空间与神圣领域的营建——大理白族住屋的人类学考察[J].云南社会科学,2009,(3).
[14]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15]黄应贵. 空间、力与社会[M]. 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