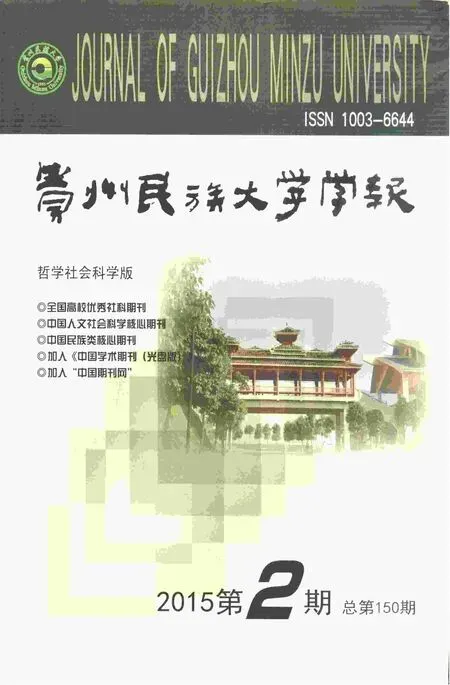梵净山域外形象论略
——基于英美主流媒体的解读①
2015-03-20刘振宁
刘振宁
(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梵净山本真形象述略
梵净山得名于“梵天净土”,被尊为“武陵正源,名山之宗”。又因“集黄山之奇,峨眉之秀,华山之险,泰山之雄”,有“崔嵬不减五岳,灵异足播千秋”的气势,而享有“天下众名岳之宗”的美誉。
梵净山是较为完整的物种“基因库”,生物多样性主要体现在基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多样性上。梵净山以其山势高峻,山体庞大,沟谷深邃,瀑流跌宕,林木郁苍而成为了世界上少有的亚热带原生生态系统地标,成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立的国际“人与生物圈保护网”(MAB,1986)成员,成为了“地球和人类之宝”。据科学考察数据显示,梵净山有生物种类多达2601 种,其中植物1800 种,动物801 种。植物中有17 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植物,动物中有19 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其中尤以“世界独生子”、“国宝”级的黔金丝猴和“北温带最美丽的花朵”的珙桐最具代表性。
梵净山也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最多的区域之一,是民族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的典型地带。梵净山位处“武陵五溪腹地,是古代‘武陵蛮’、‘五溪蛮’的世居之地,梵净山周围地区至今有28个少数民族居住,少数民族人口占铜仁地区总人口68.40%,其中土家、苗、侗、仡佬是该地区人口最多的四个少数民族。”[1]
较之前两项美名,梵净山更为世人称道的,是其作为贵州第一佛教名山和全国名山中惟一的弥勒菩萨道场所深蕴的文化根蒂。这座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山,“是佛教名山,其人文景观资源最具有地方特色的当是佛教文化,而佛教文化中则又以‘弥勒菩萨道场’最具有震慑力和感召力。”[2]
总括而论,贵州佛教法脉启于宋代,兴于明代,承于四川禅学,以山林佛教为特点,兼具自然风景之体和人文历史之魂。“从宋代建造西岩寺开始,梵净山从此有了佛教香火,成为‘古佛道场’,并被赋予了多种佛教内涵,前后进行了六次毁坍再建的过程,形成了‘一大正殿、四大皇庵’和‘四十八大脚庵’、环山四大古寺的繁荣景象。”[3]
据宋书《太平寰宇记》载,梵净山宋时名称“思邛山”,因唐“思邛县”而得名,佛教于此时传入。明初,梵净山已是佛教名山,同有数名并称,如“九龙山”、“饭甑山”、“梵净山”、“大佛山”、“大灵山”等。
考究梵净山得名之根源,主要涉及如下两种传说:一是源于饭甑山之形。《铜仁府志》有载,梵净山群峰耸峙,分为九支,中涌一峰,“山形上大下小,若釜甑然,俗名饭甑山,当亦缘此。”[4]P17循此推知,梵净山主峰金顶因形似饭甑,而“饭甑”与“梵净”音近,故相沿讹称“梵净山”;二是源于“梵天净土”之质。因明代该山梵宇遍布,寺刹林立,佛教兴盛,成一方名胜,俨然梵天净土般神圣,故将此山尊称为“梵净山”。“梵天”指一种超越时空、超越生死的涅槃寂静境界。质言之,“色界之初禅天也,此天离欲界之淫欲,寂静清净,谓之梵天”。[5]P238“净土”也称“净刹”、“净界”、“净国”、“佛国”,在佛教中指没有尘世庸俗气的清净世界或极乐世界,即“无五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垢染的清净世界,大乘佛教传说佛所居住的世界,与世俗众生居住的世间所谓‘秽土’、‘秽国’相对。’”[6]P399-400显然,梵天净土乃是一譬喻,蕴含着芸芸众生对极乐佛国人间净土的向往。
所谓“道场”,源自印度佛教之“菩提道场”,原指佛陀在菩提树下成道时所坐的金刚座处,后来引申为修行佛法所在的地方。弥勒道场,即指受到民间普遍信奉的未来佛弥勒菩萨修行或化现的场所。据《敕赐梵净山重建金顶序碑》称,“黔中之胜地有古佛道场名曰梵净山者,则又天下众名岳之宗也!旧说者以弥勒、释迦二祖分管世界,用金刀劈破红云金顶,于是一山分为二山。”[7]左属释迦,右归弥勒,释迦、弥勒二殿并立“红云金顶”之上。当然,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之说,更多源自民间传说,而且从宗教意义上讲,自有其“象征”价值和语意建构作用。就此,王路平先生曾作如是评说,“这种说法并没有知识学的史实根据,但却有宗教上的价值作用。”[8]毋庸讳言,这种现象不惟梵净山如是,纵观国内四大佛教名山的道场缘起,均可得到印证。
早在万历年间,梵净山就以其古佛道场和奇峰绝景而名震四方,被纷纷冠以“古迹名山”或“西南名岳”等美名。用时任贵州巡抚郭子章所撰《黔记》中的话说,“贵州山以梵净山为第一,可比天台。”[9]著者将梵净山与佛教天台宗祖庭天台山相比,梵净山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就礼佛盛况言,《敕赐碑》铭文有云,“自开辟迄今,海内信奉而奔趋,不啻若云而若水;王公大人之钦谒,恒见月盛而日新”。[10]到了清代,梵净山虽屡遭劫难,但亦劫后中兴,成林寺庙继续使佛名远播,香火鼎盛,朝山信徒如云流水涌。清光绪年间立的《下茶殿碑》有载,“数百年进香男妇,时往时来,若城市然”。
目前,梵净山更以其别具一格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并伴随着旅游的开发,而受到更多世人的钟爱,不仅香客争相朝觐,而且游客络绎不绝。
总之,梵净山既有绝美的自然风景,也有壮美的遗迹风景,身为“天下众名岳”的它,以其净秀巍峨的地象,以其灵异怪谲的物象,特别是以其延绵浑厚的佛教资源和文化遗迹,而令世人赞叹,成为了闻名遐迩的梵天佛国和人间圣地。诚如黄夏年先生所言:“梵净山是集生态与人文一起的名山,生态是它的魂魄所在,缺少了生态,没有山清水秀,就不会有梵净山的生命,也不会以其特有的姿态而卓立群峦。佛教是梵净山的文脉,它自传入之后,始终不弃不离,困境中不倒,顺境中大发,屡毁屡建”。[11]
梵净山域外形象窥要
既然位处边陲的梵净山,依凭其群峰竟秀,溪壑纡曲的雄、奇、险、秀、古的自然风貌和净土道场的美名,早在明清两代香火盛极一时,享誉天下。清代学者张澍曾如此惊叹道,“疑此山不独铜仁之壮观,且为全黔之胜槩也”,“匡庐武夷之胜,天台雁荡之奇,亡呂逾也。”[12]P580那么,如此闻名遐迩的佛教圣地、民族乐园、生态王国、旅游天堂,在资讯如此发达的当下,理应会引起域外媒体的极大关注,并由此产生巨大的影响,形成极佳的形象。
按照法国比较文学家巴柔的定义,“形象”是“社会集体想象物(l’imaginaire social)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对他者的描述(la representation de l’Autre)。”[13]P137因此,不管是描述的过程还是生成的形象,都始终渗透着描述者或形象塑造者文化的和情感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始终承载着一种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并由此表达了存在于两种不同的文化现实间能够说明符指关系的差距。换言之,一切形象都“投射出了形象塑造者自身的影子,是后者空间的补充和延长,因而形象这种语言主要言说的就是‘自我’。”[14]P4
那么,在域外尤其是英美主流媒体的视阈中,在西方特别是英美国人的心田中,梵净山是否同样是一块人与生物圈保护的神圣净土?是否同样是一座位尊黔境比肩五岳的弥勒道场?是否同样是一方凌空据险的洞天佛地?是否同样具有一种佛道儒巫多元共振的文化气象?是否同样是一处人天共仰的旅游胜地?然而,基于英美主流媒体的具象性信息采集显示,在域外媒体和大众眼中,梵净山至今依然是一个未知的符号,一方尚未进入绝大多数西方人心田的陌生之地。
为了较为全面地理解域外梵净山的相关信息,笔者设置了Mt. Fanjing,Mount Fanjing,Fanjingshan 和Fanjing Mountain 四个关键词,择取了英美数个较具权威且拥有较大读者群的媒体,通过逐个打开各个媒体电子网站窗口,逐一输入上述关键词检索,以期对梵净山的各种信息进行全方位的搜集。
就英国权威媒体而言,无论是被誉为“英国社会的忠实记录者”且为英国第一主流大报的《泰晤士报》(The Times),还是作为英国最大新闻广播机构的《英国广播公司》(BBC),迄今竟然只字未刊(播)有关“梵净山”的新闻报道。而号称世界前三大多媒体新闻通讯社的《路透通讯社》(Reuters),自2012年8月1日刊发了首篇题为“铜仁梵净山投资公司”的资讯以来,截至2014年2月20日,共有7 篇同质性经济类短讯,且均出现在该报“中国企业债发行日程表”栏目下。据此可见,尽管上述资讯都冠有梵净山名号,但与其文化生态毫不相干。
与此相似,美国主流媒体中有关梵净山的信息也少之又少。通览《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时代周刊》(Time)、《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基督教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以及《美国之音》(VOA)等主媒网站,梵净山的讯息少得令人难以想象。唯有《华尔街时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从经济的视角对事关梵净山(或涉及梵净山名称)的两起新闻事件给予了关注,那就是2010年9月15日在梵净山景区召开的“第五届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和2012年8月“铜仁市梵净山投资公司”发行人民币12 亿元企业债新闻。
与此形成较大反差的是,英美学者对梵净山生物多样性尤其是山中金丝猴的关注热情,远远超过了新闻媒介。
梵净山域外形象生成根由省思
由是观之,梵净山在英美主流媒体的视阈中,在域外大众的心理认知里,总体上呈现出了一种阙如情状,仅有的一些碎片式印记也主要集中于些许学者对其科学研究价值的关注方面。既然任何形象都是一个自我与他者双重推动、相互建构的结果,那么梵净山域外形象生成根由,大体上可分为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两种。究其内因而言,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管理者对梵净山自我形象打造尚存不足。对此,王路平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梵净山的知名度与当前开发的规模和成效并不相称,离第五大佛教名山之称谓尚有一定距离,这其中包括了多方面的原因,如学术上对梵净山佛教文化的深入研究不够;山中各寺庙分布较广,属地管理不一,各自为主;现有的旅游基础设施及相关配套设施较差;缺少佛教名山文化旅游氛围的营造;作为佛教文化圣地的弥勒菩萨道场的品牌内涵和核心价值彰显不充分;地形地貌复杂,交通不方便等等”[15]P18;二是媒体和文化传播公司对外宣传力度不够,过去主要聚焦于梵净山外在自然风情和潜在经济价值,既忽略了对其进行一种立体式包装,也忽视了其宏富的多维价值(包括独特岩洞地质特征、生物多样性价值、多民族和谐共荣学理、禅静合一地域现象、生态文明建构作用等)进行深度开掘和前瞻性研究。
至于在资讯发达的当今时代梵净山依然“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外在原因,主要在于缺乏国内相关信息的有效译介,从而使梵净山的独特价值与独特形象尚未进入域外媒体的“期待视野”中,更未能与域外读者、学者、观光者的期待视野彼此“融合”。唯有通过国内各种媒介的广泛推介,使梵净山相关的各种信息不断走出被隐蔽的真空状态,不断引起域外媒体的关注激情,不断唤起域外读者的心理期待,域外媒体对梵净山的关切兴趣方能日益增长,梵净山域外真实形象的构建才有可能实现。
既然一切形象不仅投射出了形象塑造者自身的影子,而且主要言说的是“自我”,那么,鉴于梵净山当下域外的形象情状,国内相关媒介(特别是梵净山自然生态、佛教文化、旅游管理机构)、学界及文化推介会,应责无旁贷地在对其形象进行立体式打造和进一步升级的同时,有意识地加大梵净山外在特征与内在价值的发掘和研究,进而加强对各种信息的输出和译介力度。与此同时,还需通过各种途径,助推域外媒体对梵净山相关信息的全面输入和吸纳,由此方有可能构建起一个相对完整真实可靠的域外梵净山形象。
[1]张明.梵净山佛教文化与生态保护探析[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
[2][8]王路平,释行愿. 论贵州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
[3][11]黄夏年. 黔贵佛教僧人与生态——兼谈梵净山的魂与脉[A].2013 中国梵净山生态文明与佛教文化论坛论文汇编[C]. 2013.
[4]中共贵州省铜仁地委办公室档案室、铜仁地区志编辑室整理.铜仁府志(民国缩印本)[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
[5]丁福保. 佛学小辞典[M]. 上海:上海医学书局,1938.
[6]任继愈.宗教大辞典[C].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
[7][9][10]张明. 梵净山弥勒道场《敕赐碑》研究[J].世界宗教研究,2012,(4).
[12]张澍撰.续黔书. 贵州府县志辑(3)[M]. 成都:巴蜀书社,2006.
[13]Daniel- Henri Pageaux. De L'imagerie Culturelle à L'imaginaire,Precis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Brunel,Pierre et Yves Chevrel ed.). 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89 .
[14]孟华. 形象学研究要注重总体性和综合性[A].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C].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15]王路平等. 装点关山:梵净山佛教文化旅游的开发研究[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