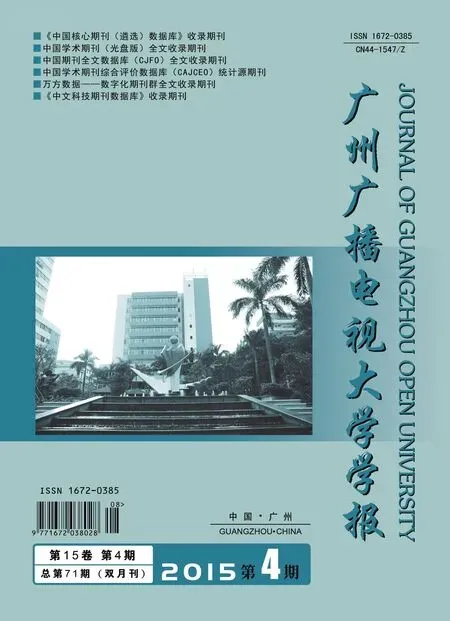灰烬的余温——路翎晚年诗歌与创作心理研究
2015-03-20彭凯
摘 要:长期以来,对于晚年路翎的创作研究都框限和遮蔽在“精神分裂”、“艺术生命枯竭”的话语模式之下,使得晚年路翎创作不管在文学批评,还是在其自身的艺术评介中都处于一种“缺席”的状态。本文通过对晚年路翎诗歌的具体分析以及对其创作心理的考察,反拨了典型的“路翎叙述”,并做了重新的文学界定。
收稿日期:2015-06-08
作者简介:彭凯,男,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
早在80年代初,钱理群先生就针对路翎(1923—1994)文学研究的盲视、冷落发出“这是一个早被遗忘、却不应被遗忘的名字”的呼吁。当时话语旨义的背后,路翎依旧被定义为弱冠之年就创作出誉为“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的《财主的儿女们》这部皇皇巨著的天才。那么,面对诗歌、散文、小说和回忆录等创作贯穿整个80年代以至90年代初,总字数不低于五百五十万字的晚年路翎,“不该遗忘”的声音是否仍存有不容置疑的意义?
一
路翎晚年的大部分创作都未能得到刊行,少数发表的作品散落在不同的报刊里显得寥落而凡常。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些创作即便放在路翎自己的文学生涯里也是无足轻重的,遑论进入本来就已经充满转型、裂变的“新时期文学”的文学史书写。在以往众多的“路翎叙述”中,其实已经形成了某种讳莫如深的定论,而此般典型“叙述”的“始作俑者”来自于冀汸先生的“一生两世”论:“1955年那场‘非人化的灾难’,将你一个人变成一生两世:第一个路翎虽然只活了三十二岁(1923—1955),却有十五年的艺术生命,是一位挺拔英俊才华超群的作家;第二个路翎尽管活了三十九岁(1955—1994),但艺术生命已消磨殆尽,几近于零,是一位衰弱苍老神情恍惚的精神分裂者。” [1]冀汸先生的论断当然不是空穴来风。1955年5 月16日,即《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一批材料》公布后的第三天,路翎被隔离审查,几天后被移至另一处关押。在狱中,隔墙的难友们“常常听到路翎在房间里困兽一般发出几声叫声,或者无可奈何的叹息声” [2],“经常大声吼叫,立即被制止,鸦雀无声,不久复大声吼叫,骂人,他已经精神失常” [3]。到了1961年7月,路翎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每天打针、吃药、电疗。甚至冤案平反后,路翎精神失常的“事实”依然可以从朋友、家人、同事的口中窥见一斑,“路翎听了,忽然撇下我,一个人冲到屋子外面,就在院子里向天大声嚎叫,发出的声音好像受伤的野兽的哀嚎,恐怖、凄厉,惨伤里夹着愤怒和悲哀……” [4]。如果说,冀汸先生是依据创作主体是否具有艺术想象与逻辑思维能力的维度否定了路翎晚年的文学生命的话,那么钱理群先生则从写作本身对其做出了盖棺之论:“怀着巨大的恐怖(那是千百次施虐的审讯造成的永远不能摆脱的恐惧),手不由己地按照那个‘时代’的命令写作,除了‘遵命’(那也是那个‘时代’千百次强迫灌输给包括路翎在内的每个中国作家的)以外,他已经不会写作!” [5]也就是说,路翎已经被改造得彻底而驯服,他的写作思维僵化地停在“文革”的标准模式中跳不出来,而 “新时期”早已宣布这种模式的失效和死亡。
以上的两种论述方式,基本上遵循了“时代灾难——个人悲剧”的理路,不同的是一个强调灾难对于个体精神的打击与扭异,一个侧重于灾难对于个体创作的改造与驯化。这里面暗藏着一个隐秘的话语逻辑,那就是灾难在个体身上产生的后果越严重,就越能证明灾难的惨绝人寰。因此,也就不难想象那些陆续去看望路翎的同样身遭缧绁的旧友都不约而同地强调灾难前后的两个路翎的霄壤之别:“在他身上,已经很难想象当年英俊的身影。更使我感叹的是他的精神状态,显得冷漠、迟钝、健忘……他还能写作么?坐在他面前,我不禁这样悲痛地怀疑。我为这样一个有着惊人才华,而且曾经是那样勤奋努力的作家惋惜。” [6]通过对一个个体的悲剧见证,从而唤起和达到对“时代灾难”的控诉、批判、反思。当这种叙述模式的目的性凌驾于生存经验之上而逐渐演变成一种固化的认知倾向时,就必然导致更多滋生的复杂事实被忽视,甚至产生被裹挟的巨大危险,所做出的解释也必将存在着偏颇。1998年3月《路翎晚年作品集》的出版,似乎也有意识地抵抗着“路翎叙述”的偏狭与粗泛,为我们重新评介一位精神界斗士的晚年艺术形象提供了广阔而纵深的视阈。由此,反观冀汸先生的表述,虽然他谈到对晚年路翎未刊稿的“失望”,但并没有撇开情感的巨大落差,对其进行冷静地艺术分析,而是在“第一个路翎”挺拔的身影下,“简单而不情愿(不甘心)地将导致变化的原因归结为‘非人化的灾难’之下的‘精神分裂’,以至于事实上拒绝了对晚年路翎所拥有的内心情感和精神逻辑的深入了解和思考”。 [7]“第二个路翎”无论以何种形象,只要不足以与之前相匹配或者在某个层面上相延续,都可能会遭致本能的不接受。即便艺术与精神病症的线性因果关系能够成立,那么当“精神分裂”本身或许只是含混其词的妄作之论,路翎的创作心理依然具有明确的意义逻辑时,那么,这种结论极有可能是虚妄的。
因而,当我们试图在恢复和尊重个人心理与社会环境的复杂性的基础上,对路翎晚年的创作心理和诗歌文本做出理性的分析时,就不得不面对和解决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一、路翎真的是精神分裂而使得艺术生命“几近于零”吗?二、路翎真的被“彻底改造”而只剩下生命的躯壳了吗?否则,也就在更深层次上偷换了文学评判的尺度乃至消解了创作的基点。
二
路翎很小就体验过家人失业、社会动荡、战争侵扰所带来的恐慌。在1941年2月27日写给胡风的信中提到:“在我小学的时候,我就有绰号叫‘拖油瓶’,我的童年是在压抑、神经质、对世界不可理解的爱与憎恨中度过的,匆匆度过的。我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很早熟,悲哀是那么不可分解地压在我的少年时代,压着我的恋爱,我现在二十岁。” [8]不断的飘离与压抑使得他的性格显得躁厉而耿介:十五岁时,就敢于在中学课堂与校长公开进行关于屠格列夫作品的辩论;当廖承志出于好意,让他把剧本“改成‘大罢工’的历史剧,以避难关” 时,他的回答是:“‘二七’的时代和我有距离,感触不到具体的东西”。所以,三十刚出头的路翎被收押入监时,这个提倡“原始强力”,重视在沉重的心理创伤的层面上,通过残酷决斗,引发精神再生的希望的年轻作家并不像深陷牢狱之灾的绿原等其他人寻找事情以填满时间的空白或内心的仓惶,而只能是“每天二十四小时,除了睡眠、吃饭、大小便之外,其余时间都侧耳可闻他(路翎)一直不停的、频率不变的长嚎;那是一种含蓄着无限悲愤的无言的嚎叫,乍听令人心惊胆颤,听久了则让人几乎变成石头。” [9]这是精神分裂吗?或许还不能妄下断语。路翎未刊散文《喷水与喷烟》对其在狱中的生活有这样的描述:
我在这监狱中维持着我度岁月的方法:每日回忆往事,其余的时间我便对我判为反革命的,伤害、侮辱我的人们和形势进行抗议,我的抗议活动有说道理,叫骂,包括大声唱歌。
在他的陈述里,那些被旁人指认为“精神分裂”症状的“长嚎”、“叫骂”都是有意识地“反抗”行为,异常的举动则是释放内心冤屈与愤怒的不得已的选择。而在“监狱”封闭的空间里,路翎并没有被自己的“疯狂”的力量完全占据,而是“理性”地思索着,“荒凉的痛楚的感觉中也想到,中国似乎在沉静地发展”。他仍然在“分裂”之外,为自己的思想与行为赋予一种并不能简单定义为“疯狂”的逻辑。
重回人间的路翎,已经年过半百。二十年南冠之灾,磨蚀了他的风华,收敛了他的锋芒,他变得迟钝、呆滞、沉默,“从没有玻璃的小窗口凝望着灰蒙蒙的天空,一坐就是一天:什么话也不说,当然更是什么字也不写了” [10]。这一颗受难者的灵魂按捺住往日岁月中内心不断涌起的风暴,平息了狂躁、愤怒、不甘,走向了平静,像一座火山一样冷却、死寂。这不是从“精神分裂”(疯狂)走向另一种“精神分裂”(沉默),而是历尽劫波后,路翎重新选择的生存方式和生命依据,从一种激流中搏斗的“原始强力”化为入海般的沉静。所以,晚年的路翎“眼睛望着夜晚深沉的天空,看着月亮的移动,浮云的飘散、聚合……透过小小窗口展现的天空想着许多许多的事情” [11],“总爱长久地站在阳台上思索眺望。直至病故的前一天,九四年农历大年初二的清晨,他还曾推窗伫立,一任思绪飞舞,溶入漫天的一片洁白” [12]。静谧的心境酝酿出的诗情升华为一首首平淡而清凉的诗歌跃然于纸上。当我们从这些诗篇中窥视到一位年少躁厉的老人在囹圄之后所选择依据的生命世界时,是不能不为之动容的。正如化铁所言:“我准确地相信:那冷漠后面,有一颗坚定清醒的心。” [13]
1981年第10期,《诗刊》发表了路翎晚年的《诗三首》,曾卓先生即以诗人的敏感对路翎的诗歌以及其创作能力不吝赞美之词:“这里没有任何伤感,他歌唱的是今天的生活。这里没有任何矫揉造作,他朴实地歌唱着在生活中的感受。这里没有感情上的浮夸,他的歌声是真挚的、诚恳的。” [14]《果树林中》展开的是平凡的生活场景,夏季浓郁芳香的果树林中,“老年夫妇”、“壮年夫妇”、“年轻夫妇”劳作之中流露出单纯的愉悦,以及少年们那青春活力的风貌。《刚考取小学一年级的女学生》则把一个小学生的欢快和忙碌通过诗歌的形式刻画的惟妙惟肖。曾卓先生说:“能够将平凡的生活提升到诗的境界,这是需要敏锐的感受力和高度的表现力……情绪的节奏融合在生活的节奏中间——这是诗的本质要求,诗的本质的体现。”这不单单是对于路翎灾难过后才华“恢复”的欣慰和激动,更重要的是对路翎创作方式以及背后的生命形式的认可和称道,那就是将遭受的深沉的痛苦砥砺成日常生活的希望。一个“精神分裂”患者是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做出改变,选择一种与之前截然不同的心态,并成为其创作的稳定心理,不论他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诗歌的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明显的情感轨迹,而且能够在“高于生活”的层面上自由思考,难道还有人疑问这不是一种有效的表达吗?在1982年所写的未刊诗稿《槐树落花》中,用清新、细腻的笔触回忆了1975至1979年当扫地工的琐碎生活:
暮春,/扫地工在胡同转角的角落,/吸一枝烟,/坐在石头上,/或者,/靠在大树上:槐树落花满胡同。
扫地工推着铁的独轮车,/黎明以前黑暗中的铁轮/震响,/传得很远,/宁静中弥满/整个胡同。
漫长的、苦涩的生活在诗人的关照下有了动人、罕见的意境,没有痛苦、愤懑、哀怨,洋溢在诗篇中的是一种巨大的宁静与清新。“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诗意” [15],朴素而渺远、平和而旷谧,真挚而明亮。路翎的诗句超越了平常的伤痕记忆,似乎抵达了形而上的,更高意义上的存在。“胡同”这个诗歌文本空间已经不再是诗人曾经打扫过的记忆空间,而升华为不受限制的思维空间,在其中,所有一切都指向生命最本真的形态。不妨较之同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似乎到处还到处弥漫着血泪控诉的声音以及情感的浮夸与变形,喧哗中几乎失去了自我的方向。路翎未被纳入此时的文学潮流,但又何尝不是幸事呢?因为从他的创作中,同时还可以看到“文学史叙述”的偏见和盲视。
三
可能以上的论述会让大家进入一个认识误区,那就是晚年路翎的内心世界业已将过去所遭遇生命跌宕、恐怖经验、艺术理想放置在他自己都不能觉察和感受的区域里,只剩下再也击不起涟漪的一汪静水,除了沉寂,没有一丝尖锐的异质的力量活跃和涌动。论及路翎从年轻时耿介的不肯屈服的本性,到入狱后的一系列非正常的行为,直至平反后的沉默,是为了解决一个论述起点的问题。也即是说,路翎的诗歌创作最后从“宁静”这一角度的出发,是主动的心理选择,是一种非“精神分裂”的逻辑转变。只有这个论述起点成立,才能抛开以往典型的“路翎”论述(冀汸)中关于“第二个路翎”没有摆脱“精神分裂”而变得“衰弱苍老神情恍惚”,以至其创作“都只是火星一闪,并没有燃烧起来……” [16]的定见,对路翎晚年的复杂精神和诗歌文本进行重新的把握和分析。如果路翎只是停留在心态的调整以及在此范围内的诗歌写作,那么仅仅能够说明他“恢复”了写作能力,能在另一个层面上进行文学创造,但并不足以显影其成就。那么,路翎在诗歌中是否还试图表达一些现实经验之外的其他东西呢?
牛汉先生曾用诗歌记录了路翎在阳光下面行走的姿态:“三伏天的晌午/路翎独自在阳光下行走//他避开所有阴影/连草帽都不戴//他不认路早已忘记了路/只认得记忆中的阳光//他的性格孤僻的女儿/远远地跟在他的身后” [17]。路翎似乎在寻找着什么,他的内心并没有被燃烧成一片冷灰,潜藏的艺术激情仍然以某种特殊的方式鼓荡着。正如张新颖论述道:“这种对平常日子‘阳光’非同寻常的‘固执’和‘焦渴’,其实可以看作一种心理精神状态的隐喻。” [18]那到底隐喻着什么呢?或许在他的诗歌中可以找到答案。
《在池塘边上》对于历史的表达则是令人战栗的:
池塘深底里有旧时候的倾诉上浮,/池塘闪光荡漾着/各时候捣衣、洗米的勤勉的农妇的影子,/以及/愤激的殉难者……
那些动荡不安的心灵惊悸被活生生地按在了水下,而当时间再也包裹不了这些携沙带泥的痛楚与死亡时,一个安静的池塘里,诗人看到了或轻或重的记忆被重新唤醒以及历史与现实的声音沉闷的咆哮。“农妇”与“殉难者”极其悖谬地重叠在“池塘”这个平常的空间里,但历史的悲剧不正是这样的吗?
《井底蛙》写青蛙跳出井里,跳到山腰上,“这时候一片树叶落在它的头上,/像受惊的麋鹿有一回被树叶击中而逃亡一样;/青蛙便说天掉下来了,/拼命蹦跳逃亡……”,但它没有放弃广阔的天地,第二次从井里跳出来,雷霆与黑云在张牙舞爪,“于是对着暴雨和塌下来的天,/青蛙鼓勇地鸣叫……但是雷雨未停青蛙惊惶而跳回井里去了,/又有几片叶子掉在它头上,/它想继续奋斗没有必要;/它仍然决定坐在井里,/他还决定忘却、取消它的奋斗的阅历,/而重新说,天只有井口那么大。”这里叙述的正是历史不断翻滚所施加在个体身上的恐怖经验,其脆弱神经对外界的惊怪乃至最后对自我的取消,是历史中个体的宿命。诗人敢于在内心承担这些惨烈,没有张惶和躲避,这难道是一个被彻底“改造”的灵魂吗?他的内心世界浮泛着从阴影中走出来的冰与火碰撞出的棱石,在时间的打磨中仍然保持着锐角,痛苦中总在试图诉说着一些与历史讲述并不一致的经验:“当年的战争的呐喊,/炮声,和枪击声,和人声,马蹄/奔跑的影像,/浓烟中急促、沉重、死亡、胜利、勇敢、激昂的/动作,/在各年的雪里沉默的蓄存;/它将长蓄存,/声音与影像——/当年曾击溃旧时代的黑暗的奴役者……落下来的雪是思恋的烟与火变化的,/人们心中有很多的,/思念的烟与火;/落下来的雪是内心的揉搓的云,/人们心中揉搓着感情的云。”(《落雪》)在大雪将要把过去的声音、影像、痕迹深深覆盖,换来洁净的白茫茫一片时,诗人的眼耳中不断闪现那些无法过滤掉的信息:急促的枪炮声、狰狞的动作以及死亡者的碑石。压抑在潜意识中的创伤记忆不断涌向心灵难以弥合的裂隙,最终在诗句里得以抚慰。
路翎在部分诗作中对于心理奇特体验的捕捉也是敏锐而精准的。这些隐蔽内容在现实与幻觉之间游移、交错和扩充,获得了巨大的意义生长的空间:
半圆的月亮,/在朦胧的晦暗的云和晕光圈之中/在大的烟囱之旁。/星斗照耀着;/星斗闪烁像是要飞翔起来。
白色的灿烂地亮着的街灯,/整齐地排列着几十只,/像是巡逻兵;/刺目的亮光像是要飞翔起来。
楼窗里灯火通明,/极其轻盈地震响着。/窗户外看见里面上楼的人急跑,/奔跑者到了杨树顶端的窗户;/顶端的窗户亮着像是要飞翔起来……
现实物象所传达的微妙感觉,在介乎实与虚的临界位置,变得梦幻、缥缈。外在的世界随着诗人的内心不断运转,“飞翔”不再是一个实在的动词,而是生命由内而外的渴求的状态。正如李辉所言:“在灵魂经历了痛苦折磨之后,在精神仍不时笼罩着分裂状态阴影的时候,他似乎更适合于把握诗的形式。” [19]当诗歌不依赖于“思想”,而把“感觉”作为诗的内核时,诗歌也就在空间上得到释放。
而最能代表路翎晚年诗歌创作成就的是长诗《旅行者》、组诗《在阳台上》以及《诗七首》。《旅行者》长达六百行,在87年初稿完成之后,一直反复修改,且可能直至临终都不认为自己已将它改定了。因此,从作者角度出发,诗歌一定具有明确且从一而终的表意目的,否则“反复修改”势必会使诗歌文本空间里的意义传达,在时间的错置中被弱化乃至销蚀殆尽(92年仍有改动笔记),而其承载的极为广阔的思想容量则始终处于不断蕃衍的未尽状态。全诗以“旅行者”的口吻进行叙述,在记忆与现实的夹缝中穿行,过去的苦痛、压迫、令人窒息的黑暗联琯着新时代的希望、繁荣和乐观。诗人试图藏匿在叙述的背后,在第三人称的掩盖下,冷静而克制地言说民族与个人既往创伤经验。但个体在历史中所承担的复杂而深切的记忆似乎难以在“他者”这一视角的转述中变得从容,反而暗自显示出压抑着的欲要突破言语限制的激情。因此,在诗歌的第三节,诗人突然将“叙述者”转变为“我”(这种转变与其说是诗人有意为之,不如说是诗歌的内在要求),历史经验也就在个体性经验中得到了统一和指认:“高耸着的是心灵的渴望/心脏是血液盈满穿着多层火焰衣服的火焰,/我探索和意识和敏感和看见和触摸到历史……”,“我于是从心脏里极深地和黑暗的地狱结成仇恨,/仇恨——刀子是总在我的身边/而有对于黑暗的知识。”视角的突变并没有带来文本结构的断裂以及叙述的歧变,反而使诗歌能指空间依凭主观情感的强烈介入而获得突围和升华。如果说诗歌前半部分是通过理智、清醒的话语指涉“民族的公共经验”,那么后半部分则是在被言说的“历史”之外竭力向意识的深层突进,将“个体性经验”的隐蔽内容放置在时空与意义的交织与矛盾中,使两种不同的“经验”指向于历史的层面都获得表述的可能。
当然,正如某些评论者所注意到的,晚年路翎的诗歌反复出现的一个词,或者说象征载体,就是——“心脏”。组诗《在阳台上》以“阳台”这样一个看似与外界相联系(阳台置于开放的空间),但又不完全自由的场地(阳台的开放只是相对的)为依托,观涉社会各个行业的二十种不同人物,包括女歌唱家、京剧女演员、青年工程师、女诗人等等。几乎每一首诗都有“心脏”这个意象,“美丽的头发的甜蜜渗透到心脏”(《京剧女演员》)、“心脏出血、出血。警号、警号”(《成功的医生》)、“夜间的睡眠里有心脏的那时的痛苦的战栗形成的恶梦”(《经过了患难》)。毫无疑问,如果创作中频繁地出现同一个意象,那么忽略它势必就难以把握诗歌的核心。从1990年3月1日到3月12日,短短十几天的时间,路翎创作出两千多行诗,其中就包括篇幅巨大的《在阳台上》、《落雪》、《盗窃者》、《失败者》等优秀短篇。路翎似乎把积蓄的心力、久伫的诗情、痛彻的思悟在一瞬间经由一颗极坚韧的“心脏”燃烧殆尽,这熊熊的“火焰”(常与“心脏”发生关系)把过去与现在的一切都化为灰烬。组诗中的人物,身份地位殊异,但共有着一颗复杂而敏锐的“心脏”,在阳台上重新构筑一个现实背后的世界。路翎似乎回到了起点,强调主观战斗激情以及原始强力,在内心凝聚着与日常生活的阴影搏斗的力量。即便不能在现实中实现自我,他也要在心灵中完成。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短时间内爆发出的出人意料的巨大诗情是诗人内心复杂的耗损,不仅消耗着自我,也消耗着自我与世界的盘根错节的联系:“心脏痛苦了,/孤单了,/走过的不是街道,/而是赤裸的大地似地;/在赤裸的宇宙里,/到来阳台上,/痛苦,战栗,想着生命的法则,/丧失者痴呆着,/有着他的实感与幻觉,找寻着法则来到阳台上。”在差不多同时写出的《诗七首》中,“心脏”这个意象依然频繁使用:“马在战场奔驰,/马的心脏知觉着经过的空间——危急的空间,/和时间,紧张的时间;/马的心脏有红色的火焰与白色的闪光外溢,/它自己看见。/它和它的骑者在这战争的时间与空间中有多重的影像出现。”诗人试图进入每一个与现实发生联系的人物或者动物的“心脏”里,透过这些截然不同的心脏,去理解散佚在日常现实中的历史的片段,以此来重新整理过去的阵痛和惊悸以及个体的存在方式。
四
当诸如“精神分裂”、“丧失创作能力”、“艺术生命已消磨殆尽”等“叙述”经由历史的见证者(本身即具有发言权)加工演绎之后,它们逐渐越过路翎创作的客观状况,而形成事实上不利于对其晚年文学形象加以评估的刻板模式,也即用个体才华的枯竭反证历史的残酷。在路翎晚年的创作中,暗含着极其清晰的话语逻辑,甚至说是诗歌理想——不断反思个体与历史、记忆与现实、日常与恐惧之间复杂的关系,乃至到最后的《在阳台上》、《诗七首》中出现了一种“将要完成”的诗歌趋势。而这种试图“完成”的创作心理,就是尽量在诗歌中“穷尽”自身的思考,将以往的经验收纳整合,其过程相当于一次对过去的梳理和总结。因而,在路翎晚年的诗歌创作中,存在着一个不断冲突的艺术世界,尽管它有所残缺而并不完整。从另一层面上说,诗人对于其创作的执着,也显示出诗人选择面对世界的方式是主动而富有逻辑脉络的。这样,随着论述起初的两个根本性问题得以回答和解决,我们也将重新窥测到晚年路翎的创作心理和不容忽视的诗歌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