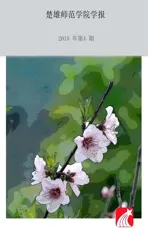清末云南诗话的主要范畴*
2015-03-19李国新
李国新
(西南林业大学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4)
“清末”约指乾隆至宣统。清末云南诗话著作主要有袁嘉谷《卧雪诗话》、由云龙《定庵诗话》、檀萃《滇南诗话》、陈伟勋《酌雅诗话》、严廷中《药栏诗话》、许印芳《诗法萃编》、朱庭珍《筱园诗话》、王寿昌《小清华园诗谈》、王崧《诗说》、刘大绅《论诗》、魏定一《作文如用兵说》,等等。这些诗话中有较多独特诗学范畴,如朱庭珍“自然”“气” “真我”等,袁嘉谷“自然” “神味”等,赵藩的“正声”等,王寿昌《条辨》中的诸多范畴,李含章“自然美”等。这些范畴的提出与诗学家的理论息息相关,是中国古典诗学中的组成部分。本文拟对清末云南诗话中较为突出的诗学范畴进行探究,以发现其内在关联性和独特的价值与意义,从而更好地理解清末云南诗话及其地位。
一、诗的根源论——气
气是中国哲学中的宇宙本体,是万物之源。孟子之养气当是诗学之气的源头,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以强调气对文的重要。另外,刘勰《文心雕龙》对气的阐述更加全面且更加深刻。可见,气不仅是哲学上的重要根源,也是诗学的本体。
朱庭珍对气的阐述较为深入且全面。其曰:“盖诗以气为主。有气则生,无气则死,亦与人同。”[1](P262)这与曹丕之论的主要观点相同。朱氏认为诗无气则其价值不大。朱氏又提供了养气方法:“故气须以至动涵至静,非养不可。养之云者,斋吾心,息吾虑,游之以道德之途,润之以诗书之泽,植之在性情之天,培之以理趣之府,优游而休息焉,酝酿而含蓄焉,使方寸中怡然涣然,常有郁勃欲吐、畅不可遏之势,此之谓养气。”[1](P262)朱氏认为,首先应斋心息虑;其次要注重学习,包括圣贤的令言令行、诗书精华;最后,将这些内化为性情与理趣等并蕴蓄之。朱氏的这一方法较为全备,也能真正提高诗歌主体的文气。朱氏养气的目标是真气,其解释道:
夫气以雄放为贵。……然非有至静宰乎其中以为之根,则或放而易尽,或刚而不条,气虽盛,而是客气,非真气矣。[1](P262)
朱氏诗歌之气有由至静宰乎其中且能自由地处在动静之间的特点,其不需要惊天动天,也不需刚而不条且放而易尽。这正体现气必具有的本体性价值。朱氏又认为: “养气为诗之体,炼气为诗之用。”[1](P263)养是从无到有,炼是从有到有之序。养气是前提,炼气是进一步的加工。可见,朱庭珍从本原地位、养成方法、最终目标等来阐述气,让气成为了一个价值较为全面的诗学范畴。
许印芳与朱庭珍一样也非常推崇曹丕的观点:“《论文》一篇,谓‘文以气为主’,乃千古不易之论。”[1](P151)在其评 《文心雕龙》时也有相似的观点:“以气为主,而创‘风骨’之说,语皆精透。”[1](P151)许氏进一步把风骨的核心要素——气突显了出来。严廷中《药栏诗话》曾谈“气骨”:“诗以气骨为主。有句无章者气弱,有格无调者骨弱。”[1](P123)严氏评诗以气骨为主,这与传统诗学中的“风骨”有较多相似之处。同时严氏又区分了气与骨,前者多与章句有关,后者多与格调有关。这实际说明气骨由章句、格调等融合而成。
王寿昌《小清华园诗谈》把气具体到“气象”“气韵”,并举了较多例子说明这两个范畴。这两个范畴的意义与前代诗学中对它们的界定区别不大,皆是通过诗歌整体呈现出的气象与气韵来评价诗歌。故王氏之气已融合了其他概念并以较为抽象的境界来评价诗。
袁嘉谷的《卧雪诗话》是清末云南诗话中出现较晚的诗话之一,对气的阐释较为全面,其云:“坐诸天阁波离殿,俯视皇州,一气可辨。”[3](P474)“一气”传统被认为构成万物之本源。《庄子·大宗师》曰:“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4](P227)袁氏的 “一气”离庄子所说的意味还差很远,因为其是“可辨”的,但它必然沾染了一些本原的意味。所以,袁氏在论诗过程中,赋予了气不同的指向:一是奇气,如“诗有奇气,意境亦深”;[3](P499)二是气度,如 “觉陶公气度尤纯耳”;[3](P693)三是诗歌的审美风貌,如 “小圃师诗以笔胜,以局胜,以气胜”。[3](P550)
要之,气漫布于清末云南诗学中,继承传统诗学中的气,把气作为诗歌的本体,同时又把气具体成诗歌的构成要素等,且提出了一些相关的审美范畴,以之来评价诗歌,呈现出较为全面的评价标准。
二、诗的道德轨范——温柔敦厚、中和
温柔敦厚与中和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清末云南诗学的轨范自然也不会偏离此途。朱庭珍云:
温柔敦厚,诗教之本也。有温柔敦厚之性情,乃能有温柔敦厚之诗。……夫言为心声,诚中形外,自然流露,人品学问心术皆可于言决之,矫强粉饰,决不能欺识者。[1](P309)
朱庭珍把温柔敦厚之性情作为诗歌教化天下的根本,并以此要求创作主体学习儒家传统的诗学价值观,从而使之蕴藏于自己的诗学意识中,且在创作时自然流露出温柔敦厚的价值观,也就可达到化成天下的诗教之作用。
王寿昌《小清华园诗谈》谈及与温柔敦厚相似的性情时云:
诗以道性情,未有性情不正而能吐劝惩之辞者。三百篇中,其性情亦甚不一,而总归于无邪,故虽里巷之歌谣,皆可为万世之典训。……学者贵取其所长弃其所短,驯而至于温柔敦厚之归,则《雅》《颂》之音,庶可复睹耳。[1](P28)
王氏的性情不是自然性情,而是能吐劝惩之辞的正性情,与孔子“诗无邪”的主旨基本一致。其性情归向温柔敦厚,与诗经中《雅》《颂》的性情一致。
另外,由云龙与师范也曾直接强调温柔敦厚之诗教的重要性,其云:“温柔敦厚,本为诗家上乘,顾后之学唐者,不得其蕴藉之旨归,徒袭其空阔之窠臼,千篇一律,可彼可此。”[2](P600)师范 《荫椿书屋诗话》曰: “温柔敦厚,诗教也。即间涉讽刺,要使言者无罪,闻得足戒,方无戾三百篇之旨。”[1](P8)两人皆把温柔敦厚视为诗歌的金科玉律。前者主要围绕后人只得其皮毛、不得其精髓的学习方法展开,后者围绕诗教的功用和价值展开。
中和是诗教的另外一端。《礼记·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5](P1422)先秦以中和育成万物的观念是中国传统诗学中的基本思维,它强调“执两用中”与“以和为贵”的审美趣味,即中和之美。作为被儒家浸染的云南诗学,中和观念自然是不可缺少的诗学表述之一。[6](P22-25)朱庭珍与许印芳是其代表。
朱庭珍《筱园诗话》曰:“孔子曰:‘过犹不及’。又曰: ‘中庸不可能也。’ 《尚书》亦曰:‘允执厥中。’释氏炼妙明心,归于一乘妙法;道家九转功成,内结圣胎,同是一‘中’字至理。盖超凡入圣,自有此神化境界。诗家造诣,何独不然!”[1](P269)朱氏不断列举孔子、《尚书》、释氏之“中”字,都是为了说明“中”观念的重要性。朱氏曾用一系列比较极端的描述来说明“中”的必要性:“太奇则凡,太巧则纤,太刻则拙,……必造到适中之境,恰好地步,始无遗憾也。”[1](P269)“太A则B”的方式是说诗歌不能趋向任何审美范畴之价值的极端,只有做到不太奇、不太巧、不太刻等,诗歌才能走向恰到好处之境。
王寿昌则曰:“(《寄中书同年舍人》)如此等作,皆雍容和雅,盛世之音也。”[1](P33)许氏所举之例被认为和雅之作,也是盛世之音。这表达出多种诗学趣向,其中包括和雅之诗是盛世之音、和雅是诗歌中至高的诗学境界等。雅者,正也。故和雅实质是中正平和的诗教观念。
《药栏诗话》将温柔敦厚与中正平和的观念结合起来考察:“至诗以温柔和平、缠绵雅丽为主,韩苏集中无此也。”[1](P142)易言之,最完美的诗应该是温柔敦厚、中正平和、缠绵雅丽各类审美趣味的糅合,这就把中国传统诗教的诸多价值观念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有较大包容空间的诗教观念,是中国诗教观念的进一步发展与延伸。陈伟勋《酌雅诗话》之“酌雅”的诗学命名或许能回答清末云南诗话对中国传统雅正观念的思考与演绎!
凭着这种传统诗学价值观的影响与介入,清末云南诗话所表现出的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与诗学观念的吸收是不曾停止的,它有着时代与区域的特色,同时也富含沾满自足意味的诗学价值取向。
三、诗与表达对象的关系——真与自然性情
清末云南诗论家非常关注真,王寿昌《小清华园诗谈》阐述得较为全面: “诗有三真:言情欲真,写境欲真,纪事欲真。”[1](P26)王氏认为诗歌之真分为三个层次:情真、境真、事真。王氏进一步解释:
何谓真?曰:自来言情之真者无如靖节,写景之真者无如康乐、玄晖,纪事之真者无如潘安仁、左太冲、颜延年。少陵皆兼而有之,故往往有生字拙句,人皆不解其故,不知乃直书所见,初不假乎雕饰者,但嫌其发泄太尽耳。如言情,陶但云:“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写景,康乐但云:“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1](P34)
从王氏对杜甫与陶渊明诗的评价看,真是情感的自然流露与表现,没有“假乎雕饰”,也没有过多的情感与语言衬托,易于被他人所接受——直书所见。故王氏认为,发泄太过不是真,生字拙句不是真,人不解其故不是真。同时,情、事均真从诗歌的构成要素来说,境真从诗歌各构成要素综合而成的抽象审美状态来说。可见,王氏的真体现在诗歌的各个层面,要求诗歌无论从具体构成要素还是综合体现出的审美目标等方面皆要做到真。
严廷中曾直接要求诗歌应有真的审美价值,其《药栏诗话》曰: “诗以真胜。”[1](P138)这一说法言简意赅,把王寿昌想表达的都包容在其中。真既是一种不受限制之自由,也是完全按照自然之状态来创作。
刘大绅与朱庭珍则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论真。刘氏《论诗 (一)》曰: “诗如人,真者传,不真者不传。……是故喜则歌,怒则骂,病则呻吟,哀则涕泣,情之真者也。……己有己之真,人有人之真;一日有一日之真,一物有一物之真,无容假也,无容袭也。”[1](P350)这一解释从诗真开始,强调诗歌主体在创作过程中不受外界影响,自由地抒发情感。并且,刘氏还区分了不同人、不同时间、不同事物之真,强调真的特殊性与差异性。朱庭珍更直接要求创作主体达到真我之境界,其《筱园诗话》曰:“善为诗者,上下古今取长弃短,吸神髓而遗皮毛,融贯众妙出以变化,别铸真我以求集诗之大成,无执成见为爱憎,岂不伟哉。”[1](P261)朱庭珍的“真我”有以下特点:一是占有前代的资源与优势;二是以出神入化的方式融贯古今;三是创作出的作品丢弃前代的成见。这一见解比起其他清代云南诗论家对真的阐述更加全面,也更具审美价值。朱氏在《筱园诗话》里非常多地强调真,如“真传”“真意”“真诗”“真气”“真诠”“真诗”等。这些要求与审美范畴更全面地体现了诗歌之真的要求与意义。
真往往与自然性情相关。袁枚说:“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否则敷衍成文矣。”[7](P234)此处性情指自然性情。袁氏认为,诗需先有自然性情然后才有真的审美价值。
朱庭珍曾将真与自然性情结合起来论:
盖自然者,自然而坐,本不期然而适得之,非有心求其必然也。……盖根底深厚,性情真挚,理愈积而愈精,气弥炼而弥粹;……天机洋溢,意趣活泼,诚中形外,又触即发,自在流出,毫不费力,故能兴象玲珑,气体超妙,高浑古淡,妙合自然,所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是也。此可渐臻而不可以强求。[1](P269)
朱氏认为,自然并非心的主观为之,而是不期而之的。同时,他又强调自然性情越真则理愈精、气愈粹,如此则诗歌之“兴象玲珑,气体超妙”,就能达到高浑古淡、妙合自然的平淡之美,也就达到了诗歌非常高的境界。朱氏实际上把真、自然性情作为诗歌非常重要的审美要求提出来,并认为它们是构成诗歌渐臻完美的必备条件。
许印芳评黄鲁直所云“皮毛剥落尽,惟有真实在”句时说:
昔贤论其胜人在诚实。学者能如黄鲁直……无用摹仿,自然吻合。……凡有撰者,勿论赋比兴,皆据现情现景抒写怀抱,而忠君爱国,哀物悼世,骨肉悲愉,亲故戚忻,缠绵悱恻之思,沉郁顿挫之致,沛然从肺腑中流出。[1](P396)
从此可见,许印芳承认诗歌真实的必要性,同时认为真诚与自然的意义一致:皆要根据现情现景进行诗歌创作,从而抒发不同类型的情感,且抒发的方式为“沛然从肺腑中流出”。
王寿昌释“自然”云:“古诗如《今日良宴会》、《庭中有奇树》是也。其次则子建之《公宴》、《美女》二篇,暨渊明之‘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1](P35)王寿昌以举例的方式解释不同层次的自然之美,认为古诗最自然,其次是曹植《公宴》等和渊明的归园田居等。从所举诗来看,古诗更加浅白如话,利用日常口头易见的词语来表达,有言有尽意无穷之美,更有吻合生活自然情趣之美。这实际上是一种自然性情的表达。
从真、自然性情等范畴看,清末云南诗论家的诗学大多把诗歌与现实的吻合程度作为追求目标,并把这些观念贯彻到诗歌的所有方面,从而使诗歌成为真与自然价值的宣导媒介。
四、诗的技术与工具性——法
法是诗歌的技术,也是诗歌创作的无形工具。每朝每代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对法的认识,特别是唐以来诗论家更加强了对诗法的认知,清末云南诗学亦不例外。
朱庭珍云:“诗也者,无定法而有定法者也。”[1](P258)朱氏讨论的不是法与不法的问题,而是强调定法与非定法的区别。易言之,朱庭珍认为诗歌的法是处于定法与无定法之间,只有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才能真正理解诗歌法的意义所在。定法是诗歌必须应用的方法。朱庭珍解释无定法道:“或以错综出之,或以变化运之;或不明用而暗用之,或不正用而反用之;或以起伏承接而兼开合纵擒,或以抑扬伸缩而为转折呼应;……时奇时正,若明若灭,随心所欲,无不入妙,此无定之法也。”[1](P258)综合朱氏所列情况,无定法就是在定法的范围下做任何可能的对于法的创新与变化,实际上是通过运用定法而达于无定法最后进入诗歌之妙境。也就是强调法为我用,而人不能被法所局限,真正使法活、使法妙:“作诗者以我运法,而不为法用。”[1](P258)“作五古大篇,离不得规矩法度。所谓神明变化者,正从规矩法度中出,故能变化不离其宗。然用法须水到渠成,文成法立,自然合符,毫无痕迹,始入妙境。”[1](P265)
许印芳在论述法与非法时,强调既要有法之迹、也要有法之意与法外意:“诗文高妙之境,迥出绳墨蹊径之外,然舍绳墨而求高妙,未有不堕入恶道者。故知诗文不可泥乎法之迹,要贵得乎法之意,且贵得乎法外意,乃善用法而不为法所困耳!”[1](P149)这样看,许印芳将“法”分为三个层次:“法之迹”“法之意”“法外意”。法之迹强调诗歌创作的具体方法,法之意强调从法的运用中透露出的意味,法外意强调诗法之外所蕴含的意味。由法之迹到法之意,再到法外意,这实际上是一个由形而下到形而上的过程,也是艺术由浅显向深入、丰富、向更高境界提升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朱庭珍说的无定而至妙境与许氏的“法外意”有较多共通之处。
清末云南诗话还涉及了较多具体的诗法,如字法、句法、章法、对法、笔法等,这些方法虽然被谈得较为随意,也多以具体的诗歌来论说,但皆是诗法的重要构成部分。有的诗论家还将诗法与文法、兵法对比。前者可从卧雪诗话中看到,后者可从魏定一《作文如用兵说》等中看到。另外,还有一些诗论家采取细节描述的方式来说明构思之法。谢履忠《论文》曰: “大抵一题前后左右,有天然步位,明手握管,一眼觑定,或用正笔或用反笔,或用翻笔或用侧笔,……深思静虑,通篇打算,烹炼既熟,成竹在胸,然后提笔直书,随意所至,顷刻文成。”[1](P346-347)谢氏将为文的过程从定题开始,细致地描述如何运思、如何布局、如何深思、如何遣意、如何成文等方法。
从清末云南诗话的整体看,关于法的讨论是其诗歌创作的本身要求,同时在理论总结时,他们从具体内容与抽象分类上做出一些新的尝试,让我们知道法的必要性和无法而极于妙境的可能性。
五、基于以上核心范畴的思考
除去上述几个核心诗学范畴:气、温柔敦厚、自然性情与真、法,清末云南诗学中集中被阐述的范畴还有较多,如清、正声、根坻、学问等。从论述的这几个范畴看,它们都是支撑中国传统诗学的核心范畴,表明清末云南诗学的发展是以吸收中国传统诗学的精髓为路径的,但同时它又有着较丰富的特色。
一是清末云南诗学保持了较大的纯真审美特性。云南地处边疆,少数民族人口较多,呈现大杂居的居住特点。由于地理位置离中原较为偏远,且靠近不发达的东亚国家,大部分是山区,故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同时,云南有着特殊的植物环境与动物环境,这些都使云南人保持着较大的真实性和原始性。而这一特性更易于呈现一种真的人生价值观。在诗学,清末诗论家注重体现自我,并把与自然的完全吻合作为追求目标。所以,对于自然与真我的诗学讨论是清末云南诗学的核心叙述内容,表明了清末云南人的生活姿态与自然环境的特点。
二是清末云南诗学作为区域性诗学有着较大的丰富性和全面性。虽然远离中原诗学,但云南诗学有着自身的地缘优势和区域优势,吸引了来自中原的主流诗学观念的介入。结合自身的特点,清末云南诗论家试图在创造自己诗学特色的同时,大量吸收中原主流诗学,这让我们看到了云南诗学中所包涵的内容非常丰富,不仅有儒家温柔敦厚与中正平和等的诗教观,同时也有从形式层面进行解释的诗法研究,这使清末云南诗话的丰富性和全面性较为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三是注重对传统诗学范畴的进一步阐释。在吸收传统诗学主要范畴的内涵与价值时,清末云南诗论家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与阐释。从气之根源上说,清末云南诗话承认前人的养气之说,并且不断地阐释气骨、气象、气韵等较为普遍的诗学范畴,但也有人将诗学中的气论进一步归结,如“养气为诗之体,炼气为诗之用”之说。在前人养气基础上,朱庭珍提出要炼气,即在积学以储宝、澡雪精神、疏瀹五脏等后,还要对形成的气进行提炼,最后达到“真气”。这一过程是作者养气后诗歌创作时对气的重新选择与加工,此时炼气与作者稍远,与诗歌文本较近。这种观念将前人注重作者养气的观念推进到了文本之气,同时注重对气的炼也体现了朱庭珍诗学的新得与发展。从对真和情景的阐述看,前人有真诗、真我、情中景与景中情、境界等观念,王寿昌《小清华园诗谈》要求情真、景真、事真,这些观念虽然是境界等中包括的意义与价值,但很少有人提出景、情、事俱真,这一提法无疑具体阐释了传统诗学中真与情景、境界等范畴的关系。
总而言之,清末云南诗话集中表现出的诗学范畴有着较大的特色与价值,是以继承中国传统诗学范畴和进一步阐释和提升为叙述与讨论动机的,它所代表的是云南边疆富于地域特色的诗学阐释方向,有益于融入中国传统诗学并推动云南诗学向理论化与现代化方向发展进步。
[1]张国庆选编.云南古代诗文论著辑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由云龙.定庵诗话 [M].见: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 [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3]袁嘉谷.袁嘉谷文集 [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4]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5]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M].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张国庆.云南古代文学理论概览[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1(4).
[7]袁枚.随园诗话 [M].顾颉刚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