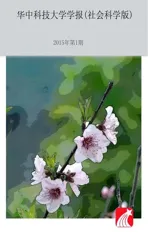从统治城市到治理城市:城市政治学研究综述
2015-03-19黄徐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300074
黄徐强,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 300074
从统治城市到治理城市:城市政治学研究综述
黄徐强,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 300074
城市政治学主要研究城市的权力结构和治理结构,两者构成梳理城市政治学范式转换的主要线索。就前者而言,它相继出现精英主义和多元主义城市权力结构论、城市增长机器论以及城市政体论等理论。这些理论的演进实际暗含了两种权力观的更迭,即由社会控制模式的权力观转向社会生产模式的权力观。就后者而言,它相继出现传统区域主义、城市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区域主义等理论。这些理论的转换预示着城市治理结构由突出政府统治转向强调协同治理。20世纪90年代至今,这两大线索出现融合,从而使得城市政治学的核心范式由关注谁统治城市转向探讨如何治理城市。无疑,这些范式对于推进我国的城市政治研究、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均具有重要的启示。
城市政治学; 统治; 城市权力结构; 治理; 城市治理结构
城市政治学主要研究在城市空间内,决定社会价值权威性分配的政治生活及其组织形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城市权力结构和治理结构。由此,城市的权力结构和治理结构不但构成了城市政治学的核心研究对象,而且也构成了理解城市政治学范式转换的两大重要论域。在探讨这两大论域的过程中,理论家们也推动了城市政治学的发展:它滥觞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并繁荣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并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统一转向探讨城市治理。由此可见,在促进学科发展的同时,理论家们对这两大论域的探讨也实现了合流,从而使得城市政治学的核心范式由关注谁统治城市转向探讨如何治理城市。
然而,与西方城市政治学的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的城市政治学可以说仍处于起步阶段。与乡村政治研究的繁荣相比,我国城市政治学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理论成果都亟待丰富。而城镇化又是目前党和国家工作的主要着力点。城镇化必然会改变现行的利益关系,引发各种社会问题。为有效化解这些问题,就有必要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城市政治学的核心主旨恰恰是探讨何种形式的权力结构与治理结构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治理。因此,梳理城市政治学的范式转换,既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又有突出的实践意义。
一、从控制到生产:城市权力结构论域的演进
公共权力及其结构始终是政治学的核心研究对象,对它们的研究不但可促进政治理论的发展,而且能提升人们对社会政治问题认识的理性程度。权力结构是指权力在社会各阶层的分配状况和运行机制,它体现为权力执掌者的社会阶层属性,以及公共政策制定的制度化流程。与之相类似,城市政治学也必然会考察城市的权力结构,并分析“谁”(who)为了“什么”(what)凭借何种资源基础取得并运用城市公共权力。理论家们对这些问题给出了迥异的回答,这些回答在促进学科发展的同时,也构成了梳理城市权力结构论域演进的脉络。
城市权力结构的论域先后发生了四次转变:精英主义权力观和多元主义权力观、城市增长机器论(urban growth machines theory)和城市政体论(urban regime theory)。学界一般认为增长机器论继承了精英主义的衣钵,政体论则接过了多元主义的大旗,但事实并非如此,如克莱伦斯·斯通(Clarence Stone)所言,在论域转变的过程中,理论家先后阐明了两种权力观,即社会控制模式(social control model)的权力观和社会生产模式(social production model)的权力观。前者将权力视为一种主体凭借掌握的资源控制客体的能力,其本质是支配;后者将权力视为一种为促进经济增长和治理社会等目标、各类主体协作的能力,其主旨是生产。以斯通划分的这两种权力观为线索,可以重新梳理城市权力结构论域的转变。
在精英主义论者看来,少数经济精英统治城市,垄断公共政策的制定权,政治权力只是经济精英实现利益的工具。弗洛伊德·亨特(Floyd Hunter)是第一个运用精英主义理论系统分析城市权力结构的政治学家。20世纪50年代,亨特运用“声望法”研究亚特兰大的权力结构时,为精英主义提供了经验支撑。他发现,经济精英差不多包揽了事关该市经济发展的公共政策。在该市,“商人是社区领导。财富、社会声望和政治机器都是社区经济精英的权力工具。……在公共事务方面,经济精英也占据着突出的位置。”[1]81这一研究一经问世便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它显然有悖于美国人秉持的自由民主理念。
自然,不断有学者批评亨特的论断,其中,罗伯特·达尔提出了与之相对的多元主义城市权力论。在这派看来,不同领域的精英控制着不同领域的政策制定权,城市由“多重少数人”统治。通过运用决策分析法研究纽黑文市的权力结构,达尔为多元主义提供了经验支撑。达尔主要从历史和现状两个维度考察该市的权力结构。他指出,自1784年至20世纪中叶,该市的权力结构逐步由寡头统治演变为多元主义政体。通过考察政党候选人的人事提名、城市重建和公共教育等领域的政策制定流程,达尔发现这些领域的权力分别由不同的精英掌控。总之,在该市,“大多数社区决策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但是,实际上,不同的小群体在不同的社区问题上做出决策。”[2]159-160
就客观效果来讲,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精英主义论者与多元主义论者之间的论辩也推动了城市政治学的兴起与发展。虽然两派针锋相对,不过他们的权力观均属于社会控制模式的阵营。差别仅在于前者认为少数经济精英掌控城市权力,后者则认为不同领域的精英共同分享城市权力。就其实质而言,这一阵营承袭的是马克斯·韦伯的权力理论。在韦伯看来,“权力就是在一种社会关系内部某个行动者将会处在一个能够不顾他人反对去贯彻自身意志的地位上的概率,不管这种概率的基础是什么。支配就是某项包含了特定明确内容的命令将会得到某个特定群体服从的概率。”[3]147由此可见,以上两派都将权力的本质定位为支配,也即他们都关注谁统治城市。
但精英主义论者和多元主义论者并未详尽说明精英为何竞相执掌公共权力。与此同时,两派的激烈争论促使哈维·莫罗奇(Harvey Molotch)和保罗·彼得森(Paul Peterson)等学者反思已有的研究。他们指出,不应仅仅关注“谁”统治,更应探讨谁为了“什么”而统治。为此,他们提出了城市增长机器论。该理论认为,基于谋取利润和竞选等目的,城市的政商会结成联盟,共同制定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于是城市变成了政商联盟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器。
莫罗奇于1976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刊载的《作为增长机器的城市》一文标志着城市增长机器论的兴起。在该文中,他指出,企业家群体会结成联盟,共同促进土地的交换价值。基于夯实税基、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市政服务等目的,城市政府也会想方设法招商引资。简言之,“任何给定地方的政治和经济本质都是增长。……一个地方的内在本质都是按照增长机器的方式运行的。”[4]309-310就此而言,莫罗奇虽然将城市权力结构的研究推进至“谁”为了“什么”而统治,但仍认为政商精英共同掌控了公共政策制定权。可见,这一权力观仍属于社会控制模式的阵营。
在借鉴莫罗奇理论的基础上,彼得森于20世纪80年代为增长机器论提供了新的理论证成。城市利益是其理论的逻辑起点,在他看来,城市利益限制了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类主体选择公共政策的范围。由此,彼得森又区分了发展型公共政策、再分配型公共政策和分配型公共政策,发展型公共政策有利于城市利益的扩张,再分配型公共政策不利于城市利益的增长,分配型公共政策与城市利益的影响不大。在实践中,地方政商联盟会推进发展型公共政策,规避再分配型公共政策。
不过,彼得森的分析并未就此结束,他指出,对于城市而言,发展型政策是一场“正和”博弈。由此,他也推演出迥异于社会控制模式的权力观:仅就发展领域而言,权力是 “社区作为一个整体认识它的目标的能力。权力所需要的不是把领导力理解为将某种意志强加于他人的能力,而是能够游说他人为共同的目标做出贡献。”[5]155由此可见,彼得森并不完全认为权力的本质就是主体支配客体,权力毋宁说更应服务于经济增长。
城市增长机器论兴起之后,同样遭到了许多批评。该理论的主要缺陷是太过强调经济要素的重要性,以致陷入了“经济决定论”。其倡导者几乎无视城市政府的自主性,更没有关注社会力量在制定城市公共政策中的作用,他们大都把城市的主要任务仅仅定位为促进经济增长,因而忽视了包括缩小贫富差距在内的其他议题。由此,在改进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史蒂芬·埃尔金(Stephen Elkin)和克莱伦斯·斯通等人就提出了城市政体论。城市政体是城市政体论的核心范畴,它是指在城市空间内的政府、经济组织和社会力量在充分利用各自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非正式的稳定的公私合作关系。
埃尔金是城市政体论的先驱,他提出了三种城市政体:多元主义政体(pluralist regimes)、联邦主义政体(federalist regimes)和私利至上主义政体(privatist regimes)。在第一类政体之下,城市政治精英控制了公共政策制定权。在第二类政体之下,城市政府在联邦政府的指导下推行满足民众福利诉求的公共政策。就最后一类政体而言,“城市是私人积累的引擎,城市政府是资本的侍女。”[6]18据此不难看出,早期的城市政体理论家仍将权力的本质定位为支配与控制。
斯通是城市政体论的集大成者。他在分析亚特兰大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种族关系和政商关系的基础上,完善了城市政体论。他发现,资源的分散性导致城市政府、经济组织和社会力量在没有其他两方合作的情况下,均很难实现自身的目标。“关键的问题是谁对解决问题有所助益。”[7]314为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目标,各方应广泛合作,结成治理联盟。在此,斯通全面阐发了社会控制模式和社会生产模式的权力观。如上所言,前一种权力观承袭的是韦伯的权力理论。与之相对,在后一种权力观看来,资源的分散性使得正式的制度安排不能独自担负起促进增长、实现治理的重任。相反,“治理的行动需要与私人行动者的合作,以及对私人资源的动员。”[8]7简言之,权力不是控制的权力(power over),是行动的能力(power to)。这样,我们也就不难发现斯通的重大理论贡献了,他将我们对权力的认识由突出纵向的支配转向强调横向的合作,从而将传统的社会控制模式的权力观变革为新型的社会生产模式的权力观。
由此,斯通也就间接阐明了治理理论的权力观基础。他强调资源依赖,也就间接地强调权力依赖,而“治理理论明确肯定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9]41但这也正是城市政体论的不足之处。它看到了资源的相互依赖,却把这一依赖限定在城市空间内,进而忽视国家和国际因素对城市的影响。因此,它虽然在政治层面探讨了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诸多要素,但仍然还是逐渐被治理理论所取代。不过,并不能因此否认其价值,实际上,这些理论也说明,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应摒弃权力的支配属性,转而不断发挥它对公共生活的积极作用。
二、从统治到治理:城市治理结构论域的演进
如上所言,单就城市权力结构这一论域而言,权力观的更替也说明城市政治学由分析谁统治城市转向探讨如何治理城市。然而,城市公共事务的治理和公共物品的供给需要组织机构的支撑,在此基础上,就形成了结构化的制度框架,并由此演变成固定的治理结构。因此,这一结构的变迁也构成梳理城市治理结构论域转变的现实基础。通过考察各派对该问题的研究,可以发现城市治理结构的论域也转向了探讨如何实现城市治理。
城市治理结构的论域主要发生了三次重大的理论演进:19世纪末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主张在城市建立单一政府的传统区域主义(traditional regionalism),20世纪50年代中期问世的运用市场模型分析城市治理结构的城市公共选择理论, 20世纪90年代突起的将治理理论引入区域治理层面的新区域主义(new regionalism)。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学者们也逐渐认识到,城市治理既不能仅靠政府,也不能单靠市场,它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多方参与和共同合作。
彻斯特·马科斯(Chester Maxey)、路德·古利科(Luther Gulick)和保罗·斯杜邓斯基(Paul Studenski)等学者共同促成了传统区域主义的兴起与发展。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城市政府的碎片化,“不仅严重有悖于地方政府的行政成本的节约和绩效的提升,而且它还严重地阻碍了所有的进步性和综合性事业。”[10]229在城市内,多个相互重叠的政府意味着服务的重叠,这也不符合规模经济的要求。更有甚者认为,“权威的碎片化以及为数众多的地方政府之间的辖区重叠是城市政府制度失败的根源。”[11]8基于此,他们根据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主张在城市区域建立起一个统一集权的大都市区政府,进而形成一个科层制的官僚体制,以此在宏观上化解以上种种问题。
然而,集权的大都市政府在解决自身问题以及对社会问题的回应上都显得无能为力。换言之,传统区域主义的主张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与此同时,深厚的“有限政府”和“地方自治”的政治文化传统也促使美国民众反对建立高度集权的大都市区政府。鉴于此,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美国城市兴起了邻里政府运动。该运动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质疑美国较大城市的规模庞大的政府机构的绩效。”[11]11因而,他们主张要还原足够小的政治单位,以使政府回归于人民,确保政府能提供满足公民多样化的偏好。这样,传统区域主义的失败以及邻里政府运动取得的成效也就构成了城市公共选择理论兴起的逻辑起点和现实基础。
查尔斯·蒂伯特(Charles Tiebout)与罗伯特·沃伦(Robert Warren)是最早将公共选择理论运用于城市治理结构的经济学家,奥斯特罗姆夫妇(Vincent Ostrom, Elinor Ostrom)推动了城市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罗杰·帕克斯(Roger Parks)和罗纳德·奥克森 (Ronald Oakerson)则完善了这一理论。前期,蒂伯特和沃伦只是简单地将市场模型运用于分析生产城市公共物品的组织形式。他们认为,作为消费者的城市居民会根据付出和收益“用脚投票”,挑选地方政府。只要“社区的数量越多,他们之间的差异越大,就越能满足消费者的偏好。”[12]418大都市区政府的运行机制类似于市场:为吸引作为消费者的居民,地方政府会相互竞争,竞相提升行政效率和效益。
随后,蒂伯特和沃伦又与奥斯特罗姆夫妇一道,提出并发展了多中心的城市治理模型。辨识公共物品的性质和类型、划分公共物品的供应(provide)与生产(product)是他们立论的前提。在他们看来,居民向地方政府表达偏好,形成公共物品的供应链。随后,根据公共物品的性质和类型,政府再决定生产的组织形式。这些形式有:政府直接生产、服务外包、特许经营和联合生产等。作为消费者,地方政府也会监督生产,督促生产单位提高效率。
不过,上述理论家都非常重视效率,却忽略了平等。由此,通过阐述地方公共经济的理念,帕克斯和奥克森试图弥补这一缺陷。具有多样化组织形式的供应单位和生产单位的复杂组合,构成了地方公共经济。他们指出,“一种结构安排好的地方公共经济一定会使供应单位的大小与所要解决的问题的规模相适应。”[13]67-68他们认为,为实现有效治理和社会公平,在地方公共经济的限度内,大都市亟须公民声音和公共企业家精神。通过增强公民声音,弱势群体可以向本社区或上级公共机构表达自身的偏好,并要求其做出有效的回应。为解决财政悬殊难题,可以诉诸公共企业家精神。简言之,地方官员的首要任务是为促进包括改善弱势群体生活境况在内的城市利益而努力。
虽然在帕克斯和奥克森等人的努力下,城市公共选择理论得到了完善,但是,就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实践而言,过度碎片化的城市政府并未取得多少成效。与此同时,英美等国的中央政府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大幅缩减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援助,权力也由中央下移至地方。由此,促进城市发展、实现社会治理的重任就落到了地方政府头上。随后,迅速席卷各国的全球化浪潮使得资本开始在世界范围内移动。“这一转变弱化了中央政府管理国家经济的能力,因而为城市区域(大部分经济活动都发生在这一区域)创造了条件,以增进由全球化的转变带来的经济收益。”[14]467这样,各国经济的竞争日益沦为城市和城市群综合实力的竞争。而促进中心城区与郊区之间的协同发展,以及不同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并解决经济发展的负外部性问题被认为是增加区域综合实力的必然要求。“治理结构——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对于保持区域竞争力的过程而言是至关重要的。”[15]50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政府都把完善治理结构和增强治理能力提上了日程。为此,学者们试图将刚刚兴起的治理理论引入到对城市和城市群的治理研究中去,新区域主义理论也由此兴起。
汉克·萨维奇(Hank Savitch)、罗纳德·福格尔(Ronald Vogel)、唐纳德·诺里斯(Donald Norris)、格里·斯托克(Gery Stoker)和戴维·汉密尔顿(David Hamilton)等英美学者促成了新区域主义的兴起与发展。区分统治(government)和治理(governance)是该理论的立论前提。统治强调的是由纵向和正式的官僚机构供应和生产公共物品;治理则认为,“可以通过与承担生产的其他政府、非营利组织或私营组织达成一系列的合同与协议,生产公共物品。”[16]161由此,就不难看出新区域主义理论的核心特征了:“它关注的是通过不同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而不是国家的官僚机构,促成大都市区的治理。”[17]10
作为现今城市政治学的主流理论,新区域主义受到了高度的关注,并被广泛地运用于实践。这也间接地说明,除强调治理以外,新区域主义必然还有其他值得重视的特征。首先,它主张,治理的主体是多种多样的。在城市政府、市场组织和社会力量均掌握一定资源的情况下,为实现社会治理,就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建立起跨部门的协作关系。其次,它认为,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不是控制与服从的权力关系,而是相互依赖的平等关系。究其原因就在于,资源的分散性使得各方为实现各自的目标,不得不交换资源、相互合作。由此,它特别强调各方之间的信任和相互赋权。最后,它强调,为实现治理,应该以过程为导向,而不是依赖于正式的结构化的制度安排。为实现共同的目标,各方应积极参与,并动员资源、分担责任,从而在合作的过程中形成非正式的网络化组织。
同时期,包括费城、休斯敦、西雅图和亚特兰大在内的许多美国城市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平等以及财政悬殊等议题上,积极践行新区域主义的理念[18]294-309。但是,美国的地方自治传统、地方政府的财税结构以及深刻的种族和阶级隔阂都限制了新区域主义的广泛推广。对此,诺里斯指出,“新区域主义者号召更大层面的区域治理只是规范性的论断。……实际上,因为新区域主义者没有将区域治理的政治因素纳入考虑范围,以至于他们的论断至多只是主观臆想。”[19]566可见,新区域主义的实效仍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确定无疑的是,城市的治理,绝不能仅仅依靠政府,它还需要市场和社会的共同参与。在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原则下,具体的合作模式完全可以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实际上,城市治理结构论域的转变与西方城市化的进程紧密相关,这些理论也是与城市化相伴随的社会经济变化对公共权力提出不同要求的反应。
三、结论与讨论:构建中国城市政治学的必要性
至此,我们可以说,城市权力结构和城市治理结构的论域在20世纪90年代都转向探讨城市治理,因而这两大论域实现了融合。我们还可以在这两种权力观和三大城市治理理论之间建立相应的联系。主张建立集权政府的传统区域主义和倡导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城市公共选择理论背后暗含的权力观,都秉持社会控制模式的权力观。相信政治权威有效性的人认为,凭借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政府就可以有效地治理城市;相信市场有效性的人认为,凭借价格的指示功能,资本就可以自发地调节利益关系,进而实现均衡。
但是,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潜在风险就决定了单独依靠政府或市场都不能有效地实现城市治理。实际上,政府、市场和社会既存在竞争,也存在合作,关键就在于建立扩大合作、引导竞争的保障机制。社会生产模式的权力观和新区域主义为这一问题提供了理论说明。新区域主义认为,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需要市场组织和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究其实质,就是社会控制模式的权力观。在这种权力观看来,在资源高度分散的现代社会,为促进经济发展、实现城市治理,政府、市场和社会有必要建立起非正式的合作关系。
无疑,西方城市政治学之所以能够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密不可分,那么,对于正在快速推进城镇化的我国而言,城市问题研究泰斗吴良镛先生早在2003年就借用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兹的话预言,“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深刻影响 21 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主题。”[20]8由此可见,我国的城镇化虽然起步晚,但其影响却巨大无比。更加重要的是,城市空间是国家地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优化城市治理结构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强化城市治理能力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基于此,研究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就是所有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然而,就目前国内与城市研究相关的学科发展而言,在依托经济学、社会学和建筑学等学科优势的基础上,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和城市建筑学等新兴交叉学科都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由此,也开创了城市经济政策、城市社区自治和城市建筑规划等研究领域。但城镇化并不能仅仅等同于经济发展、社会自治和空间建设,绝不能忽视其中的“政治”因素。否则,这些学科也就不能为我国的城镇化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撑。
此外,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势必会改变原有的价值观念、利益关系、政府职能、府际关系、治理结构和政策导向,这些就要求政治学为现实提供对策研究和理论说明,因而就有必要借鉴西方城市政治学的基本范畴、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结合中国城镇化的实际,站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高度,构建中国的城市政治学。
[1]Floyd Hunter.CommunityPowerStructure:AStudyofDecisionMakers, New York: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53.
[2](美)罗伯特·达尔:《谁统治:一个美国城市的民主和权力》,范春辉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
[3](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Harvey Molotch. “The City as a Growth Machine: 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82, No.2, 1976.
[5](美) 保罗·彼得森:《城市极限》,罗思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6]Stephen Elkin.“Twentieth Century Urban Regimes”,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Vol. 7, No.2, 1985.
[7]Clarence Stone.“ Looking Back to Look Forward: Reflections on Urban Regimes Analysis”, Urban Affairs Review, Vol. 40, No.3, 2005.
[8]Clarence Stone.“ Urban Regimes and the Capacity to Govern: A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Vol. 15, No.1, 1993.
[9]Chester Maxey.“The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Metropolitan Communities”, National Municipal Review, Vol. 11, No.8, 1922.
[10](英)格里·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华夏风编译,载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1]Robert Bish & Vincent Ostrom.UnderstandingUrbanGovernment:MetropolitanReformReconsideredWashington, D.C.: AEI Press, 1973.
[12]Charles Tiebout.“ A Pure of Local Expenditur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64, No.5, 1956.
[13](美) 罗纳德·奥克森:《治理地方公共经济》,万鹏飞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14]Frances Frisken & Donald Norris.“Regionalism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Vol. 23, No.5, 2001.
[15]Allan D. Wallis.“Evolving Structures and Challenges of Metropolitan Regions”, National Civil Review, Vol. 83, No.1, 1994.
[16]H. V. Savitch & Ronald K. Vogel.“Introduction: Paths to New Regionalism”,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 Review, Vol. 32, No.3, 2000.
[17]Daniel Kubler & Hubert Heinelt.“ Metropolitan Governance: Democracy and the Dynamics of Place”, in Hubert Heinelt & Daniel Kubler (ed.),MetropolitanGovernance:Capacity,DemocracyandtheDynamicsofPlace, London: Routledge, 2005.
[18]Allan Wallis.“The Third Wave: Current Trends in Regional Governance”, National Civil Review, Vol. 83, No.3, 1994.
[19]Donald Norris.“Prospects for Regional Governance under the New Regionalism: Economic Imperatives versus Political Impediments”,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Vol.23, No.5, 2001.
[20]吴良镛:《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载《苏南科技开发》2003年第4期。
责任编辑 胡章成
From Urban Ruling to Urban Governance: A Research Review on Urban Politics Science
HUANG Xu-qiang
(CollegeofPolicticsandPublicAdministrion,TianjinNormalUniversity,Tianjin300387,China)
Urban power structure and urban governance structure are the main research content of Urban Politics Science, and they also compose two major clues which can analyze the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Politics Science. On the one hand, as far as the field of urban power structure, there are many theories which appeared one after another, including the elitism theory, the pluralism theory, the urban growth machines theory and the urban regime theory. Via investigating these theories,we can discover two different models of power, namely social control model and social production model. On the other hand, as far as the domain of urban governance structure, there are many theories which emerged one by one as well, for example, the traditional regionalism theory, the urban public choice theory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theory. At the same time, this phenomenon indicates the transition of urban governance model from highlighting the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to emphasizing o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From 1990’s, it turns up a tendency, that these two clues began to integrate, so that the key paradigm of urban politics science transform itself to urban governance. Undoubtedl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se paradigms has som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us to promote urban politics study and enhance the capacity of urban governance in China.
urban politic science; government; urban power structure; governance; urban governance structure
黄徐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城市政治学和政治理论。
天津师范大学2014年“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项目(2014BSXR)
2014-10-13
D521
A
1671-7023(2015)01-003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