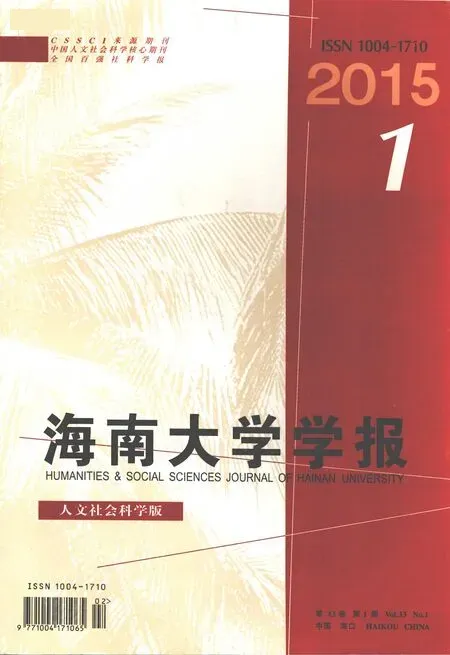古玩交易中诈骗罪认定的难题与破解
2015-03-18武良军
武良军
(海南大学 法学院,海南 海口570228)
一、问题的提出:古玩交易中诈骗罪认定之难题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司法实践中很少有将古玩交易中的欺诈行为作为诈骗罪处理的案例。人们习惯于认为,这一现象是实践中久已形成的“不打假、不三包、出售赝品不算骗”的古玩交易“行规”所致。然而,随着近年来我国各地频现司法机关将出售假古玩入刑处理的事案,这一“集体性认知”已然被证明为谬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逐渐形成新的共识,即古玩市场虽有自己的交易行规,但也不可逾越国家法律的界限,古玩交易中的欺诈行为亦有可能成立诈骗罪。但问题是,究竟何种情形下的古玩交易“欺诈”行为超出“行规”的范畴而应当作为刑事诈骗案件处理?可以说,目前我国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对此并非全然清楚。实践中,总是有许多古玩买家在交易中“打眼”后感到委屈与不公而想诉诸刑事司法机关以求帮助[1],但司法人员在面对这些古玩交易中涉及的交易人欺诈行为是否要进行刑事追诉,往往持模棱两可的态度。与实践中存在的众多古玩交易欺诈行为相比,司法机关将之作为诈骗罪处理的案例少之又少。这并非我国刑事司法机关单纯主观上的不作为,而是由于古玩交易的标的——古玩所具有的一些众所周知的特殊性,使得古玩交易中的欺诈行为能否以及何时成立诈骗罪的司法认定产生了诸多疑难。主要可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我国刑法理论和实务通说认为,诈骗罪中的欺骗行为既可以是作为的形式也可以是不作为的形式,所以一般商品交易中隐瞒物品瑕疵的行为也可能符合诈骗罪中的欺骗行为[2]71。但问题是,对于特殊商品之古玩交易中的出售人在购买人对古玩的真伪自己陷入认识错误后,单纯不予告知的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中的欺骗行为?
第二,由于古玩交易具有众所周知的高风险,购买者对于交易之标的古玩的真伪在交易时常存主观之怀疑。那么,当古玩交易中购买者已经对出售者的欺骗行为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怀疑,但仍出于侥幸而继续购买了该古玩的情形,能否因购买者对结果已有预见进而否定出售者的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行为构成要件?
第三,与一般商品不同,古玩的真伪往往端赖于当事人的鉴别能力,而鉴别能力往往因主体不同而存差异,是故,实践中常有假古玩出售者假借于此否定诈骗罪之主观故意。此外,对于实践中出售者往往事先有“真假自辨”的提示,司法机关能否径直以出售者有声称“真假自辨”的提示就否定其主观上诈骗罪的故意,实践中也存在认识上的分歧。
应当说,以上三个问题直接关涉了目前实践中绝大多数古玩交易案件的处理。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刑法理论对于这些问题的关注度仍然不高,相关论述也颇为少见,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然影响了实务对相关案件的准确处理。鉴于此,为了便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对古玩交易中有关涉嫌欺诈行为的准确处理,既不去放纵交易中的欺诈行为,也不会因过度介入而导致古玩交易市场的萎缩,本文接下来拟对以上三个问题作简要探讨和分析,以期能破解相关难题。
二、难题1及破解:交易中的不作为与诈骗罪之欺骗行为的该当
(一)不作为与诈骗罪中的欺骗行为
尽管我国现行《刑法》第266条只简单规定了“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处……”,但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已普遍认为,诈骗罪在客观上必须符合特定的行为构造: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对方(受骗者)陷入认识错误—对方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产—行为人或第三人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害[3]。从诈骗罪的行为构造中可知,欺骗行为无疑是诈骗罪成立的首要要素。理论和实务一般认为,所谓欺骗,就是“传递与事实不符的资讯”,既包括传递虚假事实,也包括隐瞒真相[4]264。对于欺骗行为,在实务中绝大多数情形都是以积极身体动作即以作为方式实施,故在理论上对于以作为方式实施欺骗行为很少存在疑义。有争议的是,诈骗罪中的欺骗行为能否以不作为的方式实施?德国法院早期的判决认为,“诈欺者也,必行骗之人以积极作为引发相对人之错误”,故而单纯缄默的不作为不可能成立诈骗[5]。然而及至今日,包括德国、日本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的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均已认为,不作为的方式亦可成为诈骗罪中欺骗行为之手段,但同时也认为,以不作为方式实施欺骗行为,“系以有告知或说明义务之存在为前提,其与其他不纯正不作为犯相同,此等告知或说明义务乃是源自于保证人地位。”[6]例如,在普通商品的交易中,店主对于所出售的瑕疵商品负有告知购买者该商品存在瑕疵的义务,倘若店主对商品的瑕疵故意隐瞒而不予告知,则可成立不作为的欺骗行为。
(二)理论争议:交易中的不作为能否该当于欺骗行为
问题是,古玩不同于通常交易中的商品,对于在古玩交易中,当购买者自己对古玩的真伪陷入认识错误后,出售者对古玩真伪的真相予以沉默并单纯不予以告知的,能否该当于诈骗罪中的欺骗行为?例如,有这样一则事案:“甲经营白丁画廊,某日,因炒作地皮一夕致富的乙至画廊参观,看上某幅标价3万元的山水摄影作品,下有‘郎’字的签名。乙虽为草包型的暴发户,但曾听说大师郎静山结合国画山水意境与西洋摄影技术,其山水摄影作品驰名中外,遂不假思索,误以为该作乃郎静山的作品,实则该作乃无名小卒郎竖子的泛泛之作而已。最后乙因误认而向甲以3万元购买该作。假设廊主甲发现乙的错误,但却不为反对表示,默默结账,那么甲所为是否构成诈欺?”③该文《论诈欺罪之陷于错误》原载于《刑事法学之理想与探索——甘添贵教授六秩祝寿论文集》(第二卷 刑法各论),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现此文收录入林钰雄:《刑法与刑诉之交错适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2页。
对此,台湾学者林钰雄教授认为,认定该案中的甲是否构成诈骗的关键在于“甲是否居于保证人地位而负有避免乙错误继续的说明义务”,对此,他的结论是,无论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抑或是根据法律明文规定的缔约说明义务(中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45条之一),均应肯定该案中甲居于保证人之地位,即负有说明的义务,因此甲构成不作为的欺骗行为[4]295。但是,也有学者表示持不同意见。例如,台湾学者吴正顺就认为,“在书画、古董品等之交易,须要自己对物品之专门知识来判断其价值,一般言之,任当事人之鉴定而成立,故其相互间之保持沉默或隐蔽事实,未必足以构成诈欺罪。”[7]中国大陆也有见解表达了相类似的立场,如有学者认为,“对于文物、古董、书画的交易,只要行为人没有实施欺骗行为,即使没有告知对方真相的,也不成立诈骗,因为该领域需要从事交易的人自身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对方没有提醒并告知真相的义务。”[8]
显然,从以上学者的论争中可知,问题的落脚点在于,对于特殊商品——古玩的交易是否应如一般商品交易一样,肯定出售者就商品瑕疵的说明义务。或许有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8条就“商品或服务的经营者有瑕疵说明的义务”的规定,来肯定古玩交易中出售者存在说明真伪的义务。然而,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的规定,此法所保护的是“为生活消费”为目的的商品,而古玩不属于以生活消费为目的,所以,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肯定古玩出售者的真伪说明义务并不妥当[9]。事实上,商品交易中经营者的瑕疵说明义务除来源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8条的直接规定外,在背后更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4条所规定的“诚实信用的原则”。是故,更多的见解可能认为,即使古玩不可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但依《民法通则》之“诚实信用的原则”也应肯定古玩交易中出售者的真伪说明义务。
(三)破解:交易中的单纯不告知并不能该当于诈骗罪的欺骗行为
在笔者看来,诚实信用原则作为现代民法一项最基本的原则,在市场交易的任何领域无疑应当得到严格遵守,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市场交易的任何领域,诚实信用原则都具有完全统一和相一致的实质内涵。应当承认,在不同的市场交易领域,对诚实信用原则实质内涵的认识,理应结合不同交易领域的交易行规和道德准则进行理解。古玩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其交易拥有着一般商品所不具有的特殊性,“其交易目的主要在于投资或欣赏而非消费;标的是文物,且很多为特定物,与一般商品相异甚大;主体也非一般公众,而是有不同层次的古玩知识、基本相同的投机心理的中等以上富裕阶层。”[1]古玩交易之所以存在无限的魅力,在于古玩交易可以带来一般商品无法比拟的利益,现实交易中,一件古玩的转手差价可能要达数十万甚至数百万。所以,根据“‘风险与利益对等分配’的市场法则和伦理基础”[10],人们普遍接受对古玩交易中的购买者应较之于一般商品的购买者科于更高的注意义务,“买者自慎”也成为了古玩交易中广为接受的“行规”。
事实上,古玩交易原本就是在考量与权衡出售者和购买者依据各自所得信息而形成的鉴别能力,如果强求国家法律将个人鉴别能力所依赖和知晓的信息都全然告知相对方,古玩交易必将失去本有的魅力,从而也将不利于古玩交易市场的良性发展。诚如有学者所言,在古玩交易中,“要求合同当事人履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式的诚实信用义务,会使合同的一方的交易技巧及通过勤奋努力获得的优势变得一文不值,无法通过占有的信息创造价值,这不利于鼓励交易,也不可能达到公平的结果。”[11]是故,与一般商品交易不同,不宜肯定古玩交易中出售者就所出售古玩之真伪的说明义务。只要不是古玩出售者积极采取虚假的说明或隐瞒真相的手段使购买者陷入认识错误,对于购买者自陷于错误认识的,出售者对古玩真伪事实情况的单纯不告知,并不能该当于诈骗罪的欺骗行为,进而上述事案中的甲也就并不成立诈骗罪。
然而,需说明的是,当购买者对古玩重要事项的认识错误于某种程度上是因出售者的先前行为所引起,就不宜再否认出售者的说明义务。例如,倘若古玩店的店主因疏忽大意将一块标明为“真品”的告示牌放在了一个仿制工艺品的旁边,导致一般顾客都会误以为仿制的工艺品为古玩真品。此时,当出售者发现购买者误以为真品便以真品的价格购买,店主便居于了保证人地位,应告知购买者真相,若店主不予告知而继续以真品出售,则该当于不作为的欺骗行为④再如,集邮爱好者B某日于集邮爱好者A家中观赏A之收藏邮票,A出于虚荣心将其收藏的一枚高仿真邮票向B吹嘘为真品,B听了A的吹嘘后动心而向A提出以2万元价格购买该仿真邮票。此时,A因其先行的吹嘘行为而产生了向B告知该邮票真伪事实的义务,即具有保证人地位,如果A不告知而将邮票继续出售给B,也构成了不作为的欺骗行为。参见张明楷:《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此外,还需注意,由于人们对于黄金饰品如金项链、金戒指等的认识也往往端赖于个人的鉴别能力,有见解可能将黄金饰品的交易类比于此处的古玩交易。但在笔者看来,应当将两者区别开来。理由是,黄金饰品的交易在我国受到严格的管控,出售者与购买者之信息来源因管控的原因可能存在事实上的不对等,故对黄金饰品的出售者较古玩出售者应科于更多的义务。当然,对于黄金饰品涉及古玩性质的,可适用古玩交易的规定,而除此之外,不能认为出售者也不存在对黄金饰品之真假的说明义务。如果购买者对黄金饰品本身是现代商品未发生认识错误,而对其成分构成即是否为黄金发生了认识错误,此时出售者都具有说明义务的保证人地位,而不考虑这种认识是否由出售者的行为所引起,都可成立不作为的诈骗。
三、难题2及破解:基于怀疑的认识错误与交易中诈骗罪的认定
(一)被害人解释学与基于怀疑的认识错误
从前述诈骗罪的行为构造可知,受骗者陷入认识错误也是诈骗罪成立的独立要素之一。错误,顾名思义,即为认识与事实真相的不相一致。通说认为,诈骗罪的既遂需要受骗者基于认识错误而交付财产,倘若行为人不是基于认识错误而是基于怜悯或同情交付财产,则不成立诈骗罪既遂,但可成立诈骗罪的未遂。本来,理论与实务均已认同,被害人对陷入认识错误是否有怀疑,并不影响诈骗罪之陷入认识错误要素的认定,也不会影响诈骗罪既遂的成立[12-13]。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被害人解释学在德国的兴起,被害人基于怀疑的认识错误能否该当于诈骗罪之陷入认识错误,于理论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德国的阿梅隆教授便是最早将被害人解释学和诈骗罪构成要件的解释相结合的学者。他提出,当被害人产生具体化的怀疑时,就不宜认为还存在陷入认识错误,自然不能以诈骗罪的既遂论处;此外,在“客观上存在足以令人怀疑的事实,主观上被骗者也确实对事实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仍将自己的财产交付给他人支配,便可以认为被害人足以保护其法益”,“评价上属于涉及风险的投机行为”,依法益保护的辅助性原则,应将此时被害人的法益排除于刑法的保护范围,即行为人不成立诈骗罪[14]345-352。这一见解在德国提出后,获得了诸多学者的认可与追随,例如有R·哈赛默、赫茨伯格、伯恩特·许乃曼等[14]356-373[15]。但同时,这一见解也遭到德国诸多学者的批判与质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无疑是克劳斯·罗克辛教授[16]。
(二)理论争议:基于怀疑的认识错误可否阻却交易中诈骗罪的成立
国内学者较为系统地将被害人解释学理论与诈骗罪之陷入认识错误要素进行结合分析,最早可能源于台湾地区的两位学者(王梅英与林钰雄)于1998年刊登在《月旦法学杂志》的《从被害者学谈刑法诈欺罪》一文。可以说,今日国内学者关于被害人解释学与诈骗罪之陷入认识错误问题的探讨,很大程度上都肇始于两位学者在该文章的开篇所精心设计的一则事案——名画伪画案。这则“名画伪画案”就涉及到在古玩交易市场中,购买者对出售者的欺骗行为产生了怀疑,但最终依然交付财产之问题的处理。该事案的基本案情是:“画廊经纪人甲向富商乙佯称其有张大千名画一幅,因欲移民加拿大结束画廊营业,急于将该画脱手,仅索价新台币20万,因该行情远低于市价,乙心生怀疑该画的真实性,但估算果为张大千名画,则获利丰富,因此与之交易,交付20万元予甲,事后鉴定该画为赝品。”[13]
熟谙古玩交易市场的人都知,诸如此类的事案在现实世界中可谓层出不穷。对于此事案,学者王梅英和林钰雄根据被害人解释学的观点得出结论为,“某甲固然施用诈术,引起某乙处分财物之行为,但某乙已心生怀疑,而且客观上亦有足以令人怀疑的事由,某乙却为求可能之暴利,疏于保护自己,因此,一方面并未陷于错误,二方面亦欠缺刑法保护之必要性,某甲因而不该当诈欺罪之构成要件;上开之解释,也符合国家刑法作为防制不法行为最后手段之基本思想。”[13]
然而,这一见解遭到其他学者的质疑与批判。例如,张明楷教授就这一点曾提出了四点质疑与批判:(1)诈骗罪虽然以被害人认识错误为要素,但并不意味着只要被害人怀疑了行为人所声称的事项的真实性,即可阻却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将被害人理论作为刑法的普通原则,并不妥当;(2)诈骗罪的特点在于被害人基于有瑕疵的意思而处分财产,因此只要被害人交付财产是基于行为人的欺骗行为引起的认识错误,那么就可以肯定被害人基于有瑕疵的意思处分财产;(3)虽然不可否认,乙之所以交付20万元给甲,也有基于“倘若果真张大千名画,则获利丰厚,因此与甲交易”的动机与目的,但被害人处分财产的动机不影响行为人诈骗既遂的成立;(4)如果认为以被害人乙产生怀疑时就否认乙陷入认识错误,可能会造成以被害人是否精明而影响诈骗罪既遂与未遂的不合理结局[2]116-118。
(三)破解:被害人是否曾经有所怀疑不影响行为人的行为性质
笔者也认为,虽然受骗者对行为人的欺骗行为产生了怀疑,但最终仍然基于认识错误而交付财物,原则上不应妨碍对陷入认识错误的认定。其理由可以从实体法和诉讼法两个角度加以论证:
第一,实体法的角度。诈骗罪的成立需被害人基于认识错误而处分财产,是故只要被害人最终是基于认识错误而处分财产即可认为成立诈骗罪的既遂,至于过程中被害人是否曾经有所怀疑并不影响行为人的性质。当然,倘若被害人最终不是基于认识错误而是基于他者的原因(如怜悯、同情等)处分财产,不存在诈骗罪既遂的问题,但这已然超出了怀疑问题所讨论的范畴。基于怀疑的认识错误,无论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都归属于认识错误,并不影响诈骗罪既遂的成立。此外,以刑法中的法益保护辅助性原则否定具体怀疑情形下诈骗罪的成立,显然过高评价了诈骗罪中陷入错误的法律地位,因为众所周知,如果行为人的欺骗行为足以使他人陷入认识错误,即使被害人最终未陷入认识错误,也可能成立诈骗罪的未遂。
第二,诉讼法的角度。从被害人解释学论者的主张来看,被害人解释学论者也并非倡导任何有怀疑的认识错误都否定诈骗罪的成立,一般认为,只有当怀疑是具体的时候,才否定诈骗罪的成立,抽象的怀疑、模糊的怀疑不否定诈骗罪的成立[14]347361。然而,实践中根本无法区分具体的怀疑与抽象的怀疑。两者的界限不仅十分模糊,且事实上也难以证明被害人在当时具体情境下究竟是基于具体的怀疑还是抽象的怀疑。当被害人由于欺骗而遭受财产损失时,基于本能的驱使,多数情形下也只可能声称自己因行为人的欺骗行为而导致认识错误。所以,是否是具体的怀疑很大程度上需依赖于被害人的供述,这在目前因为现代刑法不断强调对行为人责任原则的要求而导致诉讼证明已渐陷入尴尬的境况下,再增加司法机关对主观方面的认定,恐有难以承受之重。
职是之故,不论古玩交易中的购买者是否对交易标的即古玩产生了真伪怀疑,只要其最终仍基于认识错误而处分财产,即可成立诈骗罪的既遂。对于“名画伪画案”来说,尽管乙曾心生怀疑,然毕竟最终还是陷入认识错误而处分财产,所以甲仍然要承担诈骗罪既遂的责任,但考虑乙本身存在较大过错,量刑时可以适度考虑减轻甲的责任。
此外,我国有学者认为,司法实践之所以长期以来对古玩交易中涉及欺诈的行为不作为诈骗罪处理,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被害人对陷入错误已有所怀疑,即“购买者在购买古董时,往往明知自己购买的物品可能是赝品,但在利益的驱动下侥幸地购入‘文物’;而在那些通过碰‘运气’,期望能以较低价钱购入具有较高价值古董的‘淘宝’行为中,购买者的这种投机心理表现的尤为明显。此时就很难说购买者被骗,故而也就难以认定出卖者的行为成立诈骗罪。”[12]但事实并非如此。通过笔者在“北大法意”和“北大法律信息网”检索出与涉及古玩交易诈骗的50余份刑事判决书来看⑤在“北大法意”和“北大法律信息网”的案例库中输入案由“诈骗罪”和关键词“古玩”或“古董”,可找到相关判决60余份,剔除重复的,剩余约50余份。最后检索时间:2014年5月11日。,检察院或法院并没有将被害人可能对行为人声称的事项存有怀疑作为诈骗罪既遂或成立的判断要素之一。当然,被害人在交易中是否存在明显过错,多数情况下是被告人请求从宽量刑的重要依据。在笔者与实务中部分检察官与法官们的交谈中也发现,几乎很少有人知晓“被害人基于怀疑的认识错误能否阻却诈骗罪”这样一个理论争议。的确,尽管在实践中绝大多数涉及古玩欺诈的行为都未受刑罚处理,但这并不意味着是基于被害人解释学理论的影响,两者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联。那种认为目前我国司法实践已然考虑到被害人基于怀疑的认识错误可否定诈骗罪成立的观点,不过是理论理由的一个虚构。
四、难题3及破解:交易中诈骗罪之主观故意的判断
(一)问题所在:主观故意诉讼证明的困难
诈骗罪的成立除了在客观上须要符合诈骗罪的行为构造外,在主观上还须具有诈骗罪的故意和非法占有的目的[17]。由于我国《刑法》第14条对于何为“故意”已作出明确规定,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故理论上对于诈骗罪故意的内涵,并无明显争议。但理论上不存在争议并非意味着在实践中就不存在问题,由于理论与实践对二者关注点的不同,理论上对某问题的共识亦可能在实务中存在较大分歧。众所周知,犯罪的主观故意属于行为人的内心心理态度,除行为人以外,他人很难全然准确把握,所以实务中对犯罪主观故意的认定并非如理论上那么清晰明了。司法实践中诸多犯罪成立的判断,主观故意的认定往往都是最为疑难的问题之一。例如,我国现行《刑法》第348条的非法持有毒品罪、第192条的集资诈骗罪,等等。同样,对于诈骗罪之另一主观要素——非法占有的目的,主要的困难和分歧也存在于司法实务的具体认定中。
事实上,对于实务中的绝大多数诈骗犯罪来说,由于行为人的行为表征的主观诈骗意图较为明显,对于其诈骗罪故意的认定也非特别疑难,争议较大的主要是对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和信用证诈骗罪等罪之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但在古玩交易中情况似乎相反,非法占有目的一般并非司法实务认定诈骗罪之难点[9],有疑难的反而是诈骗罪主观故意的判断。之所以造成其主观故意认定的困难,这同样与古玩的特殊性存在莫大关联。由于古玩较之一般商品具有特殊性,其真伪、价值在很大程度上端赖于当事人的鉴别能力,而每个人的鉴别能力不同,对同一物品所做出的鉴别结论也可能存在差异。实际生活中,对于客观上为古玩赝品,但受鉴别能力之限制,肯定赝品为古玩真品的人并不少见,甚至相当专业的人士亦存在“打眼”的时候。是故,当司法机关着力于古玩赝品交易案件的侦查时,出售赝品之行为人多基于古玩交易的这一特殊性,主张当时因个人鉴别能力之限制而无法知晓所售古玩为赝品从而不具有诈骗罪的主观故意,导致司法机关对于古玩赝品交易中是否存在诈骗罪故意的认定陷入僵局。例如,几年前在网络上讨论得沸沸扬扬的“南昌首例古玩诈骗案”,就曾因为取证的困难而多次退回检察机关补充证据,以至于此案由一审到二审经历了长达三年多时间[18]。
由于主观故意在诉讼证明上的困难可能会导致已侦查、起诉的案件在法庭上因证据不足而被法官判决为无罪,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为避免已侦查、起诉的案件在法庭上遭遇法官判决无罪的不利后果,多数遂在侦查、起诉阶段即以各种理由排除相关案件进入司法程序[19]。所以说,司法实践中存在着的大量涉嫌古玩诈骗的事案之所以未能进行刑事追诉,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行为人诈骗的主观故意难以有充分的证明,当然,部分情形亦可能是因本文“难题1”所展现的实体问题所致⑥客观地说,除了这两点原因之外,司法实践对于生活中大量古玩涉假案件不作为刑事犯罪处理的原因,也可能是由于刑事政策方面的原因,即广泛处罚在市场经济不规范情形下所大量存在的古玩售假行为,可能造成大范围人的锒铛入狱。。然而,如果仅因诉讼证明上的困难而放弃对为数众多的犯罪的处理,无疑会放纵和助长相关犯罪,从而也不利于古玩交易市场长期良序地发展;同时,犯罪的认定在另一方面也必须要受无罪推定原则的限制,不可贸然将无主观诈骗故意的人作为犯罪处理。是故,如何才能准确把握古玩交易中主观诈骗故意的判断,对于古玩交易中诈骗罪的认定至关重要,某种程度上这甚至可能超越我们对部分实体问题讨论的意义。
(二)破解:交易中诈骗罪之主观故意的具体判断
前已述及,故意属于行为人的内心心理活动,只有行为人本人最为清楚,因此从理论上来说,行为人对是否存在主观上的故意最为清楚,这进而导致行为人的供述是证明主观故意理论上的最真实的来源。事实上,古今中外,行为人的口供也历来是司法实践证明主观故意最易考虑的证据之一。但人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行为人常常会通过一切方式辩称自己不存在主观上的故意,即使行为人在侦查、起诉阶段如实供述了存在主观上的故意,亦可能于审判阶段进行翻供。是故,行为人口供在现代刑事司法过程中作为证明其主观故意的证据能力实际上极为有限的,且极易导致冤假错案,从而行为人的供述往往又是最不真实的来源。虽然说主观故意是行为人的内心心理态度,但这并非意味着除了行为人自己供述以外,对行为人的内心态度就无法予以认知。从哲学的角度看,主观往往见之于客观,“人的外部行为反映其内心秘密”[20],是故,诈骗罪的主观故意往往可通过外化的客观行为表现出来。
在笔者看来,古玩交易中诈骗罪之主观故意的判断就应该努力注意从外化的客观事实去认定。由于诈骗罪之主观故意的外化客观事实主要是行为人的欺骗行为事实,进而其故意的认定必须紧密结合欺骗行为事实来判断。如果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明知所出售的古玩为赝品(如低价从工艺品市场购得),并且向购买人谎称系在老家修高速公路、挖地窖时出土的文物⑦参见北京东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07)东刑初字第1号。,或者是谎称为盗墓所得文物⑧参见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08)浦刑初字第1796号。,或者是谎称为祖传古董⑨参见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0)金刑初字第202号。,或者是谎称为在工地干活时挖取的文物⑩参见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判决书(2012年)开刑初字第272号。,即可推定行为人具有诈骗的主观故意。古玩的来源往往可推定行为人是否存在明知,如果行为人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从现代工艺品店购得涉案古玩,并谎称是祖传等,那么即可推定认为行为人在主观上认识到了涉案古玩的真伪⑪当然,有一种情形须特别对待,也就是“捡漏”的情形,即出售者有理由相信他人低价出售的古玩为真品时,这时存在推翻上述推定的可能,但证据要求上应十分严格。;而交易时行为人的表述则可进一步判定行为人交易时是否存在故意的心理态度,即是否对结果持希望或放任的态度,如果行为人交易时虚构古玩的来源,使相对方对古玩的真实性陷入错误认识,则可推定行为人存在诈骗罪之主观故意。
此外,实务中常存困惑的一个问题是,行为人明知所售古玩是赝品,但于交易时不仅不明确告知购买者该古玩为赝品的事实,反而不断向购买者做出虚假的倾向性意见(如“个人认为是真品”);与此同时,行为人也会假意提醒购买者要“自辨真假”,或是在交易场所明显处悬挂一“真假自辨”的告示,对于此种情形能否认定行为人存在诈骗罪的主观故意?也许有人认为,此时古玩出售者已经将风险告知,购买者继续购买不能认为出售者存在诈骗罪的主观故意,所导致的风险理应由购买者自担。然而,笔者不能认同这一观点。笔者认为,不能仅因行为人交易时有提醒购买者要“自辨真假”的表述,或者交易场所有提示购买者“真假自辨”的警示语,就径直否定行为人存在主观上诈骗的故意。此时,判断是否存在主观上诈骗的故意,应将重点回溯到对古玩真伪认识较为重要的古玩来源问题[9],以及虚假的倾向性意见是否可使购买者陷入认识错误的程度上。如果说,从古玩的来源上已充分证明行为人明知所出售的古玩为赝品,但在交易中仍然存在向相对人表示古玩是“真”的虚假倾向性意见,并且出售者所表述的这种倾向性意见足以使购买者陷入认识错误或在相当程度上会强化购买者自陷的认识错误,就符合了诈骗罪的行为构造,进而也可认定行为人存在主观上的诈骗故意。即使此情形下的交易中,行为人有提醒购买者要“自辨真假”或事先在店内已悬挂“真假自辨”的告示,也不能掩盖行为人主观上的诈骗故意。这也再次说明,对于古玩交易中行为人主观诈骗故意的认定,应重点把握涉案古玩之来源的查明以及交易时行为人的虚假表述。
五、结 语
本文主要从古玩交易中的不作为能否该当诈骗罪之欺骗行为,基于怀疑的认识错误是否能够否定诈骗罪既遂或诈骗罪的成立,以及诈骗罪之主观故意的司法认定三个方面分析了古玩交易中诈骗罪认定存在的难题及破解思路。通过分析可知,对于目前理论上颇为关注的基于怀疑的认识错误是否能够否定诈骗罪既遂或诈骗罪的成立,于我国司法实践是很少受关注的。虽然说,目前司法实践对于多数古玩交易中涉嫌欺诈的行为未予以刑事追诉,但这并非意味着是怀疑的认识错误阻却诈骗罪成立的直接后果,两者不存在必然的关联,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更像由理论给实务强加的“伪难题”。
职是之故,事实上目前真正导致古玩交易中诈骗罪认定存在困惑的,从实体上看,主要是出售者对古玩之真伪的单纯不予告知能否以不作为的方式该当古玩交易中的欺骗行为;从诉讼上看,则主要是交易中诈骗罪之主观故意的认定。应当说,考虑到古玩拥有一般商品所不具有的特殊性,不宜肯定出售者有告知购买者古玩真伪的说明义务,故而单纯的不予告知不应成立诈骗罪中的欺骗行为,但倘若购买者陷入错误是由出售者的先行行为所致,就可肯定此时出售者的说明义务。对于交易中行为人主观上诈骗故意的认定,司法机关不能过分依赖口供,应积极从主观故意的外化客观事实即行为人欺骗行为事实进行推定,是故,对交易古玩之来源的查明和交易时行为人的虚假表述查明是为关键。
[1]吴万军.论古玩交易中的法律适用[J].政法论丛,2012(5):123-128.
[2]张明楷.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3]张明楷.刑法学[M].第4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889.
[4]林钰雄.刑法与刑诉之交错适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5]林东茂.刑法综览[M].修订五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18.
[6]吴耀宗.诈欺罪诈术行使之解析[J].月旦法学杂志,2008(163):50-64.
[7]吴正顺.论诈欺罪之行为要件[G]∥蔡墩铭.刑法分则论文选辑:下.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815.
[8]刘凤科.三校名师讲义——刑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390.
[9]刘婵秀.特殊物品交易中诈骗犯罪之司法判定试析——以一起真实的名画诈骗案为例[J].政治与法律,2011(3):53-59.
[10]高艳东.诈骗罪与集资诈骗罪的规范超越:吴英案的罪与罚[J].中外法学,2012(2):411-439.
[11]吴晓梅.古玩交易行规的适用及公权力干预的尺度把握——胡永华与易群华买卖合同纠纷案[J].法律适用,2009(7):82-84.
[12]缑泽昆.诈骗罪中被害人的怀疑与错误——基于被害人解释学的研究[J].清华法学,2009(5):107-121.
[13]王梅英,林钰雄.从被害者学谈刑法诈欺罪[J].月旦法学杂志,1998(35):96-103.
[14]申柳华.德国刑法被害人信条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
[15]伯恩特·许乃曼.刑事制度中之被害人角色研究[J].王秀梅,杜澎,译.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2):118-126.
[16]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M].王世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392-395.
[17]林山田.刑法各罪论:上册[M].修订五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13.
[18]南昌首例古董诈骗卖方被判刑[EB/OL].[2014-05-31].http:∥news.artxun.com/shoucangpin-1701-8504507.shtml.
[19]刘远熙.论推定对犯罪主观方面“明知”的证明意义[J].广东社会科学,2011(3):243-248.
[20]陈瑞华.刑事证据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