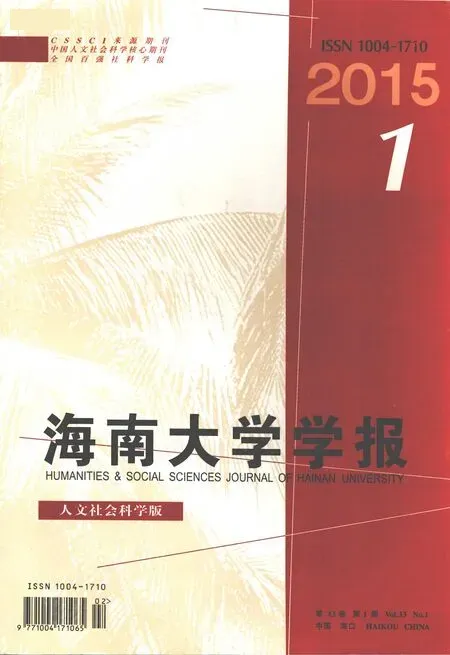鲁迅“还乡小说”的结构模式
2015-03-18张春燕
张春燕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730000)
现代文学史上,以鲁迅的《故乡》为肇始和摹本,出现了一类以漂泊在外的游子还乡为线索,以游子的视角叙说故乡的人事变迁,或以游子的新的价值观念对故乡进行价值审视的小说,因其典型的还乡结构和游子视角的运用,人们将之称为“还乡小说”。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乡土叙事中,故乡是自由野性的精神代表,以此达到与现代性文明对抗的目的,此类还乡叙事更带有精神原乡的意味;而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作家们的“还乡小说”则将故乡作为国民性话语的对象,虽然其间不乏乡愁的因素,但在其叙事中,乡愁是被遮蔽的存在。这类“还乡小说”与西方的“还乡小说”、中国传统的还乡叙事都有极大的差异。西方文学中不乏还乡模式的叙事,《奥德修记》就是以还乡为主线的故事,但以此为滥觞,西方叙事中的还乡更类似于“成长”,是英雄化的生命意志的呈现,比如《俄狄浦斯王》;中国传统还乡叙事则是以“落叶归根”、“衣锦还乡”为母题,也不同于京派文人的“精神还乡”追求。鲁迅的“还乡小说”是以还乡者的所见所感为主要内容,通过陌生化的方式,呈现老中国愚昧、麻木和奴化的精神面貌,“小说中所体现的现实与传统、新知与旧识、理想与现实的张力”[1]表达了作者的现代性焦虑。它们因其内部错位的时间、空间的对照,以及对于民族存亡的焦虑性表达而显出异质性。在鲁迅的小说系统里,典型的“还乡小说”为《故乡》、《祝福》、《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以主人公“我”的还乡为线索,形成了自我与故乡、生存与死亡、个人与历史等不同关系交织的小说群,并建构出了鲁迅对于故乡、国民、历史与自我的话语。
这些“还乡小说”之所以呈现出迥异的话语,与其文本的结构模式是分不开的。所谓小说的结构模式,是“指在较广范围内相对稳定和通行的各种总体结构方式和形态。例如:情节型结构、心理结构、散文化结构、套层结构,多视点结构等”[2]。鲁迅的“还乡小说”采用了类似“套层结构”的模式,即在叙述主体讲述的故事之中,套着另外一个故事。这一结构模式开启了多维度的话语空间,并以“我”与故人、故人与故事、“我”与故事之间的复杂对话关系生成新的结构,呈现着不同的关系和话语向度。在鲁迅的“还乡小说”文本中,这一结构模式以故乡、“我”、故人、故人讲述的故事(以下简称故事)之间的交错的关系构成了稳定的三角形结构,见图1。
叙事者“我”的言说对象是故人,意在建构一个启蒙话语中的他者的故乡;故人又在讲述一个与自己息息相关的故事,从情感和伦理的角度反观自我与故乡的关系;而故人讲述的这个故事本身也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对生命和历史本质的深度阐释。在这一结构中,实质上有三个不同的叙述者,从三个不同的维度上展开言说,并形成了三个彼此联系又独立的话语场。读者也被不同的讲述者的话语意向推至各种言说者的情感中心。于是,构成这个三角形的三个点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关系,同时,它们都指向故乡这一结构核心,与之发生着更为紧密和复杂的关系。鲁迅的“还乡小说”就是在这种复杂缠绕的关系中形成了具有内在逻辑的叙事结构。本论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分析这一三角形结构中各个向度上的内在关系,进入到鲁迅“还乡小说”的精神内里。
一、陌生化的故人相遇
鲁迅的“还乡小说”中,还乡只是小说的起因,还乡者与故乡的直接遭遇却是借由故人相遇的模式来展开的。这些众多的故人相遇的场景既是小说的展开背景,也是还乡事件本身。不同的还乡者“我”渐次遇到闰土、祥林嫂、吕纬甫、魏连殳,形成了“还乡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的叙事展开的维度,这一层次的对话是在“我”—故人—故乡的结构中实现的。由这一维度出发,叙事目的是国民性话语的建构,一改传统诗文中“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的怀乡之情,也绝不同于“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沧桑之感,鲁迅的结构方式是将相遇的故人之间的陌生提升到价值比较的话语层面。作者不断突出“我”与故人的对立性:“我”不论是面对闰土、杨二嫂、祥林嫂,还是面对吕纬甫、魏连殳,故人之间都存在着隔膜感。“我”在闰土面前感受到的是“厚障壁”;在杨二嫂所掌握的故乡话语面前处于失语状态;对于祥林嫂的追问,“我”无法回答,落荒而逃;甚至面对与“我”境遇相似、具有“我”自己的某些人格的吕纬甫和魏连殳,“我”与他们也始终保持着理性的心理距离。鲁迅将所有的故人相遇都推置到一个陌生感笼罩的场域里,传统叙事中故人相见的知己模式完全被重构而呈现出异质性:作者以“增加感觉难度和感觉时间的困难形式的手法”,达到“破坏感觉自动性”的效果[3]。异质化的相遇模式造成了话语的断裂,“我”与在乡的乡民(闰土、杨二嫂、祥林嫂)被分隔在两个并置而断裂的文化空间中,国民性、社会本质、道德伦理等问题在这种断裂中生发出来。在这一关系结构中,基本的叙事框架是“我”以理性主体出现,发现了自我与故人丧失了沟通,并由此引发“我”的出走。而“我”与吕纬甫、魏连殳的陌生,不在境遇与认知层面,甚至也不在于精神选择方面,而是在生命承受强度和精神意志方面。吕纬甫和魏连殳同样是故乡的出走者,但其出走行为遭遇到全线溃败。如果说“我”的精神本质是异乡人,那“我”与吕纬甫和魏连殳的陌生化实质是异乡人与佯装忘记和放弃自己异乡人身份的乡民之间的内在紧张。“我”与在乡的故人之间的交流失效与吕纬甫、魏连殳的理性行为的溃败相互印证,而他们的溃败以及生命力的丧失更加剧了“我”与故乡的决裂,这种精神决裂将“我”与故乡之间因价值冲突引发的出走行为上升到寻路的意志选择。“再次出走”成为鲁迅“还乡小说”的典型特征,并以此说明故人相遇的模式成为“我”精神成长的关键性事件。
还乡和出走的行为模式意味着在故乡之外有另外一个文明世界,故人相遇正是将“我”的还乡行为转化为以文明世界的价值范式为准则的审视、倾听、判断行为。故人相遇的陌生化处理,意在揭示归乡者“我”背后的文化范式与故人背后的故乡的意识系统(吕纬甫和魏连殳也最终被纳入到这一系统之中)之间的对抗。在这一结构中,故人成为了故乡的代言人,呈现着故乡的精神面貌和价值选择。“我”则作为一个理性主体审视着“我”面前的这个故人及其背后的故乡。很明显,“我”以自己与故人、故乡的距离,建构了一种以“我”为中心的关系。“我”是关系的中心,也是尺度,故乡和故人统统变为他者。这一结构模式中实质暗藏着“看/被看”的权力关系运作:“观者被权力赋予‘看’的特权,通过‘看’确立自己的主体位置。”[4]通过这种权力运作,以“我”的优势为主导、以“我”背后的价值系统为文明参照的故人相遇的陌生化结构成为叙事者在建构这一宏大的国民话语的既定模式。
其悖反也正在这话语建构过程中的不均衡性中表现出来。故人相遇模式是鲁迅设想的将启蒙话语介入现实生活的路径,但他者性建构直接摧毁了启蒙话语与故乡的交流可能。故乡被纳入到启蒙话语中,这一话语一经成型,故人不再是知己,故乡文化空间也不再是“我”可以安身的空间,还乡的重复,实则是将作为叛逃者和“反戈”者的理性自我变成了被放逐者。理性自我在建构启蒙话语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一新的价值范式带来的自我的身份焦虑:“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不管是外面的文明世界,还是故乡,“我”已经处于无地容身的境地。身份焦虑成为还乡小说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还乡小说”中“我”的直接出场表明鲁迅对于自我的疑虑进入了一个逃避不得的阶段。我”对故人的审视和言说彻底成为异己的反观,“我”以理性视角审视故人,同时,审视对象作为镜子,映射出“我”的存在,所以故人又是“我”的镜像。在这一意义上,故人相遇模式的设置其实带有虚化的特征和梦魇的性质,故人其实是分裂的自我,是在一个自省的场域里,将潜意识中的自我还原,以此进行“我”与自身的一场对话:闰土对于偶像的崇拜象征着“我”对于茫远的希望和将来的期待;祥林嫂对阴间归属的追问,在隐喻层面直指“我”的精神归属问题;吕纬甫的还乡经历,是对“我”的还乡之旅的补足;魏连殳也同样作为镜子照到“我”的情感牵绊。故人被建构成自我审视、自我反思的参照体。作者以对故人审视的方式,达到自我拷问的目的,并以此重新审视自我与世界(故乡)的关系。正是由于这种相遇和沟通的陌生化,使“我”反观到自身,从而看到了一个他者性的自我。这一自我在新的价值系统中的存在与故人在故乡空间中的存在并没有什么不同。认识自我成为鲁迅的又一难题。鲁迅试图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对于返乡的文本模拟来解决这一难题,但似乎他自己也在这一问题上陷入了一个循环的困境:由还乡—发现隔膜—出走的行为循环,进入了一个永远不能挣破的心理的甚至是认知的困境。循环的情境与心境,在形式上获得并暗示了潜藏的内容,那就是自我的存在的困境以及对于自我存在认知的困境。在这几篇激荡着自我身份焦虑的“还乡小说”之后,鲁迅试图在《伤逝》中集中清理这一存在之谜,其结果却是看到了在新的价值标准下,家的完全破毁,生命血性的沦丧,甚至低徊的忏悔也无法掩盖的道德缺陷,罪感和自审意识再次将自我逼向了死胡同。
鲁迅精神结构中的悖论性以启蒙者的身份疑虑呈现在“还乡小说”中,说明他在发现故人们的生命个体被文化规约而泯灭个体性的同时,也发现了“我”被另一种文化引导而丧失的独立性。鲁迅在呈现这两种文化的冲突的过程中,发现了生命个体的存在荒谬性。所以在国民性话语的建构中,对自我的追问成为反向的声音。“我”、故人、故乡的关系虽然依旧在以“我”为尺度的系统里,但“我”的身份焦虑成为一个重要的文本问题。在这一层面,“我”与世界的关系显然已经被反向建构。鲁迅正是在自我认知的迷障与绝望中开启了《野草》模式。从这一过程返溯回去,故人相遇所呈现出来的自我与自我的对话、追问、搏杀,实则是《野草》的预演,是《野草》的具象化。故人相遇在精神本质上,正是《影的告别》里的主体与影子的关系,是《墓碣文》自啮其身的死尸。
二、故人与故事
由故人相遇模式营造的国民性话语与自我的对峙向内部延伸,是以“故人讲故事”的结构实现的对于生命个体与历史、伦理、情感的关系的还原,是对于国民性原因以及个人在历史中的存在的追问和剖析。“故人讲故事”的结构设置在鲁迅的“还乡小说”内部呈现出令人惊异的一致:在以“我”与故人的相遇为契机的还乡叙事中,嵌套着一个故事:《祝福》里祥林嫂重复讲述阿毛被吃的故事;《在酒楼上》吕纬甫讲述着为小兄弟迁葬、为阿顺送剪绒花的故事,更深处还有吕纬甫与老发奶奶相遇时后者讲述阿顺死亡的故事;《孤独者》中魏连殳讲述祖母的故事;《故乡》里嵌着少年闰土的故事。这一故事虽然不是由故人讲述,但以回忆口吻舒缓道来的叙事者与面对成年闰土和杨二嫂时的叙事者明显带有不同的人格,所以少年闰土的故事也已经具备了这一结构的雏形。这些故事之所以能被提炼出来,是因为它们呈现大段的不被打断的独白性质。虽然出现在还乡模式之下,但故事本身的发生和结束都不在“我”的还乡经历之中,而是在“我”的还乡经历之外,开启了另外一个言说场域。故人以小说的另一个言说者的身份出现,他们与自己讲述的故事、故乡构成了“还乡小说”结构中的又一关系结构,即故人—故事—故乡构成的话语场。
这一层次突破了国民性批判话语的表象,进入到文化和历史的内质。故事不是“我”对于还乡经历的讲述,而是故人开始剖开自己的生存和情感的内里,讲述着关乎死亡的故事:死去的阿毛、小兄弟、阿顺、祖母。月光下少年的消失也正是美好生命的消逝。“故人讲死亡故事”的叙事骨架和话语内质不断重复过程中,故事的封闭的内核性质得到彰显。它们深嵌在文本内部,以被讲述的形式完成自己的言说。这是对于个体生命形式的还原。不同人讲述的封闭而循环的故事统统进入到死亡命题,重复性的死亡故事隐喻着生命的霉变和灵魂的死亡,直接指向的是故乡本身的一成不变和缺乏自省。
故人—故事之间的对话关系同样触目惊心:故事都作为主人公生命形态的镜像存在:少年闰土的故事是“我”的幻梦消失的镜像;阿毛被吃是祥林嫂被吃的隐喻和暗示;小兄弟和阿顺的死亡构成吕纬甫如死亡般存在的镜像;而魏连殳讲述的那个孤独的被欺凌的祖母的故事,更是魏连殳的“独头茧”的生命镜像。故事成为鲁迅“还乡小说”的话语内核,那就是生命存在形式与死亡形式的不断复制和衍生。“我”与故人互为镜像,故人与故事互为镜像,同时,故人与故事的关系在“我”和故人的身上得到复制:宏儿与水生将是迅哥儿与闰土的翻版;“我”与魏连殳的关系是魏连殳与祖母关系的继续。鲁迅“还乡小说”内部这种不断循环、纠缠不已的悲剧性更是在形式层面展示出生命的困境:生命形式、甚至文化范式的繁衍和复制。所有人都进入到不得超越的生命轮回。“我”、吕纬甫、魏连殳、故乡的乡民(闰土、祥林嫂、阿顺、祖母、甚至小兄弟、阿毛)与故乡之间的对话关系至此成为混沌的互为镜像:这是一个陷入了轮回与因袭中的生死场。在这一层面上,故人与故事之间的关系和结构正体现着从祖母到魏连殳的“丝”的实践过程。少年闰土到中年闰土的变化,祥林嫂生命的走向,都不会逸出这一结构;吕纬甫与魏连殳的结局,是鲁迅对于异乡人命运的文本实践,其设想依旧陷入了挣脱不得的存在困境:即便他们发现了故乡生命内核的死亡气息,也逃脱不得。
这一结构模式是如何体现了“丝”的作用的?其秘密就在于这个死亡故事本身潜藏的亲缘与伦理性。鲁迅的小说中,与参与到叙事中的“我”同时出现的意象还有久别后的故乡、家与路(行走)。这些意象总是集中出现在一篇小说内部,捆绑式的意象群在鲁迅小说整体中异常醒目。其中隐藏的重要关系就是故乡与家的同构性。《故乡》少年闰土的故事暗含着“家”的变迁,“我”与闰土的隔膜与“我”的家的颓败是一体的。《祝福》文本在“我”的叙事层呈现出祥林嫂与鲁镇的对峙关系,而在内部,祥林嫂一遍一遍重复的阿毛的故事,却是一个家破人亡的故事,将祥林嫂逼向魂灵之问的,更是亲人的相继死亡。同样,《在酒楼上》吕纬甫的讲述一开篇就是:“我曾经有一个小兄弟,是三岁上死掉的,就葬在这乡下。”这个迁葬的故事在故人相遇的层面上被放置在了批判的位置,但吕纬甫的讲述中暗含着家的破败以及兄弟的天人两隔。《孤独者》祖母的死斩断了魏连殳与寒石山的联系,但是祖母的死,也使他“放弃过去一直坚持的对爱承诺的有意义的生存,向世俗的无意义生存迅速堕落”[5],没有血缘的亲缘性虽然决定了魏连殳的悲剧走向,但也是他有意义的生命存在的唯一信仰。
故乡与家的同构是以主人公与儿子、兄弟、母亲、祖母的亲缘性象征个人与历史之间的继承性,而家与死亡的并置,则隐喻亲情对于自由的自我意志的扼杀。家成为文化象征符号,以其对于民族文化历史的记忆连接着现在的生命个体与民族历史。这个故事就这样触到了民族文化秘史的内核。代代相传的文化攫取了故乡全部的生命力量,它规约着身在其间的所有人的生命形态只能是麻木的生存。它不断吐出新的导向死亡的丝,造了无数的独头茧,将无数的人裹在孤独里面。“还乡小说”的国民性建构被还原为个人、历史、亲缘、伦理、死亡的交缠,这也正是“丝”的实践过程的还原。在故人的讲述层面,鲁迅的思考已经不是国民的劣根性,而是开始审视生命本身:身在历史中的存在命定性,以及爱与伦理的牵绊。
家的出现将“我”的讲述与故人的讲述分离成不同的话语倾向。“我”的言说指向的是自我与故人、故乡的对立关系,是对于乡土中国的理性审视;而故人的讲述则构成了对于理性审视的悖反,是自我与传统的斩不断的联系。所以由故人的讲述过程中透露出来的生命痛感,故乡才真正释放出情感力量,叙事者在理性审视,但作者设置的另一个话语端,即故人,在讲述故事时流露的对于生命痛楚的感同身受,成为结构文本的内在动力。当读者被带入到故人的话语向度上,人们感受到的是祥林嫂的丧子之痛,是吕纬甫在迁葬和送花过程中的温情和感伤,是魏连殳对于祖母的感激、爱、怜悯与愧疚。综观鲁迅的小说整体,可以说,只有在这一个还乡的系列里,才有了痛感传递。故人引导的话语意向体现出来的是对于个体生命存在和消亡的还原,具有贴近生命本身的力量。内核故事与其讲述者之间的亲缘关系斩断了“我”的理性的启蒙视角,当这个故事出现的时候,读者的视角立即从由“我”的讲述引导的启蒙观照,被反推到故人的立场上,从而凸显了“我”与故乡众人一致的对于生命的漠然,也因此间离了读者对于叙事者“我”的话语意向的认同。
三、在情感阻断和修补之间
情感阻断是鲁迅“还乡小说”中的暗藏的模式。从“还乡小说”的三角形结构(见图1)中,人们能看到一个被遮蔽的关系结构和言说区域浮出水面,即“还乡小说”中“我”与故事之间的情感阻断关系以及这种阻断中暗藏的鲁迅的精神结构的复杂性和生命选择的悖论性。竹内好认为鲁迅小说中“总觉得作者是在什么地方躲开了似的”,“他没把自己投放在作品里”[6]。在“还乡小说”的结构中,不论是“我”与故人,还是故人与故事,各个关系维度上都呈现出双重的话语意向,有着双向的价值思考,人们似乎的确无法把握作者的位置。但从“我”—故事这一维度进入,鲁迅本人的立足之处,反而明显了。
要进入这一情感阻断,首先需要将鲁迅纳入到这种对话关系中。需要指出的是,所有的内核故事:少年闰土、小兄弟的死、迁葬、顺姑、非亲生的祖母,都是鲁迅的亲身经历。这些真实发生在作者身上的小故事作为还乡叙事的内核被放置在故人的讲述中和“我”的审视中。吕纬甫讲述完小兄弟的故事的时候,紧接着一句:“——阿阿,你这样的看我,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了么?”显然,“我”对迁葬故事的反应是惊讶或者不满的。“我”不理解吕纬甫迁葬事件中对小兄弟的感情,也不理解送剪绒花这一行动背后的温情;同样“我”也不理解魏连殳在祖母去世时的大哭;“我”对于阿毛故事也绝不动声色。“我”与故事之间的疏离开启了“我”—故事—故乡之间对话的文本空间,并使“我”与故事站在双向的价值尺度上形成叙事的张力。阻断构成了话语的两极:一端是西方文明的价值框架之下“我”对于故事—故乡之间文化传承关系的审视和阻断;一端是由鲁迅与真实故事之间的血肉相连出发,从故事的亲缘视角对于“我”—故乡之间断裂的审视和修补。自我在国民、历史、文化、价值之中的理性选择体现着鲁迅生命主体的生成过程,但挣扎在共鸣与阻断之间的“我”却是对鲁迅自身处于故乡、亲情、价值世界中的悖论位置的还原。
这个话语场中,“我”与故事的情感阻断是故事的死亡性和因袭性得以言说的前提。正是因为情感阻断的设置,故事—故乡维度上营造的话语被推置在了“我”的审视之下。理性自我在远距离的审视中穿透故事的死亡性质,从故事与故乡的关系中突出了导向死亡的病灶本身,即文化和伦理的因袭性带来的对于自由生命的束缚。鲁迅的医学经验进入到他的创作中,其表现形式是“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7]526,而情感的阻断正是鲁迅的医者思维在文本中自我疗救方式的实践:通过理性自我审视伦理自我的创伤和痼疾,并剖开、切割和清理自己的身体和灵魂,以此自救。以“我”在故事(亲缘、伦理、传统、文化)面前的不介入,阻断传统的因袭性质,从而形成了读者与传统文化的阻隔关系,从而达到启蒙目的。
情感阻断的结构方式同时又是关于生存选择的哲学思考。情感阻断不是指向具体的情感和事件,而是指向某一种既定的文化形式和道义原则,是文本结构方式之上的生存方式的选择。是通过对传统的情感、文化、道义的摒弃获得自知和力量的生命存在方式。这一结构在鲁迅的文学世界中有无数的具象:《野草》中以防止自我“蹉跌在‘爱’——感激也在内——里”[8]而拒绝善意和施舍的过客正是这一结构方式的人格化;《铸剑》里的宴之敖者以头颅和身体的断裂为方式进行复仇。“还乡小说”中“我”与故事的阻断,也正是通过自我与传统的断裂完成对自我和国民的精神救赎。而这种血肉之痛的舍弃,才能够实现纯粹的、自由的、拥有战斗力的自我。其行为效果正是拒绝喝“没药调和的酒”,从“大痛楚”中获得“大欢喜和大悲悯”[7]178-179。这种对于断裂的痛楚的品味也正是鲁迅的生命哲学,“我”对于故事的拒绝,实则是将自己的痛苦外化于自身之后进行审视、自啮、玩味,以此获得对痛苦的驱除。
而在另一维度上,“我”与故事的情感阻断,则是故人相遇陌生化的实现路径。将“我”的价值观照从故事中撤离之后,故事本身的言说褪去了社会、价值色彩而呈现出自然状态的亲缘性。从这一视角反观“我”—故乡之间的断裂关系,其结果却是将离乡的现代知识者推到了道德的审判台。处于新的价值系统中的“我”在这种反向的审视下,暴露了冷漠和承担力不足的缺陷。“我”对闰土的断语“辛苦麻木”是那样武断和生冷,全然没有对于木讷但温情的少年好友的谅解;“我”在对待祥林嫂的时候更是进入到“与‘故乡’的伦理秩序的‘同谋’关系”[9]194;“我”面对吕纬甫的故事时情感的逃避;“我”对于魏连殳的不理解以及与其交往的整个过程都贯穿着某种偷窥欲望。决绝的情感阻断突出“我”在以新的价值系统评判故乡时的冷漠。这种审视之下“我”也被放置在审判席上。故事中隐含的传统人情和道德从被摒弃的绝地进行了反抗,揭示了“我”在新的价值系统中的存在危机。
所以作者不断突破这疏离的情感关系以修补“我”与故乡之间的断裂:《故乡》深情描写月光与少年;《在酒楼上》不惜笔墨地描写雪中废园,“我”与吕纬甫面对废园达到了情感共鸣;《孤独者》里也有“在后园的平坦处和一伙小朋友塑雪罗汉”的温馨笔触。如果说,“我”与故事的情感阻断是价值选择的需要,那“我”与故乡的情感修补则是鲁迅对于自我价值选择背后的道义的原点的深刻认知。记忆中的故乡在文本中的亮色提示读者,鲁迅所使用的西方的文明话语最终被纳入到了民族精神的重塑话语之中。这也说明了鲁迅是“在承认西方现代文明优越性的前提下接受科学、理性、进化、个人等价值观,从而对中国的文化传统予以抨击扫荡;但在精神归趋上又忠于民族(而不是文化),坚守着民族的平等与对立原则”[9]70-71。还乡系列之后的《朝花夕拾》甚至《故事新编》都是在此立场上的情感和精神的回归。
情感阻断的结构方式对应着鲁迅的精神结构的复杂性:理性的鲁迅审视着自身“对历史进程和新的价值标准的深刻理解及意识到自身与这一进程和价值标准的背离的心理矛盾”[9]114;而伦理的鲁迅比任何人都清醒地意识到,他的价值选择的自觉性正是源于他的对于传统道义的主动承担。正如研究者指出:“鲁迅是在显示的意识层次上以中国传统为一有机体而对之做无情的全盘攻击;但他对具体事实的确切感与他内在的精神力量,导致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说明一些传统的道德原则与价值。这些道德原则与价值虽然已经离开了它们在过去架构中的碇泊之处,它们却是他内在的、纯正的理智与道德的肯定的一部分。”[10]“我”与故事的情感阻断结构,实质是鲁迅的双向自审和双向罪感的精神结构:理性的自我以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审视故事,发现的是自我身在其中的罪感。他的价值选择上的优越感、崇高感并不能抵消他对于传统道德的自觉接受带来的罪感;由亲缘故事反观理性自我,发现的是情感的断裂、文化继承的断裂、甚至是归宿断裂导致的他对于自身来处的背叛的罪感。身在其中的罪恶感与情感背叛的罪恶感成为双重的心理折磨。这种撕裂的痛楚进入到小说文本中,即演化为一次次的决绝的自我摒弃和情感的清理,又一次次执拗地回归和修补。理性自我与伦理自我被放置在双重的质疑位置,这一生存选择中凸现出来的是生命主体的危机,鲁迅在审视自身灵魂的搏杀,并将双重的自我都放逐在荒原之上。他弃绝了自我与传统的关联,同时将自我从新的价值系统中剥离出来。因此所有的“还乡小说”都指向了“行走”,这正是鲁迅精神选择中体现的生命的韧性和强度。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在鲁迅的“还乡小说”系列中,“我”、故人、故事构成了稳定的结构关系。每一关系维度上都形成了独立的话语场,每一组对话关系中都存在着不同的言说意向以及悖反的价值向度,情感阻断形成了彼此拒斥的力量。各个维度上都有一个反推力,每一个话语场中都有双向度的言说和建构的倾向。“我”与故人的关系中,“我”以理性视角言说故人,意在建构一个启蒙话语框架之下的启蒙对象,但也被故人的映射反推到自我存在的荒谬境遇上;在故人与故事层面,故事在言说着故乡内部的死亡和生命形式的复制悲剧,但又将故事的讲述者带入到无法挣脱的亲缘关系中,直指自我与故乡、传统的割不断的联系;同样,在“我”与故事的关系中,“我”通过拒绝与故事的交流而阻断传统的因袭,又从故事的亲缘视角对自我与故乡的断裂进行修补。层层的言说指向,又进入到层层的反推。这个反推是鲁迅的惯用手法。是一种话语方式上的自我反抗性质。所以鲁迅的“结论常常是封上了打开,打开了又封上,封上了再打开”[11],竹内好所说的不知道作者在哪里,正是由于竹内好触摸到了鲁迅话语中的不同的言说意向。他进入到一个磁场,却发现了各个方向上的力量,作者的形象和位置反而不确定了。如果把握到鲁迅在言说意向中的情感阻断,那么,各个向度上的话语场域就豁然开朗了。鲁迅,即是这个阻断本身,正是在这个反推力上。
[1]夏岚.《故乡》及20年代的“归乡”类小说[M]∥上海鲁迅纪念馆.上海鲁迅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128-134.
[2]王先霈.小说大辞典[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1:25.
[3]艾亨鲍姆.“形式方法”的理论[C]∥茨维坦·托多罗夫.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蔡鸿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31.
[4]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349.
[5]汪卫东.鲁迅的又一个原点——1923年的鲁迅[J].文学评论,2005(1):156-164.
[6]竹内好.近代的超克[M].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91-94.
[7]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8]鲁迅.书信·250411致赵其文[M]//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77-478.
[9]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0]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158.
[11]王乾坤.鲁迅的生命哲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