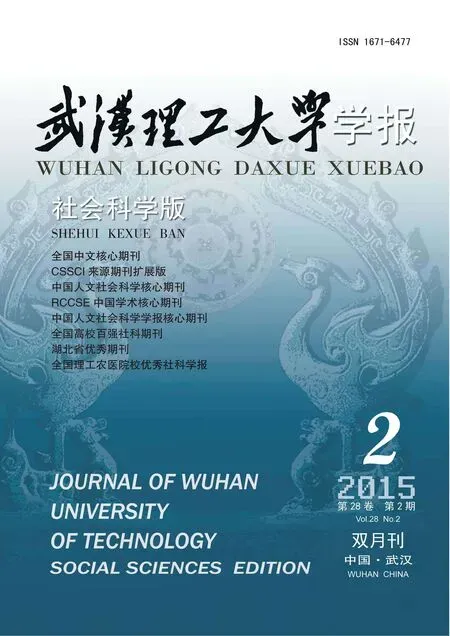卡尔维诺与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美学相似性探微
2015-03-18陈曲
陈 曲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卡尔维诺与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美学相似性探微
陈 曲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卡尔维诺与米兰·昆德拉都是当代享誉世界的小说家,他们的小说独树一格,颠覆了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传统。他们都倾心于小说美学的构建,且二者的小说美学在各具特色的同时也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他们对小说“轻”的召唤——简洁、精确的艺术,“思”的召唤——颠覆传统叙事性小说的思想小说,以及对“杂糅”的召唤——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打开了有关小说书写的新的可能性,为未来的小说发展指明了独特的路径。
卡尔维诺;米兰·昆德拉;小说美学;诗与思
卡尔维诺与米兰·昆德拉都是当代享誉世界的小说家。他们独具匠心的小说刷新了小说原有的样貌。与此同时,二人都对小说美学颇感兴趣,都拥有一套自己独特的小说美学范式,并为未来小说的样貌作了大胆预测。
一、小说是“轻”的艺术
按照卡尔维诺的说法,他与米兰·昆德拉都属于晶体派作家。当然“晶体”是一个包含多种意味的概念,但其中也突出地表明了其轻盈的气质,不属于沉重、驳杂、琐碎一脉。关于何为“轻”,在卡尔维诺《未来千年小说备忘录》里,有详细的描述:他从古希腊神话人物柏尔修斯说起。柏尔修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因为是他把女妖美杜莎制服的。美杜莎的头发是毒蛇,而一旦被美杜莎的目光注视过,不论什么事物都会瞬间被石化。那么柏尔修斯是如何成功切下美杜莎的脑袋的呢?柏尔修斯利用了反光。这样,他就不用直视美杜莎的眼睛,却又能看到她的行动。在他成功后,他并没有将美杜莎的脑袋丢弃,而是用布包好,将它背在自己的身上。“如果在战争中遇到危险,他只要抓住那由毒蛇构成的头发把血淋淋的头颅掏出来,那颗头就变成了他克敌制胜的武器。”[1]320
而这里的柏尔修斯在卡尔维诺看来就是小说家的化身。小说家不愿意直面坚硬的被石化的现实,而是选择用另一种轻盈的方式去反观和超越现实。但这并不是对现实的背离和逃避,正如卡尔维诺自己所说的:“当我觉得人类的王国不可避免地要变得沉重时,我总想我是否应该像柏尔修斯那样飞向另一个世界。我不是说我要逃避到幻想与非理性的世界中去,而是说我应该改变方法,从另一个角度观察世界,以另外一种逻辑,另外一种认识与检验的方法去看待这个世界。我所追求的各种轻的形象,不应该像幻梦那样在现实与未来的现实生活中必然消失。”[1]322
卡尔维诺通过神话找到了作家面对生活和写作的方式——“轻”。然而世界为何能以轻的方式呈现或者说轻的依据何在,卡尔维诺在古典作品中寻找依据。他在卢克来修的《物性论》中看到以原子为基础的宏大世界。在卢克来修看来,世间万事万物都是由原子构成的,那么这个世界就具有同一性和亲缘性。同时原子在依据自己重量下坠的过程中,会在无法确定的时间地点发生原子的偏离运动,从而原子与原子之间发生撞击。正是因为这种撞击,事物才得以产生,世界也是在这种原子的偏离运动中形成的。原子的偏离运动代表了一种对秩序的打破,对另一种逻辑的向往,同时也是轻逸的展现。紧接着,卡尔维诺又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看到了具有亲近性和流动性的世界。正是因为世界的这种流动与亲近,所以万事万物不是铁板一块的,而是可以随时变形,从一种状态变成另一种状态。那么这个世界不是稳定的,而是轻逸的。卡尔维诺声称自己在这里找到了“轻逸”的理论依据,并一路细数,拉出了卢克莱修、奥维德、卡瓦尔坎蒂、莎士比亚、昔拉诺、莱奥帕尔迪、卡夫卡等,构筑了“轻”的文学地图的重要据点。他将卢克莱修的《物性论》与奥维德《变形记》看成是对“轻”的最重要的文学解释和依据。卡尔维诺以这个为线索带出了一系列作家,并认为他们是“轻”的传承者和“原子论”的追随者,并最终在此印证了柏尔修斯神话所带来的启示:文学应该是对世界沉重感的超越。它应该始终是站在另一种维度与逻辑、另一种思考的模式与灵动的思维之上的。
可见卡尔维诺提出“轻”的概念是一个作家面对坚硬世界的一种反思;无独有偶,这也是米兰·昆德拉所认同的。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写道:“十九世纪昏睡过去的想象力突然被弗兰兹·卡夫卡唤醒,他完成了后来超现实主义者提倡却未真正实现的——梦与现实的交融。这巨大的发现并非一种演变的结果,而是一种意想不到的开放,这种开放告诉人们,小说是这样一个场所,想象力在其中可以像在梦中一样迸发,小说可以摆脱看上去无法逃脱的真实性的枷锁。”[2]20小说的结构与这个世界可以不同。小说不一定要按照所谓的真实性去安排它的发展,不一定要按照世界的样子去按部就班地描摹。只有小说以无比轻的方式、梦的方式呈现,才有可能接近所谓的现实。而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正是米兰·昆德拉和卡尔维诺所厌弃的。事实上,现实主义因为它的“事出有因”的因果关系为后来的小说家所诟病。现实主义看似真实的描摹世界,反而是一种极大的谎言。这种谎言建立在人们对世界稳固不变的认识和安全感之上,建立在一种轻信的态度之上。它为我们编织了一个充满因果逻辑的,从一开始就能推测结局的充满理性气质的世界。然而我们越来越发现现实主义最不现实,与此同时,它变得越来越沉重,在这里不允许梦的爆发,偏出因果律的旁枝,一切都要按照理性、常识去勾画。这条锁链紧紧勒住了小说家的脖子,有一度使得小说家不能呼吸。这也是卡尔维诺对新写实主义的背离的原因。或者说,现实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上的代言,它被认为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传声方式。而真正的小说应该与政治远离,不是充满惰性的。它应该逸出政治话语之外,从另一种角度去反观世界,用另一种认识和检验方法去看世界。卡尔维诺和米兰·昆德拉都在倡导小说的另一种逻辑、另一种角度。与这个充满惰性沉重的世界形成一种相反的张力。
二、小说是“思”的艺术
米兰·昆德拉曾明确地这样表示:“穆齐尔与布洛赫在小说的舞台上引入了一种高妙的、灿烂的智慧。这并不是要将小说转化为哲学,而是要在叙述故事的基础上,运用所有手段,不管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叙事性的还是思考性的,只要它能够照亮人存在,只要它能够使小说成为一种最高的智慧综合。”[2]21他在对小说提出另一种召唤——思想的召唤。同样,卡尔维诺对这个概念是极为推崇的,并付诸于实施的。他生前的最后一部小说《帕洛马尔》可以理解成一部思想笔记。在这部小说中,卡尔维诺将人物的情感、心理、社会层面的信息全部抽离,他只关注人物作为一个思想主体的存在。主人公帕洛马尔是谁、长相、身份、来历我们全然不知,我们感受到的仅仅是一个面对无际宇宙的孤独思考者。他思考的范畴小到沙滩里的沙、乌龟、海浪、小草,大到整个世界与宇宙。他将这些全部纳入到自己的思之范畴。
这样的一种小说书写方式是对19世纪带有强烈描述与叙述气质小说的一种反抗。19世纪的小说建立在严谨的理性大厦和因果律之中。人物永远是小说的主线。为了人物的真实,小说家必须给人物设置相应的细节的真实,所以人物一出场,就像拿着自己的身份证明一样,读者知道了他全部的信息。但米兰·昆德拉和卡尔维诺认为这样的一种人物与故事的设置似乎将小说最有意味的东西割除了,那便是思考。即便传统小说有思考,也必须是建立在繁琐的人物与事件设置之上的。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小说不能直接关注思想呢?为什么必须要借助于这“桥”的东西呢?小说为什么不能直刺核心呢?小说家们开始反思并逐渐将“思”纳入小说书写当中。
我们承认“思”与“诗”是一对矛盾的概念。二者之间的关系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定位。“思”与哲学的和谐关系似乎更加理所当然。文学往往与美的追求联系在一起。文学可以显示真理,然而与哲学或神学比起来,就要相形见绌。长久以来,文学依附于神学和哲学,仅仅因为它的独特的形象性和感性特质。柏拉图贬斥文学为影子的影子。然而我们可以明显感到,自从文艺复兴将“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后,人们开始对启蒙理性进行反思。余虹在《诗与思的对话——海德格尔诗学引论》中将西方思想发展分为三个阶段[3]:第一是原诗意阶段(前苏格拉底——柏拉图时期),思的基本样式是神话;第二是非诗意的阶段(柏拉图至康德),思的基本样式是神学与哲学,思鄙视诗;第三是向诗意之思回返阶段(后康德时期),思发生了“诗性的转向”。从康德以来,有一批哲学家将艺术或者说审美主义看成是人类最理想的归宿。叔本华和尼采将之推向顶峰。叔本华认为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无欲无求,只有在艺术的静观当中,才能达到此种状态。而尼采的生命美学将艺术和审美设为最高原则,艺术在这里得到了极大的彰显。而海德格尔把艺术提升到真理显现的方式的高度上,他说“艺术的本质或许就是:存在者的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4]65,“艺术让真理脱颖而出”[4]59。哲学上诗性的回归给小说思想的召唤提供了土壤,也可以这样认为,小说中的思想的召唤让哲学重新开始反观自己,反观真理发生的方式。既然艺术是真理发生的方式而不是其他,那么思想小说,或者说用小说去思考无可置疑。米兰·昆德拉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从塞万提斯开始谈起,借助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回顾,力证欧洲小说持续地发现存在并勘探存在。
而卡尔维诺也同昆德拉一样,受这个时代思想的滋养,认为小说是另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它与科学拥有同等的地位,成为了一种认识工具。而这种将小说认为是认识世界的工具的思想,卡尔维诺也是受到了意大利文学传统的滋养。从但丁开始,就致力于一个百科全书性质和宇宙学的工作。他试图通过词语来建构宇宙的模样,这是一个意大利文学中很深的传统。从但丁到伽利略,文学的概念被认为是一张世界的认知地图。对知识的渴望驱使着写作最终变成神学的、推理的、魔幻的、百科全书的或者被认为是自然哲学或变形的、视觉观察的。卡尔维诺想赋予小说一种世界地图的性质,通过以小说这种百科全书性质的文学来达到对世界的认识和对知识的获取。在《帕洛马尔》中,他完全是以对事物的认识为依托,去安排整部小说。主人公帕洛马尔在借助胡塞尔现象学方法认识事物失败后,不断探索,最终达到了与自我、与客体的和解。可见卡尔维诺与昆德拉都在强调思想的召唤。思想不再是拒斥在小说之外的东西,而是本该属于小说的一部分,甚至可以成为核心的部分。
三、小说是“杂糅”的艺术
华莱士·马丁在《当代叙事学》中将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的起源定义在了杂糅上。小说是一种对多种文学体裁的杂糅,是一种对多种内容的杂糅。杂糅这个概念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对小说最为一劳永逸的定位,而这个特质也受到了昆德拉与卡尔维诺的关注,并有着自己的发展。昆德拉在谈到布洛赫的《梦游者》时谈到了他的几个有趣的地方:多元历史主义、不同元素(诗句、叙述、格言、报道、随笔)的参杂。多元历史主义类似于庞大、渊博的百科全书。因为小说有一种非凡的融合能力:诗歌与哲学都无法融合小说,小说则既能融合诗歌,又能融合哲学,而且毫不丧失它特有的本性,小说有包容其他种类、吸收哲学与科学知识的倾向。这是米兰·昆德拉所欣赏的,同时他将这种多元历史主义继续发挥,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小说美学——一种小说对位法的新艺术(可以将哲学、叙述、梦幻联成同一种音乐)。也就是被后来很多学者认为的——小说中的复调。复调是昆德拉对小说这种可以涵盖大量内容文体的一种处理方式。昆德拉的复调小说首先强调的是对文体的一种杂糅:小说可以接纳几乎所有的文体类型,包括神话、历史、寓言、报告、论文等等文体,它可以和各种文体对话,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而极为相似的是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小说备忘录》里提到的最后一个特质——内容多样性,实际上就是在对小说杂糅性的一种强调。他以加达的小说《梅鲁拉纳大街上一场可怕的混乱》为例提出了自己“内容多样”的小说特质。卡尔维诺认为现代小说应该像百科全书,应该是作为认识的存在,并且是网罗世界各种关系的存在。
而这种百科全书般的杂糅特性是小说这门样式最为突出的特点。在小说的发轫期,拉伯雷的《巨人传》、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都有着一种试图杂糅万物并包蕴各种题材的气势。这样的特质在18世纪的流浪汉小说中也异常明显。在之后的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中,小说家们同样试图在自己的小说中达到一种对世界全方位的认知。比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作家们藏着宏愿,试图完成一本无所不包的书。而这样的愿望在20世纪依然存在甚至更为明显。布洛赫、穆西尔、普鲁斯特等等都带有这样的气质。
因为小说这种明显的特性——杂糅,卡尔维诺与米兰·昆德拉都将之推到一个重要的位置。然而杂糅如何完美实现?作家想在自己的书中达到包罗万象,那么就必然牺牲了文学自身的清晰性,小说最终无法完成。这个悖论如何解决?而两位小说家在面对这一问题时的解决方法又极为相似。卡尔维诺将内容多样的小说大致分为了四类:首先是单一的小说,像辞书中词条的说明,它可以在不同平面上作出各种解释。其次是内容多样的小说,即以众多的主体、众多的声音、众多的目光代替为唯一能思索的“我”。这就是米哈伊尔·巴赫金称为“对话”的模式,“狂欢节式的”模式。再次,这类作品非常希望能包罗一切,却找不到一个恰当的形式,划不清自己的范围,结果变成结构上未完成的作品,如穆西尔与加达。最后一类作品,则是相当于哲学中的非系统性思维,靠一句句格言,靠点状的、互不连接的思想火花来展开故事[1]412。卡尔维诺毫不犹豫地推崇最后一类作品,并认为这样一种相反相成,包容着世界复杂性却又结构上及其简略的小说才是小说发展的最好方向。而昆德拉也再不满布洛赫的未完成的作品中提出新的呼吁:第一,一种彻底简洁的新艺术(可以包容现代世界中存在的复杂性,而不失去结构的清晰性);第二,一种小说对位法的新艺术(可以将哲学、叙述和梦幻联成同一种音乐);第三,一种小说特有的随笔艺术(也就是说并不企图带来一种必然的天条,而仍然是假设性的、游戏式的、或者是讽刺式的)[2]84。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小说发展方向的规划极为相似。由于小说杂糅的特性,他们推崇百科全书,或者说多元历史主义,然而由于杂糅所带来的混杂性,未完成性是他们无法忍受的,他们都在致力于一种简洁的艺术,一种省略的艺术。形式的轻盈却包蕴着内容的驳杂。
四、结 语
在同样的时代滋养下的两位小说家,其小说美学有太多相似之处。小说经历了尴尬的被边缘化的境地后,卡尔维诺与米兰·昆德拉这两位有着理论自觉的小说家都在思索小说未来的发展走向。同样,他们对待小说的态度也颇为相似。卡尔维诺在诺顿讲坛的开篇便说“我对文学的未来是有信心的,因为我知道有些东西只能靠文学及其特殊的手段提供我们。 ”[1]317在《小说的艺术》中,米兰·昆德拉说:“……但我并不想预言小说未来的道路。其实我对此一无所知。我想要说的只是:假如小说真的应该消失,那并非是因为它已精疲力竭,而是因为它处于一个不再属于它的世界之中。”[2]22尽管二者的语气一喜一悲,但我们可以感觉到二者对小说自身发展的信心。
[1]卡尔维诺.卡尔维诺文集:第5卷:寒冬夜行人、帕洛马尔、美国讲稿[M].萧天佑,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1.
[2]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董 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3]余虹.诗与思的对话:海德格尔诗学引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16-26.
[4]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文 格)
On Similarities of Calvino and Milan Kundera's Novels Aesthetics
CHEN Qu
(SchoolofLiberalArts,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
Calvino and Milan Kundera are renowned novelists in contemporary world.They also go to the aesthetics of the novel structures.There are many similarities in their novel aesthetics.They put forward some new novel ideas of the “lightness”,“thought” and “hybridity”.It provides some new possibilitie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novel.
Calvino;Milan Kundera;novel aesthetics;poem and thought
2014-10-05
陈 曲(1980-),女,陕西省咸阳市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讲师,主要从事西方后现代小说美学研究。
I01;I054
A
10.3963/j.issn.1671-6477.2015.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