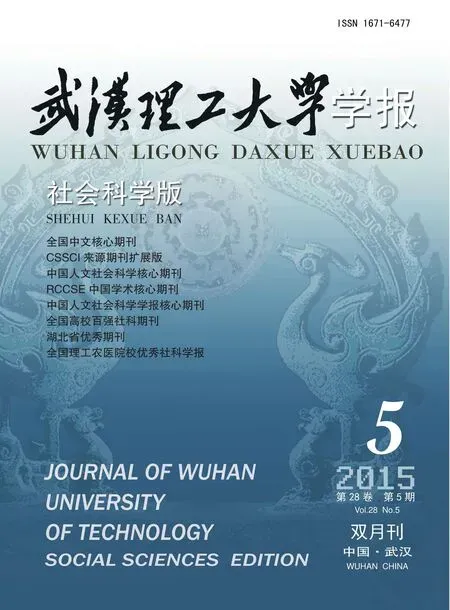莎士比亚与“天才”观念*
2015-03-18张同铸南通大学文学院江苏南通226019
张同铸(南通大学文学院,江苏南通226019)
莎士比亚与“天才”观念*
张同铸
(南通大学文学院,江苏南通226019)
莎士比亚在欧洲激起了激烈的争论,在新古典主义者看来,莎士比亚是个野蛮人,在那些力图要摆脱法国文学影响的人们看来,莎士比亚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类型,这其中,英国人最先得益,其次便是德国。围绕莎士比亚的有关讨论的最大成果,便是“天才”观念的成熟。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为“天才”定义,尽管没有明言莎士比亚和新古典主义,但他的“天才”观是完全站在对莎士比亚认同的基础上的。
莎士比亚;天才;新古典主义;康德
晚年伏尔泰常常攻击莎士比亚,他指出,仅仅受本民族读者欢迎的作者不可能是伟大的及规范的作者。与之相对应,他反复强调法兰西的趣味——其代表是新古典主义,是欧洲趣味的核心,其他民族则只能对这种欧洲趣味作一些贡献。法语在欧洲成为贵族的语言,这与新古典主义的影响是不无关系的。但是由于高度重视规则,重视语言的典雅,对于创作反映生活的广泛性和自由度都带来了很大的束缚,同时也对各国民族文学的形成造成了桎梏。在新古典主义者看来,莎士比亚是个野蛮人,但是在那些力图要摆脱法国文学影响的人们看来,莎士比亚正是他们所需要的类型,这其中,英国人当然最先得益,其次便是德国,而围绕莎士比亚的有关讨论的最大成果,便是“天才”观念的成熟。
一、围绕莎士比亚的争论
卡西勒说:“18世纪英国文学每当讨论到天才问题,每当它试图规定天才与规则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抽象推理便立即转到了具体事例。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碰到了两个名字——莎士比亚和弥尔顿。可以说,他们构成固定的轴心,关于天才问题的一切理论研究便绕之旋转。作家们都力图通过这两个伟人的范例去把握天才的最深刻的本质;可用以描述天才的一切可能的理论,都适用于莎士比亚和弥尔顿。”[1]
在莎士比亚和弥尔顿这两人中,也许莎士比亚要更接近于天才的本质。因为有关这位莎士比亚,就目前所知道的资料而言,他出生于乡间小镇,只受过有限的一些教育,20岁左右到伦敦谋生,在戏院看守马匹和做些杂务,又作过演员,演了一些次要角色。由于在戏院工作,能有机会接触戏剧表演,所以掌握了戏剧创作的一些程式,逐渐参与戏剧脚本的改编,很快就脱颖而出,名声大噪。这样一位成长背景的乡间小子,却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英国文学界最耀眼的明星,这种情况如此神奇,甚至引起诸多研究者的怀疑,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这位创作了那么多彪炳史册的作品的莎士比亚?
按照托尔斯泰的研究,莎士比亚在他的那个时代并不受英国人待见:“在18世纪之前,莎士比亚在英国不但没有特殊的声望,他得到的评价还低于其他同时代的剧作家,如本琼森、弗莱彻、鲍蒙特等人。这种声望肇始于德国,再从那儿转回英国。”[2]这个看法比较偏颇,与托尔斯泰出于个人趣味或宗教信仰而讨厌莎士比亚有关。在莎士比亚当时,的确有人出于嫉妒而攻击过莎士比亚,称他为“一只暴发户乌鸦”,骂他是“地地道道的打杂工”,写了几句虚夸的无韵诗就自以为能同最优秀的作家媲美。但这些只证明了莎士比亚的影响之深,事实上托尔斯泰所提到的受欢迎的剧作家之中的本琼森就对莎士比亚极为推崇,他在为第一部莎士比亚戏剧集写题词的时候由衷地说:“因为我必须扯上你同辈的伙伴,指出你怎样盖过了我们的黎里,淘气的基德、马洛的雄伟的笔力。”这些戏剧家与莎士比亚同时代而稍早,可以说是他的前辈,琼森认为莎士比亚已经超过了他们。他将莎士比亚与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等希腊大家相提并论,“得意吧,我的不列颠,你拿得出一个人,他可以折服欧罗巴全部的戏文。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3]这是发自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声音,值得特别重视,可是遗憾的是托尔斯泰由于个人趣味的不同,无视这些话语。
比莎士比亚稍晚的爱德华杨格盛赞莎士比亚、弥尔顿等人,认为莎士比亚是“现代人中最大的星辰之一”,他学问并不多,这一点本琼森也指出,他不大懂拉丁语,更不通希腊文,但他属于天才,天才是自然的门生,并不需要进什么专门的学校,他们的作品具有高度的独创性。天才是巨匠,学问只是工具,而且这种工具并不能总是起到积极的作用。当你对古人的作品过分崇拜、过分敬畏的时候,它反而会压制你的才能。“学问咒骂自然真率之美和无伤大雅的细微疏漏,并为常常是天才无上光荣的渊源的自由,立下种种清规戒律”。[4]13而像莎士比亚这样的天才,他不用以乏味的模仿降低自己的天才,尽管他有诸多缺点,知识不多,但他精通两部书——“自然的书和人的书”,因为他,“不列颠舞台上至少有和希腊舞台上同样多的天才”。[4]39即使是德莱顿,作为一位法国新古典主义的推崇者,也认为莎士比亚是个例外:“在所有近代或在古代诗人中他具有最广阔、最能包涵一切的心灵。自然的一切总是在他面前,而他随手招来,并不费力。他描写任何东西,你不但看得见,还能摸得着。那些指责他没有学问的人倒是恭维了他;他是天生有学问的;他不需要戴上书籍的眼镜去窥察自然;他向内心一看,就发现自然在那里。”[39]77他尊崇莎士比亚,但认为莎士比亚是不可模仿的,他可以不需要学问与遵守规则,可是其他人则不可以,很显然不是每个人都是“天生有学问的”。
不过托尔斯泰的看法在另外一种意义上是合乎现实的,在莎士比亚同时代以及稍后,固然有琼森、杨格等人为他辩护,但是可以想见的是,必然有与之对立的一派,这在杨格的《试论独创性作品》中其实就已经隐含了,那些缺乏天才,更注重学问的人咒骂莎士比亚,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琼森和杨格的观点是对这些人的回应。这也可以说莎士比亚在当时的英国远远没有达到声誉的顶峰。即使是德莱顿,他在盛赞莎士比亚的天才之后说:“他往往平凡无味,有时调侃之词流于俏皮,严肃之语变为浮夸。”[5]77这在17世纪之后更为明显,其时在欧洲文学界占据统治地位的是法国的新古典主义戏剧,以及他们的创作法则,尤其是“三一律”。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莎士比亚完全是个不通任何规矩的“野蛮人”。1663年,一名叫索比尔的法国人以半外交的官方身份访问英国,回国后写了一本叫《航行》的小册子,用很不礼貌的口吻报道了英国的戏剧活动:“他们的喜剧,不会受到法国人的欢迎。他们的诗人,根本不考虑地点和与时间的统一,他们的喜剧情节,从头到尾约需25年。第一幕,王子刚刚结婚,下一幕他的儿子已开始游学与建功立业了。”[6]法国人之所以如此取笑英国戏剧,是因为他们的新古典主义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受其影响,英国新古典派批评家托马斯莱梅攻击莎士比亚的《奥赛罗》,说它是“淡而无味的残酷的闹剧”。[7]16
不懂规矩的莎士比亚狠狠地折磨了他的英国同胞,同时也包括法国的作者和文学批评家,其中就有著名的伏尔泰。作为法国新古典主义后期最优秀的代表,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18世纪法国文学、哲学界的关键人物,伏尔泰曾对英国文学给予了很大的注意,尤其是他对于莎士比亚发表了很多值得深思的观点。伏尔泰在1726年三十出头的时候因为得罪了法国的贵族,被放逐到英国居住了两年。在英国居住期间他会见过蒲伯、斯威夫特、杨格等人,并观看了不少英国戏剧。当时的伏尔泰刚刚创作了史诗《亨利亚德》,也许是因为年轻气盛,该史诗违反了新古典主义的严格规则,他急于在英国文学中发现例证,从而有助于说明他的观点:现代史诗必须有别于古代史诗,艺术手法带有一定的地方性,它深值于民族趣味之中。这时他发现了莎士比亚。他认为莎士比亚尽管丝毫不懂戏剧艺术的规律,也没有高尚的趣味,但是“他创造性地发展了戏剧。他具有充沛的活力和自然而卓绝的天才。”不过这位作家是不可模仿的,对于那些抄袭他的人,“在莎士比亚作品里获得成功的地方,却在他们的作品中被喝倒彩。”[8]但是晚年的伏尔泰对莎士比亚越来越反感,甚至非常后悔自己年轻时对莎士比亚的推许,他说:“令人惊骇的是这个怪物在法国有一帮响应者,为这种灾难和恐怖推波助澜的人正是我——很久以前第一个提起这位莎士比亚的人。在他那偌大的粪堆里找到几颗瑰宝后拿给法国人看的第一个人也正是我。未曾料到有朝一日我竟会促使国人把高乃依和拉辛的桂冠踩在脚下,为的是往一个野蛮的戏子脸上抹金。”[7]48
二、莎士比亚在德国的影响
法国新古典主义在创作实践和理论上都以古希腊、罗马为典范,取得了高度的成就,产生了几个代表性的卓越作家,最主要的是高乃依、拉辛和莫里哀。他们的作品语言典雅、矛盾集中,在遵守严格规范的同时创造了优秀的作品。因此法国的新古典主义很快成为欧洲文学的标杆,在各国尤其是在上流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由于莎士比亚的巨大存在,英国人便能够跳出新古典主义的理论束缚。无论是德莱顿,还是蒲伯或约翰生,他们都强调规则的重要性,认同法国人的艺术趣味,但他们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强调天才或自然。而约翰生则是公认的莎士比亚评论专家,他编过《莎士比亚戏剧集》,并且为《莎士比亚戏剧集》写过《序言》。约翰生说:“诗人的任务不是考察个别事物,而是考察类型;是注意普遍的特点和注意大体的形貌。”[5]87如果说在这里我们还看到布瓦洛的影子的话,那么莎士比亚则让他成为约翰生。他对莎士比亚的戏剧作了很高的评价:“莎士比亚超越所有作家之上,至少超越所有近代作家之上,是独一无二的自然诗人;他是一位向他的读者举起风俗习惯和生活的真实镜子的诗人。他的人物不受特殊地区的——世界上别处没有的风俗习惯的限制;也不受学业或职业的特殊性的限制,这种特殊性只能在少数人身上发生作用;他的人物更不受一时风尚或暂时流行的意见所具有的偶然性所限制:他们是共同人性的真正儿女,是我们的世界永远会供给,我们的观察永远会发现的一些人物。”[9]在这些话语里仍然可以看到新古典主义的趣味,可是由于莎士比亚,约翰生对“三一律”作了猛烈的抨击。新古典主义者认为戏剧要做到逼真,那么同一个舞台,第一幕在亚历山大里亚,第二幕就不能在罗马。约翰生则提醒说,舞台不过是舞台而已,观众绝没有以为它就是亚历山大里亚。既然如此,假如第二幕把它叫做罗马,有何不可?对于时间不超过24小时的限制,约翰生指出:“万事万物中,时间对于幻想是最唯命是听的;幻想几年的度过和几小时的度过是同样不费气力的事。在回想中我们很容易把实际行动所需要的时间加以压缩。因此当我们看见对实际行动所作的戏剧模仿时,我们也就乐于容许这个时间的被压缩了。”[5]90在“三一律”中,约翰生唯一认为应该坚持的就是情节一致律了。这位古典主义趣味的支持者,同时又是莎士比亚戏剧的鼓吹者,发现自己远离了自己一直被教导的原则,不无担心地说:“我被我自己的大胆几乎吓住了”。他不自觉地动摇了自己所力图维护的新古典主义的堡垒,而浪漫派即将从堡垒的缺口登上历史舞台。
正如托尔斯泰所指出的,在英国之外,德国人从莎士比亚那里获得了无数的灵感,他们从他这里取得了为建立完整的德意志文化所必须的精神支持。从16到18世纪,德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还比较落后,他们起初是积极向法国学习的。用莱辛的话说就是:“德国人不想要自己的性格。我们仍然是一切外国东西的信守誓约的摹仿者,尤其是永远崇拜不够的法国人的恭顺的崇拜者;来自莱茵河彼岸的一切,都是美丽的、迷人的、可爱的、神圣的”。[10]这种忽视德国自身民族传统的做法必然会引起反弹,莱辛便是其中最早的一位。为了与法国的宫廷趣味相抗衡,他把目光转向英国,提倡学习莎士比亚。法国新古典主义矫揉造作,其笔下的人物“都喘着英雄主义的粗气,甚至连不应该有英雄主义气质或确实没有英雄主义气质的人物——作恶者——都是如此”[11]161,莎士比亚与他们比起来要平民化得多,因而更加鲜活,更加具有时代气息。正如伏尔泰所注意到的,在拉辛笔下的军人是这样描述安静的夜晚的:“啊,万物俱息,军队,风儿,海王星。”可是在《哈姆莱特》中则是:“连只耗子的动静也没有。”伏尔泰曾对此评价:“是的,先生,一个卫兵在哨所或许会这样回话;但在舞台上当着一国显贵的面却不会。显贵们吐属庄重,因此在他们面前,他应当用同样的气度来表达自己。”[7]49这里充分反映了他的宫廷趣味和描写准则。莱辛认为和法国作家比起来,莎士比亚要伟大得多,他把莎士比亚和荷马相提并论,说:“关于荷马的一句话——你能剥夺海格力斯的棍棒,却不能剥夺荷马的一行诗——也完全适用于莎士比亚。他的作品的最小的优点也都打着印记,这印记会立即向全世界呼喊:‘我是莎士比亚的’!”[11]375莱辛在比较了法国和英国的戏剧和民族性格之后说:“法国人的习性是想显出自己比实际较伟大一点,而英国人的习性却喜欢把一切伟大的东西拖下来,拖到自己的水平。法国人不欢喜看到自己老是在滑稽可笑的一方面被人描绘出来,他骨子里有一种野心驱遣他把类似他自己的人物描绘得比较高贵些。英国人则不高兴让戴王冠的头脑享受那么多的优先权,他认为强烈的情感和崇高的思想不见得就只属于戴王冠的头脑们而不属于他自己行列中的人。”[12]他提倡学习莎士比亚,其着眼点在于要建立德国本民族的戏剧。他的思想对后来的德国作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莱辛之后,赫尔德也非常注重莎士比亚,他的观点直接影响了青年歌德。赫尔德是莎士比亚最热情的歌颂者,他不吝赞美之辞。针对有人批评莎士比亚戏剧缺乏规则,赫尔德指出不能以古希腊艺术为标准来衡量莎士比亚,也绝不能要求今天的英国产生古希腊那样的艺术。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正是那些新古典主义者,那些号称遵循希腊艺术规则的人,违反了希腊艺术的精神。他指出:“亚理斯多德懂得在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中珍视索福克勒斯这种天才的艺术,并且在一切论点上都几乎恰恰和近代人随意曲解他的著作的说法相反……这位伟人也是本着他那个时代的伟大精神进行哲学的探讨,后来人们硬要从他的著作里抽出清规戒律作为舞台上的八股,对于这些幼稚的、限制人的琐屑无聊的东西,亚理斯多德是丝毫没有责任的……假如亚理斯多德复生,看到人们把他的规则错误地、违理地运用到完全另一种性质的戏剧上去,那他当作何感想!”[13]72-73他指出在距离希腊那么远的时代,历史、传统、习俗、宗教、时代精神、民族性格等各个方面都与其迥然不同,要求这种人再完全按照希腊规则来创作是荒唐的。而莎士比亚的伟大在于他就他所能发现的那个样子采用了历史,用创作的天才把千差万别的材料构成一个不可思议的整体,这正是“有一个天生有神力的凡人,恰恰利用性质相反的材料、通过极不相同的写法,产生了(与希腊戏剧)同样的效果:恐惧和怜悯!而且两种情感还达到了那第一种材料和写法当初未必能够达到的程度!这个人在他的事业上真是幸运的天之骄子啊!正是这崭新的 、初次出现的、完全不同的东西显示出他在本行上的原始力量。”[13]78莎士比亚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是因为他只是而且总是自然的仆人。在他的作品里,诗人掌握的时间和地点的变更以最大的声音喊道:“这里不是诗人!是造物主!是世界历史!”[13]82只有那些最可怜的人才会认为莎士比亚的戏剧是最笨拙最荒唐的东西。可以说正是赫尔德的这种不遗余力的倡导,直接导致了德国文学的巨大飞跃。
三、康德对“天才”的定义
尽管在康德的三大批判尤其是《判断力批判》中并没有提及莎士比亚,但是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康德是非常熟悉莎士比亚戏剧的,尤其是在他的人类学讲座中。在《实用人类学》第一卷“论认识能力”中他就举了莎士比亚剧中人物福斯塔夫来说明想象力的特性。而在《判断力批判》中,他尽管没有明言莎士比亚和法国新古典主义,我们从他的行文和褒贬上却可以明确地看出,他的天才观是完全站在对莎士比亚认同的基础上的。
康德说:“美的艺术的产品中的合目的性虽然是有意的,但却毕竟不显得是有意的;也就是说,美的艺术必须被视为自然,虽然人们意识到它是艺术。但一个艺术产品显得是自然却是由于虽然惟有按照规则这个产品才能够成为它应当是的东西,而在与规则的一致中看得出所有的一丝不苟;但却没有刻板,没有显露出学院派的形式,也就是说,没有表现出这规则悬浮在艺术家眼前并给他的心灵力量加上桎梏的痕迹。”[14]320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将其解读为是对莎士比亚和法国新古典主义的对比,如果说康德出于谨慎所以并没有点名的话,引文中提及的“学院派”则毋庸置疑透露了此中消息。新古典主义强调“三一律”,强调各种规则,赫尔德就已经指出这些都是违背自然的,在这一点上康德显然认同赫尔德的观点。他并且进一步指出“天才是与模仿的精神完全对立的”,如果过于强调模仿,“艺术在某个地方就停滞不前了,因为对艺术设立了一个界限,它不能够再超出这个界限,这个界限也许很久以来就已经被达到并且不能再被扩展”。所以艺术是有规则的,但这种规则只存在于伟大作家的作品中,别人要想了解规则只有通过作品,而决不可能从任何公式中得到这些规则,不然的话,对美的艺术就可以按照概念来规定了。因此康德对“天才”作出了如下的定义:
1.天才是一种产生出不能为之提供任何确定规则的东西的才能,而不是对于按照某种规则可以学习的东西的技巧禀赋;所以,原创性就必须是它的第一属性。2.既然也可能存在原创的胡闹,所以天才的产品必须同时是典范,亦即是示范性的;因此,它们本身不是通过模仿产生的,但却必须对别人来说用于模仿,亦即用做评判的准绳或者规则。3.它是如何完成自己的产品的,它自己也不能描述或者科学地指明,相反,它是作为自然来提供规则的;因此,一个产品的创作者把这产品归功于他的天才,他自己并不知道这方面的理念是如何在他心中出现的,就连随心所欲地或者按照计划想出这些理念并在使别人能够产生出同样的产品的这样一些规范中把这些理念传达给别人,这也不是他所能控制的(因此,天才这个词很可能是派生自genius[守护神],即特有的、对于一个人来说与生俱来的保护和引导的精神,那些原创的理念就源自它的灵感)。4.自然通过天才不是为科学,而是为艺术颁布规则,而且就连这也只是就艺术应当是美的艺术而言的。[14]321
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康德对于艺术的要求是极高的,只有那些真正的原创性的作品,也就是天才的作品才能称之为艺术,他们为艺术创作提供典范,提供规则,后人可以对其模仿,但那些模仿之作无论在任何意义上讲都是无法与他们对之模仿的作品相比的。莎士比亚的作品就是高度原创性的,虽然新古典主义者们责骂他不懂规则,非常粗野,而且也不管那些古典主义者是多么精致,对于他们眼中的古代作品的模仿是多么惟妙惟肖,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新古典主义者是无法达到莎士比亚的高度的,对于他们来说,这个高度甚至是无法想象的。他们与希腊古典作品只存在着形式上的相似,但莎士比亚虽然常常违反他们的那些规则,却与那些古典作家在精神上高度相似。事实上就连天才自身都无法明确地说出他们创作的方式,因为这是授之于天的,更别提那些根据古代的作品来制定规则的人了,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他们的规则是多么的无聊和荒谬。
当然并不能因为康德如此的强调天才,就认为他完全否认了规则。他指出虽然天才的原创性的艺术,即真正的“美的艺术”和那些模仿的艺术,也就是“机械的艺术”之间有极大的区别,但是没有任何美的艺术一点儿都不具有某种“符合学院规则的东西”,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这些规则是构成艺术的基本条件。即使是莎士比亚,如果他对于戏剧规范没有一星半点的了解,他也就只能永远是一名乡下的威廉了,现在传世的莎士比亚作品将统统化为零。有些东西是必须被设想为目的的,比如说创作的一些基本规范,例如诗歌的音步、韵脚等等,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所有的作品都只不过是一些偶然的产品,而不可能有真正的艺术。但这里似乎与他强调的原创性产生了矛盾,不过这在康德的体系里并不是大问题,他在对“美”的鉴赏判断的契机中就对其予以解释:“合目的性可以没有目的”,而且“惟有一个对象的表象中不带任何目的(无论是客观的目的还是主观的目的)的主观合目的性,因而惟有一个对象借以被给予我们的表象中的合目的性的纯然形式,就我们意识到这种形式而言,才构成我们评判为无须概念而普遍可传达的那种愉悦,因而构成鉴赏判断的规定根据”。[14]228-229这对于鉴赏判断是这样,对于美的艺术的创造同样是这样,目的(规则)必须被内化,以不被明确意识的方式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也就是不露斧凿痕迹。据此,将莎士比亚与亦步亦趋、小心谨慎的新古典主义者比起来,高下立判。
众所周知,康德的美学思想对德国以及世界文学的影响极大。但康德艺术观念与莎士比亚的关系似乎少有人加以注意,基于此,本文对其略加阐述,不仅可以对康德美学中的一些相关观念有一个更清晰的了解,也算是对即将到来的莎士比亚400周年忌辰的一点微薄纪念。
[1]卡西勒.启蒙哲学[M].顾伟铭,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315.
[2]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文集:第14卷[M].陈燊,丰陈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388.
[3]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委员会.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3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2-3.
[4]杨格.试论独创性作品[M].袁可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5]佛朗霍尔.西方文学批评简史[M].张月超,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
[6]维姆萨特,布鲁克斯.西洋文学批评史[M].颜元叔,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164.
[7]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1卷[M].杨岂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The Relations between User-to-user Interaction,Co-creation User Experience and User Co-created Value:An Example of Non-trading Virtual Community
TU Jian-bo1,CHEN Xiao-gui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Beijing100144,China;2.Zhu jiang School,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Guangzhou510900,Guangdong,China)
With the background of non-trading virtual community,an empirical research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was used to verify the eff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user-to-user interaction,co-creation users’experience and user’s co-created value.Meanwhile a method of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mediated effect of co-creation user’s experien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ser-to-user interaction and user’s co-created value.The results show that with the help of co-creation users’experience,user-to-user interaction has a positve effect on user co-created value,and the cocreation user’s experience partial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ser-to-user interaction and user co-created value.
virtual community;non-trading;user-to-user interaction;co-creation users’experience;users’co-created value
I561.09;I109.4
A
10.3963/j.issn.1671-6477.2015.05.035
2014-12-04
张同铸(1975-),男,江苏省淮安市人,南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西方当代文艺理论、民间宗教与民间文艺研究。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4HQ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