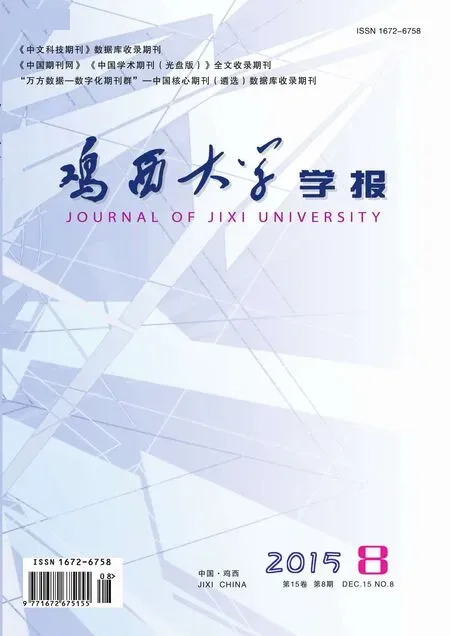陶渊明田园诗之美学追求
2015-03-18赵新新
赵新新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530006)
陶渊明田园诗之美学追求
赵新新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530006)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从事田园诗创作的诗人。他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不仅劝勉农民勤力耕种,而且亲自参加劳动,以诗歌表现劳动之甘苦。他怀有济世壮志,但囿于黑暗的社会现实,只能归隐田园。在对壮志的坚守和对“自然”状态的追求中,陶渊明最终成就了自我的“真”。
陶渊明;田园诗;美学追求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社会环境极为复杂,为保持品性的高洁,他选择了归隐田园。他善于发现美,因而田园万物入目即为诗。陶渊明的诗歌平淡中可见警策,朴素中又不失绮丽,这都得益于他的诗学主张——返古守拙以求真。
一 为立善而返古
魏晋时,玄、儒、释、道互相争鸣,陶渊明虽受到各家思想的浸染,但他仍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受古时圣贤之治的影响,他极看重农业生产;但迫于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又只能安贫固穷;然而,无论出仕还是归隐,他都胸怀济世壮志,以期实现儒家“立善”之理想。
1.重农。
农业是我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命脉,是国计民生之本,所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会对农业生产给予极大关注。他们劝勉百姓勤力耕种,告诫百姓遵守农时。作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陶渊明对底层的劳动者给予极大关怀,他不仅劝勉农民勤力耕种,而且亲自参加劳动,对农民的不幸遭遇报以深切同情。
作为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陶渊明极其重视农业生产,劝勉百姓、督促农事的思想在他的诗歌中随处可见,《劝农》便是一首劝勉农民勤力耕种的四言诗。在诗歌的第二章,诗人先后写了后稷播殖、舜禹躬耕、《周书》八政以食为首,借古时治世表明农耕与劳动的重要性;第三章再现了“纷纷士女,趋时竞逐。桑妇宵兴,农夫野宿”的劳动场面;第四章引用冀缺夫妇、沮溺稼穑的典故对那些“曳裾拱手”的众庶加以批判。诗歌的中心在于“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一句,因此,劝农是诗人重视农业生产的一个表现。
躬耕,是陶渊明重视农业的又一表现。“封建社会和儒家思想本是鄙视劳动的,两晋南北朝士族尤甚。”[1]《劝农》的“孔耽道德,樊须是鄙。董乐琴书,田园不履”则是对儒家鄙视劳动的态度的批判。“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秉耒欢时务”均是陶渊明躬耕场面的再现,是对儒家思想的超越。此外,诗人在长期的劳动中还与农民建立了一种平等和谐的关系,“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都是这种关系的真实反映。正因诗人亲身体会躬耕之甘苦,加之与底层劳动者有深厚的感情,所以对百姓生存之艰、稼穑之苦的忧虑更深。“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这些诗句通过对诗人辛勤躬耕却终至穷困的描述,反映的是广大劳动者生存的艰难。因此,叹民生之苦、忧稼穑之艰,亦是诗人重农思想的体现。
2.固穷。
“固穷”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袁行霈先生指出它是“穷而不移,不因穷而放弃道德原则”。[2]陶渊明熟谙儒家学说,极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他本心怀壮志,却生不逢时,迫于当时腐败的政治、频繁的战争和黑暗的现实,陶渊明无法实现济世安民的壮志,只好归隐。他的隐居生活是相对穷困潦倒的,“凄厉岁云暮,拥褐曝前轩。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陶渊明不仅要应对穷困的生活,还要承受来自各方的压力,“年饥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别人的劝诫尚可不当回事,但面对哭泣的妻子、饥饿的儿女,诗人的内心怎能不苦苦挣扎一番?“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岂忘袭轻裘,苟得非所钦”,在贫与富的交战中,诗人最终选择了固穷安贫。而他之所以能做出这一艰难抉择,主要在于儒家所提倡的个人道德与节操,也正是《咏贫士》七首中荣启期、黔娄、袁安等贫士所具有的不为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的高洁品性。通过返古,诗人向古代的贫士学习,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高尚,最终成为能够独善其身的高洁之士。
3.济世。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陶渊明青年时就怀有壮志,渴望建功立业。他始终奉行“仁”的思想,既然“四海之内皆兄弟”,那又何必再因血缘来划分亲疏?基于此,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确实做到了“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与此同时,儒家的“立善”思想也贯穿于他的交友上,《酬丁柴桑》中有“餐胜如归,聆善若始”一句,逯钦立先生认为餐胜如归是说“吸收胜理至言如同归家那样喜悦”,[3]聆善若始是说“倾听善言如同第一次那样新鲜”。[3]诗人笔下的丁柴桑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符合儒家期待,而陶渊明与这样的人不仅情趣相投,而且两心相知,这无不彰示出他的济世壮志。
与此同时,诗人的心怀壮志还体现在对那些功成名就之人的歆羡上。在《咏二疏》中,陶渊明高度赞扬了疏广和疏受“高啸返旧居,长揖储君傅”的行为。诗人咏二疏,重点在歌颂其“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的行为。与二疏的辞官不同,陶渊明辞彭泽令是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无奈之举。在对二疏的歌颂中,也不乏诗人对二人能受到朝廷赏识并予以重任的歆羡之情。《咏荆轲》一诗也写得极为豪放,蒋薰指出这首诗“摹写荆轲出燕入秦,悲壮淋漓,知浔阳之隐,未尝无意奇功,奈不逢会耳,先生心事逼露如此”,十分恰切。
陶渊明的济世壮志还表现在惜时上。“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无一不在劝勉自己和他人珍惜时间。逯钦立先生指出:“勉励,劝勉为善事也”,[3]由此可知诗人惜时的目的仍在于实现自己济世安民的壮志。而他的这种惜时的态度和渴望建功立业却不得的焦灼心理,在归隐之后也并未消失。在《九日闲居》一诗中,诗人面对“人生不满百”的现状,提出了“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的解决方案,想要通过借酒消愁、服菊延年的方式增加生命的广度,然而“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长生实不可得。诗人也想有所作为,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战乱频仍、百姓流离,统治者争权夺利,置苍生于不顾,他的政治主张不被认可,济世热情也为黑暗现实所消磨。无奈之下的归隐使得诗人面对时光飞逝却无所作为的焦灼又加深一重。“仕与隐,道路尽管不同,但中间并不存在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4]陶渊明的出仕是为了实现大济苍生的壮志,选择归隐后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而是始终心系百姓和社稷。所以说,仕与隐只是诗人在不同背景下事先壮志的两种不同方式。
二 为求美而守拙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政治黑暗、官场腐败、战乱频繁。在这一背景下,作为心怀济世安民之壮志的知识分子,他看到了社会的腐败和危机,但却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归隐田园。“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诗人将自己的归隐视为“守拙”,实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返归自己的率真性情,洒脱无拘;二是远离世俗,回归田园,过上一种躬耕自给的生活。这是对人性之美和田园之美的探寻。
1.率性任情。
陶渊明为人真实,毫不虚伪矫饰。他想做官时,便对亲朋说:“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且直言为官的原因在于“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丝毫不以做官为荣。在“风波未静,心惮远役”之时,他乐为彭泽令是因“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担任彭泽令期间,陶渊明令二顷五十亩公田种秫,待成熟便用来酿酒,釀熟之际便取下头上葛巾来漉酒。他喜饮酒,好友颜延之留下来的两万钱都被他送到了酒家,充作酒资。陶渊明还喜欢菊花,他的宅边就种有几丛菊花。他曾经在重阳节时坐在菊花丛中,满手把菊,王弘派人送酒给他,便就着菊花饮酒,直到喝醉才回家。他喜欢音乐,但却不解音律,为此便蓄有一张无弦琴,酒后便抚弄它来抒发情怀。他不欲做官时,便“敛裳宵逝”,认为“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不愿受制于口腹之欲,辞职归田,也不以归隐为高。陶渊明读书重在“会意”,著文重在“自娱”,逢亲旧招引,则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正如苏轼在《书李简夫诗集后》所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者,贵其真也。”
2.归隐之美。
陶渊明是一位隐士,钟嵘将其评为“古今隐逸之宗”。他早年意气风发,历经忧患也不曾懈怠对理想的追求,直至晚年仍是“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甚至通过描绘一幅世外桃源的蓝图来寄托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向往。朝政腐败、现实黑暗和生活重压并未使他流于颓唐,而是置身田园,在躬耕中寻找人生乐趣。
陶渊明善于发现美,他的田园诗从景色、劳动、人情和生活四个方面展现了田园之美。“山涤余霭,宇暧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还有那宅边的菊丛,堂前的桃李,檐后的榆柳,院子里的竹树,日夕的山气,归巢的飞鸟,无不自然而美好。与此同时,诗人还通过躬耕发现了劳动的价值,体悟到劳动之美。“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田间劳作虽然辛苦,但面对“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他却满心欢喜,并进一步得出“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的结论。此外,诗人归隐田园后,在与淳朴的农民的交往中也发现了田园中的人情之美:“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诗人的率性与农民的淳朴相结合,无论闲谈农务、相邀耕植,或是齐聚欢饮,都是令人愉快的。
陶渊明体悟到庄子“道无处不在”的思想,所以入目万物皆为诗。冯友兰先生说:“真正风流底人,有情而无我。他的情与万物的情有一种共鸣。”正是因为陶渊明“把自己的胸襟气韵贯注于外物,使外物的生命更活跃,情趣更丰富;同时也吸收外物的生命与情趣来扩大自己的胸襟气
韵”,[5]所以使得“自然景色在他的笔下,不再是作为哲理思辨或徒供欣赏的对峙物,而成为诗人生活、兴趣的一部分”,[6]山水草木不再是一堆死物,而是情深意真,既平淡无华又具盎然生机。因此,“无论是微云孤岛,时风景雨,或是南阜斜川,新苗秋菊,都到手成文,触文生趣”。[5]
三 返古守拙以求真
陶渊明有律己严正肯负责任的儒家精神,然而当时“左右政局的士族和军阀所热中的是争权夺利,他们既不想整顿政治,也无意收复失地”,[1]与陶渊明所推崇的往古之时的圣人之治相背离。《论语·卫灵公》云:“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受这一思想的影响,陶渊明选择了归隐。张国安教授指出,“历史是以‘德王天下’的历史”。[7]君主顺天之德,则天下承平,百姓真淳;反之则真风渐逝,民心趋伪。“于是佐君王以续其德,新礼乐,淳风俗以济苍生,便成了个体实现其人生价值与意义的最高方式。”[7]陶渊明归隐田园,独善其身,也成为他大济苍生的一种特殊形态。
诗人复返自然,并非纵情山水,醉心于谈玄论虚,而是脚踏实地,依止于田园的躬耕生活。“鸟弄欢新节,泠风送余善”“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诸如此类的诗句中,诗人的劳动生活被审美化、意象化了,他的济世之志也暂时获得了慰勉。起初的躬耕生活确实为陶渊明带来过一定程度的精神愉悦,田园也成为他当之无愧的精神乐园。然而,长期的劳动后,他却经常受到饥寒的威胁,甚至不得不出去乞食。此时,审美与生活已不再浑然,济世远志也遭到怀疑,诗人的坚守变得苍白无力。面对此情此景,他提出“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想要借酒忘忧,审美寄愁。然而“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醉酒不可取,长生实难得,迟暮之感与生死之虑时时在诗人心中盘旋。因壮志难酬,此时诗人内心空前愁苦,在空前的绝望中,他与日夕的山气和归巢的飞鸟相遇。“‘南山寿’的意象终于实现了价值意向性转换,已成了入息(日夕)、入墓(日暮)的象征。自由的飞鸟,欣然有托的恰是死亡”。[7]这样的相遇,使得陶渊明对死亡有了新的思考。在他的心目中,死亡已不再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虚情假意,也不再是“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的强颜欢笑。“向死而生”的观念消解了诗人满腹的愁苦,使他意识到济世安民之壮志并非徒然。
陶渊明向往古时的圣贤之治,便营造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世外桃源;他想要保持品性的高洁,便归隐田园,寻求一种万物顺其自然而运行的状态。归隐是对人性异化的否定,在否定中他又肯定着自己济世安民的壮志。荀子曰:美善相乐。在对善与美的追求中,在对“向死而生”的体悟中,陶渊明成就了自我的“真”。因其“真”,陶渊明方成为中国文学史上难以超越的文化符号。
[1]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2]袁行霈.陶诗主题的创新[A].陶渊明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4]钟优民.陶渊明论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5]朱光潜.诗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6]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7]张国安.陶渊明:一次千年不辨的文化冒险[J].人文月刊,2004,12.
The Aesthetic Pursuit of Tao Yuanming’s Pastoral
Zhao Xinxin
(School of Liberal Art,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Nanning,Guangxi 530006,China)
Tao Yuanming is the first poet who engaged in pastoral poem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H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agriculture,personally participated in the labor,and to the performance of rural life through poetry.He has ambitions,but because of society's dark,he had become a recluse.In the pursuit of his ambitions and the"natural"state,Tao Yuanming finally achieved himself.
Tao Yuanming;pastoral poems;aesthetic pursuit
I207.22
A
1672-6758(2015)08-0130-3
(责任编辑:郑英玲)
赵新新,硕士,广西民族大学2013级古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
Class No.:I207.22 Document Mark: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