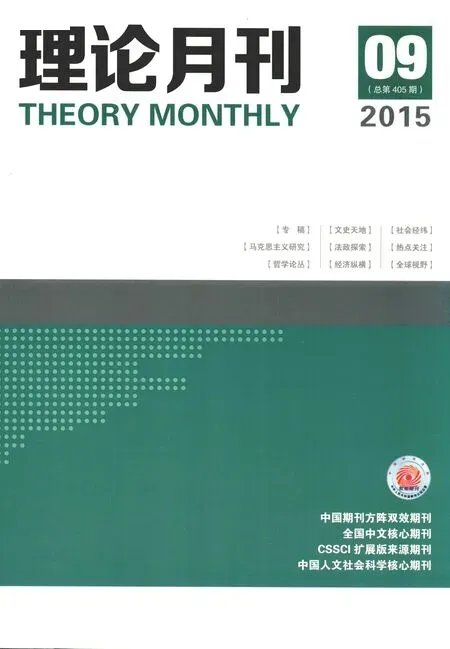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民事责任的法理溯源及其承担
2015-03-17李新天易海辉
□李新天 ,易海辉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民事责任的法理溯源及其承担
□李新天 ,易海辉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近年来,企业基金会在数量上日益增多,增长速度较快,但发展水平还不高。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民事责任在法律责任体系中具有基础性、根本性地位,对基金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的责任制度及其落实情况不尽人意。从法理上看,其民事责任的义务源主要有忠实义务、注意义务和服从义务。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要充分发挥企业基金会作为基层社会组织的作用,就需要对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民事责任的请求主体、情形、方式等方面不断健全,确保其民事责任的落实。鉴于基金会制度的建立以公司制度为参照,在完善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民事责任制度上,可以充分借鉴公司法的有关做法。
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民事责任
1 现实问题: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①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基金会事项一般由理事会决策,秘书长执行。监事负责监督理事会的行为。理事会设理事长和副理事长。但实际运转中,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理事等都有相应的决策、管理权,甚至一些基金会基本由秘书长掌控,决策与管理职能混淆。这些人实际上为企业基金会的高级决策、管理人员或称为内部控制人。《基金会管理条例》仅对理事等有关主体的法律责任进行了粗略规定。为行文方便,本文将以上人员统称为内部控制人,但不包括监事。民事责任的薄弱
所谓企业基金会是指,由企业家或企业出资发起设立,且出资金额超过基金会原始资金50%。[1]2006年以来,我国基金会每年保持16%左右的水平快速增长,而且新增的基金会以非公募基金会为主。[2]尤其自2008年汶川大地震以来,民间慈善事业迎来新的发展,出现大量非公募基金会,其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公募基金会。其中80%以上的非公募基金会都以企业基金会方式注册。企业以营利为目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社会责任。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慈善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社会责任,[3]设立基金会是企业开展慈善活动的重要途径。截止2013年底,全国企业基金会数量约有800家,约占全国各类基金会总数的四分之一。[4]以企业基金会为主体的非公募基金会,将日益成为我国慈善基金会的主要力量。
“财团选任了董事会(惟一而且必要的机关),才有了行为能力。”[5]因此,企业基金会作为法律拟制的财团法人,需要作为自然人的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理事等内部控制人具体负责决策、管理。它们能否忠实、勤勉履行职责,事关企业基金会能否有效运作和不断发展。而现行有关内部控制人法律责任的立法极其薄弱和粗糙。实践中,“非营利组织运转出现问题,其理事很少遭到外部和内部的惩罚,几乎不承担任何风险。”[6]而良好的责任制度以及责任的有效落实,有利于保障捐赠财产的安全,有利于保护企业基金会的法人财产权,还有利于促进企业基金会的规范治理和发展,巩固和发展社会慈善事业。可以说,内部控制人民事责任制度的薄弱、不健全,是影响基金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前,理论界对基金会法律责任制度关注也较少,专门研究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民事责任的成果几乎未见。①经中国知网检索,目前仅南京大学税兵教授对非营利组织董事责任进行了初步研究,其成果《非营利组织董事责任规则的擅变与分化—以美国法为分析样本》发表于《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1期。有关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民事责任制度的专门研究成果未见。企业基金会属于非公募基金会,基金会主要财产来源于企业捐赠,在独立性上不及公募基金会。企业和企业基金会关系的特殊性,容易导致后者沦为前者的附庸,共同为企业之私利而损害公益。因此,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责任承担问题更具复杂性,值得深入研究。
慈善被称为社会的第三次分配。[7]包括企业基金会在内的公益慈善组织,其重要性日益受到政府重视。企业基金会作为社会公益组织,是创新社会治理,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力量。随着经济的发展,慈善理念的深入,未来企业基金会将大有潜力可挖。在此背景下,本文拟对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民事责任承担的法理基础及其制度建构进行探讨,以期进一步推动我国企业基金会的改革与发展。②
2 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民事责任的法理溯源
从法理上讲,法律责任源于义务的存在,是由于违法行为、违约行为或法律规定而产生的不利后果。[8]民事责任是法律责任的一种,主要是财产责任。企业基金会与其内部控制人之间本质上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这种代理关系通过法律、章程或有关协议来加以规定,主要体现为《基金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企业基金会章程。根据《条例》规定,企业基金会必须设立理事会,从全体理事中选举理事长、副理事长和秘书长。同时,有明确的章程是企业基金会设立登记的必要条件,而章程是财团法人的“大宪章”。作为最终代理人的内部控制人,为了实现委托人的利益,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违反这些义务,便要追究其法律责任。基于企业基金会作为公益法人的特殊性,以及委托代理问题的普遍性特点,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民事责任的义务源主要有以下几种:
2.1忠实义务
任何委托人都希望代理人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行为准则。同时,委托人之所以将目的事业交由代理人办理,是出于对代理人的高度信任。因此,代理人应忠于受托之事,最大限度维护和实现委托人的利益。委托人的信任和代理人的忠实,是所有委托代理关系最核心的要素。信托关系是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受益人和委托人可为同一人。“受托人对受益人最根本的义务是忠诚义务,必须完全忠诚于受益人利益,排除对自我利益和第三人利益的考虑。”[9]从代理人角度而言,其负有的忠实义务是基于委托人的信任,是一种信赖义务。对机构受托人的雇员而言,属于受托人的关联人,直接或间接处理信托事务,同样对受益人负有忠诚义务。[10]
就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而言,在企业基金会的决策管理过程中,应当以实现企业基金会目的事业为行为最高准则,不得追求自己之私利。如禁止自我交易,即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或内部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主体与企业基金会之间直接或间接的交易。“(自我)交易表面上发生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当事方之间,实际上却只由一方决定。”[11]相比公司,企业基金会不具有类似前者的财产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产权特点。企业基金会财产捐赠人不享有剩余财产索取权,在企业基金会中没有作为类似出资人的股东的监督。因此,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控制下的自我交易,更容易导致个人利益凌驾于企业基金会利益之上,使基金会利益受损。实际上,各国对非营利法人普遍规定了禁止自我交易规则。《条例》第23条也规定:“基金会理事、监事及其近亲属不得与其所在的基金会有任何交易行为。”
2.2注意义务
民法上最早规定了侵权者的一般注意义务,商法上的董事注意义务源于前者。[12]美国《示范公司法修正本》对董事注意义务进行了规定,即:“(1)怀有善意;(2)要以正常的谨慎之人在类似处境下应有的谨慎那样去履行义务;(3)采用良好的方式,这是他有理由相信符合公司利益的最佳方式。”[13]美国《非营利法人示范法》对董事义务作了同样的规定。①参见1987年《美国非营利法人示范法》第8.30条第I款。在商法上,董事的注意义务本质上是一种善良管理义务。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作为基金会法人的决策管理者,也应当具有公司董事类似的注意义务。其应当依照法律和章程,运用自己的经验、知识和技能,积极、谨慎、善意管理基金会。
这种注意义务以一般理性之人所及之水平为判断标准。如果企业基金会与内部控制人之间有特别约定或要求的,还需达到特殊的注意义务。善良管理人应具备受托事项处理应普遍达到的注意程度,此程度高于处理自己同等事务标准。[14]在美国,其慈善基金会通过信托法来规定,其中就规定了受托人的注意义务。如《美国信托法重述(第2版)》第174条规定:“受托人必须合理注意,最起码保持一般人的注意义务;如果委托人是因受托人具有较高注意技能而赋予信托时,受托人应遵守比一般人较高的注意义务。”[15]
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在决策管理时未开展详尽的调查、咨询,未运用充分的知识、技能,未依照科学的决策程序,未尽相关监管职责等,导致基金会财产受损或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即应当构成违反注意义务。违反注意义务是判断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主观是否有过错的依据。当然,依据违反注意义务的程度不同,有故意、重过失和轻过失等之分,因而有不同的法律责任。《条例》第43条规定:“基金会理事会违反本条例和章程规定决策不当,致使基金会遭受财产损失的,参与决策的理事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体现了对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决策的注意义务要求,即要依法、依章程科学、合理决策,否则即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3服从义务
财团法人没有社员,也没有社员大会,对董事会的控制由国家的监督来完成。[16]国家监督一方面通过制定相应的成文法规范董事会的行为,另一方面通过相应的执法机构对董事会执行法律情况进行检查。作为财团法人的企业基金会,必须服从国家法律的规定,具有守法的义务。如各国法律一般要求慈善组织必须进行信息披露。在美国,法律认可的免税非营利组织每年必须填写国税局规定的相关表格,以便公众查询;日本《公益法人设立许可及指导监督标准》要求公益法人必须将其活动内容和财务情况向主管机关报告,进行营利活动必须向税务部门报告,并将相关资料公之于众。因此,作为企业基金会行为能力的履行者,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有义务遵守国家有关基金会管理监督的法律规定。
另一方面,企业基金会缺乏股东大会,其行为能力基本受限于基金会章程。其内部控制人必须服从章程的规定,在章程规定的范围内行事,不能超越章程规定的行为范围。如果要超越章程规定的目的范围、权限,必须遵循相应的章程修改程序。如美国便对公益性法人章程的修改,设置了严格的程序。②正如国外有学者指出:“非营利组织理事会要对约束组织发展的内外部法律法规、原则、标准一概服从,即具有服从责任。”[17]如果,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不遵守国家法律对企业基金会的管理监督规定,不服从章程规定的行为范畴和准则,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3 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民事责任的承担
所谓民事责任的承担,是指责任人承担因自己的违法或违约行为所引发的民事不利后果。目前,有关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民事法律责任的规定,主要体现在《条例》第六章“法律责任”部分。《条例》作为行政法规,对基金会内部控制人的法律责任规定较粗糙、抽象,导致责任难以落实。责任制度的不健全,致使对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缺乏有效的制裁手段,无法对其履职施加有效的压力。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民事责任的承担,涉及追责主体、追责情形、责任方式、免责事由等。
3.1关于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民事责任的请求主体
确定谁有权请求追究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的民事责任,是启动责任追究的逻辑起点。在非营利组织发达的美国,虽然对此问题在理论上依然存在争议,但实践中通常由检察官来行使诉权。[18]相比,《条例》对此问题只字未提,凸显立法的粗糙,缺乏专业性和技术性。这很大程度上导致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民事责任的落空。当前,对企业基金会进行监管的主要是民政部门。采取事后监督的方式,对基金会法人组织追究行政责任,而非对基金会内部控制人个人追究民事责任。这体现的是行政管理模式,由政府行政权来管理,而非司法模式,即由相关主体行使诉权来规范。笔者认为,应当建立健全由捐赠人作为利益相关者为主,企业基金会监事以及检察机关为辅的追责主体。这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变企业基金会监管主体过于狭窄、效果不理想,法律责任难以落实的局面。
3.1.1赋予捐赠人民事责任请求权。企业基金会缺乏类似公司法人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特点,不存在股东剩余财产索取权。这导致企业基金会理事会作为错误的决策者,其责任的追究最终取决于自我追究自觉性。如此,显然存在人性的背离和矛盾,责任自然难以落实。为此,有观点认为:“应当采取公司法上“刺破公司面纱”的做法,直接追究过错者的责任”。[19]然而,即便在该规则诞生地的美国,法院也很少适用。一方面,因为商业市场瞬息万变,法官并不能轻易判断内部控制人决策时是否妥当,其事后审查未必能保证判断的正确性。另一方面,适用该规则是对公司有限责任的动摇,影响极大。[20]而且刺穿面纱是针对股东滥用有限责任的情形,而非针对公司内部控制人。在企业基金会中,内部控制人并非基金会的出资者。采取类似“刺破公司面纱”的做法,似有不妥。笔者认为,应当借鉴公司法上股东派生诉讼的做法,赋予捐赠人针对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损害基金会财产的行为,以自己的名义代企业基金会向法院提起诉讼。①由于基金会法律制度主要借鉴了公司法律制度,在很多内容上具有相似性。因此,在责任制度构建上,相关内容亦可以进行借鉴。
捐赠财产是否合理使用与其慈善目的的实现具有直接关系。捐赠人是企业基金会财产损害赔偿的直接利益相关者。《条例》第39条仅规定了捐赠人针对基金会违反捐赠协议的撤销权。撤销仅为行为的终止,不足以对现有损害事实进行弥补。仅有撤销权,难以对基金会造成足够的压力,无法弥补捐赠人慈善目的受损的后果。建议立法赋予企业基金会捐赠人的民事责任请求权,即当捐赠财产没有按照捐赠协议管理、投资或使用时,捐赠人有权向法院独立提起诉讼,要求内部控制人予以赔偿。
捐赠人向企业基金会进行捐赠是为了慈善目的,②保障这一目的实现依赖彼此间的捐赠契约 (包括明示契约和隐性契约)。赋予捐赠人赔偿请求权,能够有效防止受赠人随意抛弃合同和其他法律责任,降低捐赠-受赠这一过程中的代理成本和交易费用。[21]赋予捐赠人赔偿请求权,从个体上讲,是对其民事权利的维护所需,这种权利更多的是体现为一种精神利益。从社会整体而言,是维护社会公众慈善信心所需。
3.1.2赋予监事民事责任请求权。监事是企业基金会的监督者,具有独立于理事会的地位,负责监督理事会的行为。根据《条例》第22条的规定,目前监事只享有质询权、建议权和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权。我国《公司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行使下列职权:(六)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即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提起诉讼。”笔者建议,基金会立法可以借鉴公司法的做法,赋予监事对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的追责权,即规定监事有权代表企业基金会,在发现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违反法律、章程,使慈善基金会遭受损害的,要求民事赔偿。
3.1.3应赋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现代检察制度起源于法国,民事检察制度也最早在法国确立,检察机关被认为是公共利益的代表,检察官广泛参与民事诉讼。检察机关将公诉权扩展到民事领域的公益诉讼,不存在法理上的障碍。[22]大陆法系国家普遍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力。[23]我国民事诉讼法未明确规定检察机关为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难以满足保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其情形主要针对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能有效改善目前公共利益保护薄弱的局面。基金会关系社会慈善心理的发展,具有公益性和社会公共性。因此,针对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损害基金会利益,导致基金会财产损失的,当捐赠人(企业)怠于请求追责时,检察机关应有权提起公益诉讼,请求法院追究内部控制人的民事责任,从而维护公共利益。建议立法及时明确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地位、范围、程序等。
3.2关于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民事责任的请求情形
何种情形该追责,在现有责任制度中并不健全。《条例》只在第43条规定了决策不当和私分、侵占、挪用财产两类责任情形。可以说,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民事法律责任的情形极为不充分,不利于促进其积极履职尽责。
一方面对程序性问题缺乏规范。如擅自修改企业基金会章程。章程为企业基金会预先设立了能力范围。修改章程必须要经过特定程序。如果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为个人目的,未依照特定程序,擅自修改基金会章程,是否应追责?另一方面,责任情形涉及的实体问题种类较少。基金会投资收益遵循“不分配约束”原则,投资收益不得在管理人员、理事、组织成员等人员间分配,必须全部用于基金会目的事业的发展。[24]违法分配投资收益或财政收支不当同样未予明确。实践中,许多基金会的支出不符合《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人员工资和管理费用大大超出公益活动经费。[25]为了避免超越法定的支出比例,假借名目将人员工资和管理费用计入项目费用中,或者由捐赠企业来承担相关行政费用。[26]还有如披露的信息损害国家利益、公序良俗、侵害个人隐私或其他违法情形的,都未明确法律责任。
笔者认为,基于企业基金会作为公益法人的根本属性,相比以营利为目的的私益法人,其社会影响更广。出于保护公益的目的,在责任情形上应当比后者更严格、更充分。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在决策管理过程中,其行为既可能是一般程序性违法违规,没有造成基金会实质性的损害,也可能是实体性违法违规,造成基金会实质性的损害,如目的事业未有效实现、财产损失、名誉受损等。如有学者就指出:“财团法人运行过程中的问题分为程序和实体两类。前者如财团重要事项不经过董事会或者评议员会而由少数特定董事决定等。后者又分为事业运营方面的问题和财务运营方面的问题,如收益事业的盈余未完全用于公益事业,或支出比例过高;为特定企业债务进行担保,并以财团财产代为清偿等。”[27]对此,有必要借鉴公司法的有关做法,赋予相关主体针对企业基金会运作过程中出现的程序性问题和实体性问题,均有权提起相关诉讼,请求法院要求企业基金会或内部控制人予以纠正、赔偿。
3.3关于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民事责任承担的方式
根据现行民事法律及《条例》等法律法规,基于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责任行为的义务违反情形,其民事责任承担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3.3.1返还财产。即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将违法侵占的基金会财产,归还给基金会。《条例》第43条第2款规定:“理事、监事以及专职工作人员私分、侵占、挪用基金会财产的,应当退还非法占用的财产。”此规定明确了内部控制人的财产返还责任方式。实际上,对基金会财产的私分、侵占或挪用,都是对基金会的侵权行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返还财产是法定责任承担方式之一。因此,在财产返还可能的情况下,企业基金会有权请求内部控制人返还该财产。当然,返还财产作为民事责任承担的方式,仅指返还原物。[28]
3.3.2赔偿损失。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给基金会造成财产损失的,需要对基金会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条例》第43条第1款规定:“基金会理事会违反本条例和章程规定决策不当,致使基金会遭受财产损失的,参与决策的理事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赔偿损失既是合同法也是侵权责任法,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之一。在赔偿损失的额度上,一般采取填补损失原则,但也存在惩罚性赔偿的做法。美国是惩罚性损害赔偿的诞生地。惩罚性赔偿以加害者存在故意为前提,要求在补偿性损害赔偿以外,另外施加一定额度的赔偿责任,[29]以起到对加害者的惩罚、威慑作用。笔者认为,基于企业基金会的公益性,代表公共利益,有必要引入惩罚性赔偿原则,适当提高内部控制人对财产损害的赔偿额。
3.3.3将违法所得归于企业基金会。即企业基金会的归入权问题。《公司法》第148条第2款规定董事、内部控制人的违法违规获利应当归公司所有。这是公司归入权的规定。公司之所以享有归入权,是因为内部控制人违反了忠实义务。对公司内部控制人违反忠实义务所获之利收归公司,也是国际通行做法。相比,立法目前未规定基金会法人的归入权。基于慈善法人的特殊性,美国联邦税法对非营利法人规定了禁止个人图利原则。在企业基金会等非营利法人中,任何人不得追求个人利益,从而损害法人的利益。因此,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违反忠实义务,非法获取个人利益的,应当将所得归于企业基金会。
除了上述几种责任承担方式外,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责任承担方式。笔者认为,以上责任方式同样适用于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这些责任方式,既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比如,可以要求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停止侵害基金会财产的行为,返还侵害的财产;错误决策的,既要赔偿损失,同时给基金会造成名誉或公信力受损的,还需要赔礼道歉,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3.4区分企业基金会法人责任和基金会内部控制人个人责任
企业基金会和其内部控制人均是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而企业基金会的运作又是由内部控制人掌握。在企业基金会责任制度不健全或缺失的情况下,内部控制人很可能利用基金会法人有限责任来谋私利。因此,在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利用基金会名义做出有关法律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时,应根据不同情形对两者责任有效区分。
3.4.1区分对内责任和对外责任。对内责任主要是指内部控制人对企业基金会的责任,基于信义义务而产生。内部控制人违反信义义务,企业基金会可以通过制止违法行为、提起诉讼等寻求救济。对内责任是内部控制人对企业基金会承担的责任,不是对基金会之外的第三人承担的责任;包括内部控制人与基金会之间的契约责任,也包括内部控制人对基金会的侵权责任。对外责任,是指内部控制人对企业基金会之外的第三人的责任。此种责任源于内部控制人的违约行为或侵权行为损害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这种责任必须基于内部控制人利用企业基金会的名义作出的行为所致。由内部控制人利用自己名义独立所为之行为,与企业基金会无关,自然责任由自己独立承担,与企业基金会无关。
3.4.2区分目的内和目的外责任。有观点认为:“应当区分慈善法人目的内行为和目的外行为,目的内行为的损害由慈善法人承担,然后向过错者追偿;对于目的外行为,慈善法人无需承担损失,应由具体过错者来承担。”[30]《条例》并未对此进行区分,仅规定了决策管理者对基金会所应承担的责任,也即上文所言的内部责任。在国外,内部控制人利用法人名义进行违约或侵权行为,其责任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德国模式,即法人对受害人单独承担责任;瑞士模式,即法人对受害人先单独承担责任,然后由法人追究过错者的个人责任;日本模式,即法人与行为人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芬兰和印度尼西亚模式,即法人不承担责任,直接由过错者承担责任。[31]
在公司法中,我国采取的是瑞士模式,而基金会制度主要吸收了公司制度。因此,以企业基金会名义作出的目的内的行为,其责任模式同样可以采取瑞士模式,先由基金会对外承担法人赔偿责任,对内区分是否由内部控制人的过错造成不利后果来追偿。对以企业基金会名义作出的目的外行为,是直接由内部控制人来承担责任,还是由基金会承担责任后再追偿,取决于对基金会财产所代表的公共利益和保护交易安全和第三人的信赖利益之间的衡量。企业基金会和第三人都属于平等的民事主体,两者都平等地受法律保护。笔者认为,即使是目的事业外行为,只要是以基金会名义作出的,仍有必要采取与目的内行为相同的责任模式。企业基金会的损失,事后向过错内部控制人追偿即可。采取直接由过错者承担责任的模式,额外增加了第三人的交易成本,不利于市场秩序的维护。
4 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民事责任的免除
《条例》未规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法律责任的限制或免除情形。作为法人,企业基金会在投资过程中,面临与公司相同的商业风险,不可避免存在决策失败的情形。相比公司内部控制人而言,各国公司法一般对其法律责任都规定了相应免除情形。鉴于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的有限理性,以及公司与基金会在法人治理结构上的相似性,在内部控制人民事责任承担上,应合理借鉴公司法上董事法律责任免除的做法,设置一定的责任例外情形。对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的法律责任严苛到何种程度,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内部控制人职位的吸引力和履职的积极性、独立性问题,也关系到增加企业基金会运作成本问题。结合国外以及公司法上的有关做法,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民事责任的免除情形可以有以下几种:
4.1依据业务判断法则而免除
如何判断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是否尽职尽责,履行善良管理人的义务,学术界并未有成熟观点。美国《非营利法人示范法》规定:“董事符合本条行为的,董事不因其作为董事通过决议或者未通过决议而对法人、任何成员或者其他任何人承担责任。”①即董事尽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对营利法人公司的董事,也作了相似的规定,也即业务判断法则。[32]只要董事行为符合该法则,即可免于司法审查,被法院推定为尽到了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其目的在于保护董事的独立执行力,维护其经营管理的积极性。[33]
①参见1987年《美国非营利法人示范法》(RMNCA)第8.30条第IV款。
企业基金会作为公益慈善法人,其目的事业在于非营利公益活动。同时,为实现基金会财产的保值、增值,可以进行相应的投资活动。一方面,公益活动虽然没有商业投资活动类似的高风险,但由于公益活动社会影响的广泛性、公众性,也需要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审慎确立基金会项目、合法妥善支出捐赠财产。另一方面,进行商业投资活动,则需面对商业风险。在商业风险充斥的市场环境中,要求任何时候都决策正确,显然勉为其难。因此,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民事责任承担上有必要采取业务判断法则,即内部控制人在基金会公益活动以及商业投资活动中,只要是在善意、掌握充分信息,并且是无利害关系的前提下作出的业务决策,即使造成企业基金会财产损害不利后果的,也可以免除责任。正如有观点指出:“应当允许当事人援用业务判断规则为自己辩护,对恪尽职守且无过错者,不应当追究其责任,避免不合理的惩戒形成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34]
4.2依据企业基金会章程规定而免除
如上文所言,企业基金会缺乏社员大会,其目的事业和行为准则都主要通过章程来规定。章程一定程度上是企业基金会设立人慈善意思的集中反映。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必须依照章程的规定,开展公益活动。如果章程对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的行为设定了具体的免责情形,即可免除该行为引发的法律责任。但须特别指出的是,通过章程事先规定来免除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民事责任的情形,只能是其违反注意义务的情形,而不能适用于违反忠实义务的场合。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对委托事项的忠实,是根本义务和基础内容。因此,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违背忠实义务的免责内容,不得在章程中规定。另外,章程虽然是意思自治的体现,但章程关于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法律责任免除的规定,不能违背法律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否则仍不得免除。
4.3对理事会决议持明确反对意见的
理事会是企业基金会的决策机构,对章程的修改、募捐和投资活动等重要事项进行集体决议。理事会会议决议以会议记录方式,由出席表决的理事审阅、签名。依据决策者负责原则,理事应当对理事会的决议承担法律责任。原则上,如果理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法规或基金会章程等,致使企业基金会财产等利益遭受严重损害的,参与决策的理事应对企业基金会负赔偿责任。但如果理事能够证明表决时,本人对理事会所做决议明确持反对意见,拒绝在理事会会议记录上签字,或所持异议明确记载在理事会会议记录的,其法律责任应当免除。
4.4受企业基金会设立人实际控制的
从法理上讲,企业和企业基金会之间是一种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但两者之间却实际存在着千丝万缕的控制与被控制或影响与被影响的复杂勾连,企业基金会对企业具有较强的依赖性。[35]由于出资的性质,企业基金会的独立性不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管理上,作为主要捐赠人的企业家或企业在决策中起决定性作用;二是项目运作上,基金会与企业社会责任部门职能擂同,未体现基金会的公益性。因此,项目更多的是为了塑造企业形象;三是基金会员工大多为企业员工。缺乏独立性的后果是,基金会的公益让位于企业的利益,基金会的公益项目更多成为企业的一种 “作秀”。[36]
企业和基金会之间的资本嫁接,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企业对基金会的控制。这形成企业对基金会的隐名控制人或实际控制人。如果一项决策并非由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决定,而是由企业实际指示所成,在此情形下由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承担决策责任,显属权责不一致,缺乏公平性。因此,当决策受企业实际控制时,应当免除企业基金会内部控制人对该决策的民事责任。
[1][2][4][26][36]刘忠祥主编.中国基金会发展报告(2013)[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42,5-6,146,55,165-166.
[3]王银春.“21世纪中国慈善事业与慈善伦理”研讨会综述[J].探索与争鸣,2011,(1):80.
[5][16]〔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M].王晓晔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50.
[6]William G.Bowen.When a Business Leader Joins a Nonprofit Board[J].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4,September 1.P39.
[7]王晖.重大自然灾害社会援助机制研究——以汶川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为例 [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107.
[7]苏晓宏.法理学基本问题[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252-253.
[9][10]刘正峰.美国商业信托法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254,272.
[11]〔美〕罗伯特·C·克拉克.公司法则[M].胡平等译.北京:工商出版社,1999.117.
[12]陈本寒,艾围利.董事注意义务与董事过失研究--从英美法与大陆法比较的角度进行考察[J].清华法学,2011,(2):73.
[13]〔美〕罗伯特·W·汉密尔顿.公司法概要[M].李存捧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51.
[14]赖源河,王志诚.现代信托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24.
[15]Section 174 of Restatement(Second)of Trusts,1959.
[17]DavidO.Renz.AnOverviewofNonprofit Governance[A].Philanthropy in the US:An Encyclopedia,Dwight Burlingame,ed.2002.
[18]税兵.非营利组织董事责任规则的擅变与分化—以美国法为分析样本[J].政治与法律,2010,(1):140-142.
[19]王雪琴.慈善法人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164.
[20]马齐林.美国法院“刺破公司面纱”考量因素之实证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法治研究,2013,(6):63.
[21]李喜燕.慈善捐赠人权利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115-116.
[22]黄生林,王武良,朱再良,孙远,陈雷.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问题研究[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109.
[23]潘申明.比较法视野下的民事公益诉讼[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209—219.
[24]徐宇珊.论基金会--中国基金会转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33—34.
[25]周婷玉,胡梅娟,杨维汉.从“牙防组”看基金会黑洞[J].瞭望,2007,(25):13.
[27]罗昆.财团法人制度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155-161.
[28]王利明.民法(第5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592.
[29]〔德〕格哈德·瓦格纳.损害赔偿法的未来——商业化、惩罚性赔偿、集体性损害[M].王程芳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112.
[30][31]王雪琴.慈善法人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156-166,163.
[32]赵玲.公司治理:理论与制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56.
[33]李燕.美国公司法上的商业判断规则和董事义务剖析[J].法学,2006,(5):146.
[34]冯辉.从“基金会事件”看我国基金会法律监管机制重构[J].东方法学,2011,(6):87.
[35]转引自杨团.关于基金会研究的初步解析[J].湖南社会科学,2010,(1):55.
责任编辑许巍
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5.09.023
D923
A
1004-0544(2015)09-0123-08
国家社科基金(14BFX169)。
李新天(1965-),男,湖南邵阳人,法学博士,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易海辉(1983-),男,湖南醴陵人,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