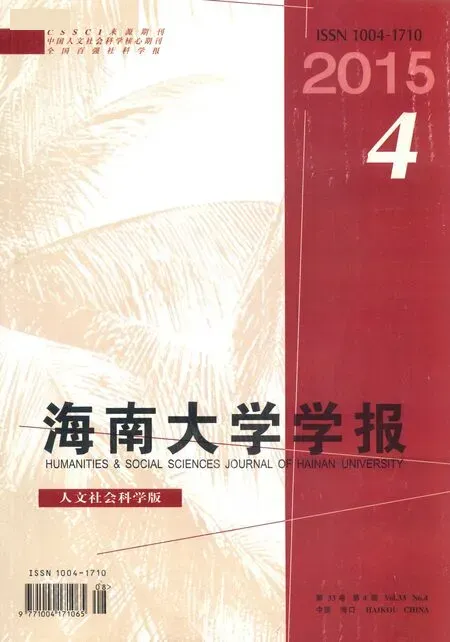现代性别权力关系的隐形书写
——对巴金《家》中主仆爱情关系的分析
2015-03-17刘园,张宏
刘 园,张 宏
(1.海南大学文学院,海南海口570228;2.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北京100024)
现代性别权力关系的隐形书写
——对巴金《家》中主仆爱情关系的分析
刘 园1,张 宏2
(1.海南大学文学院,海南海口570228;2.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北京100024)
对《家》中鸣凤与觉慧之恋进行了精神分析,认为小说对这一恋情的描写清晰地透露出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巴金的潜意识欲望,也体现了现代性的性别权力关系。在这一意识形态叙事策略中,鸣凤并未获得现代意义上的人性的尊严,毋宁说,她的“主体性”又被新的压抑机制所贬抑。
精神分析;性别权力关系;主体性
平静的水面被扰乱了,湖里起了大的响声,荡漾在静夜的空气中许久不散。接着水面又发出了两三声哀叫……只是空气里还弥漫着那哀叫的余音,好像整个花园都在低声哭了。
这是《家》对鸣凤投湖自尽之后凄婉的景物描写,也是历来被称道的文字段落之一,它也向来被认为是《家》的华彩部分——觉慧与鸣凤之恋的悲剧性的高潮。与这段恋情有关的章节是全书最具悲剧性与抒情性的段落。在一般的文学史著作和文学批评中,这段爱情是新一代文化英雄觉慧抛开世俗门第观念,追求自由爱情的英勇行为。鸣凤之死自然也就成为对封建文化的激烈抗议。
但是,如果对小说进行细读,却不难发现叙事的裂缝。这次跨越阶级鸿沟的“纯真”的恋情变得越来越浑浊与含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践,这一恋情恰恰体现了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巴金的多重潜意识,同时也体现了现代性的性别权力关系。
鸣凤之死是必然的,只有如此才能最终成全这个爱情神话。即,只有死才可以最终消除鸣凤与觉慧之间的绝对的差别,使爱情呈现出超越世俗的纯真性。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压抑这段爱情的“封建文化”才成为反历史的,压抑“普遍人性”的反动力量。
我越来越怀疑觉慧的爱情。小说中,觉慧对鸣凤的爱情除了小时一起长大之外,并没有更多的爱情基础,这种爱情更像是少年人青春期对异性的冲动,美丽的鸣凤只是觉慧萌动的性意识的最初对象,如果刻薄一点说,觉慧的言谈举止之间流露出一种公子哥对下层漂亮女孩的轻薄之意。我们不妨看看小说中所描写的二人的第一场见面:
很快地鸣凤就走出来了。他听见脚步声,故意把两只脚放开,站在门中央,阻碍着她的路。
她默默地站在他背后,歇了一会儿才说:“三少爷,让我过去。”她的声音并不高。
不知是他没有听见,抑或是他听见了故意装着未听见的样子,总之,他并不动一下。
她又照样说了一次,并且加了一句话:太太还要她去做事,但是他依旧不理睬她,他像石头一样站在门槛上
“鸣凤,……鸣凤!”上房里有人在叫,这是他的继母的声音。
“放我去,太太在喊我了”鸣凤在他后面着急的低声说:“去晏了,太太要骂的。”
“挨骂有什么要紧,’他笑了,淡淡地说:“你告诉太太说,在我这里有事做。”
“太太不相信的。倘若惹得她发脾气,等一会儿客走了,说不定要挨一顿骂。”这个少女的声音依旧很低,屋里的人不会听见。
这时候另一个少女的声音响了,他的妹妹淑华大声说:‘鸣凤鸣凤,太太喊你去装烟!”
他便把身子一侧,让出了一条路,鸣凤马上跑出去了。
这段爱情对觉慧的意义远不如对鸣凤重要,鸣凤漂亮的面孔像是三少爷生活的点缀,他为外面的世界所吸引,并不是经常地想起鸣凤,在以“五四”青年自居的觉慧那里,自由的爱情似乎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鸣凤填充了他的这一空缺。
他也并没有准备为鸣凤放弃现有生活,没有为跨越阶级差别而牺牲的打算,反倒时存放弃之意。并时时遗憾于鸣凤的仆女的身份。这一段文字清楚地表明了觉慧的真实心态,当他发觉自己爱上鸣凤时:
“不会有的,这样的事情做不到,”他自语道。
“假使真有了这样的事情呢?”他又这样地问自己。于是他想像着会有的那种种的后果,他的勇气马上消失了。他又笑着说:“真是梦想!真是梦想!”
但这梦想也是值得人留恋的,他好像不愿意立刻就把它完全抛弃。他又怀着希望地发出一个疑问:“假使她处在琴姐那样的环境呢?”’
“那当然不成问题!”他自己决断地回答道。这时候他真正觉得她是处在琴的环境里面了,于是在他与她之间一切都成了很自然,很合理的了。
过了一些时候,他又笑起来,他在笑他自己,他说:“怎么会有这样的痴想!……这简直说不上爱,不过是好玩罢了。”
事实上,如果觉慧对鸣凤具有真正的爱情的话,因为地位与能力的差别,这种爱的责任应更多的由觉慧来负,包括做出现实利益的牺牲。但觉慧并无此意,甚至他连鸣凤最后的求援也忽略掉了:为了那篇在他看来十分重要的“社会革命”的文章,他居然忙到连鸣凤“只说两句话”的再三请求都不予理睬,因此,对鸣凤之死,觉慧要负很大的责任。
如果再做更深层的分析的话,还能看出更多的内容。觉慧与鸣凤的爱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而且,事实上,这不平等正是他们爱情可能产生的原因:虽然鸣凤并不求成为“三少奶”,但如果觉慧也和鸣凤一样是高公馆的一名小厮,这种爱情还可能产生吗?从本质上讲,鸣凤对觉慧的爱和觉慧的少爷身份是分不开的,觉慧的三少爷身份正是一种特殊的性感魅力的起源,鸣凤不是也遗憾于自己不能像小姐们一样得到少爷们的追求吗?不难发现,在《家》中,鸣凤并不具有起码的平等意识。所以,这种爱从一开始就具有居高临下的性质,事实上,正是从这里觉慧体验到一种快感,觉慧的梦显示了这一点。在梦中,鸣凤成为资产阶级小姐,但二人私定终身后,鸣凤的父亲又将她许配给了中年官吏,在二人划船逃跑时被鸣凤父亲的汽船追赶,小船被大浪击翻。这个梦的意义,它所流露出的觉慧的潜意识是明白的:既有渴望鸣凤与自己同属于一个等级,从而消除爱情障碍的愿望;又有与鸣凤同属一个阶级之后会失去鸣凤的担心,深层的恐惧与焦虑其实在于怕鸣凤与自己同属一个阶级而失去爱情的优势。梦中的这一段对话是意味深长的:
“觉慧,”她握着他的手,唤他的名字。
他装做不听见的样子。她又叫了一声,他依旧不回答。
“你为什么不答应我?”她嗔怒地问道。
“你平时不是这样唤我的,”觉慧摇着头开玩笑地说。
“我现在不同了,”她得意地答道,“我不是你们的丫头了。我也是一个小姐,跟琴小姐一样的。”
“真的?我怎么没有听见说过!”觉慧惊喜地说。
“但是现在你亲眼看见了。现在什么都不成问题了。我跟你是平等的了。你看见我父亲吗?”
“你父亲?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你有父亲!”
“我父亲,他如今有了钱,他很久就想着我,到处访寻我的踪迹,后来才晓得我在你们公馆里头,正是你爷爷要把我送给冯家做姨太太的时候。他来找你母亲商量把我带走了,还是你母亲出的主意,把我的旧衣服丢在湖边,说是投水死了。……我就跟我父亲到这儿来。这是我父亲的花园。你不看见那座洋楼?我和我父亲就住在洋楼里面。现在我跟你中间再没有什么障碍了。我只问你现在还爱不爱我?”
觉慧随着她的手指去看那所西式楼房。他听见这句问话心里很高兴……从小说中,我们似乎也可以窥见青年巴金自己的潜意识。
这部小说基本上是巴金早年生活的自叙传,“那些人物,那些事情,已经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任是怎样磨洗,也会留下一点痕迹。我想忘掉他们,我觉得应该忘掉他们,事实上却又不能够。到现在我才知道我不能说没有一点留恋。也就是这留恋伴着那更大的愤怒,才鼓舞起我来写一部旧家庭的历史,是的,‘一个正在崩溃中的封建大家庭的全部悲欢离合的历史’。”[1]小说中的人物大多都有巴金家族生活的原型,可以说,觉新就是巴金的大哥李尧枚,觉民就是巴金的“三哥”李尧林,而觉慧正是巴金自己。至于其它人物如高老太爷、克安、克明等人也都是以巴金的爷爷和几位叔父为原型而创作的。
事实上,这部小说还是巴金的精神自叙传,巴金与觉慧当时具有相近的思想水平和性格气质,他自己也承认,觉慧正是自己的影子。那么,符合逻辑的是,在觉慧的身上也折射了巴金本人的理想、愿望,甚至无意识愿望。所以,在鸣凤的书写中,也书写上巴金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潜意识。很多人指出过,鸣凤的气质更像一位小资产阶级女性,的确,在鸣凤身上我们见不到多少下层劳动者女性的痕迹,现代文学作品写到这类女性时,往往强调她们的健康、单纯,自然,甚至无知中的了无机心(如沈从文笔下的翠翠),而不应是具有过于优雅的气质,伤感、委婉的情感。而鸣凤甚至在劳作了一天后还有自我反思的习惯,细腻曲折的思考,自怨自艾的低徊之态都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性格特征。所以,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分析,巴金作为文本外的“觉慧”,事实上赋予了鸣凤以对等的小姐的身份,将鸣凤改换为了琴。
同样,由于觉慧是巴金文本中的替身,在巴金本人的潜意识中,自然要极力回护他,他的确也是这么做的。例如在鸣凤之死的情节上,作家就通过巧妙的叙事策略解救了觉慧的道德危机:通过觉慧的无意“疏忽”(何况还是因为忙于社会革命)与得知真相之后的疯狂寻找的补救行动,再加上伤心的忏悔与追忆,小说原宥、洗刷了觉慧的道德责任。其实,觉慧抽不出时间去听鸣凤的那两句话是牵强的,无论从日常逻辑还是从性格逻辑、情节逻辑上都说不通,但巴金必须如此安排,因为他无法承受觉慧事先得知鸣凤要送给冯乐山作“小妾”的后果:那样一来,就把觉慧推上了必须反抗,解救鸣凤的困局,不如此他将被蒙上道德的污点。但这种解救是觉慧所不能完成的,因为他可能根本就不愿意去完成,他不愿意为了鸣凤去承担一系列沉重的代价。所以,不管如何牵强,巴金都不能让觉慧事先得知这个重要的消息。鸣凤必须去死,而且这一动向觉慧事先应处在不知情的状态中。
从这一意义上说,《家》对觉慧的塑造正是巴金对自我形象的想象,这一美好境像正是他渴望成为的文化英雄。而鸣凤,一方面,作为价值客体,体现了觉慧的神圣魅力;另一方面,她的毁灭有力地突显了文化英雄所要反抗的旧势力的黑暗与罪恶,从而间接地成为觉慧们自身合法性的证明。在这一意识形态叙事策略中,鸣凤事实上并未获得现代意义上的人性的尊严,毋宁说,她的“主体性”又被新的压抑机制所贬抑。
然而,我们或我们年轻时的感动都中了巴金的叙述圈套,因为他笔下的爱情根本就不是爱情,这套爱情的话语是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制幻术,是一种神话。说到这里,我无法不引用黄子平先生对《家》的精彩的论述:“……‘爱情’——亦具有同样的咒语般的治疗或反治疗作用。……对奔向新前程的孩子们来说,它是信念,旗帜,屏障,是射入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是社会和政治进化乌托邦的情感对应物,唯独不是爱情本身。(《激流》三部曲中的“爱情”甚至有意无意地涤除了其中的性爱成分)……显然,非如此不足以保证爱情的纯洁性和战斗性。这种纯洁性和战斗性必然要求人物(尤其是是女性人物)殉道式的献祭。鸣凤,……湿淋淋的尸首,死者的形象既是控诉又是升华。爱情作为神话咒语的两重功能:诅咒与超度,完满地实现在这些死者美丽凄婉的形象上。”[2]
或许,还可以补充一点,这套制幻术还迷惑了作家自身,但是,在小说的字里行间,还是泄露了意识形态与作家潜意识内部的秘密。
[1]巴金.巴金选集:第1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426-427.
[2]黄子平.命运三重奏:《家》与“家”与“家中人”[J].读书,1991(12):96-103.
[责任编辑:林漫宙]
Invisible Writing of Modern Gender-Power Rel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Master-Servant Love Relationship in Ba Jin’s Home
LIU Yuan1,ZHANG Hong2
(1.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Hainan University,Haikou 570228,China; 2.School of Literature,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24,China)
While carrying out a psychoanalysis of the love between Mingfeng and Juehui in Home,the paper holds that the description of their love clearly reveals the subconscious desire of Ba Jin as a petty bourgeoisie intellectual and also embodies the gender-power relation with modernity.In this ideological narrative strategy,Mingfeng doesn’t gain the dignity of human nature in the modern sense,and to be exact her subjectivity is depreciated by a new suppression mechanism.
psychoanalysis,gender-power relation;subjectivity
I 206.6
A
1004-1710(2015)04-0100-04
2015-05-09
刘园(1992-),女,山东成武人,海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2012级学生。
张宏,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