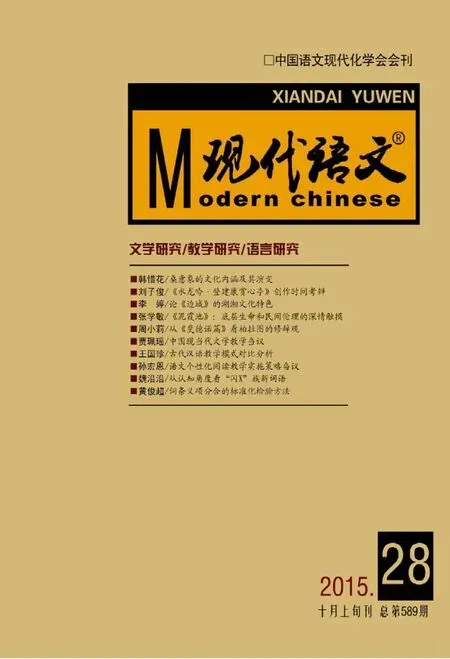桑意象的文化内涵及其演变
2015-03-01韩惜花
○韩惜花
文学研究
桑意象的文化内涵及其演变
○韩惜花
摘要:在神话中,“空桑生人”所显示出来的神性,是人类自我生殖力神化的曲折表达。到了《诗经》时代,源于神话的桑林崇拜则成为男女之间婚姻恋爱的独特背景。秦汉时期,历代文人有意识地借助桑林这一特殊意象宣扬新的伦理道德观念和文化价值观念。《陌上桑》及其拟作的大量出现正是这种现象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桑意象桑林崇拜文化内涵《陌上桑》
早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桑意象就已频频出现,有“日出扶桑”“空桑生人”之说。这两个神话传说表明,桑在中国古代的信仰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桑树被赋予更多的社会文化内容,桑树是神树、生命之树、生育之树,和女性生殖有着紧密联系。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古人选择桑林作为祭祀场所、桑林之社的行为以及后世大量与桑林有关的文学作品产生的原因。
一、桑林崇拜的神话与民俗之考察
桑在古人信仰中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中国古代民俗文化中产生了很多桑树生人的神话传说。许多圣贤英雄总是诞生在以桑命名的地方,这强化了桑文化原始信仰的神秘色彩。《易·否·九五》爻辞即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的呼喊,这一观念在“伊尹生空桑”等故事中明显地反映出来。《吕氏春秋·古乐》述颛顼生于若水,实处空桑,登为帝。夏朝开国者启,也是其父大禹与其母涂山女在桑树旁爱情生活的结晶。被中华民族长期尊为“至圣”的孔夫子,其出生地也离不开桑。为何这几位圣贤的诞生均与桑有关,这不能不令人想到古时桑林之约的旧俗和桑林祭祀祖先神明的动机,同时也表明古人对桑的强大繁殖能力的信仰与崇拜的浓厚意识。在文化意义上,桑“是古代生殖崇拜观念的象征物,代表着生命与生殖力, 因此才会产生桑树生人的神话。”[1]也正如法国著名汉学家桀溺早就指出的,圣贤的出生,“令人想起桑园是两性相爱的习惯场地,桑树也自然在传说中成了生儿育女的奇树了。”[2]以上桑生神话生动地体现出农桑文化和农桑信仰的特色,可见人们已经习惯于把桑林看作生命最初的发源地。
在中国,桑林成为殷商民族以及古代若干其他民族祭祀祖先神明的圣地,也成为了男女相会祭祀高禖的场所。这种“空桑生人”的桑林崇拜信仰,在稍后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地演变为实在的人间礼俗,桑所具有的生殖文化特征通过在桑林圣地举行的祀高禖、男女相亲相爱的古俗得以再次体现,桑林因此也就成为人间男女欢会野合的地方。据《周礼·地官·司徒》的记载,周代尚有“会男女”的礼俗,其时间在“仲春之月”,地点就在社祭的场所。《墨子·明鬼》云:“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路史余论》曰:“桑林者,社也。”可见桑林至晚在殷商时就成了社的代称。《春秋》记鲁庄公二十三年“如齐观社”,“三传”都以为这是非礼的行为。《国语·鲁语上》也认为此举为“弃太公之法”。《谷梁传》释“非礼”之故“是以为尸女也”。郭沫若先生据《说文解字》卷八释:“尸,陈也,象卧之形。”认为“尸女”即“通淫”之义。[3]所以鲁国的大臣以其不合礼制而反对鲁庄公前往。但齐人并不以此为怪,齐国社稷之祭,云集而至的青年男女,此时可以不拘礼法,不守禁忌,自由交往,甚至发生性关系。《左传·成公二年》:“巫臣聘诸郑,郑伯许之,及共王在位,将为阳桥之役,使屈巫聘于齐且告师期,巫臣尽室以行,申叔跪从文,将适郢,遇之,曰:‘异哉!夫有三军之惧,即又有桑中之喜,宜将窃妻以逃者也。’”[4]此则材料正道出了那时男女桑间欢会之习俗。这表明在周初的确存在一个较宽松自由的男女桑林相会的古俗。所以后世把男女偷欢淫逸之事称为“桑中之约”。青年男女之所以选择在桑中野合,其目的在于通过人的交配生殖行为,去影响农作物或大地女神的生长繁殖。《易》否卦九五爻辞云:“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这里的苞桑就是指生命力旺盛的桑树,桑树在中华古人的文化意识中是生殖、爱情的象征,表达了一种祈求生儿育女的危机感和急迫感。其大意是说,他要断子绝孙了,让人的生育能力像苞桑一样吧,让人的命运与苞桑联系在一起吧。宋兆麟先生在《生育神与性巫术研究》一书中则以大量的民俗、民族学资料证明,高禖祭祀后来演变为上巳节,其主要内容最初以求子、求偶为主,会男女则是其基本形式。[5]可见,桑林之社与男女之会、祀禖及后来的上巳节在本质上乃是一回事,它们的渊源都可追溯到神话中作为生殖信仰的桑树崇拜。这种桑中古俗在《诗经》中以“桑林”和“采桑女”两类意象而形成了最为诗意的表达。
二、 桑林原型在《诗经》中的积淀
据笔者统计,《诗经》中涉及桑意象的共有22篇,其中《国风》13篇,《小雅》7篇,《大雅》与《颂》各1篇。其中《魏风·汾沮洳》《小雅·隰桑》《鄘风·桑中》《魏风·十亩之间》《豳风·七月》等最为典型,诗中的桑意象皆是以桑林圣地男女之合的古俗为基础,从桑与生殖崇拜信仰的联系中引发出来的。
《魏风·汾沮洳》中写道:“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异乎公行。”闻一多先生认为“这是女子思慕男子的诗”。[6]诗中的女子采桑的地点是汾河边上,但她关心的并不是采桑之事,而是一位经过此地的小伙子。她不仅十分欣赏他那英俊异常的外貌,并且推测出他是不同于纨绔子弟的高雅青年,其爱慕之情溢于言表。今人或以为是思妇之诗,写一位女子是如何热切地等待“君子”到桑林中与她幽会的,诗中关于桑树枝繁叶茂的形象的反复强调,特别是关于桑叶的茂盛、柔润、幽郁的性状的尽情赞美,寄托着诗人对曾经欢会的深刻记忆与再度亲历的热切企盼。桑在这里既是写实,同时又喻指物境人事之好,成为代表着女性泛意识的一种独特的情绪符号。
《鄘风·桑中》又写出了青年男女在桑林中幽会的情景:“爰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根据传统的说法,“《桑中》,刺奔也。卫之公室淫乱,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窃妻妾,期于幽远,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此说显然与诗义不合。《诗经新解》认为:“《桑中》是卫国贵族青年抒写与情人幽会的诗。”[7]“这‘桑中’我以为即卫地的‘桑林之祀’,……‘社’为地神之祀,但后来也变成聚会男女的所在,与高媒的祭祀(祭媒神)相混。”[8]郭沫若认为桑中即桑林所在之地,上宫即祀桑之祠,士女于此合欢。[9]上古蛮荒时期人们都奉祀农神、生殖神,以为人间的男女交合可以促进万物的繁殖,因此在许多祀奉农神的祭典中,都伴随有群婚性的男女欢会。郑、卫之地仍存上古遗俗,凡仲春、夏祭、秋祭之际男女合欢,正是原始民族生殖崇拜之仪式。而《桑中》诗所描写的,正是古代此类风俗的孑遗。
又如《魏风·十亩之间》:“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桑者”当特指采桑之女。细味其意,此诗是以男性口吻,唱出了那种甜蜜中的尴尬。十亩桑林之内,已是采桑人散布各处,十亩桑林之外,还有采桑人在源源不断地前来,人多眼杂,不便久留。姚际恒《诗经通论》认为:“古西北之地多植桑,与今绝异,故指男女私者必曰‘桑中’也。此描摹桑者闲闲、泄泄之态,而行将与之还而往,正类此意。”[10]本来这就是一篇描写青年男女在桑中幽会的情歌。但故事的女主人公更大胆了,她在采桑时竟然不畏人言,公开与所爱的男子携手而行,同归共处。
在《豳风·七月》中还写到这样一种情况:“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这位女子似乎十分专注于自己的采桑劳动,但同时真正要传达的则是“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的情感。孔颖达指出:“公子为女公子,女心伤悲乃是民之风俗。”其实就是桑林会男女之风俗。方玉润说:“‘殆及’者,或然而未然之词也。”“《七月》二章的末二句应是指采桑女忧虑能否与‘公子’同时出嫁,而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仓庚鸣’的仲春之月,正值一年一度的祀高禖、会男女之际,身在桑林圣地的采桑女不能不‘无端而念及终身,无端而感动目前’。”[11]我们认为,《七月》二章同样应纳入桑崇拜的文化背景下,结合桑林男女的礼俗来理解。
人类学研究者认为,远古先民多以植物象征女性,而鸟则多与男性象征有关。鸟作为男性的比喻,桑作为女性的象征,二者一旦结合,同时出现于诗作中,就整合为一种有着特殊涵义的文化符号。鸠食桑椹,是桑林中常有的自然景象,这种景象又在某种特定的文化含义上,象征了桑林中另一种蔚为时风的人文景象,即上文所述与高祀的文化主题相关系的男女杂游或民间野合之俗。这一意象所具的隐喻作用,就直接发生于诗人对现实人生的作为和认知中。
总之,《诗经》中这些涉及桑意象的篇章都描写了女子采桑过程中对异性的渴慕之情,这代表着人类相诱相亲的最初渴望,而这也正是以自由结合为精神底蕴的桑林原型在民间的积淀,是原始桑林崇拜信仰在古代民间的继承和扩展。
三、后世文学对桑意象文化内涵的承继与异变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先民把桑林视为兴云作雨的神明,并形成了桑林之约这样的古俗。桑林由祭祀之所逐渐演变成了男女之间轻歌曼舞、谈情说爱之地。在山西襄汾张村东战国早期出土的青铜圆壶的颈部,有一组采桑舞纹饰,类似的图像还出现在四川百花潭圆壶、河南汲县山彪镇战国墓出土的青铜圆壶和河南信阳战国墓出土的青铜刻纹的椭圆杯上。这些青铜器上的采桑舞纹饰,是一种在中国古代非常流行的“桑间濮上”的民间歌舞,它也可作为一种古代贵族妇女的燕乐舞蹈和祭祀礼仪,即桑林之舞。这些材料其实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男女相会于桑林、唱歌跳舞、谈情说爱的社会风俗。因此,作为青年男女活动中心地的桑林,必然引起过路人注意。
战国以降,桑林中不时有调戏采桑女的风流韵事发生。《楚辞·怨世》中记载了孔子在桑林中的艳遇:“路室女之方桑兮,孔子过之以自侍。”西汉刘向《列女传》有秋胡在桑林戏妻之事,汉乐府《日出东南隅》描述秦罗敷坚拒太守的故事,只是情节略有变化。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在这几个故事中采桑女与男子相遇的地点都在桑林,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其原因在于桑作为一种古老的意象,有它特殊的文化内涵,而且这一传统文化内涵已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心中。创作者可能对人物情节等要素作改变,却始终割舍不下桑树情怀。正如孔狄亚克所说:“习惯做法和习俗,正如在生活中的大部分其他事物所遇到的情况一样,使这个本来是应需而生的东西,随后变成了装饰品,但是,在必要性不复存在以后,其用法却依然如故地长期存留下来了,特别是在东方民族中更是如此,他们的性格自然而然地与某种会话形式相适应,这种会话形式通过动作来充分表现出他们生气勃勃的性格,同时通过显明易懂的形象的不断反复的重视,使得这种性格得到极其满意的发扬。”[12]高祀、桑中祈雨、桑林相会作为从农耕文化和生殖崇拜文化中“应需而生”的特殊的“会话形式”,已经深深地植入人们心中,并且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
进入汉代社会,在儒家文化强有力的传播下,这种男女相悦欢会的行为已逐渐为儒家道德观念所不容,被视为离经叛道之举。但行之久远的旧婚俗并不那么容易从生活中完全消失,传统习惯在每代人心中总会留下深刻的记忆,不时地还有人想重温旧梦。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桑林是男女寻欢作乐的特定场所。男性对采桑女的追求、调戏乃至欢会野合是社会道德所允许并提倡的。只是随着文明的进步与礼制的发达,仲春之际的男女桑林欢合的古俗日渐消失了原有的特征,并日益受到指责,被涂上“淫乱”的色彩,《礼记·乐记》中就有将“桑间濮上之音”斥为“亡国之音”的记载。这种变化大约从春秋战国之际即已开始。《诗经·将仲子》即已透出这个信息,“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它虽然也是以男女欢会的古俗为文化背景,但女子的伤悲却是这一古俗与新起的礼教之间的矛盾在女性心灵中投下的阴影,女子开始“畏父母”“畏诸兄”“畏人之多言”,这和《桑中》《隰桑》等诗所表现出的男女相爱的天真、欢快、热烈的旋律很不一致,显得有些压抑、低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透露出“采桑”母题在未来的历史中必然发生文化变形的消息。
桑不再是自然意义上的桑,而是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文化内容。桑林的旧地时时引发人们的双向联想,由桑林可很自然地联想到男女幽会的旧俗,由男女的幽会又很容易联想到桑林。《列女传》中采桑女的言行体现了礼教规范下的一种必然选择,也是对中国传统女性忠于礼教的社会期待。而故事中的女子对男子求欢要求的不同方式的拒绝,所透露出来的乃是新旧两种道德观的冲突。上古桑林中的引诱结合变成了中古桑林中的断然拒绝,汉人通过秋胡戏妻等故事改造了桑林原型,宣扬了儒家教义。
《陌上桑》等一系列的中古桑林叙事诗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受汉乐府《陌上桑》的影响,魏晋至六朝采桑题材的诗文创作出现了高潮,有的拟作《陌上桑》,如齐人萧子显的《日出东南隅行》和陈人徐伯阳的《日出东南隅行》,都延续了《陌上桑》赞颂桑妇美德的主题。有的作品只铺陈采桑女的艳丽,如西晋陆机的《日出东南隅行》极力铺写桑妇的美貌,梁简文帝萧纲的《采桑》诗中的桑女形象亦美不胜收。有的侧重桑妇的空闺之怨,如南朝颜延之《秋胡诗》中桑妇呼唤着忠贞的爱情,齐人王融《和南海王殿下咏秋胡诗》抒写桑妇思念丈夫的幽怨离别之情。梁代吴均《采桑》云:“无由报君信,流涕向春蚕。”抒写桑女的相思离别之苦。这些诗作的主题各有不同,但都是在遵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这一基本前提下展开的。
总之,在神话中,“空桑生人”所显示出来的神性,本是人类自我生殖力神化的曲折表达。到了《诗经》时代,源于神话的桑林崇拜则成为男女之间婚姻恋爱的背景。在《列女传》和《陌上桑》中,桑林则又由男女相爱的圣地变为男女冲突的场所。作为生殖圣地的桑林蜕尽了神圣的色彩,源于男女生命本能的桑林欢会活动被无行文人对采桑女的调笑与纠缠所替代。这正是古俗消失、新道德观念逐渐确立、文化价值观念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而《陌上桑》等诗中的采桑女对男性所持的与先秦女性不同的态度,则是新旧两种道德观念的冲突的体现,也是封建礼制对妇女日常行为规范要求加强的体现。
注释:
[1]刘怀荣:《“采桑”主题的文化渊源与历史演变》,文史哲,1995年,第2期。
[2]桀溺:《牧女与蚕娘》,钱林森:《牧女与蚕娘——法国汉学家论中国古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77页。
[3]郭沫若:《郭沫若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45页。
[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05页。
[5]宋兆麟:《生育神与性巫术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
[6]闻一多:《风诗类钞甲》,《闻一多全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67页。
[7]雒三桂,李山:《诗经新解》,济南:齐鲁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页。
[8]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05页。
[9]郭沫若:《甲骨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8页。
[10]姚际恒:《诗经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67年版,第95页。
[11]李先耕校,方玉润著:《诗经原始》,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2页。
[12]孔狄亚克:《论语言的起源及其进步》,《人类知识起源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38页。
(韩惜花山西太原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030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