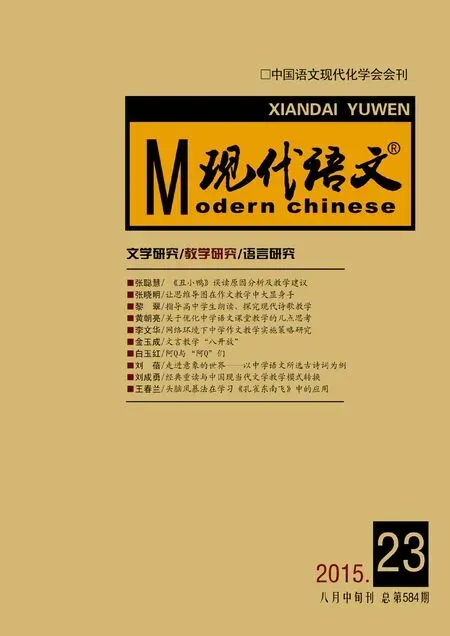阿Q与“阿Q”们
2015-02-28白玉红
◎白玉红
一
毫无疑问,《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中最著名的一篇,也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它向我们展现了辛亥革命前后一个畸形的中国社会和一群畸形的中国人的真实面貌,这一形象已经成为文学史上永不褪色的经典。
20世纪初的中国处于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政治上,古老的中华民族一直遵行的封建帝制正在慢慢瓦解;社会上,传统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要面对来自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辛亥革命虽然在形式上推翻了满清王朝,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阿Q正传》即以这一时期的中国农村社会为背景,其描写的未庄是一个极端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而阿Q则是一个身心受到严重戕害的落后农民的典型。小说共九章,每三章可构成一个部分。前三章写阿Q的阶级地位、经济地位,概括勾勒阿Q以“精神胜利法”为中心的性格特征;中间三章写阿Q遭遇的压迫和剥削,进一步刻画阿Q的性格,表现阿Q的处境,揭示了时代矛盾;后三章写阿Q在革命到来之后的性格变化和悲惨命运。
《阿Q正传》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它成功地塑造了阿Q这个令人难忘的艺术典型。鲁迅直指个体内心,探寻灵魂世界的秘密。他身上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国人的几乎所有弱点:愚昧、奴性、自私、胆怯、因循守旧、敌我不分、极度自尊与极度自卑、欺软怕硬、自欺欺人等等。阿Q愚昧,他死到临头还相信“人生在世总免不了被砍头的”,甚至还为签字画押的圆圈画得不圆耿耿于怀;阿Q奴性,他“造反”要得到“假洋鬼子”的批准,见到“知县大老爷”就忍不住两腿一软要跪下去;阿Q自私,他为了自己的生存不惜与王胡、小D作对;阿Q胆怯,他抢劫也只敢望风,明明垂涎举人的财物,听见枪声却只敢远看;阿Q因循守旧,他幻想革命成功也就是把秀才、“假洋鬼子”家的家具搬到土谷祠,而不是搬进秀才家,他还嫌弃吴妈“脚太大”;阿Q敌我不分,一旦革命成功,他认为“第一个该死的”居然是与他一样受压迫的王胡;阿Q极度自尊同时极度自卑,他老是说“先前曾经阔过”,但是一旦受到打击,就说“我是虫豸,好嘛”,“第一个自轻自贱”起来;阿Q欺软怕硬,他欺负比他更弱小的小尼姑和小D,不敢反抗任何一个比他强大的力量;阿Q有着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他被打了,心里说“儿子打老子”,他画圆画不圆,就说“孙子才画得圆呢”,甚至可以在吃亏后打自己几个嘴巴,觉得“打的是一个人,被打的是另一个人”,于是就心安理得地胜利了……
每一个成功的文学典型都是共性内容与个性形式的对立统一,而其共性内容又必然是历史具体性和社会一般性的对立统一。阿Q也不例外。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其行为表现是乡村流浪雇农的写照;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其奴性性格是专制主义的产物;从心理学的角度看,阿Q是分裂人格的典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其性格是反映辛亥革命必然性及局限性的一面镜子;从哲学角度看,阿Q又是人性异化的典型。由此可见,对于阿Q这样复杂的典型性格,很难用线性的因果关系从单一角度来加以解读,其系统的典型意义或认识价值,不仅大大超出了鲁迅创作当年执意在《阿Q正传》中写出“现代的我们国民魂灵”来,并由此而“开出自省的道路”的初衷,而且超越了阶级、国界和时代,揭示了人类普遍的人性弱点。就像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说的:“阿Q不但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
当然,《阿Q正传》的卓越之处不仅在于其精神内涵的深广,还在于其艺术格式的别致,其“讽刺的写实模式”和“悲喜剧交融的风格”,被评论界誉为综合了传统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等各种不同趋势的有别于传统写实并卓具现代审美特点的“更为高级的现实主义”,代表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学走向主客观交融的最新趋向。
二
《阿Q正传》充分显示了鲁迅卓越的文学创造力和想像力,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也影响了一代中国文人的创作。它自发表之日起就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但它并不是作为一个完成了的终极产品摆在人们面前。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中,它作为被改造的“国民性”的一种文化原型,被不断地解读模仿再创造,成为文学史上颇有意味的文学现象。
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时期作品中的“阿Q”相具有麻木、遗忘、欺软怕硬的特点。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社会是一段被压迫民族不断摆脱奴役、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反帝反封,实现民族解放等意识成为影响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主导性因素,新文学也就自然而然地承担起改良社会人生,改造国民性的责任。而阿Q身上所具有的因长期受压迫而导致的精神奴役和鲁迅对旧传统的深刻批判意识顺应了时代的主题,对小说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时期的作家,特别是文学研究会的乡土小说作家群,自觉师承鲁迅,塑造了不少具有“阿Q相”的人物形象。许钦文的《鼻涕阿二》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菊花既是被奴役者又奴役人的性格,有明显模仿《阿Q正传》的痕迹。阿二在家里经常受到祖母、姐姐等的戏谑、侮辱,就象未庄人侮辱阿Q一样。阿二从肉体到精神上都遭受了极大的摧残,但她却总能在巨大的屈辱中无赖般地乞求、苟活,并总能在自我安慰中实现心理平衡。甚至连丈夫阿三沉水死去,自己又被婆婆卖掉这样的悲惨命运,她也能“默默服从”。然而她一旦当上了有钱人的姨太太,由奴才变成了主子,就转而去虐待奴婢,其打骂的架势和威风决不亚于阿Q欺负小D和小尼姑的。阿二这种麻木、自欺欺人以及欺软怕硬的奴才心理不正是一个活脱脱的“女阿Q”吗?又如王鲁彦的《阿长贼骨头》。这篇小说的主人公阿长也和阿Q一样都生活在落后的村镇,他们一样是流浪汉,一样偷盗,迷恋又瞧不起女人。在现实生活中,他向来搞不清该恨谁、爱谁。偷项圈被打,脱身后却很快忘了这段屈辱史而去变着法报复比他更弱的人了。这阿Q式的“遗忘”使阿长心里“舒服的非常”,极具讽刺意味。再如蹇先艾的《水葬》中的主人公骆毛,因偷东西被抓,就被村人按当地风俗沉入水中处死了。小说写闭塞的边远乡村,人们还受着原始野蛮习俗的愚弄,对于水葬之类的暴行,既不以为残虐,更没有想到改变它,仿佛这样做是天公地道,而受害者骆毛在被处死时也说:“再过几十年,又不是一条好汉吗?”又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而旁人则无一不麻木不仁地赶去充当看客。小说充分地揭露了农民的愚昧、麻木、自欺欺人的特性。同样的作品还可举出彭家煌的《陈四爹的牛》、王任叔的《阿贵流浪记》、许杰的《赌徒吉顺》、台静农的《天二哥》等。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无一不明显地带有阿Q精神的烙印。与鲁迅笔下阿Q相比,这些作品中的“阿Q相”在本质上没有大的改变,同样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村人,都具有愚昧落后、麻木不仁、健忘以及自欺欺人、欺软怕硬的奴才心理,是对阿Q形象的补充和反复昭示。当然,由于受到时代变化及作者自身思想认识深度和艺术气质的影响,这一时期作家作品中的“阿Q相”又有其独特的特点。这些乡土作家不是始终扎根于乡土的,而是一批远离了故乡,寄寓在北京、上海等都市中接受现代文明洗礼的年轻人。他们在都市经受现代文明的种种冲击,再回头审视自己早年生活过的穷乡僻壤,对本土文化进行历史的“反观”与“反思”,虽然视野较开阔,但还缺少把握农村复杂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眼光,往往单纯地描绘出了落后愚昧的农村生活图景,只摹写出了阿Q的相貌,难以写出阿Q魂魄。又因为他们习惯于以一种居高临下的眼光来审视,因此对这种“阿Q相”往往批判有余,同情不足,甚至冷嘲热讽,难以达到鲁迅的深邃,但他们那种强烈的启蒙意识和责任感却具有进步意义。
新文学第二个十年中的市民阿Q,具有苟安、攀比心理,出人头地的名利思想。与农民阿Q相比,这一时期作家的视角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向读者展示了城市小市民、小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和生存状态。故事的主人公涉及了更广泛的领域,包括工人、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本家等。他们除了具有阿Q的盲目自大、自欺欺人和奴性心理外,同时还具有市民文化的独特特点:苟安、懒散、攀比心理以及梦想出人头地的名利思想等。20世纪20年代末的中国,由于西方工业文明的强烈冲击,引起中国从城市到乡村社会生活的急剧震荡,产生了现代都市与传统农村的严重对立和相互冲突。这一时期作家较多关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化过程中的社会各个阶层的历史命运及性格。但阿Q时代并未死去,而是得到了不断地延续,描写对象扩展到了市民阶层。例如以写“京味小说”而著称的老舍,他第一个把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过程中在东西方文化互相撞击影响下,中国小市民阶层的命运、思想与心理引进了现代文学领域并获得成功。他的长篇小说《赵子曰》写的是北京一群大学生虚度年华,消极颓废的生活,赵子曰讲究面子、爱慕虚荣、受人奉承便得意忘形,连考试时名列榜末也自我安慰:“倒着念不也是第一么?”又是一个典型的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老舍笔下的人物形象虽然是城里人,但仍是“乡土”中国的子民,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的包袱,他们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都是很保守、闭塞的。《二马》中的主人公马则仁即使走出中国来到伦敦,置身于西方现代文明的文化氛围中,也仍然迷信、中庸、懒散、奴性十足地生活于洋人之间。他的生活信条就是得过且过,他和阿Q一样,都是落后的国民,只不过阿Q生活在老中国的乡村,老马则是华侨,旅居国外。老舍有意把老马放到异国情景中去刻画,试图从中西文化比较中更明显地突现落后国民性的悖谬之处。同样的例子还有张天翼的《包氏父子》中的包氏父子,他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不尽相同,但在追求心理满足这一方面,与阿Q之间又有割舍不断的联系。
三十年代下半叶,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作家们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倾向,抗日文学不断涌现。另外,由于民族矛盾极度恶化,促使作家们重新寻找中华民族落后的原因,阿Q精神话题又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沿着鲁迅开创的“改造国民灵魂”的文学道路不断探索的作家,在30年代初期的东北作家群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与鲁迅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女作家萧红,她以强烈的批判意识,从描绘故乡生活中去针砭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的缺憾。她的被誉为“沉默国民的灵魂的别传”的《呼兰河传》中那些呼兰河人,因循守旧、头脑麻木、自欺欺人又盲目自大,以阿Q式的精神欺骗来平衡自己。明知吃的是瘟猪肉却不承认,大家心照不宣就行。其中的有二伯更是心甘情愿于自身奴隶地位的阿Q。有二伯的籍贯不清楚,姓名不清楚,只有一个乳名“有子”,如同阿Q。有二伯的人生态度为“虽然也长了耳朵,但一辈子也没听到什么”,这足以代表呼兰河人的人生态度。萧红和鲁迅一样,也深深体会到中国人麻木、愚昧的精神状态,并为他们这种自欺欺人、自我满足的生活状态感到痛苦。在《呼兰河传》中,萧红也描写了一些看客,看“跳大神”,看洗“热水澡”,看冯歪嘴媳妇和小孩的无聊的人。这些看客不仅麻木地看着他人他物(猪、鸡、马)的悲惨命运,而且也麻木地看着自己的人生道路。“看客”的出现,表明了作家对封建文化的批判不仅仅停留在浅层次的野蛮陋习上,而且达到了文化心理和人格的深度,揭示了这些人内在生命力的萎缩和枯竭。萧红通过“看客”的众生相、社会相,画出了沉睡的国民灵魂,在历史文化的批判中蕴涵着改造国民灵魂的愿望。所不同的是,鲁迅展示的是阿Q灵魂的麻木,笔触着力在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而萧红的《呼兰河传》则戳到了人物生命层面的痛穴,“他们就是这类人,……逆来的,顺受了”。萧红表现的似乎是更加本原的永恒的苦难,她从生存的意义上把生命意识的麻木写到了极致。
中华民族身上因袭的精神负荷太重了,这就决定了其摆脱“阿Q”式的病态走向新生的过程必然是艰难而又漫长的。路翎的一系列小说就深刻体现出这一点。如《罗大斗的一生》中罗大斗是一个在父亲的颓废和母亲的恶毒打骂中长大的破落户子弟,从小就养成了下流、卑怯、欺诈、谄媚的奴性。作为阿Q的隔代子孙,罗大斗以其鲜明的遗传基因与他的前辈取得了血缘上的认同。
与前两个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作品更加成熟而深刻。萧红的《呼兰河传》将批判的触角深入到造成这种国民劣根性的保守顽固的封建制度上,从而使作品蕴涵了改造国民灵魂的思想意义,达到了与鲁迅的不谋而合。而路翎的进步性在于他并不是简单地写出了人物的“阿Q相”,他已经深刻认识到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农民的觉醒和解放决不是一个简单而轻松的过程,其中必然包含着剧烈而痛苦的心灵针扎。因此,他的作品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和物质上的贫困,不仅仅为他们的苦难和不幸悲凉地哀叹几声,他所关注的是如何使他们从平庸疲惫的生活和愚昧胆怯的性格中解脱出来。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基本目的是希望在批判剔除国民性弱点的基础上重塑国民灵魂,但对于具有理想的国民性格的“新的人”,鲁迅却未曾在作品中表现出来,而路翎在民族处于血与火挣扎奋斗的年代,在他的作品中塑造出了具有“原始强力”和“英雄性格”[1]的人物作为新的国民性的理想模式之一,并希望借此否定和对抗疲软的生存状态,振兴起民族的精神与生命,因此显示出了进步而深远的意义。
三
阿Q形象在鲁迅之后的作家笔下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改造和重塑,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鲁迅巨大的影响力和阿Q形象强大的艺术魅力使然。黑格尔说:“一个艺术家的地位愈高,他也就愈深刻地表现出心情和灵魂的深度,而这种心情和灵魂的深度却不是一望而知的,而是要靠艺术家沉浸在外在和内在的世界里去探索,才能认识到。”[2]在20世纪那个动乱的时代背景下,鲁迅创造了神奇的艺术形象——阿Q。阿Q的形象无疑是经过艺术夸张了的,但他的“精神胜利法”、他的悲剧命运,却不是无中生有、主观臆造的,而是深刻地揭示出了中国人灵魂深处最真实最顽固的一面。鲁迅说过,他写《阿Q正传》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伪自由书·再谈保留》),是想“写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并揭示出造成这种国民性弱点的根本原因,即以儒家、道家、佛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和封建制度。鲁迅借此对我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地剖析和批判,认为正是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思想,对中国人起到了麻醉的作用,它扼杀了人的个性,把人变成没有个性和自主精神的奴隶,甘于过着敷衍了事、苟且偷生的生活。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吃人”的文化,但是,“吃人”的凶手一方面来自封建制度和伦理道德,另一方面则来自被传统思想僵化了的人的内心。最可悲的是已经麻木了的民众,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吃的悲惨命运。所以,要把中国人解放出来,就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通过社会革命砸破旧的制度;另一方面要充分揭露传统文化的罪恶,把人们从愚昧、野蛮和奴隶的心态中解救出来。鲁迅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创造了阿Q这一形象。阿Q是一个“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3]的奴隶,他不仅呈示了清末民初的一个普通百姓的灵魂,更是借这一形象多方面地曝光了国民性的痼疾。阿Q虽然被枪毙了,但他的阴魂不散,时时附在中国人的身上,因为这种国民性弱点已深深植根于国人的灵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新民主主义的胜利,民族生存危机正一步步缓解并逐渐消失,而“国民性”问题却依然存在,从一代代作家对阿Q精神的阐释中可以看出,阿Q精神具有极强的延续性。因此,对阿Q精神的批判不仅属于鲁迅,也属于后代有志于启蒙国民灵魂进步性的作家。
《阿Q正传》是建立在现实真实基础上的经典力作,蕴含了极其丰富的生活哲理,对人性剖析也极具深度。无论是从思想性或艺术性来讲,都有极高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阿Q以及以后子孙们身上的“精神胜利法”可以说是近代的一种社会思潮。在20世纪上半叶那个特定的时代里,封建统治阶级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疯狂侵略造成的不断失败的处境,既无法清醒地正视现实,也无法承认失败,更无法奋发图强,可他们照样要维持其统治,于是,自欺欺人、自我安慰的“精神胜利法”便应运而生了。从农民自身而言,奴隶的地位和反抗失败的历史,也是产生和接受“精神胜利法”的温床。因而,阿Q形象有着恒久的意义,它既是一个时代依稀可见的背影,又是一面镜子,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在里边照出自己的某一形象来,这也是阿Q形象的典型意义之一。
注释:
[1]何满子.读鲁迅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71.
[2]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张环,李志远,魏麟,杨义.路翎研究资料[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7: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