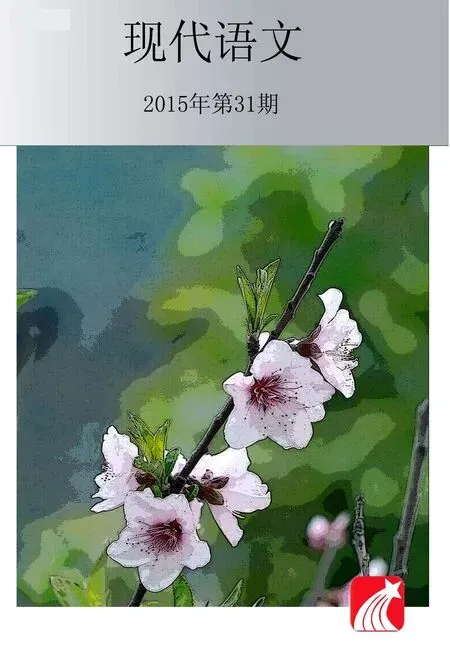李锐小说研究综述
2015-02-28许菲菲
○许菲菲
李锐小说研究综述
○许菲菲
摘要:李锐作为创作数量较大、创作成绩突出、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当代作家,一直受到评论家的广泛关注。纵观近40年对其作品的研究可以看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其单部作品的解读与评价,尤其是几部广受欢迎的长篇小说;二是贯穿性单方面研究和论述,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对其作品的叙述语言、叙述技巧以及主题意义的关注;三是整体性综合分析和比较分析,从李锐总体的创作出发来定位他的文学作品在当代文学格局中的地位,发掘其中的特色以及存在的局限。
关键词:李锐小说研究综述
李锐,男,1950年9月出生于北京,祖籍四川自贡。自1974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开始,迄今为止已发表各类作品百余万字。出版有小说集《丢失的长命锁》《红房子》《厚土》《传说之死》,长篇小说《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银城故事》《人间:重述白蛇传》(和蒋韵合著)、《张马丁的第八天》,另有散文集若干。同时李锐的作品曾先后被翻译成瑞典文、英文、法文、日文、德文、荷兰文等多种文字出版。
尽管李锐的作品备受关注,也曾数次获奖,但就当下的作品评论而言,还是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其散文《拒绝合唱》尽管报纸、网络等媒介对其报道不少,但搜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却只有一两篇文章,其另一部散文《不是因为自信》更是没有专业性的评论文章出现;在小说方面,其中短篇小说集《丢失的长命锁》《红房子》《传说之死》《假婚》也是几乎没有评论性文章。李锐以短篇小说见长,但他最受评论界关注的作品是其长篇小说,每部作品都有为数不少的评论,但是即便如此,长篇作品的评论还是存在很多有待梳理和甄别的问题。
本文在追踪了近40年来众多的研究文章之后,重点选取了当代文学评论界多家权威刊物和一些知名评论家的代表性观点,综合论述李锐小说中的热点问题,对李锐小说研究做一番梳理,试图寻找研究的薄弱点和空白点,以便深入研究。研究李锐的文章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对单部作品的解读与评介;二是贯穿性单方面研究和论述;三是整体性综合分析和比较分析。
一、单部作品的解读与评介
《厚土》是李锐写的一组七篇副标题为“吕梁山印象”的集束短篇小说的总题目,1989年十一月同时由国内有影响力的大刊物(《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山西文学》)分别推出,一时引起评论界的强烈关注。时至今日,这种延续性的关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艺术技巧方面,在这个方面又可以分出两个分支,一个是从传统文论的角度进行的批评,以金汉的《短篇艺术的新收获——读李锐的集束小说《厚土》和韩鲁华的《〈厚土〉透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艺术视觉:读李锐小说〈厚土〉等三篇》为代表,如题,两篇文章分别从短篇小说的形式创新和心理结构的刻画这两个方面来论述。李锐作为一名本土性很强的作家,倡导用“方块字”来表达自我,可以看出,李锐的创作初衷还是比较传统的,延续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发展脉络,所以说从古代文论的角度来对其进行解读还是比较贴切的,研究者也相当多地集中在对这方面的开拓上,他小说的形式以及人物的刻画手法是非常突出的两个方面。另一个分支是从现代文论的角度来进行批评的,以罗丽娜的《新历史主义语境下李锐〈厚土〉的美学价值》和李彦文的《永世为农的文学表达——重读李锐〈厚土〉系列小说》为代表,两者分别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和审美批评的角度对《厚土》进行了解读,这种解读多少有些“牵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当下作家的任何创作都不可避免地暗含着“现代性”或者说“当代性”的部分,即便作者是无意识的,所以说评论家在这个层面的挖掘对于李锐自己的创作或者是其作品的多角度的挖掘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厚土》另一个层面的关注主要体现在对其价值取向的论述,以对其中的女性形象和它所体现的中国文化为重点。河南大学王艳云所写的《黄土地上的精神守望——〈厚土〉的价值取向新论》具有很强的总结性,其对《厚土》进行了回顾和重新解读,指出了它的立意在于“土”,并指出了“土”的表现形态,李锐大多数作品都是以“土”为核心的,如何去解读它的丰富内涵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王艳云的这篇文章着重指出了它的民间文化传统和民间生活方式这一“民间“的立场,具有启发性。
1993年李锐出版了长篇小说《旧址》,这是一个讲述有着近2000年历史的古老家族的故事,背景宏大、叙事老练,却并没有像《厚土》一样在中国评论界引起广泛争议,但在美国却得到了很大的认可,李国涛翻译的美国著名评论家菲利普•甘朋发表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上的《盐的歌剧》代表了外国知识分子眼中的李锐叙事。他们指出,李锐的叙事风格优美地融合了各种因素:编年史、抒情诗甚至是某些戏剧性。仅就这一点而言,国内的评论家是很少关注的。用一种西方的视角来解读中国极具本土性的作品,这篇评论性的文章是起到了某种示范作用的作品,不仅仅是西方的资源“为我所用“,更多的是站在一个东西方融合的立场来评介作品,才能算得上是比较公正的。在国内,对这部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家族叙事的探究和对人性、历史的主题探究这两个方面。事实上就像李洁非所说:“《旧址》作为一部家世小说不同于以往任何同类作品的地方,例如《家》《春》《秋》三部曲、《子夜》甚至《红楼梦》——在这些小说中,家族的衰落无非就是家族的衰落而已,可是,这在《旧址》里却意味着一种文明总的句号。”或许这也就是作家李锐创作这部作品的初衷,也因此可以说这些评论的延展性较小,都是围绕着一个小的方面不断地延伸,没有可以称之为“创新”的东西。
李锐于1996年出版长篇小说《无风之树》,李锐说:“自从《厚土》结集之后,有三年的时间一直没写小说,之所以不写,是因为心里一直存一个想法,怎样才能超越《厚土》……直到写完《无风之树》,我才觉得这一次是真正超越了自己,这中间花了整整六年的时间。”这部被李锐自己称为“超越了自己”的小说也的确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但关注的重点由《旧址》时期的主题性分析转变为了艺术技巧方面的超越,即便是在李锐好友李国涛、成一等为《无风之树》举办的讨论会上,即整理而成的《一部大小说:关于李锐长篇新著〈无风之树〉的交谈》中,大家的关注点也都放在了写作的“技术性”层面之上,包括故事结构、叙事方式,等等。相应地,批评界对这部作品的关注也主要集中在口语倾诉和叙事策略上,以《叙述就是一切:李锐小说〈无风之树〉的叙事学分析》为代表,将这部作品的叙述和叙事进行了细节性的解读。当然,也有两三篇文章对这部作品的主题思想进行了分析,王春林所写的《苍凉的生命诗篇:评李锐长篇小说〈无风之树〉》最有借鉴意义,他作为长期跟踪李锐写作的评论家,在这个时候对文本的生命价值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解读,对纠正批评的片面性具有重要意义。综上所述,对这部作品的关注还是存在很严重的“侧重”的,当然,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李锐作为一位成熟的作家,在进行了持续的“叙述训练”之后所能达到的“讲故事”的高度,在哪些方面有了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延展。但倘若对这部主题繁复且具有交响性质的长篇创作缺少一种主题性的把握,不得不说是一种缺憾。
继1996年出版长篇小说《无风之树》后,1997年李锐又接着出版了长篇小说《万里无云:行走的群山》,这部作品远没有《无风之树》来得热闹,基本没有引起评论界的多大关注,对它的解读也不完全,但是仅有的两篇评论性文章似乎已经足够说明这部小说的价值。著名评论家南帆发表了《叙述的秘密——读李锐的长篇小说〈万里无云〉》,从话语类型、自然环境、传统文化等几个细节入手对其进行了解读,而周政保的《口语倾诉的方式(或叙述就是一切)——关于李锐的长篇小说〈万里无云〉》从口语叙述的角度对其做了细致的解读,但也仅仅局限于此。《万里无云》和《无风之树》作为两部“捆绑式”出版的作品,显然不可能使它们同时得到应有的关注,而且李锐的这部作品也多有重复自己之嫌,两部对文革进行文化批判的作品立场大同小异,遭到冷落或许也是可以理解的。
李锐小说中有一块神圣的版图——他的故乡四川自贡,他以自贡为原型的作品除了上述的《旧址》之外,还有2002年出版的《银城故事》,这距离上部书稿的出版已有六个年头,这种沉寂在某种程度上也显示了作者的某种野心和转变。《银城故事》描写了一座由地质资源开采、开发、发达继而到资本迅速膨胀的内陆城市。评论家对于这部作品也极为关注,主要表现在对其主题意义的探索上,这种探索集中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张力表现上。在这个方面探讨比较成熟的有王春林的《智性视野中的历史景观》和顾明霞的《现代性的历史失败与启蒙者的话语悖论》,前者侧重于对不同于教科书的历史观念的挖掘,而后者侧重于现代性和启蒙的关系,这是两篇中规中矩的评介文章,但他们的扎实就在这个地方——对这样一部对中国民族资本进行宏大叙事的作品来说,越是贴近传统,越是符合李锐对城市、革命和人生的基本观念。当然,不可否认,作为一部成熟的作品,肯定具有多方位的的视点,评论家对这部作品的关注还显然不够。
2006年李锐出版了新的短篇小说集《太平风物:农具系列展览》,这部小说集共有十四部短篇小说(另有两篇附录),每部小说都以一种农具命名,格式统一。这部作品的出版是李锐给文坛带来的巨大惊喜,但同时,在这十四部短篇中,每篇作品受到的关注度并不是等同的,甚至还有很大的差异。评论家谈论较多的是《袴镰》《残藕》,其次是《犁铧》《连枷》。总体来说评论家对这部小说集的关注度和这部作品应该挖掘的意义并不相匹配,就现有的评论而言,也是拙多精少。对于这些作品的艺术技巧,谈论的文章很少,以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赵晖的论文《寂静之维下的艺术探索——评李锐“农具系列”》最为精到,其针对这部作品中的艺术手法和技巧进行了较为精准的分析,算是弥补了这一缺憾。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论文发表的时间为2005年,而作品出版的时间为2006年,这个时间错位,更可看出评论者的一种综合观察、体味的超前眼光。大多数评论家是在“农具”这一特定概念所引申的意义上作文章,从农村的现代性(田园的衰落)、生存的苦难这一体两面着手来试图解读李锐的文化思考和批判。李锐针对这部作品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说过:“如果仅是对社会的批判与关注,我不会写这些小说。如果我只是写农具都消失了,农民很贫困,他们被欺压被剥削,是被侮辱被损害的,那还停留在批判现实主义或者社会学的层面上。”然而现实是大多数的评论家也仅仅是对这个层面进行解读。这是一部可谓前无古人的作品,如果进行更深入、更有意义的解读,我想应该是批评家要关注的问题。
“重述神话”是由英国著名的坎农格特出版社发起,邀请各国著名作家对其本国的神话故事进行再创作。继苏童的《碧奴》和叶兆言的《后羿》之后,李锐和其妻子、著名作家蒋韵联袂推出了“重述神话”系列的第三部《人间:重述白蛇传》,将民间流传千年的人妖之恋做了一次属于他们的叙述。它于2007年问世以来,得到了诸多评论家的一致好评,大家惊叹于两个风格成熟且差异很大的异性作家的完美融合。但也因此,很难去说这部作品是属于李锐的还是蒋韵的,所以在评价这部作品时也就需要摒弃双方的风格影响,就作品而言就足够了,所以我们在此不再论述李锐在这部作品中的表现,仅仅指出这部作品对李锐而言又是一次超越。
李锐最新的长篇小说是出版于2011年的《张马丁的第八天》,虽然李锐一再强调这部作品名称中的“张”和“马”要用繁体字,但是在书籍的流通和传播过程中还是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表明了李锐对“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我”的坚持,特别是对于这样一部描写晚晴的动荡、义和团的兴起、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的作品。李锐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已经是花甲之年,但他说:“这部作品不是他的‘终结之作’,而是他的‘开始之作’。”也许由于这部作品是新作,评论家还没有来得及认真探索,对这部作品的评介到目前为止还是很少很薄的,和其之前的作品相比,显然没有显示出应有的影响力。倒是李锐自己不得已站出来说话了,他详细地讲述了自己创作的背景、吸收因素以及创作的企图(见《“煎熬“的历史观:〈张马丁的第八天〉及其他——作家李锐笔谈》和《李锐:来一次没有遮挡的“正面进攻”》)。在评论家的评介中,王春林的《纠结:文化冲突中的人性困境透视》算是李锐的一篇知音之作,从“文化冲突”这一具有现代性的角度对其作品进行解读就有了更大的视野和更深广的包容性。但除了这篇文章之外,也罕见其他深入的解读,这和这部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性是不相匹配的,所以说对这部作品的评介还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二、贯穿性单方面研究和论述
李锐作为一个风格鲜明的作家,对其整个创作过程做贯穿性的分析,以便能够解读出“李锐之所以成为李锐”的原因,对于更好地理解他的作品,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评论家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探索和努力。
这些研究文章有明显的类别划分:较少部分的文章在对其做叙事技巧和创作语言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大部分的文章都在对其进行主题价值意义方面的探讨;显然,在评论家眼里,李锐对于中国文化、中国人心理的探究远远要比其对文体的创新和探索值得重视。
对其创作语言,评论家的主要着眼点大多放在了其对语言的自觉性追求、口语化叙述和语言的诗性特征这三个方面,而且仅就这三个方面而言,论述的也不是非常完整和彻底。以康志宏的《“语言自觉”的呐喊——评李锐创作中的语言意识》和李娜的《谈李锐小说对语言的自觉追求》这两篇文章对李锐对语言自觉性追求的解读为例,就存在很多问题。事实上,李锐不仅在创作中自觉地贯彻自己的语言自觉,而且李锐自己就曾发表过《语言自觉的意义之一、之二、之三、之四》《被简化的语言》等对语言自觉进行探讨的文章。如果在李锐的这种引导下更好地解读其作品,走得更深入,才是评论家真正要关注的。可现实是上述两篇评论文章都是在李锐自己论述的周围进行“隔靴搔痒”式的解读,没有新鲜的观点呈现,更没有更进一步的深入,重复李锐本身不能构成解读,这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说是一种失败。
李锐的叙事也是很多评论家的主要关注点。在这方面的研究显然要比对其语言的研究来得丰富和全面,论述的角度涵盖了叙事姿态、叙事修辞、叙事结构、叙事声音、叙事视角等几个非常重要的维度,阐述也非常到位。比如翟永明的《李锐小说的叙事结构分析》就将李锐的小说结构分成了钟摆式结构、众星拱月式结构、时空交错式结构、多线并置式结构这四种类型。又以王秀红的《浅析李锐小说的叙事视角》为例,她把李锐作品的叙事视角分成了零焦点叙事、内焦点叙事和外焦点叙事这三种类型,文章浅显易懂而富有说服力。他们的共同点就在于抓住了李锐的“立场”:李锐作为一名致力于讲故事、讲好故事的作家。在这个层面上讲叙事应该是他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理应对叙事进行非常深刻和丰富的探索,显然评论家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充分。问题在于李锐作为一名风格独特的作家,他的叙事和其他同类型的作家叙事有哪些异同,他在哪些方面又做了何种程度的创新等问题却没有任何评论家关注到,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伟大作家的区别不在于都是用了某些技巧,而在于独属于他的技巧他使用得到不到位,这是非常重要的。
评论家对李锐主题意义的评介和解读,呈现出非常驳杂的局面。如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对李锐主题意义的探究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各抒己见”,每个人都可以“言之凿凿”。但从另一角度看也显示出了某种问题。以对李锐小说中的悲剧意识进行的评介为例,就有《李锐小说的悲剧意识》《李锐小说中的悲剧意识》《李锐小说中的悲剧意蕴》《试论李锐小说的三种悲剧形态》等四篇文章,当你放在一起看时,就会发现这几篇文章的论述实际上是大同小异的,不外乎历史悲剧、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等这几个层面。李锐是一个擅长写悲剧的作家,越是擅长写悲剧,其对悲剧的理解也应该更为多样和富于自己的见解,不可能是几个宽泛的悲剧类型就可以概括所有的,这样就会造成削弱李锐创作意义的可能。这种现象在李锐主题意义的探索中并不是个例,又以对其作品中对人的生存、生活的观照的解读为例,就有《生存困境的无尽歌哭——论李锐小说中的叙事主题》《生命困境的执着追问——李锐小说研究》《试论李锐小说对人类存在困境的追问》《试论李锐小说对人类生存困境的逼视》《宿命与荒诞的生存——试论李锐小说对人类存在困境的追问》等几篇文章,翻来覆去的内容都是大同小异的。越是从大的视点着手,重复论述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仅就生命、生存困境这一点对李锐的作品进行解读,还是有很多细节可以挖掘的,比如对女性生存的描写,对人的生存所抱有的态度在不同的作品中的表现是否不同、区别在哪里,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点,可是基本上没有评论家愿意花这样的慢功夫来挖掘。事实上,李锐创作的全部精华就在于对其细节的处理上和别的作家有很大不同。当然,也有很多很好的评价存在,比如蒋银芬的《李锐小说中的三晋文化影迹》就是很好的说明,站在李锐作为具有地域特性的写作视角上看,才会有更具有阐释性的意义,而不是人云亦云。
三、整体性综合分析和比较分析
对李锐的整体性综合分析相对于贯穿性单方面的评介还是较为薄弱的,毕竟李锐作为一位正值创作高峰,而且创作数量非常大的作家,想要对其做一种“一劳永逸”的定论还是为时太早。但是,也正是因为如此,对李锐的现有创作做一种整体性的把握和探究也是十分必要的。
对李锐的创作进行整体性评价最早的是1987年李国涛发表的《李锐的气质和艺术》,他说他不想谈论李锐某些作品的优劣,只是想谈论李锐的个性和气质追求,他认为李锐在“天真”和“冷峻”这两个方面同时发展、互相交织,“天真,在赤子之情意义上的天真;冷峻,在深刻理解历史和现实的意义上的冷峻。而且天真之中可以有深刻,冷峻之中也可以有温情”。在李锐的创作还不是特别丰富的1987年,李国涛不去讨论作品,而是致力于挖掘李锐叙事和表达的气质,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折中的积极办法。从这个侧面对李锐进行的整体性解读,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对某个在发展、成熟过程中的作家进行任何定论都是不合时宜的。
90年代,对李锐进行整体性评价的主要有两位作家,而且都是对李锐相当熟悉、有所追随的评论家:成一和周政保。成一于1993年发表了《不是选择——李锐印象》,实际上这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整体性评价,只是成一选择了1993年这个时间节点对李锐在这一年的创作和活动进行了介绍和生发,但作为李锐好友的成一还是在点滴间侵入了李锐个人创作的风格和理念,越是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东西,在表现作家的时候越有真实的价值,或许成一的初衷就是这样的。另一篇文章是周政保于1998年发表的《白马就是白马……——关于小说家李锐》,这篇文章主要着眼于“李锐之所以成为李锐”这一点,就其所独有的风格进行了论述,在某些层面弥补了在贯穿性单方面研究中对李锐“成因”的忽视。
进入20世纪,随着李锐创作的逐渐丰富,评论家的“野心”也开始膨胀,希望可以做出更为全方位和多角度的整体性评价,于是,在第一个十年,就出现了多篇在总体性上谈论李锐创作的文章。比如曾和李锐有过对话,并出版过《李锐、王尧对话录》的著名评论家王尧把他发表于2004年第一期《文学评论》上的文章直接命名为《李锐论》,足见作者的雄心,其主要论述了两个方面:一个是李锐眼中的“本土中国”;另一个是李锐的汉语写作或者说语言焦虑。这是篇论述详尽、深刻的文章,指出了许多具有现代性的问题,以及李锐所做的启蒙性的追问,从这些方面来说是不错的,当然,无论如何,也只是在某几个层面上实现了对李锐的论述,而非完整的评价。值得注意的是,李锐的夫人蒋韵在2006年曾发表了一篇名为《我眼中的李锐》的文章,这篇文章可以说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她对他的关注是心灵深处的,对李锐的柔弱与坚强、写作的缘由、李锐的个性与气质等都做了一个很好的说明,给评论家提供了非常好的辅助资源。李彦文的《不是之是——李锐小说研究》从三个大的层面对李锐的小说进行了解读:乡土中国的双向煎熬,民间、知识分子与主流意识形态,历史回溯中的悲伤意识,大体上概括出了李锐研究过程中的主要方向,而且做了一些更深的阐述。
和整体性的分析相比,比较分析的文章也不是很多,在一个大的语境下想要确定作家李锐的位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毕竟单是维度的划分就会有问题,但认真的评论家们还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探索。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早的梅惠兰发表于1992年的《凝冻的厚土与跃动的大地——李锐与李佩甫创作比较》:“山西有个李锐,河南有个李佩甫,这二李好像憋足了劲儿比赛似的,一个写高原厚土,一个写中原大地……李锐更多地感触了历史在现实中的浓缩、凝聚与积淀,李佩甫则敏感于现实对历史的偏离、背叛与抛弃。”从乡土中国的表现这个层面进行了比较论述,突出了李锐对待历史和现实的态度。另一篇比较有特色的文章是施学云2004年写的《沉寂与骚动——试比较鲁迅、李锐的乡村书写》,将鲁迅和李锐的乡土文学进行了比较,指出鲁迅、李锐的乡村叙述文本在乡村生命形式的书写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并且各自的书写都有某种程度上缺失,笔者通过比较发现原因存在于文本产生的时代文化背景、作家各自的独特的生活经历及其思想指归等方面,而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两位作家启蒙观的差异。梁鸿所写的《当代文学视野中的“村庄”困境——从阎连科、莫言、李锐小说的地理世界谈起》这篇文章角度也非常新颖,从当代作家群中选择了“乡村书写”这个角度,对他们进行了比较,他概括指出阎连科的耙耧山脉——封闭与对立,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语言的盛宴与感官世界,李锐的吕梁山脉——口语与独白,每个“文学地理”都自成体系,显示了作家对所熟知的地理环境所倾注的心血。在更大的视野内进行比较的有《东西方男子汉的文化意蕴——李锐〈好汉〉和海明威〈老人与海〉的文本比较》和《韩国民众文学与中国底层文学比较研究——以李文求、黄皙暎、赵世熙、李锐、刘庆邦、曹征路小说为中心》,它们都侧重于中西对比的视角,前者说“中国的好汉在经历了莽撞和冲动之后成熟了,重新回到了女人的怀抱,享受着人间的天伦之乐;西方的老人虽说积累了许多的人生经验,但他的经验只是与天地、自然斗争的经验,只是在斗争中获得更大的刺激与乐趣”,这一观点很有意思,对细节的挖掘也很到位;后者则通过将李锐和韩国作家李文求进行比较来研究通过农民形象表现的农村共同体的变化,很有新意。他们的共同点都在于很好地把握住了李锐的创作在当代文学创作格局中的位置,进而以这个“点”进行由“点”到“面”的辐射,在经度和纬度上都可以找到极具创新性的话题,不得不说这种方法对于诸如李锐这样的作家来说是非常合适的,可以有更准确的把握。总之,在对李锐作品的比较研究这一块中国批评家还是做了很大的努力,有很多很有影响的成果。
综上所述,李锐作为一名非常具有地域色彩、不断尝试超越自己的作家,相较于其创作,批评家对他的关注还是远远不够的。如上所述,不管是单篇作品的评介还是整体性的综合评价都存在很多的问题,甚至有些问题还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在一些作品中甚至出现了只有叙述技巧的论述而几乎没有对主题性意义的挖掘的情况。优秀的批评家可以成就伟大的作家,作家需要知心的批评家,李锐也一样。无论怎样,李锐的创作在继续,对他作品的批评也就不应该停止;李锐的创新在继续,批评的脚步理应走得更远。
参考文献:
[1]金汉.短篇艺术的新收获——读李锐的集束小说《厚土》[J].名作欣赏,1987,(05).
[2]韩鲁华.《厚土》透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艺术视觉:读李锐小说《厚土》等三篇[J].小说评论,1987,(06).
[3]罗丽娜.新历史主义语境下李锐《厚土》的美学价值[J].科教导刊,2011,(06).
[4]李彦文.永世为农的文学表达——重读李锐《厚土》系列小说[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06).
[5]王艳云.黄土地上的精神守望——《厚土》的价值取向新论[J].平顶山师专学报,2003,(02).
[6]李国涛译.盐的歌剧[J].当代作家评论,1998,(03).
[7]李洁非.废墟上的铭文——李锐长篇小说《旧址》的主题分析[J].当代作家评论,1993,(04).
[8]李国涛,成一等.一部大小说:关于李锐长篇新著《无风之树》的交谈[J].当代作家评论,1995,(03).
[9]游士慧,吴晓红.叙述就是一切:李锐小说〈无风之树〉的叙事学分析[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12).
[10]王春林.苍凉的生命诗篇:评李锐长篇小说《无风之树》[J].小说评论,1996,(01).
[11]南帆.叙述的秘密——读李锐的长篇小说《万里无云》[J].当代作家评论,1997,(04).
[12]周政保.口语倾诉的方式(或叙述就是一切)——关于李锐的长篇小说《万里无云》[J].南方文坛,1997,(04).
[13]王春林.智性视野中的历史景观——评李锐长篇小说《银城故事》[J].小说评论,2002,(05).
[14]顾明霞.现代性的历史失败与启蒙者的话语悖论[J].当代文坛,2002,(05).
[15]赵晖.寂静之维下的艺术探索——评李锐“农具系列”[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06).
[16]宁二.李锐:以方块字面对文字的消失[J].南风窗,2007,(03).
[17]傅小平.来一次没有遮挡的“正面进攻”[N].文学报,2011-08-01.
[18]李锐,续小强.“煎熬“的历史观:《张马丁的第八天》及其他——作家李锐笔谈[J].名作欣赏,2011,(08).
[19]翟永明.李锐小说的叙事结构分析[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04).
[20]王秀红.浅析李锐小说的叙事视角[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1,(01).
[21]蒋银芬.李锐小说中的三晋文化影迹[D].云南: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22]李国涛.李锐的气质和艺术[J].当代作家评论,1987,(04).
[24][23]成一.不是选择——李锐印象[J].当代作家评论,1994,(03).
[24]周政保.白马就是白马……——关于小说家李锐[J].当代作家评论,1998,(03).
[25]王尧.李锐论[J].文学评论,2004,(01).
[26]蒋韵.我眼中的李锐[J].书屋,2006,(02).
[27]李彦文.不是之是——李锐小说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28]梅惠兰.凝冻的厚土与跃动的大地——李锐与李佩甫创作比较[J].中州学刊,1992,(01).
[29]施学云.沉寂与骚动——试比较鲁迅、李锐的乡村书写[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08).
[30]梁鸿.当代文学视野中的“村庄”困境——从阎连科、莫言、李锐小说的地理世界谈起[J].文艺争鸣,2006,(05).
[31]刘蜀贝.东西方男子汉的文化意蕴——李锐《好汉》和海明威《老人与海》的文本比较[J].名作欣赏,2003,(12).
[32]李胡玉.韩国民众文学与中国底层文学比较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许菲菲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3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