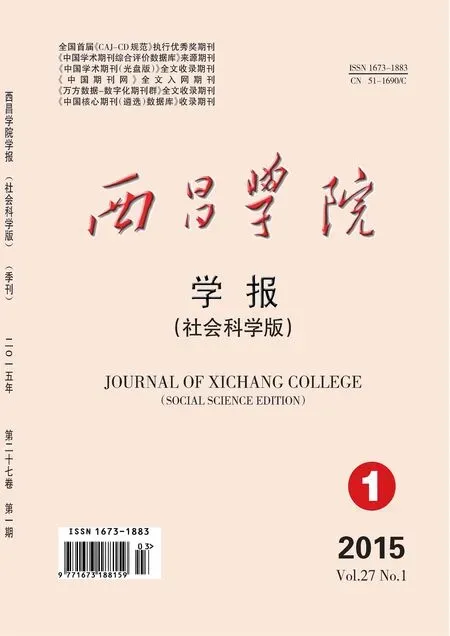《挪威的森林》:此在与彼在迷乱交错的存在意识
2015-02-28王慧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5)01-0039-03
收稿日期:2014-11-13
作者简介:王慧(1980-),女,汉族,河南商丘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审美文化、性别研究。
《挪威的森林》(以下简称《挪》)中那个现代社会被村上春树概括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理想价值缺失,个人主体迷失,随之而来的是存在感的稀释,社会连带意识的分崩离析。人虽在这宇宙间活着,却感觉早已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而其心所向往的,在现实中又无法找寻。《挪》真切地呈现出这种“此在”与“彼在”相互迷乱交错的存在意识,即村上春树所谓“不存在的存在感和存在的不存在感” [1]26,准确地传达了现代人孤独空虚而又绝望挣扎的精神状态,同时也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救赎意识,尝试为陷入生存困境中的人们探索某种可行的生活态度和存在方式,并为我们提供一种哲学思考:怎样突破生命的有限性和不确定性而达到一种无限性和确定性的永恒存在。
一、此在:存在的不存在感
村上春树所谓“存在的不存在感”在《挪》中表现为一种存在感的迷失和对迷失的反抗以及反抗无果而带来的精神痛苦。
绿子称“整个世界就是臭驴粪”,木月和直子就像“无人岛上长大的光屁股孩子”;活泼如春天般小鹿的绿子在家庭和学校两个常住空间被遗弃荒原,大喊“孤独得要命”;永泽表面看来春风得意所向披靡,实质却“在阴暗的泥沼中孤独地挣扎”;而“我”(《挪》的主人公渡边,下同)对现实存在更有着强烈的虚无感,“我”总觉得一切似乎都脱离了现实,甚至“有时会产生莫可名状的感慨,自己居然生活在如此奇妙的行星上”。这准确地传达出现代繁华都市的人们孤独、空虚、无奈、惆怅的存在状态,而这正是村上春树也是众多后现代主义作家共同的创作主线和基调。
人类最大的敌人其实不是别人,而是自己,身处孤独空虚的人们试图用各种方式进行自我拯救。永泽似乎天生就有一种拯救自身的能耐,能把不正常因素全部转化为系统化和合理化,但他在物欲横流中追求的“清心寡欲”不过是一种“模糊淡薄”。木月和直子为了从与社会连带意识的分崩离析中逃脱出来,拼命抓住“我”这根“链条”,试图通过“我”同外部世界连接起来,结果却未能如愿。木月和直子又何尝不是“我”努力寻求美好憧憬的内部世界或说理想世界的“链条”?但是同样“我”的希望也未能如愿以偿。木月和直子显然不属于现实世界,她们只是非现实美好世界洒向现实世界的两颗种子,刚发芽就被扼杀了,根本不能实现“我”通往非现实理想世界的希望。而“我”作为一个现实存在,又有着许多非现实的因素。而且对于现实,“我”不止一次表示,总有一种强烈的不知身在何处的迷失感。
萨特认为存在有两种不能互相还原的存在形式:对意识来说超越的存在和意识本身。其中“对意识来说超越的存在”是一种“自在的存在”,是对笛卡尔所谓“我思”的反思之前的存在,即“反思前的我思”,它不是物质的产物,而是一个虚空、干净、本来就存在着的意识,一个脱离人的意识之外的存在,被一个异于自己的存在支撑着 [2]11-27。《挪》中每个人都试图抓住对方来拯救自己,但他们所试图抓住的,却是这种超越了人的意识本身的存在,强烈模糊而又捉摸不定,最终他们只能在泥淖中挣扎,越陷越深无法自拔。村上春树形象地称之为“存在的不存在感”。
“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带给人们无限丰富的物质和无限可能的高科技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活空间的被挤压和强烈的精神异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主体的迷失、社会连带意识的分崩离析或曰“精神断绝”。在现代日新月异的高科技和完美得近乎无懈可击的强大政治体制面前,作为个体的人类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异化为历史长河中茫然迷失的精神傀儡。人虽活在这宇宙间,却感觉早已不存在于现实中。所以小说最后这样写道:“我现在哪里?我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全然摸不着头脑。”对我们生活的时代和社会,除却虚无和绝望,挥之不去的惟有幻灭和无可奈何的悲凉。
二、彼在:不存在的存在感
《挪》中的女性似乎都具有一种精神慰藉的隐喻。从直子身上“我”能找回现实存在中早已不存在的类似乡愁的温馨。我俩的关系可以说从一开始就相连于生死的边缘,两人几乎成了彼此成为自己足以立足现实存在的坚强理由,承载着对方对未来生活的希翼和对非现实存在的一种憧憬与信仰。特别是初美,她的风度情态激起了“我”强烈的“心灵震颤”,唤醒了“我”自身深层意识中那部分长眠未醒的憧憬:一种类似少年时代的憧憬,一种从来不曾实现而且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憧憬,这是“男儿糅合着田园情结的永恒的青春之梦。”但是这种憧憬和梦幻早已在现实的挤压下被深深潜藏埋没在意识深处,不敢不能不愿提及,以至于被封锁、遗忘,但是人们潜意识中又固执地寻找苦苦地追求。
如果说直子和初美代表人们内心对过去已逝美好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的话,那么绿子则是一位具有浓郁现代气息的女郎,富有挑逗性而又不失纯情,她活在当下并游刃有余地穿梭其中。她们虽性格各异,但在“我”的生活中充当了同一个功能:精神慰藉。
所以当直子病情加重时,“我”脆弱的内心世界犹如蓄意构筑在假想基础上的虚幻之城顷刻间轰然倒塌。直子的死给了“我”致命的打击,“我”几乎不能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孤魂野鬼般漫无目的地游荡,一种更大的空虚无助无所适从感,一种来自宇宙间神秘的宿命式的信息不断笼罩袭击着“我”,“我”已分不清生与死的界限,更找不到自己在现实中的位置。直子的死堵塞了我通往理想世界的探求之路。木月的死“曾把我的一部分拽进死者世界”,让我意识到“死并非生的对立面,死潜伏在我们的生之中”。如今直子的死“又把我的另一部分拖到同一境地”,这让“我”意识到:“无论熟谙怎样的哲理,也无以消除所爱之人的死带来的悲哀……我们惟一能做到的,就是从这片悲哀中挣脱出来,并从中领悟某种哲理。而领悟后的任何哲理,在继之而来的意外悲哀面前,又是那样的软弱无力。” [3]347
林少华在总结村上春树的作品深受读者痴迷的原因“在于他作品的现实性,包括非现实的现实性。”村上春树自己也说他想建构这样一个世界,“现实的是非现实的,非现实的同时又是现实的” [1]22。的确,村上春树作品中的非现实性世界和人物其本质上都具有一种奇妙的现实性,这是一种“特定社会环境中生态的真实和‘感性’的真实”,敏锐而又含蓄地传达出整个社会的时代氛围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倾斜失重的精神世界,从而象征性地、寓言式地揭示了当今时代和社会的本质的真实。
三、阿美廖:精神理想的乌托邦
“我”虽生活在都市,却对大自然寄寓了一种宗教式的深情,苦苦寻觅心目中理想的故乡和精神家园,村上春树说:“我对失去的东西怀有非常强烈的共鸣或者说同情感(Sympathy)。” [1]26这是一种怀旧情绪,同时也是一种对未来的向往。《挪》开篇便呈现一种田园情结:“连日温馨的霏霏细雨,将夏日的尘埃冲洗无余。片片山坡叠青泻翠,抽穗的芒草在十月金风的吹拂下蜿蜒起伏,逶迤的薄云紧贴着仿佛冻僵的湛蓝的天壁”,置身于此,可以“呼吸草的芬芳,感受风的轻柔,谛听鸟的鸣啭” [3]2。这“天人合一”般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活何尝不是一种对理想生活诗意的描绘?
《挪》中最能表达这种诗意生活的恐怕还是“阿美廖”疗养院。在那里,疗养就是生活本身,与外界隔绝,安静,空气新鲜,自给自足,人们互助互爱,同时参加体力劳动,人与人之间可以推心置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再有尔虞我诈,不再有勾心斗角,也不再有冷漠与隔膜。这里,“阿美廖”显然是一个象征,是一个生活在看似正常的社会里的人对真正意义上正常社会的理想,那里的生活的确是一种与大地母亲亲和的最本真意义的生活方式。
但是,在提供这样一个人类理想栖息地的同时,“我”也无情地打破了这种幻想。在“阿美廖”餐厅进食时,“我竟奇异地怀念起人们的嘈杂声来。那笑声,空洞无聊的叫声,哗众取宠的语声,都使我感到亲切。在这奇妙的静寂里,心里缺少一种踏实感。”“我”离开时,“好几次停住脚回头张望,总觉自己似乎来到了引力略有差异的一颗行星,这的确是另外一个世界。”“阿美廖”毕竟是“桃花源”,是试图建立在现实存在的人间仙境。直子的死无情地宣告了它的失败。“我”希求返朴归真的努力和对乌托邦理想的找寻,也化为泡影。
詹明信说:“在后现代主义的崭新空间里,‘距离’(包括‘批评距离’)正是被摒弃的对象。我们浸浴在后现代社会的大染缸里,我们后现代的躯体也失去了空间的坐标,甚至于实际上(理论上更不消说)丧失了维持距离的能力了。” [4]414在这样的社会反抗的彻底性已经成为不可能,只能处于怀着反叛的愿望及彻底反叛的不可能这样一种尴尬位置上,觉醒、抗争、妥协,在失落的状态下复归现实 [5]19。如此,反资本主义社会的乌托邦理想没有了进入到社会实践层面中去的可能性,而只能仅仅作为一种思想存在。“多元主义话语”以表面的宽容实际上却达到了对异己同化的目的。詹明信就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社会“反抗力量都难免被重新吸纳,而一切干预的形式都难免在不知不觉间被解除武装,取消了抗衡的实力。而实际上,反抗形式本身也正好隶属于对反抗形式加以吸纳的体制系统,原因是对抗的形式始终未能于其自身和所对立的体制系统之间建立起一个真正具批评实力的距离。” [4]414于是“我”因失去“批评距离”从而成为一个处于社会边缘化的“边缘人”。
鲁迅先生说过,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清醒之后无路可走。经历了一番精神游历,已经清醒了的“我”返回现实后究竟何去何从?“我”像陷入进退两难的泥沼,滞重而深沉,“只有昏暗的泥沼无边无际地延展开去。”“我”迷失在“此在”与“彼在”相互迷乱交错的存在意识里。对于“我”这样的生命是悲哀的,但对这生命之悲哀又是无能为力的。
四、结语:诗意栖居的可能
然而,村上春树又是独特的。他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对待无奈和孤独的态度——既受其控制,又能超然于外并把玩之。这其实是一种救赎意识。村上春树在《舞!舞!舞!》中这样写到:“跳舞!不停地跳舞!不要考虑为什么跳,不要考虑意义不意义,意义那玩艺儿本来就没有的……不能停住脚步,不管你觉得如何滑稽好笑,也不能半途而废,务必咬紧牙关踩着舞点跳下去。” [6]56不停跳舞而不考虑其意义,这也是《挪》中“我”的选择,我虽然无法判定我位于何处,也不确定自己前进的方向是否正确,但我仍然一步步挪动步履。这里看似无意义的“挪动步履”本身就成为生命追求的意义。关于这一点,村上春树说得很清楚:“任何人在一生当中都在寻找一个宝贵的东西。但能够找到的人并不多。即使幸运地找到了,实际找到的东西却已受到致命的损毁。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继续寻找不止。因为若不这样做,生之意义本身便不复存在。” [7]车票不是总要丢吗?索性让它丢个彻底、丢个痛快,不妨以“无我无心”的境界乘车,即一种对现实不作任何选择的选择态度。这样,“我”就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去尽情享受乘车过程,享受车窗外不断变幻的风景。
这里,村上春树尝试为陷入生存困境中的人们探索某种可行的生活态度和存在方式,并为我们提供一种哲学思考:人生第三种生存的可能性。对现存文化、生活方式和状态消解的同时,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在有限的人生中追求无限,突破生命的有限性和不确定性从而达到一种无限性和确定性的永恒存在。
荷尔德林有句诗:“劬劳功烈,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然而,《挪》中“我”这种活法是否可以称得上是某种意义上的“诗意地栖居”,抑或这本身就是对现实存在的一种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