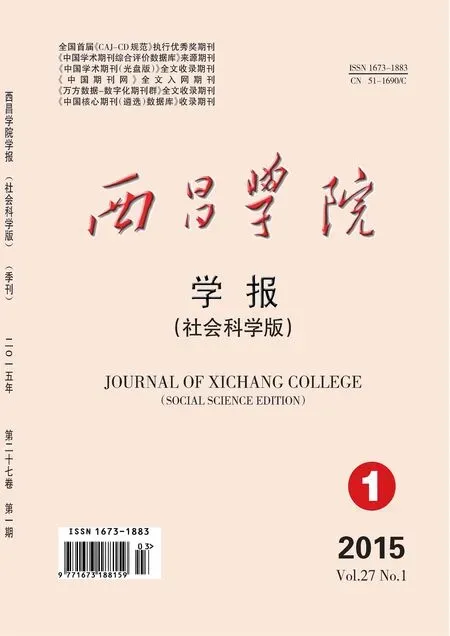略论艾芜与许地山小说中人物的不同
2015-02-28田晓青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5)01-0028-04
收稿日期:2014-12-10
作者简介:田晓青(1989-),女,汉族,山西朔州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艾芜和许地山同属于二三十年代的作家。由于所处的年代一致,在写作的很多方面他们存在着共同点,比如对下层人民的关注和描写。而作为具有个性的作家,他们又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对于艾芜,这个党员作家,不少学者从他的心灵路程来解读他的作品及其思想。而许地山,人们又多注重他作品中表现出的宗教意识,同时,对此产生的意义和作用,学术界褒贬不一,但无论如何都不会动摇其大师的地位。本文从作品中人物这一角度来对两位作家进行比较,浅析他们在写作手法及思想传达方面的不同。
一、作品中人物所处的故事情节不同
(一)普通故事中的平凡者
有人说,在读艾芜的《南行记》时会认为他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写道:“在人们的想象中,讲故事的人就是从远方归来的人,但他们同样喜欢听守在家里,安安分分过日子,了解当地的传说、典故的人讲故事”。整部《南行记》中,作者都是用一种极其朴素的叙述方式来讲一个个故事,没有曲折离奇也并不是为了某种深层次的哲理和意蕴来讲,只是像街头闲话一样复述自己的经历,让别人了解,这样就使人物在不经意间融入读者的生活,并始终保持着故事的那种原生态和作者的亲身经历。对于这个故事中的人物,他的命运有着怎样的遭遇和结局也都成为合情合理的了。就拿“野猫子”(《山峡中》)这个人物来说,她是一位长着“油黑蛋脸的年轻姑娘”,可爱而又可怕,像岩石中的一朵小花,挣扎着在一群凶恶的“盗贼”之中生存,在这样的环境中,她逐渐形成了“野猫子”的性格:泼辣、恶毒但有不失她天性的热情和可爱,它会和男人们调侃,会很熟练地与“我”演戏从而达到偷窃的目的。这样,即使在后面读到她曾参与把受伤的同伴抛入江中也不足为奇,与此同时,她那孩子般的天性也能让我们对她有几分喜爱。老头子是人们敬重而害怕的对象,而“野猫子”却是不怕他的。文中这样描写:“女儿却不怕爸爸的,就把木人儿的蓝色小光头伸向短短的络腮胡上,顽皮地乱闯着,一面呶起嘴巴,娇声娇气地说:‘抱、嗯、抱,一定要抱!’”当老头子假装不要的时候,她仍然“不依不饶”,最后老头只能屈服。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纯真、可爱的女孩,她像所有女孩儿一样在父亲面前撒娇。
(二)曲折情节里的苦命人
许地山小说中的人物却不是这样平凡地“生存”,他们所在的故事往往是曲折离奇的,特别是那些带有爱情线索的作品,如《命命鸟》中的加陵与敏明、《商人妇》中的林荫乔和惜官、《缀网劳蛛》中的长孙可望与尚洁、《换巢鸾凤》中的和鸾与祖凤、《枯杨生花》中的云姑与日晖乃至《黄昏后》中的关怀与其之妻,这些人物的经历都相当波折,就拿《缀网劳蛛》来说,尚洁和长孙可望的悲欢离合可谓曲折多变:逃离婆家的童养媳尚洁与曾帮助过她但没有爱情的长孙可望结合,在一次巧遇中,尚洁因出于慈善之心搭救受伤的盗贼,遭到丈夫的嫉妒而被刺伤,丈夫要与她离婚,她一个人呆到士华岛,不久,丈夫在牧师的启迪下接尚洁回家,可自己为了赎罪忏悔,只身一人去了海岛受苦受难。一对夫妻几番波折,有平静有吵闹,使整个故事曲折迂回也耐人寻味。
同样是写底层人民,在不同的情节故事中让这些人物给读者以不同的感受:周四嫂的悲剧(《一个女人的悲剧》)、陈酉生的无奈(《乡愁》)、“野猫子”的让人又憎又恨,在那些朴素的故事中让人觉得亲切,而命运多舛的惜官和尚洁不仅让读者感受到这个人物存在的悲剧,也使整个故事跌宕起伏、富有传奇性。
二、人物的塑造方式不同
(一)艾芜小说中人物的塑造方式
1.富有个性的语言描写
艾芜在塑造人物性格时总习惯让人物用自己的语言去体现自己的特点,而很少用心理描写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去表现。不同的人物即使说同样的话语时,他的语气、语调也是不同的,艾芜就把这种区别运用在人物塑造上,并且成为他的一个写作特色。
《我的旅伴》中,老朱、老何是两位热心而又幽默的伙伴,他们在一起扫除了“我”旅途的寂寞,这在很大程度上由他们的谈话排遣掉的,其中有这样一段:
老朱呵斥地说:
“那还不如回你贵州老家去变猪,跑来这里做个啥?”
老何笑着说:
“可惜就因为不是猪呀!一个人喜欢到处跑跑跳跳,喜欢到处看看稀奇,喜欢能够自由自在的过日子,呵,一个人喜欢的多着哩!”于是老何又向我说道:“我就喜欢在外国地方,不管你推车也好,抬滑竿也好,没有哪个舅子笑你!也没用哪个老表耻你!你在路上,再也碰不着你的亲戚,再也看不见你的本家。你走你的,用不着脸红。要是你肯吹牛,你请人写封信回去,说你在外国做皇帝,都准有人信进去。”
这说得老朱笑起来了,嘲弄他道:
“好好好,你就写信回说你在外国地方做滑竿皇帝好了。”
这样的一段对话把人物乐观幽默的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
2.由表及里的表现方式
艾芜在描写人物时常常采用的表现方式是由表及里。在《端阳节》中,开篇第一段就出现了下山的太阳、蓬生着杂草的无数坟头和那天上飞着的燕子、蝙蝠。随后一个人物——老三出现,他“把脱下来卷着做枕头的破衣,抖开来,披在身上,一壁将睡在另一块石碑上的伙伴,用足踢着。”展现出两个人互相逗笑的场景,并引出了一个隐喻的意象“鬼”。他们两个人的打闹吓着了孩子,又把做了亏心事儿的张大爷吓得“魂儿都飞了”,而且在紧张中提及了到最后也不知道原因的事件,那就是杨先生的死。第二天,人们如往常一样搭台唱戏过端阳,扮成的韩林在人群中显得十分威武,而在按照当地风俗追杀韩林时,张大爷却也“光着头赤着足尾着跑来”,两个人成为一伙一起跑,老三一面拖着他跑一面有趣地笑着。后面吼着千百个声音:“围着,围着不要放他走哪!”“牛在田埂上乱跑,哞哞的叫着。息在树林里的群鸭哇哇的叫着,飞了起来。正月的黄昏,不安静了。”扮鬼的老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的躁动。这样的结局已经把老三嬉笑怒骂下隐藏的乐观显现出来,这是何其的亲切,相比之下人们内心的思想是何其的落后。
(二)许地山小说中人物的塑造方式
许地山在创作时,对于人物的塑造通常习惯通过人物自己内心的情感波澜和行动把其性格显现给读者并波动他们的心弦。《春桃》是标志着许地山走上切实沉着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一部作品。它刻画了一个在挫折不断的人生中坚强、勇敢地做自己主人的女性形象——春桃。当动荡的生活中出现了两个男人——李茂和向高时,这位再也平凡不过的妇女做出了很不平凡的抉择,她抛掉世俗的观念,和两个男人共同面对生活中不断袭来的恶浪。最终,她以自己坚强的意志感动了他们也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在这里,春桃的语言并没有多少独特的个性,但是她的内心情感世界却让我们觉得她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子。她信奉自己的真理,并且更值得可赞的是,她将这真理付诸实践。当李茂让她把自己送走时,她果断地制止了他,并且把因无法面对这件事的向高找回来,在两个男人的面前,她内心的强大已经掩盖了她外表的娇小。而这两个男人,他们的情感波澜不仅表现出他们自己那种朴实的情愫,而且更加衬托出春桃果敢、坚强的性格。李茂后悔打破妻子和向高的幸福生活,在内心里即使有一万个不情愿,也想表现出一个男人的“义气”,他写休书、烧结婚的龙凤贴、最后上吊,想要把那份平静归还给他们。向高虽然在和春桃相处的这段日子里已经离不开她了,但只因“没拜过天地,没喝过交杯酒,不算两口子”,也想成全他们这对苦命夫妻。而春桃既不想做无情无义之人甩掉残疾的丈夫,又不想舍弃这份患难之情,三个人的感情复杂交错,在矛盾中翻滚着。这种人物关系的复杂和内心世界的纠葛以及人物的行动元素让我们对人物性格的把握更加鲜明、准确。
三、人物的精神状态和人生观
(一)艾芜作品中人物的至纯至真和乐观助人
1.至纯至真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说到人物的“原生态”,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与艾芜的南国世界可以称得上是两个代表。在沈从文的作品中,自然景色秀丽,人们淳朴善良,没有争斗,都是以一种宽厚、仁爱之心待人,读他的作品会让读者置身于理想的桃花源。与沈从文这种清静,纯美的梦幻世界不同的是,艾芜笔下的人物展示给读者的是一种原始的张力,他们粗暴、强悍,总是桀骜不驯,比如有这样一段描写:店老板不待回答,就把刚提起的斧头,连忙放下,向我冷笑道:“不要你的烂包袱?要是要烂包袱就好了!”“店老板却不说下去了,朝手板心里吐一点唾沫,重复捏紧板斧,劈柴起来,嘴里只冷嘲似得这么说了一句;‘还是让他自家试试去吧’。”(《荒山上》)这样看上去粗野、蛮悍的人物形象在艾芜的作品中比比皆是,无论是《山峡中》的“野猫子”、《松岭上》的老货郎,还是《私烟贩子》里的老陈头,亦或《森林中》的马哥头,他们身上都有这种原生态、回归自然的艺术魅力。
2.乐观助人
《我的旅伴》中,“我”在向泰国女人卖酒的过程中结识了两个抬滑竿子的人——老何和老朱,这两个人成为“我”旅途中的伴侣。他们靠脚力吃饭,辗转在山间的各个地区,本不景气的生活在他们的眼中却是自由逍遥的,他们一路上打打闹闹,斗嘴聊天,让无聊的旅途充满了欢笑和轻松。这种对待生活的乐观态度感染了“我”,也能够感染读者。这样的乐观态度在“野猫子”、胡三爸(《快活的人》)等人身上也存在。在当时的文坛,被用作题材的有被资本家压榨的工人、有被地主剥削的农民,他们都处在被同情的一列,但他们却或是胆怯或是冷漠,而艾芜笔下的主人公却很热情,总愿意帮助那些在苦难中的人们,即使他们一样贫穷。《森林中》的马哥头就是这样一位热心的人,他在半路上救过一个因财产被抢而自杀的商人,虽然这个人在关键时候会想着出卖他,但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想过要丢下他,而且为了让他继续活下去还把有限的口粮分给他。这样的人在艾芜的小说中构成了一个“热情的流浪汉”系列。
(二)许地山作品中人物的宗教情结和消极避世
1.宗教情结
谈到许地山的作品,给人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是浓郁的宗教气息。像小说中出现的:法论学校、晚祷、礼拜、乞食、涅槃、讲经说法、极乐寺等意象,都使其小说流溢出某种宗教的气息,除了这些实实在在的存在物以外,鲜活的人物身上更带有这种意味。作品中一些人物的命名便是这样:定慧(《给诵幼》)、迷生(《给小峦》)、了因(《答劳云》)、少觉(《覆少觉》)等等。其次在人物的身上也总是弥漫着这种气息:敏明和加陵以情死为超度,尚洁以宗教精神对待生活中的不幸以及惜官的乐天知命也是这样。这与许地山自己的宗教情结分不开,他的一生与佛教和基督教的渊源甚深,这很自然地为他的人物涂上了宗教的色彩。《商人妇》中的惜官很早就嫁给了林荫乔为妻,林好赌,欠下很多债,惜官变卖家产送他到南洋。几年后,她经过千辛万苦到南洋找丈夫,不曾想林已经娶她人为妻,自己还被卖给印度商人为妾,之后受尽折磨,到最后她便认为“人间”一切的事情本来就没有什么苦乐的区别,你造作时是苦,希望时是乐;临事时是苦,回想时是乐……”这种苦乐不别的信念自慰亦以慰人,既有消极又有刚毅,但无论什么都是释迦和基督的幽灵在徘徊。
2.消极避世
在宗教的影响下,人物不免有些消极厌世的态度,这同艾芜笔下那些大胆、粗鲁的形象完全不同。就拿《命命鸟》来说,一对正处于风华正茂的恋人,享受着人间最美好的爱情,但在遇到家庭反对时,最后双双携手投湖自尽,看似他们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了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满,实则是他们以消极的态度断送了自己可能会有的幸福生活。其他人物虽然没有选择放弃生命,但也没有反抗只是屈服。尚洁就是这样:她在生活上“无论什么事情上头都用一种宗教底精神去安排”,外面的人说她是不正经的女人,她毫不在意,当她被丈夫刺伤时只是用宗教的理论安慰自己。在她的内心里可能认为那些教条可以抵挡一切,但生活带给她的仍然是不断的伤害。其实无论信奉宗教与否,人生都是充满了曲折和磨难的,面对这些困苦,轻易放弃的不是信仰所致,而是我们的人生抉择。
四、结语
作为一位小说家,总会伴随着这样的两个问题:你代表哪一群人在写(你为谁而写)?你以怎样的身份在写?而作为一篇甚至一部小说而言,它不仅要有文学价值还要有它的社会价值,只有两者皆获,才可称为好小说。对于这两位作家,无疑是站在人民的立场写作,那么他们作品的文学价值呢?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否则也不会编入史册。艾芜作为一个左翼作家,其身份就表明他作品的鲜明倾向——鼓舞人民,再加上他的笔名——“艾芜”与“爱吾”谐音,更能说明这一点,而且从那些乐观向上的人物身上也深有其感。那么对于许地山这位颇受争议的作家来说,其作品中的宗教意识到底是积极还是消极,还需要我们客观对待,而对他的贡献也不能因片面的观点而否认,我们应该站在特定的背景环境下,从不同的角度去评价、探讨。